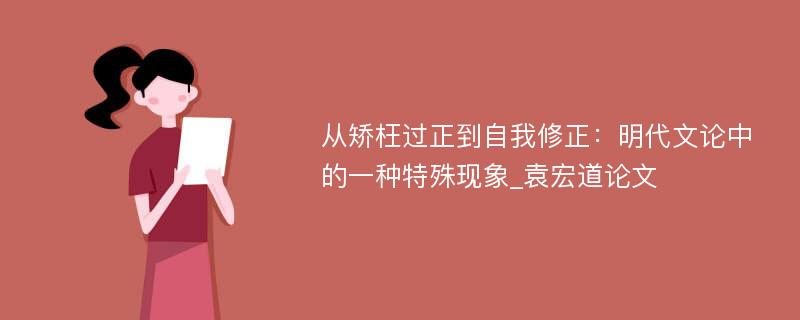
从矫枉过正到自我修正——明代文论中的一个特异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矫枉过正论文,文论论文,明代论文,现象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明代重要文论家都有从矫枉过正到自我修正的理论转变,这一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 明代文论 前后七子 复古 反复古 公安派 竟陵派 唐宋派
明代诗文创作,就其整体来说,成就不及唐宋两代,但诗文理论却开始步入了总结时期,其论争之激烈也是空前的。文坛因此而出现门户林立、派别众多的复杂局面。他们既不像前代各学派那样相互间无明显的关联,亦有异于清代桐城派独霸文坛200余年的状况,围绕着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彼此或讥讽攻讦,或声应气求,“你方唱罢我登场”,显露出清晰的因果联系和承传关系。
明代的文论家,因其对复古问题的态度不同而分列于三大阵营。复古阵营的开创者为宋濂、高启、方孝孺、林鸿、高棅、李东阳等人,到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时,复古恶习臭气熏天,严重窒息着明代文坛。于是,属于反复古阵营的公安三袁奋起反抗,其推陷廓清之功显著。嗣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继续高举反复古大旗,却在反复古斗争中误入了幽深孤峭的迷途。存在于复古与反复古两大阵营之间,又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折中派阵营——唐宋派。唐宋派传统古文理论的衣钵,到明末由艾南英、钱谦益和黄宗羲等人继承了。同时,论争中一度败下阵来的复古派的余烬,又被明末的陈子龙复燃,不过如同死亡前的回光返照,瞬间的光亮之后,便没了生机。
用运动的观点看,如果把有明一代有关诗文理论的论争进展比喻成一条激荡澎湃、浊浪排空的大河,那么,再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考察,便不难发现,这条大河的每一河段下层都潜伏着暗流,正是这些暗流的不停回旋与冲击,推动着上层主流的流动,调节着主流的方向与速度。这些暗流,就是明代许多重要的诗文理论家早年的矫枉过正和晚年的自我修正。
一
先看矫枉过正。
李梦阳论诗主张复古,其精神实质是主张学习古人诗作中最优秀的东西,然而,沿着这个思路却因严格了时代界限而走向极端:“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汉无骚哉!’山人于是则究心骚赋于唐汉之上。”(1)“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2)“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宋无文”的结论,确为不尽科学的矫枉过正之言。其论文主张师法秦汉,认为学古是必经之路,又不恰当地将学习古法与临帖相比较:“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3)认为文学创作就像写字临帖一样,是明显地违背文学自身的规律,何其荒谬!
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溺于陶,谢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亡于谢。”他菲薄谢灵运和韩愈,以为诗文古法自兹而亡,亦为过当之言。钱谦益曾就此批评说:“昌黎佐佑六经,振起八代,文亡于韩,有何援据?”(4)批评切中肯綮。
关于李攀龙文学见解与创作的偏颇之处,王世贞《艺苑卮言》已经指出过:“李于麟(攀龙)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袁宗道则指出李攀龙另一过当之言:“沧溟(李攀龙)赠王(世贞)序谓:‘视古修辞,宁失诸理。’”(5)文宗秦汉,却要求只作秦汉语;重视古文法,却宁可“失诸理”,这都有失偏颇。
王世贞较之李攀龙,可谓才高誉隆,然亦有授人以口实的矫诬轻毁之辞。论诗,他虽有“捃摭宜博”(6)的大家胸怀,但又不免在“师匠宜高”(7)观念下说出“贞元而后,方足覆瓿”(8)这样的话。论文,也在同样的取法乎上的理论指导下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9)东汉文不如西汉,而六朝文又不如东汉,再往下,唐文不如六朝文,而宋文又不及唐文,最后干脆说“元无文”,持论何其偏激也。此外,袁宗道《论文》在谈及李攀龙“强赖古人无理”时,也指出王世贞“不许今人有理”:“其赠李序曰:‘六经固理薮已尽,不复措语矣。’”而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王世贞主张作品的一字一句都要力肖古人,要学用古官制、古地名。他认为,即使司马迁再生也难再写成《史记》,因为“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书赋颂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10)此论一出,于是一些复古派作者专事模仿古语古字,以致复古派文章越写越艰涩古奥,诘屈聱牙。
这种现象,在反复古派中也同样存在,所不同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最能显示反复古派对复古派冲击与涤荡的是袁宏道。袁宏道“信出手腕,独抒性灵”的主张,既是对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革新精神的继承,又是当时公安派反复古的战斗宣言,其正确性与先进性自不待言。但其矫枉过正的严重性亦是不容回避的。从“人情必有所寄”(11)出发,袁宏道偏激地认为“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12),并进而倡言“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13),这样便公然割裂了历史,完全否认了对优秀遗产的继承。唯其如此,“宁今宁俗”(14),从倡新滑入了倡俗的歧途。袁宏道的反复古理论,反映在文学发展观上,针对复古派的衰退论,提出了“一代盛一代”(15),这虽是矫复古派之弊,但也难免过当了,因为文学发展的状态纷纭复杂,决非简单的衰退论或进步论所能概括的。“变”是袁宏道革新思想的灵魂,但他的“变”又陷入了机械论,把当时的八股文也作为新事物加以肯定:“以后观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16)说八股文“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17)。袁宏道论诗文主真,但又过分强调作家的个性,从而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其《显灵宫》诗“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虽是有感于朝事日非而发,但如此论诗确是有意否定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了击垮论敌,针对复古派尊重老杜、轻视东坡,袁宏道特别地扬苏抑杜,说“其(苏轼)才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李白、杜甫)之上,故宜卓绝千古”(18)。另外,针对复古派尊重当代的李、何,袁宏道又偏偏来恭维当代的徐渭,说他“诗文崛起一代,一扫近代芜秽之习”(19)。这都有失过当。袁宏道的这种偏激之辞在《与张幼于书》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家。’”
继公安派而起的同属于反复古阵营的竟陵派,力矫公安三袁的浅率与俚俗,希求另辟蹊径,但又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狭僻的道路。他们论诗主张“幽情单绪”(20),刻意于“孤怀孤诣”(21);论文则“喜拈其不著名而最少者”,以为“有一种别趣奇理,不堕作家气”(22)。旨在标新立异,要说前人所未说的话,要写前人所未发现的情与景。钟惺在《与谭友夏信》中甚至说:“我辈诗文到深无烟火处,便是机锋。”既主幽深,便不能不离却世情,因幽而至于冷僻,因深而至于晦涩,大有从元、白而变为郊、岛之势,谭元春不就明确推崇孟郊诗“貌险而其神坦,志栗而其气泽”(23)吗?可见,东野一派早已成为竟陵派的宗师了。
复古派与反复古派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那么是否可以说,作为折中派的唐宋派因其折中而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唐宋派的文学理论是在矫正七子派拟古不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也同样存在着过正的现象。前七子反宋儒,王慎中则说:“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24)有意将宋儒之书与圣贤经传并列。到唐顺之则发展为有意标举迂腐俗滥的宋理学家邵雍:“三代以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25)在《读东坡诗戏作》中,唐顺之又说苏诗能够“扫除李杜刍狗语”,不惜以“刍狗语”轻贱李杜,来抬高苏诗的地位。唐宋派中反复古最力者当为归有光。归有光在驳斥王世贞等人文宗秦汉时,却说:“文章在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26)而元文实在担当不起如此过誉之辞。
二
上面概述了这些作家诗文理论中所存在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但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情况是,他们的思想到了晚年又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变。
李梦阳早年尺尺寸寸于古人,到了晚年终于认识到自己规行矩步、模拟古人的诗歌并无价值。他总结自己和一般文人诗的特点是“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27),转过来承认他的朋友王叔武“真诗乃在民间”的意见,悔恨地说:“予之诗,非真也。……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28)由于开始意识到真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意义,李梦阳便不再恪遵《诗大序》里关于诗歌的那套理论,反过来盛赞《西厢记》和表现男女情爱的民间诗歌。“空同子称董子崔张剧当直继《离骚》。”(29)“空同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30)将《西厢记》的地位提高到与《离骚》同等,主张诗文都要向《锁南枝》学习,足见李梦阳已经从一味主张剽窃拟古转向了主张抒写性情。
何景明的转变较之李梦阳还要早些。当初,李、何俱为复古派的中坚,共倡“诗必盛唐”,但不久,何景明对盛唐诗,特别是李、杜诗有新的看法,认为“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而古作尚有离去者,犹未尽可法之也”(31)。到后来,对于杜甫诗歌就直接提出了批评:“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32)批评杜甫诗不近人情。此外,何景明以“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33)来反对李梦阳早期的“刻意古范,铸形宿镆”(34),以求“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35)。这不正说明他努力从拟古的泥潭中走出吗?
王世贞“晚年定论”,早已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他晚年悟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36),并意识到文艺的某些特征,如“五色错综,乃成华彩”、“经纬就绪,乃成条理”(37),注意到诗的意境:“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38)对李攀龙诗的摹仿剿袭开始表示不满:“于麟节奏上下,聱师之按乐,亡勿谐者,其自得微少。优孟之为孙叔敖,不如其自为优孟也。”(39)论乐府,他极称李东阳“奇旨创造,名语迭出,纵未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40)。对归有光行云流水般的文风也十分赏识。相形之下,他对自己追悔不已:“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41)他早年力排苏轼,而晚年病重卧床时,却于苏轼集子手不释卷。
唐宋派中晚年转变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唐顺之身上。由其神气之说发展而下,晚年的唐顺之一变其工于文字技巧而追求“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42),力主“真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43)。在《与洪方州书》中,他也说过:“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熔,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的字句。”不再取法唐宋,唯求直抒胸臆,堪为公安文论的嚆矢。
在反复古斗争中,袁宏道堪称一员主将。然而,这位主将到了晚年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时,忏悔意识却与日俱增。首先是思想发生了变化,“觉龙湖(李贽)等所见,尚欠稳实”,“遗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44)。世界观的转变,必然引起审美思想的转变:“诗文之工,决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为近道也。”(45)这是对自己早年所倡导的“信出手腕”的公开否定。在《哭江进之序》中又道:“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然余所病,正与进之同症。”对自己早年一味追求的“新切”表示了悔悟。同时,他大谈中和之道:“喜不溢,怒不迁,乐不淫,哀不伤,和之道也。”(46)早年那奔走疾呼、摇旗呐喊的气象已不见了踪影。与之相适应,其“性灵说”也有了不同的内涵:“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47)以“淡”作性灵说的内涵,与早年所高倡的“真率”相去已远。沿着这个方向转变下去,最后袁宏道终于走向了保守。“学以年变,笔随岁老,故自《破砚》以后,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生动,无一篇不警策。”(48)这是小修对中郎晚年的评定。
袁中道早年跟着兄长习作抒发性灵之作,中年后逐渐看到了公安末流片面强调性灵而抛弃必要的“法”的流弊,转向主张“情”与“法”相结合,“以意役法,而文之精光始出”(49)。鉴于公安末流在内容上倾心风花雪月,在形式上有失粗滥,他提出了忠告:“毋舍法,毋役法为奇,毋徒嘲咏花雪、作不磊落事可也。”(50)
三
明代文论出现早年的矫枉过正和晚年的自我修正的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其中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具体的原因。
以共同原因而言,矫枉过正主要导源于意气用事,而之所以会意气用事,又是由下述一些因素决定的。首先,明代文人重师承,其喜结社、爱标榜的癖好,较之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显得突出。从前后七子、公安三袁到东林党、复社、几社,不论规模大小,历时长短,或为文学研究,或为政治斗争,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和共同的志趣。《明史》载,李攀龙倡诗社,有所谓“五子”、“七子”入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行状》云,宏道“年方十五六,即结文社于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如此结社,在标榜自己的同时,势必树立众矢之的,结果一哄而起,其矫枉过正也就在所难免了。其次,一般文人思想的矜持与思维的惰性,也是矫枉过正产生的诱因。处于封建末世的明代文人往往不易接受不同的意见,要想冲破论敌的惰性防线,论者往往从斗争策略出发,有意矫枉过正,认为非过正不足以矫枉,以期收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此外,中国封建文化季世的历史沉积,孕育了明代许多文人的小家子气,他们失却了汉唐士人的虚怀大度与磊落光明,却承袭了宋元一些文人在民族矛盾中养成的狭隘与固执的畸形心态。他们持见易于偏颇,言论流于谩骂。此风自七子始,而大播于文学批评中。前后七子之诋諆时人,及其相互诋諆,自不用说。徐渭将复古派之诗骂为“鸟言”(51),袁宏道将复古派的创作说成“粪里嚼查,顺口接屁”(52),更是信口雌黄了。受肆意谩骂习气的影响,诗文评论又如何能不矫枉过正呢!再者,矫枉过正也是霸权欲望不断膨胀的结果。明代文坛门户林立、流派层出,这就不免有人要争夺文坛的霸主地位。这些争霸,有的是在门户、流派之间进行的,有的却是发生在门户、流派的内部。李梦阳之反对李东阳、公安三袁之反对王世贞,都属于前者,其争霸的迹象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何景明之反对李梦阳,则属于后者,其争霸意识在言论中虽未表明,但我们可以从其实际言行中窥见一斑。《明史》何景明传载,李、何二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两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争霸一起,便易于意气用事,便会矫枉过正。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矫枉过正现象的出现,也与部分文人借指摘名人来张扬自身的主张有关。汤显祖曾在南京公开标涂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文赋,大出七子之丑,已肇其端。后钟惺、谭元春急功近利,不恤趋旁蹊曲径以有别于七子与公安。结果,钟、谭一家之言既立,而矫枉业已过正。
如果说早年的矫枉过正是明代文坛激烈论争的副产品,那么晚年的自我修正便是众多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辛苦探索所修来的正果。转变在晚年发生,与作家生活阅历的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钱谦益说王世贞“少年盛气……门户既立,声价复重,譬之登峻阪,骑危墙,虽欲自下,势不能也。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消歇,浮华解驳,于是乎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53)。评定十分公允。王世贞晚年的转变和阅历相关,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此其一。其二,晚年改正也反映了一条重要的文学规律,即文学批评虽然可以百家争鸣,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应该说,明代文坛各家各派的文学理论,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合理成分,在反复的论争中,合理的东西终会被人们所承认,而不合理的东西也终将为人们所遗弃。这就意味着对别人正确观点的虚心接受与对自己的错误观点的大胆舍弃。就某一派系、某一具体作家来讲,在论争中,其理论的正负因素不断消长,始终处于流动状态。而消长的结果,必然使负面渐渐转向正面,从而不断接近真理。当然,转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对本派流弊的深切不满。一种文学主张在提出的时候,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其中的合理成分也较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流弊渐出。这时,不但会引起别派文人的强烈攻击,而且也必将唤起本派文人的觉醒,促使其转变与改正。如同属于复古派的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因有感于“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薄弃晚唐,自诩初盛,有称大历而下,便赧赧然”(54)的盲从学风,开始认识到复古末流刚刚学诗便大谈格调的流弊,并由认识上的转变进而提出严肃的批评:“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55)
这种独特的现象之所以集中出现在明代文论中,除了上述的这些共同的原因外,结合具体作家来说,又有各自具体的原因。
李梦阳矫枉过正有两个文学上的具体诱因。其一是源于对陈献章以理入论的强烈不满。陈献章论诗主“宗程(颢)崇邵(雍)”,尤其强调以邵雍的《伊川击壤集》为宗法对象,其诗溺于理学,丧失真趣。李梦阳对此极为愤慨:“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56)由反对陈献章,从而直接反对宋儒宋诗,从而崇唐诗,从而大倡复古,从而言之过正。其二是源于对李东阳茶陵派诗歌创作的不满。在矫正台阁体平庸肤廓的诗风方面,李东阳确为七子的先导。但李东阳作为台辅重臣和文坛领袖,却在政治上依偎于刘瑾,在文学上有意无意地排斥文学复古阵容中的新进之士,其拘牵于腐朽的庙堂文化的心态和日趋萎弱的诗文创作,使李梦阳极为不满。于是,李梦阳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大倡古学,希望给日渐式微的明中叶诗文创作注一针强心剂。李梦阳的晚年修正也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受其同龄人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思想的影响。王阳明晚年四处讲学,加之其政治上的影响,其心学在生前就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注目。《明史》本传载,“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心学是主观唯心的,追求表现自我。对心学的关注与接受,是李梦阳晚年论诗主真主情的必要契机。其次,宋元以后,俗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由兴盛走向全面繁荣,其崭新的形式和旺盛的生命力,逐渐引起了文人的重视。在这种大气候下,李梦阳在晚年心气渐平、回头猛省时,自然赞同“真诗乃在民间”之类的主张。
袁宏道矫枉过正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即“左派王学”的恣情放任思想。袁宏道与“左派王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交好。李贽倨傲倔强,任才使气,其疏狂不羁的个性深深影响了袁宏道。于是他认为世人唯有殊癖才是名士,由此论文论诗全任感情,全凭意气。其晚年转变,也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因素需要强调,即源于儒家积极用世、关心现实的思想。关于这点,早在30年代林语堂等人倡导小品文时,鲁迅先生就指出袁宏道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57)。晚年肆意放荡的性格收敛起来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风便引导他开始重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甚至走向偏重于“法”的保守一面。
唐顺之与王阳明弟子王畿有着很深的交往。王畿性格“坦怀任意”,追求“真性流行”(58)。唐顺之十分推崇王畿的学说,《明史》本传载,他“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迎月忘寝,多所自得”。《明儒学案》评道:“唐荆川谓先生笃于自信,不为行迹之防,包荒为大,无净秽之择,故世之议先生者不一而是。夫良知既为知觉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是崖撒手,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老。虽云真性流行,自见天则,而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王畿亦儒亦禅亦老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直接诱发了唐顺之晚年的转变。
总之,明代文论出现矫枉过正与自我修正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封建社会末世文艺理论界躁动不安的心态,展示了他们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不断冲击下,上下求索的艰难历程。同时也警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在考察一代文学史,研究一种文学派别,乃至一个具体作家时,一定要进行动态的辩证的分析,切勿将动态的现象静止化,将相对的问题绝对化。
注释:
(1)李梦阳《潜虬山人记》。
(2)李梦阳《论学》(上)。
(3)李梦阳《再与何氏书》。
(4)(53)钱谦益《列朝诗集》。
(5)袁宗道《论文》(下)。
(6)(7)(8)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
(9)(37)(38)王世贞《艺苑卮言》。
(10)(39)王世贞《与张功甫书》。
(11)袁宏道《锦帆集》。
(12)袁宏道《与潘景升书》。
(13)(52)袁宏道《与张幼于书》。
(14)袁宏道《与冯琢庵师》。
(15)袁宏道《与邱长孺》。
(16)(17)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
(18)袁宏道《梅客生书》。
(19)袁宏道《徐文长传》。
(20)钟惺《诗归序》。
(21)谭元春《诗归序》。
(22)钟惺《诗归选·评王季友诗》。
(23)谭元春《郊寒辨合集》。
(24)王慎中《再与顾未斋书》。
(25)唐顺之《与王遵岩书》。
(26)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
(27)(28)李梦阳《诗集自序》。
(29)徐渭《曲选》。
(30)李开先《词谑》。
(31)何景明《海叟集序》。
(32)何景明《明月篇序》。
(33)(34)(35)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
(36)王世贞《宋诗选序》。
(40)王世贞《书西涯古乐府后》。
(41)王世贞《归太仆赞序》。
(42)(43)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
(44)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
(45)袁宏道《与黄平倩》。
(46)袁宏道《和者乐之所由生》。
(47)袁宏道《过呙氏家绳集》。
(48)(49)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
(50)袁中道《花雪赋引》。
(51)徐渭《叶子肃诗序》。
(54)(55)王世懋《艺圃撷余》。
(56)李梦阳《缶音序》。
(57)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58)王畿《与荆川书》。
标签:袁宏道论文; 李梦阳论文; 唐顺之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王世贞论文; 明史论文; 李攀龙论文; 景明论文; 复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