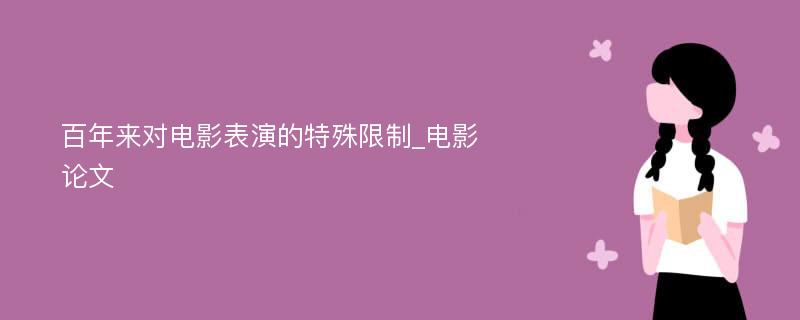
百年桎梏 论特定限制中的电影表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桎梏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电影银幕影像运动构成的创作中,看起来既合情合理,又似乎不太公平的,是电影演员所处的位置,是在特定“限制”中的电影表演。
世界上有众多在各自专业上有突出贡献的著名艺术家,而知名度最高、最受新闻媒介注目、最易成为公众偶像的,恐怕莫过于电影演员了。这是否与观赏者的电影视觉美感,在人的感知能力中特殊敏锐有关呢?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作为电影基本特征的银幕影像运动造型原理,具有强大的视觉张力呢?
在这里,我想借此顺便阐明一个简单而又在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论题。即电影作为后工业化时代诞生的艺术,是一门具有最复杂的创作过程而且极富艺术魅力和社会意义,又最易于被世界各民族、各阶层、最广大的民众所乐于接受的大众艺术。我认为,高尚的电影艺术是具备艺术性和娱乐性、社会思想性和生动形象性高度完美结合的特殊品格的。或者说,电影艺术具备这种包含广阔的思想内涵和高尚情操,与生动的形象和赏心悦目完美结合的巨大可能性,因而最易于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的特征。
然而,翻开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历史,真正创造电影,真正为电影艺术不懈奋斗而功勋卓著的并不是演员。或者说主要的、或者说首先并不是演员。
很遗憾,电影的诞生是科技发展和金融投资为基础的,通俗一点讲,就是“钱”和“机器”。当1895年12月28日由美国人爱迪生与法国人卢米埃尔使这个新生儿呱呱坠地的那个日子起,电影还只是一种新奇的魔术戏法,中国人曾叫它为“西洋镜”。直到本世纪初期,在西方,电影的编、导、演与别的制作者一样,都是听命于出资人的雇员。尽管观众已经十分风靡于此,但它只被看作市井小民的娱乐,有身份的人是决不贸然出入电影院,以免被人发觉,去看不入流的东西而难堪。在这段日子的前前后后,先是科学家和经营者在推进着它,并成为电影真正的始作俑者。而且,电影就是以向观赏者出售门票开始与人们见面并被社会逐渐承认的。此后,才有各种艺术门类的出类拔萃者蜂拥而至,在这个崭新的艺术领地里开拓,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屡有建树,诞生了一些电影史上令人瞩目的著名艺术家、技术专家和经营专家(制片人)。而作为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并进行情感交流的演员,以其特殊的可视形象和鲜明而具有个性的艺术才华,把众多的合作者挡在身后,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兴趣和巨大注意。
电影发展至今,依然是由金融投资、经营决策、技术进步和艺术创新共同支撑着,并在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理论研究的认知活动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进步的一种文化现象。电影演员毫不例外地要在种种“限制”中表演,或者说从事着极其艰难、特殊然而较易成名的艺术劳动。
令人神往以至长年使成千上万少男少女涌向好莱坞的“明星制度”,本身就是对电影表演的一种“限制”,只不过在眩目的竞争中掩盖了这个制度的残酷性。作为美国电影商业化的标志,从一开始就与欧洲较为重视电影导演艺术地位不同。从好莱坞刚形成电影大企业的时候起直到今天,公众首先知道的是男女演员,观众选择自己要看的电影时,几乎还很少考虑导演的名字,演员成了票房的“晴雨表”,电影明星成了电影企业赚钱的法宝。
在早期好莱坞,除了像格里菲斯和塞纳特少数几个有声望的导演之外,电影明星几乎“统治”了电影。在20年代以后一段时期里,“导演”一词曾被用为指监督演员和对剧本进行解释的人。导演成了影片公司制造明星的主其事者,他们的贡献,就在从一个候选人身上发现制片商所要求的有票房号召力的某种类型,发现其成为这种类型偶像所特有的视觉魅力。摄影师也要在摄影技巧上借助于光影色彩的运用,制造出明星的形象的某种神秘感,某种超尘脱俗的梦幻感。一个明星一旦制造出来,他就被限制在特定的类型之中,被老板们作为出售给大众视觉愉悦的产品。
希区柯克在拍摄《深闺疑云》这部影片的时候,成功而巧妙地使用了加利·格兰特,成了一个说明杰出的导演怎样同影片公司单纯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并能左右影片创作的有趣例证。
格兰特是一个热情焕发、使人感到有高尚的道德、教养、智力和能把事情办好的人物。他经常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银幕上,使他总是取得成功,观众对他十分崇拜。希区柯克用格兰特扮演一个既有魅力但性格中又有某些阴暗面的角色时,他就能对人物性格的两重性进行一些出色的分析研究,如同在《美人计》中那个既有罪又无辜亦好亦坏的格兰特时,获得了卓越的效果一样。《深闺疑云》这部影片的核心就在于一个有魅力的男人(格兰特扮演)内心是邪恶的,他的妻子(琼·芳登扮演)逐渐怀疑了,直到认为他可能狠心毒死她。希区柯克原来的观念是让格兰特作为反面人物出现。但他意识到使用名演员时会受到种种“限制”,在后来拍摄的这部影片里,他不得不巧妙地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从而造成了意想不到而又扣人心弦的“悬念”。导演曾对这种改变作过如下的说明:
《深闺疑云》的正确结尾(我想那样拍,但是根本没有那样拍)是琼·芳登写信给她的母亲,说她爱自己的丈夫,但是感到他是一个杀人犯。她不想再活下去了,而且愿意死在他手里。但是她认为应当不让他危害社会。他端着一杯放了毒药的牛奶来到她的房间,把牛奶递给她。她在喝下去之前说:“你替我把写给妈妈的信寄走好吗?”然后,她喝下牛奶死去。淡出。再淡入一个短镜头:“兴高采烈的格兰特吹着口哨走向邮筒,把信扔进去,结束。但是,你们要知道加利·格兰特可是不能扮演杀人犯的。
影片未能使明星的类型从正面人物变成反面人物,但希区柯克利用了这一点,使影片疑窦丛生。后来斯坦利·多南导演的《猜字游戏》中也同样利用了格兰特,他让观众从女主角扮演者奥黛丽·赫本的眼光来看他;她不知道他到底是凶手,还是好朋友。在观众的视觉记忆中,格兰特在十多部影片中都扮演正面人物,因此,虽然证据越来越充足,从理性上观众推断格兰特必然有罪,但内心总怀疑:“他怎么会有罪呢?”从而悬念越来越强。《猜字游戏》在最后结束时,格兰特公开了他是侦察罪犯的政府官员的身份。《深闺疑云》最后拍成的结尾也证明他是无罪的。尽管从琼·芳登的视角看来,所有线索都会使人认为格兰特是凶手。如果这个角色不是影响很大的明星演员扮演,观众就不会感到捉摸不定,而会简单地认为这个人物是有罪的,银幕影像运动推进的过程中,“悬念”,也就不会那么强了,观众的参与感会消失殆尽。
(二)
电影演员比之于别的表演艺术受导演的“限制”特别强。在不少杰出的导演艺术家手中,造就出一批批著名演员。例如中国导演谢晋就被公认为是一位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演员的大导演。而在有一些导演的“限制”中,许多演员只能一直充任“平庸”的角色。也有些导演喜欢经常启用同一名演员,比如吴子牛对于陶泽如,黑泽明对于三船敏郎,以及上面提到的希区柯克对于加利·格兰特,都出于对待电影观念的某种一致,或者在气质、素养方面的共同倾向,或者某种默契。这一类合作与优秀的导演以敏锐的目光为自己的影片选择好合适的演员一样,能使导演对于演员的“限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配合,使电影表演在银幕影像构成创作上发挥出独特的光彩。
主演过《老枪》的法国著名演员菲力浦·努瓦雷与导演贝尔特朗·埃维尼埃之间,据说无论在形体上还是在各自经历上都有相同之处。埃维尼埃发现努瓦雷是一个戏路很宽的演员,不墨守陈规,乐于自自在在地去创造角色,因而在不断的合作中又加深了情谊。埃维尼埃甚至说,努瓦雷是他的“自传体演员”。当然,努瓦雷所感兴趣的不是导演希望通过影片反映他自己,他感兴趣的是活动于影片中的故事和情景中的人物本身,喜欢导演对具体事物的利用和那种精雕细刻的特色。努瓦雷十分明确地理解导演是把想要表现的一切蕴含在具体的场面和结构中,演员则在其中还有发挥的余地,足以丰富角色。他说:“当一个演员出现在银幕上,如果他演得好,他总要带来些新意。”
由此可见,演员只有明确理解导演的银幕影像构成的观念,才可能有自自在在的表演。而且创造性地丰富角色的形象,即“总要带来些新意”。同时,也可能避免人为地制造真实感而带来的矫揉造作,只有在导演的“限制”中自如地表演,才能具有真实感。
同时,启用非职业演员也是银幕影像运动构成对电影表演的“限制”的一种特殊现象。导演可以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段,使得从未演过戏的外行人也能较好地担负起赋予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任务。曾经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得过大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名片《偷自行车的人》,就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其中有一场表现儿童演员坐在路边哭泣的戏,这组镜头是怎样拍出来的呢?导演德·西卡说,为了表现画面上这个角色规定情境中的表演,他们当着这个小演员的面,故意把他最心爱的一个玩具弄坏,他便哭起来了。摄影师抢拍了这个镜头。事实上如此,电影拍摄时,导演可以从肉体上“强迫”演员产生某种角色特定的感情和外表上的效果。采用这种方法也不只限于非职业演员或儿童角色,因为在电影银幕上的影像运动画面是还要经过剪辑组合而成的。导演在根据样片指导剪辑的过程中,将进行一次总体的重新组合。因此,电影所要求的“真实性”与自然状态下连贯的真实事件是完全不同的,与舞台表演时的场景转换的延续形式也是不相同的。
为了银幕影像所要求的真实性,导演要求演员改变形体,比如《午夜狂奔》中的男主角罗伯特·德尼罗为了适合角色的需要,特意去墨西哥晒太阳,同时节食减肥,在半个来月中体重减轻20磅。比如《芙蓉镇》里徐宁为了在形体上接近生过3个孩子的农村妇女“五爪辣”, 拼命进食,吃得胖了10公斤。这种要求演员随时流眼泪,真的打耳光,真的从高层建筑上跳下来等等,就是电影的“真实性”对演员表演的特殊“限制”。据说在日本导演小林正树拍摄《做人的条件》那部影片时,有一场戏表现仲代达夫被军队内务班十名士兵殴打,为了“真实性”,导演要求扮演老兵的演员攥紧拳头狠命真打,结果把仲代达夫打的鼻青脸肿。于是,仲代提出说:“我明天可没法拍戏了。”导演回答说:“没关系,可以接下去拍第二个镜头。”演员顿时垂头丧气,却又无言以对。
有意思的是,著名导演爱森斯坦关于导演与演员问题的论文竟还用了一个《狼与羊》的题目。他说:“导演所表现出来的‘专横’在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呢?首先是在集体的某一个权利平等的成员表现出了对风格不够理解的时候。因为不管你怎么说,说这是独裁也好,或是什么也好,导演反正要对作品完整性、统一性风格总体负责。这是他的职责。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导演是个统治者。……对于演员来说,最困难的是使演员的处理与电影特殊因素的风格相符合,这些特殊因素,远不是演员随时都能领会和理解的。”然而,事情往往会“物极必反”,正是当时提出了“理性电影论”的爱森斯坦,在拍摄《十月》时启用了一个外形酷似弗·依·列宁的工人尼康德洛夫来创造第一次革命领袖的银幕形象。除了由一些列宁特有姿势的在装甲车上演说的全景画面之外,整个儿糟透了。爱森斯坦以邀请一个没有表演才能和技巧的人来作导演独裁尝试的失败这样昂贵的代价,为此后史楚金等著名特型演员的演出成功“交了学费”。
演员必须接受电影拍摄是有一幅一幅矩形画面连接起来这样一个技术性事实,必须适应导演将一个场面分解成若干个镜头,并从各种位置拍下角色表演的这种特殊创作行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导演可以从最后一场戏开拍,也可以将相同位置的场面或季节、气候、环境相同而在情节上完全不连贯的戏集中起来拍。一开始按照顺序拍摄一部电影的情况,自梅里爱把摄影机从对准舞台移到室外和摄影棚的那个时代起,恐怕就已经没有了。为了适应电影的这种方法,演员不可能按剧情展开的时间顺序去把握角色。这种与舞台演出的时间顺序完全不同的电影非连续性表演,对于演员来讲无疑有时会感到痛苦;为了拍摄几分钟的场面,往往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去表演被分解成多个镜头的戏,并且保持身体形态和声音状态的稳定一致。而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这些镜头的画面往往是以秒作为单位来计算的,最长也不过四五分钟。演员表演的时间完全由导演决定,违背导演规定的表演最后可能在一把剪刀下被消灭掉。
(三)
电影表演的一个原则,简单一点说,就是要在摄影机的取景框以内做戏。摄影镜头的变换,演员必须要以自己的身体去适应,同时必须省略掉某些平常的动作。不仅要理解导演对演员表演的分割和裁剪,而且要有意识地去配合。只有领会电影银幕构图的规律,才能使自己不单纯只是作为一个“素材”而存在,而是成为影像运动中能够发挥表演艺术独特魅力的重要因素。
在电影的种种“限制”中表演,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电影观众的视线是由银幕影像运动组成的视觉注意转移的规律决定的。电影演员在表演时,不像舞台演出那样受到舞台边框构成的规定空间的“限制”。在那个舞台上,只要不超越舞台空间,他们可以尽情发挥,因为舞台剧观众有选择视点的自由。当然,当演员背离剧情的规定情境,自行其是,一味把脸朝向正面,迫使观众翘首观看;或心血来潮,忽然来一个怪异的动作,使对手演员手足无措,从而引起观众的注目。这种过火的表演,在斯坦尼体系中是不允许的。但舞台剧导演此时是没有可以制裁的剪刀,这把剪刀掌握在观众手里,与演员同一时候同一场合参与创作的观众的哄笑和“喝倒彩”,实际上就是一把制裁演员表演的剪刀。
而电影的空间只受银幕边框的“限制”,对于演员来说,表演的空间是不确定的。有时候你与人对话时,表演很细腻,而在银幕影像构成中,你可能只像芝麻似的一个小点。像《黑炮事件》中党委班子几位领导到施工现场,一路讨论着关于赵书信的严肃的“问题”,话题很重要,但在画面上,大型橙黄机械带着吼声的前景运动,却似庞然大物,把领导班子的成员挤在尘土飞扬的角落里。但观众对导演的意图和情景的描写是完全能够接受的。有时,演员又与观众贴得很近,近到可以看到手指节因紧张而发白的颤抖,看眼睛,以至瞳仁中微微的泪光映出的视象。
作为叙事艺术重要因素的对白,演员也是完全受“限制”的。你声情俱茂的说白可能只是画外音;你的窃窃私语,却可能因在画面中居于特写位置而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例如伯格曼的《野草莓》的开始部分,老教授伊萨克·波尔格开始乘汽车进行长途旅行,去接受荣誉学位。他的儿媳玛丽亚陪他同往,回到因感情纠葛而分居一个月的丈夫那里去。伯格曼在汽车上安排的第一次交谈,只拍下两个人的对话,摄影很高明,但并无特别的艺术处理使观众分心,这是真正具有电影真实性的。
一段似乎随便、甚至琐碎的对话,与汽车和开车没有关系,而且是低调的,但它却十分明显地完全适合视觉因素:一部汽车里的两张心事各异的脸。而反映的是伊萨克对儿媳无端的不满,以反对抽烟为借题发挥的口实。但它反映出的内涵却为以后的剧情发展形成了前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伯格曼怎样使对话同地点联系起来。在开车出发时的车座里,为小事情而恼火,与伊萨克前往接受荣誉的严肃目的之间显然不相称。但他营造的近距离视觉形象内心的冲突却吸引了观众的紧张注意,从而,他以此为开端,来展开伊萨克的整个精神没落过程,其中包括悲剧性的恍然大悟的一次驶向他的往事的长途旅行。
在“限制”中的电影表演,就像在严格的足球规则中踢球。可以有平淡无奇或者被裁判以“黄牌”警告乃至“红牌”罚下场的,也可以出现球王贝利和马拉多那、贝肯鲍尔。其中的奥秘便是两个,一是技巧,二是灵性。
演员不是木偶,只是任导演摆布。优秀的演员必须有高超的技巧。现在被称之谓有“绝活”的,姜文就是一个。另一条则必须有生活的体验,按谢园的说法叫作“重整心灵的再现”。霍夫曼演克莱默,是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而当他演“雨人”时,则用半年时间生活在疯人院。刘晓庆演芙蓉姐就在王村磨了半个月的米豆腐。他们没有忘记对具体人生必须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以演员自我这块原料去体验。在每一部影片中演一个人物时,都要通过认真和研究生活并进行艰苦的形体练习,来完成整个角色的内心体验,使人物的外部形象尽可能完善地结合。那样,就不管你被安排在近景、远景或特写,也不论从哪个场景开始颠三倒四地拍摄,尽可以适应导演对银幕构图的设想,准确自如,全身心投入,使自己不至于失去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特具价值。
不论是所谓“本色演员”也好,“性格演员”也好,能不使自己在某部影片中离谱,又具备塑造角色的能力,摈弃“假模假式”的关键,确实在于对生活本质的谙熟,加上这种精神内质的外化,成为恰如其分的形体动作。自我欣赏、抢镜头、装腔作势的演员,眼下实在太多了。所以,把视觉形象的内在意义作为创造角色的核心问题提出来,不但有对电影表演理论研究的价值,同时具有现实意义。
希腊神话中,莫摩斯就抱怨用泥和水造人的普罗米修斯当时没有把人的心脏造在体外,使得人的内心世界无法让人一览无余。电影表演艺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
“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那些赋于思想家和艺术家的行为以高贵性的东西只能是心灵。人的各种心理能力中差不多都有心灵在发挥作用,因为人的诸心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着的。”〔1〕
可惜的是,电影由于导演和摄影及后期制作的特殊手段,使许多脸蛋标致或者身材优美的人们,以为当电影演员可以像“无技巧剪辑”似的采用所谓“无技巧表演”,或者被行家们称之为“没有表演的表演”。荒唐得即使能上“镜头”,也是两眼空空如也,目中无物。因为演员本身心中没有生活的体验,角色的心灵空虚了,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再加上没有形体的训练,以为自己就是天生演员的料。殊不知中国三百六十行中都借用“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戏曲表演行话来强调基本技能训练的重要,真格地“冬练三九,夏练六伏”。好象唯独电影表演只要长一副漂亮的外壳就能行;对白请人配音,骑马叫个替身。此风盛行,则既是“演员们”的悲哀,也是电影的耻辱。电影表演没有全身心的投入,电影视觉美感之说只有哭的份儿了。
想想一部整个儿以务虚为主的《孩子王》,主演谢园在导演陈凯歌的“制约”中的顿悟,似乎可以揣摩出一点电影表演的奥秘来。陈凯歌说:“你谢园塑造孩子王,全片700个镜头,你占了520余个,想象中是以一个人物为轴来转的影片,你更多的是站在叙事和情绪的中心,反正我对你的要求是这样的,既要从肖像层面上托现出当年知青的质感,又要在精神层面上合乎导演交给你的意念和细节中富有象征意味的真正内涵。”
谢园发现《孩子王》有很多重戏,戏里尽是“愣神儿”的镜头。开机前问导演下一个镜头是什么内容,导演说:“愣神儿和无可奈何。”于是开拍。一看样片全傻了。从人物整体到细部掌握都不准确。既缺少人物的真实体现,又没有完成导演意向上的要求,若即若离,魂不附体,“有心报国,无力回天”。谢园再三捉摸,反复体验,用他再三捉摸经验后的论题称之为《重整心灵的再现》,终于悟出“孩子王老杆子,之所以要平和,要‘一吃、二唱、三不争人先’,之所以要平静,要没有任何脾气,都在于他不平和、不平静,他要强制自己,要寻找到内心世界里真正的依托……”成功的孩子王谢园和吴子牛电影中的陶泽如一样,在情节淡化的影片中,全身心投入创造角色的任务,在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影片里焕发出异彩。
一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室也。故神荡而形伤,心静则形全,意在完形,必先理神。”
而在电影“限制”中的表演被分出来的所谓“性格演员”与“本色演员”,都逃不掉对艺术规律的认知和技巧的磨练,只不过前者要能“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谈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万洪语)“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而后者则要能如“和氏之壁,不饰以五采,隋候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语)“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故意填坑岸也。”(颜之推语)。
所谓“虽云色白,匪染弗丽”,“顺合众心,不违人意”也好;或者“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也好,都是某种“限制”,有流芳千载的传世之作之大文豪们尚且各有节制,自限其规,何况广为传播而大都随行上市之电影表演者乎?“即行即止,这就是表演技巧的最单纯而最正确的真理。”(郑君里语)
在特定“限制”中的电影表演,是一种遵循电影特征的艺术创造,而且是一种寓形神于一体,将形体与心灵整体和谐而完美地表现于千万观众面前的塑造人的精神的创造。好的电影演员,正是在这“限制”中脱颖而出、得心应手的高明的艺术家。
而且,毫无疑问,电影视觉美感的极大部分是由演员(优秀的)直接传达给它的接受者,并在以亿万计的电影观众心目中,留下真、善、美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演员非凡的知名度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