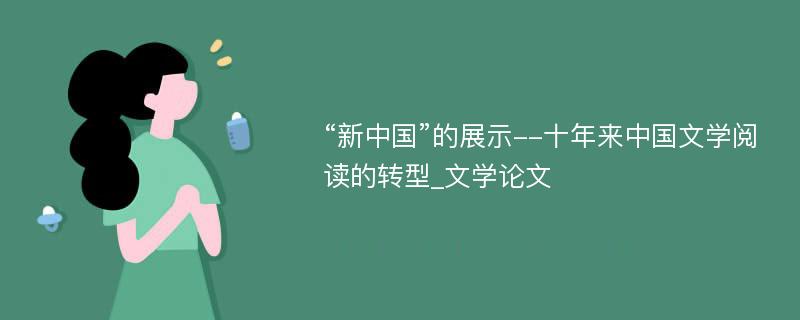
“新新中国”的展现——十年来中国文学阅读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新论文,中国论文,十年来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和平崛起促使文学发生变化
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其实是中国文学和文化深刻变化的时期。遥想十年前,知识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是一些对于未来充满了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的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热的呼叫的时刻;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这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时刻。1995年的时候,中国刚刚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消费社会才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刚刚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国的发展的许多今天看起来简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里的十年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学”在“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一个“新新中国”对于“新文学”的多面的、复杂的冲击我们已经无法不正视了。十年的光阴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新的时代已经由开端到成熟的过程。十年过去,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和那些悲观的预言完全相反的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国”。
在1995年的时候,许多人根本不承认消费主义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但中国的现实当然比故步自封的判断有力量,这一现实在已经达到了根本无需讨论的地步。中国在今天迎来的“和平崛起”的可能,不是由宏大的“现代性”的高蹈的叙述中获得的,是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追寻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平常的愿望中出现的。中国人的百年强国梦的实现也是在这种追求消费和满足的潮流中出现的。其实对20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一系列“论战”已经有了“现实”的回答。今天的“现实”的出现胜过了任何美丽的言词。中国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和挑战,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中国“脱贫困”和“脱第三世界”的大历史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形态。中国业已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力量,而我们面对的文学和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似乎也是我们原来没有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学领域中许多变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继续深化。这里有几个趋向异常明显:首先,作家的“换代”业已完成,当年一线重要作家的影响力今天已经开始渐渐消失。新一代作家的崛起和发展越来越清晰,显示了作家的“换代”的趋向;一个畅销书机制业已形成,品牌型畅销书的发展和纯文学的小众化的品种的分化日益明显。大众的畅销的文学作品和小众化的“纯文学”并存的景观已经清晰;长篇小说在文学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趋于市场化的运作,成为文学运作的中心;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前所未有的势头。这些变化都显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深刻的历史转变。但这里最关键的变化可以说就是两个方向的明晰化:一是中等收入者文学品味的崛起,另一个是青少年作者和读者的崛起。这两大走向其实是文学的“中产化”和“青春化”的趋势。这都是十年前的历史趋势的展开,也是当今中国文学发展的标志。
文学的“中产化”
文学的“中产化”,其实就是“中等收入者”对于写作和阅读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文学想象乃是社会转型的表征。社会变化为新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中等收入者”被写入报告,无疑显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等收入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在1995年时,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已经开始出现。但十年之后,这一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异常明显的程度。
对于文学想象来说,中等收入者的品味和价值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已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小说家邱华栋最近接受采访时也点明:“我觉得,从鲁迅到莫言这不到一百年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这些优秀的作家,写作的背景都是农村和农业社会,而未来能够成为汉语文学的增长点的,毫无疑问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
其次,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被日常化。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日常生活的再发现的进程,完全主导了新的文学想象。它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在消费之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而中产阶级的温和和保守的社会性格及与跨国资本和全球化的内在的联系都使得文学更加世俗化。各种激烈的意识形态主张,无论是左的或者右的都在社会中变成了边缘的思潮,已经无法被社会接受,而仅仅变为满足中产阶级的现实的挫折感和文化冲动的消费品。
个人负责的价值观的崛起和“优雅”的崛起成为一种文化标志。个人力争上游乃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基础,而和这一基础相关联的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负责的价值乃是文学表达的前提。一切已经由传统的社会负责转变为个人自己负责,个人生存的问题只有个人自己承担。与此同时,“优雅”的崛起也是文学的重要现象,这种“优雅”以怀旧为标志。这种怀旧一方面是怀念现代中国“优雅”一度得到充分展现的旧上海的文化,一面是在中国历史中压抑“优雅”的时代去寻觅“优雅”的潜流。
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因素。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文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又仍然表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在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察。我们如何在面对这种新的现象和话语的发展时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肯定,而是在认真地回应它提出的复杂的问题,给予同样复杂的观察和思考,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这里,思考这一文学想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尖锐性之间的平衡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文学的“中产化”并不遗忘和忽视“底层”。在“中产化”的潮流中对于底层的关切,期望底层的力争上游、改变命运,也是“中产化”的一种表征。
文学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的“青春化”
文学的“青春化”就是文学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的“青春化”。2004年2月2日《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用了一个中国的少女作家的形象作为封面,并将几位少年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一代的代表。这一报道其实显示了近年来出现在中国的“青春化写作”崛起产生的文化意义已经浮上了台面。中国少年的文化经验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全球化的一个形象,也在迅速地全球化,成为中国在“和平崛起”中的形象的一个部分,也是这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新新中国”的某种象征。今天的“青春化写作”是一种和主流的文学界毫不相关的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和市场的现象。但文学的市场格局被他们改变了,少年的一朝成名动摇了原有的文学秩序。“文学”的概念和价值判断的标准都面临冲击。毫无疑问,这些几乎毫无写作经验的少年人的试笔之作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几乎完全看不出任何妙处,往往会被视为胡言乱语或肤浅的自我表达,这却受到了和作者同样年轻的读者的追捧和欢呼。这些现象的矛盾性在于,这种“青春化写作”俨然已经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却仍然被许多人看成不登大雅之堂的莫名其妙的流行读物。这种写作的风格和内容仍然是“不成熟”的,却成了不胫而走的新的文化象征。
“青春化写作”引发的震动有两个有趣之处:一是这种震动几乎完全是在和主流的文学界没有联系,也和文学批评的话语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出现的。无论是主流的“纯文学”还是主流的和大众文化相关联的通俗文学其实都和这种“青春化写作”有严重的断裂。文学界几乎没有对于这些现象作出反应,而文学市场的格局就已经改变了。“青春化写作”的出现是和正统的文学界的话语方式和运作完全不同的新的存在。在受到市场支配的文学出版业对于他们的追捧越来越剧烈的同时,好像文学界仍然保持沉默。二是这些写作的市场也是完全依赖一个与主流文学的市场不同的空间来运作的。他们的读者也是和主流文学大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那些作者的同代人。他们原来似乎仅仅是一种成人主流文学边缘的“儿童文学”的对象,是文学市场的最边缘的力量,常常被视而不见,但今天这个青少年的巨大的阅读市场已经是任何人都不能视而不见的了。它没有动摇文学界的批评和阅读机制,却动摇了作为这一机制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出版的机制。让文学出版随他们的崛起而舞动。于是,“小鬼当家”的文学的低龄化的运动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形成了巨大的新兴产业。
这种“青春化写作”的发展乃是青少年文化的独特性的产物。这种写作具有非常明确的电子游戏和网络时代青少年的文化特征:首先,它的情节和故事往往都是片段性的,是由情绪的片断的连缀和流动来展现个人的私密世界。故事情节的线索都极端的不明晰,往往仅仅是一些生活断片或感情起伏的模糊迷离的线索的即兴的书写。其次,这些作品的经验的范围也仅仅是个人的私生活的琐碎的事物。大量对于成年人来说几乎是没有趣味和意思的抒情的片段和来自青少年文化自身的文化符号和素材的自由调用展示了一个个人的世界。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游戏式的感情体验具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青春化写作”是某种叛逆性和顺应性的混合。“青春化写作”在内容方面表明了一种对于当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某种反叛的情绪,却也在形式和运作方式上顺应了这一逻辑。第四、这种“青春化写作”是一种亚文学的出现,它是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高度混合,也是对于主流价值的反叛和认同的混合。它一面以反叛的姿态和发出不同于成人世界的声音的愿望,高度地吸引被消费的趣味所支配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阅读和写作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学习”“读书”,而被家长或长辈视为一种相当积极的事情而受到了许多支持和认可。
中国的青春化的趋势是文化发展的总体走向,这个走向的真实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一个新的丰裕社会业已形成。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革和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多样化提供了条件。二是中国出生于相对丰裕的社会中的第一代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青少年的图书消费业已展开成为阅读的主要力量。梁启超呼唤的“少年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展开。这也是一个“新新中国”历史的新的展开。
十年过去,文学在“中产化”和“青春化”的方向上走到了今天,它们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学”的既定的概念,而和一个新的“新世纪文化”相互应和,体现了“新新中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环境下的新的文学的出现。这种新的文学当然未必是理想化的,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学中想象自己,书写时代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