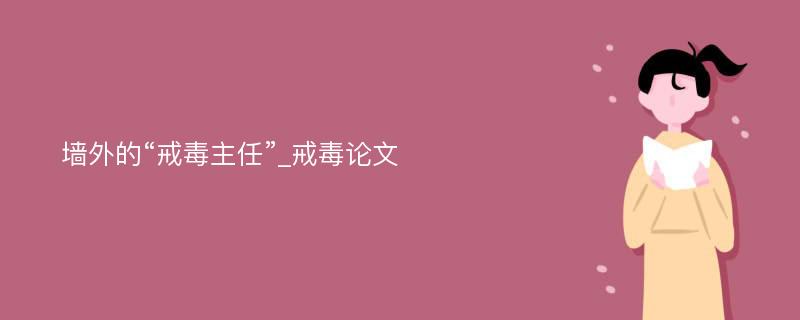
大墙外的“戒毒所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长论文,墙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医生警告过,再来一次就走掉了。”吕焕皋去年8个月内2次中风,说起自己的病情,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老婆对他唯有叹气。午夜,这个右半身偏瘫的61岁犟老头,居然还要一瘸一拐地出门,去酒吧,去KTV。 进到那些犬马声色、光影不羁之地,他先给周围人发点小费,请吃夜宵,人家自然当他是夜场老板。他坐在角落,无比耐心地,看着那些男女们,在粉末作用下把头摇得忘记了世界存在,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才渐消停。然后,他主动递上名片,说:“有空来我公司,我们聊聊”,又或者,不合氛围地来一句,“趁早戒毒,有困难找我”。 这出手阔绰的老板,说出如此“大煞风景”的话,人家当他是“怪人”。 但他是说真的。已经有800位被白色恶魔侵蚀过身体、剥夺过灵魂的吸毒者,曾经或现在,成为他的员工。 第一辆禁毒车 关于自己“混迹”夜场,他对记者的解释是,“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这名社会工作者,会把居民区的“小巷总理”们请来座谈,你一言,我一语,社区内的“毒情”很快被和盘托出。然后就是核实。他夜访被“点名”的酒吧,坐定后,将手指放于鼻下,做擦鼻涕状,边问:“有伐?”果然,服务员心领神会地点头。接着问价格,对方答“500”,他即刻一副唬弄不了的表情,“外头行情260,想坑我?” 待掌握了实情,他跑到某某小区,慷慨激昂——多少酒吧在贩毒,多少人在吸毒,多少人关在强制隔离戒毒所,“你们还敢不敢评‘无毒小区’?”对方尴尬得半天回不上话。 老吕之所以跟禁毒“杠”上了,是为祭奠他的恩人和挚友们。 吕焕皋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生意,当时一位前辈曾鼎力相助,借给他几千元当启动资金,对此,吕焕皋感激不尽。然而,这位恩人却为追求“腔调”,不幸染毒,自此无心料理生意,万贯家财化为股股青烟后,还举债购毒,走上了不归路。 犹记1993年某日,恩人前来借钱。吕焕皋满心狐疑:这么有钱的老板还问我借钱?但念及旧恩,仍是借了。一年后,他才从旁人口中得知恩人的种种异样,跑去质问,瘾君子痛苦道:自己真心想戒,身体却屡屡叛变,被海洛因“滋补”后,整个人轻飘飘的,但不吸时,就跟鬼一样…… 最后一面,是在追悼会上。恩人躺在棺材里,因吸毒过量,曾经鲜活的身体,佝偻得不足1米。 家破人亡背后,还有可怕的愚昧。吕焕皋熟悉的人当中,有人从事运毒,把一个包裹从徐汇送到静安,得5000元,却浑然不知是犯罪,反认为这是“给朋友帮忙”。跟吕焕皋同时起家的一位朋友,吸毒后千万资产耗尽,最后只能“以贩养吸”,以致被判死刑。吕焕皋后来找到了死囚的律师,得知犯人直到临刑前都没想通:“以贩养吸”只是我个人的事,怎么就定了死罪? 吕焕皋掐指算来,他的旧友中,吸毒过量致死的、吸毒贩毒被判刑的,两只手数不过来。痛心之下,他找到了“刑警803”(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的蔡立群,这位后来被公安部追授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也深切感到,全民对毒品的认识何等匮乏,政府层面要重视缉毒,更要重视宣传。于是,吕焕皋自告奋勇,自掏腰包百万元,参照国外宣传禁毒经验,于1998年与蔡立群等一起,筹划设计出了全国首辆禁毒宣传车。 难忘那年,为定制宣传车,吕焕皋和蔡立群两人在上海客车厂一呆就是3个月。他俩和工人们一起,蹲在路边吃盒饭,蔡立群还不停地去买饮料,晚上则是啤酒宵夜,去犒劳那些加班加点的工人。那辆新颖别致的“流动禁毒展览馆”,终于赶在1998年5月全国第一次大型禁毒展之前完工。车子开到北京,参加全国禁毒展的领导上车参观,见到车内充分运用声、光、电、模型、实物、图片和录像各类手段,介绍什么是毒品,毒品有哪些危害,披露毒品违法犯罪案例,宣传禁毒法律法规,都不由盛赞“上海做法”。不久,车开回上海,又在工厂、院校、社区、街头火了整整半年。吕焕皋至今仍得意,“想当年,早6点到晚8点,市民排队等着看。车外打上一行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带毒50克以上,最高死刑!你想想,光这一辆车,挽救了多少人?” 特殊的员工 禁毒宣传车着实风光了一阵,老吕就此上瘾了。这瘾头,令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工作者周有光颇为感慨。周有光是上海市原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现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首批筹建人员,他告诉记者,强戒所1996年挂牌至今,整整18年了,老吕跟每一任所长都很熟悉,“第一任所长都退休了,老吕居然还在搞禁毒”。 2000年,吕焕皋的企业,成了全上海唯一一家与强戒所签订“关于安置解教人员就业协议”的民营企业,14年来已吸纳800名吸毒者就业。而且,在周有光的印象中,除了一名成功戒毒者自主创业并先后安置30名脱毒同伴外,吕焕皋之后,再无效仿者。 吸毒者谈不上是合格的劳动者,对于这一点,吕焕皋再清楚不过,“他们做事没力气,总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走路还没我这中过风的人稳呢”。但当年,一听说吸毒者重返社会后,因找不到工作自暴自弃继而复吸,或为了隐瞒前科忐忑不安时,吕焕皋不忍心了。他掂量一下自己企业的实力,很快拍板,“能救一个是一个”。 为此,他专门腾出20余个床位,挖掘出绿化、保安、技术服务、电工等岗位,就等吸毒者来。根据协议,在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内,只有那些表现优异的戒毒者,可以提前2周至3个月,被安排到吕焕皋的企业实习,包吃包住,还有五六百元的工资,工作一段时间后,留走自愿。 但吸毒者改造之难,远超老吕想象。谈及伤心事,他向记者叹口气,“说多了都是泪啊”。 这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数字。在他迄今收纳的800名吸毒员工中,复吸率高达97.5%。 一旦抓到现行,老吕是毫不讲情面的。2012年底,5名戒毒人员在吕焕皋的企业聚众吸毒,老吕会同相关部门处理,5人再次被强制隔离戒毒。很可惜,其中一人,离正式回归社会只剩2天了。 老吕不想隐瞒,为了禁毒,他把自己的儿子也搭进去了。今年32岁的儿子,4年前因为跟老爸安置的吸毒人员时有接触,也受到毒品蛊惑,毒资用掉几千万元。日前,儿子强戒期满,为巩固成效,老吕又将他送往外地继续强戒。老吕说,对吸毒者,最仁慈、也最负责的做法,就是送他(她)去强戒所。这话,说给别人,也说给自己听。 想回家的阿强 有个寓言,关于农夫与蛇。别人都觉得,老吕就是那“农夫”。 这位“农夫”,总为吸毒者辩护——戒断,是世界性难题!他告诉记者,吸毒者们何尝不知毒品之害,何尝不想挣脱地狱,有些人匿名向警方举报了自己,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强戒所;还有人发誓断掉毒瘾,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不避讳用真名,面对镜头也不要求用“马赛克”遮挡脸部,以期自我加压,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半年后还是复吸,为逃避警察的一次例行检查而仓皇跳楼,摔成了重伤…… 吕焕皋说:“你不能否认这些人当时戒断的决心。复吸率这么高,不是吸毒者太无能,而是魔鬼太强大。” 禁毒专家、上海市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张俭琛也告诉记者,强戒所普遍存在“二进宫”、“三进宫”现象,最厉害的有“七进宫”。但事实上,吸毒者对毒品的情感反应出乎外界意料,“他们首先是恨和怕,其次才是想。这就提示我们,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动员,标本兼治,才能挽救更多的吸毒人员”。 因此在吕焕皋眼里,吸毒者首先是受害者和特殊病人,其次才是犯罪分子。 而支撑他当了这么多年“农夫”的,是800人中迄今没有复吸的20人。 “病人”阿强便是这20人之一。 记者见到阿强时,他戴着帽子,压低的帽檐下,是灰黄的面色。他告诉记者,他的双手一直浮肿着,人特别容易乏力,内脏器官至少比同龄人衰老10年。这些,都要拜十多年的吸毒史所赐。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强做音响生意,9个月就净赚190万元,得意之际,不慎染毒,海洛因、冰毒、K粉遍尝,烫吸、口服、注射各种玩法皆试。他曾经的毒友中,有人口腔大块溃疡,舌头烂得像地图;有人精神恍惚,没等“下了头”、“散了冰”,开车就走,结果人和车在江中一起被捞上来;有人变成欺诈型人格,谎话张口就来,为了毒品六亲不认,甚至拿着刀子问父母要钱;还有人为追求“境界”而进行静脉注射,剂量未控制好,身体便直接硬了…… 阿强去过3次强戒所。第一次出来,一年后复吸;第二次出来,当天就复吸;第三次出来是去年1月份,他被安排到吕焕皋的企业工作,迄今未复吸。 他知道,吸毒者没有未来,持续吸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因为怕死,他多次戒毒,生理上的戒断并不是特别困难,一般一周到10天,就能熬过去。最怕的是心理上的落差,毒品曾给予他极端的享受与快乐,使他没齿不忘,这便是心瘾。与此同时,刚刚从强戒所出来的人,极度脆弱、自卑,他们一方面要努力对抗心瘾,另一方面又特别容易在变化了的外界环境和人们的目光中受到伤害,从而再度堕落。 他第一次复吸,是因为意志不坚,又回到了原来的圈子里,“朋友在吸,你不得不吸,否则他们不放心”;第二次从强戒所出来,他决心远离过去的圈子,然而,身边的至亲和好友却把他看死了,“照你这德性,一辈子戒不了毒”。这标签一贴,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而第三次戒毒后,他发誓无论如何不吸了,“父母年纪大了,万一他们走时我不在身边,会造成终生遗憾,还有女儿要读高中了,我生怕她需要我时我不能陪伴”。 但阿强向记者坦言,父母和女儿是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老吕的企业作为他回归社会的“缓冲带”,很可能他会再次放弃。 他告诉记者,在强戒所的许多同伴,都对进入到这个“缓冲带”望眼欲穿。对他们而言,尽管现在社区里有专门的社工帮他们介绍工作,也会刻意为吸毒者隐瞒既往痕迹,“但许多工作需要看档案,你的老底无处遁形。尤其是在你回归之初,往往承受不了这种心理打击,它会摧毁你所有决心和信心,让你再一次自暴自弃”。 而在老吕的企业,安置吸毒人员已被公开化,阿强至少不用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再者,他还能通过劳动获得固定收入,由此渐渐恢复社会地位,也让心理阵线变得坚固起来,“当你不用为正常的生活担心时,你才有可能变得正常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对戒毒人员最好的帮助”。 阿强觉得,每位戒毒人员,都需要这样的过渡和缓冲,“这个过渡期,1个月肯定不够,最好是1至3年,但除了这里,没有其他企业愿意这样做”。 对吕焕皋而言,复吸者一次次让他伤心,但他依然坚信吸毒者对抗恶魔时付出的种种努力。他也依然愿意坚守承诺,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能救一个是一个”。 的确,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将心比心的。老吕两次中风,那些曾被他帮助过的吸毒人员,蜂拥着前来看望,令老吕很是安慰。病榻前,阿强更是左右服侍,用心照料,视老吕为亲人。对于阿强,老吕还是忍不住要给他机会,而今公司里有一部分场地租赁给了100多家单位,都由阿强负责收租,光现金租金每月就是几十万元。这笔巨款,对于曾经的吸毒者而言,何其诱人。但阿强明白老板的良苦用心,所以每次刚收到现钞,他都想方设法尽快上交,从不过夜。 阿强是在老吕公司里一处仓库的后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时,仓库门半掩着,能透点光亮进来,他就坐在半阴的光线中。临到采访结束,他告诉记者,想改过自新的人往往特别敏感,内心就如同这扇门,随时准备关上,但也能随时开启。 他还说,吸毒圈有句行话,叫做“上路”,就是去了不想回,把命都豁出去的意思。 但在这里,他坚定了回家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