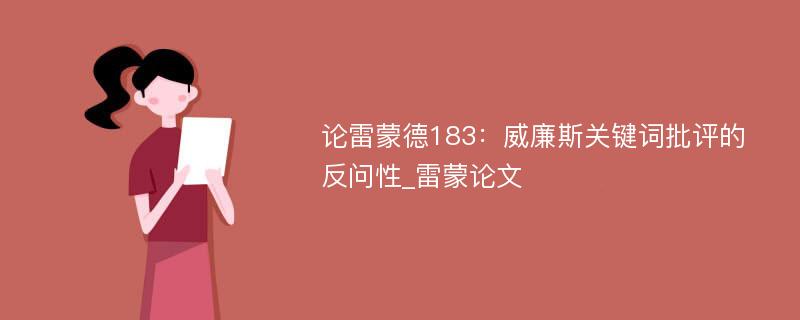
论雷蒙#183;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反辞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书论文,雷蒙论文,威廉斯论文,关键词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1-0110-07
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与“新左派”的领军人物,雷蒙·威廉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力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与理查·霍加特的《读书识字的用途》(1958)、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一起被认为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伊格尔顿曾将雷蒙·威廉斯与法国的萨特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战后乃至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1]孕育于文化研究母体之中的“关键词批评”,就源自雷蒙·威廉斯的创造性想法。“关键词批评”以核心术语为考察重心,从历时和共时层面进行梳理,揭示出词语背后的政治思想倾向与人文踪迹,具有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开阔的理论视野。
一、“关键词批评”的生成及其反辞书性
雷蒙·威廉斯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开创了以“关键词批评”为社会和文化研究有效路径的独特方法,被视为“关键词批评”兴起的标志。其实,雷蒙·威廉斯早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即联系社会发展考察“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文化”(Culture)这五个在现代意义结构中极为重要的词语之语义嬗变和用法变化,开始了其“关键词批评”的早期实践,亦可谓之“关键词批评”的萌芽。雷蒙·威廉认为这五个词在关键时期发生的用法变化,是我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特定观点发生普遍变化的见证,即:对我们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机构的思考;对设置这些机构所体现的目的的思考;对我们的学习、教育、艺术活动的目的与这些机构的关系的思考。[2](P13)当年,雷蒙·威廉斯本想让《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作为《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附录出现,但是由于出版社提出全书必须删减,威廉斯只好忍痛割爱撤下这一部分的内容。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增补,《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方独立成书,1983再版时又增加了21个词条,词条量臻达131个。在“关键词批评”中,雷蒙·威廉斯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疆域,从社会大视角和多语境角度诠释文化及其时代新质。雷蒙·威廉斯以历史语义学和关键词钩沉为写作方法,甄别遴选处于文化与社会研究“网结”要位的核心术语,力图通过细致的考辨梳理,凸显词语的政治立场与人文印迹,呈现出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与其开放的研究理念相契合,“关键词批评”在借鉴辞书编撰理念和文本体例时,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反辞书性,在对文学(化)现象和问题的多元探讨中昭示了文学(化)理论与批评行进的多条路径。
所谓反辞书性自然是相对于辞书性而言的。辞书性指的是辞书通常所应葆有的权威性、客观性、规范性、基本性、全面性、简明性等基本属性。辞书即辞典,亦作词典,而“典”字即含“标准”之意。辞书通常被视为典范性的工具书,通过汇编一定数量的词语条目,按音、形、义等顺序编排,并逐一解释,以供人检索查考。而包括雷蒙·威廉斯在内的“关键词批评”的实践者,大多否认意在编撰关于关键词的辞典。雷蒙·威廉斯就反复强调他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并非一本辞典,也非学科的术语汇编,而是对文化与社会类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3](P15)。的确,雷蒙·威廉斯只是借鉴了辞书编撰的外壳,其重心却落在解析文化与社会之上。洪子诚、孟繁华谈到《当代文学关键词》的编撰动机时也表示,主要不在于“编写一本有关当代文学主要语词的词典,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而是“质疑对这些概念的‘本质’的理解,不把它们看作‘自明’的实体,从看起来‘平滑’、‘统一’的语词中,发现裂缝和矛盾,暴露它们的‘构造’的性质,指出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变异,与当代文学形态的确立和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从对象内部,在内在逻辑上把握它们,来实现对‘当代文学’的反思和清理”[4](P2-3)。然而,不论“关键词批评”的始作俑者及其后继者的编撰初衷如何,“关键词批评”显然在批评形态和文本构造上仍然受到了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理念与体例的启迪和影响,具有较强的语汇积聚性。尤其是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形式上仍然按音序编排,对术语的选择和阐释也体现了辞书的基本性、全面性和简明性。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问世后“备受关注,广为征引”[5],“关键词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个研究领域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至今方兴未艾。上个世纪末开始,西方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中的关键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以文化、文论和文学领域为甚。如《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drew Bennett,Nicholas Royl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1995)①、《文学理论关键词》(Julian Wolfreys,Key concepts in literary theory,2002)、《新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Meaghan Morris ed.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2005)、《文学与文化理论批评关键词》(Julian Wolfreys,Critical Keyword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2004)、《当代文学关键词》(Steve Padley,Ke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06)等。此外,还出现了“劳特里奇关键词系列”、“批评新成语”、“批评思想家系列”之类的系列丛书。随着文化研究渐成显学,“关键词批评”近年登陆中国后也被广泛接受和大量应用,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研究路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赡。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2)、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2002)、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2006)等。还出现了“文化研究关键词”(2006)、“人文社会科学关键词丛书”(2007)等丛书,《外国文学》、《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南方文坛》、《电影艺术》等刊物则专辟了“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关键词解析”、“当代文学关键词”、“电影学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等“关键词批评”专栏。“关键词批评”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以他们深刻独到的学理思考和充满生机的批评实践,冲击着传统的批评理念和批评话语,显示了强劲的理论穿透力。
雷蒙·威廉斯之后的“关键词批评”著述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趋向,其辞书性的比重也各有差异。有的更偏重于辞书性,如《哥伦比亚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词典》(Joseph Childers and Gary Hentzi,eds.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1995)、《文化理论家辞典》(Ellis Cashmore,Chris Rojek,eds.Dictionary of Cultural Theorists.London,New York,Sydney,1999)、《当代文学理论术语》(Jeremy Hawthorn.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2000)、《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廖炳惠编著,2006)等。其中,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2007)既具有显著的术语汇编类专科辞典的特性,在体例上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该书收入43个词条,每个词条分为“关键视窗”、“关键视点”和“关键著作”三部分。“关键视窗”以三五百字对所涉关键词语进行简单勾勒,可视为“引子”;“关键视点”分列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和用法;“关键著作”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相关重要著述的索引。也有的辞书性微弱,文论性则愈益彰显,如《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drew Bennett,Nicholas Royl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1995)、《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陈思和著,2002)、《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2006)等。其中,陈思和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文论性极强。作者选择了“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这五个极富创见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关键性术语,各选录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对这些关键词的阐述,一篇是相关的当代文学个案研究,把文学史理论研究的学术性论文与当代文学批评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理论研究来推动文学批评,以批评实践来检验理论探索”[6](P3),体现了理论见解与批评实践的有机结合。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不论辞书性的多寡,运用“关键词批评”的相关著述已经在实际上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工具书或准工具书。因此,“关键词批评”著作大多既可以被视作理论辞书,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辞书。雷蒙·威廉斯以对关键语汇词义演变的敏锐理论洞察及独特体例构思开启了“关键词批评”研究的文本范例,本文接下来将着重探析其“关键词批评”所具有的反辞书性品格——非权威性与文论性。
二、“关键词批评”的非权威性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突破了传统辞书以话语权威姿态对词条进行“一锤定音”式或曰“标准答案”式的定评界说,在对关键语汇词义的解析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与延展性。
显然,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使用中会发生裂变,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现实身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使用者那里也会产生意义差异。词语意义的演变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变迁合力作用的结果。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正是通过探询词语意义的变化过程,从语言角度深入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及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揭示其中隐含的意义差异、矛盾、断裂和张力。雷蒙·威廉斯采用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对关键词进行解析,他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重视词义的延续、变异、冲突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3](P23)。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学科自身的特性,很多概念在鲜活的批评实践中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关键词批评”也相应地表现出了极富弹性的批评思维特征。陈思和就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序言中坦言所论五个关键词的内涵意义是他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丰富的,到写作该书时也还在尝试之中,所以本来也就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6](P3)通常,采用“关键词批评”的研究者虽然在比较与鉴别各种观点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却并不试图给出一个最后的结论。这种充满学术张力的研究方式与思维方式表明研究者认识到这些概念的意义与理论活动和阐释实践不可分割,因此,他们的阐释意图并非是要提供一个有关这些关键词界说的“标准答案”,而是注重关键词的开放性与流变性,重视其缘起、生成语境、基本理论意指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
我们不妨以雷蒙·威廉斯关于“标准”(Standards)词条的解析[3](P296-299)作为一个例子,由此管窥其“关键词批评”的非权威性。雷蒙·威廉斯在简要联系盎格鲁诺曼语、古法文、拉丁文等对“标准”进行词源学上的追溯后,指出15世纪出现了“标准”一词的现代用法——“一种权威的来源”、“合乎标准的要求”。雷蒙·威廉斯认为“标准”的这一意指除被广泛用于重量与度量的标准规格外,还延伸到其他领域,具有普遍的“指南、规范”之意。雷蒙·威廉斯在对“标准”的词义演变进行阐析时,又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通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深度观照:一是注意到其演变过程中的衍生词的词根意指与“旗帜”有关,并指出“王室旗杆”(the Royal Standard)是个代表权威的标记;二是注意到19世纪出现了“标准英文”(Standard English)这一具有阶级色彩的词语,而与写作、算术等方面的能力指标一样受到教育机构支持的“标准英文”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正确语言,旨在纠正以英文为母音者所使用的“不正确”的英文;三是花费较多笔墨辨析了“标准”(Standards)所具有的“一般的复数名词”和“具有复数形式的单数名词”的特点,指出前者意义上的“标准”可以被归纳和准确地标示出来,而后者意义上的“标准”则意指“共识的”或“具有说服力的”。在对“标准”词条的释义中,雷蒙·威廉斯强调了“标准英文”的阶级色彩,在谈到“标准”一词的“具有说服力”意指时,还特别说明这种所谓的“标准”往往带有某些有意的模糊与含混。雷蒙·威廉斯的这些微言大义背后其实都是有潜台词的,它们隐而不显地表现了他对某些优势话语群体所谓“标准”及对任何事物都企图以“标准”衡量的做法含而不露的嘲讽,这也与其关注非精英文化及弱势群体的批评立场紧密相关。在词条末尾,雷蒙·威廉斯笔涉“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意涵的演变(从明确意指——“当一个标准被设定时,工资就会参照这个设定的标准来断定”到转向更一般的意指——“我们实际拥有的收入与条件”)和质疑“生活标准”是否真的可以测量时,又注意到了此处“标准”并非指“一致同意的标准”,而是与“旗帜”的隐喻有关,进而提出“未来的标准”这一具有新意的说法。他所谓的“未来的标准”既不对权威进行溯源,也不认可现存的可度量的状态,而是向着更好的目标迈进。雷蒙·威廉斯还注意到“标准”(Standards)的普遍正面用法与“标准化”(Standardizations)的负面用法相冲突,指出在工业方面标准化没有争议,而应用到有关精神与经验的事物中却常被排斥,如人、教学等就不应该被标准化。雷蒙·威廉斯敏锐地发现,如果不察觉到“标准”(Standards)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数形式的单数名词,就可以被用来无视必然的争论或将评价与定义的过程挪用至自己特定的结论。在此,雷蒙·威廉斯意在提醒我们注意评价和定义这种看似“权威”的言说方式背后所隐匿的话语陷阱,正如他在导言中所指出的存在辞书权威性被有意“挪用”的现象那样——挪用辞书中适合其辩论的词义,却排除那些不合适的词义[3](P17)。
在雷蒙·威廉斯看来,辞书显示的是“当时大众所认为的适当解释”。他虽然并不否认辞书具有权威性,也承认这种权威性不会因为词义会随时空变化而有所减损。但他不客气地指出了辞书的局限性,因为它只是在不断修订词义,其认定的词义并非一定具有适宜的普遍性[3](P26)。他更看重的是超越辞书“列出一系列现在通用的意义”,并强调对于不同种类的词,尤其是那些牵涉到思想及价值观的词,此种定义方式是不可能和不恰当的。雷蒙·威廉斯追求的是,通过查询历史词典或阅读历史随笔、当代小品文等方式,超越“适当意义”的范围,发现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以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3](P17)雷蒙·威廉斯重视关键词在日常生活关系中呈现出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而不同的研究者对这种变异性和多样性的研究本身也是多样的。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合在《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对一些关键词进行解析时,就注重将理论研究与文本范例分析结合起来,在对文学问题的多元探讨和文学文本的多维解读中“呈现了文学理论的多种可能途径”,也体现了赛义德所倡导的“复调式的阅读”和“多元对话的复调效果”,从而“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看待和理解文学的方式”[7](P4)。在第2章《读者与阅读》中,他们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著名的十四行诗《奥西曼德斯》为范例进行文本分析,通过文学理论近几十年来发展中涌现的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流派对该诗解读的分歧,说明“《奥西曼德斯》赋予读者和阅读的,也像它所牵连的事物一样多”,并指出文学的阅读与被阅读的关系“令人惊奇地纠缠不清:不仅是我们在读诗歌,而且诗歌也读我们”[7](P17)。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认为词义的演变,“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往往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语言的社会运用乃是‘各种转换、利益和控制关系表演的舞台’,词语是各种社会力量交往互动的产物,不同倾向的社会声音在这里冲突和交流”[5]。雷蒙·威廉斯认为意义的变异性是语言的本质,他还透过意义变异的表象洞悉了许多重要的词义往往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由优势阶级所形成的这一真相——在社会史中,很大程度上,许多关键的词义都是由占优势的阶级塑形的,并由某些特定行业所操控,导致一些词义被边缘化[3](P18)。基于此,雷蒙·威廉斯冀望“从词义的主流定义之外”,“找出那些边缘意指”[3](P24)。他认为,通过深入细致地探究词汇的意义及其用法的变化,能够把握其后隐匿的动机和意识形态意图,发现社会的权力所在和权力分配机制,进而找到抵抗权力的源泉,工人阶级就可以“掌握所有用以传达社会转化的工具”,积极表现自己的语言的力量,把这些力量转化成为挑战“官方意义”霸权和变革社会的武器。[5]可见,雷蒙·威廉斯不仅不认同由优势阶级所掌控的那些重要词义的权威性,反而正是要通过细致地辨析和揭示词义的流变,尤其是“主流定义”之外的“边缘的意指”,来削减这种或显或隐地烙有意识形态印痕的词义的权威性。
三、“关键词批评”的文论性
除削减词义的权威性外,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批评”还不再像传统辞书那样宣称具有客观性,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文论性。不过,雷蒙·威廉斯的这种文论性并不是像论文那样直接张扬个人的见解、立场与偏好,而是将这些隐含在对词义的简略梳理和精当辨析之中,读者往往需要细心揣摩,方能领悟其言外之旨。正如陆建德曾经指出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具有论辩的特征,“我们应对书中论辩的风格予以特别的关注”,“有些地方我们稍不留心就可能捕捉不到嘲讽、挖苦的话外之音”[8](P5)。其文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对关键词的遴选体现了编撰者的立足点与批评理念。
众所周知,各个学科领域都存在着一批身系学科魂灵命脉的核心语汇。这些核心语汇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理论能量,又与一个学科的重点、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休戚相关,它们对于人们科学认识研究对象乃至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而批评家对关键词的遴选和阐述绝非随意性的行为,因为无论是从浩若繁星的词语中筛选出构建语汇“星座”的关键性词语,还是关于不同流派、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语境对同一个或相近词语使用上的显著或微妙的差异甚或对立进行考辨,都体现了批评主体的批评立足点、批评理念、批评视阈和批评敏感度。雷蒙·威廉斯就是紧密围绕“文化”与“社会”来选择与之息息相关的131个关键词的,并赋予关键词两个相关层面的意义:一是在某些情境及诠释中重要且相关的词;二是在某些思想领域中“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语。[3](P15)
“文化”可谓雷蒙·威廉斯遴选出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也是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回溯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批判传统,以及“文化”一词在W.布莱克、T.S.艾略特、W.莫里斯等人著作中语义演变的历史,指出“文化”与“阶级”、“工业”、“民主”等的关联性蕴含了思想和历史的结构。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威廉斯进一步从三个层面探析了“文化”:理想文化,指阿诺德主张的以高雅文学艺术为代表的精选文化传统;纪录文化,指各类媒体记载的人类经验和知识生活;社会文化,指社会机构和日常生活表现的特殊生活方式。[9](P57)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威廉斯则以“文化”一词的拉丁文词源Colere所具有的“栽种”、“照料”意涵为考察的起点,联系其在法文、古英文中的意指,对“文化”一词词义持续复杂的演变进行辨析。他指出在所有的早期用法中,“文化”都是一个表示“过程”的名词,意指对某物(尤其是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雷蒙·威廉斯还发现,16世纪初,“文化”通过隐喻,由“照料动植物的成长”延伸为“人类发展的历程”。他认为18世纪后“文化”意指主要有三类: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随后,雷蒙·威廉斯又通过对“文化”在德文、北欧语言与斯拉夫语系中的人类学用法及对相关衍生词Cultivation(耕种、栽培、教化)、Cultivated(被耕种的、有教养的、优雅的)的检视,指出其意义的复杂与变异彰显了思维观点的差异、暧昧或重叠,包含了有关活动、关系与过程的不同观点,这种复杂性并不是在“文化”这个词语中,而是在这些不同的含义所呈现的问题中[3](P92)。可见,雷蒙·威廉斯不是把“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东西,而是在历史的动态发展和词义的复杂演进中认识“文化”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这也充分体现了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立足点与编撰理念。
其二,“关键词批评”具有隐在的体系性。
从显性层面看来,“关键词批评”似乎缺乏严密的体系性。其实,如珠玑般散落着的一个个关键词自成系统,其后潜隐着相应的理论脉络,构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结式”批评。这些关键性词语决不是一颗颗孤立地散发炫目光芒的星星,而是如雷蒙·威廉斯在进行关键词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特定词汇与另一些词汇构成了一个“星座”,进而彰显出该词汇所具有的复杂意义。譬如,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一词与“阶级”、“艺术”、“工业”、“民主”所产生的关联性就不是仅限于思想层面的,而应扩大到历史的层面。[3](P13)雷蒙·威廉斯自言在撰写《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一书时,一直希望能够设计出一种清晰的阐述方式,以使一些特别的词汇在其分析中能够表现出内在的复杂关联性。他也曾考虑过按学科、主题等方式编写,但发现这种模式在呈现出词汇某一方面关联性的同时,又会相对遮蔽在其他方面的关联性。雷蒙·威廉斯以Realism(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为例,认为如果把它置放于文学主题类词汇中,会凸显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意指,却不易显现其在哲学、商业及政治上的意指。[3](P25)最后他还是决定以按照所涉及词汇首个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为众多传统辞书采用的编排方式,但他特别在每个词条后面以“互相参照”(cross-reference)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词汇之间的相互比较和内在关联。此外,在具体阐析某一语汇词义时,雷蒙·威廉斯还往往联系相关语汇进行延展性释义。如在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词条中,雷蒙·威廉斯就强调了它与Art(艺术)、Subjective(主观的)、Utilitarian(功利的)的联系与区别,并在词条末尾以“互相参照”(Cross-reference)的方式列出了Art、Creative、Culture、Genius、Literature、Subjective、Utilitarian这7个相关词汇。因此,“关键词批评”并非像其表面形态那样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术语并置串联而成的,而是具有隐在的体系性。雷蒙·威廉斯以这些关键词为“结点”勾连了相关层面的问题,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辐射作用,提纲挈领地勾勒了所涉及批评对象的整体状貌,在以散点透视的形式微观解剖批评对象的同时,又巧妙地进行了总揽全局的俯瞰式批评。
其三,“关键词批评”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
由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偏重于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解读文化与社会语汇,以致有人批评他把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渗透到对关键词的解释中,充满党派之见。其实,这与他本人的阶级出身、政治立场、理论渊源均有极为紧密的关联。出生于劳工家庭的雷蒙·威廉斯,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即投身于成人教育事业,关注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面临的社会、经济、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并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雷蒙·威廉斯曾加入由牛津大学一些社会主义教员负责的“工人教育协会”,《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即他在“工人教育协会”授课时与学生讨论后的结晶。雷蒙·威廉斯还积极参与为工人阶级和民众争取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现实斗争,支持并推进激进的民主政治运动。雷蒙·威廉斯的家庭出身背景、丰富的社区生活经验、长年从事非学院式的大众与成人教育的工作经历及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斗争实践,均为其进行包括“关键词批评”在内的文化理论探索和研究夯实了现实基础。就理论渊源而言,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思想虽受到F.R.利维斯的直接影响,但他最终实现了对利维斯的文化至上论和精英文化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秉持平民立场的雷蒙·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精英文化”,而是被共同占有、平等参与创造和共同控制的“共同文化”——既能被社会中的精英所理解,也可以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雷蒙·威廉斯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姿态和民主思想,力图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进行探析和批判,强调理论研究对社会实践的干预性。在1974年升任剑桥大学戏剧学院教授后,雷蒙·威廉斯仍然在剑桥大学这一学术权威中心,以其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向精英文化固守的阵营发起挑战。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如果细细品味我几乎所有的著述,你就会明白我一直在批驳我所指向的英国官方文化。”[10](P2)
雷蒙·威廉斯直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对词义的评论并非不持任何立场,并以《牛津大辞典》为例,指出辞典的编纂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样“不具有个人观点”、“纯学术性”、“未含主观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而是可以“洞悉编辑们的意识形态”。[3](P18)不过,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并未直接彰显个人立场,而是如上文所举“标准”词条一样,在对词义的细微辨析中暗含针砭。陆建德以雷蒙·威廉斯对“福利”(Welfare)词条的释义为例,指出其结尾所言“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这个词汇出现在1939年,它有别于战争国家(the Warfare State)”,就巧妙地通过“Welfare”与“Warfare”这两个头尾押韵的词语的对照,婉曲地讽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削减福利待遇的那些政界人物有1939年二战爆发时纳粹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之嫌疑,有力地抨击了撒切尔夫人及其追随者。[8](P5)“关键词批评”是雷蒙·威廉斯政治追求、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交互影响、逐渐发展的结果,他通过意义与语境的探讨,在现实的关系、社会秩序结构及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揭示意义与关系的多元化与多变性[3](P22),寻绎这些关键词意义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异变。
雷蒙·威廉斯主张概念的意义与鲜活的理论活动、阐释实践密不可分,其“关键词批评”所具有的反辞书性,昭显了开放的批评理念与充满学术张力的思维特点。他通过关键词钩沉这一写作模式,对文化与社会的关键性词语进行历史语义学考察梳理,并结合其生成语境、基本涵义及在批评实践中的发展、变异,揭示隐身于词语之后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性。我们在充分认识“关键词批评”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关键词批评”萌生之初即与政治视角紧密相连。雷蒙·威廉斯视词语为社会实践的浓缩、政治谋略的容器,注重在语言的实际运用、意义变化中挖掘其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然而,政治视角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要谨防政治视角从“一维”成为“唯一”。
注释:
①此书原名为《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Andrew Bennett,Nicholas Royle.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Theory,London:Pearson,1995),中译者鉴于此书以关键词的形式架构全书译作《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