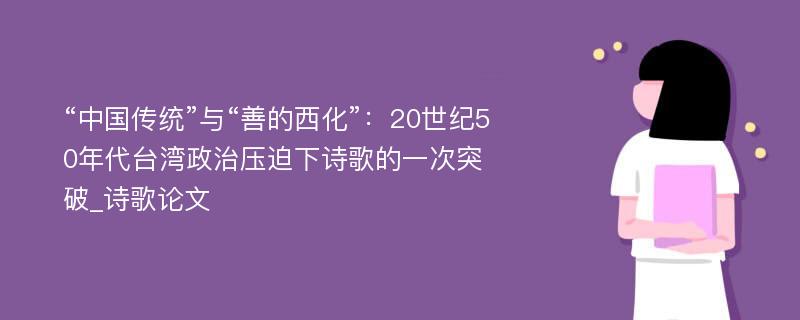
“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1950年代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6-0042-08
关于1950年代的台湾诗歌,有这样一组数字值得关注:1950年代台湾出版的诗集有171种,1960年代233种,是个并非歉收的时期。其中蓝星诗社37种,创世纪诗社28种,现代诗社33种,其他诗社和个人自印的诗集约有三四十种,超过诗集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诗歌评奖情况也值得关注:1950年起,张道藩主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每年“五四”和11月孙中山诞辰两次评选短诗、长诗奖,很难避免反共意识形态的影响;但1955年端午诗人节开始评选新诗优秀作品和1957年成立的“中国诗人联谊会”编选诗集,则带有较浓郁的文学民间色彩了,余光中、白荻、林泠、向明、洛夫、罗门、痖弦等青年诗人由此脱颖而出。1950年代有影响的诗刊《新诗周刊》(1951)、《诗誌》(1952)、《现代诗》季刊(1953)、《蓝星》周刊(1954)、《创世纪》(1954)、《南北笛》诗刊(1956)、《今日新诗》月刊(1957)等基本上是民间诗社和诗人所办,尤其是《蓝星》、《现代诗》、《创世纪》三大诗刊几乎“一统”了此时期的台湾诗歌,而其内部有着多种诗歌创作实践。这种情况提醒我们,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存在着政治性“战歌”、“颂歌”外的多种文学民间空间。事实上,1950年代的台湾诗歌是同时期中国诗歌中成果最丰盛的(谢冕先生在2008年澳门大学“第二届汉语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谈到,他主持编选“中国新诗大系”,1950年代卷入选的诗中台湾诗歌居多)。这种丰富性中,“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是两个最值得关注的诗歌空间。
1952年余光中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时,梁实秋著文称赞《舟子的悲歌》是“一本兼容旧诗和西洋诗的新诗集”①。“兼容”而成“新诗”,不仅是余光中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1950年代台湾诗歌在政治压抑下突围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在诗人各自的创作实践中慢慢形成,不仅使“五四”后的新诗传统得以延续,而且弥补了新诗的某些缺失。这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1950年代尤为珍贵。
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颂歌”和“战歌”占据“主流”,其中一些作品被看作“感情深至,意向真切”而得到传布,如获1957年诗歌奖的《革命之歌》(邓滋璋)赞颂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如一粒种子/虽被久久地埋在黑暗的土中/微小的生命仍鼓舞着向上的意志/冬天踩遍,依然不死/只等春雷来引发暴动,如一场革命/然后去更新地面的风景。”王禄松1956年获诗歌奖的《栖霞山》被看作“意象活泼雄壮”:“是满天彩霞飞来山上做红叶,/还是满山红叶飞向天边做彩霞?/当我挟着斜阳,迈上山冈,/我的诗心被熊熊的叶火,煮得十分斑斓。/是一抹斜阳煮熟了万顷红叶,/还是无边红叶煮熟了一颗斜阳?/当我们披着明霞的金缕衣,步上山冈,/我的歌风,把红叶吹起像火蝶飞扬!”这些“颂歌”、“战歌”虽有想像、激情,却难以摆脱“战斗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深刻反映出台湾1950年代的文学危机。
与此同时,“五四”后新诗的传统仍在台湾诗坛顽强展开着。1956年覃子豪(蓝星诗社)和纪弦(现代诗社)的论争、1959年苏雪林和覃子豪等的论争围绕“中国传统”和“现代西化”展开,正是“五四”后新诗传统在台湾1950年代环境中的不同展开。覃子豪1930年代在北平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和日本东京中央大学,诗艺视野较开阔,抗战期间所出诗集《自由的旗》和《永安劫后》已经走出个人苦闷世界,表现民族苦难和觉醒。1950年8月他在台湾花莲写下《追求》一诗,诗人面对落日西沉的茫茫大海展开的想像,既有特定年代的不懈追求,又有不甘于生命沉沦的感叹;既有现代意象象征意味的多义性,又会唤起项羽、荆轲等的古典想像。看重“自由的创作”和“诗艺的本质”,表现生命力的内涵更是覃子豪诗歌坚持的追求,1951年他和诗风一向“温柔敦厚”的钟鼎文(其诗在1930年代就受到王任叔的高度评价)在《自立晚报》出版《新诗周刊》,1954年移至《公论报》更名《蓝星周刊》,蓝星诗社因此问世。此后,覃子豪对台湾新诗运动出力甚大,被称为“诗的播种者”。纪弦1930年代在上海就与戴望舒、徐迟等合资创办《新诗》周刊,所出《行过之生命》等三本诗集已享有30年代现代派诗名。抗战期间,他留居上海,成立诗领土社,出版《诗领土》杂志和“诗领土丛书”,在战时沦陷区延续了战前现代派的艺术脉络,他此时的《夏天》等七种诗集也坚持“纯诗”立场,强调主知倾向。1948年纪弦到台湾,担任中学语文教员的他依然钟情于现代诗艺,1953年主办的《现代诗》季刊和1956年发起的“现代派”都反映了他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歌赋”的“成就好比一座既成的金字塔”,现代诗“要在另外一个基础上,建立一座千层现代高楼巨厦”②的信念出发,努力倡导现代主义诗艺。苏雪林这一“五四”文学宿将也是从对1920年代的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评价出发来批评台湾1950年代的“现代派”诗潮的。所以他们之间的论争正是“五四”后新诗传统的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论争是根植于1950年代台湾诗坛的现实土壤的,例如覃子豪在与纪弦的论争中就强调现代诗要注重“自我”的即“民族”的主体性,而针对苏雪林对台湾现代诗的批评,覃子豪则指出,台湾的现代诗不但与中国大陆李金发、戴望舒等的象征诗有很大不同,也与法国象征派诗歌有很大差异,它是一种融合了许多新影响之后的“综合性的创造”③。这一见解中包含了台湾现代诗蜕变的本土实践,它有可能日后使台湾外省籍和本省籍诗人的现代诗艺努力合流。而在1950年代,它起码表明了,台湾现代派诗社的努力是在政治压抑下的文学突围,而这种突围在诗人个性的创作中有了丰硕的收获,其中的经验值得关注。
1955年,郑愁予在他的第一本诗集《梦土上》的《后记》中说,“无所为而为”是其诗作的“主旨”。后来,他解释这“无所为而为”是一个“单纯的诗人”的“气质的原生”,“一方面他(她)不会优游于世外,因为其内心无一刻不在关切人类的状态——性灵的,文化的,欢乐以及苦难的——且时时引为创作的原生力;另一方面他应该不会在意自己名声与利益的增长”④。1950年代的台湾,官方对文艺不仅有压制,也不乏诱惑;而“退居”台湾的作家,就其人生阅历的背景而言,很难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直接构成对抗关系。这种情况下,“无所为而为”的“气质”对诗人是一种自救,而“中国传统”和“现代(善性)西化”就是台湾诗人艺术生命的自我“救赎”。
离散的历史命运、孤岛的隔绝境遇,在国民党政治、军事溃败的背景下影响着台湾诗人的创作心态。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沧桑感、时间流逝感、命运无常感等既应和此时诗人心境,又能使其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制约。郑愁予能在1954年写下《错误》这首日后半个多世纪流传甚广的诗作,就在于他将“国之大殇,乡之深愁”处理成浪子想像中母亲恒久的期待,一种在时间流逝中更真切的“对大自然‘仁和’的体念”,在婉约蕴藉的意象、轻灵自由的节奏、一波三折的想像、朦胧迷离的意境中表现得富有意味。正是“自幼就怀有的一种流逝感”,且“与诗俱来”⑤,无形中主宰了他写诗的一切,使他得以摆脱那个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阴影。例如《小站之站——有赠》一诗,写“一如旅人的梦是无惊喜的”年代,“两列车相遇于一小站”,车窗两两相对,偶尔有人“落下百叶扉”,“会不会有两个人同落小窗相对/啊,竟是久违的同志/在同向黎明而反向的路上碰到了”(后来作者将诗中“同志”一词改成“童侣”)。这一题材隐约可见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渗透,然而,诗人将这不早一分,不晚一秒,不前一步,不后一寸,恰恰在久远而开旷的时空中的相遇呈现于“风雨隔绝的十二月,腊末的夜寒深重”中,“小站之站”就成了刹那之时、咫尺之地的生命喜悦的象征,《小站之站》也就弥漫出浓重的生命无常感。而在《梦土上》中,更有许多表达生命漂泊感和时间流逝感的诗句:“我自人生来,要走回人生去/你自遥远来,要走回遥远去”(《小河》);“我不愿是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石人”(《偈》);“你当悟到,隐隐地悟到/时间是由你无限的开始”(《崖上》);“生命本是一窗/一燕飞过,一壁虎爬过/一瓣因我而悴的春花落”(《远景》);“终有一次钟声里,终有一个月分/也把我们静静地接了去”(《钟声》),人生的漂泊中不断感悟日常琐事蕴含的心灵的漂泊。郑愁予到台湾发表的第一首诗《老水手》(1951)就表达了生命的流逝感:细雨黄昏中,一位上岸来的老水手,“不过是/想看一看/这片土地/这片不会浮动的屋宇”,由此却“翻起所有的记忆”。郑愁予诗的时间流逝感接通了中国文化传统,也通向“佛理中解说悟境的‘无常观’了”⑥。当这种“流逝感”、“无常观”成为诗人心灵历程的一种深层沉潜,其诗作就突破了1950年代在由战争政治对峙造成的海峡隔绝中孕发出的“乡思乡愁”,而包孕起浪子生涯对生命的真切体验。“中国传统”就是这样使诗人走出战后台湾“战斗”年代的政治阴影,后来《郑愁予诗集》成为惟一入选“影响台湾30年的30本书”的诗集,又在“台湾经典30部”的书单中名列诗类“前茅”,为好几代台湾读者所喜爱,甚至许多迁居国外的中国人带着《郑愁予诗集》去国,“就像带了一撮家乡的泥土”⑦,大概都是因为郑愁予对“中国传统”有深刻感悟吧。
从楚辞、史记到三国演义、红楼梦,中国文学沉积下充满人世苍凉感、历史沧桑感、命运无常感的传统,这种文学境界在1950年代的台湾文坛具有特殊的救赎力量,它使台湾作家,尤其是大陆赴台作家摆脱特定年代的政党、阶级意识来看待国共战争后的台湾局势、历史恩怨,有的作家甚至由此“脱胎换骨”,从家国的变迁、个体的脆弱和不可知中体悟到民族文化传统的恒久,求得自身求生意志、灵魂感应能力与文化母体的永恒合一。这种“脱胎换骨”是作家自身艺术生命蜕变的结果,又足以抗衡种种外部压力,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压力对于创作的异化。
郑愁予是随家人迁居台湾的,而对于那些自身就是国民党军人等身份的诗人而言,突破“国家”意识形态的拘囿更为困难。此时东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成为对政治“现代性”最有力的抗衡。蓝星社的周梦蝶随国民党青年军到台湾,从军12年。他在军中开始诗歌创作,却崇拜庄子,以“梦蝶”自命,其作品构筑了一个诗禅合一的艺术世界。他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1959)所收诗作大都写于军中,《孤独国》一诗言:“这里没有文字、经纬、千手千眼佛/触处是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这里白昼幽阒窈窕如夜/夜比白昼更绮丽、丰实、光灿/而这里的寒冷如酒,封藏着诗和美/甚至虚空也懂得手谈,邀来满天忘言的繁星”,无念、无界、无相,这些禅宗美学的基本意涵,成为“诗和美”的源泉;而那种“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的境界成为周梦蝶最独特的诗境。“宇宙至小,而空白甚大/何处是家?/何处非家?”(《绝响》);“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无尽上/无尽在我刹那生灭的悲喜上”(《摆渡船上》)……这些诗句无不闪现东方的睿智和玄妙。《孤峰顶上》写“你”从“静寂”开始,在“雪花”和“春雷”的点化下,心便化蝶“进入永恒”,“踏破二十四桥的月色(典出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笔者)/顿悟铁鞋是最盲目的蠢物!”,不再“日夜追逐着自己的影子”。这种“无往”的诗境足以使诗人在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环境中不痴迷,不失足了。
周梦蝶的诗作是个“孤独国”,但并非回避现实,只是诗人从其信奉的中国传统哲学出发,以自身的确切体验去折射现实世界,这种主体性的发挥使诗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都呈现为诗人的内心体验,而诗人诗禅合一的内心足以筛洗掉现实的假象,他的《孤独国》是1950年代中国历史和台湾现实的个人化表现。
至于如“创世纪诗社”这样的“军中”诗社(该诗社由张默、洛夫、痖弦等军人于1954年“双十节”在左营成立),其集体背景更制约了创作。事实上,《创世纪》发刊词《创世纪的路向》提出的三项主张中有“彻底肃清赤色黄色流毒”的楬橥,该刊第4期也响应台湾当局“积极推展的战斗文艺”而刊出了“战斗诗特辑”。但后来“创世纪诗社”成为台湾新诗史上历时最久、活动最活跃,影响也极大的诗社,原因在于它的变化。《创世纪》早期就提出了“建立新民族诗型”的主张,强调“民族新诗”要担负起“培养民族生机,唤起民族灵魂”的使命,要表现“我国文学高度美”,也要继承中国“白话文学的血统”⑧。这种“新民族诗”固然展现中国诗歌的美学境界和东方民族生活情趣,但其诉求的民族意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却可能配合宣扬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宣传政策。从早期《创世纪》所刊诗歌看,也确实难以逃脱这种拘囿。在这种境遇中,西方现代主义成为文学突围的方向。
在战后台湾文学史中,“现代主义”始终具有革命性意义,1950年代的现代诗潮,1960年代初期的现代小说潮,1960年代中期的现代文化思潮,一波接一波地冲击了台湾社会的专制文化、僵化政治、保守心理、愚昧习气。“现代诗社”是1950年代台湾诗坛最早倡导现代诗潮的,这个诗坛的成员其实“大多对现代主义的本质与精神无深刻之体认,在气质和风格上彼此尤不相洽”⑨,他们之所以聚合在一起,是借助于现代诗潮“替新诗坛打破政治主宰一切的思想控制,也争取到若干程度的自由创作空间”⑩。三大诗社中,“创世纪诗社”的“现代转型”最有影响,甚至使它“自1960年起,成功地取代了‘现代诗社’和‘蓝星诗社’在台湾新诗历史上原有的地位,而成为此后台湾新诗坛里‘西化’的代表”(11)。
前述“创世纪诗社”的“军中”背景正是在现代诗艺的追求中转化为诗的“世界性”、“纯粹性”背景。早期“创世纪诗社”在其话语表达还难以摆脱“战斗文艺”影响时就“不能苟同那些没有诗素,没有思想,没有通过艺术形象,而只喊口号,空发议论”的所谓“诗”(12),之后也坚持“反对粗鄙堕落的通俗化”,“反对离开美学基础的社会化”,“反对三十年代的政治化”(13)。这种民间诗社对诗艺的自觉追求让他们把眼光自然投向现代主义诗潮,使得他们的军队题材创作也有了深刻变化。“创世纪”“三驾马车”之一的痖弦1951年开始诗歌创作,1965年息声诗坛,1957、1958年是他诗作最丰饶的年份。《上校》一诗写抗战时期的骁将来台湾后穷困的暮境:“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自火焰中诞生/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1943年//他曾听到历史和笑//什么是不朽呢/咳嗽药刮脸刀上月的房租如此等等/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从抗日战地的残疾,到战后贫微的日常生活,两个戏剧性场景的多重对比,在口语运用和叙述语言的再造中建构起特定气氛不断加浓的意象空间,在“不朽”引发的反讽意味中传达出军人面对历史和人道的双重陷落的哀怨愁绪。这里的记忆塑像充满了历史忧伤和人生无奈,但没有一点政治意识形态的诉说。
作为军中诗人,痖弦高度警惕于坠入政治文学的陷阱,使“自己头上的桂冠拆得一叶无存”,所以,他一直强调“诗,究竟不是一面战旗”(14),他的诗作追求“可感”而“不可解”(15),这就使得其诗作充盈感性的真实而避免了清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侵入。《深渊》(1959)是首近百行的抒情诗,纷沓而至的都是怪诞的黑色意象:“肉体展开黑色的节庆/在有毒的月光中,在血的三角洲,/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扑向一个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额头”,“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在两个夜夹着的/苍白的深渊之间”,“在鼠哭的夜晚,早已被杀的人再被杀掉。/他们用墓草打着领结,/把齿缝间的主祷文嚼烂”。这些“深渊体验”以一种整体性的象征呈现了一个人鬼相杂的世界,而又不具体指向什么,令人震栗的真实传达出人性的麻木、堕落和社会的黑暗、荒诞像深渊一样难以逾越,让每个人都会“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幸”,真实丰富的感性转化为一种生命的诗意,省思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知性也由此立足于真实的感性。
现代诗潮的世界性、反省性使这些“军中”诗人对战争的思考获得了一种人类性视野,12岁就进空军幼年学校的罗门一直以“战争”作为他新诗的主要题材。虽然他大部分战争诗写于1960年代,但他1961年写的《麦坚利堡》(该诗获菲律宾马可仕金奖,罗门也由此被称为“战争诗的巨擘”)能超越阶级战争、民族战争的立场,视战争为“人类生存困境”(16),在人类悲悯、人性抚慰的层面上审视战争,并逼近了人类终极命运的拷问,的确是他1950年代跻身于台湾现代主义诗派的结果。这种战争叙事的突破在1950年代更有其意义。
罗门还是台湾城市诗的重要奠基者,被称为“中国现代人中经营都市意象迄今历时最久、成就最丰硕的一位”诗人(17)。1950年代至1960年代,台湾的现代城市问题并不明显,但浸淫于现代主义的罗门已经敏感到都市文明进程中人的物化、异化。1958年,罗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曙光》,其中《城里的人》是他都市诗的开山之作,表达了他对城市中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同情、关怀。1961年前,他就发表了大量都市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对都市悲剧性存在的剖析,而象征都市生活的“十字街头”和作为救赎喻象的“十字架”的结合往往构成其思维指向。长诗《都市之死》的题记“都市你造起来的/快要高过上帝的天国了”就隐含了“十字街头”和“十字架”的“对峙”,全诗五章也处处呈现出这种“对峙”:“礼拜六人们经过六天逃亡回来/心灵之屋经牧师打扫过后/次日又去闻女人肌肤上的玫瑰香/去看银行窗口蹲着七个太阳”;“都市挂在你颈项间终日喧叫的十字街……/教堂的尖顶吸进满天宁静的蓝/却注射不入你玫瑰色的血管”,“十字架”也最终沉沦于“十字街头”的狂乱中。这些都从都市沉浸于官感肉欲的生活截断了人和自然的联系,也隔绝了人们精神的沟通中写出了都市的沉沦,裸露出人类无法克服自我脆弱和难以抗拒环境宰制的悲剧性挣扎。
1950年代台湾诗坛现代诗潮极有意义的是其内部有着种种分歧乃至不同的流脉。现代主义独立的思想姿态本来已跟当局的文化政策构成对立,而各现代诗社之间,同一诗社内部时有不同的创作实践,对现代主义理论时有修正,由此表现出来的对峙、争论以及各自的变化,呈现的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上的成熟形态。
“创世纪诗社”从“民族新诗型”转向现代主义诗艺,选择的是超现实主义。在这一选择中,洛夫的创作最值得关注。这位被称为“诗魔”的“军中”诗人1949年赴台时,行囊中军毯一条、冯至及艾青诗集各一册。洛夫是1958年写作《我的兽》开始显露其实践超现实主义的个性,就是说,他是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选择超现实主义的。洛夫看重超现实主义,当然也看重其突破认知的固有模式,去体悟“人在跳开既有‘实相’的观察时,有另一种甚具创造性的观照”(18),但他更是从自己的艺术本性上去理解超现实主义。洛夫一直相信潜意识是“人的最纯粹、最真实”(19),“也是最充沛的一部分”(20),才接受超现实主义,力图在跟潜意识的直接“对话”中,以“完整的呈现内心世界”来实现诗的“纯粹性”。这种努力使他在金门炮战题材的组诗《石室之死亡》中实现了超越性观照。当洛夫从形成、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去接受超现实主义时,他不断从自己原先熟悉的中国古诗中发现了“超越人类的实际经验”却又在“情意之中”的超现实主义。他说:“虽然我曾一度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后来通过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发展成我个人的风格时,已经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不一样了”,“我在中国古典诗中,特别是唐诗中,发现有许多作品,其表现的手法常有超现实的倾向,不仅是李商隐、李贺,甚至包括李白、杜甫的作品,都有介于现实与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以宋朝严羽的说法,这就是妙悟,或无理而妙,也可以说是诗的言外之意”,“所以后来干脆我从我们老祖宗所走的路线——妙悟的路线——中去发掘诗的奥义,然后通过不断的实验去追求前人未曾试探过的路子。”(21)这样,洛夫感悟到了中国古诗中“使无情的世界化为有情的世界”,“使有限的经验化为无限的经验”,“使不可能化为可能”的“超现实”(22)的丰富资源,从而对法国超现实主义有了修正和超越,并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产生了高度崇敬:“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到宋朝,已至化境,故多妙悟之论。那些突破语言限制与理性障碍的透辟之言,实有助于我们对诗本质与结构的了解。”(23)中国文学的传统理论成为对现代理性的反思、批判,这一思考开始于1950年代台湾诗坛的现代诗潮中,到1970年代已相当成熟,实在不应该湮没。洛夫的创作实践在1950年代的台湾诗坛具有某种普遍性,那就是从“西化”起步而“回归”传统,“中国传统”和“现代(善性)西化”的沟通是1950年代台湾诗歌留给后世的最好启示。
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余光中从1950年代开始的思考最值得关注。前述余光中是从“兼容旧诗和西洋诗”开始诗歌创作的,其早期诗作浪漫抒情,较接近“新月”徐志摩格律派的形式。1958年,余光中写下了他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现代诗《西螺大桥》,借台南浊水河上那座“钢的灵魂醒着”的大桥,表达了各种力交接、叠合、咬紧而成强者的思索,表达了“渡河”,异于己而成生者的感悟,他由此称“我的灵魂也醒了”。从1958年起,余光中三度赴美,广泛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但又回台湾本土创作,他把自己的这种经历称作“善性西化”:“守家的孝子也许勉可承先,但不足以启后;出走的浪子承的是西方之先,怎么能够启东方之后;真能承先启后的,还是回头的浪子。浪子回头,并不是要躲回家来,而是要把出门闯荡的阅历,带回家来截长补短。”(24)他从美国诗人佛罗斯特(余光中总对别人讲,别人的缪斯是女性,他的缪斯是男性的佛罗斯特)的创作中领悟到用“现代”提升“传统”、用“传统”拓展“现代”的思路:“他是现代诗人中最美国的美国诗人”,但“他的区域情调只是一块踏脚石,……他的诗乃往往以此开端,但在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行若无事地,观察泯入沉思,写实化为象征,区域性的扩展为宇宙性的,个人的扩展为民族的,甚至人类的”,“他的诗体恒以传统的形式为基础,而衍变成极富弹性的新形式”(25)。这种“善性西化”“主张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对传统进行再认识、再估价、再吸收的工作”(26),又将“今古对照”视为“生完了现代的麻疹”而获“免疫”力,由此而“脱离狭义的现代主义”(27)。就是说,先从中国传统中走出来,去西方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接受洗礼,不仅为了获得观照传统的参照,而且为了拓展源头的活水,“中国诗的现代化”和“现代诗的中国化”成为“共同促成中国的文艺复兴”(28)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思考开始于1950年代后期显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不断革故鼎新中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动态沟通的努力,表明台湾诗坛开始借助于“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两翼力量来推进台湾诗歌的创作实践,已经不单单为了抗衡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而是真正着力于台湾诗坛的自身建设。
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是1950年代台湾诗坛争论的焦点,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现代中国的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29)但对于文学而言,作家具体的创作实践提供的个人经验远比理论争论得到的共识更有意义。正是这种经验的丰富让1950年代的台湾诗歌为后世关注。当年,向明(蓝星社)宣言:“我视理论如敝屣,绝不跟别人的笛音起舞。”(30)罗门的“第三自然”理论强调用诗人精神活动的深度来同构原始的田园自然和人类自我高度发展的都市自然。这些追求都是注重用个人经验来沟通传统和现代。所以聚合在“现代诗”旗号下的台湾诗人即便在同一命题上也往往显示出不同。例如羊令野、覃子豪的诗跟周梦蝶、洛夫一样有“诗禅合一”的追求,但羊令野从旧诗起步的创作经历使他的现代诗更灿然如从传统中走出,古典的精神和传统写意的手法结合表达出现代社会世俗享乐中的人生超脱和审美超越;而覃子豪则是在经历了创作的多种探求后,最终在他1950年代后期的诗作中完成了由情到灵到禅的过程,体物悟性见佛禅成为诗的诞生过程。因此,今天我们关注19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潮,恰恰要关注其中的个人化追求,这甚至关系到日后台湾诗坛的走向。
“现代诗归宗”是1950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的趋势,“创世纪”发起人张默自述经历过的“歌咏海洋的浪漫时期,拥抱现代主义的实验时期,回归传统的反省时期”(31)在许多台湾诗人创作中都发生过。但一种文学向传统回归时往往会出现以松弛跟现实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为代价的价值偏移,这在1950年代更意味着文学跟官方政治的妥协。此时更需要诗人保持强烈的精神探求。商禽“创世纪”年AI写作下的《长颈鹿》、《用脚思想》等诗作之所以为后世传诵,就是在“拘禁”和“逃亡”的意象世界中表达了“身”、“心”两分的剧痛和对思想自由的渴望。所以,余光中等之所以强调先走出传统,到西方世界经历风雨,再回到传统,就是希望在思想自由、行动解放中沟通传统和现代。事实上,余光中等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多次论争中对现实种种危机有着高度警觉,往往采取两面“开弓”的批判姿态。这使得当时台湾诗坛“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沟通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洛夫1958年经历了金门炮战,1959年开始在《创世纪》发表以此为题材的组诗《石室之死亡》,而在《石室之死亡·自序》中,洛夫有言:“超现实主义的诗,进一步势必发展为纯诗。纯诗乃在于发现不可言说的隐秘,故纯诗发展至最后阶段即成为‘禅’,真正达到不落言诠、不着纤尘的空灵境界。”这种既在人生层面又在艺术层面理解“禅”的看法,正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性特征。这样,洛夫将西方的超现实主义引向了东方的“禅”。而《石室之死亡》之意象来自古典意象群落,面壁破室之意也有其传统渊源,表达的生死观更缘自庄子的“齐生死”。《石室之死亡》在1970年代初就被选入多种英文版的中国现代诗选,一个重要原因是编选者认为它从潜意识出发开掘人性中神性与魔性的纠结,在生命的放逐感、孤绝感中有“存在的发现”,而实际上,正是将超现实主义引入中国禅的努力才使得《石室之死亡》在人类哲学的开阔背景上达到了人性和生命体验的深度。在现实政治对峙严重的1950年代,台湾诗人却往往有形而上层面的探求,其中的缘由还值得探讨。
1950年代初期,覃子豪写下过组诗《向日葵》,其中《向日葵之一》将诗比作太阳,诗人用自己真实的生命去完成太阳的形体,年老之时,诗人剖开自己的胸膛,将一生心血的果实,一粒粒撒播在大地上。这种献身缪斯的精神是台湾诗人所共有的主体精神,是台湾诗坛在政治高压的1950年代得以播传新诗种子的最重要的动力。“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正是这种艺术精神的时代结晶,它们最终使1950年代成为并非诗歌歉收的年代,并揭示了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建构。
注释:
①引自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②张堃专访纪弦:《从“横的移植”谈起》,《创世纪》第122期,2000年3月。
③覃子豪:《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自由青年》第22卷第3期,1959年8月。
④⑤⑥⑦郑愁予:《郑愁予诗的自选》,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7,9,3,9页。
⑧王岩:《谈民族新诗》,《创世纪》第4期,1955年10月。
⑨洛夫:《中国现代诗的成长》,《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第3页。
⑩(11)张双英:《20世纪台湾新诗史》,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144,228页。
(12)本社:《诗人的宣言》,《创世纪》第4期,1955年10月。
(13)本社:《请为中国诗坛保留一份纯净》,《创世纪》第37期,1974年7月。
(14)(15)痖弦:《诗人手札》,《创世纪》第14期,1960年2月。
(16)罗门:《时空的回声》,台北:德华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17)林燿德:《罗门论》,台北:台湾师大书苑,1993年,第64页。
(18)简政珍:《创造性的理论》,《创世纪40年评论选》,台北:创世纪诗社,1994年,第3页。
(19)(22)黄宝月:《煮茶谈诗访名诗人洛夫先生》,《心脏诗刊》1987年第1期。
(20)(21)《联合文学》编辑部:《因为风的缘故——午后书房访洛夫》,《联合文学》第50期,1988年12月。
(23)洛夫:《与颜元叔谈诗的结构与批评》,《中外文学》第4期,1972年9月。
(24)徐学:《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第128页。
(25)余光中:《死亡,你不要骄傲》,《左手的缪思》,台北:文星书店,1963年,第71-73页。
(26)(27)余光中:《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76,277页。
(28)余光中:《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第299页。
(29)痖弦:《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台北:天视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9页。
(30)张双英:《20世纪台湾新诗史》,第217页。
(31)张默:《落叶满阶·自序》,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第3页。
标签:诗歌论文; 现代诗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台湾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覃子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