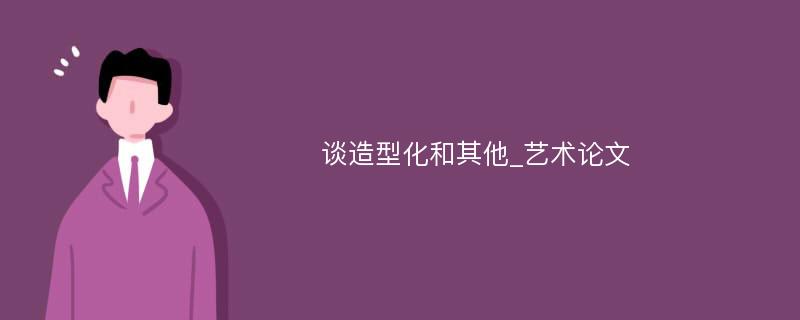
漫谈程式化及其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其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知从何时起,常见在批评某些影视作品时总爱用“程式化”、“脸谱化”这样的词,好像它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代名词。也有人把京剧的失落归咎于程式化。甚至有的著名京剧演员在著书立说时也说:“要程式,不要程式化”。最近在报刊上见到一篇评介新编京剧《风雨同仁堂》演出成功的短文,说赵葆秀的演唱:“没有一点程式化的痕迹”。且不说该剧中所唱的西皮二簧各种板式,即便有所创新也是程式化的,假如真的一点程式化的痕迹都没有,那还叫京剧吗?程式化怎么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大家探讨。
程式化认定 应该肯定,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堂堂正正的程式化艺术。不但京剧,中国一切传统艺术形式大都是程式化的。程式化造就了与西方写实艺术完全不同的中国写意的富于装饰性的艺术形式。西方采用写实手法,是因为他们把美的本质归结为物体外在的形,因此重在形似,是再现性的艺术;中国自古便把美的本质归结为神,创造了程式化的写意手法,属于表现性的艺术,所谓“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写实与写意,再现与表现成为交相辉映的东西方两大艺术体系。所谓脸谱化不过是京剧程式化在化妆方面的表现。它利用写意夸张和图案化的手法,创造出无数古代人物鲜活的艺术形象而活在人民群众中。谁让你把它用到写实的艺术中去呢?那不是程式化与脸谱化的错误。又何必非以中国戏曲的特色来比喻另类作品的缺欠不可呢?“鸟不解走,兽不解飞,两不相解,哪得相讥”,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君莫非》说得好。
所谓程式,就是准则、标准或规范的意思。《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在“京剧”条目下这样说:“京剧舞台艺术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锣鼓、化妆、脸谱等各方面,通过无数艺人的长期舞台实践,构成了一套互相制约、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它们作为创造舞台形象的艺术手段是十分丰富的,而用法又是十分严格的”。既然在文学、表演……等各方面都是有程式的,且十分“严格”,那么不是程式化又是什么呢?程式化本不是贬义词,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呢?
应该感谢我们的先人创造出程式化、脸谱化这一独特的表现手法,创造了独特的京剧的美。否定程式化无异于否定京剧,否定中国戏曲,甚至否定中国一切传统艺术形式。至于程式化的艺术如何顺应新时代,现代京剧与程式化的关系,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关系等等那是另外讨论的话题。
程式化基因 京剧的特点之一是综合艺术,它综合吸收容纳了许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而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几乎都是程式化和富于装饰趣味。京剧自不必多讲,且大略看看其它艺术形式的程式化表现,它们都是京剧的重要成分,是血脉相通的。
比如绘画:国画与京剧公认为国粹艺术。与西画光影造型、追求色彩、重在形似不同,中国画以线造型、讲究笔墨、重在神韵。以成就最高的山水画为例,古人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形貌的山体变化,规范出若干种用笔程式,如斧劈皴、披麻皴、荷叶皴等等,用不同的皴法表现山体的多石、多土、雄伟或秀丽等不同的特征,与京剧程式手法异曲同工。其最高标准不是“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等外在表现,而是形而上的“气韵生动”。大约15个世纪以前,南齐谢赫的论绘画六法就将其列在首位。例如人大会堂中《江山如此多娇》那幅画,画家并不重在画出具体的哪座名山或山峰,而在于表现祖国大好河山的整体气势和神韵。不用程式化的手法是无法表达这番境界的。西方写实的油画里还没见过一幅能把高山大河苍茫气势表现出来的风景画,因为它太写实了,太“科学”了,焦点透视只能画出固定角度所看到的大山局部,而任何局部都是有限的。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比如雕塑:无论秦俑汉雕,隋唐石窟造像,宋代彩塑以及明陵神道石人石兽,虽时代不同,风格各异,但与西方雕塑写实主义完全不同的写意装饰风格则一脉相承,有着一套人物造型的规范程式。民间艺人总结出来一句话说:“美人无肩、武将无颈”。按传统审美观点,塑造仕女要溜肩膀。京剧舞台上旦角即按此标准,古时女上衣没有接袖的,以此弱化双肩。不似现代女士,连夏天穿的短袖衬衫也需加以垫肩。塑造武将不能露脖子,方显得威武雄壮,寺庙中的金刚力士韦驮等塑像均按此标准。京剧花脸便吸收了这一程式,要穿厚厚的胖袄,造成“武将无劲”的视觉效果。相反丑角往往不要护领,故意露出长长的脖子,显得既可笑又寒碜。
舞蹈是人体造型艺术,几乎任何舞蹈都不是自然主义的,必然是装饰性和程式化的,这就使舞蹈能够在戏曲开始形成的时候自然地融和进去,成为戏曲重要的构成因素。一说戏曲原本来自古代歌舞,还有一种说法:我国的古典舞蹈自融入戏曲之后便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对于舞蹈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哀,但也说明戏曲艺术的博大包容性,它竟吞并了古典舞蹈。而我国舞蹈自汉代始便把武术、杂技等表演融合进去,这就给戏曲艺术开辟了广阔天地。京剧武打便吸收了许多武术和杂技的套路(程式),成为京剧精彩的一部分。这种程式化的“打把子”(还有脸谱),曾经被某些用西方眼光审视中国戏曲的人说成是落后和不文明的表演方式加以指责和讥讽。试想假如京剧没有程式化的武打,其剧目可能要删去一半。《长坂坡》、《挑滑车》、《三岔口》,用西方写实手法该怎么演?在西方歌剧或话剧舞台上常有双方比剑决斗的情节,以我们的眼光看来那打斗实在很简单,“不够一卖”。这样说并非比较谁优谁差,实因“卖点”不同,不能用一种艺术规律作为另一类艺术的参照系。还是元稹老先生说得好:“犬不饮露,蝉不啖肥。以蝉易犬,蝉死犬饥”。
文学和音乐是戏曲的根本,虽然都不是具象的,但在形式与手法上也都离不开程式。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是诗歌,第一部诗歌集是完成于近三千年前西周时代的《诗经》。与西方同时代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不同,它不是再现历史事件的叙事,而是表现性的抒情。中国的文学从来便与音乐结缘,诗歌有严格的格律规范,宋词和元曲就更是按一定的词牌曲牌制定。学习诗词先要掌握程式,所以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之说。京剧所以叫戏曲,是因为戏(文学)和曲(音乐)紧密相结合的,这是遗传的关系吧。
是否可以这样说: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是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重要手段。京剧是吸收了各种传统艺术的营养而诞生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它的体内自然蕴含着程式化的遗传基因,京剧是堂堂正正的,地地道道的程式化艺术。
程式化流变 当年梅兰芳先生访问苏联演出,非程式化的祖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很能理解京剧的的程式化表演。他的解释是“有规则的自由活动”,倒也深入浅出。自由在规范之内,个体寓整体之内,个性在共性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审美观和价值观的最高体现吧。我想,小到一场足球比赛,大到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不就是有规则的自由吗?
任何艺术程式也不是僵死的,再严格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变革、审美趣味的变化而变化。程式化确有可能造成一些人甚至一个时代的死板和僵化。那是个人的素质或时代风气使然,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这样的先例,但终究是会摆脱而向前发展的。
京剧的历史其实是很短的,还不到二百年。但它的发展和变化不能说不大。有老照片和老唱片留下可作比较的资料。听陈德霖和张君秋的唱,无论声乐和器乐都有鲜明的时代感,不可同日而语。至于造型,且不谈《中国京剧》每期封面戏画早期京剧人物的扮相,看看老照片,无论化妆、服装、形态,那感觉与今天有多大差异(至于现代题材的新编戏这里暂且不谈)。可惜当年没有录像,后来人无法看到表演,不管一些回忆录把过去讲得多么完美,就整体而言在程式化的各方面其改革发展和进步都是很大的。一代代有创造的演员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说到化妆,想起王树芳对老旦化妆的改革,她把老旦画漂亮了,虽然受到一些非议,我以为她是顺乎潮流的。过去唱老旦的都是男性,老旦戏又大都是开场戏,在化妆上就不那么讲究。现在老旦行均为女演员。想想戏校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谁不看重自己的形象,老旦不能像青衣花旦台上那么漂亮已觉遗憾,绝不愿把自己再画老丑,与男性老旦心态显然不同。何况老旦俊扮既符合京剧舞台上以美为原则,也并不脱离人物。如《打龙袍》中的李后、 《钓金龟》中的康氏, 算来也不过40多岁。如果说王树芳的改革是成功的,还在于得到年轻一代演员的效仿而流传下去,成为老旦化妆的新程式。
当然在改革尝试中也有不太成功的。比如曾看过一出新编战国时代的历史剧,剧中有一位大将军,其身分地位与屠岸贾相仿,也由花脸扮演,但没勾脸而像是揉脸,远看像黑风利似的,脏乎乎的,穿着如改良靠那样的服装,(也并非战国时代样式,又何必呢?)扮演者是位著名架子花脸,他演的屠岸贾十分精彩。这出戏可难为了他。大将军发威发怒发狠时,按老程式或掏翎子——头上空空的;或抓手袖——穿的是紧袖;或踢袍——下摆短短的;或撕扎——胡子是粘的,只剩下搓手和跺脚,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时我忽然悟到屠岸贾那扮相从头到脚都有戏,服装和化妆的程式是为程式化的表演服务的,即“互相制约”和“相得益彰”。放弃了旧程式,又没有新的可替代,只好“写实”。而真实的大发脾气又有什么好看的呢?原来京剧观众的艺术享受重在于欣赏程式美,内行的观众还要看个性化的流派美。没有这些,还不如看古装电视剧。
人们常说“京剧应该姓京”,就是说改革与发展需在程式化的大原则之内。假如你能够把共性的程式演出个性风格来,对传统的程式作出独家演释又能为观众所接受,哪怕是在唱念做打中有一个方面,甚至一方面中的一个点,你就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流派。京剧的发展可以说就是流派的发展,流派的发展就是个性的发展。是由一代代演员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渐变过程。不似西方变革那样剧烈和走极端。用梅兰芳先生的话说就是“移步不换形”,这是中国式的发展和变革。
北风也有转南时 多年来,不少人对程式化的京剧抱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观态度,称之为“夕阳艺术”、“博物馆艺术”。有的认为应让它自生自灭,何必死马当活马医,并不时为它唱挽歌。其实不然。事实证明,近年来京剧的大环境越来越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不会被世人抛弃的,世界文化交流越频繁越是如此。我们看到京剧锣鼓一响,便能把海峡两岸、港澳同胞、遍及全球的海外侨胞召唤在一起,这就是京剧的魅力,也是传统文化的凝聚力。中央领导人重视京剧并非缘于个人的好恶,那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倘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真的消失了或被哪个民族所同化,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存在价值。连北美的印地安人和澳洲的毛利人都拼命挖掘和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要从博物馆中走出来,我们凭什么要为京剧唱挽歌任其自生自灭呢!
我们抱乐观态度,并非幻想京剧会回到过去一统天下舞台的地位,或“文革”中全民唱戏的“盛况”,那并非正常的。今天的世界,一切都变得多样化。京剧(包括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仅仅是多元舞台世界中的一元。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也自有其存在价值。这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对京剧来说由一统天下到多元中的一元反差是大了点,因而颇感失落是可以理解的。京剧在国内是失去了部分观众,但它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得到众多的观众,这也是一种补偿和平衡。张别古说:“西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艺术的审美轮回其实也是这样。当西方写实艺术和它们的理论原则发展到极端时,那些崇尚自由的艺术家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最不自由的。许多要表达的思想靠写实是无法表现的。回过头来看京剧,很多表现手法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京剧程式化的虚拟手法以及时空观念反倒是自由自在的。他们对京剧这个老而新的东西越会有一份新的理解和兴趣。听说年轻的老旦演员郑子茹现在国外搞起了现代舞,并得到导演的赞赏,她以其京剧的功力和理解演来得心应手。东方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两极走到一起来了,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它说明京剧艺术本身蕴藏着许多东西尚待我们自己去再认识和开发。其实许多有见地的国内外人士都在下手了,而京剧有时反倒耽心自己的穷途末路。或许经过一段彷徨之后,随着东西方更多的交流,浮躁心态的逐渐沉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高,国内眼界大开的青年一代也将会比较而发现自己传统艺术的价值。历史总会给真正优秀的东西以再度辉煌的机会。
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一书序言中说:“如果世界上的艺术精华,没有客观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他的话有的不幸而言中。作为一个古都,北京的古建城门城墙被拆除不是一件不可挽回的损失吗?所幸的是古典京剧虽然在十年“文革”中险遭灭顶之灾,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现在社会处在大变革时代,也可以说是“趣味改向之时”吧,我们欣喜地看到各方面为保护京剧所作的努力。《中国京剧》98年第4 期“编后记”中说:“本刊自创刊之初就想在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上多为京剧振兴做一点实事,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义务”。特别强调了对京剧来说理论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客观标准”来保护京剧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