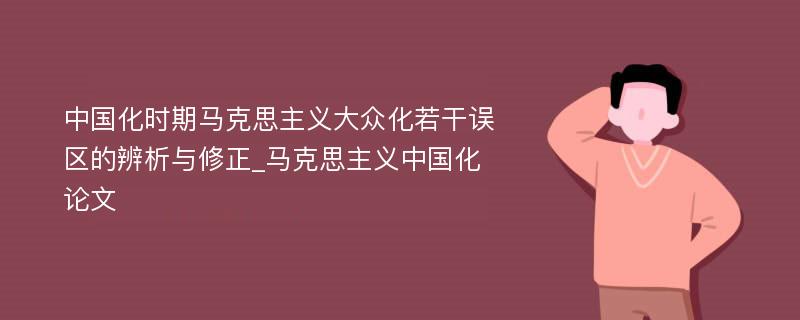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若干误区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误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应实现“中国化”,而非“西洋化”;体现“时代化”,而非“学院化”;走向“大众化”,而非“精英化”;回归“整体化”,而非“图谱化”;做到“民族化”,而非“民族主义化”;坚守“马克思主义化”,而非“相对主义化”。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洋话”不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参照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表述上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西洋话”。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说“洋话”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出现了迷恋“洋话”的倾向,“洋话”成为衡量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重要参照系。
迷恋“洋话”首先表现为以西方的流行话语解释马克思。西方的时尚话语刚刚登场时往往光鲜亮丽、光彩夺目,但大多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过是“五分钟的明星”,随后马上就归于沉寂,湮没无闻了。现代西方最时髦、最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话语不见得是最有生命力、最有真理权的话语,也不见得是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话语。用这些流行话语来解读马克思显然是不合适的,将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的流行话语粘连起来,将马克思打扮成时髦的“好莱坞明星”也是不合适的。把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匪夷所思的自我演绎,展开美轮美奂的自我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独特的内容在西方的流行话语中消解于无形,马克思搭建的学术舞台却让一群跳梁小丑在“演戏”,这些“跳梁小丑”喧宾夺主、自以为是的演出完全盖住了马克思的光芒,“马克思”却沦为了尴尬的龙套演员。
迷恋“洋话”还表现为用西方的时髦理论消解马克思。现在有些人迷恋西方的思想理论,将西方的地域性理论上升为普世性理论,将西方理论的特殊性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正因为有了西方学说的中介,马克思主义才得以顺利出场;正因为西方学术的担保,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当代在场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西方理论的裁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才有了切实的保障。
当前要深刻反省学术界存在的迷恋“洋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既向各个国家的实践开放,也向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开放,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向当代西方的流行话语和流行思潮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这就要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原则,坚守自身独特的思想内容,坚守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而不是无限度、无原则的开放;不是无所顾忌地向对方靠拢,也不是没有底线地倒入对方的怀抱,而是批判性地吸取对方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西方有西方的矛盾特殊性,中国有中国的矛盾特殊性,西方的话语在西方能用但在中国却不管用、不适用、不能用。将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话语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无条件地嫁接到中国,由于无视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特殊历史语境以及特殊的国情,恐怕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不少西方学者秉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将西方的选择作为我们的选择,将西方的模式作为我们的模式,将西方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将西方的思路作为我们的出路。我们不能落入西方的陷阱,跟随着西方的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独立的精神、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信,对西方的学术话语和发展模式展开前提批判,寄希望于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这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也是我们的文化权力。
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要说“大众话”,不能沦为少数精英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表述上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大众话”、“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贴近大众,而不是沦为少数精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
当前,理论界晦涩文风盛行,这种文风已经严重伤害了理论本身的亲和力、感染力,严重阻隔了理论通达大众的道路,也严重疏远了大众走进理论的距离。
任何理论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内容是思想的呈现,形式是内容的展开方式。内容好,形式不好,照样难称好文章。所谓形式好,关键就是文风要好,表达要好,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来就是要掌握群众,群众也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尤为重要。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明确反对“把哲学变为胡说”,他对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文风问题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他说:“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①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晦涩文风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文章越来越难懂。”②其实,德国古典哲学的开辟者康德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晦涩文风。康德哲学被举世公认为文风晦涩的典型代表,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也认为哲学研究应该是高深的,而表达应该是通俗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很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③20世纪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指出:“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④与此相反,我国少数学者偏好于使用高深的词汇表达浅显的道理.把清晰的东西说得让人如坠云里雾里,在貌似高深的烟雾之下掩盖着连篇废话。其实,绚丽的“学术包装”,生造的概念和术语都不能弥补思想的浅薄。学术的深度与思想的深邃无需通过“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方式来体现。理论创新离不开创新术语和概念,但这不是首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邓小平没有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这无损于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邓小平没有使用纯学术化的理论语言,但这无损于邓小平思想的深邃。邓小平理论用最精练的语言回答了最复杂的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回答了最深刻的问题,试想有哪部高深的学术著作能出其右者。
当前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文风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虽然要有个性,但绝不能变为学者个人自言自语的理论独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要尽量使用公共性的概念和术语,聚焦公共性的话题和问题,这样才能与大众产生心理共鸣,才能让人有“众里寻他”之感。淳朴的文字、优美的文笔、清新的文风同样能表达深刻的思想,热衷于生造概念和术语的人只不过是想以此掩饰文中没有“干货”的恐慌,期待以“一俊遮百丑”,然而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其实,朴实无华的文字并非苍白无力,如能揭示问题的真谛,直指问题的要害,同样可以彰显深邃的内涵和巨大的张力。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浅入深出是装学问,钻研得很肤浅,表达得很深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头重脚轻根底浅”,表面上有学问,实际上装高雅、装深沉、装学问,徒有虚名并无实学;深入深出是假学问,照搬照说,无法融会贯通,说出来很深奥,充其量是个理论的“留声机”;深入浅出才是真学问,看问题入木三分,钻研得很深刻,表达得很通俗,融会贯通,娓娓道来,依靠思想的力量说服人,依靠理论的魅力征服人。
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任人涂抹的“角色”,不能以“图谱化”的名义和手法来肢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一整块钢”。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精要归结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还是把它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它实质上都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是相对的,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同一课题,即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各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真理性及其内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论证的,哲学提供的是论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济学则是对科学结论进行经济必然性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其论证结论的概括和总结。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正像列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它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某一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图谱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图谱化”,也即马克思主义“脸谱化”,就是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一张张支离破碎的“图谱”,在“图谱化”的过程中“肢解”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消解于无形。马克思主义“图谱化”在国内外均有市场。在国外,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学者扬言马克思主义存在“某某空场”、“某某缺失”,试图以某个思想流派来弥补马克思主义的“空场”或“缺失”,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系列“图谱”,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下半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图谱化”还表现为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从人道主义到科学主义的“断裂论”等等,不一而足。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图谱化”表现为“以西(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马”、“以海(海德格尔)解马”、“以后(后现代主义)解马”的解释框架流行,这些解释模式原封不动地套用他人的致思逻辑和分析框架,将马克思主义纳入这套框架之中进行解释,马克思成为一个任人涂抹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海德格尔化”、“后现代主义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的“图谱化”、“脸谱化”,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察,然而其实质却是“肢解”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赋予马克思主义似是而非的思想内容,变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两个马克思“对立论”,还是恩格斯马克思“对立论”,抑或是马恩列“对立论”,这些提问的动机都怀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色彩:提问的目的并不是要对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之间的学术关系和思想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而是为了通过在理论上颠覆一方从而连根拔除马克思主义,进而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合法性。在马克思主义“图谱化”过程中,各种“主义”粉墨登场,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各种“化”都有,唯独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沦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干瘪躯壳或“符号”,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往里面填充自己的私货。可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能以“图谱化”的名义和手法来肢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四、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入乡随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但不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是从“民族”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⑥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民族气派是马克思主义的个性特质,是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民族的在场方式。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无所谓共性;从理论形态的特殊性来说,只有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超越民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富有西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只是富有俄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入乡随俗”的结果,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产物,而不是“民族主义化”的表现。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搞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不是搞什么“民族共产主义”。
现在,复兴国学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前有少数学者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封建化,主张用儒家学说来“儒化”马克思主义,有的甚至主张恢复儒家学说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些偏执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儒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蕴含了厚重的东方智慧。儒家文化在某些方面达到的高度确实为西方古代文明所不及,甚至也为西方近现代文明所不及。正因为如此,“复兴儒学”、“取其精华”才有其合理性。然而,“复兴儒学”的同时不能将其意义人为地无限拔高,在“取其精华”的同时不应忘了还要“去其糟粕”。“复古论”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古人,这是被历史彻底抛弃的方案。当前,有人鼓吹把儒家学说当作一种宗教来复兴,倡导把儒教定为国教,把儒学定为“国学”,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用儒家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有人甚至认为,当今社会,仍然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须知,儒家文化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它没有经受过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洗礼,从总体上来说,它仍然是落后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至于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相比,它更是低一个层次。儒家文化的主体是属于心性道德、修身养性、德性伦理的学说,其内容博大精深,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重点关照的领域,也是西方伦理学说难以超越的。儒家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正因为有这种先进文化的指导,中国才能独步历史,谱写了古代中国的辉煌篇章。然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儒家文化的意义范围和作用领域则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全球秩序重建等诸多时代课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如果以为儒家文化在近现代依然能够担当中华民族指导思想的重任,那么,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一举超越独步历史千余年的东方王朝的历史就无法解释,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民在同各条道路、各种主义的较量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历史的误会了。所以,在今天,试图将已经走下神坛的儒家文化简单复活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试图抱持一种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复兴国学也是无能为力的。
五、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立场和确定性内容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某种“风云变幻”的时尚理论或快餐文化
马克思主义包含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即它具有独特的立场和确定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无论怎么发展,无论怎么“化”,这个立场始终不能变,这些内容始终不能丢,变了、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相对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百宝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内容在这种“赞誉”中面临着消失的风险。“相对主义”的解释倾向习惯于将西方的时髦思潮和时尚文化往后追溯至马克思,试图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从而宣称自己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在这种无限度、无节制的还原中成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尚“达人”,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风云变幻”的时尚理论,能不断地转换角色、变换身份介入各种现实问题,马克思似乎“怎么都行”:马克思既是现代性的建构者,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开拓者;既是女权主义的开山鼻祖,又是生态主义的精神导师;既是人本主义的伟大旗手,又是科学主义的真正英雄;等等。这里面还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就不得而知了。“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有一百个“马克思”,“马克思”的身份游移不定,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化”的解释中若隐若现,马克思主义处于一种空前的悬疑之中。任何人只要能想象得到,都能以自己的语言演绎出一个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叔本华曾经描述过类似的现象,他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⑦今天,马克思主义似乎也浑身长满了嘴巴,每个嘴巴都说着与众不同的话语。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前繁荣,学术研究空前自由,然而在实质上是解释的随意化,无底线、无限度、无边界,这种“怎么都行”的解释倾向必将导致马克思主义虚无主义化。
当前要反思对“马克思”的解释限度问题。马克思主义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也是有边界的,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马克思主义不管其功能多么强大,也是有限度的,不能将其视为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主观任意地解读“马克思”,将其上升为一个“怎么都行”的全能型英雄人物,也无法改变马克思与生俱来的“有所为、有所不能为”的“宿命”。那种将马克思“万能化”的企图既不能抬高马克思,也不能抬高自己。相反,那样做只会贬低马克思的本来价值,而不会抬高马克思的身价;只会带给马克思“过多的侮辱”,而不会带给他“过多的荣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任何真理一样,“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⑧。马克思如果活到21世纪,畅游于各色人等编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大观园中,欣赏这一幕幕的壮丽景观,他一定会再一次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⑨
“马克思”的解释限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合理的呢?在我看来,就是要自觉地思考文本和时代的深处,以“问题”为中介实现文本与时代之间的对话和交融,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引入到我们对当代生活、当代实践的思考,带着时代的问题走进马克思、走进文本,彰显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陈曙光:《谈谈“理论”与“问题”》,《湖湘论坛》2008年第4期。
③《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④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
⑤《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⑦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5页。
⑧《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