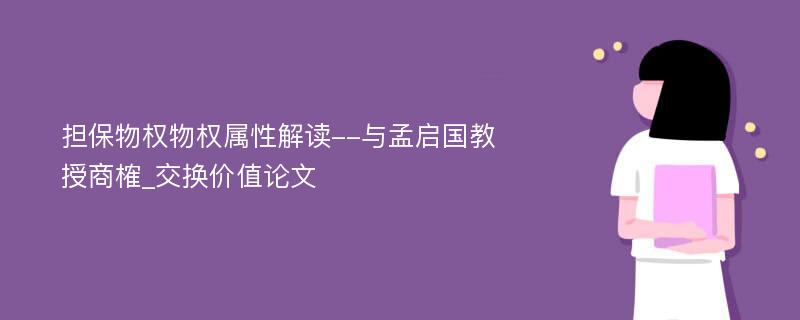
担保物权的物权属性解读——与孟勤国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权论文,国教论文,属性论文,孟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9)01-0146-07
多年来,担保物权作为一种物权,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共同构成民法物权体系,已经被绝大多数民法学者所认同。在我国已经完成的物权立法中,担保物权也正如多数学者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实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理性回归。但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武汉大学孟勤国教授提出了物权二元结构理论。在孟教授这个由所有权和占有权组成的物权二元结构里,担保物权是没有位置的,因为担保物权既不属于所有权,也不能完全归入占有权,如果物权法里规定了担保物权,二元结构岂不变成了“三元结构”?孟教授极力反对将担保物权归入物权法调整。《物权法》颁布以后,孟教授又多次撰文阐明这一观点,认为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作为物权,“是一种有逻辑缺陷的思维”[1],“使物权立法成为不讲道理的立法”,“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东施效颦的典故”[2]。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揶揄已经颁布的国家法律,是否妥当尚须思量,但是,担保物权的权利属性却是一个严肃的民法理论问题,无论如何都来不得半点调侃。
其实,担保物权是否应该在物权法里规定,学术界早有不同看法:“是继续保留担保法作为单行法,还是依民法通则模式统一作为债的担保形式呢?或是依传统大陆法模式分解为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呢?或是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样,既保留大陆法的法典传统模式,又辅以完全英美法模式的单行法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3]但反对在物权法规定担保物权的学者,一般却并不否认担保物权是一种物权。例如,李开国教授在文章中即主张“抵押、质押、留置及让与担保等担保方式,以不纳入物权法规定为好”,而应放在债权法。但其理由是:“将抵押、质押、留置和其他债的担保方式一起放在债法中规定,建立统一的债的担保制度,有利于明确法律的适用范围,张扬和实现法律的制度价值”,防止出现《担保法》和《物权法》“两个单行法都规定抵押、质押、留置的局面”。李开国教授在同文中仍然承认“抵押权、质权、留置权都具有物权性质”[4]。李明发教授也指出:“在《担保法》已经先行公布实施的情况下,即使制定物权法,既不应该也无必要再对担保物权作具体规定了。”但他同时又说“这也许是不科学的但却是合理的立法选择”,因为“担保物权是民法物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徐武生先生说:“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仍应通过修订《担保法》的途径进行,而物权法关于担保物权可只作出原则规定”,但他也承认“担保物权具有物权性,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6]。
与上述学者不同,孟勤国教授在主张将担保物权“驱逐”出物权法时,却采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担保物权的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担保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可以另行研究,但肯定不是物权”[7]。
担保物权是否应当纳入物权法,本来仅仅是一个立法体例选择问题,或者说立法者到底是从担保物权的权利性质着眼,还是从担保物权的调整功能着眼;到底是追求一国物权制度的完整,还是追求债的担保制度的统一。然而按照孟教授的说法,担保物权根本就不是物权,如此一来,物权法中规不规定担保物权就不仅仅是一个立法体例的问题了,而是对担保物权的权利性质的准确认定问题。这就需要学术界认真对待和思考孟勤国教授的观点,并开展严肃的讨论。
对于孟勤国教授“担保物权不是物权”的观点,王利明教授已经给予了回应,从各国立法实践以及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性、支配性、排他性、追及性等方面全面论证了担保物权的物权性质[8]。但是,王利明教授主要是从正面入手来分析的。笔者试图从孟教授反对将担保物权作为物权的具体论据切入,以作为典型担保物权的抵押权为例,对其观点提出质疑,以便澄清一些问题,加深对担保物权权利性质的认识,并向孟教授请教。
一、抵押权人不能对抵押物的实体进行事实上的直接支配吗
孟勤国教授说:“传统物权理论认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物上利益的排他性权利。因此,物权被认为是支配权。……担保权,既没有所有权那样的最终支配力,也常常没有用益物权那样的现实支配力,一个抵押权从设立到消灭,抵押权人对物从来不能实施传统物权理论所说的直接支配。”[9]在他看来,这种不具直接支配性的权利,不能作为物权。这是他提出“担保物权不是物权”这一观点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物权的定义多种多样,但物权是一种对物的直接支配权,这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直接支配性是物权的核心和灵魂。只要证明一种权利对物具有直接支配性,那么将这种权利划归物权的范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反过来,如果一种权利对物不具有直接支配性,那么也就可以断言这种权利不是物权。所以,孟勤国教授从不具有直接支配性的角度出发来论证“担保物权不是物权”,是很合适的。但问题是:担保物权真的对物不具有直接支配性吗?
所谓支配,是指对物加以控制、管领、处分;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借助于他人的意思或行为,即可实现[10]。这是学术界对“直接支配”一词的经典表述。物权人对标的物的支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物的实体进行有形的事实上的支配,一种是对物的价值进行无形的法律上的支配。那么,担保物权人能否对担保物进行这两种支配呢?对于后一种法律上的支配,学术界争论不大,一般认为即使不占有担保物的抵押权人,也可以直接支配抵押物的价值,而不失其支配性。当然孟勤国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将在后文分析。最有疑问的是前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孟勤国教授说:“抵押权人不占有物,不能在物上做点什么;债务按时履行,抵押权自然消灭;债务不能按时履行,抵押权人只能请求以变卖或拍卖担保物的价款优先受偿,也不能将担保物收归己有或自力处理。”[11]从抵押权的发生到抵押权的消灭,我们找不到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进行有形的事实支配的成分。
但是,“担保物权是为确保债权的实现而设定的担保制度,其存在与发展当然与债权的存在与发展相关。可以说,担保物权是随着债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债权的发展而发展的”[12]。而债权法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状态”[13]。所以,担保物权肯定不是一套僵硬的制度设计,而显示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物权品质。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担保物权。基于这种认识,孟勤国教授断言“一个抵押权从设立到消灭,抵押权人对物从来不能实施传统物权理论所说的直接支配”,恐怕就有点为时过早了。
试举日本2003年通过的担保物权制度修正案为例。日本法务省法制审议会自2001年2月开始着手调查、修改担保物权与民事执行法,于2003年3月将《为改善担保物权及民事执行制度之民法等部分修正案》正式提交日本国会,并于7月25日获得通过。与以前担保物权制度的修改重在扩大抵押物范围的做法不同,日本此次《修正案》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强化抵押权的效力。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增设了强制管理制度,并以此作为与拍卖并列的一种抵押权实现方式。根据这种强制管理制度,主债权届期未受清偿后,抵押权人可以对抵押不动产进行长期的直接运营、管理,并收取不动产收益以抵偿债权,直至债权获得完全清偿[14]。显然,按照这一最新修正案,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支配性大大加强,在特定情况下由对抵押物价值的支配转变成对抵押物实体的全面的、现实的控制和支配。
日本建立抵押权人强制管理制度的背景是:日本许多抵押权是在房地产泡沫大盛时设定的,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作为抵押物的不动产价格一落千丈,低于甚至远远低于被担保债权额,届期未受清偿的抵押权人即使拍卖抵押物也不足以回收债权。以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债权人为摆脱这种困境,只能采取抵押物租金物上代位的办法,希望通过日久天长的租金累积来回收更多债权。但日本民法对租金物上代位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而且这种做法与抵押人保有抵押物使用收益权能的抵押权基本制度构造发生矛盾。其实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抵押权人对租金进行物上代位后,抵押人根本无法获得租金收入,所以许多抵押人干脆就放弃了对抵押物的出租,任抵押物荒芜闲置,抵押权人对其也无可奈何,租金物上代位变成了泡影[15]。面对这种尴尬局面,立法者果断地赋予了抵押权人对抵押物进行直接运营、管理的使用收益权能,大大增强了抵押权对标的物实体的支配力度。显然,这是一种明智之举。
其实,上述情况在我国也存在,如何进一步增强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有效支配程度,也是我国今后完善担保物权制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环境下抵押权的实现效率不高,手续比较繁琐,成本比较大。正如方流芳教授所说:“抵押权的实现必须交纳诉讼费、评估费、拍卖费和强制执行费,实现抵押债权的成本大大超过无担保债权”,“抵押权实现成为诉讼成本最高的一种司法救济”[16]。再加上抵押物变现困难,有些抵押房产原本就是“烂尾楼”,根本无法变现,抵押权人的债权很难通过一次性拍卖抵押物获得清偿。而有些抵押物在抵押权设定时属于可以让与的流通物,后来由于抵押权人不能预见和控制的原因却变成了禁止流通物,无法通过拍卖抵押物实现抵押权。在此情况下,实务中出现了要求设立抵押资产管理公司的呼声[17]。由抵押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对抵押物,尤其是价格已经大幅下跌、变价后不足以清偿债权或者根本无法变价的房产,进行专业化管理和经营,以确保抵押物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这种管理经营显然不能局限在现行担保物权制度所规定的简单的拍卖、折价、变卖上,而应包括直接出租、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招商引资、投资入股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就要求立法者突破抵押制度的现有框架,在特定情况下赋予抵押权人更为强大的现实支配权能。
类似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例如,在德国,按照《法院出售法》的规定,抵押权人可以申请法院将争议财产(抵押物)交财产保管人保管,财产保管人是强制执行法院的助理人员,“他有为保持财产的经济价值及其生产能力而必须做一切作业的权利与义务”,债权人(抵押权人)从保管财产所得得到清偿。而且,移转抵押物的占有并以抵押物的孳息清偿债务,作为一种抵押权的实行方法,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也是存在的[18]。按照英美法,占有担保物并进行经营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担保权实行方法,而抵押物接管制度在英国、美国、希腊、挪威、西班牙都在广泛使用。根据英国法,抵押权人委托接管人后,还可以解散抵押船舶的船组人员或企业的董事①。已有学者指出这种抵押权实行方式“对于我国颇有借鉴之价值”[19],“是实现抵押权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非常值得利用的实行方式”[20]。
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挑战,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支配范围、支配能力有逐渐扩张的趋势,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延伸到对抵押物进行全面的、事实上的支配的方向上去。在此制度演变背景下,孟勤国教授认为“一个抵押权从设立到消灭,抵押权人对物从来不能实施传统物权理论所说的直接支配”,这个结论就下得有点早了!
二、抵押权人不能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法律上的直接支配吗
孟勤国教授说:“为了掩盖担保权的非物权性,学者编排出用益物权支配物的使用价值、担保物权支配物的交换价值的说法。”“‘担保物权支配物的交换价值’是个伪命题”,“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原理是一面镜子,一下子就照出了‘担保物权支配物的交换价值’的荒谬面目”。“依政治经济学常识,交换价值并非商品之常态,只出现于商品交换之时,而且交换价值因供求状况而呈现某种不确定性,抵押物究竟能变卖或折价多少人民币,只有实现了抵押权才能知道,在此之前,交换价值仅是一个期待,对一个未来才可能有的东西,如何直接支配?”“即使认为商品的二重性可分别支配,也只能说用益物权支配物的使用价值,担保物权支配物的价值。”“或许,其所说的交换价值仅仅是指担保物的价值,这更不对。担保物的所有权仍有依法转让的情形,说明担保物的价值仍在所有人的直接支配下,不然,所有人拿什么转让担保物?”[21]
我们可以将孟教授的上述论证归结为两个层次:第一,担保物权人理论上根本不能支配物的交换价值;第二,担保物权人理论上虽可以支配物的价值,但实际上担保物权人又不支配物的价值,因为在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所有人)仍可依法转让抵押物。
在第一个论证层次上,笔者认为孟教授成功了一半。政治经济学认为,“交换价值就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上的关系或比例”。“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商品与商品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22]。按照这一理论,正如孟教授所说:“交换价值并非商品之常态”,在抵押物折价、变卖、拍卖之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根本没有出现,仅仅是潜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显然是无法支配的。所以,以前有些学者笼统认为担保物权支配物的交换价值,这是值得推敲的。但是,如果就抵押权的实现而言,说抵押权人支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已经现实存在。当然,孟勤国教授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交换价值是绝对不可能支配的,因为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的比例关系,既然是一种比例关系,就不可能被支配,比如美金和人民币的汇率为一比八点几,我们可以支配美金,也可以支配人民币,但绝不可能支配一比八点几这个比例关系”[23]。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交换价值固然是一种比例关系,但这种比例关系是通过一定的实物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常讲“一把斧子换20斤大米,20斤大米就是一把斧子的交换价值”[24],难道这20斤大米不能支配吗?所以,笔者认为,孟勤国教授在第一个层次的论证上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但是,在第二个论证层次上,孟教授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一)抵押权人在抵押权实现之前始终支配着抵押物的价值
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凝结或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而“一切商品都凝结着这种人类劳动”。“一切商品都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19]。所以,与交换价值不同,价值是商品之常态,在抵押物折价、变卖、拍卖之前,抵押物的价值就已经存在了。抵押权人支配抵押物的价值理论上是不应该存在问题的,孟教授对此也不否认。但孟教授认为抵押权人实际上不支配抵押物的价值,理由是抵押人仍然可以依法转让抵押物,“说明担保物的价值仍在所有人的直接支配下,不然,所有人拿什么转让担保物?”这就值得怀疑了。
1.从我国《担保法》解释论的角度
《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第三款前段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据此学者一般认为,《担保法》是采取了抵押物转让价金物上代位的立法例。根据这一规定,抵押人即使依法转让抵押物,也不能完全支配抵押物的价值,否则为何还要求通知抵押权人呢?为何还要求抵押人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呢?而按照同样采取转让价金物上代位立法例的《意大利民法典》第2867条的规定,受让抵押物的第三人(而不是抵押人)应当将购买抵押物的价款直接支付给抵押权人,不能向抵押人支付。可见,抵押人即使依法转让抵押物也无法支配价款,抵押物的价款是由抵押权人支配的,抵押权人直接支配抵押物价值这一点在此表现得很明显。
不过,孟教授书中又提出:“价款又不等于价值”[25],意思是说,即使抵押权人支配抵押物转让所得的价款,也不能认为抵押权人对抵押物的价值构成支配。其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价款不过是价格的货币实物形态,而价格又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支配价款和支配价值只不过一个是支配事物的表现形态,一个是支配事物的本体,二者在法学上的区分意义并不大。政治经济学常说:“商品购买者要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就必须支付这个商品的价值”[26],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说商品的购买者要“支付这个商品的价款”,可见价款与价值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分必要。抵押权人支配抵押物转让价款,完全可以说明抵押权人支配着抵押物的价值。
2.从立法论的角度
当然,对于我国《担保法》的上述规定,学者大多是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应当放弃转让价金物上代位的立法例,承认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的所有权并未丧失,抵押人仍得自由转让抵押物的所有权[27]。而且,抵押物转让价款既不需要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也不需要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我们应当抓住制定《物权法》的良机……以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替代提前清偿和提存制度”[28]。按照学者的这一立法设想,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无须通知抵押权人,更无须征得抵押权人同意,可以向第三人自由转让抵押物的所有权,所得价款由抵押人取得,抵押权人既无权过问更无权支配转让价款,只能在债权届期未受清偿时,追及抵押物的所在实现抵押权。表面上看,正如孟勤国教授所说的那样,抵押物转让所得的价款是由抵押人(所有人)完全支配的,根本不存在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支配。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情况下,第三人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在与抵押人进行抵押物交易时,对抵押物上的抵押权负担状况进行了解后,考虑到抵押权人嗣后追及拍卖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的巨大危险,是不可能支付全价购买抵押物的。日本学者近江幸治先生已经举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房屋市场价格1200万元(日元),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1000万元,那么,第三人会向房屋所有人花多少钱购买这座房屋呢?近江幸治先生说是200万元[29]。史尚宽先生更是明确指出:“不动产所有人于抵押权设定后,得自由将抵押标的物让与他人,然不妨碍抵押权人之行使抵押权。此时自抵押标的物之时价减除抵押债权额,以其余额为买卖价金。”[30]也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买受人因购买抵押物而向抵押人支付的价款,一般应是抵押物市场价格与担保债权额的差额。因为抵押权具有追及效力,所以担保债权额那部分第三人是不会支付给抵押人(所有人)的,第三人或者将其留作日后涤除抵押权时使用,或者作为嗣后抵押权人追及拍卖抵押物时丧失抵押物所有权的预先补偿。
可见,抵押期间即使抵押人可以自由转让抵押物,他也不能取得抵押物的全部价值,与担保债权额相当的那部分抵押物价值仍然是由抵押权人牢固地支配着。孟勤国教授看到抵押人可以依法转让抵押物,就认为抵押权人丧失了对抵押物价值的支配,似乎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当然,最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没有采纳学者的观点,而是在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从而剥夺了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自由。这一规定饱受学者的指责,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管制思维仍在作怪,可以说这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发展的任性立法”[31]。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按照《物权法》的这一规定,抵押权人在抵押权实现之前对抵押物价值的支配变得更为牢固,其物权性更为明显。
(二)抵押权人在抵押权实现时直接支配着抵押物的价值
其实,学术界认为抵押权人直接支配抵押物的价值,主要还不是体现在上述抵押权实现之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支配。抵押权人之所以能够直接支配抵押物的价值,最根本的在于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可以直接就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其债权,而无须借助于他人的给付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才指出:“担保物权是一种特别的价值权……是一种以标的物的价值来优先受偿的变价权或换价权。……换价权为担保物权的本质……忽视换价权则无法捉住担保物权的本质。”[32]在抵押权的实现过程中,抵押权人对抵押物价值的直接支配性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孟勤国教授对此深不以为然,他说:“有学者说,担保权人的拍卖申请权无须义务人介入即可行使,故可视为是直接支配,这未免过于牵强!……拍卖申请权更多地体现公权力和程序法的价值,与担保权人的直接支配与否风马牛不相及。”[33]
确实如此,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大多是通过申请人民法院依照强制执行程序拍卖抵押物来实现的。但这只是权利的行使方式、方法问题,并不能影响我们对抵押权权利性质的判断。一种权利采取什么方式行使是一回事,而这种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混淆。例如,形成权通常是依权利人单方面意思表示的方式来行使的,于到达相对人时发生效力,但是也有一些形成权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形成之诉)行使,由法院作成形成判决才能发生效力。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重大误解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以及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方式订立的合同,撤销权人应通过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来行使撤销权,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形成权的行使方式特殊就否定它们的形成权性质。
抵押权需要借助公权力通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德国、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取的办法,体现了立法者追求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对各方当事人利益衡量的结果,并不能以此作为我们判断抵押权权利性质的依据。抵押权到底属不属于物权,关键还在于抵押权人能否对抵押物的价值直接支配。
如前所述,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借助于他人的意思或行为,即可对物加以控制、管领、处分。抵押权人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并就拍卖价款优先受偿,既不需要征得他人(包括抵押人)的同意,也不需要他人的协助,其直接支配性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需要请 求法院对抵押物予以扣押并拍卖,但这并不意味着抵押权就因此而变成了请求权。因为民法上所谓请求权的实现需要借助他人行为的协力,是针对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义务人而言的,而法院并非实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更非权利人的相对人、义务人。法院帮助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属于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保护,如果说这种公权力的运用就是他人行为的协助,就可以据此认定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是请求权,那么,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最终都要请求国家公权力的救济和帮助,是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可以称作请求权呢?
但是,孟勤国教授又说:“难道一般债权人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需要债务人同意或协助?”[34]言外之意,如果抵押权人直接申请拍卖抵押物构成对物的支配,那么,一般债权人也可以说对物有支配力,因为一般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也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和协力,一般债权岂不也可以称为物权?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债权的客体是给付,是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而人的行为是不能由他人直接支配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债权人不可能对债权的客体进行支配。当然,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原来的各种债权会转化为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金钱债权,一般债权人确实可以对债务人的物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也确实不需要债务人的旧意或协助,但一般债权人并不是直接针对债务人某一特定的物提出主张,只要能清偿其金钱债权,执行债务人的房屋、电视机、冰箱、机器设备还是库存产品,甚至债务人的股权、知识产权、对于第三人的债权,一般债权人并不关心。债权只是针对债务人全部财产的一种“漫射”的权利[35]。而民法上所谓支配,必须客体特定,客体小特定不存在支配问题。只有客体特定,才存在支配的可能性。所以,一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物根本谈不上“支配”。而与此小同,抵押权人对债务人物的支配,自始至终是固定在特定的抵押物上。即使抵押物辗转到了第三人的手中,抵押权人也可以追及特定抵押物的所在,主张并实现抵押权。即使抵押物毁损、灭失,物质实体不存在了,抵押权的效力也追及到抵押人就该特定抵押物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上,物的特定转化为价值的特定。可见,抵押权的客体始终是特定的,因而才有直接支配的可能。之所以认为抵押权人的拍卖申请权属于对抵押物的物权,而一般债权人的拍卖申请权却不属于对债务人总体财产的物权,原因就在于后者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债务人的总体财产仔存一种所谓“物的替代”的现象,即一项具体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另一项具体的财产所替换[36],所以,债务人的总体财产只是一个“容器”,“就像一个钱包始终不变地存在,不管里面内容如何”[37]。因而,一般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不具有特定性的总体财产虽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但却根本不可能构成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对特定客体的“支配”。
更何况,一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申请强制执行,需要先提起给付之诉获得确定的终局判决或其他执行名义,而抵押权人申请拍卖抵押物,则系“担保物权之自动发展而当然的被行使”[38],“为非讼事件之一种……如抵押权已依法登记,债权之清偿期业已届至而抵押物又系存在者,法院即应为准许拍卖之裁定”,即使债务人对债权之存否行所争执,也需另行提起确认之诉以求解决,而小能阻止抵押权之实现[39]。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一般债权人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本质上是债务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债务人需以其全部财产(责任财产)来清偿其全部债务,这是债的一般担保,而抵押权属于债的特别担保,二者有很大的不同[40]。把抵押权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强制执行程序拍卖抵押物来实现抵押权,与一般债权人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来清偿债权同样看待,就混淆了债的一般担保和特别担保,而实际上“两个事物小处于同一层次上:一个指的是权利本身的对抗力,另一个则是保障权利的制裁”[41]。
三、结论
在论证“担保物权不是物权”的过程中,孟勤国教授还提出了其他理由,但如前所述,对物的直接支配,是物权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从制度发展的趋势来看,担保物权在特定情况下有向直接对物的实体进行事实上的支配的演变动向;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自担保物权的设定到担保物权的实现,担保物权人一直对担保物的价值进行着法律上的直接支配,其对物的直接支配性是非常明显的。担保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法律特征,将其作为一种物权在我国《物权法》上加以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孟勤国教授否认担保物权的物权性,值得商榷。
当然,一种权利到底是不是物权,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是笼统地进行判断,只有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内,结合这种权利应有的结构属性和价值功能,才能就这一问题得出明确的答案。虽然,从基本层面上看,如上所述,担保物权具备了物权的法律特征,但要彻底完成担保物权在我国法律上的物权化过程,使得担保物权具有全面的物权品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的担保物权的有关制度尚须进一步加以完善。
收稿日期:2008-10-11
注释:
① 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之强制执行,以查封、拍卖、强制管理之方法行之。”所谓“强制管理”,指执行法院对于已查封之不动产,选任管理人实施管理,以其所得收益清偿金钱债权之执行行为(参见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8~4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