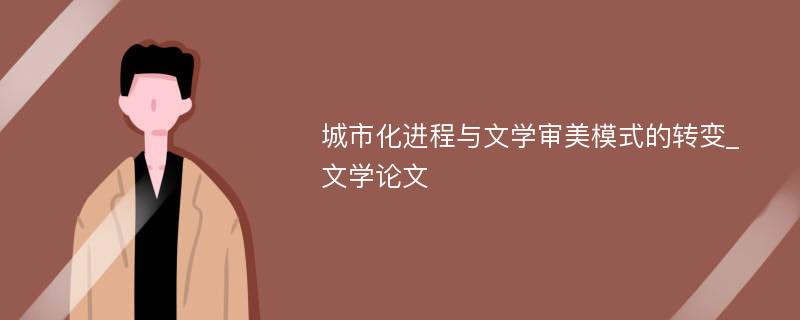
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的兴起。它不仅以全新的文学样式,出现在传统的文学审美领域,而且,这种在现代都市背景下形成的文学审美经验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写作、传播乃至评价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变化因为是迥异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审美方式,因此,直到今天,对以上海为背景的城市文学的审美评价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课题。
1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学的形成,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开埠以后。这种划分的文学史依据在于,上海开埠之前,在文学史上,上海本地几乎没有产生过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家,也没有提供过具有地方特色的审美经验,在当时国内的一般文人学士心目中上海是没有什么文学地位的。开埠以后,上海的文学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海成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城市,不仅吸纳了不少国内的文人学士,而且,一些外国的传教士和文化人也来上海落户,建立印刷出版机构,出版文化读物,创办报刊,传播异域的思想文化。在这种新的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上海社会,的确有其非常独特的表现,上海的本地经验,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人生经验,可以说,它完全刷新了以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基础,所以,从文化上讲,差不多所有初到上海的外地读书人,在他刚到上海时,都会有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还不仅仅是初来乍到时的那种新奇,而是上海所提供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内地的读书人所从未见到或从未想到过的。到了上海,这些外地的读书人有一种原有的人生经验就此中断的感觉。就拿19世纪的文人王韬来说吧,当他离开苏州,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不禁被眼前所见到的上海景象所打动:
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注:转引自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
这种原有经验的中断和被搁置的悬空感,差不多是各历史时期的所有外来的读书人在上海的真实人生感受。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现代评论派代表人物陈西滢,在1927年写的《物质文明的上海》一文中,也表达了自己初到上海时的新鲜感:
我们再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的附近去走一回,就可以看见无数的宽敞的花园,精致的别墅,住在里面的舒服,我们相信一定胜于北京的清故宫和古代的什么阿房宫、金谷园。就是经过上海暂住的旅客,也一定会觉得大华、华安的饮食起居比哪一个大都会的旅馆都比得上吧。再走到南京路,极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一连就有三个,其余的中国的,外洋的种种色色的衣食杂用的商铺,五光十色,叫人眼睛都看得晕花。此外有的是戏园、电戏、咖啡馆、跳舞场,公娼、私娼、赌场、烟窟,以及种种说不出,想不出的奇奇怪怪的消遣的花样,娱乐的场所。……(注:陈西滢:《西滢文录》第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外来者对上海的这种新鲜感,首先是由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品格所决定的。因为上海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产生影响,最根本的一点,是上海提供了许多原来中国本土所没有的东西,换句话说,人们对上海的文化想象,是伴随着对外开放这一特色而展开的。像外滩的建筑群、大马路上的电车、伫立街头的咖啡馆和百乐门跳舞厅等等,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初到上海的外来人,即便是他对外来文化已有听闻,但第一次在上海那么真切的见到这些物质存在时,头脑中还是不免会有所震动。不仅如此,上海作为一座具有现代风味的城市,其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这就是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构成。一般中国的传统城市,大都是行政型城市,也就是说,是以政治或军事的重要性为主,而逐渐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但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以商业贸易为主,逐渐而成为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中心。立足于商业贸易基础上的上海,有着与中国别的城市不同的运行规则和道德评判标准。譬如,金钱意识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我们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学家们对上海最深的印象,是上海这地方讲究钱,相应地影响到对人对事,也喜欢以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在这一问题上,文学的表现构成了最为复杂的社会图景。一方面,上海在现代作家笔下成为最憎恨的对象。如茅盾在《子夜》中,将上海描写成一张血盆大口,贪婪而无耻。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艺术家们最最留恋之地,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散落在上海里弄的亭子间里,寻找着个人的事业前途。亭子间作家差不多成了上海艺术家的代名词。从历史上作家艺术家们在上海的发展情况看,商业社会对于上海文化艺术的刺激和促进作用,积极的方面似更大一些。从20世纪前半段的情况看,上海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中心,具体地说,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重要的新文学人士,最后都选取上海作为居住地;最有影响的文学论争和艺术尝试,大都发源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密切联系;国内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文学刊物都是在上海发行或在上海印刷后发往全国各地。所以,在上海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商业社会的发展,对塑造新的文学、文化所产生的最丰富和最多样的影响。另外,近代上海的发展,是以流动人口为主体而构成的社会。据李右之的《上海乡土地理志》所记:
……同治间,人口共五十余万。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孳生日众。近年(1927年前后——引者注)各省兵事,来沪者益多,居民号称百万,殆又过之。户口之众,超过京、津、汉三埠,人烟稠密,几有人满之患。惟本邑人数之多,实由五方杂处,客藉多于土著,良莠自不能齐。……(注: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3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给城市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一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集中在一起,带来了各地的文化,造成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二是多元文化格局下成长起来的新的文化,自有一种独特的品格。这种品格在理论上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但其迥异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这一点应该是明确的。事实上,从文学史上看,上海的文学发展,的确是在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发展成长的。我们不妨从文学的类型来看,近现代以来,国内没有一座城市的文学在风格类型方面,像上海文学发育得那么齐全。1920年1930年代的上海文学,不仅有表现底层生活,充满反抗激情的左翼文学,也有描写都市情调,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新感觉派小说。既有脱胎传统文学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也有效仿西洋都市文学的唯美主义诗歌。这些文学流派拥有自己的作家群体和期刊阵地,也有着自己的读者群体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审美探索中,上海一地的文学最终形成了富有现代特色的“海派”文学的总体特征。
除了外来影响、商品经济和流动人口带来的多元化文化影响因素外,应该强调的是上海的社会文化基本上是在一种较为平和的环境中成长,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战乱基本上没有中断上海经济和文化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上海由于租界等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常常成为战乱时期东南一带躲避战争威胁的屏障。譬如近代以来几次大的战乱,基本上都没有在上海发生,即便有一些小的战乱,也是在很短时间内便告结束。这样的社会发展条件,保证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能够不断延续下来,既保持了已有的历史成果,又能够不断开发出新的发展机遇。所以,上海文学在20世纪总的是在一种开放的格局下,不断累积创新的经验。这种良好的社会发展机遇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近百年来,是国内其他城市所很少能够具备的。这也就难怪近代以来同时开埠的几个城市,最终对近代中国在各方面产生影响的,特别是产生文化影响的,只有上海—个城市的原因了。
2
如果说,上海是近百年来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而这种现代气息得益于它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历史条件。那么,从文学审美方面讲,这种富有现代意味的城市化进程,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以为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言,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商品经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上海是近现代中国商品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文学创作最活跃、出成果最多的地区。一般文学史研究都承认,从1920年代开始,上海成为中国的新文学中心。(注:有关这一论述,我在《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一文中有所分析。文章刊于《上海文化》1995年第一期。另收入《商务印书馆一百年》。)但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上海就已经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影响。据统计,《马关条约》之前,全国总共5种文学期刊,全都在上海。另外,当时出版的小说,上海占据绝大多数。(注: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页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从文化渊源关系考虑,照理,北京或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文化条件都要比上海好,但为什么上海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文化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发展呢?这当然从理论上向我们提出了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我觉得更应该注意考察的是,上海都市文学的起步,最早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形态。换句话说,上海的文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起步的,最初的上海文学主要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从目前的研究来看,19世纪上海一地的文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娱乐消遣为主的通俗故事;另一类就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政治小说。前一类作品,尽管现在保留下来的不算多,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作品是与这座商业城市的成长同步进行的。有那么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专门读书的,在劳累之余需要娱乐放松,因此,听说书、看通俗小说是再顺当不过的事情了。适应于这样的需要,以娱乐为主的通俗文学在上海一地发展起来。后一类社会政治小说,产生的时间比前一类要迟,它是在上海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已经可以产生社会影响的条件下,一些文化上有所寄托的文化人有意识地利用上海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政治上宣传自己的主张。譬如,梁启超1896-1898年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利用上海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大胆淋漓地宣传变法思想,抨击顽固保守派的观点,他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他那种酣畅淋漓的文风,一扫桐城文的传统风格,使得普通读者意识到报章文体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到了20世纪初,以上海为背景的近代文学更是风起云涌,形成了近代以来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不仅创作数量占据当时国内的大半以上,而且,在小说理论等审美问题的思考上,都有非常新的探索。如,黄人、王国维等能够参照西洋的悲剧理论和人物性格理论来分析、阐释当时的文学创作。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也在世纪初的小说创作上获得了响应。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文学杂志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构成了世纪初上海文坛的新局面。但应指出的是,这些“新小说”和新文体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内,大都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讲述普通人儿女情长的言情故事,及模仿外国侦探故事的探案小说。这些作品在上海文坛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余风所及,直至今日。这些被文学史家称为通俗文学的东西,在历史上曾被一些严肃的艺术家所不屑和看低,但它的确也是上海这一商品社会的产物。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在于满足普通市民阅读消闲的娱乐需要。虽然大多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但也不乏有特色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对现代小说的成长是有较大的帮助。譬如,像《九命奇冤》这类作品,在小说结构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事实上,通俗文学的存在与严肃的文学的发展并不像我们后来一些人所想象得那么水火不相容,至少在上海都市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不少作家的成长离不开通俗文学的帮助。如,现代作家刘半农、叶圣陶、施蛰存和张爱玲等,多多少少都与鸳鸯蝴蝶派小说有联系,有的是模仿这些小说的笔法开始文学创作,有的是在鸳鸯蝴蝶派主持的文学杂志上刊发作品而渐渐为人熟悉。而且,通俗文学的读者群与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之间,除了有各自的分野之外,也有重叠之处。上海文学的这些历史经验,其实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很充分地揭示了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商品经济对上海都市文学的影响,最具体的还是体现在上海的都市文学的成长有一整套体制上的保证。这套体制主要是通过报刊杂志等传媒介入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来平衡文学发展的生存环境。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作家这一行业一直被视为是自由职业,他们不像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作家,靠教书为生,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的爱好。上海的作家大多是靠写作为生的职业文人,他们借以为生的生存空间,主要是上海的报刊杂志及各大出版机构。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丁玲、郭沫若等,在上海时,都是靠给出版机构写稿谋生。所以,上海的都市文学与当时主要传媒——报刊杂志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这种关系,对上海都市文学的影响很难用一个好与坏来概括。就其在文学史过程中的表现来看,至少有这么四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以杂志为核心,形成风格相似的同人性质的文学探索。如,《创造》季刊对于浪漫主义风格的探索,《论语》、《宇宙风》等对于幽默文风的尝试,《现代》对于现代主义的集中介绍,《小说月报》对于东欧文学及现实主义文学的引进。二,是作家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出版、市场的影响。譬如,《小说月报》1921年的改版,客观上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但就出版商方面来考虑,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旧有的文学格局不能带来商业上的盈利,只有顺应时势,才能使杂志的出版不亏本。(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改革《小说月报》的前后”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三,杂志风格样式非常多样。有像《北斗》那样态度激烈的左翼杂志,也有《西风》那样带有绅士风格的译文,有《紫罗兰》、《万象》这类适合普通市民口味的读物,也有《良友画报》这样图文并茂的轻松出版物。可以说,近代以来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推出了各种风格的文学杂志,其花样之多,是后来人所难以想象的。四,有源源不断的作家艺术家后备队伍。上海因为有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又有不少文化艺术机构,所以,对文艺人才的社会需求量超过国内的其他城市,不断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来上海求学,寻求个人的事业前程。亭子间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栖身之地,那时的上海有容纳四面八方文学人才的胸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品市场的运作调节,只要有市场,就会不断对新的文艺人才产生需求,而新的文学人才在上海因为有用武之地,当然自然而然地汇集到这里来了。所以,近现代以来上海一地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学人才,并不是上海本地特别能出人才,而是上海的商品社会的体制能够不断推出新的人才,也需要这种不断变化的文化格局。相比之下,国内的其他城市就缺乏这种运行的社会机制。
第三,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今天的研究者在回顾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历程时,可能会感到奇怪,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动荡岁月中,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斗争非常激烈,但另一方面包括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却照样能够在上海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30年代,虽然国民政府也有书报检查制度,但一些今天看来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作品还是不断出版。这些现象反应出抗战之前上海复杂的社会生活格局,譬如,租界的存在客观上保护了左翼作家作品的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上海的商品经济体制保证了上海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斗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找到一种较为独立的审美空间来发展自己。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是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从出版的角度讲,既要出版,又要免于卷入意识形态争斗之中,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贴近文学文化本身来出版。商务出版的小说、学术著作,在文化态度上可能较为平和,但今天来看有特点,包括“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沈从文的散文集等,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另外像开明书店的一些文学出版物,也有相似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上海都市文学的发展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风貌,绝大多数靠得是文学审美自身的魅力。当然,历史上包括国民政府在内,都希望从意识形态方面来控制上海的文学,但上海文学总体上讲,是在商品经济的市场上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事实上,上海都市文学的发展也正是在市场中得到发展的。哪怕是那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出版物,其实也是在市场上寻找立足之本,包括国民党所扶持的文学,因缺乏市场,最终也自动告退。第四,文学创新与民族特色的关系。上海的都市文学无疑是最具有前卫色彩的,可以说,那些现代主义的艺术尝试以及其他种类的外来艺术样式,大都最早通过上海一地的艺术实验而在中国文学领域落户的。这些文学创新活动在当时的社会上曾引起过不同意见的争论。譬如,30年代穆时英的小说创作在上海风靡一时,但穆时英的作品同时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沈从文甚至认为穆时英的小说一言以敝之,那就是“邪僻”(注:沈从文:《论穆时英》,《大公报·文艺》6期,1935年9月9日。)。这样的批评尽可以批评,但从文学史角度来看,穆时英的小说至今仍然不失其重要性,甚至也没有因为他的作品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失去了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特色。同样的情况,如李金发的诗作,尽管外来影响的痕迹非常鲜明,但今天看依然不失本民族的审美特色。因此,立足于上海的文学史经验,我们可以对一些文学发展中的文学关系问题,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认识。
3
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类型,可供我们分析研究的地方相当多。由于其历史形态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于它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学发展方式有着相异之处,因此,要对它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城市化进程在中国至今还处在成长阶段,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审美经验的转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城市中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习惯与在乡村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方式,肯定有所区别。城市中的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往往使敏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看到商品经济与文学的人文情怀相抵触,甚至是矛盾的方面,但从历史上上海都市文学的发展情况看,商品经济与文学的生存环境未必就是一种抵触的关系,我甚至认为商品经济所寻求的市场意识,在文学方面反倒能够不断产生一种创新的机制。在这些方面,历史上上海文学的繁荣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上海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