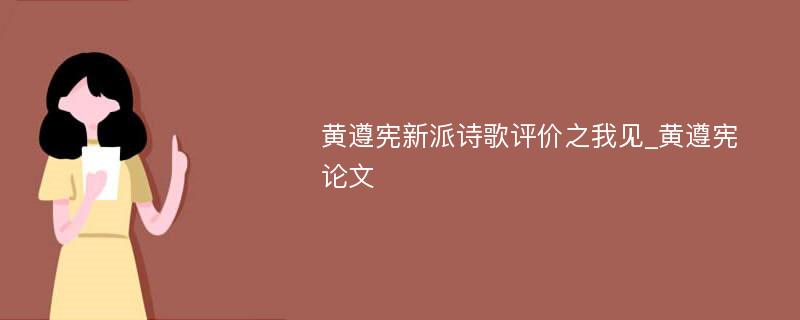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quot;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派论文,评价论文,黄遵宪论文,quot论文,公度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5—0073—10
对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学术界意见较为一致。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要之,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1](P24) 陈三立说:公度“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2](P1127)。高旭说:“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3](P1282) 他如康有为、丘逢甲、狄葆贤、潘飞声、徐世昌、林庚白、汪辟疆、吴宓、钱仲联诸先生,于黄遵宪的“新派诗”,均极力称赞[3](P1275—1308)。20世纪中期和后期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如游国恩、季镇淮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以及任访秋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管林、钟贤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等,都对黄遵宪的“新派诗”评价较高。其原因,正如王瑶先生在《谈晚清新派诗》中所分析的:“在没有彻底打破旧诗形式以前,要使诗能够容纳一定的民主主义的内容,而又不至破坏诗的表现力量,使诗仍能够发生艺术的作用,这就是新派诗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从这种意义讲。黄遵宪可以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代表诗人;不只在他的诗中富于反帝爱国的精神是这样,在诗的艺术成就上也是这样。”[4] 王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新派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意见是十分中肯和有见地的。他的这一观点确立了评价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的基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对于黄遵宪的“新派诗”,唯钱钟书先生有不同的评价。他在《谈艺录》中说:
(黄公度)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5](P23—24)
对钱先生这段评论,笔者想就如下三点谈些不同看法,请专家指正。
质疑之一:黄诗中是否仅“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先生说,公度是“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
黄遵宪的部分海外诗,由于创作主体对外国文化尚缺乏深入的认识与体验,可能有此毛病。比如他早期写的《日本杂事诗》(1890),其中有些诗是记述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维新前后的变化。因为作者旨在记事,所谓“网罗旧闻,参考新政”[6](P6),加之又采用短小的七绝形式,从诗的兴象与韵味来衡量,都有欠缺。说黄遵宪这类的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似无不可。但黄遵宪大部分描写新事物的诗,如著名的《今别离》、《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登巴黎铁塔》、《海行杂感》都应属“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佳作,并不缺少“新理致”。
描写异域的社会生活、自然风光,礼赞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科技、文学和艺术),体验全球性境遇中的感受,这本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放眼世界之后所出现的新的人文景观和新的审美感受,是近代诗人视野拓展、审美范围扩大、思想感情发生时代性变化的具体表现,黄遵宪诗歌有关这方面的内涵,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这个问题如果提得再高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和重要方面。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从原典出发,去解读黄遵宪的诗作。在黄遵宪的“新派诗”中,《今别离》是最为人们所熟悉和称赞的。何藻翔在《岭南诗存》中说:“《今别离》四章,以旧格调运新理想,千古绝作,不可有二。”[3](P1301) 陈三立评为“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作者神通至此,殆是天授。”[3](P517)。在解读这组诗作之前必先说明,为什么近代诗坛对《今别离》如此赞不绝口呢?原因就是梁启超所总结的黄遵宪“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或如范当世所分析的,该诗“意境古人所未有,而韵味乃醇古独绝”;也就是王瑶先生一语道破的:在近代,当旧形式还未被彻底打破之前,要想表现新内容,而又使诗不失其为诗,继续保持其艺术魅力,黄遵宪的《今别离》这类诗已达到了当时“新派诗”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今别离》用的是《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的旧题,写的却是近代科学的新成就。诗人以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东西半球昼夜相反这一自然现象来抒写男女离情,真是别开生面,独具韵味,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佳作,陈三立推之为“绝作不可再有”。这虽不免有过誉之嫌,但其惊喜、赞赏的态度亦由此而见。请看他咏轮船、火车的第一首: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这首诗的用韵与句意受到唐代诗人孟郊《车遥遥》的影响[3](P517),但诗人的感受已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所写的离情别绪,而是渗入了一种现代性的体验。诗首二句“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虽源于孟郊《远游联句》中的“别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但这里的舟车已非古代的马车、木船和轿子,而是现代的轮船、火车,“一刻既万周”,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的神速既使诗人感到惊奇,又增加了抒情主人公离别的悲伤:“眼前双轮驰,益增中心忧。”诗人说:“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古代的舟车可因人的感情需求而自由支配,可快可慢,可走可停;但现代化的轮船、火车却是按时间开动的,它不理会离别、送行双方别离的悲苦,而稍停片刻,“明知须臾景,不许少绸缪”,只要钟点一到,舟车马上启动。既不怕狂风,也不畏巨浪,无情地把对对情侣分开。现代舟车速度之快又让送别的一方难以接受,“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只好期待着:“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这首诗突出了现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惊人的速度,这对19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以火车、轮船的高速度来凸现情侣分别时的痛苦感受。这种由近代文明所引发的现代性的感受及生活体验是古典诗歌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诚然,这首诗虽然明显地受到孟郊《车遥遥》的影响,但同是抒写男女离愁的苦痛,同是以舟、车作为离别的抒情载体,黄遵宪的感受却有别于孟郊。《今别离》中的时空全变了,因而诗人的人生体验便具有了时代标志,也就是一种现代性。这点应引起研究主体的特别珍视。
这种时代标志或者说是现代性,使它的时空模式已不同于古典诗歌离别之作的时空模式。在黄遵宪的《今别离》中既有古今之别,也有中西之殊。这种古今、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在《今别离》另一首诗中有更突出的体现。诗云: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昨夕入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这首诗以东西两半球的时差(昼夜相反)咏一对情侣相思中的错位。在古代中国,虽也存在着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时间差,但由于活动空间的相对固定和生活的慢节奏,在人的时空意识上并不存在多大差距。黄遵宪写此诗时因生活在英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已有相当的了解,他认同于地圆说,对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已有实际的生活体验。诗人也正是以此为兴奋点想象一位妻子思念她远在海外的丈夫时梦魂的错位。
妻子做了一个梦,梦魂漂洋过海寻丈夫而去。“昨日入君室”,掀开床帷,人却不在,大约睡得迟吧!妻子又想到,“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因为双方所居为东西半球两地,正好昼夜相反,“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妻子抬头见明月正照在窗上,而此时的丈夫却刚好黎明披衣。正因为“眠起不同时”,所以“梦魂难相依”。这种两地昼夜时空的错位,使夫妻双方连在梦中相会都失去了可能,这便更增加了相思的愁苦与悲痛。生活在封闭境遇中的中国女性又无力冲破这种阻力:“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只有以海枯石烂永不变的爱来回报对方了。但客观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爱的坚贞更增添了相思的痛苦,“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表现了诗人一种新的审美取向。他不仅为西方文明的进步感到惊喜,而且把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亲身体验诉诸诗歌。它一方面开阔了古典诗歌的视野,增添了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也给传统诗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改革之风。封闭的诗歌传统要打破,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新理念逐渐进入中国诗人的审美范围。黄遵宪的创作实践为近代诗界革命树立了一面旗帜。
在黄遵宪诗中,新意境的诗篇是丰富多彩的。他不仅借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达诗人的一种新体验、新感受,而且还通过生活中常见的花的意象表达一种新理想和新的观念。他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就是一首这方面的代表作。梁启超批评此诗是“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1](P30—31)。这话大体不错,但并未点出诗的主旨。诗中确有新知识、新理趣,如云:“地球南北倘倒转,赤道逼人寒暑变。尔时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时之花开满县。”这里面显然含有地球运动、自然界变化的道理,但我以为这首诗的“新”,主要还在于表达了一种新理想、新观念,即表现了诗人一种“四海一家、和睦共处”的开放意识。诗中写诸花共处的神态:
一花惊喜初相见,四千余岁甫识面;一花自顾还自猜,万里绝域我能来;一花退立如局缩,人太孤高我惭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妩媚非粗踪。有时背面互猜忌。非我族类心必异;有时并肩相爱怜,得成眷属都有缘;有时低眉若饮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时仰首翻踌躇,欲去非种谁能锄;有时俯水嗔不语,谁滋他族来逼处;有时微笑临春风,来者不拒何不容。众花照影影一样,曾无人相无我相……。[3](P601—602)
诗人这里借花喻人,诸花的种种表现,恰是处于封闭状态下、互不来往的各国人民乍相会时的神情:或孤高自傲,目无他人;或畏缩自惭,互不接触;或互相猜疑。以为异种不能同心;或心存欺侮,同类自相残杀。诗人的理想是四海一家。携手共进。诗云:“传语天下万万花,但是同种均一家。”“花不能言我饶舌,花神汝莫生分别。”寓意是十分鲜明的。诗人所表达的是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和生活理想。再如:
主人三载蛮夷长,足遍五洲多异想。且将本领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养。莲花衣白菊花黄,夭桃侧侍添新妆。双花并头一在手,叶叶相对花相当。……如竞笳鼓调筝琶,蕃汉龟兹乐一律。如天雨花花满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黄白黑种同一国。
全球的各色人种和睦相处,这里分明是对大同世界的向往。黄遵宪在他的诗中对“大同世界”可谓三致意焉。仅在《己亥杂诗》中。“大同”就多次出现。“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他如“蜡余忽梦大同时”、“物情先见大同时”。再如《病中纪梦述寄梁任公》诗中云:“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足见诗人对大同世界的礼赞与向往。这种新的时代理想在他的另一组诗《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中也有反映。该诗其五有云:“昔日同舟多敌国,而今四海总比邻。更行二万三千里,等是东西南北人。”
“同舟敌国”,是春秋时代人吴起的一句话。《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对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这是讲历史,而今却是四海一家、天涯若比邻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广阔的胸襟和开放的观念。
在黄遵宪的海外诗中,除了吟咏西方自然科学新成就和自然现象的诗作外,还有描写异国风光、风士民情之作,也特别令人瞩目。诗中许多新意境让接受主体大开眼界。《伦敦大雾行》就是一例。这是一篇写得别有风味的佳作。英国伦敦有雾都之称,每年九、十月之交,伦敦即有大雾出现。每当此时,白昼晦冥,家家室内点燃灯火,面壁而坐。“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离离火焰青,漫漫劫灰黑。如渡大漠沙尽黄,如探岩穴黝难测。化尘尘亦缁,望气气皆墨,色象无可名,眼鼻若并塞。”“出门寸步不能行,九衢遍地铃铎声。”雾气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诗人在篇末笔锋一转,写道:“吾闻地球绕日日绕球,今之英属遍五洲,赤日所照无不到,光华远被天尽头。乌知都城不见日,人人反抱天堕忧。”这里颇有反讽意味。19世纪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天下,故有“日不落帝国”之称。但自己的首都伦敦反倒浓雾弥天,不见天日,以致人人有天欲堕之忧。这里或许隐寓着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讽讥。
黄遵宪这类“新派诗”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固然是因为它书写了域外的新事物、新景观,奇思妙想,绚丽多姿,令人神往,具有诱人的艺术力量。黄诗中的“新意境”,不仅在于它所描写的域外题材之新,更重要的是诗中所表达的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想、新理趣,给了读者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这是认识评价黄遵宪的“新派诗”时必须特别强调的。也正因为如此,钱先生说黄遵宪的这类诗,只“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是很不公平的。
质疑之二:关于黄诗因袭前人诗意的问题。
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座丰厚的文学宝库,后代诗人在创作中曾不断地汲取它的营养,借鉴它的艺术经验,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远的不说了,以近代诗人而论,即使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诗人也曾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过艺术营养。被评论家誉为“奇境独辟”、“别开生面”的诗人龚自珍,他的诗歌就受到屈原、庄子和李白的影响[7](P485)。他曾说:“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7](P485);“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7](P469)”;“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7](P255)。就具体创作而言,龚自珍诗歌中好用“怒”字,如“畿辅千山互雄长,太行一臂怒趋东”[7](P502)、“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7](P440) 等就是受到《庄子》“草木怒生”、“大鹏怒而飞”的启示。再如,勇于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谭嗣同,他的《怪石歌》以排比的散文句式写怪石的千姿百态,奇形异状,就明显地受到韩愈《南山诗》的影响。倘究其源,韩愈的《南山诗》又受《诗经·小雅·北山》及辞赋的影响,比物取象,尽态极妍,排比叠字,曲尽其妙。以上举例,意在说明,在诗歌创作中,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并不为奇,因为中国古典诗歌这个引力场能量实在太大了。关键在于继承中要有创新、开拓。
话再说回来,钱先生举的黄遵宪的这两首诗:《番客篇》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并不像《谈艺录》中所评论的,前者“不过胡稚威《海贾诗》”;后者“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云云。为申拙见,本文还是只能从解读原典文本入手。
《番客篇》是黄诗中一首著名的长达两千余字的叙事诗。该诗以华侨婚礼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我国南洋华侨的生活风习。另方面,诗中通过蒜发叟对婚宴上几位座上客的介绍,反映了华侨在南洋创业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切怀念和有国不能归的悲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诗中指出“国势弱”而又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无力维护华侨在国外的正当权益,而且还对归国的华侨富商,虎视眈眈,为窃取巨资,竞“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镬?”诗人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倘将此诗与诗人的《逐客篇》合读,更能体悟这首诗的深刻寓意。对黄遵宪这样一首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批判精神的长篇叙事诗,钱先生为了说明黄诗“无新理致”,仅以一句“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轻轻带过,其评价不仅“词气率略”(钱先生自评语)[5](P347),而且也不准确。黄遵宪《番客篇》真的是因袭胡天游(字稚威)的《海贾》诗吗?
胡天游的《海贾》是一首七古,全诗四十二句①,诗写沿海一带的富商为了巨额利润,买断东南诸省的棉丝织品,通过海上走私卖与日本和西方商人(“交易从倭蛮”),然后换回各种洋货,“载归王侯宅,百倍不计资”。为了赚钱,他们出生入死,“金钱出波涛,死生幸蛟螭”。这便是诗的大意。
胡天游的《海贾》与黄遵宪的《番客篇》,从题材、语言到艺术手法并无什么共同点,更看不出后者对前者的因袭和继承。钱先生的“不过”云云,在这里大约主要是指二诗在题材上的相近。其实,胡天游诗中的“海贾”和黄遵宪笔下的南洋华侨是相异的两种群体,并无共同之处。
钱先生评黄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的第二个举例,是《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此诗也是黄诗中的名篇。钱先生说:“《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这个“不过”云云,从表面上看还多少有点关联。黄诗的“莲菊桃杂供一瓶”与《淮南子·俶真训》中的“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毕竟有点貌似。但黄诗所抒写的思想意蕴却远不是《淮南子》这二十个字所能涵括的。
必先说明,黄遵宪写此诗的命意并不是原于《淮南子》,而是诗人外交生活中的亲身感悟。据钱仲联先生的《黄公度先生年谱》记载:诗人在任新加坡领事期间,因患疟疾,曾借居华人山庄养病。《己亥杂诗》第59首自注云:“潮州富豪佘家,于新加坡之潴水池边,筑一楼,三面皆水。余借居养疴。主人索楼名,余因江南有佘山,名之曰佘山楼。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亦奇观也。”[3](P833) 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即写此事,其主旨的确立即是对此感悟的生发,与《淮南子·俶真训》中那四句话并无关系。倘硬要联系,那二者只能是巧合而已。
评论作家的创作,能寻找出这位作家或具体作品继承关系的蛛丝马迹,有助于对作家创作的深入认知,但仅仅据其篇名或诗中某些词语的相近或相似,就判定这篇作品就是因袭了某某作家的哪首诗,而再用“不过”的句式下断语,这是否有点轻率之嫌呢?当然,我上面的解析与判断是否言之成理,甚或是曲解了钱先生的原意,那还请专家指正。
质疑之三:黄诗使用新名词,能否等同于“亦犹参军蛮语作诗”。钱先生说:“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钱先生的意思是,黄遵宪使用新名词入诗,并无什么新鲜之处,不过像“参军蛮语作诗”或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
先说参军蛮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云: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一次诗会,饮酒,他提笔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公问:“娵隅”为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后因称少数民族语言为蛮语。如果说,以新名词入诗“亦犹参军蛮语”或“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这种情况在诗界革命初期夏曾佑、谭嗣同的所谓“新诗”中也许可以找到。今各举一首为例: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8](P36)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曾为其作注云:“冰期、洪水,用地质学家言。巴别塔云,用《旧约》闪、含、雅弗分辟三洲事也。”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9](P246)
这首诗更是天书,有些词语倘不注释实在无法解读。比如“喀私德”,系英语Caste的译音,这里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成若干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系英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谭嗣同和夏曾佑这类“新诗”,曾如梁启超所言:“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1](P49)
对于谭嗣同、夏曾佑等“二三子”“新诗”中的这些谁也“无从臆解”的佛、孔、耶教经典。稍后,梁启超即作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1](P50)。因为这类“新诗”中的语言,“除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对于“新诗”阶段这类“经典”语(亦可称为新名词),正如钱先生所指出的:“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一评语,用在谭、夏的“新诗”上,尚称妥当;倘推而广之,用来评价黄遵宪的“新派诗”,则与事实不符,也有失公允。
众所周知,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语言符号是表达思想和事物概念的,随着社会的变化,新思想、新事物的出现,语言必然要更新,因此新名词的出现,乃是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在语言上的反映。诚如王国维在指出新学语新名词的输入是20世纪初文坛上最显著的现象时所分析的:“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0](P178) 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诗歌要革新、变化,首先就要涉及到语言。因此,在诗中出现新名词乃是必然的现象,也是诗歌革新的必经之路。或者说,它是促进旧诗蜕变、新诗诞生的催化剂。黄遵宪自己就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3](P762) 诗歌要向前发展,必然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就表现在语言上。梁启超曾提出“新派诗”必须具备三长:即新意境、新语句和旧风格。尽管“新语句”和“旧风格”常有矛盾,但作为反映近代新思想、新意境、新风味的“新派诗”必然要有新语句,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诗中必然要有新名词的出现。
黄遵宪诗中的典故和新名词与谭嗣同、夏曾佑诗中的新名词最大的不同点有二:一是黄遵宪使用新名词不是为了时髦,而是为了更好地反映时代内容;因此像谭嗣同、夏曾佑“新诗”中的“巴力门”、“喀私德”、“巴别塔”、“琉璃海”等佛、孔、耶教经典之类的新名词,从未见到。二是黄遵宪使用的新名词,不是只有“吾党二三子”才能懂得、“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的“故实”[1](P50);而是多数人都能了解的新词语。
黄遵宪诗中的典故和新名词,乃是出于表现近代新思想、新事物的需要,是近代新词语的一部分,不用这些新名词,就无法表现近代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和新的文化。质言之,不使用这些新名词,就不可能出现近代诗歌史上的“新派诗”。近代诗中这种新变革,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衡量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黄遵宪诗中用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独立、国家、爱国、革命、立宪、专制、国会、议员、国民、监督、领事、留学生、殖民地、共和、世纪、维新、法律、外交、传统、演说、假面具、炮台、地球、赤道、气球、同盟国、红十字、十字架、十字军,动物、植物、几何”,还有一些外国译名,如“欧罗巴、美利坚、鄂罗斯、格兰脱、亚细亚、伦敦、巴黎、哥伦比亚、苏彝士河”等②。这些新名词读者既容易看懂,而且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已成为现代汉语词语中的一部分。黄遵宪把这些新名词用之于自己的诗,实在是一种语言的革新,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钱先生说,黄诗使用新典故、新词语,像古人以蛮语入诗,或以佛典、梵语入诗一样,并无什么新鲜之处。把二者等量齐观,其偏颇是十分显明的。试问:上文所举黄遵宪诗中的新名词,有哪一个像蛮语中的“娵隅”呢?
所谓“新派诗”,一般指诗界革命前后革新派诗人所写的诗,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黄遵宪。黄遵宪的诗代表了“新派诗”(亦即诗界革命派的诗)的最高成就,因此如何评价黄遵宪的“新派诗”就涉及到对近代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评价问题。在本文对钱先生关于黄诗评价三点核心内容提出质疑后,我们再重新回到论文的逻辑起点:即如何评价黄遵宪的“新派诗”。
对黄遵宪“新派诗”评价最高、最得其要领的是近代另一位新派诗人丘逢甲。1900年冬他在读《人境庐诗草》稿本后写道:
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是为诗中嘉富洱;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纵横捭阖,卒告成功,是为诗人中俾思麦。[11](P316)
丘逢甲所指的“新世界诗”,也就是我们说的“新派诗”,主要指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四卷之后的诗,即他离开日本到美国之后写的诗,因为《人境庐诗草》卷四第一首是《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可见所谓“新派诗”主要是指写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的诗歌。在19世纪末,这类“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诗较之传统的古典诗歌是一次革新,虽然它未能全部抛弃“旧风格”(“旧形式”)是其历史局限;但对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我们仍应当给予历史主义的评价。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肯定。
第一,它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的审美领域,开拓了诗歌新的艺术世界。
古代的诗歌,其题材主要是写本国的事物,而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其审美范围则扩大到国外,特别是与中国昼夜相反的欧美诸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乃至异国风光,民俗民情,都成了诗人吟咏的对象。上面所举《今别离》、《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以及常为人称道的《伦敦大雾行》、《苏彝士河》、《登巴黎铁塔》均是其代表作。这些作品,内容新鲜,为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对开阔国人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均有积极的意义。黄遵宪诗歌中这些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并不是作家凭空想象或依靠一些文字材料连缀成章,而是诗人个人的亲身感受。所以黄遵宪的“新派诗”写来视角新颖、感受深刻、形象生动、富有诗美,这点研究黄诗的人众口一词,无庸赘言。而在我们肯定黄遵宪“新派诗”审美范围的扩大这点时,更不应当忘记的,是它对近代诗坛的积极影响。在黄遵宪创作实践的带动下,近代诗坛特别是诗界革命派诗人纷纷提出扩大诗歌审美范围、创造新意境的主张。康有为提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12](P288);丘逢甲说:“直开前古不到境,笔力纵横东西球”[13](P84),梁启超提出新歌要具有“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14](P190)。在其影响下,以《清议报·诗文词随录》和《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新派诗”千余首,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黄遵宪“新派诗”所带来的这一巨大影响是文学史研究者绝对不能忽视的。
第二,新的感知方式和新的审美感受,是黄遵宪“新派诗”时代性的进步。这应是评价“新派诗”更重要的一点。
所谓感知,是诗人对外部世界的刺激进行选择、评价和组织的过程。黄遵宪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长期的外交生活,丰富的国外经历,以及一定的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使他的思维方式较之当时一般的士大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对世界的选择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一元走向多元。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又使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作者对月的感知和审美感受就和古代诗人有了很大的差别。月亮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原型,中秋望月,更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主题,不论是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还是濮淙的“一夜梦游千里月,五更霜落万家钟”(《闻梁蘧玉已寓京口》),这个月亮都还只是诗人行止中的明月。在诗人想象中,它的空间范围的极限也未超出神州本土。而在黄遵宪这首诗中,由于诗人是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他对月亮就具有了全球境遇中的感受。“茫茫东海波连天,天边大月光团圆。送人夜夜照船尾,今夕倍放清光妍。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登程见月四回明,归舟已历三千里。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面对茫茫大海及轮船行驶之速,黄遵宪意识到时空在发生变化。诗人置身太平洋,“一舟”四句,已完全进入全球性的感受与体验。此时的宇宙已不再是古典性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种“中国即天下”的宇宙,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千世界”。在这个全球性的时空中,诗人的审美感受不复是古典式的仲秋之夜的皓月当空,因为西方没有中秋节,“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在西方人的眼中,八月十五/中秋节/团圆节和其他时间的月亮“圆了”一样。“只作寻常数圆缺”,表明黄遵宪对月亮的认识已属现代性的感知方式。正因为感知方式的变化,他面对太平洋上的明月所产生的审美感受也就具有了现代性。再看下面的诗句:
岂知赤县神州地,美洲以西日本东,独有一客欹孤篷。此客出门今十载,月光渐照鬓毛改。观曰曾到三神山。乘风竟渡大瀛海。举头只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
诗人在这里明确地把自己置于全球的境遇中。“岂知”二句,点明中国只是全球的一部分:“美洲以西日本东”。特别值得注意的,诗中用了“大瀛海”的典故。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人邹衍谓儒者所称中国,于天下只占九九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还有八个,乃所谓九州也,四周有裨海(小海)环之。被小海环绕的九州又可称为一大州,像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其外又有大瀛海环绕,此即邹衍的“大九洲”说。这里的“大瀛海”,指诗人曾经多次渡过的太平洋。但诗中援引邹衍“大瀛海”这一象征性的典故,寓意十分鲜明,它标示着黄遵宪已扬弃了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宇宙观,而具有了全球意识。
诗人正置身于太平洋舟中,时值中秋之夜,遥望故乡,浮想联翩。“举头只见故乡月,月不同时地各别,即今吾家隔海遥相望,彼乍东升此西没。”“举头”句源于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但这里只是想象之词,诗人在太平洋舟中是见不到故乡月的,因为处在东西两半球的中国与西方诸国是相背的,“九州脚底大球背”。且月不同时,昼夜相反,“被乍东升此西没”,这些新的感知,正是基于诗人一种崭新的全球观念。黄遵宪在诗中书写东西半球昼夜相反,脚底相背,在今天已属于小学生的常识,但对当时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却系闻所未闻。这和他在《今别离》中所写的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事物一样,都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3](P3),这种全新的审美选择和艺术感受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黄遵宪率先成功地将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和信息展现在封闭的中国人面前,其意义是巨大的。诚如当代著名诗论家谢冕先生所说:黄遵宪是率先把西方世界升腾起来的工业革命的光芒“投射在中国诗歌黑暗天空的第一人,他把当日世界那些最新的观念和信息,以及他所亲历而又为国人所陌生的异域风光展现在中国那些封闭的耳目之前,他使中国诗歌甚至使中国社会着实地经受了一次强刺激”[15]。黄遵宪在诗歌创作中这种新的感知方式和审美感受对于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示范意义。尔后以描写新事物、新思想和域外风光著名的蒋智由、康有为、金天羽、高旭、吕碧城等人都是承袭着黄遵宪所开拓的“新派诗”的道路前进的。评价黄遵宪的“新派诗”,对这一点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第三,“新派诗”的语言走向符合文学发展的要求。
“新派诗”在诗歌语言发展上是有贡献的。要而言之,即它的语言走向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语言走向是一致的。众所周知,近代文学的语言走向大要有二:一是语言的通俗化;二是语言的近代化。关于前者,已有多人论述。黄遵宪早在1868年写的《杂感》中就已提出“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虽然这一早期主张的诗学意义大于其实践意义。黄遵宪本人的诗歌创作并未能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口”,但结合《杂感》全诗来分析,他反对言文脱节、主张言文合一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所谓“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竞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这一点,他在尔后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又作了更详尽的阐述,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语言与文字存在的距离。这点我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走向世界的诗人黄遵宪》一章中已有阐释[16](第2卷,P29—30),兹从略。
语言的通俗化始终是黄遵宪努力的方向,他虽然未能完全实践“我手写我口”的理论主张,但他仍有不少诗篇写得通俗流畅,明白如话,像《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送女弟》、《小女》、《己亥杂诗》中的若干篇什都具本色,几乎如话家常,特别是他后期写的《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幼稚园上学歌》、《新嫁娘诗》等,明白如话,语言的通俗程度并不“雅”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周作人称黄遵宪的诗“开中国新诗之先河”[17](P326) 大约也是就此而言。
关于语言的近代化,我这里主要指新名词的运用。“新派诗”中使用新名词,是为了反映当时先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的需要,是现实生活飞速发展的投影,这些新名词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它对于促进现代汉语的发展,丰富其表现力是一大贡献。当然就现代汉语的整体而言,它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
黄遵宪“新派诗”语言的另一特色则是散文化,也就是“以文为诗”。黄遵宪在他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3](P3) 所谓“伸缩离合”,就是打破诗歌固有的句式、格律,纵横开阖,伸缩自如,以便更好地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抒发其感情。他的《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聂将军歌》均是这一语言特色的代表作。
第四,对诗体革新的贡献。
尽管梁启超对黄遵宪的“新派诗”评价很高,“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1](P2)。作为“诗界革命”的一个探索者,他并不满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一诗学理想。因为黄遵宪清楚地知道,“新意境”与“旧风格”是有矛盾的,因此,黄遵宪晚年提出了诗体改革设想,名曰“杂歌谣”的“新体诗”。关于“杂歌谣”的构想,及其在诗体革新上的意义,我已在拙作《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和评价》[18] 胡有详细论述,恕不重复。我这里所关注的是黄遵宪关于“歌词”的创作。像他晚年写的《出军歌》③、《军中歌》、《旋军歌》以及上面提到的《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便是他的“新诗体”(即“杂歌谣”)在创作上的实践。这类“新诗体”,除形式上的自由活泼、艺术风格的多种多样外,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在促进诗与音乐结合上的贡献。
中国的古诗本来是和音乐相配合的。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三者是分不开的。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全部入乐,所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词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言出于声,依声填词,与音乐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后来诗词均与音乐脱节。而在西方,欧美国家,颇重视歌曲,王韬在他的《普法战记》(1873)中最早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和德国诗人阿恩特(1769—1860)的《祖国歌》引入中国,黄遵宪晚年提出“杂歌谣”的构想,从事“歌词”创作,就有可能受到外国歌曲的影响,当然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诗与乐合的这一传统。
关于“歌词”的创作,黄遵宪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长期酝酿的结果,他到过世界各地,欧美、日本都十分重视唱歌教育,“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语”[1](P77)。这对黄遵宪是有影响的。黄氏喜欢日本的俚曲歌谣,他在《日本国志·礼俗志》中有专门记载,并写有《都踊歌》,此歌就是日本京都地区男女且歌且舞时的“歌词”。黄遵宪又生于山歌之乡,自幼喜爱山歌,对山歌歌手十分钦羡:“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3](P55) 看来,黄遵宪关于“歌词”的创作是他晚年实践诗体革新,促进诗歌与音乐结合的重要的一环。他写的《出军歌》④,后选入“学堂乐歌”,由近代音乐家李叔同(1880—1942)选曲配歌,在当时颇有影响。黄遵宪认为这类歌词“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3](P1259),可见他是十分注意其音乐特点的。他还仿西方列队歌曲形式,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此歌凡十九章。据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其歌以一人唱,章末之三句,则由诸生合唱。”[1](P60) 黄遵宪用古代乐府诗中的“和声”来相对于西方歌曲中之“副歌”。“和声”的合唱,反复歌唱,既深化了主题,又增添了一唱三叹之妙。他的《幼稚园上学歌》也被选入《最新妇孺唱歌书》(光绪三十年五月初版)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光绪三十三年初版),可见黄遵宪所写的“歌词”在当时的反响。
黄遵宪的“歌词”创作对近代诗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他的影响下,近代诗坛出现了“歌词”创作的热潮,丘逢甲、梁启超、康有为、高旭、马君武、秋瑾、金松岑、杨度等人都写有“歌词”体的诗歌;另一方面,在黄遵宪《出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的示范下,随着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又出现了“学堂乐歌”,恢复了古代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在沈心工(1870—1947)、曾志忞(1879—1929)、李叔同的努力下,掀起了“学堂乐歌”的创作热潮,编辑出版了《学校唱歌集》三集(1904—1907)、《民国唱歌集》(1912)、《心工唱歌集》、《教育唱歌集》、《中文名歌五十曲》,以及金松岑编的《新中国唱歌》、《女子新歌初集》(1914)、叶中泠编的《小学唱歌》、胡君复编的《新撰唱歌集初编》等。在评价“新派诗”时,对黄遵宪的诗体改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也不应忘记。
以上四点是认识、评价黄遵宪“新派诗”的主要方面。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我仍想重申: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尽管从诗歌艺术上来衡量还不是那么成熟,在中西诗歌艺术融会上也存有缺憾,它也未能达到古典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但我们仍应当承认,“新派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它是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桥梁,是由旧诗走向新诗(白话诗)的必经之路,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都是诗歌发展、变革历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就这一意义上来讲,“新派诗”的历史地位,它的文学史意义要高于它的审美价值。我还要说:孤立地看“新派诗”,特别是从当代人的知识背景,黄遵宪等人的这些诗或许并无什么特别的新奇之处、新鲜之感,但倘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便能发现“新派诗”不论是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是在由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的转型方面,它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
收稿日期:2007—03—06
注释:
① 见钱仲联《清诗纪事》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0~4831页。
② 据刘冰冰博士统计,黄遵宪诗中使用的新名词有201个,计社会科学类74个,自然学类5个,人物、地名等专用名词122个。详见刘冰冰《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运用》,《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③ 以下所举黄遵宪的歌词,限于篇幅,均不引原文,此类文本见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人境庐集外诗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另见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 黄遵宪的《军歌》共二十四章,分《出军歌》、《军中歌》和《旋军歌》,各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