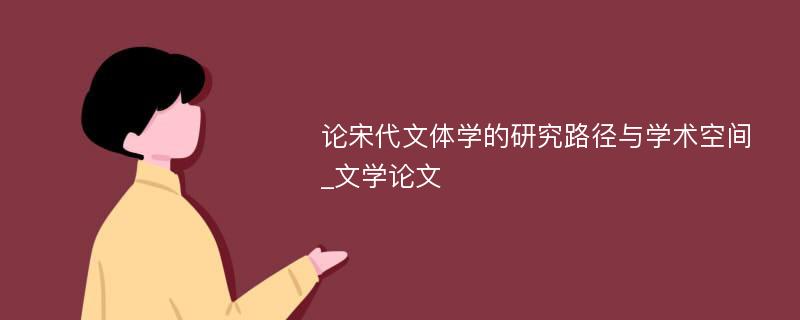
论宋代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文体论文,路径论文,学术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9)02-063-04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形态嬗递演进的历史。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有极大的学术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笔者认为,文献史料是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和基石,而文体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则是宋代文体学的两翼。宋代文体学研究应该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努力把文体研究和文体批评研究有机地融通结合起来。本文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体为关注核心,注意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一些问题,思考了如何对几乎是空白的两宋时期的文体学进行研究,探讨了断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范式。
一、当前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现状
吴承学、沙红兵在2005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一文,“通过对基本内涵与对象的探讨,勘划了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大致范围和性质”。该文认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等六大方面。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建立古代文体学学科还存在争议,认为诸多问题尚待深入周密的探究;但古代文体学研究早已从昔日的冷门逐渐转变为富有巨大潜力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依笔者看来,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主要就是三大块:首先、文体研究。这包括具体文体、文体间关系和文体发展流变的研究。其次、文体理论的研究。诸如作家的文体意识、文论家的文体批评和古代文体理论史的梳理。再次、有关古代文体文献史料的搜辑整理。针对不同情况可以采取点校、资料汇编、集释等多种形式,这是文体研究的基础工程。概而言之,文献史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石,而文体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是文体学的两翼。无论文体学学科能否成立,文体学本身都不失为一门具有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的学问。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体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呈蓬勃发展的良好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古代文体学方面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就专著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推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和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二书堪称新时期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标志性论著。其二、成立了两个文体学研究中心,召开了一系列以文体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于近年相继成立文体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还创办了国内首家以文体学研究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网站。文体学已成为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古代文体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不过,这一阶段发展虽快,却也有它不成熟的地方。首先,研究意识和理念存在偏差,对古代文体缺乏一种“了解的同情”。文体研究一直以来多把注意力集中到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门类上,以今人的文体观为标准去衡量想象古代的文体状况,“以今律古”的偏差直接影响了古代文体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古代文体的“原生状态”。其次,研究布局极不平衡,缺乏整体规划。就文体批评研究而论,多年以来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一段,其中又以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研究为主,其他时代的文体批评均付阙如,似乎文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史中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古代文体研究文献的辑集整理也亟待展开,除了《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常见常用论著外,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有价值的文体史料,如明代贺复徵编选的总集《文章辨体汇选》、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包含的文献资料就异常丰富,尚须我们善加发掘利用。我们欣喜地注意到,王水照先生主编的煌煌十卷本《历代文话》已经出版,标志着古代文体文献的整理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吴承学先生主事之《中国古代文体史料集释》和《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学》也在进行之中,非常值得期待。再次,文体研究和文体批评研究各行其是,仿佛两股道上跑的车,割裂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犹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需要相辅而行一样,文体和文体批评也不宜分而视之,它们是整个文体学研究的两翼,最佳途径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上述诸端是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在文体学的研究路径中,断代文体学研究无疑是方兴未艾的新鲜课题。到目前为止,已有两部断代文体学研究专著面世,分别是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贾奋然《六朝文体批评研究》。魏晋南北朝无疑是古代文体理论研究较为充分的朝代,能不能把目光转移到其他缺乏关注的朝代?能不能把某一朝代的文体研究和文体批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论述?能不能从文体学的视角审视解决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问题?在思考过程中,宋代凸显出来,宋代文体学逐渐进入了笔者的学术关注视野。目前的学术界如果能对几乎是空白的两宋时期的文体学进行一番考索探究,当能给当前蓬勃展开的古代文体学研究提供一点启示,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二、宋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何谓文体?一般认为,文体是文学作品的语言系统、结构形态、表述形式诸要素的有机统一,它既指文学体裁,也指不同体制、体式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文体”又称“体”、“体裁”、“大要”、“大体”、“势”或“体制”等,这些概念范畴的内涵相当丰富,分别指向文体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结构形式和风貌特质等理论层面上的诸多问题。
华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三千年遗留下来的文章典籍浩如烟海。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学史、文章史亦即一部文体流变史。各种文体的萌芽、初步成型、发展成熟、完备定型,乃至变化演进、此消彼长,深刻反映了社会、时代、语言、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就古代文学史而论,一直以来重点关注的文体主要是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类别。这四种文体并非在文学发展史上同时出现、齐头并进的,它们的萌芽、草创、发展、成熟、凝定、变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文体的地位、价值、影响和相互关系在文学史上也各不相同。
先秦作为古代文体的萌生期,主要文体形态表现为诗、骚、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汉代的主要文体是赋和散文,诗歌出现了新变的迹象。魏晋南北朝可以看作古代文体学历程中的一个承启上下的关键时期,文体和文体理论都获得了跨越式的蓬勃发展。诗歌方面的永明体昭示着近体格律诗不久就会瓜熟蒂落;骈体文成熟并给赋带来了一定的骈化色彩;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应用性文体,如表、章、奏、议、对等公牍文,碑、诔、哀、吊等哀悼性文体,书信、铭、箴等其它文体,都流行广泛、有较大发展;小说一体也草创伊始而规模初具。唐宋两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文体获得大发展的时代。古代各种文学文体和应用文章都大体完备、走向繁荣。唐代诗歌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骈文应用范围广泛,散文文体在中唐进行了可贵的改革探索,唐传奇的出现代表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尚待充分发展的词体又给宋代文学留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宋代文学大致是顺着中唐以来的发展路径而继续前行、蔚为大观的,融会贯通成为总的时代特征。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中唐至北宋一段为我国封建社会一大转关。宋代是具有近代指向意义的近古的开端,是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说:“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1]在综合基础上求新求变正是宋代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如果考虑到文体发展的均衡性和发达程度,宋代文体学比唐代更为全面深入,我们不妨把宋代定位成一个文备众体的时代,诗歌、散文、小说、戏曲都在蓬勃发展,各自走着属于它们自身的文体流变之路。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体嬗变,总的趋势是新陈代谢、与时俱进。文体嬗变的基本方式约略有三种:首先,文体内部的继承和革新。每种文体都有渊源流变的复杂过程,譬如诗歌,从古体到近体,从四言、五言再到七言,屡次突破自身传统形式,诗体得以不断演进,旧与新之间的继承创新关系明晰。其次,文体与文体间的相互渗透和吸收。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文体间发生关系往往会深刻影响到文体的形态。宋代的文赋和四六,就是因为赋、骈文分别与散文发生了艺术上的交叉和渗透,从而产生变异,呈现出某种新变色彩。文赋和四六分别是一种散文化了的赋和骈文。再次,外来文体形式的冲击和移植。这是指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体通过某种传播媒介,与本国固有文体发生关系并有机融合,而形成新的文体。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从西周到宋实际是一部诗史,而南宋开始,线路开始转向,此后就是小说和戏剧的时代。而这,是与印度文化的介入和影响密不可分的。他写道:“我们至少可以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和戏剧。……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的福分。”[2]佛教文化的输入不但促进了“宫体诗”、“永明体”的出现,还增添了变文、偈颂等新品种,深刻影响改进了中国古代固有的文体形式。
为了能立体地、多层面地研究宋代文体,我们可以从文体的生成和嬗变方式的角度,把宋代文体约略分为承袭前代而续有发展的文体(诗歌、散文、词等)、文体间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异的文体(文赋、四六等)和新创文体(话本小说、宋杂剧和南曲戏文等)三种形式。显而易见,上述文体并不在一个平等层面,它们的体制、功能也颇不相同。诗、词、散文、文赋、宋四六略属于一个层面,这是宋代的主要文学文体。至于宋杂剧、南曲戏文、笔记、诗话,有的还未成熟,有的可以归并到散文中去,还有的文体形态呈现为散文、骈文、诗词的综合体。总之,每个时代既有新文体应运而生,也有旧文体寿终正寝,还有些文体穷则思变,在汲取新鲜血液后获得新生。一般而言,后来的文体必然会向比它历史悠久、地位显赫的强势文体寻求依傍。
至于古代文体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形式,每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乃至嬗变、衰亡的历史,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思潮,反映了文学创作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古代很多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文体批评,最负盛名的《文心雕龙》实为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许多重要问题都与文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古人的辨体、尊体和破体的文体观念,雅文学与俗文学,诗学里的唐宋诗之争,词学里的“以诗为词”和词“别是一家”等等。深入研究古代文体学,对理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推进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研究往往能起到纲举目张的显著效果。
文体问题在宋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尤其凸显、特殊和重要。传统的宋代文学研究,从文献整理,到作家作品、源流派别、思想艺术等等,成果极为丰富。传统研究虽分体为之,然而并非以文体为研究的本位与核心。宋代的文体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关于宋人的文体意识,各种文体的形态与关系,文体的分类和文体批评的特征,尤其是宋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破体为文现象及其意义等,虽有学者从某些方面予以注意,却较少作深入系统的观照考察,由此言之,宋代文体学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空间。
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唐至北宋一段,承前启后,为我国封建时代一大转折。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3]。宋代文化繁荣和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是文坛的花团锦簇与文学理论的深入推进。相对而言,宋代的文体形式和文体批评也同样呈现出新的形态和特征。金代王若虚云:“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4]推崇备至。宋代文体形式的新变发展带动了文体理论的突破创新。宋代文体学是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关捩点,它上承六朝隋唐,下开明清,以宋代为文体研究的坐标中心,可以把握我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形态、发展脉络和地位价值。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多方面推进,文体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对各种文体形态及其理论的研究开始予以较多关注。宋代文体学研究的是前人有所启而未遑发,尚属薄弱而又亟待开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文体角度研究宋代文学,有助于充分认识宋代文坛所展现的多种文体相辅相成、百花齐放的文学繁荣局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人的文体观念、把握宋代诸文体发展流变的轨迹、确定诸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探讨文体交融互渗对文学史演进所具有的深层意义,有助于从宏观把握文体和文学的关系、探索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
三、以文体为核心观照宋代文学
文体研究无论在中国抑或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牵涉广泛的大学问,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文体学却主要源于西方。西方文体学与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美学等很多学科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的文体研究没有致力于本国文体理论的系统化与学科建设,而主要呈现为一种输入西方理论、借鉴他国方法的单向流动局面。不必讳言,这种以吸纳输入为主的局面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对于积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体研究而言,在学术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尤需慎重,应始终对古人怀有一种“了解的同情”,万不可简单地以西律中、以今推古。显而易见,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体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文体,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没有严格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古代的文学并不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而是当时整个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古人秉持的是一种泛文学或曰杂文学的观念意识,开放性的文学概念致使文学不断拓其疆宇,无所不包。不过文学还是具有一定的标准,不妨把敷文藻饰和审美效果算作古代文学区别非文学的认定因素。因为古代文学内容的广博,古代文学文体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大大超出了今天“文学四分法”的涵盖范围。美国文论家韦勒克、沃伦说:“文体学的纯文学和审美的效用把它限制在一件或一组文学作品之中,对这些文学作品将从其审美的功能和意义方面加以描述。只有当这些审美兴趣成为中心议题时,文体学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5]研究古代文学,适宜具备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文学史观;而研究古代文学文体,则最好采用宽口径的大文体观。以审美价值为标准界定古代的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就能把古代的大部分文体纳入研究视野,让研究更符合古代文体的原生状态,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由此言之,我们所说的古代文体学实是一种以文学为本位、文体为关注核心的综合立体研究。
作为一种断代文体学的研究尝试,宋代文体学研究可以深入探究两宋时期的文体和文体批评,通过文体这一研究路径,进而审视宋代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问题,以期开辟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新领域,对文体研究本身而言,也必然能得出富有理论价值的新见解。
就具体问题而言,宋代文体学发展的学术空间实在很宽广。文体形态和文体理论,宋代诸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推进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比如,古代文体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很多在古代十分重要而历来缺乏研究的文体尚待开掘;而宋代文体批评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也少有人关注。古代文体分类的情形尤其复杂,宋代在文体分类方面有没有新进展?宋代文体批评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宋代文体研究的意义及相关理论问题颇为耐人寻味。在解决诸多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把宋代文体学置于整个古代文体学的系统流程中加以观照,就文体的古今之变、雅俗之辨和文化意味等论题进行翔实而全面的评述。显而易见,这种研究是富于创新色彩的,是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新探索。
笔者在研读了大量文献史料和研究素材后,对于宋代文体学,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思考,同时阐明与之相应的学术观点:
一、定位问题,宋代文体学的历史定位。我们不妨把宋代文体学定位为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宋代文备众体,各种文体都获得极充分的发展空间,承袭前代的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戏曲、小说也崭露头角、一试身手。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作为古代文体论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宋代文体批评多层面、多角度地深入探究,提升了文体研究的理论水平,对明清两代的文体批评有重要影响。
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其时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但它们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地一枝独秀,而是有其它多种文体与其相互扶持,相互交流,乃至相互竞争,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新鲜血液和推动力量。宋词是一代之所胜,但不是一代之专擅,词的大放异彩端赖“文体大家庭”的众星拱月、一力扶持。
三、经过细致考辨,可以推断联系宋代各文体的纽带是散文。虽然宋代的各体文学发展较为均衡,但并不意味着宋代文体的发展是平行的,没有主次的;通过对宋代诗、词、散文、赋、骈文、话本等主要文体的流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辨梳理,可以得知诗、词、赋、骈文、话本等都或多或少接受了来自散文的影响。散文能对其他文体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多方面接受散文影响,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增强了文体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了传统文体的更新和新兴文体的发展,使宋代文学出现多次重大开拓。
四、各种文体的协调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文体犹如物种,文体生存状态犹如生物界的生态体系。物种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类型,包括中性作用、正相互作用、负相互作用,而文体间也具有相互依存、竞争的关系。各种文体相互参融、相互渗透是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文心雕龙·通变》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体间的参融借鉴有利于发掘各种文体的表现潜能,极大地丰富艺术技巧,对创造别开生面的文学面貌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宋代,如果没有赋与散文的相通合流,就没有文赋的出现;没有诗和文的渗透,就没有词在格调境界上的提升;没有诗、文、词等几种文体的综合融摄,就没有戏曲和话本小说的重大开拓。
五、文体演变的背后具有耐人追寻的文化意味,文体的发展和演进往往映衬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特质。宋代文体学的创辟新变根源于成熟繁荣的宋代文化背景,研究文体离不开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文化对文体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
王蒙说:“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文学构思的怪异表现为文体的怪诞。文学思路的僵化表现为文体的千篇一律。文学个性的成熟表现为文体的成熟。文体是文学的最为直观的表现。”[6]宋代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宋代的文体实践和文体理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非常突出。作为一块引玉之砖,拙文旨在引发学术界对几乎是空白的宋代文体学研究的更多关注。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体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诗歌论文; 宋朝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