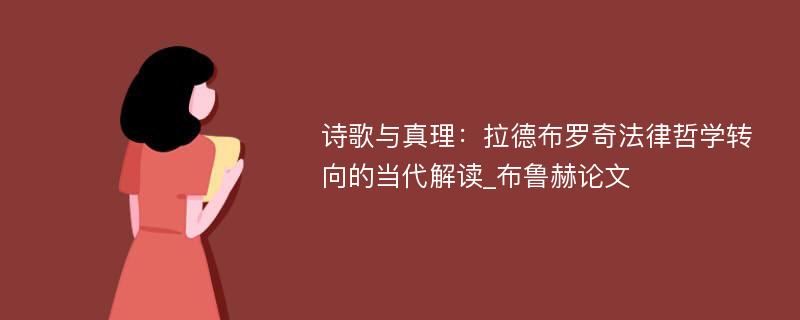
诗与真: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向的当代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德论文,布鲁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数年诉讼,引人瞩目的“柏林墙射手案”终于在新世纪初宣告谢幕。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对克伦茨、凯斯勒、施特雷利兹等人的有罪判决。在长达58页的判决书中,大法官威尔哈珀先后十余次提到一位德国法学家的名字——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他宣称,由这位法学家原创并以其姓氏命名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如今已经不再适用。① 所谓“拉德布鲁赫公式”,是拉德布鲁赫在194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法律的不法和超法律的法》中提出的:凡是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是构成正义的核心——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不正确的法,甚至根本就缺乏法的性质。② 二战后,由美、苏等战胜国组织的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战犯们辩称,他们并没有犯罪,只不过是在执行战时德国的法律。一筹莫展的法官们苦苦寻觅,终于在“拉德布鲁赫公式”中找到了作出有罪判决的依据。二战后至今,这一公式一直被德国法院援用,也成为海牙国际法院审理战争和种族犯罪的法理依据。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欧洲人权法院突然宣布“拉德布鲁赫公式”无效,是否如学者所预言的那样:以富勒目的论为核心的新自然法学终于倒下了虚张声势的道德大旗,而以哈特规范论为核心的实证主义,虽然一度破绽百出,却在现代司法技术和程序规范的协助之下重回主流了?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溯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拉德布鲁赫时代,重新审视他的法学哲思,并对他去世后法学界争论不休的所谓“转向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一、争论及其源起
从1902年完成博士论文,到1949年去世,拉德布鲁赫的写作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有史以来动荡最剧烈的半个世纪中,拉德布鲁赫在从政从教的间歇,在不同政局和思想背景下撰写的著作,并没有型构一个结构完美、无懈可击的体系,相反,其间充满了冲突和张力。这些冲突和张力引发了德国乃至世界法学界的激烈争论: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在二战后有没有经历重大“转向”?二十世纪后半叶,拉德布鲁赫成为法哲学论争中最经常被提到的人物,在著名的“富勒—哈特之争”中,就多次出现拉德布鲁赫的名字。时至今日,争论旗鼓仍未偃息,以S.L.鲍尔森等为代表,关于拉德布鲁赫的研究还在继续。④
最早提出“转向说”的,是弗莱堡大学教授弗里兹·冯·希佩尔。在1951年出版的《作为法哲学思想家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中,希佩尔指出,在前期拉德布鲁赫和后期拉德布鲁赫之间,经历了一次类似禅宗顿悟的“大马士革体验”。⑤在道德重建论主导的战后思想背景下,不少学者(很难说不是移情功能的作用)认同希佩尔的观点,认为拉德布鲁赫的思想经历过重大转向,并多将转向原因归之于战争创伤。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在经历了纳粹时期巨大的社会变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后,拉德布鲁赫开始修正他以前的理论观点,转向了‘温和形式的自然法’。他认为,为了使法律名符其实,法律就必须满足某些绝对的要求。他宣称,法律要求对个人自由予以某种承认,而且国家完全否认个人权利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另外,拉德布鲁赫还放弃了他先前的一个观点,即在正义和法律确定性之间发生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实在法必须优先。他认为,法律实证主义使德国无力抗御纳粹政权的暴行,完全非正义的法律,必须让位于正义。”⑥
而以拉氏弟子考夫曼教授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持“连续说”的观点,反对“转向说”。他们认为,虽然拉德布鲁赫前后论述小有出入,但总体上是连贯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考夫曼认为,必须完整地理解拉德布鲁赫的作品和人格,否则就会错误地归纳拉德布鲁赫思想的特征。当人们把拉德布鲁赫打上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相对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自然法学者或其他什么印鉴时,就决不会获得完整的拉德布鲁赫形象。只有掌握了拉德布鲁赫二律背反、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才能正确地评价他。一旦把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看作是“非此即彼”的认识模式、在“麻木不仁”的意义上来解释拉德布鲁赫的实证主义,就自然会在拉德布鲁赫的思想中发现裂变,看到“初期的实证主义的拉德布鲁赫”与“晚期的基督教自然法学的拉德布鲁赫”之间的不同。考夫曼的结论是:拉德布鲁赫思想决没有根本的改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不求永恒占有,但求持续接近。持“非此即彼”观的人们,认为法学家要么只能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者,要么只能是彻底的自然法学者,不但“根本没有考虑到问题的点子上”,而且正是拉德布鲁赫经常严厉批评的观点。如果问拉德布鲁赫是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或是不是一个自然法学者,这一提问立场本身就是错的,拉德布鲁赫总是同时属于二者,但随时又各有侧重,因而归根结底,他是超越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的。⑦
拉德布鲁赫的另一名弟子艾里克·沃尔夫也持坚定的“连续说”。他认为,虽然拉德布鲁赫第一次明确提出正义的价值位阶高于法的安定性,是在二战后的《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中,但早在一战前的《法哲学入门》中,他就已经使用“自然法”一词作为引入这一新思想的理论工具。拉德布鲁赫所说的自然法,不是古典的实在论的自然法,也不是所谓“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而是在每一实在法自身中都存在的一种正当化的根据。拉德布鲁赫区分的正义、安定性与合目的性这三种价值,只不过是同一法律理念的三个不同的作用方向。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正义、法的安定性、合目的性三者之间的交互冲突,是正义与其自身的对话,是所有法律不可消解的内在紧张关系,是法律与生俱来的基本矛盾。直至晚年,拉德布鲁赫仍然认为,上述矛盾和悖反既不可能在形式上得以消弭,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其实质内容。他固守这一看法,只是强调的重点时有不同。沃尔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促使拉德布鲁赫对其法哲学思想进行根本的改造。
1990年代后,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向问题的争论也延伸到了中国法学界。大陆学者多数持“转向说”,如最早介绍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的沈宗灵教授认为,二战后,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批判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迅速地转向自然法学”。此外,张文显教授认为,拉德布鲁赫的后期言论“标志着他转向了自然法,这一行动彻底瓦解了德国的新康德主义。”何勤华教授认为:“纳粹政权对法制的摧残和在法西斯主义法律之下干的大量暴行,深深地刺激了拉德布鲁赫,促使他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出深刻的反思和重大修改。”陈根发教授认为,“拉德布鲁赫抛弃了他坚持多年的法律相对主义立场,将注意力集中转向以正义和人的尊严为内容的人类终极价值的自然法。”⑧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只是较低程度地认同“转向说”,他们更细致地注意到拉德布鲁赫学说中的连续因素,并将它们与变化因素区别开来。如米健教授认为,二战后拉德布鲁赫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以往关于法律价值的相对主义观点,但他具有的自我放弃而实现历史的转变、不自我否认而面向思想潮流的能力,在转变中没有偏离已选定的方向。舒国滢教授也倾向于“转向说”,认为经历了纳粹统治的剧变后,“拉德布鲁赫的思考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五分钟法哲学》反映了他的“重新思考”,《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则清晰地确立了“新获取的立足点”,但同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拉德布鲁赫“思想的多线条交织的复杂性,很难用‘自然法学’、‘实在法学’或‘实证主义法学’来概括其思考的主旨。”⑨ 台湾学者林文雄也认为,“拉德布鲁赫晚年虽然偏向于自然法论的倾向甚明,但仍未达于放弃其法哲学基本立场的程度。”柯耀程则认为,拉德布鲁赫在法哲学领域中调和了实在法与自然法势不两立的僵局,向沉沦已久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⑩
二、政治与学术间的使命抉择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拉德布鲁赫的自然法思想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呢?要真正理解一位法学家,尤其是,要真正理解一位在政治动荡年代中担任政治要职的法学家,仅仅阅读其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学说和思想一旦与政治意识形态接壤,就不再是单纯的学说和思想,而是成了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政治行动本身。(11)
拉德布鲁赫是吕贝克人。吕贝克是魏玛共和国18个邦区中最小的区,远小于强邦普鲁士。(12) 与盛气凌人的普鲁士人不同,吕贝克人大多信奉共和主义,拥护新生的魏玛共和国。共和国成立第一年,正是基于这种拥护,拉德布鲁赫加入社会民主党,从学界转入政坛。次年,他当选民主党议员党团成员、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新社会民主党党纲的修订。用拉德布鲁赫自己的话来说,“法律职业人不仅要成为实在法的侍者,而且还必须成为正义的侍者”。传统的以实证、内推为特色的德国法律职业作风,在拉德布鲁赫看来,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社会人民国家的要求,“要有新的法律职业人、新的职业观点和职业立场”。(13)
然而时运不济,魏玛共和国从建国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多舛的命运。巨额负债、路线纷争、政治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无名险阻,紧紧地缠绕着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马克贬值了40%,更为巨幅的贬值还在后头,经济崩溃还仅仅是开始。1920年,国防军和右翼政治家集团在基尔发动“卡普政变”,企图恢复一战失败后退幕的君主政体。拉德布鲁赫与另一位民主派法学家赫尔曼·黑勒一起,试图阻止政变分子与工人的流血冲突,一度被叛乱者拘捕,面临死刑威胁,幸而政变很快失败,才免遭劫难。这一经历使拉德布鲁赫意识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划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不可能持续兼顾。政治活动整天吵吵嚷嚷,缺乏学术活动的理论根基,但却比教授在研究室里的沉思默想更有力。在动荡的政局中,任何不知抉择、骑墙其间的人,都会被挤得粉身碎骨,“即使傻瓜手中的枪,也比智者的全部理论更有力”。(14)
1921年10月,拉德布鲁赫由总统艾伯特提名出任维尔特内阁的司法部长,迅速着手起草《少年法院法》等法案,开始新设劳工法院、扩大罚金刑适用、减少短期自由刑等工作,其整体思路是,将魏玛民主精神纳入法治模式并确定下来。当然,最重要的,是新刑法典的起草。没有人比拉德布鲁赫更适合这项工作了。学生时代的拉德布鲁赫,就是古典规范论大师宾丁和刑事社会学派李斯特的双重弟子。作为学者,他是李斯特和费尔巴哈的思想继承人,主张矫正主义,改恶为善,反对威慑和报复,反对死刑。但是,作为司法部长,拉德布鲁赫更为深刻地理解时代的要求,更清醒地意识到,刑法典的成功修订,远比学术派系之争更重要。当必须解决一项实际的时代任务的时候,就一定要把乌托邦的理想、学者的理性构思与现下的可能性、局限性区分开来。(15)
然而,德国的政治形势,正朝着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最黑暗的方向发展。经济持续恶化,共和政府举步维艰。普鲁士不断叫嚣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巴伐利亚屡屡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战后德国的困境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归咎于民主派的外交柔弱和政治胆怯。极右的民族主义早已急不可耐,很快将不满情绪具体化为血腥行动,1922年6月,两个青年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暗杀了外交部长拉特瑙,因为他是民主派,是犹太人。就在拉特瑙遇刺这一天,马克对美元的比价还维持在350马克兑1美元,七月就跌至670马克,八月跳跌至2000马克,十月更是暴跌至4500马克兑1美元。(16)
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没有人可以僵守路线一成不变。恶劣的政局汹涌向前,根本不会理睬法律家对正义的忠诚。拉德布鲁赫意识到,墨守成规的传统德国法律职业到了应当警醒的时候,“法律就是法律”、“马克就是马克”、“选票就是选票”的实证信仰在和平年代行得通,在混乱时局中只会沦为陈词滥调,不但一无是处,而且害人害己。在拉特瑙的悲剧面前,那些君主制时代选拔出来的正规法院法官,不可能采取有力措施阻止灾难再次发生。共和国必须坚定地运用权力捍卫自己。在维尔特内阁的紧急会议上,拉德布鲁赫积极赞成根据《魏玛宪法》颁布一项保护共和国法令,对于那些公开赞颂和煽动暴力政治的人进行惩处。法令还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立“保护共和国国家法庭”,专门审理反对共和国的罪行。(17)
正如拉德布鲁赫意识到的那样,学术与政治是如此不同,不但分属不同的道路,而且需要不同的使命感。学术活动依据已有的资料,面对全方位的受众,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政治活动面对变幻莫测的利益关系甚至生死存亡,在不同的受众面前须采取不同的表达策略。政治活动中的术语运用、修辞选择以及论证方式转换,从来不在于保持连续性,而在于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激发受众的情绪,进入他们的思想边界,树立权威性。(18) 因此,如果说拉德布鲁赫有时让人觉得忽左忽右,显得立场并不坚定,那可能是因为撇开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只是从学术角度看问题。只有将拉德布鲁赫的言行与其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其真实立场才能被理解。正如维亚克尔在评价萨维尼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所进行的法学更新可被视为司法政策行动。就此而论,如欲掌握其意向的全貌,就必须认知他对当时的纷乱与各种方向所持之政治基本态度如何。”(19)
作为职业法律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拉德布鲁赫,是持中间偏左路线的政治家,从政初年,纳粹势力尚未占领政治主舞台,政府是由中间偏左或偏右立场的党派联合组成的,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持共和国的稳定。在妇女权利、劳工问题、出租承租关系、非婚生子女等问题上,拉德布鲁赫的左倾立场,是与共和政府平息社会矛盾的立场一致的。而在卡普政变后对极右分子的审判中,拉德布鲁赫的偏右路线,同意对鲁登道夫将军不予起诉,对叛乱分子处以较低刑期,则是内阁左右派系间的妥协的产物,为了尽快达成一致,不得已而为之。(20) 时局多变,措不及防,作为司法部长的拉德布鲁赫,当然不能坐而论道,而是要与整个内阁一起,在动荡的政治波涛中寻求平衡,防范极右和极左两方面的敌人。(21) 拉德布鲁赫最亲密的朋友坎特洛维奇的名言“法学不要摆脱政治,以便不使政治有一天摆脱法学”,似乎正是拉德布鲁赫学术与政治活动的写照。(22)
认为拉德布鲁赫在二战后经历了一次“大马士革体验”、从实证主义立场转向自然法立场的观点,显然没有看到,其实早在1920年代,这种立场的变化就已经作为整个德国法学界的一种重新思考而展开了。自保罗·费尔巴哈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德国法律家们一直都被要求绝对服从成文法,他们信奉的理念是“法官必须执行法律,不管他是否喜欢。没有什么比一个法官把个人的是非观念置于法律之上更受唾弃。”(23) 但是,在前所未有恶劣形势面前,学者可以坚持“法律就是法律”,司法部门却不可能再简单地执着于“马克就是马克”、“选票就是选票”,它们突然不再可靠和可信了。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土壤中,自萨维尼以来被认为已渐行渐远的自然法,萌发出新的生机。二战后拉德布鲁赫主张“法律的不法和超法律的法”,乃是对战前已经破土而出的新自然法思想的肯认与诠解。纽伦堡审判只是为拉德布鲁赫提供了立论的契机,他关于实在法不可能脱离自然法而独立发展的思考,早在战前就已经开始了。
三、海德堡的精神烙印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拉德布鲁赫,而不是别人,来完成在实在法和自然法之间重建桥梁的学术使命呢?无疑,拉德布鲁赫作为学者政治家、作为魏玛共和国法制重建亲历者的身份,是这种历史选择的关键因素。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担任要职的法学家,并不止拉德布鲁赫一人,最高法院院长西蒙斯、行政法院院长德莱夫斯、国会议员卡尔、许金等,也都是当时法学界的显要人物,为什么不是他们,而是拉德布鲁赫呢?这或许与拉德布鲁赫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背景,特别是海德堡学术圈中受到的多方面思想熏陶有关。
二十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在德国非常流行,几乎每一位有声望的德国思想家,都在某一方面属于新康德派。(24) 1903年12月,拉德布鲁赫受聘于海德堡大学,开始在这所北德名校任教。与拉德布鲁赫一起受聘进入海德堡大学的,还有西南新康德主义的领军人物文德尔班。文德尔班的到来,加上此前已任教海德堡的公法学家耶里内克、社会学家韦伯、神学家特勒尔奇,以及后来的李凯尔特、布洛赫、雅斯贝斯、卢卡奇等,使海德堡大学一下子成了新康德主义的中心。正是在这里,拉德布鲁赫从李斯特那里获得的刑事社会学派思想,获得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出发点。这时,新时代刚刚开始,战争的阴影尚未显现,德国法学界正痴迷于用法学家精湛的手艺,将目光聚焦在1871年《刑法典》的修订工作上,期望制作出一部如同1900年《民法典》那样的完美作品。但是,处于法学思想形成期的拉德布鲁赫,并不满足于成为一名法律教义学家,他深知“立法者的三处修正,可以使一个法学图书馆全部变成废纸”的道理。(25) 他迅速地融入了海德堡学术圈,与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用旺盛的求知欲汲收新的知识,将它们溶化在自己的思想中,为建立一门包含哲学和心理学、历史学和文化理论的法哲学作准备。(26) 在1932年版《法哲学》中,拉德布鲁赫开宗明义地声明,他的法哲学“是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特别是拉斯克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理论为背景的”。(27)
新康德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从机械的唯理论、唯意志论,回到康德的基本问题去:何为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人应当在哪里设定知识的界限?如何在科学与道德的对峙、牛顿力学和卢梭道德哲学的对峙、宇宙决定论和意志自由的对峙中,找到新的基点。(28)正如拉德布鲁赫指出的那样,康德哲学让我们认识到,不可能从“是”中得出“好”、“正确”或“应当”,也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因为它“现在是”、“过去曾是”或“将来会是”,就能说明这种“是”就是“正确”。在康德的视野中,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进化论,就分别是从现有事实、已有事实和将来事实中得出“必然”的结论,都是应当否定的。(29)
新康德主义是在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没头没脑的折衷主义陷入困境之后产生的。在认识论上,它与实证主义同样持乐观态度,认为对于现实,只有科学才能发展可验证的陈述。但是,新康德主义比实证主义更为精巧,不是草率地将事实与价值分割为断裂的两个部分,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然后对其关系进行审慎地考察。正如哲学家夏特莱所言:“说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真实陈述,并不是肯定它将提供全部真理,这就是康德与孔德之间的全部区别。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是孔德的近亲,但康德比孔德精妙得多。”(30)因此,新康德主义不同意实证主义,但也并不全然反对实证主义。在价值论上,新康德主义持相对主义的立场。如同康德,他们既反对怀疑论,相信从数学和物理中可以获得知识,也反对独断论,认为感知只有识别它能够触及的东西,因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31) 拉德布鲁赫从耶里内克和韦伯那里获得了这种对价值的新视角。耶里内克既反对以拉邦德、凯尔森为代表的严格实证主义的国法学,也反对以政治敌友、非常状态和决断理论为核心的右派国家理论,在两方面都与拉德布鲁赫不谋而合。在1878年出版的《法的社会意义》一书中,耶里内克已经将法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法是一种确保社会维续并发展的“最小化的伦理”,而且这种伦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32) 耶里内克的观点显然影响了拉德布鲁赫。然而,拉德布鲁赫发现,价值相对主义反对认识客体对于认识主体的决定作用(客观主义)。也反对认识主体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共识(理性主义),随时有可能陷于无是无非、无对无错的不可知论,这是新康德主义要加以解决的。自康德以来,理性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人皆有理性,皆有通过感知和知性来塑造自己的能力,从而皆有平等地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但是,一旦无限度地夸大这种理性,质疑一切意义上的真理、本质、标准、根据,将主体间性扩大为超越于主体之上的无法克服的东西,就会丧失共识的基地,如康德所言,要么陷于“没有概念的盲目感知”,要么陷于“没有感知的空洞概念”。(33)
拉德布鲁赫是通过拉斯克的思想,来解决价值相对主义的缺陷的。拉斯克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好友,很早就建立了学术联系。“他们一位是新康德主义的终点,另一位是现象学的起点,像两根电极一样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34) 胡塞尔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将“一”仅仅当作“一”,将马仅仅当作马,将鹿仅仅当作鹿,而不管人们用什么语言描述它。拉斯克通过引入这些基本观念和分析工具,剖解柏拉图以来的物质精神二分法,将内容和形式统统作为可经验的现象来处理,从而克服由于精神对于物质的判然两分而导致的不可知论,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足。拉斯克认为,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总是怀带着将“一切”化约为“一”的野心,而相对主义则主张每个人对“一”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一”也会成为“一切”,对于同一事物,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不同看法,任何一种都不具有绝对的地位。拉德布鲁赫接受拉斯克的两条基本思想,一是事实和价值之间具有对立的关系,二是所有价值、效力、感知和意义都是以经验为其立足点的。他将这些思想运用到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划分中去,将自然科学、文化科学和宗教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价值态度,即价值无涉、价值关涉和价值超越,价值哲学的三个分支分别是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他指出:“价值关涉的立场是文化科学方法论的立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涉及价值的事物,法律的概念只有在有意识地去实现法律理念的现实情况下才能够被确定。法律是一种人类作品,并且像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一个无视人类作品价值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对于法律,或者对任何一个个别的法律现象的无视价值的思考也是不能成立的。”(35) 相对主义属于理论理性,而非实践理性。价值相对主义兼具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因素,但却不是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因为它仅仅放弃了证明最终立场的科学根据,但并未放弃其立场本身。不同的思维方式建立在人的差异性基础之上,并且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适的、形成相同的信仰。如果人们清楚自己持有哪种立场,那么他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他们就能够平静地对待自己,也可以平等地对待别人。
正是海德堡学术圈的熏陶,使拉德布鲁赫逐渐将宾丁的实证规范理论与李斯特的法社会学思想熔于一炉。实证的因子,无时不在拉德布鲁赫的血脉里流淌,1933年前的拉德布鲁赫,或者更早追溯到1910年代的拉德布鲁赫,当然都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但他决不是十九世纪思想潮流意义上的陈旧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自然经验主义在人文科学中半吊子的效仿者,而是用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学说解除了怀疑论危险的实证主义,是受歌德思想熏陶的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
四、正义、安定性与合目的性
在法律多元价值的众神之争中,拉德布鲁赫从未完全倒向任何一方。早在大学时代,他不听宾丁劝阻、转到李斯特的课堂听课,从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正是李斯特的教诲,使拉德布鲁赫更深刻地体悟到法的多重性格:它是实证的,必须在使用中才有效,又不是实证的,极端冷漠无情必会扼杀法的生命;它是价值关涉的,只有当以正义为取向时,才具有法的特质,它又是价值无涉的,无论谁,都不能以正义为由,颠覆法的安定性。(36)
1919年,经历了海德堡新康德主义洗礼的拉德布鲁赫已经充分认识到,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证经验主义可以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法则为理所当然,但社会科学领域,却决非放诸四海而皆准。他指出:“法律实证主义,是现实政治时代、霸权国家时代在法律上的部分反映,是对权力的盲目崇拜”。经历卡普政变和拉特瑙遇刺的政治变故后,他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根据内容和形式对实在法进行评断,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起一座思想桥梁,将自然与实证联结起来,对实在法的效力进行“超实证的或自然法的评价”。他提醒法学界,要注意法律实证主义的过度泛滥导致法律与正义的疏离:“过去的实证主义时代只是极端片面地看待法的实在性和安定性,造成的结果是:长期以来,对实在法的合目的性和正义性作有计划的考察陷入了停顿,法哲学和法政策学十几年来也一直保持沉默。”(37)
但是,实证主义是二十世纪前期挥之不去的时代背影,是拉德布鲁赫希望摆脱而不可能彻底摆脱的东西。1939年4月,他女儿事故丧生次月,拉德布鲁赫曾谈到:“我非常吃惊地意识到,我是多么深地植根于实证主义时代,尽管我的自由法倾向却正好想摆脱掉它的束缚。现在我又觉得实证主义甚至又似乎是一种理想,我们还必须得痛苦地接受它。”(38) 他这里所说的“自由法”概念,来自坎特洛维奇。道同则谋,在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经常能够找到坎托洛维奇的影响。作为德国自由法学运动的领军人物,坎特洛维奇是最早反对机械适用法律的法学家之一,他对过于严格地解释法律的做法深恶痛绝,主张扩大法官的裁量权,避免法律总是被作过于狭义的解释而陷于僵死。(39) 即使二战之后,拉德布鲁赫也没有彻底抛弃法律实证主义,仍然认为“任何一种实在法,若不考虑其内容,自身均拥有一种价值:有法总是还好于无法,因为它至少还产生了法的安定性。”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法的安定性应当放在虽非最高、但亦非常重要的位置,法的安定性“在合目的性和正义之间占有颇受注目的居中位置:它一方面是为公共利益所要求的,但另一方面也为正义所要求。或者说,法应是安定的,它不应此时此地这样,彼时彼地又那样被解释和应用,这同时也是一项正义的要求。”(40)
另一方面,拉德布鲁赫从来没有完全同意自然法,也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自然法。他的早期著作《法学导论》,已经显示了对自然法非常成熟的见解。虽然不像斯塔姆勒那样,从人对环境的烦闷抑塞感和逃遁欲,揭示出自然法思想的心理学起源,但他认识到,从方法论起源的角度看,自然法是从自然科学那里获得了启发,发现了法律规则与自然规则一样具有的自在性。(41) 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法学派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法哲学流派”,“结出了自然法的丰硕成果”,“完成了一项世界历史的使命”。(42) 在此后的著作中,拉德布鲁赫也从来不是一味地拒斥自然法,而是寻找自然法理论的漏洞所在,探求在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如何搭建桥梁。在1914年《法律哲学概论》中,他已经初步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发现,古典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场所,皆有同等效力”的自然法,之所以难以令人信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多地强调这种自然法乃是“出自人类普通理性”。而事实上,“时异国殊,而谓国民间之法律现象,必悉为此有同等效力之自然法所支配,准诸纯经验,断难置信。”(43) 他指出,古典自然法的关键缺漏,在于总是希望“把想使之生效的法律冒充为已经生效,而把想使之失效的法律冒充为已经失效”,希望依据一元的价值法则,来判断实在法的有效性,这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计谋”。他反对的并不是古典自然法的理论本身,而是其立论方式和理论依托,反对的是“于种种法律现象之中,惟认一自然法为真理。反乎此者,则命之为讹律。”(44) 这种僵硬的、不容变通的立论方式,在有可能导致背离法的目的性方面,其实是与实证主义没有实质差别的。
在拉德布鲁赫那里,自然法和实在法,“好”与“是”,“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从来没有被放到完全割裂的位置。它们既非盟友、亦非敌手,它们的亲疏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自然法有时用作实在法的深固堡垒,有时又反过来对抗实在法。”即使在二战之后,他也没有完全倒向自然法,仍然认为:“自然法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够得以实现。”已经脱离政界的拉德布鲁赫,已经不需要如同早期那样,注意自己的言论所针对的特定受众,他坦然地接受自然法中的有益部分,同时指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的具体方面还包含着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稳固的实体。”(45) 拉德布鲁赫既“深深地植根于实证主义”,又不是那种“法律就是法律”的褊狭实证主义,只是希望通过法的安定性以实现法的目的。拉德布鲁赫主张“超法律的法”,同时作了“超法律的法不能与以前的自然法等同”的说明。因此,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域中,拉德布鲁赫可能不停地在作必要的“转向”,正如在任何具体语境中,法的安定性、正义性和合目的性之中,总是有一个会处于相对的优位。但是,就其学说的整体路向来说,要证明其前后期思想之间的转向,就如同要在脱离具体语境的情况下区分出法的安定性、正义性和合目的性何者优于何者,可能完全是徒劳的。
五、结语:诗与真
思想的光芒会折射成什么样子,不仅取决于光源的性质,还取决于折射它们的镜子。(46) 没有必要坚持说,从始到终,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这对任何处身动荡岁月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可能都太严苛。所谓“拉德布鲁赫公式”,不是提出了某种自然正义标准超越了实在法的安定要求,而只是为具体语境下衡量这三者的轻重缓急提供了参考。唯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拉德布鲁赫超越前贤的思考路径。
对拉德布鲁赫思想的理解,不仅取决于他的著述,还取决于他的生活、政治活动和所追随的那些伟大心灵。这里必须提到的,还有拉德布鲁赫学术生命中的两位更重要的人物:费尔巴哈和歌德。作为李斯特的导师,费尔巴哈与拉德布鲁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如影随形”。拉德布鲁赫虽然崇敬李斯特,但这种崇敬并不全然出于对李斯特法学思想的认可,还出于对其人格的景仰、心灵启迪和事业引领的感恩。他并不完全同意李斯特,例如,他对李斯特的刑事特殊预防观就持保留意见,同样,也并不完全反对将李斯特作为主要论敌的宾丁。拉德布鲁赫在费尔巴哈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影子:一位充满激情的立法家,一名酷刑反对者和法治理念的斗士,一颗怀带内疚的矛盾的心灵。(47)
歌德则“伴随着拉德布鲁赫的终生”。再也没有谁,比歌德更深地影响了拉德布鲁赫的思想。(48)经历了孤独的精神流放之后,正是在歌德深邃的思想中,拉德布鲁赫觅得了诗意的安居。在自然与实证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诗与真之间,本就不存在隔离的天堑,如歌德所言:“诗与真之间本无二致,现实的精神便是真正的理想”。(49) 人不同于泥石草木之处,在于其命运始终处于游移之中,未来如何,无人可见。每个人都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处的时代,从起点到终点,都不可能摆脱自己作为所处时代人质的命运。为了知晓自己的命途,人总是企图冲决自然法则的网罗,寻访藏于神界的法器。然而,人毕竟是人,不同于神,无以在神界自由穿梭。人用语言命名世界,用言语交流,用文字书写,而语言文字却如泥石草木一般无心无灵,因此,人总是被紧紧捆绑在自己编就的牢笼之中,一切对于此世的理解,对于自身命运的把握,都难以避免地在这牢笼之中展开。牢笼中充满着的矛盾,本就是这世界的脉络与经纬。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倘若世界最终不是矛盾,生活最终不是选择,那么一个人的此在将是多么的多余!”(50) 唯有放弃那种根本性地解决这个世界所有问题的幻想,才可以远离癫狂。寻找问题在什么地方,将其限制在可以被理解的范围之中,才是本真的存在之路。(51)
注释:
① Case of Streletz,Kessler and Krenz v.Germany,Applications nos.34044/96,35532/97 and 44801/98,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Strasbourg,22 March 2001.Also see Case of K.-H.W.v.Germany,Application no.37201/97,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Strasbourg,22 March 2001.
②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和超法律的法》,收录于[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171页。
③ 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④ Stanley L.Paulson,Lon L.Fuller,Gustav Radbruch,and the“positivist”theses,Law and Philosophy,Volume 13,Number 3/August,1994,pp.313—359.Stanley L.Paulson,Radbruch on Unjust Laws:Competing Earlier and Later View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5,No.3(Autumn,1995),pp.489—500.Heathcr Leawoods,Gustav Radbruch:An Extraordinary Legal Philosopher,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2(2000),pp.489—515.
⑤ [德]弗里茨·冯·希佩尔:《作为法哲学思想家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转引自[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大马士革体验”语出《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悔改归主”、“扫罗在大马士革传道”。
⑥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⑦ [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⑧ [日]铃木敬夫:《拉德布鲁赫法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湘潭大学法学院编:《湘江法律评论》(第2卷),湘页译,第242页。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8页。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3页。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陈根发:《论东亚的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第1页。
⑨ 米健:《拉德布鲁赫的生平及其思想历程》,收录于[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第214页。舒国滢:《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述评》,http://www.fatianxia.com/paper_list.asp?id=18981,访问日期:2008年1月8日。
⑩ 林文雄:《法实证主义》,元照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73页。柯耀程:《Radbruch的生平与法学思想》,《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72期,第188页。
(11) 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
(12)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220页。
(13)(15)(36)(38)(47)(48) [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第213、58、63、67、121、124、78、118、136~137、118页。
(14)(16)(17)(20)(23) [瑞士]埃里希·艾克:《魏玛共和国史》,王步涛、钱秀文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卷第133、218、225、220、162~163页、下卷第72页、上卷第291页。
(18) 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es,vol.1,p.150.
(19) [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下册,第375页。
(21)(29)(35)(51)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2~4、13、7页。
(22) 除坎特洛维奇外,拉德布鲁赫的“自由法”的倾向,也可能受到了同时代法国法学家弗朗索瓦·惹尼的影响。参见[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和欧洲法学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24)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37页。
(25) [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和欧洲法学家》,第394~395页。
(26) [法]米歇尔·勒威:“恩斯特·布洛赫访谈”,张双利译,载《复旦哲学评论》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另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传》,第141页。
(27)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注1。另参见[美]庞德:《社会哲学法学派》,邓正来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期,第143页。
(28)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30) [法]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冀可平、钱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35~136页。
(31)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448~449页。
(32) [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和欧洲法学家》第222页,第224~225页。
(33)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433—439页。
(34) Karl Schuhmann and Barry Smith,Two Idealisms:Lask and Husserl,Kant-Studien,Vol.83(1993),p.450,pp.455—465.
(37)(44)(45)(50)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第24、24、25~26、1页。
(39) [德]埃里克·沃尔夫:《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生平和思想》,收录于《法律智慧警句集》,第220页。
(40)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公正和超法律的公正》,收录于《法律智慧警句集》,第170页。
(41) [德]司丹木拉(斯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张季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2)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43) [德]拿特布尔格斯它(拉德布鲁赫):《法律哲学概论》,徐苏中译,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年版,第5页。
(46) [德]卡西尔:《卢梭、康德和歌德》,刘东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9页。
(49) [德]卡西尔:《卢梭、康德和歌德》,第114页。
标签:布鲁赫论文; 法律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相对主义论文; 自然法论文; 法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