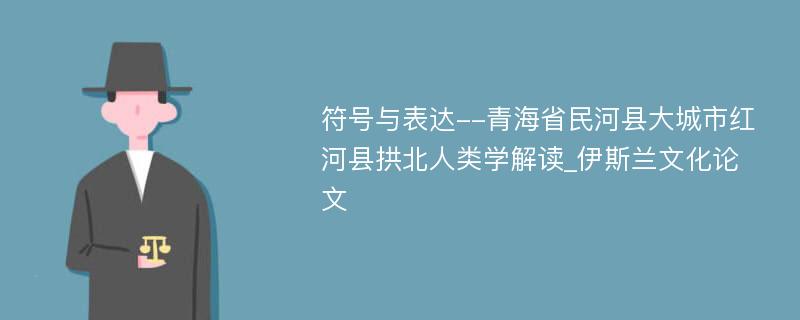
符号与表达——青海省民和县塔城乡红合岘拱北的人类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塔城论文,和县论文,青海省论文,人类学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5)06-0125-06 拱北建筑是西北回族伊斯兰文化最有特点的物化形态或显性形态,是回族宗教认同和精神信仰的重要载体。拱北作为门宦的墓葬建筑,是西北地区特别是甘宁青地区回族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标志,承载着和清真寺不同的功能,也具有和清真寺不同的文化意蕴。青海省民和县塔城乡红合岘拱北就是一个典型个案。2013年2月的一天,笔者陪同家人去红合岘拱北点香,见到了庄严肃穆的红合岘拱北,由于当时不是举行“尔麦里”①仪式的时候,没有记录到尔麦里仪式的过程,但是,拱北建筑中一些特殊的文化符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文试对这些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红合岘拱北的历史变迁 “拱北”一词是阿拉伯文Qubbah的音译,原意为圆顶建筑或拱形墓亭,是中世纪流行于西亚、伊朗、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后专指苏非派穆斯林在圣裔、先贤、长老、导师的陵墓上修建的圆拱形建筑。红合岘拱北在甘宁青地区的苏非派穆斯林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新疆的穆斯林经常到这里点香上坟。这座拱北坐落于青海省民和县塔城乡红合岘村,始建于清宣统年间,属嘎德忍耶门宦。红合岘,本是一个地名,因三条红土山梁汇合于此而得名,但在宗教里给其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认为很早以前在这里有先哲妙体显现火样红的奇迹,因此起名红火岘(“合”与“火”音相同)。据民间口碑相传,其墓主人是穆罕麦德·舍木素地尼。他是巴格达人,被信教群众尊为穆圣后裔,于10世纪中叶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在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传教授道,于1049年3月25日与世长辞,享年84岁,葬于甘肃省永靖县川城乡东端的烟囱山。后由华寺门宦道祖马来迟将其墓搬迁至青海省民和县塔城乡红合岘村,并修建拱北。后来拱北交给了嘎德忍耶门宦管理。在历史的洪流中,拱北几经变迁,1983年于原址重建,方位坐北朝南,呈六楞形,三层,高约23米。一层青砖砌筑,底基周长19.8米,正南为拱门,其余五面为砖制堂子,正北堂子则有大型砖雕龙凤图案,别具一格,题有掌尺师傅姓名及建造年月;二三层为木瓦结构,汉式建筑,雕梁画栋,玻璃装修,六檐翘飞,饰以鹁鸽。顶层攒起,装有宝瓶,显得高耸肃穆。1992年增修东西7米,南北5.5米的大殿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中部三间,呈“凸”字形,与坟园接通,设小门,可瞻仰“古图拜”墓陵。[1]现在,修有与中国传统陵园相似的院门,院门里面的回廊墙壁上画有鹿的形象,院子中央立有石狮子。 二、文化符号的隐喻表达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Cassirer)说过,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他会创造符号。他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2]。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是一种隐喻的表达,是人类情感和意识的形象流露,反映了人类一定的文化、宗教、信仰、习俗。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中,符号的功能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某种文化理念的隐喻表达或传达。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拱北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这一符号除了含有表层或平面的指向(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影响)以外,还通过圆形穹顶、八卦亭、山、鹁鸪、狮子、鹿等次级符号表达着文化涵化、文化交融、文化变迁、文化开放等更深层的意蕴。 1.圆形穹顶 红合岘拱北的墓亭虽然是八卦亭,也就是八角亭,但其穹顶却是典型的圆形建筑。这种建筑是阿拉伯圆形建筑风格与中国古典飞檐斗拱建筑风格的巧妙结合,有其深刻的象征意义。拱北是为纪念苏非教团的先贤、导师、“谢赫”“穆勒师德”而修建的,但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纪念。在苏非信仰中,导师或“道祖”是在“教乘”和“道乘”方面都有很高修养的人,他们的“境界”不同于常人,他们可以和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相通,可以在真主面前为一般的信教者说情,引领人们在后世进入天堂。他们在生前是导师,是引路人,在死后仍然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他们的灵魂永远是和真主相通的。伊斯兰教认为,穆圣是全体穆斯林的导师,也是人类的导师。在他之后,法学家、筛海②都是穆斯林的导师。苏非教众在“导师”“道祖”去世后主动捐钱捐物,在他们的陵墓上修建象征高尚品德和特殊权力的拱北,就是借助这一“媒介”表达自我的需求。将导师的陵墓穹顶修成圆形,意味着他们的精神能通向真主,并与真主的属性相重合,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观念产生了交融。《淮南子》说:“天道以圆,地道以方”。古人在很多建筑中表达了“天圆”这一观念。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上天”和伊斯兰文化所称的“真主”不是一个概念,但在用“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表达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上有其一致性。“象征符号的目的并不在于直接唤起某种行为,而是作用于人的意识,激起理性思考和情感反应。”[3]圆形穹顶这种拱北符号,在作用于认识它的不同对象——信众、参观者、研究者的意识时,会激起不同的情感反应,产生不同的意义,这还与圆形具有的多重象征所指③功能有关。刘鸿模认为,圆形历来被认为是最完美的现象,其简单完整的形式意味着完满、和谐、团圆、幸福,圆形“在圆周上,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它又意味着封闭、首尾一贯。[3]德国汉斯·比德曼著、刘玉红等译的《世界文化象征词典》列举了圆圈、圆形的各种象征意义。如圆圈是最完美的形状,圆圈没有开始,也没有方向,由此,用圆来象征上帝,意为完美和超越人类理解力(无界限、永恒、绝对)。“……在象征学中,圆圈的对立面是正方形,后者与世俗世界和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圆圈代表上帝和天堂,正方形代表人类和大地。”[4]在伊斯兰教中,安拉是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主,他无始无终,无形无色,无方位,无大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圆的内在意义相契合。 圆形符号在藏传佛教中也屡屡出现,如金轮(或法轮)[5]。在印度和远东的视觉艺术里,四星形或者八星形圆是常见的宗教形象的类型,这些圆是用于冥思禅定的工具。[6]可见,圆形符号的象征意义在世界文化中具有普遍性。拱北的圆形穹顶所隐喻的其实就是建造者内心对信仰的理解和期望。它除了象征与真主的沟通外,还象征着墓主人道行的圆满、人生的圆满,象征着今世和后世所构成的信仰的整体,象征着认主独一、“天人合一”这种苏非信士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 山这一符号形象以其高大、雄奇、挺拔、险峻、神秘等特有的性格和气质常常进入文学家、艺术家的视野,被文人墨客、画家、音乐家吟诵、描绘和歌唱,同时,山又以其远离尘世的孤傲、与天相接的庄严、云雾缭绕的虚幻等特征进入宗教修行者的视野,成为很多超凡脱俗的修道者向往和迷恋的佳境。在中国,佛教、道教对山情有独钟,寺庙、道观往往建在深山中,与山相依为命、相辅相成,山因佛、道而声名远播,佛、道凭山而保持其高洁的秉性。一般来说,伊斯兰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主张关注现实、融入现实,所以清真寺建在人群最集中的地方,信教群众围寺而居,形成一种穆斯林特有的社会组织——哲玛尔提。可是,西北地区苏非学派的拱北却往往建在山上,如青海西宁的凤凰山拱北、青海化隆的奄古鹿拱北、宁夏固原的二十里铺拱北。红合岘拱北也是建在民和县塔城乡的一座小山上,拱北的内部资料特别提到,该拱北东屏妥家山、西望凤凰山。山光水色,钟毓灵秀。在这里,“山”与拱北建筑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山这种符号有什么隐喻的意义呢?《符号与象征:图解世界的秘密》一书说:“靠近天堂的山或被人类敬佩,或被人类畏惧。世界各个宗教莫不视山为神圣的代表,山常与天神、灵魂及预言有关。”“山的所在地常不在我们可及之处,遥远、神秘、又富有挑战性,常是宇宙神力生命的化身。”“高海拔的地方总是与神圣的探索联系在一起,是心灵的超越、纯净和永恒的象征。”“攀登圣山的朝圣之旅,代表的是渴望、启蒙和尘世欲望的抛弃;在精神方面,山顶联结了全然自觉的象征意象。”[7]《世界文化象征词典》也谈到:“事实上,山脉已成为接近上帝所在的一种普遍象征。它高高地超越芸芸众生而接近于天国。其顶峰往往云遮雾掩,更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揣测,……圣山或作为神启之地的山峰常常作为神力的象征而在绘画、雕刻、建筑作品中频频出现。”[4]可见,山在宗教的语境中具有一种神圣性。苏非主义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伊斯兰学派,它强调信仰的神圣性,强调通过苦行、通过艰难的修持达到与真主接近的目的。西北地区门宦的先贤或其创始人、历代导师都是通过严格修行达到较高境界的人。为他们建造的拱北选择在山上或有山的地方,这里的山已变成了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符号。它代表了墓主人的崇高、尊贵以及其灵魂的超越与永恒。同时,拜谒拱北的人们要到达拱北,必须要一步步攀登上山,象征苏非修道的艰辛与付出,但只要以无限爱主的精神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地修炼,终会达到最高境界,山同时给了人们一种光明的指示。另外,在中国文化中,“山”与“仙”谐音,“山”与“仙”在语言上构成了一种象征能指与象征所指关系,山象征着葬于此上的墓主人就是世人尊崇的贤哲。“由于汉语具有声调语的属性,汉字‘六书’很早就形成了谐声、假借的原理,所以,中国文化中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大量的基于谐音而生成的象征。通过谐音原理形成象征及隐喻,乃是中国文化创造中的一个重要途径。”[8]“山”与“仙”之间也通过谐音关系发生了意义联系,构成了谐音象征,“山”这一灵秀而庄重的实体成了“仙”的表征。“仙”本是道家文化概念,这里,伊斯兰教与道教共用这一概念,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涵化。中国西北的苏非派将先贤或导师称为“仙”,有拱北碑文为证。宁夏固原二十里铺拱北在乾隆十九年(1754)扩建后曾勒碑记事,名曰《回教先仙碑》。碑文曰:“先仙不传其名,康熙中,乡人每见有在山讽(应为诵——笔者)经者,近而视之杳无踪迹。后有西域老叟至此,曰此山有先仙遗冢,吾教宜礼奉焉。启土视之,得墓志一方,泐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这里不称先贤而称“先仙”,不是笔误,而是有意为之。“仙”的内涵与苏非派追求灵魂升华的信仰是契合的。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殊表达,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里实现了对接。 “在象征意义上,鸟类飞行的本领使它们被认定是天界与尘世之间的信使。飞行意味着从尘世有形的肢体束缚中解脱出来,因此鸟类也象征着灵魂。”[7]在古代埃及的艺术、古希腊的神话中,天神、天使都被塑造成长着翅膀、能飞行的超能形象,这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向往。在鸟类中,鸽子具有的和平与灵魂的象征意义是世界普遍认同的。现在,人们举行像奥运会这样的世界性的大型活动时都有一个放飞和平鸽的仪式,以显示人类追求和平的愿望。鸽子象征和平的符号意指跟《圣经》故事有关。[4]在伊斯兰教中,鸽子更享有崇高的荣誉,穆斯林对它充满了感情。这不仅是因为鸽子将橄榄枝衔回来给了努哈圣人,更是因为它曾经保护了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故事》描绘,穆圣在传教初期,受到古来氏贵族的反对。他们阴谋暗算穆圣,在一个晚上,穆圣与他的好友、坚定支持者、后来的岳父艾布·伯克尔一起逃出麦加城,准备向麦地那迁徙。他们从家里出来后,逃到了麦加附近的牛山,隐藏在那里的山洞中。那些谋害他的人到山洞搜索时,洞口结满了蜘蛛网,鸽子在悠闲地觅食,一片荒凉的景象,好像从来没有人到过这里,于是,他们放弃了谋害穆圣的企图。由于鸽子的出现,穆圣得到了保护,穆斯林们赢得了和平。由此,鸽子被视为真主派来的信使,穆斯林们真心地尊重它,爱护它。西北苏非学派的穆斯林更是对鸽子抱有特殊的感情,它作为一种符号,会出现在穆斯林家庭、清真寺、拱北、道堂的装饰画中。“鹁鸽”是青海民和、甘肃永靖等地区回族方言中对鸽子的称谓。在红合岘拱北的八卦亭建筑上雕有欲飞的鹁鸽形象,这在伊斯兰教与清朝统治者充满矛盾的时代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表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期盼和平,喜爱和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鹁鸽”更是象征着宗教和谐、民族和谐、社会和谐。 在动物界,狮子是王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和狮子接触以后就被它的力量和气质所震撼,产生了想象。狮子成为人类的文化符号后,就具有了特别的象征意义。狮子是古代印度君权和护佑的象征。早期佛教选用狮子作为佛陀释迦牟尼的象征,佛陀也叫释迦僧格,意即释迦狮子,即释迦部落的狮子。雪狮是西藏的动物徽相,装饰在旧政府的官印、硬币、钞票和邮票上。狮子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相结合,逐渐成为吉祥的象征,成为继龙、凤、麒麟之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瑞兽[9]。狮子舞或石狮子中的狮子形象就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民俗的狮子舞或石狮子在佛教文化圈或汉文化圈中有广泛的认同,而在伊斯兰文化圈,其作为偶像崇拜是被排斥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红合岘拱北的院子中矗立着两尊狮子雕像,仔细观察,这种狮子没有圆睁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其他造型与银行门前、桥梁前面等处的狮子形象一样。拱北中这种没有眼睛的石狮子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呢?我们来看看,阿拉伯有没有狮子,阿拉伯的狮子又被人们赋予了什么象征意义?据《旧唐书》记载,唐中宗时,有大石(食)国使请献狮子。可见,唐代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是有狮子的。《明史·西域传·天方》记载,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赉礼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鸵鸡归”。天方,即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可见,明代,阿拉伯国家有狮子是确凿无疑的,只是这里,我们看不出狮子和阿拉伯及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在阿拉伯的民间有很多关于狮子的故事,如《山猫和狮子的故事》《狮子和木匠》《狮子和羊》《狮子和胡狼》《狐狸、豺狼、狮子》,这些故事中,阿拉伯人是将狮子当作百兽之王对待的。阿拉伯的诗歌中也有很多描写狮子凶猛的篇章。由此可知,在他们的文化中是用狮子来比喻国王和英雄的。阿语中,“阿萨德”就是狮子的意思。但是,仔细翻阅《古兰经》,却没有找到关于狮子的记载。可以推断,狮子和伊斯兰的信仰观念没有发生联系,苏非派的信仰中也没有将狮子和导师联系起来。这是伊斯兰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所决定的。那么,怎么解释在西北地区门宦拱北中出现的狮子雕像?它是汉文化或佛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吗?是文化融合的象征吗?周传斌教授认为,从固原二十里铺拱北的历史和建筑看,存在着以回族为载体的伊斯兰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互动关系,拱北坐北朝南的空间布局、八卦亭、太极与龙等文化符号都是两种文化交融共享的象征。[10]杨文炯教授也谈到,清真寺的一些文化符号是国家大传统符号体系在地方性社会中存在的突出表征,也是地方性社会纳入国家体系的一种反映。二龙戏珠、百鸟朝凤、龙凤、麒麟、龟等符号成为清真寺表达自我“正统”性的工具和“语言”,也成为“一个亚群体维护自我生存空间的文化选择。”[11]可见,清真寺的“二龙戏珠”、“百鸟朝凤”、“龙凤”、“麒麟”、“龟”等文化符号是国家权力和国家认同的象征。联系到红合岘拱北院子的狮子雕像,笔者认为,这种符号跟苏非信仰没有关系,也不是回道对话或伊佛对话的表现,它除了表达一种陵墓守护者的意义外,在更深层次上则象征着国家权力和大文化传统的存在,以及在这种权力支配下,回族地方性社会或草根社会求得自我生存空间的内心渴望,即我认同国家的统一和一体,那么国家就要允许我的存在和发展,回族爱国爱教思想的形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狮子”王者的形象代表了最高权力,把它放在院子中央意味着在大传统社会中要遵守以国家为中心的规则。 鹿作为和人类接触密切的富有灵性的动物,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有对它的崇拜。如整个欧亚草原遍布供人膜拜的“鹿石”,西伯利亚和中国境内的阴山、贺兰山、中卫等地,都发现有鹿的岩画。北方萨满教崇拜的神灵中有鹿神。中国古代的东胡族、鲜卑族和女真族均以鹿为图腾。东胡族人常将刻有鹿纹图像的石碑竖立于祖先的墓前,而蒙古族则有圣狼勃儿贴赤娜和美鹿豁埃马兰成婚生下一个叫马塔罕的男孩,此男孩即是成吉思汗祖先的传说。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也有祭祀鹿神的习俗[12]。中国古代,鹿虽然单独没有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但是它作为龙和麒麟的融合元素,构成了龙和麒麟这两种祥瑞的神性特征。鹿角因为强壮有力,坚韧美观,而且富有生命力,被人们赋予示强、通天、喻权等神性,而融合进了龙的形象。在麒麟的形象创造中,鹿(雄鹿)是最重要的融合对象。鹿的角每年脱换一次,鹿的生态可塑性强,森林、草原、高山、平原,热带、寒带,它都能够生存。这是生命力的象征。因此,在鹿的人文化过程中被赋予了象征长寿、成仙、谐禄(福寿)等品性。尤其是鹿成仙的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庞进著的《中国祥瑞——麒麟》一书讲述了几个鹿成仙的故事。[13] 鹿不但自己能成仙,还可以助人成仙。比如,汉代纬书《春秋命历序》载:“皇神驾六飞鹿,化三百岁。”东晋葛洪《抱朴子·杂应》言:“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者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蹻。”所谓“龙蹻”、“虎蹻”、“鹿蹻”,指的是道家修行到一定程度,可以凭借的三种脚力、三匹坐骑,有了这三蹻的帮助,就可以上天入地,与神往来[13]。由此可见,“仙化了的鹿”跟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是道教里的神物之一。人们骑上它,沾上它的仙气,就可以化仙,成仙升天,这是道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最高理想,同时也表达了人们遨游太空、探索宇宙的某种愿望。这跟嫦娥奔月、玉兔升天的神话故事所蕴含的意义相契合。伊斯兰教虽然反对崇拜偶像,但在其向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接触,在不违反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保留某些地方文化的因素是常有的事,而且,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宗教,在世界各地,伊斯兰教原则一致,而伊斯兰文化则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以致我们现在在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很难分清楚哪些是原汁原味的伊斯兰,哪些是“地方性知识”,哪些是民族习俗和传统。前面谈到,古代的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鹿崇拜,这些地区的一些民族在接受伊斯兰后,在其文化中保留某些鹿崇拜的痕迹是不难理解的。特别是鹿助人仙化的传说与苏非主义脱离尘世,与真主合一的精神追求能够产生共鸣,以致在苏非的物化的语言中借用“鹿”的形象来隐喻修行目标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或者以“仙化的鹿”象征已经得道的苏非大师、苏非导师也是可能的。15世纪初,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东来撒马尔罕,觐见帖木儿汗,其所著的《克拉维约东使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星期日,再登程前进,抵一处名狂人村(Deli Koy),此名称之得来,由于全村居民,皆系抛弃尘世,静坐修炼,成为回教中修士,所谓“迭里迷失(Dervish)者。邻近各村镇皆不时来朝拜这座村中的修道士。病人也到这里来求医,居民称这些修道士为长老,其中有一位年高道深者为道长,极为一般修道士所敬重,奉之若长辈。帖木儿经过此村之际,曾赴修道士静房访问,并在道长所居之处休息若干时,附近各方拜谒修道者,多送来礼物,哈达(Adak)等。村中即以道长之地位为最高,居民皆尊修道士为长辈;修道士既不留须,又不留发,无分冬夏,身披旧毡衣,往来过市。手弹铜弦,口念诵词。现在他们的道院的大门上绘有圆月形徽饰,于其上悬有鹿角或羊角一只。每位修道士之门前,必悬有兽角一具。”[14] “迭里迷失”或“迭里威失”是中国史籍中对伊斯兰苏非修道者的称谓。克拉维约的这部游记详细记载了中世纪中亚地区苏非修道盛行的状况,他所说的“道院”的大门上“悬有鹿角”值得研究中亚苏非主义的人们重视。作者虽然没有揭示挂鹿角的用意,但我认为这是苏非修道的一种标志,表示他们不屑尘世、不屑富贵繁华,只追求心灵的圣洁、精神的升华。鹿是中亚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古代中亚人在他们的历史遗迹中留下了许多“鹿石”雕刻。“鹿石”是指在一些四面体或圆形的石柱或石板上面,凿刻有各种动物、古代武器及其他动物的图形,而其中以鹿形为主,因此将此类文化遗存通称为“鹿石”。鹿石有很多形态。在有的鹿石刻画中,鹿角刻得长而美,增添了鹿的威武的气概。整体鹿群均向着太阳呈奔驰状。有学者认为,鹿石表现了古代中亚地区的民族对太阳的崇拜,是图腾文化的遗存。鹿石是萨满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教祭天、祭祖、崇拜各类神灵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祭祀巫术祈求于苍天、先祖、神灵,以赐福于祭祀者,立碑和鹿石,并刻有太阳、石堆、鹿形等图形,立于生态繁茂的山区或部落首领、勇士墓地附近,其目的是为了产生同岩画一样的巫术作用,使部落牧获丰盛,力量强大[15]。中亚突厥人伊斯兰化以后,萨满教的某些影响仍然存在,或以一种新的方式和含义渗透进了伊斯兰信仰体系中。“鹿角”可能就是经过取舍以后保留下来的,它以坚韧的力量指向苍天,指向宇宙,喻示着苏非修士们内心的渴望。苏非信仰传入中国西北地区以后,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对鹿的一些特性的崇敬,“鹿”的形象很容易被回族民间接受。在红合岘拱北大门入口处墙上的绘画中就有体态轻盈的鹿的形象。这一文化符号就是一种隐喻,它是苏非主义所认同的“鹿”的形象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仙鹿”形象的结合,用来表示苏非导师的品级。 拱北信仰是伊斯兰苏非信仰的一种符号化的模式,在拱北中存在的各种文化符号,也存在于佛教、道教、古代萨满教以及民间信仰的文化的物质化的语言表达中,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这些文化相互影响的反映,也不是伊斯兰文化与这些文化融合的表征,它们只是人类在精神层面共有的表达方式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代的契合、相遇,是文化涵化的典型。 ①“尔麦里”是阿拉伯语“amal”的音译,意为善行、善举或善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回族穆斯林在文化适应中赋予了“尔麦里”新的文化内涵和存在表现形式,使得“尔麦里”原有的善行含义又增加了将宗教节日、传教先贤、苏非门宦创始人及其后各辈亡故的教主忌日所进行的诵经、赞圣、宴请宾客和普通回族家庭进行的搭救(纪念)亡人活动等,都称为“尔麦里。” ②筛海(Shaykh),又译为“舍赫”、“谢赫”,意为长者、长老、导师,宗教上有很高声望的长者。 ③刘鸿模在《象征符号论——论象征之三》一文中,将象征分解成象征形象和象征意蕴两种要素。作为与符号诸概念的一种对应,他将象征形象称为象征能指,将象征意蕴称为象征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