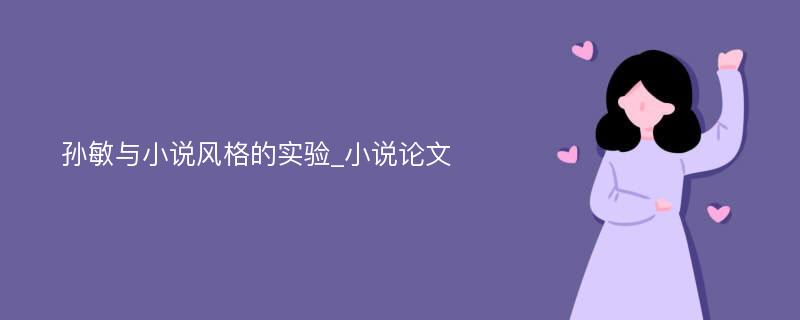
孙甘露与小说文体实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露论文,文体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先锋小说家中,孙甘露独特的反叛性与创造性无疑引人注目。在小说形式实验的探索路上,他比任何志同道合的同伴都走得更远,因而也更为孤独。在文学专业圈外,他几乎寻找不到读者;即便在圈内,能理解并赏识他的作品的评论家又有多少?他的创作真正是“曲怪和寡”,读完它需要反常规的阅读经验和一定的智力及勇气。孙甘露也不象其他先锋小说家如马原、余华、苏童等拥有不少创作上的追随者与仿效者,他的难以重复与不可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人缺乏他那种形式主义追求的极端勇气。然而也正因为此,孙甘露一旦受到赞扬,这赞扬的声音必定分外高亮,不吝形容词的最高级用法。事实上,孙甘露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标帜。尽管许多人觉得他的小说不忍卒读与难以索解,但提起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时还是会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他。同时,孙甘露的作品得以发表,也是文学观念开放性与宽容度的一次亮相。多样化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并固执为信条,其必然的逻辑结论便是:怎么都行!
1986,《上海文学》刊登了孙甘露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访问梦境》。小说列在“作协上海分会青创会首届学员小说专辑”的名下,似乎有习作的意味,但其意义却是属于文学史与小说理论的。这是一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一篇反体裁、反小说的小说,一篇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和倾向的小说。它对小说艺术惯例的冲击是颠覆性与挑战性的,它制造着小说的新法则或无法则、小说的新疆域或无疆域为自己确立合法性。小说中出现的“反陈述节”事实上可以看作为有关小说自反的一个隐喻,本文由此透露出其反叙述的叙述特征与众声喧哗的节日狂欢色彩。
从文体说上,《访问梦境》是一篇“杂语体”小说,它是小说、诗歌、散文、神话、寓言、哲学论文、谜语、寓言、语言游戏等诸种元素奇妙的混和,体现了无中心无规范的后现代特征。当然它是叙述的,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正是这一点它能勉强进入小说,然而这种叙述又是反叙述的。所谓“反叙述”,就是说徒有叙述的形式与书面进程的过程,却无叙述的实质,即叙述无所谓开头与结尾,叙述所负载的情节也没有起源,更没有发展。小说分割成几十个段落,读者完全可以从中间任何一个段落开始阅读,周而复始地循环;或者象玩扑克牌那样将几十个段落的秩序打乱,按新的组合重新阅读;这都不会改变你的阅读感受和接受效果。因为小说叙述的内容是零散化的和精神分裂式的,是梦意识的片断呈示与叙述语言的自律之流,读者可以感受到叙述正在进行,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叙述的时空运行法则与叙述内容的关联性。人物、情节、环境,一切都处于不确定之中。人物缺乏可以辨认的面目、身份与性格,情节丧失了时间、地点、现实、历史以至神话的提示与参照,环境则逃离现实的记忆而躲藏在梦境的深处。小说真正地成为意识的“迷宫”,它不再提供“内在统一性”的抓手以资读者进入阐释与索取意义之门。从某种程度上说,孙甘露的小说是供阅读的,而不是供解释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正因为它不为解释而写作,是为写作而写作,相反倒为任何一种自由解释提供了可能性与合法性。美国学者弗·杰姆逊曾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同:“你读乔依斯也许会就某一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思考,竭力想找出其存在的理由,而读品钦的时候,如果他的作品真正使你感兴趣,你只会想多读一些,因为这是一种陶醉而不需要任何解释。”他接着指出:“后结构主义理论正是对解释的一种抨击。……所有当代的理论都抨击解释的思想模式,认为解释就是不相信表面的现实和现象,企图走进一个内在的意义里去。所有以这种解释性方法思维的思想模式都被后结构主义理论抛弃了。”(注: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83页,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 )需要补充的是,反解释与任意解释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反解释是反对“深度模式”的解释,张扬“平面化”;同样,任意解释也是对深度模式“中心”的颠覆,以处于“边缘”的多样化消解“中心”的确定性意义。不管怎样,对于孙甘露的小说而言,小说的刺激性、神秘性、不可索解性和新鲜的阅读经验就是他写作的目的。如果要追寻精神分裂性叙述内容背后隐藏的意义,那么首要的意义即是对小说内在统一性及读者逻辑阅读欲望的消解,是倡导反小说的叙述与反小说的阅读。
《访问梦境》从题名上看就有一种将“梦境”实体化与异己化的倾向。叙述者访问的是自己的梦境,而这个梦境却可以与自己脱节而成为审视的对象。这尽管有悖常理或仅仅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却可以用梦的自相缠绕或梦中之梦来解释。总之,“梦境”所圈定的叙事空间已预设了叙述话语任意行动的自由和自我证明的合法性;同时,“梦境”的对象化也使其上升到与“存在界”同样具有实体意义的层面,它的非真实化足以与存在的真实性抗衡。这篇小说之所以难以索解,除了上述的零散化与精神分裂性内容外,还有二个重要原因。一是梦境即想象界由于自足自律而向存在界关上大门,成为深度梦境与潜意识的想象,它与存在界的沟通只是大门上的偶然并随意凿开的几许小孔,其中包涵的现实与历史的信息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模糊变形的。尽管从理论上说任何梦幻与想象都根源于存在,但在想象界与存在界之间有意沟通和故意隔绝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二是小说中想象界与符号界的某种背离。不仅想象背离存在,符号也背离想象,叙述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叙述内容,成为自律自为的语言之流,成为为语言而语言的语言游戏活动。正如小说中所陈述的一个观点:“这是一个词藻的世界,而词藻不是用来描写想象的。想象有它自身的语言,我们只能暗示它和它周围事物的关系,我们甚至无法逼近它,想象中的事物抵御我们的词藻。”既然语言不能描写想象与梦境,当然更不能呈示存在,语言只能返回到自身的语法与修辞之中,任何探究语言所负载的意义的行为将是徒劳无益的。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者语言,都堆砌着大量互不相干与难以索解的意象,如丰收神、闪闪人、迷宫、剪纸院落、《审慎入门》、反陈述节、幻术大师、失散者协会、睡意广场、《流浪的舞蹈者》、橙子林、白色的梯子等等。它们是半透明的语言之流,是伪装成确定性象征的语言表象,都有着感性的诗化的语言外壳,似乎依循艺术惯例指向着抽象的哲理内涵或观念形态,然而当你认真地用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法”去索解其隐喻义时,你已经落入了预设的语言“陷井”,因为它们根本上就是随意性的语言建构,是幻觉自律或语言自律的产物,是无内涵或无穷内涵的语言的文学游戏。
从《访问梦境》始,孙甘露执着地实验一种反小说的小说边缘文体。这种文体最大的两个特征是“仿寓言体”与“语言游戏”。从小说的外观与阅读整体感觉上看,它最象寓言,但已无寓言文体含义的确切指向性与内在统一性,有论者称之为“现代寓言”,事实上更确当的说法是“后现代寓言文体”,戏拟寓言行为的本身即是对寓言寓义确定性的一种反讽,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寓言或反寓言的传统阅读模式倒是它的隐蔽目的。1987年孙甘露发表了《我是少年酒坛子》,这是一篇三、四千字的短篇,是《访问梦境》与稍后发表的《信使之函》两座浪峰之间的一个过渡。从反小说的角度说,它比《访问梦境》表露了更鲜明的主体自觉意识。作品仍可归入“后现代寓言”。它分引言、场景、人物、故事、尾声五个标题,将小说原本彼此融合一体的元素拆解开来,以此反小说的传统结构与传统阅读;同时,五个标题下的内容又分别是对标题即小说元素的颠覆,比如“场景”是无场景,“故事”自我解说为“一只空洞的容器”,“引言”、“尾声”只一、二句话,不仅与故事无关,而且恰恰是反故事的起源与发展的。从语言游戏方面说,“场景”一节共四个自然段,每段列出一个中心意象,即“一九五九年的山谷”、“一九五九年的秘密”、“一九五九年之前的一个片断”、“一九五九年的信心”。这一语言游戏方法在《信使之函》中便发展为几十个“信是……”的句式。在这里需要顺便提示的是,“一九五九年”、“信”这两个意象之所以反复出现、把玩不休,完全是因为它们与孙甘露本人的经历、意识与潜意识有一种神秘性的“缘份”,由此成为叙述的出发点与梦境的动源。孙甘露生于1959年,曾在邮局任送信的工作。略去这两个背景,我们会感到无法参透的迷茫;但把握此背景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因为我们仅仅知道孙甘露选择游戏道具的根由,却无法改变游戏本身的性质。
《信使之函》最具表征性与奇特性的是“信是……”的句式。在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里,竟然运用了五十多个“信是……”的统一句式。如果不是穿插在散文体的语言排列中,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它与博喻性的诗歌相类比。从文体上说,这是诗歌因素对小说的强行嵌入。然而作者却让这一句式承当多种多样的叙述功能:它是上行叙述的概括或下行叙述的提示;它是叙述的断裂、衔接、过渡、跳跃与转折;它使叙事空缺有了以假充真的填补物或使叙事重复有了外观分离的标帜;它使片断、分裂、模糊的叙述内容至少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直观的内在统一性。“信是……”句式由此替代人物、环境、情节成为小说的主干,它似乎君临一切地支配着小说的其它元素,又似乎是引导读者穿越小说迷宫通往意义内核的路标,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信是……”句式在小说中是自成体系的,是自律自为和自我繁衍的,它与人物、情节貌合神离,它与意义的关系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说,它是以反小说形式与后现代特征推出的一次文体实验与一场语言游戏。
“信是……”句式是一种判断,也是一种定义。“是”的两端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然而,当同一个能指符号能同时下五十多种定义的时候,下定义的方式本身就是颠覆“定义”的,并且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再是符号与现实的关系,而是叙述主体幻想中的能指符号不断变化与流动的意义指涉过程。事实上,五十多个“信是……”句式并非意味着所指意义的终结,也就是说,“信是……”句式完全可以无穷尽地“玩”下去。第一个“信是……”是对符号所指的承诺,第二个“信是……”是对上述承诺的颠覆,从而建立新的承诺。于是承诺与颠覆周而复始地循环,能指的确定成了看不见尽头的延搁过程,所指的意义零乱分散地向四面八方播撒,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意义的过剩、模糊与不确定。多定义即无定义,每个定义都体现了不完整性,众多零散化的定义则意味着无中心无本源,它们以符号游戏的方式颠覆了现实及其意义的完整性与确定性。小说通过五十多个“信是……”句式所表达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联系。德里达为了瓦解意义的确定性,就曾反对“定义”的单一固定含义,认为语言不过是分延的永无止境的游戏。
当“信是……”句式被无数次地重复,而其确定意义却在零乱中迷失时,小说的叙事语言也就彻底地能指化了。也就是说,能指不再代表所指,符号不再指代现实,小说不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的意义之解。小说中的上帝、老处女、耳语城、信使、僧侣、六指人、致意者、诗人、锯木作坊等意象构成的能指系列,与所指的关系是似有若无的,就象“信”这一能指一样,可以被置入意义集合群中,任意地滑向一个不断被颠覆与重建的意义指涉过程。如果谁还遵循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传统契约去苦苦索解文本的确定隐喻义或主题,那就是落入了小说的迷宫与语言的陷井,或者说你背离了文本规定的游戏场景与游戏规则。你必须以游戏之心待游戏,而不要抱着寻求答案尤其是唯一答案、确切含义、作者本意之类的功利之心。如果你能在小说的能指系统中翻出五、六十种(就象“信是……”句式那样)甚至更多的解释(不当回事地随意说说就行),那你就是这场阅读游戏的胜者,并显示你在智力与创造力上超越了作者。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信起源于一次意外的书写”。这句话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不仅是它处于醒目的末尾,也不仅是叙述者“我”有意“挑选”的一句话,还不仅是“我”将它看作“一个企图逃避结局的开端”,即既是结局又是开端,在周而复始中占据着双重身份与特殊性功能位置,更为凸现的还是它的句式,它同样是下定义,却一反“信是……”的老例,以示区别与独具匠心。这句话其实是小说之“眼”,是无数次地颠覆中心后推出的中心,点出了这篇以“信”为题、以“信使”为叙述者的小说创作的一个大秘密,即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与偶然随意的语言操作是其本质。书写成了书写的目的,语言的意义在于自身。王岳川说:“德里达为自己的反逻各斯中心理论确定了这样一个命题:‘本文之外,别无它物’。文字与文字构成一个流动的意义指涉过程,文字不需要指涉形而上学的真实。文字必须只看成文字,词语必须看成词语,而不是当作真实、实在、权威或存在(在场)的显现。究极而言,文字就足以使本身永远不朽。”(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意外的书写”与语言的游戏。
1988年发表的《请女人猜谜》是孙甘露小说实验的又一个台阶。这篇小说可归入元小说一类,也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关于虚构的虚构”。当小说全力关注于自身形式时,当小说实验几乎要究尽想得到的各种技巧时,元小说也许是一种合符逻辑的必然抉择。加拿大学者高辛勇指出:“后现代文学作品的普遍特征之一是它的‘自我反观性’,或‘自反性’(self-reflexivity)。所谓‘自反’的意思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叙说中涉及文学本身,或是以文学为主题,或是以作家、艺术家为小说主角。更有一种自反现象则把叙事的形式当为题材,在叙事时有意识地反顾或暴露叙说的俗例、常规(conventions), 把俗例常规当为一种内容来处理,故意让人意识到小说的‘小说性’或是叙事的虚构性,这种在叙说中有意识地如此反躬自顾,暴露叙说俗例的小说可称为‘名他小说’(metafiction)(或译‘元小说’、 ‘后设小说’)。”(注: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第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请女人猜谜》就是这样一篇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自反小说。小说从叙述者谈论《猜谜》的写作开始,不久又申称:“在写作《请女人猜谜》的同时,我在写另一部小说:《眺望时间消逝》。”接下去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眺望》的虚构内容以及关于这一虚构的虚构过程。于是,《猜谜》的写作变成了《眺望》的叙述,《眺望》实际上就成了《猜谜》的本文。这究竟是一篇小说还是两篇不同的小说?作者故意混淆这一点。《猜谜》的题名提供了叙述动机,但叙述者背叛了他的承诺,其叙述结果便是《眺望》,而《眺望》还是置于《猜谜》的名下。这是有意的偷换还是无意的颠覆?是故事中套故事的神秘“中国盒子”还是自咬尾巴的情节灵蛇?这就是读者要费思量的智力游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篇自我指涉的小说:虚构的小说指涉小说的虚构,《猜谜》的写作意在暴露《眺望》写作的虚构性与想象性。其意义是关于小说本体论的。孙甘露不仅强调了小说想象性与虚构性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表明小说与现实“镜象关系”之外的各种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想象与真实界限模糊、二元背反的可能性,或者说,小说建构为“迷宫”的可能性。
《猜谜》与《眺望》犹如两面镜子相对照,互映出虚虚实实、无穷无尽的自我影像。这是一种二元对衬的叙述方式,利用人物、事件、场景、细节的重复与对称、交替与错迭,造成相似相补而相对相悖的故事关系,给人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不确定之感。《猜谜》声言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小说所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还活着”,“小说中使用了她们的真实姓名”;但《眺望》恰恰抖漏故事的虚构与荒诞,“士”与“后”作为主人公不过是性别符号。这双重文本不仅构成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觉、承诺与背叛的对立,而且也神秘互渗地具有互文性。《猜谜》中的护士成了《眺望》里的后,《眺望》中的士又成了《猜谜》中的“我”。这种人物穿越文本的随意置换,说穿了无非证明小说本质上是想象的产物,小说家在创作中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了解了作者的这一小说观,我们就不会惊讶作为虚构人物的“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地成了我的妻子”。因为,“如今,我已确信,我是有预言能力的,只要我说出一切并且指明时间与地点,预兆就会应验”。叙述者在这里几乎运用着上帝的口吻:“上帝说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但须指出的是,叙述者“我”在小说里也是被虚构的一个角色,一个自我想象所及的一个人物。小说不仅制造了双重文本,而且还意在呈示多重文本的互文性。罗布—格里耶的《嫉妒》、弗朗索瓦·萨冈与亨利·詹姆斯未指明的小说,甚至《博物》杂志上的文章、照片,都与《猜谜》、《眺望》互相渗透互为解释。于是,“本文的意义产生于与其它本文构成的横向语境与纵向补替中。本文依赖其他本文,又区别于其他本文,它的意义网络中期待补充和替换。本文是一个永远超出自身的意义索取过程,是一系统运动‘踪迹’。 ”(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事实上,《眺望》中的“士”就是本文间互文性创造的产物,他永远处于不确定的动态过程之中,他是惊天动地的人物、一个瞎子、见习解剖师、巫师、守床者、球僮、老人、店员、诗人、与魔鬼签约的小说家、忠诚的爱人、偷情者、媒婆、喻世者、凡夫俗子、谋士、臆想者等等。这么多摇摆不定的角色,其实来源于各种小说中男性形象,由叙述者的幻觉将他们合而为一。当“士”作为能指关闭了通往现实的所指领域时,当“士”只能存活在幻想中时,“士”也就成了无所不包而又空洞无物的“能指”了。“空洞的能指”是制造小说迷宫的秘诀,这就是孙甘露小说实验的意义所在。
反体裁、元小说、语言的自律之流是孙甘露实验小说的三个重要内容。他确实提供了具有陌生化与新奇感的小说,给读者上了“小说能写成怎样”的一课。他的形式主义追求与后现代主义倾向无疑有激发思考的价值。但他将符号界、想象界与存在界隔离,表露了回避现实与冷漠生活的姿态,同时也意味着对大众读者的拒绝。这样的小说实验最后难以为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