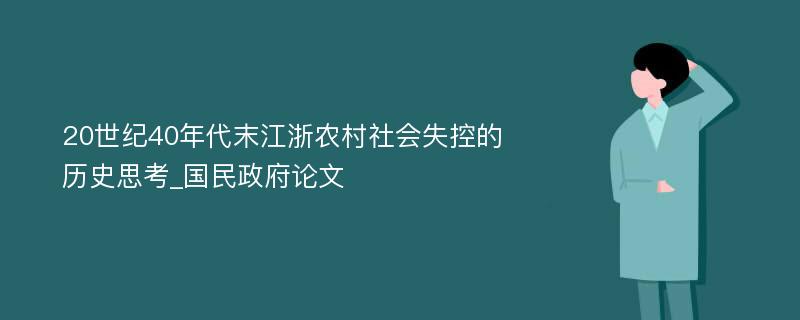
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失控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浙论文,后期论文,年代论文,农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4)02-0085-06
19世纪中叶以后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又一个秩序动荡的时代。迄止1940年代后期,社会动荡有增无减。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国民政府采取各种举措以图稳定社会秩序,但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急剧激化并导致社会失控。本文拟从19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结构入手,分析乡村社会失序的因素,进而思考国民政府社会控制失败的深层历史根源。
一
20世纪初,由西方传来的地方自治思想广为传播,清政府承认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本,并在乡镇实行地方自治,国民党也强调建立地方自治、树立民权是实行训政的重要举措。作为群众自治团体的保甲组织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稳定地方秩序和发展社会经济中,一度起到了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战后经济重建,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对沦陷地区的社会控制,以重建政府的权威。江苏和浙江是为国民政府提供政治、经济资源的核心地区,因而也必然成为战后国家重建政府权威的重点省份。为了便于实施社会控制,国民政府重建保甲制度,着手减少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层次,在江浙部分地区实行撤区并乡,强化对保甲组织的支配力度。[1]由于这种措施局限于纯粹机构性的改革,不能使基层政权符合国家在乡村实施强势社会整合的目标。国家政权转而扩大党团网络,在各县党部以下增设国民党区分部,增建三青分团,后来还将党团合并,增加党员人数,以扩张其社会政治基础。另外还通过增加地方军事机构,扩建中统、军统组织,在县一级建立保安团,在各乡镇成立自卫队,[2]企图借助暴力威胁或暴力实施强迫人民就范。所有这些依赖强制手段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举措,随着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的解构而归于失败。这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是,仅就国民政府重建保甲组织、强化农村社会控制而言,与战前保甲组织的作用相比,战后保甲制度在社会整合中已经难以恢复作用。
其一,与抗日战争以前相比,战后保甲人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按照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政令,保甲人员需符合一定标准,例如规定保长需为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曾任公务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者;曾经训练及格者;曾办地方公益事业者等。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其时遴选保甲人员尚有一定标准。尽管在实际执行中,不一定能严格按照规定任命合适的人选,但在江浙乡村,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近代教育起步较早,保甲人员的学历、职业、身份因此而有一个基本的限制,其中不乏热心乡里事业的精英分子。战后与战前相比,由于保甲职事繁重,征收捐税和征派壮丁尤其得罪乡邻,乡村中有地位、有知识的人,往往寻找借口逃避任职,而乡村无赖为了从中谋取私利,则觊觎保甲职位,保甲人员的身份结构随之发生转变。保甲人员的学历结构也与战前的规定相距甚远,如浙江省新昌县中北乡第十二保共有10位甲长,仅有4人为高小毕业,其他几位为初小毕业或肄业,甚至还有身为保长而目不识丁者,(注:《新昌县中北乡第十二保甲长履历表》(1946年7月),新昌县档案馆:M4-13-190。)保甲人员的整体素质随之下降。
其二,保甲组织的职能难以恢复至战前状态。按照制度的设计,保甲组织的理想职能包括:“政教合一,警卫联系;劳动服务,交通水利;复查户口,从事登记;编练壮丁,明耻教训;建仓积谷,为民防饥;禁绝烟毒,破除迷信;普及教育,保学推行;礼义廉耻,生活求新;管教养卫,工作途径。”(注:《浙江省绍兴区保长训练班证书》(1936年),新昌县档案馆:M8-5-27。)这是战前国民政府对保长们的行为要求,但保甲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保甲长所起的作用却与理想的设计相去甚远。江浙地区一些保甲人员因为忙于田间劳作,将保务置于一旁,不管不问;一些保甲人员则忙于经商,常常外出不归,使乡公所无可奈何;还有一些保甲人员纵容保民,对抗乡公所派出的公务员,致使乡公所在乡村推行其意图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国家政权的控制力量往往至乡镇一级而止,难以深入农村基层社区,国家在农村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目标尚难以实现,强势社会整合的企图自然落空。
其三,保甲组织的工作人员极不稳定。从笔者所接触到的县级民国档案看,抗日战争以前,江浙保甲人员的任期大都时间较长,保甲提出辞职较为少见。40年代后期,保甲人员的任职时间普遍缩短,而且离任的原因大部分是保甲人员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如1946年,塘栖镇新履任的7位保长中,有4位任职不足一年就提出辞呈。1949年,新昌县一位保长任职不足半年也要求准予辞职。从辞呈中列举的辞职理由来看,尽管保甲人员请求辞去职务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最为普遍的借口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忙于生计,疏于保务。(注:参见塘栖镇镇长吴少士给杭县县长的呈文,余杭区档案馆:91-3-63。)这些都是诉诸于文字的辞职理由,当然,也不能排除文字表述之外的原因。如笔者在江苏省盱眙县采访的一位保长,担任保长职务仅3个月,就因为派捐任务繁重,征收困难,而自己又不愿得罪邻里而辞职。保甲人员难以稳定,保甲组织的重建自然缺乏成效。
其四,与抗战结束以前相比,保甲组织官治化倾向趋于弱化。按照30年代保甲组织初建时的设想,保甲是一个乡民自治的组织,但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1939年推行新县制后,保甲组织官治化的倾向越来越强。但在江浙农村,经过抗日战争后,官治化的趋势反而转向弱化。一方面,有能力的人们倾向于逃避担任保甲,可以随意辞去职务,保长还可以召开保民大会或甲长会议,选任新的保长或免去旧的保甲人员;另一方面,进入保甲组织的土豪劣绅往往只顾一己私利,乡镇公所对他们的约束力较之对战前保甲人员的支配能力,大为下降。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保长都难于符合乡长所代表的国家基层政权对保长的角色期待。在国家与农村趋于恶化的关系中,保长的角色表现既难以符合保民对他的角色期待,也难以符合乡长对他的角色期待,有时在国家与农村的利益矛盾中,保长所扮演的“国家代理人”与“乡村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对他提出的要求也会彼此冲突。一些保长在角色冲突中选择了逃避基层政权对他的期待,致使保甲组织无所作为。如果仔细思量保甲组织逃避乡镇公所控制的原因,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保甲制度设计中的固有缺陷。作为自治机构的保甲,其权威是源于保民自下而上的选举,这就要求保甲代表乡民的利益,而作为基层政权机构的乡镇公所,其权威却来自于县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在20-30年代国家政权处于强势地位而国家与农村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时,保甲呈现出官治化的趋势。到40年代后期,由于国家政权转向弱化而国家与乡村的冲突又转趋激烈,保甲不愿卷入政权与乡村的对立关系中,官治化程度自然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保甲会倾向于代表乡民利益。前述之保甲人员对乡镇公所消极怠惰,逃避公职,其根源也在于此。可以说,保甲组织重建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就在于国家未能解决政权机构与自治组织二元分立的政治难题。
二
明清时期,国家在人力与组织方面所受到的制约,阻止了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社会,国家建立地方社会秩序只能通过委托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承担责任。就一般情形来说,官吏与士绅是行动一致的,并保持相对和谐的关系。在江浙两省,因为科举鼎盛,有一个较他省更为庞大的士绅阶层。直至20世纪初叶,士绅作为地方政治精英,一直承担着农村基层社会整合职能。尽管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及数年后的帝国统治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体系,但直到二三十年代,士绅在社会整合中仍有着积极作用。抗日战争中,土豪劣绅乘势崛起,小规模地方武装割据势力也趁机壮大。由于劣绅对政权权威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而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则直接挑战地方政权的权威,与国家争夺对乡村资源的控制权。在新的精英阶层难以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在农村重建权威的努力,迫切需要传统精英阶层在社会整合中恢复积极作用,但此时江浙农村的现实却是传统精英缺位。精英阶层在乡村社会控制领域中缺失缘于士绅阶层内部及其外部的多重因素。
首先,士绅阶层分化造成的力量衰落,导致江浙乡村中的精英阶层缺位。一方面,江浙士绅阶层发生了职业取向的分化。力农——经商——科举——入仕是传统士绅家庭跻身精英阶层的基本路径。科举制度废除遽然中断了士子向上攀登进入官僚阶层的道路,但在江浙两省,由于乡村工商业经济素来发达,又地处近代西方价值观念影响较深的东南沿海,士绅中不乏思想开明者,他们受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召唤,纷纷转向经营实业,身份一变而为商绅,从传统精英阶层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江浙士绅发生了居住地域变化。他们受到近代崛起的上海等城市生活的吸引而纷纷离开乡村,同时也由于士绅文化水平较高,多数家庭饶有财富,容易转向城市谋取新的职位。此外,由于江浙两省进入仕途的士绅数量众多,乡村士绅与政权结合紧密,一旦遇到变局,在乡村以外的出路较广,甚至谋求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乡村权威领域。士绅阶层的职业分化、城乡分化,造成江浙农村整个精英阶层的衰落,他们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随之失去,到40年代后期,江浙农村社会控制领域已经处于精英缺失的状态。
其次,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是江浙乡村精英阶层缺位的另一个原因。江浙的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大多源自抗日战争时期。如江苏省常熟县东乡(即从西面的福山到常熟县城,南面到阳澄湖以北,东面到太仓县界的地区)有各式各样的武装势力。徐市、东张、珍门等13个市镇都有人数在二三百左右甚至更多的土匪。此外,还有占据着一二个市镇或几个乡,有几十个人、专行敲诈勒索、派捐派款的小股土匪。他们大都各自在占领区内向人民派款收捐,不时互相火并,争夺地盘。[3]这些小规模地方割据力量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并未遭到削弱,相反,有些地方割据力量由于势力扩张,向所控制地区的农户、商户征收赋税,并由保长到各家各户去征集,[4](p.520)与地方政权争夺农村的经济资源。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势力较为强化的苏南和浙北地区,这样的割据势力也威胁着地方政权的权威。张阿六活动于南汇沿海地区,广收门徒,其徒弟吴桂泉活动于六灶、祝桥一带,收有徒弟500-600人,专事敲诈勒索,称霸地方。王伯祥是活动于太湖、奉贤、南汇、松江、金山一带的惯匪马柏生的徒弟,广收门徒,在周浦、召楼一带独霸一方。[2]由于乡村不靖,士绅为了逃避灾害,纷纷迁居城市,远走他乡。小规模地方割据势力增长,排挤了精英阶层的世俗权力,与精英阶层在国家与乡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相比,他们为了掠夺乡村经济资源,时常与地方政权发生冲突,威胁着国家政权对农村的社会控制,直接引起国家在农村社会行政权力的削弱。
再次,基层政权与土豪劣绅的结合也会引起乡村权力结构中的精英阶层缺失。20世纪30年代,国家在强化基层政权和建设保甲组织过程中,抑制土豪劣绅介入乡村事务,并有意扶植新的政治精英,但由于新公职人员等精英分子的影响有限,国家政权时常需要借重于传统精英阶层的号召力。抗日战争中,土豪劣绅介入地方官僚机构和保甲组织,传统精英分子则洁身自好,不仅远离政权机构,而且退出农村世俗权威领域。40年代后期,地方政权为了强化对农村的资源掠夺,转而与土豪劣绅相结合,劣绅则利用担任保甲职务之便操纵乡村政治,以图为个人谋取私利。(注:参见石溪乡第十一保保民给县政府的呈文(1946年6月17日)及镜屏乡第十三保乡民代表丁金弟等给新昌县党部书记吕某的呈文(1947年3月24日),新昌县档案馆:M1-1-147、M1-1-158。)基层政权与土豪劣绅关系的变化,使一些劣绅代替传统精英成为乡村“领袖”,传统精英则被排挤出乡村控制领域,导致乡村政治生活中的精英阶层缺位。而国家为了强化社会控制,就不得不越来越依重于暴力手段,政权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解构已经不可避免。
三
二三十年代,江浙地区经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江浙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国民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富庶的江浙地区,并在此展开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抗日战争中,富庶的江浙成为敌伪攫取资源的核心地区,城乡市场及农村手工业也因之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希望稳定的社会秩序,国民政府也希望尽快实现江浙经济的恢复。然而,好景未长,随着内战重开,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财富的掠夺,城市工业凋蔽、农村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佃业纠纷加剧,江浙农村经济资源因而枯竭。
战前江浙农业、农家副业与手工业均十分发达,战后由于原料短缺、金融萎缩、城乡市场沟通受阻,依赖市场的农家副业与手工业迟迟不能恢复,严重影响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例如,养蚕育茧和缫制土丝是江浙农村的重要副业及手工业,八年抗战中,70%的沿海桑田被毁。在浙江,单是国民党军队砍伐的桑树,就有10亿株以上,欲图恢复,至少要10年时间。加上物价高涨,育蚕收入低微,不够维持生活,蚕农改斩桑树以种植杂粮,桑田面积更是逐年减少,产茧量也一落千丈。杭嘉湖三区在战前每年可产蚕茧33万担以上,1946年至多可收4万担,还不及战前1/8。浙江50万蚕农因此陷于破产绝境。江苏情形与浙江相似,如无锡一地,往年产茧量4万担左右,1946年收购总量只1万余担,仅及过去的1/4强。[5]农村金融机构的堕坏,也是手工业难以恢复的因素。20-30年代,国民政府致力于农村金融网络的构建,在经济发达的浙北地区,每一市镇平均至少有1-2家银行,信用合作社数量增加也很迅速。这些金融机构虽然在扶弱助贫方面成效不大,但对农村经济仍有积极作用。[6](p.15)抗日战争中,江浙各大小金融机构均撤至后方,原来金融业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农村金融亦成停顿状态。[7]战后,金融机构难以重建,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恢复更加缺乏保障。如仅浙江省要想恢复战前之桑叶、改良种、鲜茧、生丝产量,“其费用当在千亿左右。”[8]由于缺乏金融事业的支撑,农家赖以为业的蚕桑经营根本无力恢复。此外,由于内战重开,政权对农村的社会整合缺乏成效,粮食价格暴涨,交通破坏,民力凋残,重建中的农村市场网络再度发生断裂,农村手工业因为缺乏市场支撑而难以复苏。具有经营家庭手工业传统的江浙农村,大量劳动力不得不拥挤在土地上,农民家庭收入锐减,不仅难以支付迅速增加的赋税负担,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缺乏保障。
战后城市工业凋蔽使大量农民向农村回流,使江浙农村的失业更加严重。抗日战争以前,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江浙两省劳动力供过于求。虽然许多农业劳动力兼有副业,但这些兼营副业的劳动力每年的副业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9个月,少的仅有3个月,实际上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至于那些外出劳动力,由于上海、无锡、杭州等城市的工业生产萎缩,纷纷返流,使江浙农村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战后,由于沿海城市经济恢复尚未完成,内战已再度爆发,市场萎缩,人民贫困,工业产品销路清淡,连累工业也走入下坡路。例如,到1949年初,上海大部分工业已走到山穷水尽之境,资力脆弱者已纷纷停工倒闭。纺织业尤其如此,在沪、杭等地,失业之丝织工人日渐增多。不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中断,且有大量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农村劳动力失业问题再次激化。所以,江浙两省长期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至40年代后期更加突出。在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大的苏南和浙北地区,这一问题尤其尖锐。1947年统计杭县8个乡镇,共计劳动力270089人,其中无业者为126167人,占总量的比重高达46%。源于城乡经济恶化的农村劳动力失业,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收入下降,连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注:《杭县墉栖区人口籍别、职业登记表》(1947年12月),余杭区档案馆:91-3-104。)占江浙两省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佃耕农民的生活境遇等而下之,可想而知。
在农村经济衰退中,土地所有者转嫁资源困乏的危机,提高地租率,导致了普遍的佃业冲突。30年代,租佃制下的江浙农民地租负担已经十分沉重。在普遍盛行分成租佃制的浙东地区,地租率往往高达50%。[9]4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收入下降以及劳动力向农业的回流,依赖土地为生的人口较战前增加,地租率又较30年代有所上升。以浙江省桐乡县为例,1930年每亩田租谷为94.59-94.89斤,1946年每亩租谷增为100斤(以18两加4钱老秤计算)。(注:参见五泾乡乡长因一桩田产纠纷案给崇德县政府的呈文,桐乡市档案馆:M6-1-148。)地租率加重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凋蔽不仅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状况恶化,也使得依赖地租为生的土地所有者受到压力,并试图将家庭经济衰退的后果转嫁到佃户身上。业主不仅可以借口佃户拖延或无力交租而提请撤佃,还可以不加名义随意撤佃,有的业主甚至对地方习惯和法令要求给予维护的永佃权也不予尊重。这对于在经济萧条中本已处于劣势的佃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佃业关系随之恶化,佃业纠纷也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佃户失去佃权后,因为对业主无能为力,不得已将“挖佃”的农户告入乡镇公所,由此引起佃农与佃农的纠纷,这一现象可以说是业佃纠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明由地权不均引发的社会冲突已经十分普遍。现实亟需国家采取有力的措施缓解乡村中“人与人为敌”的对立状态。然而,国家政权不仅对改革土地制度无能为力,对分成租佃制也采取纵容政策,这样自然不能缓解佃业纠纷,地主阶层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冲突难以避免。
在上述家庭经济凋蔽、失业增加和佃业纠纷转剧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为了支付内战等巨大开支,仍要加紧对江浙农村的掠夺。如浙江省政府为了催征1946年的田赋,不仅要求各县派遣科员以上人员下乡实地督促、保甲长挨户催督和检验,还通饬警察机关协助追征。(注:《浙江省三十五年度田赋紧急催征办法》,新昌县档案馆:M1-1-162。)如此竭泽而渔的结果只能是农村经济资源枯竭,农民生活陷入绝境,国家不但难以从农村获取资源,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学者们在总结1940年代后期社会控制失败的根源时,往往从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来加以分析,将社会控制失败归咎于国民政府的政治衰败、统制经济政策及其未能致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的重建和恢复。(注:周念忠、祝灵君:《从政治发展看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重庆:《探索》,1999年第1期;汪朝光:《战后初期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的若干问题》,上海:《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也有学者从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接触的层面予以思考,认为地方势力过于庞大及其盘根错节使国民政府无计可施,不得不在阶级冲突的农村中竭力维护现状,因而难以建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注:吴贤辉:《一个被现代化变革浪潮所淹没的政府——再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泉州:《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唐贤兴、唐丽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然而,40年代后期社会控制的失败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因为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顶点,此时农村经济崩溃加剧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性冲突和农村与国家的对抗,而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的缺位,土豪劣绅和小规模割据势力的膨胀,又增加了国家控制乡村的成本和困难,保甲重建失败使走投无路的国家政权更多地诉诸暴力,但无论何种手段都难以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整合,更难以遏制农村社会结构崩解的趋势。在此种背景下,经济恢复也好、政治重建也罢,都会在农村社会冲突加剧的现实中流于纸上谈兵,更遑论建立“民主自由”的结构了。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整个社会需要从根基上重新构造。
收稿日期:2003-0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