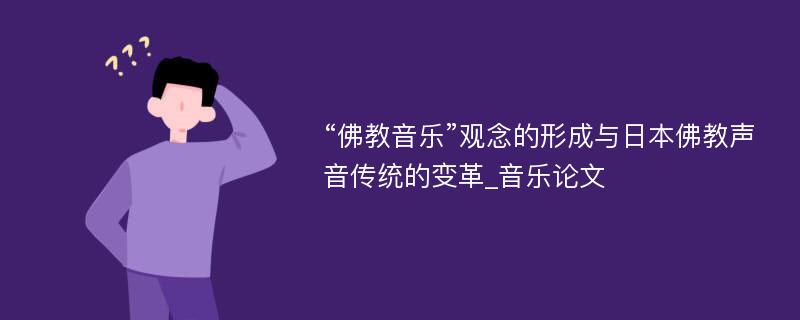
“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与日本佛教音声传统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日本论文,概念论文,传统论文,音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5)03-0094-11 “声明”发祥于印度的梵呗,由中国传到日本之后流传至今。虽然“声明”是一种祈祷国泰民安的佛教修行方式,是以表示虔敬信仰为目的的宗教活动,但是“声明”静谧空灵的声音又能给人们带来一种音乐的美感。因此可以认为“声明”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一门音乐艺术。 我们现在一般将“声明”看作一种日本的“佛教音乐”。在音乐词典中,将日本佛教音乐定义为僧人在举行佛事时所用的声乐,其中尤以“声明”为主。“声明”由中国传到日本之后,相继出现了以日文创作的“教化”、“和赞”、“表白”、“讲式”、“论义”等日式声明种类,也由此派生出并非由僧人而是由居士所唱的“和赞”、“咏歌”、“念佛”等声乐形式。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名为“节谈说教”的说唱形式,即由僧人于法事结束后向民众宣传佛教教义的活动演变而来的说唱。值得一提的是,佛事上由盲僧负责演奏琵琶。一般来说,他们在居土家庭举行佛事时使用琵琶说唱,后来此说唱形式也衍生出其他各种民间说唱种类。江沪时期初,出现了吹奏尺八的普化宗僧人,后来也派生出了民间尺八音乐①。 那么,日本“佛教音乐”的概念究竟从何时开始?笔者认为“佛教音乐”这一概念诞生于日本音乐学者对“声明”开始研究之后。我们同样也可以从美术界的相关事例中找到近似的史实。明治中期(19世纪末),日本美术学者冈仓天心和美国美术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赴日本奈良进行佛像调查,首次将秘藏佛像纳入了日本“佛教美术”的范畴②。在他们的美术研究工作之后,原来供奉于寺院里用于祈祷的佛像成为了博物馆里可供欣赏的日本佛教美术对象。于日本近现代音乐而言,同样如此,在音乐学者提出“佛教音乐”的概念之后,原本寺院里僧人们用于宗教唱诵的“声明”成为了一种“艺术音乐”,成为了在音乐厅的舞台上表演的“佛教音乐”。 “佛教音乐”概念出现后,“声明”传统本身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如有变化,“声明”研究对“声明”传统又有何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近现代日本声明的详细研究情况,试图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声明”研究与“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过程(由“声明”走向“佛教音乐”的历程);第二,“佛教音乐”概念对声明语境的影响;第三,在“佛教音乐”新的语境下,声明传统如何改变。 二、由“声明”走向“佛教音乐”的历程 关于日本“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中国的相关事例。据周耘教授所述:“从佛经分析,佛教不仅有音乐的概念,并且将音乐分成了两类:一类称作梵音,也可称妙音、海潮音,就是正统的寺院梵呗,为严格意义上的佛教音乐;另一类称作世间音,即形式多样内容广阔的世俗音乐。对于佛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的高低优劣,佛经中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以往,山门以内僧侣之间,基本不使用佛教音乐的概念术语,只用梵呗、梵音、海潮音等来指代。久而久之,许多僧侣形成了佛教没有音乐,音乐与佛教无干,音乐就是‘世间音’的强烈认识。其实,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音乐学家入某些寺院调查采录佛教音乐,还令僧困惑不解:‘我们佛教没有音乐呀?音乐不是社会上的吗?’时至今日,这已不成问题。寺院梵呗就是佛教音乐,佛教音乐是传统音乐文化的珍贵遗产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也成为佛教界僧侣间的共识。”③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音乐学者对“梵呗”研究的开展,僧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学者口中的“佛教音乐”概念,这与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在此,笔者将通过分析日本近现代声明研究的状况,来详细阐述“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过程,即由“声明”走向“佛教音乐”的历程。 “佛教音乐”概念的形成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出现“声明”的专门研究与“佛教音乐”概念;之后,形成日本多种音乐皆来源于“声明”的观念;最后,“佛教音乐”概念的延伸。 (一)“声明”的专门研究与“佛教音乐”概念的出现 尽管19世纪末已有谈及“声明”的音乐概论著作,但对“声明”的专门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1868年,日本开国成立明治政府之后,在新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的同时,也传入了欧美各种学科与艺术文化。在音乐方面,1879年成立了国家音乐研究所“音乐取调挂”(后称东京音乐学校,现名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当时,“音乐取调挂”有三个项目:第一,创作融合东西方音乐的新音乐;第二,培养人才,振兴国乐;第三,开展学校音乐教育。为了完成第一个项目,“音乐取调挂”同时对西方、日本音乐进行调查与研究,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 日本音乐研究开始之后,“声明”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只是出现在日本音乐的概论之中。1884年,“音乐取调挂”在其所编写的《音乐取调成绩申报书》当中的《音乐沿革大网》一文中谈及了“声明”④,另外,在1888年日本学者小中村清矩的《歌舞音乐略史》⑤和1891年“音乐取调挂”人员神津专三郎所著的《音乐利害》⑥中也提到了“声明”,但并未将“声明”归为日本音乐的主要种类。由此可见,此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声明的文章,仅在概论中有所指涉。 20世纪初,音乐学者正式开始了有关声明的专门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活动是在东京音乐学校内建立研究所并开展了有关“声明”的调查。1887年,“音乐取调挂”更名为东京音乐学校,开始培养音乐家与音乐教师。1907年,为了调查和保存日本传统音乐,东京音乐学校在校内建立了“邦乐调查挂”的研究所。研究所对雅乐、平家琵琶(使用琵琶伴奏的说唱)、能乐、筝曲、三味线等各种日本传统音乐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就是“声明”。 该研究所的音乐学研究员兼常清佐于日本京都数所寺院搜集“声明”相关资料后,东京音乐学校为了公开调查的成果,于1916年举办了雅乐及“声明”图书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东京音乐学校同时将雅乐资料与“声明”资料进行了陈列,并将这些资料整理编目,最终出版为《雅乐及声明图书展览目录》一书⑦。在这本目录的附录上介绍了雅乐及“声明”,指其都是“日本在古代形成的音乐”⑧,而且还特意说明了此次的陈列资料是“公开千年以来封存秘密经库”之后所获得的成果⑨,这就如同笔者在开章时所记述的美术学者调查佛像、公开秘藏佛像一样。总之,当时的东京音乐学校举行了展览会,展示了珍贵的、未公开的“声明”资料,为后世的“声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兼常清佐早在1913年,即东京音乐学校进行“声明”研究之前,就已发表了含有“声明”内容的文章《日本音乐》⑩。他在文中分析平家琵琶的旋律时曾谈道“声明”,尤其是他将“声明”置于“佛教的音乐”(11)的范围,还指出了日本音乐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各种日本声乐来源于声明”(12)的看法。1920年,兼常清佐向京都帝国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日本音乐一观察》(13),现代音乐学者蒲生乡昭教授则将这篇论文看作日本学术史上首篇以音乐学研究为课题的学位论文(14)。兼常清佐在这篇论文中以“声明”为例,考察了日本声乐结构的共同特征。他出于分析旋律结构的目的,对“声明”种类之一“引声”的部分旋律进行了详细记谱,并在五线谱中使用了三连音与装饰音记法。分析中,兼常清佐利用五线谱来比较“声明”与民歌的旋律,结果发现“声明”的调式与民歌的调式并无太大差异(15)。总之,兼常清佐在“日本音乐”的名目下,将“声明”称为“佛教的音乐”,并对其进行了论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将“声明”视为佛教音乐归入到了“日本音乐”的范围之内。 (二)“各种日本音乐来源于声明”的观念 虽然兼常清佐在1913年所写的文章《日本音乐》中,较早地指出了当时的日本音乐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各种日本声乐来源于声明”(16)的观点,但是在“声明”的相关专著中,日本音乐史学家的这种观念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得以出现。例如,1931年,天台宗“声明”家多纪道忍在《日莲宗声明乐谱》(17)中阐述道:“佛教音乐(即‘声明’)对其他日本音乐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近来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研究。”(18)对他而言,当时的日本音乐学家已开始强调“声明”研究,因为“声明”是各种日本音乐来源的观念在当时已经较为普遍。大山公淳、岩原谛信皆与多纪道忍持有同样的见解(19),岩原谛信谈道:“日本音乐史离不开‘声明’,‘声明’史也离不开日本音乐史。”(20)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声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地位比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因为当时的“声明”在日本音乐概论中仅被略微提及。 实际上,“声明”作为各种日本音乐来源的观念亦可见于当时发表的日本音乐史研究文献。例如,田边尚雄在《日本音乐讲话》中说明,猿乐(能乐的前身)、田乐(与农耕有关的艺术)和平家琵琶(使用琵琶伴奏的说唱)皆来源于“声明”(21)。音乐学者伊庭孝在其著作《日本音乐概论》(1928年)(22)中也对“声明”进行了论述:“日本音乐具有这样的特征,即歌手开始演唱时并不使用律管进行定音,而是自行决定音高开始发声,这种习惯便是来源于声明的表演。”(23)如上所述,当时的日本音乐学家将“声明”归入日本音乐的主要种类,“声明”研究在有关日本音乐概述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一点从当时各种音乐体裁介绍的章节排列顺序中可见一斑。他们极力主张“声明”对其他各种日本音乐体裁有重要影响。如此一来,“声明”便具有了作为一种日本音乐门类的坚实地位。因此,从今天看来,“声明”研究者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这项“探索日本音乐的起源”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佛教音乐”概念的延伸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声明”研究急速走向衰退。直到战后1948年,汉语音韵史与中国文献学专家水谷真成发表了《声明本展观目录》(24)之后,“声明”研究才重新得到复兴。1954年,东洋音乐学会在此学会会刊《东洋音乐研究》上编辑了有关“声明”的专刊《佛教音乐研究》(25),吉田恒三、岩原谛信、田边尚雄等学者们在此专刊上发表了论证较为充分、详细的论文。此专刊首次以“佛教音乐”为题收录了音乐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各学科学者们所写撰写的论文,并涵盖了有关“天台宗声明”、“真言宗声明”、民间传承的“念佛”等各种佛教音乐。此时,现今辞典中所记载的日本“佛教音乐”的概念业已形成。而此专刊中收录的几篇论文后又被重新收录于1972年发行的专著《东洋音乐丛书》之第六部《佛教音乐》(26)当中。此书中还收录了有关西藏佛教音乐以及印度宗教音乐的论文,因此,此时的佛教音乐概念已跨出国门。现今,日本音乐学者仍然以“声明”为主展开对佛教音乐的研究,然而民间传承的各种佛教音乐或国外佛教音乐还没有成为日本音乐学者所重视的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19世纪80年代“声明”在日本音乐概论中仅被略微论及。20世纪10年代后,音乐学家们将“声明”置于日本音乐的范围内进行研究,音乐学界出现“佛教音乐”的概念。他们从“声明”艺术中探索日本音乐的起源,主张“声明”对其他各种日本音乐体裁有着重要影响。20世纪30年代,“声明”确立了其作为一种日本音乐的坚实地位。战后,“佛教音乐”不仅指僧人所唱之“声明”,而且还包括了居士所唱的“念佛”等民间声乐以及国外的佛教音乐。那么,这种“佛教音乐”概念的出现是否会给“声明”本身带来变化?笔者将在后两部分论述音乐学家所提出的“佛教音乐”概念对“声明”语境及其传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佛教音乐”对声明语境的改变与拓展 战前的“声明”研究主要以学术论著为主,而战后的音乐学家们则频繁地参与举办舞台上的“声明”音乐会等活动,拓展了其自身的工作领域。同时,僧人唱诵“声明”的语境也在改变,举行宗教仪式的僧人们被赋予了表演音乐家身份。 (一)“声明”的舞台化 1966年11月,日本政府建立了国内第一座国立剧场。此国立剧场的职能为:第一,主办传统艺术音乐会;第二,培养传统艺术传承者;第三,开展与传统艺术相关的调查研究。1966年11月,为纪念国立剧场的开业举行了首次“声明”音乐会,并于之后每年举行一次。到2015年2月为止,累计已有51次之多。 在剧院首次举行的“声明”音乐会上,表演了日本天台宗流传的“声明”乐曲与真言宗法事。由于这一场音乐会为日本国内初次实验,舞台上的演出使用了与寺院相同的传统形式,因此在日本“声明”历史上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国立剧场通过这场音乐会,也在此后自豪地表示:“人们首次认识到了‘声明’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声明’也终于获得一般大众的认可。”(27)僧是学者片冈义道和栗山明宪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加注了对“声明”曲目的解释。同时,日本音乐学家吉川英史、民族音乐学家小泉文夫等学者们也对“声明”的历史和音乐理论分别进行了说明,并强调了“声明”对日本其他传统音乐的影响。他们在此提出的“声明”定位与战前活跃的学者们所提出的定位有相同之处,即注重从“声明”艺术中探索日本音乐的起源。“声明”初登舞台之时,音乐学家们在战前研究的基础上,主张各种日本传统音乐起源于“声明”,并强调了“声明”在日本音乐史上享有的重要地位。所以,他们对“声明”在舞台上的普及做出了不少贡献。 笔者认为,通过音乐学家们将“声明”作为一种佛教音乐的研究工作,原本在寺院里作为宗教行为供奉的“声明”才能够登上舞台,被众人欣赏。音乐学家们将“声明”与琵琶、尺八等日本传统音乐一样看作音乐艺术,并对“声明”的音乐性以及其历史进行了研究。战前,音乐学家们已强调各种日本传统音乐皆来源于“声明”,并主张“声明”在日本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才会在以保存与振兴日本传统音乐为目的的国立剧场开业典礼的重要时刻,上演“声明”的音乐会。 某些音乐从原来的表演场所分离出来继而被搬上舞台的情况,是一种更换语境的实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是日本的“声明”,各个国家的各种音乐都在舞台上得到展现。近年来,对于这种剧场“舞台化”的音乐表演,有些学者引出了“原生态”的学术概念。田联韬教授将民歌的“原生—态”和“原—生态”进行了区别:“前者是指原生形态的民歌,关注点是民歌的音乐形态,包括音乐本体特征、演唱方法等;后者则是指在原初生态环境中的民歌,强调的是民歌生成与存在的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28)。该音乐被舞台化时,可以保持其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由于舞台化是更换语境的一种状态,所以无法保持“原—生态”,只能在非舞台展示的情况下保存该音乐的“原生—态”。 就“声明”而言,它在其原本的语境中曾发挥着宗教仪式的实用功能(“原—生态”)。然而随着舞台化的进行,尽管僧人们在舞台上能够实现“声明”的“原生—态”艺术表演,但“声明”本身所具有的“原—生态”宗教仪式功能可能被消减。那么,僧人们登上舞台时是否完全放弃了实现宗教的行为,始终从事的是艺术表演?在下一部分,笔者将对僧人们于舞台上实现的音乐性与宗教性目的进行阐述。 (二)僧人在舞台上实现的音乐性与宗教性目的 “声明”的舞台化改变了传承“声明”的僧人对“声明”本身的理解。“声明”的唱诵原本是寺院里的一种宗教行为,然而它在音乐厅作为一种音乐艺术时,僧人们唱诵“声明”的意义与在寺院里唱诵的意义存在极大区别。例如,在国立剧场举行的首次“声明”音乐会上,宗教行为与艺术表演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首次“声明”音乐会上演时,有位僧人曾认为,虽然在没有供奉佛像的场所举行法会,有违本义,但如果将佛像供奉于舞台,佛像便会化身为暴露于台上的娱乐对象,所以对此颇为苦恼(29)。他们在台上表演真言宗法事“大般若转经会”时,僧人们为了遵循纪念国立剧场开业的这一宗旨,在舞台上念唱了“剧场安稳、兴隆文化”的词句。所以,从这一行为当中,我们可以不难发现:他们一方面将“声明”从宗教仪式现场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艺术表演搬上舞台,另一方面,又伴随祈祷剧场昌盛的宗教行为,唱诵了“声明”,同时实现了宗教行为、艺术表演这两层不同含义。他们在变换语境的舞台化情况下,尽管不能够完全实现“原—生态”的“声明”唱诵,但仍然在极力接近“原—生态”,并企图实现宗教行为。 关于这种在宗教行为与艺术表演之间产生的矛盾,我们仍可以参照中国道教音乐的事例。据刘红教授所述:“道教音乐从宫观道场搬上舞台作宗教艺术表演之后,道教音乐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人们也开始通过这种脱离纯宗教形式的舞台表演而认识了道乐并慢慢接受了‘道教音乐’这个概念。为了提高道乐表演能力,有些宫观还派道士进入专业表演团体或音乐学院学习乐器演奏和音乐理论。这种作舞台表演的道教音乐形式的出现,引发了部分道外学者对道教音乐能不能继续保持道乐固有传统的疑虑,这些疑虑包括:有专业音乐人员参与道教音乐的表演,道教音乐是否仍然维持着单纯的宗教色彩和具有宗教的代表性?经专业音乐人员运用专业技术加工、编配之后的道教音乐,是否还具备道教音乐的传统本色?受过专业音乐技术训练的道士,是否会影响他们对传统道乐的继承和认同?”(30) 随着道乐的舞台化进程,人们开始慢慢接受“道教音乐”的概念,以及道士们将它视为舞台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在追求着道乐的艺术性。所以,道教音乐在舞台上发挥得更多的是艺术审美价值。对“声明”而言,搬上舞台之后,其本身所具有的音乐性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立剧场开始向现代作曲家委托创作以“声明”为体裁的现代音乐作品。据多次表演这些新作的僧人新井弘顺法师说,就他自己而言,他并不认为僧人是职业音乐家,但他的师父青木融光大师在海外表演时却被称为“音乐家”,并且非音乐专业的僧人在参与现代音乐作品时,同样被要求读谱及接受音准训练。新井弘顺法师认为,初次参与音乐现场时接受训练的经验是非常重大的改变(31)。 音乐学家提出“佛教音乐”的概念之后,随着“声明”的舞台化,僧人们不仅充当举行仪式的宗教人,而且还获得了舞台表演的音乐家身份。他们在舞台上实现的两种目的——宗教行为与艺术表演,时常会遇到一些冲突。然而当他们每次面对这样的矛盾时,都会重新考虑唱诵“声明”的意义以及“声明”传统的本质。笔者认为,他们的这种思索使得“声明”传统的本身开始转变。那么,在“佛教音乐”概念出现后的新语境中,“声明”的传统到底有何变化?若是“声明”传统已有变化,我们是否还能够将之视为传统?以下,笔者将阐明“声明”传统在“佛教音乐”的新语境中究竟如何改变。 四、“佛教音乐”的新语境中声明传统的改变 接下来,笔者将引入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提出的观点——“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32),以此对“声明”传统的改变进行考察。 “传统”一词令我们联想到从古代一直不变地传承下来的东西。然而,现在被视为“传统”的事物却都比我们想象的出现得晚,其中不乏近现代人造的事物。对此,霍布斯鲍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开展合作研究,出版了论文集《传统的发明》一书。他们对英国王室仪式等传统的发明过程进行解读,针对传统权威性的形成过程,阐明了这些传统实际上是随着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变迁而被构建出来的。 1992年,此论文集译成日文之后,日本音乐学者们开始以各种音乐为对象,对“传统的发明”这一话题进行验证。例如,日本音乐学家渡边裕教授以日本民谣为例,阐明了这一传统发明的过程:在近代,为了强调民谣的权威性,民谣歌手确立了民谣的传统唱法“正调”(某些流派的民谣传承者们皆认为具传统性、正统性的唱法)的概念(33)。 “传统的发明”并不将传统看作静态,而是看成一种可变的动态。在日本,除渡边裕教授的研究成果之外,各种音乐研究常常皆以传统权威性的形成过程为中心,对“传统的发明”进行论述,而忽略了这种所谓“传统”的声音本身的变化。关于这些课题,笔者在阐释受民间音乐影响的佛教音乐“咏歌”时已有说明:音乐的传统,特别是当传统被口传时,总免不了有变化,也就是说“正调”在不断产生渐变;音乐传承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正调”变化的同时,他们将已变的“正调”再次确认为“传统”(34)。音乐传统是经由不断再创而来,呈现出不断演变的动态。 针对本稿前文论述的“声明”而言,在“佛教音乐”概念出现后的新语境之中,“声明”的舞台化也是“声明”传统再创造的一次契机。“声明”传统一边受到“舞台化”新语境的影响,一边产生渐变。例如,僧人们上演以“声明”为体裁的现代音乐作品时,接受了音准的训练,对他们在寺院做声明法事时的唱诵方式也有不少影响。僧人们登上舞台后,虽然唱诵“声明”的方式有一些变化,但笔者认为他们必定重新确认了“声明”的传统,并再创了“声明”的“正调”。 接下来,笔者将对复原“声明”法事的工作过程、“声明”唱片的制作过程以及“声明”的五线谱化等多个问题,以“传统的再创造”为核心来阐明“声明”传统在“佛教音乐”新语境下如何改变。 (一)复原“声明”法事的工作过程 进入21世纪后,音乐学家开始致力于古代“声明”乐曲的复原工作(35)。例如,音乐学家泽田笃子教授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僧人合作复原了在日本中世纪已失传的佛事“最胜会”。最胜会是讲说佛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佛事,即日本南京(奈良)三会之一。公元830年,敕于日本奈良药师寺举行的“最胜会”之后,每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之七日间均奉敕举行。1528年,药师寺讲堂与举行“最胜会”时供奉的绣佛烧毁后,此佛事便失传。 泽田笃子教授对“最胜会”进行了调查:第一,通过阅读《最胜王经》,他们对此仪式及其教义进行了分析;第二,对此仪式的成立过程和历史进行了考察;第三,通过考虑现代佛教仪式的习惯,复原“最胜会”的佛事(36)。为了在舞台上复原此仪式与“声明”演出,泽田笃子教授对“最胜会”从音乐学、佛学、美术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一,与佛学专家一道对《最胜王经》进行分析;第二,对“声明”传统乐谱进行解读后,将其译成西洋五线谱;第三,在美术学家的协助下,复原了奈良时期制作的阿弥陀三尊绣佛原画与当时僧人所穿法衣。 2003年,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泽田笃子教授与传承“声明”的现代僧人们合作,在舞台上重新复原了佛事“最胜会”的演出。排练演出时,僧人们一边参考学者复原的“声明”乐谱,一边按照“声明”的现行惯例进行演出。在法事的最后阶段,现代作曲家的器乐曲新作以法乐身份上演。2003年,此“声明”演出获得了由日本文化厅主办的艺术节音乐部门的奖励。为了复原已失传的“声明”乐曲,音乐学方面的研究不可或缺。因此,研究“声明”的音乐学不仅在研究方面,更在表演实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那时起,约五百年前失传的“最胜会”成为了奈良药师寺大讲堂每年例行的仪式活动。 这种复原工作是在以往“声明”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和“声明”舞台化实践的基础上才得以成功。在这种新语境下,“声明”传统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在约五百年后复原佛事“最胜会”时,虽然学者们的细致考证基于史料,但此佛事在舞台化时,没有完全复原一如往昔的佛事形式,还需要加入创作新曲等创造性手段,并非原来寺院环境中的情形,而是舞台新语境下的表演。由此可见,此演出不是“原—生态”,也不是“原生—态”,而是创造性的佛事演出。 僧人们参与此佛事演出时重新界定了佛事传统,且将被再创的佛事编入他们一系列的传统定例仪式之中。在舞台化表演的基础上,他们对“入堂”等仪式程序加以更改(37),将新创的“最胜会”佛事从舞台又搬到原来的语境(即寺院)当中。从此以后,此“最胜会”以“原—生态”佛事的形象在药师寺大讲堂每年出现至今。 (二)“声明”唱片的制作过程以及“声明”五线谱化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声明“舞台化”的展开以及“佛教音乐”概念的普遍化,唱片公司越来越致力于制作“声明”唱片,研究者们也在这些唱片封套里撰写了学术水平极高的唱片说明。例如,录音唱片《真言声明》(金田一春彦解说,Polydor,SMN-9002-1/4,1964年)、《天台声明》(片冈义道监修解说,Polydor,SMN-9001-1/4,1964年)的讲解文字都被重新收录于1972年发行的专著《东洋音乐丛书》之第六部《佛教音乐》(38)当中。这两张唱片都在日本政府文化厅主办的艺术节上获奖,说明唱片不仅在学术上享有很高价值,作为艺术作品也获得了极高评价。 随着唱片制作的发行,研究者也踊跃使用以西洋五线谱为载体的“声明”记谱法。例如,“声明”五线谱集《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一卷)(1969年,简称为《乐谱篇》)(39)是由民族音乐学家小泉文夫等人编著。他们使用五线谱记录下了在《新义真言声明集成(唱片篇)》(真言宗丰山派佛教青年会新义真言声明集成刊行会,Victor,PRD-13003/14,1963-1965年)中所收录的“声明”录音。 在《乐谱篇》中使用五线谱记录“声明”旋律的目的为:第一,将“声明”的传统准确地传承下来,用五线谱代替传统的“声明”乐谱可以当作“模范课本”普遍使用;第二,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40)。此乐谱集的编者们采用五线谱记写“声明”的规约性记谱(prescriptive notation),不仅可以为不了解传统“声明”乐谱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声明”音乐结构,还可以为“声明”传承者们(僧人们)使用五线谱起到指导作用。 实际上,“声明”的五线谱记谱法对“声明”的传统形式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关于《乐谱篇》,小泉文夫等民族音乐学家认为,五线谱记谱法对“声明”传统形式的保存、继承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五线谱记谱却呈现出“声明”传承者所使用的传统乐谱与“正统”的“声明”录音之间的一些矛盾(41)。因此,1995年以后,传承者屡次对正统的唱法即“正调”进行了讨论,终于在2006年最终确立了“正调”的“声明”唱法。同时,传承者也按照此唱法修订了“声明”的传统乐谱(42),并重新录制了“声明”的正统诵唱。 由此可见,音乐学家所制作的录音与记谱促使了传承者们更加关注“声明”传统的变化。然而传承者并非直接借用了音乐学家所制作的五线谱规约性记谱,而是自己动手修订了传统的规约性乐谱与录音。可以说,“声明”的传统是由传承者自身不断地再创造而得来的。 包括“声明”在内的各种日本音乐在传承上都遵循着独特的“家元”(43)传承制度,日本音乐的传承者们竭力保存以往的音乐形式,但是音乐传统的演变不可避免。有时,对于这种音乐传统的变化,传承者并没有意识到已经接受并传承了这些变化,却经常敏感地意识到传统本身的变化。例如,音乐学者开始着手对“声明”研究并称之为“佛教音乐”之后,“声明”进入舞台化、制作唱片等新语境,“声明”传承者必然会意识到其传统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全世界的各种音乐传统进入到新语境中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那么,在这种新语境中,我们应当怎样将音乐的传统传承下去?本文提出了两个实例:第一,研究者对已失传的佛事进行复原与舞台化后,其佛事编入佛寺每年举行的一系列传统定例仪式;第二,传承“声明”的僧人们参考研究者所创的“声明”五线谱,重新编辑了规约性声明记谱。虽然这两种实例有所区别,但传承者都并没有完全接纳研究者的新方法,而是依据自身的习惯与原则再创了“声明”的新传统。由此,笔者认为再创造音乐传统的主体应当是传授其音乐的传承者。无论音乐学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都会影响音乐语境的改变,也会对音乐传统产生影响。音乐学者也需要了解他们自身对音乐传统本身有何影响,并且需要考虑他们如何参与音乐传统的再创造。 日本进入明治时期以后,音乐学家通过对原来作为宗教行为唱诵的“声明”进行研究,界定其为日本传统音乐的一种——“佛教音乐”。当然,人们将“声明”的音声作为音乐来进行享受并非始于近现代,而是早在近现代以前便已出现。例如,我们可以在古代佛典上发现许多“音乐”、“乐”一类的词语。然而,近现代音乐学家提出“佛教音乐”的概念使得“声明”登上舞台,被人们欣赏,也正如其他日本传统音乐西方古典音乐一样。音乐学家对保存“声明”传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使用五线谱记录“声明”的同时,也对“声明”的唱片和CD制作工作进行了协助。 在这种新语境中,“声明”的传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音乐学家对复原佛事的工作做出很大的贡献,因此其佛事首先登上舞台,而这种佛事演出即非“原—生态”,亦非“原生—态”,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表演。此后,僧人们将这种佛事搬回原来的寺院环境中,并将已经更改的佛事舞台形式作为新的传统仪式实施举行。在此,创造性佛事演出在原来的语境中成为正统的宗教行为,即是再创造性“原—生态”。 由此可见,“原—生态”不是从古代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而是在不断演变,甚至有可能被再创。完全不变的“原—生态”不可能存在,然而,在已变的“原—生态”中还是否是传统音乐的面貌?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传承者本身在已变或被再创造的“原—生态”音乐中还能否辨认出其传统,毕竟传承者自身的认识对其音乐传统是否存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成果也会对传承者的传统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除传承者以外,音乐学者也需要致力于这些重要课题:如何传承音乐艺术?如何再创造音乐传统?总之,我们音乐学者需要慎重地重新考虑我们所做的研究对音乐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并且重新考虑如何与传承者保持合作关系、如何参与音乐传统的再创造过程。 ①[日]平野健次:《日本音乐大事典》,东京:平凡社,1989年,第66页。 ②[日]神林恒道:《美学事始》,东京:劲草书房,2002年,第115-117页。 ③周耘:《曼妙和谐——佛教音乐观》,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6-57页。 ④音乐取调所:《音乐取调成绩申报书》,出版者不明,1884年,第138页。 ⑤[日]小中村清矩:《歌舞音乐略史》,东京:吉川半七,1888年。 ⑥[日]神津专三郎:《音乐利害》,东京:神津专三郎,1891年。 ⑦东京音乐学校:《雅乐及声明图书展览目录》,东京:东京音乐学校,1916年。 ⑧东京音乐学校:《雅乐及声明图书展览目录·附录雅乐声明图书的搜集与分类》(雅楽及び声明図書展覧目録·附録雅楽声明図書の蒐集と分類に就て),东京:东京音乐学校,1916年,第2页。 ⑨同上,第5页。 ⑩[日]兼常清佐:《日本音乐》(日本の音楽),东京:六合馆,1913年(蒲生美津子、土田英三郎、川上央重新编录:《兼常清佐著作集》,东京:大空社,2008年,第1卷)。 (11)[日]兼常清佐较早将“声明”看作“佛教音乐”(同上,第83页)。1917年,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也在其文章《声明音律》(声明の音律に就て)上将“声明”称为“佛教声乐”([日]田边尚雄:《声明音律》,《音乐》,1917年,第8卷第8号,第1页)。 (12)同注⑩,第82页。 (13)[日]兼常清佐:《日本音乐一观察》(日本の音楽に就ての一観察),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1920年([日]蒲生美津子、土田英三郎、川上央重新编录:《兼常清佐著作集》,东京:大空社,2008年,第3卷)。 (14)[日]蒲生乡昭:《兼常清佐对日本声乐旋律进行的分析》(兼常による日本の声楽旋律の分析について),[日]蒲生美津子、土田英三郎、川上央:《兼常清佐著作集》,东京:大空社,2010年,别卷,第174页。 (15)同注(13),第141页。 (16)[日]兼常清佐:《日本音乐》(日本の音楽),东京:六合馆,1913年,第82页。 (17)[日]多纪道忍:《日莲宗声明博士》,静冈:日莲宗法要式研究会,1931年。 (18)同上,《日莲宗声明博士·洋乐谱》,第1页,新堀欢乃译。 (19)[日]大山公淳在《声明的历史及音律》的《序言》中将“声明”形容为“佛教的声乐”、“在佛教仪式中使用的古典声乐”,他说:“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日本声乐基础的一部分来源于声明。因此,我所写的声明历史与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见大山公淳:《声明的历史及音律》(声明の歷史及び音律),和歌山县伊都郡:密教研究会,1930年,第1页,新堀欢乃译。岩原谛信在《声明教典》的解说篇中说明了“声明”对其他日本音乐的影响,并确定了“声明”在日本音乐史上的地位,见岩原谛信:《声明教典》(解说篇),高野山(和歌山):松本日进堂,1938年,第10、24页。 (20)[日]岩原谛信:《声明教典》(解说篇),第10页,新堀欢乃译。 (21)[日]田边尚雄:《日本音乐讲话》,东京:岩波书店,1926年,第154页。 (22)[日]伊庭孝:《日本音乐概论》,东京:厚生阁书店,1928年。 (23)同上,第668页。 (24)在这篇目录中,水谷真成介绍了有关“声明”的第一手资料(岸边成雄博士古稀纪念出版委员会:《日本古典音乐文献解题》,东京:讲谈社,1987年,第203页),为“声明”音韵研究奠定了基础。 (25)东洋音乐学会:《佛教音乐研究》(仏教音楽の研究),《东洋音乐研究》,第12、13合并号,东京:音乐之友社,1954年。 (26)东洋音乐学会:《佛教音乐》(东洋音乐选书6),东京:音乐之友社,1972年。 (27)国立剧场:《国立剧场二十年史》(国立劇場二十年の步み),东京:国立剧场,1986年,第55页。 (28)田联韬:《原生态:“原生—态”,抑或“原—生态”?》,《人民音乐》,2009年第9期,第15页。 (29)[日]蒲生乡昭:《作为音乐的声明》(音楽としての声明),《乐剧学》,2000年,7号,第83页。 (30)刘红主编:《天府天籁——成都道教音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 (31)[日]新井弘顺、芝祐靖、服部幸雄、三隅治雄、山田庄一、(司仪)权藤芳一:《乐剧与国立剧场:成果与课题》(楽劇と国立劇場=その成果と課題)(研讨会记录),《乐剧学》,1997年,第4号,第40-43页。 (32)[英]霍布斯鲍姆、兰杰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Hobsbawm,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第1-15页。 (33)[日]渡边裕:《接触异文化的民谣:以“正调江差追分”为例考察自我象征的成立与变迁》(異文化接触の中の民謡—「正調江差追分」にみる自己表象の成立と変容),[日]寺内直子·渡边裕:《日本音乐、文艺接触异文化的结构——1900年开办巴黎万国博览会前后东西方观点的相互改变》(日本音楽·芸能をめぐる異文化接触メオニズムの研究——1900年パリ万博前後における東西の視線の相互変容),《平成13~15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1))研究成果报告书》(平成16年11月版),研究课题号码13410018,第144页。 (34)[日]新堀欢乃:《近代佛教教团与咏歌》(近代仏教教団とご詠歌),东京:勉诚出版,2013年,第169-244、248-250页。 (35)此研究的主要文章有:[日]泽田笃子:《药师寺最胜会形成过程之研究——从仪式、音乐的传承与创造的视角来考察》(薬師寺最勝会の形成過程の研究——儀式·音楽における伝承·創造の視座から)(平成13~15年度科学研究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大阪:大阪教育大学,2004年;[日]近藤静乃:《中世纪如法经十种供养的奏乐与伽陀——以妙音院流派伽陀的复原曲为主》(中世如法経十種供養における奏楽と伽陀——妙音院流伽陀の復曲をめぐつて),《乐剧学》,2008年,第15号,第1-25页。 (36)[日]泽田笃子:《药师寺最胜会形成过程之研究——从仪式、音乐的传承与创造的视角来考察》,同上。 (37)通过对演出节目单上所写的仪式程序(泽田笃子:《平成十五年度文化厅艺术祭赏大赏受赏纪念公演药师寺“最胜会”复兴上演》药师寺最胜会复兴上演实行委员会,2004年4月19日)与在药师寺官网上所记载的仪式程序(药师寺:《最胜会的日程、式次第》,2015年2月16日阅览,http://www.nara-yakushiji.com/contents/saisyoue/nittei.html)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找出二者之间的一些差别。 (38)东洋音乐学会:《佛教音乐》(东洋音乐选书6),东京:音乐之友社,1972年。 (39)[日]栗山明宪、小泉文夫:《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一卷),东京:新义真言声明集成刊行会,1969年。 (40)同上,第xxiv页。 (41)《乐谱篇》(第一卷)的续篇《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二卷)(真言宗丰山派佛教青年会出版委员会:《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二卷),东京:真言宗丰山派佛教青年会,1998年)中,编辑乐谱的音乐学家近藤静乃也回顾了《乐谱篇》(第一卷)的记谱工作,并明确了制作“声明”五线谱记谱的目的,即正确地呈现传统“声明”乐谱与“声明”诵唱者实际所唱的旋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见真言宗丰山派佛教青年会出版委员会:《新义真言声明集成(乐谱篇)》(第二卷),同上,第19页。 (42)[日]新井弘顺:《丰山声明大成》,东京:丰山声明大成刊行会,2006年。 (43)“家元”指的是某种特殊技艺者的家族或流派的根本,即最具其流派的正统,并统管其流派的人士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