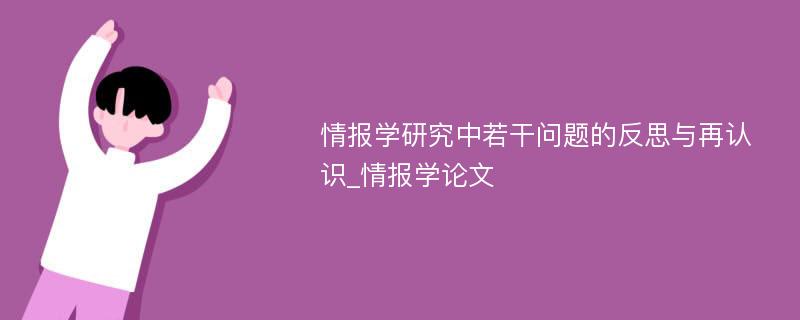
对情报学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反思和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情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情报学基础理论的问题,最近又引起了诸多学者的热心探讨,情报学学术期刊上最近一年关于情报学基础理论和情报学发展的文章顿时多了不少,2006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图书情报档案下就有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这似乎也是对跨过21世纪大门五年后情报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和反思。可见,情报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在经受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的冲击和适应下,其发展方向和基础理论仍备受情报学理论界的关注。
1 对情报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总的来说,最近一年关于情报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是批评之声多于支持之意,并且就一些情报学基本事实性问题的看法,大家也是众说纷纭。有文章认为情报学发展已经日臻成熟完善,而文献[1]则认为情报学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文献[2]提到甚至有些人以为情报学迄今仍称不上科学;文献[3]认为进入21世纪的情报学正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在一些重大理论上存在着分歧,同时也标志着情报学正处于一个学科转折时期,一个思维变革时期,而也有学者认为情报学在跨过21世纪大门后将取得极大的发展;文献[4]认为当情报学核心阵地巩固之日,理论作用得以彰显之时才是情报学成熟之期,而目前显然不是。对于情报学教育问题,文献[5]认为情报学教育已经基本能与信息、网络时代相适应;而文献[6]则认为情报学教育存在着极大的内在不平衡性,要求我们反思和总结情报学的发展问题。对于许多学者认为的情报学发展有着边缘化、泛化、弱化和信息化的生存危机[7],有学者在博客上以“情报学的博士点、硕士点的大力发展作为论据进行反驳”。
社会科学问题容易受到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某些问题的争论是在所难免,可以理解。然而,对于一些学科发展现状基本认识的看法上,存在着如此诸多争议,则让人不得不认真思考。一方面的原因在于部分学者在研究时缺乏一种客观的精神,用词不够谨慎,使表述不符合事实,个别的更是意气大于理性;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在于该学科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使同一领域不同类群的人们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不过,一般来说,不满意者多来自基层的科技情报所、图书馆以及一些早期的情报工作者,而一如既往进行研究的大都是information science的推崇者。仔细观察近些年来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研究者的身份,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具有高学历的中青年情报学研究者以及一些情报学学生开始对情报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种种疑问。在对情报学发展现状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上,笔者以为这已不仅仅是个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牵扯着不同群体研究者的理念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报学家应当承担起学术的责任,对情报学信仰的责任,对情报学后来者进行引导的社会责任。
情报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对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的重要作用这里已毋庸赘言,日本地域狭小,资源短缺,但作为一个情报大国,其全方位的情报战略为国家战后的复兴、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的高度竞争的世界里,中国要获取长远的可持续竞争力,就必须发挥情报的建设性、战略性作用,让情报在各个层面上产生溢出效应,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一些情报学专家认为情报将在这个新的时期有所作为,情报学将大大发展是不无理由的。日本人早已把情报分析力视为国力指数的十大要素之一,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8]。而中国的情报实践工作也曾经有过辉煌,在20世纪60、70年代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两弹一星的发射提供了情报支持,完成了“耳目、尖兵、参谋的使命”[9]。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情报工作在我国的实践现状有弱化的趋势,情报工作的地位有所下降,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与指导应用于实践的情报学理论的不健康、不平衡发展有很大关系。不可否认,随着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浪潮,情报技术较以前有长足的进步,而基础理论的发展却裹足不前,大家对情报学发展的方向、研究对象等一些学科基本问题无法取得一致,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仍陷于争论的泥淖中,不得不承认,情报学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有学者提到了政府的制度救济[10],在笔者看来,这对情报学来说,无疑是一个耻辱。情报学也曾经有过辉煌,情报实践也曾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却要寻求政府的制度救济,这恐怕是情报工作本身的问题,是情报学自身发展的问题。笔者从未听说过经济学、政治学和物理学、社会学要寻求什么制度救济,对于出现目前这种现状,笔者想问,对比早期我国情报学、情报工作的大发展,我们对情报学到底做了什么?此外,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是要求情报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技术、制度、文化、资源相适应,而非要求社会为某一学科的生存做出什么,提供什么。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一个学科发展无法适应社会,学科理论止步不前,在当今学科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终将面临被取代的危机,这也是学科的生存规律,是知识新陈代谢的一种必然现象[11]。正如前面所述,情报学由曾经的辉煌到目前不得不承认的没落衰弱,远不是那些情报技术等从物理层面所能解决的,情报学本身是一个人文结构,需要人文精神的支持,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
对于一位情报学家所说的:“情报学研究已经不是提出什么问题或理论,而是将现有的各种理论进行整合”,笔者认为,无论是整合现有理论还是另辟途径创新地提出新的理论,只要能为大部分情报学者所接受,能为情报学的信仰者们所认可,都是可行的,因为学科本身就是有一群学科信仰者们所共同认可的理念所组成、所发展的。
一位情报研究者认为目前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章较少,并且在这些文章中也是对问题的总结概括居多,提出解决办法者却很少。然而,创新地解决问题还是要站在深刻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当然我们也要加紧思考、创新的力度,尽可能构建一个合理的、为我们大部分情报学信仰者们所认可的基础理论体系,真正为情报学在新世纪的辉煌注入活力,为情报学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下面,笔者首先就情报学发展中关乎基本理论构建的两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希望能够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把握情报学的本质、精髓,为构建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创造条件。
2 关于intelligence和information
对于Intelligence science和Information science的讨论,虽然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真正白热化争论的导火线应该说始于90年代为适应社会信息化浪潮国家科委所作的情报改信息的决定[12],以致使全国各地的科技情报机构悉数改称科技信息研究所。之后,学术界对情报、信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声讨之声此起彼伏。而情报信息之争也逐渐引起了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由翻译引起的问题,认为情报学本来就是intelligence science[13],认为应该树立另一种情报观(intelligence study)[14]。而目前我国的情报学在国际交流中用的是information science,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早期我国的情报学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难以在发达国家寻找完全对等的学科与实践活动,直到1990年竞争情报的引进之前,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尚未找到开通国际学术交流渠道的接口,情报研究的学术论文很少引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文献,情报界的出国考察报告很少反映国外情报机构中类似我国情报研究的工作现状。我国的情报研究理论与应用成果也难以输出。而欧美发达国家竞争情报研究理论的兴起,方为我国情报理论研究打通国际学术交流的通道提供了契机[15]。而information与 intelligence的争论和学术研究的矛盾事实上是原本存在的,只是在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原本隐没、不甚突出的问题逐渐显化、激化而已。
笔者以为:
(1)对于国家科委所作更名决定而引起的学术界对此的质疑声讨,笔者以为是大不应该的。科学本身的发展是独立的,有着它自身内在的规律,真正学术的研究是不应该受到所谓行政的影响的,也绝非是一个国家机构所能影响的。况且,国家科委所作的决定是一个行政机构名称的正常更改,是国家机构的独立行为。如果把学科发展本身的一些问题归罪于一些国家机构的更名,把科学本身的内在机理归结于一些外部因素,恐怕有些勉强,难道情报学的发展必需某种程度上的制度救济吗?不过,既然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影响和争论,也反映了我国情报学自身与科技情报工作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我国情报学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的事实,反映了我国情报某种程度上的“地方特色”,难怪乎一些文章称情报学无论在实质内涵上还是学科称谓上都具有中国特色[16]。此外,也不得不承认情报学本身的内在脆弱性,它的生存和发展要建立在某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甚至仅仅是情报工作的工具。难怪乎一些人认为情报学迄今仍称不上科学[17]。一门科学是要建立在一类实践活动之上的,因此要构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为情报学明确一个服务的方向、实践的平台,使之有广阔的生存基础,然后再把握这些实践工作的规律,作为情报学理论的基础和支撑。
(2)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之争的直接原因在于学术的国际交流。正如前面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学术交流较少,竞争情报的引进是一个突破口,随着90年代国际上信息化的影响,我国情报学研究也呈现出信息化的趋势,情报学顺势与国外的information science相匹配。目前情报学研究现状的一个事实是情报学简直已成了信息科学,使得information science似乎更加反映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使得information science用来进行国际交流确实更加合适。然而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情报学的信息化在中国并非很成功,引进多于创新,泛谈多于实用,并且在翻译时也时常遇到大家不可理解的现象,如文献[18]在介绍国外学者Brooke E.shekdon时,称其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情报学院前院长、荣誉教授,而介绍Rush Miller时用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对于同一个英文单词information,有时用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之中,却采用不同的有争议的翻译用语,着实给情报学的学习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和障碍。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真的是我们所说的情报学吗?这的确令人怀疑,值得思考。
对于出现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争论,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们含义的区别而大谈特谈,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或者处理的原则,对此笔者以为:
(3)我们有必要将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严格分开,“信息爆炸”就是“信息爆炸”,绝非“情报爆炸”;图书信息学就是图书信息学绝非图书情报学。对于学术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我们要借用国际通用的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将我国的library science和所谓的information science相结合,即图书信息学,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强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而在这其中进行信息社会学、信息法学、信息伦理等方向的研究也是情理之中,合乎学科发展方向和人们的认知心理。
(4)对于我们的情报学,我们宜采用保持原有传统特色,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同时为适应现代信息社会信息化的需要以及坦诚面对信息与情报的某种客观关联性,我们在区分信息与情报、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基础上还要进行有限度的整合和融合。情报学要吸收现代information science关于信息检索、信息搜集等方面只要与最终情报获得有关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也是产生高质量情报产品的必要工具),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报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对于情报学的交流,笔者以为还是以情报学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为基础、为标准,而非为了国际交流而牺牲我国情报学自身的生存土壤。我们搞情报学研究的目标是为了情报的推广,发挥情报的溢散效应和经济效应,使我国真正成为情报大国,成为输出情报理论的基地,而非不断吸收information science的接收器。
3 大小情报观的争论
所谓大小情报观之争实际上是我国情报工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众所周知,我国情报学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因此当时的情报学以研究科技情报的规律为主。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情报工作地位的相对下降,为使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进步和市场化的要求,突破早期科技情报工作的局限性,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19],就产生了要将情报工作拓展到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趋向和呼声,此即所谓的“大情报观”,它和“小情报观”的区别在于情报实践的范围不同,“大”“小”之说也完全是从范围的宽广上来说的。
笔者下面所要说的是另外一种情报观,也是目前我们很多人在使用“大小情报观”时所实际指代的对象。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情报学研究的泛化、信息化现象逐渐严重,一种以信息现象(如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信息法律、信息伦理、信息道德、信息管理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情报学研究观随之受到大家的关注,有研究者在表述这种现象时就用“大情报观”予以替代(如文献[20]中就提到目前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方向仍以所谓的“大情报观”为主流)。而与之相应的是一部分情报研究者不满意情报学研究过分信息化的现状,为情报学的日趋边缘化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忧,主张固守情报学研究的本位,坚持情报学的特色,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此即所谓的与“大情报观”相对应的“小情报观”。这种“大”“小”情报观的争论已远远不再是内容范围上的扩展,而是研究对象上的本质区别。
对于前一种情报观,虽也有争议,但大部分人还是认同情报学应该适当合理地拓展情报理论研究和情报实践工作的范围。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情报观实际上只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理论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21],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对情报学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不过应用范围的扩大对于我们从实践中总结理论,对我们情报学理论建立在更加广阔的实践基础之上是有帮助的。
对于后一种情报观,学界在“信息”与“情报”的争论中表现了不同的看法。一般“大情报观”的支持者们认为情报学研究中加重信息的比例是为了适应信息化的浪潮,为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拓展情报学的生存土壤,并且这种情报观占据着情报学界的主流。正如文献[20]所说,目前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方向仍以所谓的“大情报观”为主流。这些也可以从我们一些情报学专业核心期刊的载文内容上看出。而反对者认为,在今天的情报学刊物上,传统的情报计量和情报检索研究已不是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管理、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信息政策、信息伦理、信息安全、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知识挖掘、网络信息、搜索引擎、数据仓库、竞争情报、电子商务、系统集成、数字图书馆、全文检索等全新的广泛的领域,认为这种研究表面上繁荣,实际上是在承受着异化的后果:研究对象模糊不清;基础理论支离破碎;方法体系杂乱无章;学科定位无所适从;专业教育随机摇摆;情报学疯狂地抢占信息科学群体的地盘,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为已有,而不是本质上、核心上深化和发展的情报学,这种盲目的扩张可能导致情报学走向消亡[22]。这种情报观正引起“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的激烈争论[23]。部分学者认为竞争情报代表着情报工作发展的方向[24]。认为情报学在渗透和融合上,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保持发展的均衡性,使得情报学的学术尊严和学科地位在新的环境下逐渐削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情报学本身该具备的学科影响力[25]。认为情报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内热外冷和超界研究现象[26]。认为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目前只能在物理层面上解决问题[27],而情报学本身则有很强的人文性质。总的来说,这种情报观的争论其本质在于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拓展和延伸,而不像第一种情报观的本质仅仅在于学科应用对象和应用范围的变更上,是学科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后一种情报观则隶属情报学基础理论问题,反映了在新的环境下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问题。它是人类探索科学本身的一种体现,其正确合理与否关系到情报学作为众学科一分子,其对其他学科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关系到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影响着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和持久生命力。
前面对两种情报观进行了详细的表述,对于第一种情报观,我们只要认识到它作为情报学发展史上的一段背景情况即可,对我们目前的情报学研究影响不大。而后一种情报观,则需要我们慎重对待,它关系到情报学的基础理论和长远发展,至于采取什么态度,我想各位情报学同仁会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客观公正的看法。笔者基本的认识是:大的缩小,小的扩大。这其实也牵扯到了information情报观和intelligence情报观的问题,至于如何确定把握“缩小”与“放大”的标准和量度,限于篇幅问题笔者以后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
收稿日期:2006-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