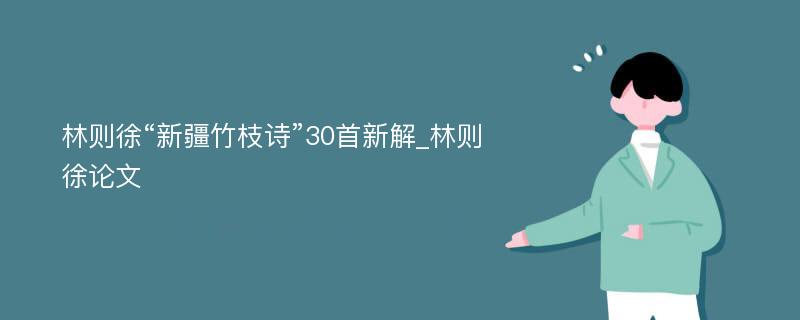
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三十首》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枝词论文,林则徐论文,新解论文,三十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3)02-0086-09
清代,我国因称伊斯兰教为回教,所以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称为回回,将维吾尔人称为回人或回子,将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称为回部或回疆。
近代伟大的爱国英雄林则徐因禁烟抗英无辜戴罪,流放新疆三年之久。在伊犁两年期间,参与垦荒修水利,成效卓著。道光帝遂传谕林则徐前往南疆勘地。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深入南疆半年的时间里,不仅履勘垦地近六十万亩,而且入乡问俗,以竹枝词的形式着力吟咏。
竹枝词,乐府名。本巴渝(今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是流行于当地、可以配上乐舞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歌辞。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歌咏巴山蜀水间的民间生活风俗和男女恋情,也曲折地流露出他遭受贬谪后的幽怨愤懑之情,盛行于世,产生颇大影响,为人称道和效仿,遂作为诗体之一而流传,此后历代诗人争相吟咏仿制,曾写过各地《竹枝词》,杂咏民情风物,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和谐,文笔轻快。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则别具一格,诗中运用大量维吾尔语,形象地反映维吾尔族在清代的历史、制度;反映农作节气;反映历法、宗教;反映文化艺术;反映建筑、医疗;反映衣食起居;反映婚嫁丧葬;反映生产落后荒凉之状和人民生活艰辛之情。
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据光绪丙戌福州本宅刊本《云左山房诗钞》卷七刊载为二十四首,(注:请参见周轩《林则徐诗选注》,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1~279页。)但在2002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卷中却为三十首(录自邱远猷藏钞本)。不仅增加了原来没有的六首,而且原来的二十四首中有十首的字句有所改动,(注:《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六册诗词卷,第242~246页。全集编辑委员会本卷编辑说明:“本卷采用的底本,优先选用手稿或手定本,其次则友人的录存,最后才用《云左山房诗钞》或其他钞本,尽可能保存原貌”。新增六首为之二、之七、之八、之二十一、之二十八、之二十九。字句改动的诗句,在文中注明。)这就使《回疆竹枝词三十首》给我们一个前所未见的新面貌,本文试做新解,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反映维吾尔族在清代的历史、制度
“别谙拔尔(回部第一世祖,见各史传)教初开,曾向中华款塞来。和卓运终三十世(至玛哈墨特止),天朝拓地置轮台”(之一)。“别谙拔尔”,维吾尔语音译。原意指圣人,也指使者、先知。清代文献常以别谙拔尔作为穆罕默德的代称。即诗中夹注的“回部第一世祖”。穆罕默德(约570~632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在他身后,艾卜·伯克尔、欧默尔、奥斯曼、阿里相继为“哈里发”(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和卓,波斯语Khwaja的音译,原意为显贵、富有者。后为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玛哈墨特,即玛罕木特。据《西域图志》记载的《回部世系》,玛罕木特为穆罕默德的第二十九世孙。其子波罗尼都、霍集占两兄弟(史称大小和卓)为第三十世孙。从目前传世的所有新疆和卓世系来看都是穆罕默德家族,是他的女儿法蒂玛与阿里的后裔。其实,这些所谓的“世系”是根本不可靠的,是一些伊斯兰教上层分子抬高自已身份的自我标榜。公元17世纪时,新疆的和卓为争夺宗教统治权而分为白山派与黑山派。白山派阿帕克和卓失利后出逃,向西藏佛教首领达赖喇嘛求援。达赖喇嘛利用对当时天山北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影响,写信要他帮助阿帕克和卓重建政权。噶尔丹趁机发兵12万人,于1678年攻入喀什噶尔。阿帕克和卓执政后,大力发展白山派,屠杀监禁黑山派,为向主子噶尔丹交纳每年10万两白银的贡金,推行繁重赋税,横征暴敛,并为自己修建豪华陵墓(即今现存的阿帕克和卓麻札,误传为香妃墓)。阿帕克和卓后被以黑山派为主的暴动群众杀死。白山派内部又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血混战,长子与次子相继被杀,三子玛罕木特被信徒拥立为喀什噶尔的统治者。为了战胜白山派,黑山派请求准噶尔部援助。于是准噶尔再次发兵南疆,于1713年占领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诸城。将两派首领即白山派的玛罕木特和卓与黑山派的达涅尔和卓都带往伊犁。后来感到直接治理南疆比较困难,于1720年又将达涅尔和卓放回南疆,委任他为南疆六城执政,仍年纳贡金。达涅尔和卓死后,又命其子分别掌管各城,玛罕木特在羁押中死去,其子大小和卓仍拘禁伊犁。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出师伊犁,平定准噶尔部之后,决定利用大小和卓在南疆的影响,实行对南疆的和平统一。遂将大和卓波罗尼都放归南疆,令其招服回众。而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小和卓霍集占看到其兄波蜀尼都在清军的支持下获得成功,更诱发了他的权力欲,遂潜回南疆,一面以宗教为号召煽动信徒反对清朝,一面劝说其兄自立,发动分裂叛乱,史称“大小和卓之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清军攻占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败逃巴达克山,清军进剿,巴达克山首领苏勒坦沙擒杀大小和卓,将其尸首献交清军。和卓家庭从穆罕默德第一世算起,至大小和卓恰是第三十世。林则徐在诗中夹注“至玛哈墨特止”,是不准确的。中华,历史上以指中原王朝,诗中指清王朝。款塞,叩向关塞之门,一般指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王朝通好纳贡或归附。在清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前,维吾尔族各部曾多次向清中央政府纳贡通好,由于准噶尔部落割据天山以北、占领南疆,使这种联系一度中断。拓地即开拓疆土。《云左山房诗钞》本做“辟地”。轮台,公元前60年(汉神爵二年),西汉王朝曾在乌垒城(今轮台县东策大雅)设西域都护府,正式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于惠远城(今霍城县惠远乡),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此诗意为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曾向大清朝纳贡通好。和卓家族从穆罕默德第一世算起,到大小和卓第三十世为止,便丧失了对维吾尔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统治权。大清在新疆设置机构,统辖管理。
“归化于今九十秋,怜他伦纪未全修。如何贵到阿奇木,犹有同宗阿葛抽(阿奇木之妻也)”(之六)。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清朝平定了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之乱,继汉、唐、元之后,重新统一了新疆。到林则徐作此诗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经历了八十多年的统治。九十秋即九十年,为大略年数。伦纪即人伦纲纪。《云左山房诗钞》本做“人纪”。阿奇木,维吾尔语音译,即阿奇木伯克。伯克为新疆特有的维吾尔族官名,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清朝用伯克制度管理维吾尔族地区。阿葛抽,维语音译,原意指大婶大嫂,也指夫人,今多写作“阿格恰”。诗中即对阿奇木伯克妻子的通称。之六意为:新疆归于大清统治快九十年了,但他们的人伦纲纪还没有完全讲究,为什么尊贵到阿奇木伯克这样的人,还有出自同一宗族的妻子?
“百家玉子十家温,巴什何能比阿浑。为问千家明伯克,滋生可有毕图门(毕图门,回语一万也。近闻伯克派差,每一明定以万口)”(之二)。玉子今多写作“玉孜”成“于孜”,维吾尔语数词“百”。玉子伯克为百户长。“温”为维语数词“十”。“巴什”为维语“头领”之意。阿浑今多写作“阿訇”,为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苗普生先生评说:“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以后,其后裔流亡浩罕,阿浑便成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的集中代表,并拥有神圣的权力。阿浑日益成为一种能左右社会的力量。所以,阿浑的社会地位愈高,愈表明宗教势力的强大,而利用宗教危及清朝在新疆统治的可能性愈大,这是清朝实行政权分离政策的根本原因。”(注:苗普生:《伯克制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明”为维语数词“千”,明伯克为千户长。毕图门为维语数词“一万”。之二意为:维吾尔人十户称为“温”,百户设一名玉子伯克,但这些头领都不能与阿浑相比。听说近来规定千户长所辖为万人,不知每位明伯克属下是否达到这个人数?
“众回摩顶似缁流,四品头衔发许留。怪底向人夸栉沐,燕齐回子替梳头”(之八)。摩顶为佛教受戒时,摩受戒者的顶。缁流即指僧徒。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提督杨芳、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奏议四品以上伯克方准蓄留发辫,其四品以下均不准妄自蓄留,获得清廷批准。(注:《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页。)栉沐即梳头洗面。“燕齐”,各级伯克被授予三至七品的官秩外,清朝还要拨给他们一定数量的耕地和种地人,称为“燕齐”。之八意为:南疆的维吾尔男子都是剃光了头,看上去就像僧徒一样。可是四品以上伯克的头发却是保留着,向人夸耀着每天都由“燕齐”为他梳头。
“关内惟闻说教门,如今回部历輶轩。八城外有回城处,哈密伊犁吐鲁番”(之三十)。关内,与关外相对而言。因新疆地处嘉峪关外而称呼。教门,指伊斯兰教。輶轩为轻车。古代帝王的使臣多乘輶车,后因称使臣为輶轩使。林则徐奉旨南疆勘地,借以自称。八城,即林则徐履勘南疆所历经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这八城。之三十意为:我在关内只听到新疆盛行伊斯兰教,可以前从未身临其境。如今受皇上之命乘车周历南疆八城。之外,维吾尔人聚居的回城,还有哈密、伊犁、吐鲁番。
二、反映南疆农作、节气
“爱曼都祈岁事丰,终年不雨却宜风。乱吹戈壁龙沙起,桃杏花开分外红”(之三)。爱曼,维语音译,官员之意。《云左山房诗钞》本做“欲祝阿林岁事丰”。阿林,维语音译,今多写作“阿里木”,指知识渊博有学问的人,能预测年景丰歉。龙沙,古时泛指塞外沙漠之地,诗中指风卷黄沙飞旋之状。之三意为:南疆的官员们都祈祷今年能有好收成。虽说南疆一年到头不下雨,但风却是很多。吹得戈壁上黄沙飞卷,吹开了桃花杏花,分外鲜红。
“不解耘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之四)。这首诗说,南疆的农作不用锄草松土,也不用施粪肥田,种子一经撒在地里,收成好坏就由天安排了。好在南疆地旷人稀,土地可以轮换耕种,种上一年,歇土两年。
“柳树流泉似建瓴,众来排日讽番经。便如札答祈风雨,奇术惟推两事灵”(之二十六)。瓴是房屋上仰盖的瓦,也叫沟。建瓴指由高处向下引水。“众来排日”为众人连日。《云左山房诗钞》本做“求泉排日”。番经,即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札答,古时书写用的小木简,指迷信人驱邪求福的符箓。奇术,《云左山房诗钞》本做“齐术”。惟推,询问和推算。这首诗意为,南疆雨稀少,又多沙碛地,农田亦用柳木槽引水灌溉,还要连日诵念《古兰经》,就像关内用符箓祈求风雨一样,好像这种卜问推算之法很灵验似的。
三、反映维吾尔族历法、宗教
“太阳年与太阴年,算术斋期自古传。今尽昏昏忘岁月,弟兄生日问谁先”(之七)。伊斯兰教历又称回历,有太阳历与太阴历之分。太阳历主要供农事方面使用,太阴历主要供日常生活、宗教活动和历史纪年使用。根据日历推算斋期自古有之。由于回历比公历每年少10~15日,月份在一年四季中不固定,以致人们对年月模糊,有的兄弟之间谁先过生日也不清楚。
“亢牛娄鬼四星期,城市喧阗八栅时(八栅尔即北方之集,南方谓墟,盖指散而言)。五十二番成一岁,是何月日不曾知”(之十二)。亢牛娄鬼,为四个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指星移斗转。八栅,维吾尔语音译,今多写作“巴扎”,集市、市场之意。五十二番成一岁,据清人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记载,清代南疆维吾尔族奉行回历,“以八栅尔计算,每七日八栅尔一次,每八栅尔五十二次为一年。”林则徐南疆勘地的《乙巳日记》三月二十四日记载:“凡回子有贸易处,皆谓之巴咱尔,亦作八栅。其七日一期者,如关内之墟集。”本诗自注为《云左山房诗钞》本所无。是何月日不曾知,指回历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年,不置闰月,因此春夏秋冬的月份在回历上不能固定,宗教活动和年节日在一年四季轮流出现。之十二意为:大约是天上星移斗转过了四个星期,就是南疆各地喧闹熙攘赶“八栅”的日子。七日为小八栅,四星期为大八栅,五十二个星期就是一年。因以“八栅”计算时日,所以人们对月日大多不清楚,而年节的月日也从来不固定。
“把斋须待见星餐,经卷同翻普鲁干。新月如钩才入则,爱伊谛会万人欢”(之十)。把斋,回历规定9月为斋月。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必须白天不食不饮,晚上日落见星,才能吃饭,俗称斋戒、封斋,也叫把斋。戒期满后,10月1日改为正常生活,举行庆祝活动,称为开斋节。普鲁干,即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传教过程中,以安拉“启示”的名义陆续颁布的言论汇集,共30卷,114章,6200余节,内容大致分为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伊斯兰教和有关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制度、伦理规范,穆罕默德及其传教活动的记述及根据传教需要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传说、寓言和神话等。除此还有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叫做“圣训”,对《古兰经》起着注释和补充的作用,二者共为伊斯兰教立法的主要依据。规定了教徒五项必行的宗教功课,即念(念经)、礼(礼拜)、斋(斋戒)、课(天课)、朝(朝觐)。而做礼拜时,就要阅读、背诵《古兰经》或“圣训”。入则,维语音译,意为斋戒,今写作“肉孜”。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又将开斋称为肉孜节。爱伊谛,维语音译,传统节日之意。指把斋戒期满后回历10月1日的“肉孜节”或此后12月10日的“古尔邦节”。古尔邦节源于阿拉伯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相传穆罕默德之前一位名叫易卜拉欣的“先知”,梦见安拉要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以示忠诚。易卜拉欣翌日将儿子带往山谷,正当举刀欲杀时,安拉派天使送来一只羊,并对他说,安拉已知他的诚意,要他用这只羊代替儿子作牺牲。所以古尔邦节又被称为宰牲节。林则徐吟咏南疆斋月一过,天上新月如钩的时候,就是肉孜节了。接着就是古尔邦节。穆斯林们杀牛宰羊,欢度节日,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走亲访友,互相拜会,奏乐起舞,万民腾欢。
“作善人称倭布端,诵经邀福戒鸦瞒。若为黑玛娃儿事,不及供差有朵兰”(之二十九)。伊斯兰教劝人行善,作善事之人被人称赞。倭布端,维吾尔语意为“好”。鸦瞒,今多写作“雅满”,维语恶行之意。黑玛娃儿,维语赌棍之意。朵兰,今多写作“多浪”。多浪人是维吾尔族的一部分,能歌善舞,“多浪舞”久负盛名。主要聚居在塔里木河畔的阿克苏、巴楚、麦盖提、莎车一带。清统一新疆后,多在各台站当差,运送物资。此诗意为:伊斯兰教劝人多行善事,戒除恶行。若是当赌棍的话,那还不如在台站供差的多浪人。
四、反映维吾尔族文化艺术
“字名哈特势横斜,点画虽成尚可加。廿九字头都解识,便矜今雅号毛拉(官文作莫洛)”(之五)。哈特,即“字”的维语音译。毛拉,阿拉伯文maula的音译。原意为先生、主人,后成为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维吾尔文有二十九个字母,字体略有倾斜,自右至左横写,还要上下加点添划。能解读伊斯兰教经卷并有研究者,便可获得庄重而文雅的称号“毛拉”。
“城角高台广乐张,律谐夷则少宫商。苇笳八孔胡琴四,节拍都随击鼓镗”(之十三)。夷则,音乐律学中的名称。在音乐十二律吕相生表中列为第九。宫商,音乐调式名称。汉族的五声音阶中包括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苇笳,即觱篥,也作筚篥,维吾尔语今称“巴拉曼”。气鸣乐器,上开八孔(或九孔),管口插有芦制的哨子。汉时起源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后为隋唐宴乐及唐宋教坊音乐的重要乐器。觱篥从骨管、角管改为竹管,都是用芦苇做簧,又称“苇笳”。胡琴,是唐宋时对来自北方或西北各族拨弦乐器的统称,将四根弦的拉弦乐器呼为“四胡”。节拍指乐曲中周期性出现的节奏序列。击鼓镗,打鼓震敲之声。《诗经·邶风·击鼓》:“击鼓其镗”。指维吾尔民族乐器手鼓和纳格拉(铁鼓)的震响。每逢佳节或喜庆之日,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总是在城角楼台、屋顶高处摆开乐队,乐曲声欢快而远扬。旋律和谐于夷则律,与汉族的五声音阶大不一样。苇笳八个孔,胡琴四根弦,整个乐曲的节拍和舞蹈的旋律,都随着手鼓、纳格拉(铁鼓)的响声而进行。林则徐在《乙巳日记》中,就有二月十五日“入库车城之南门,回人于山楼上鸣金奏乐”的记载,可资证明。
五、反映维吾尔族建筑、医疗
“厦屋虽成片瓦无,两头榱角总平铺。天窗开处名通溜,穴洞偏工作壁橱”(之十四)。南疆的大小房屋很多都是夯土板筑或土坯砌成,平顶没有瓦,两头的椽子也总是平铺(“榱角”在《云左山房诗钞》中做“榱桷”)。这种建筑适合南疆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而墙壁较厚是为了冬暖夏凉。维语中把天窗叫做“通溜”,他们还偏爱在室内墙上挖洞作成壁橱。
“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周多被白杨遮。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围成满壁花”(之十五)。还有那白杨围遮的高楼(多为清真寺、官府、富豪之家),顶部就像哈萨克毡房、蒙古包一样,修成圆拱形的。墙上用石灰粉膏装饰涂抹(“石粉围成”在《云左山房诗钞》中做“石粉团成”),看上去就像开满了白花。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族建筑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清真寺、麻扎等宗教建筑上,其形制和风格多为尖顶拱形洞式门窗,穹窿形大圆屋顶,使其建筑成为新疆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
在乾隆朝统一新疆之前,准噶尔部落统治天山南北,曾在南疆纵兵骑马欺凌掠夺。维吾尔人为防备他们,都把门窗修得很小,以后竟形成了习惯。林则徐到来时依然如故,他记述说:“准夷当日恣侵渔,骑马人来直造庐。穷户仅开三尺窦,至今依旧小门闾”(之十六)。
维吾尔医有着悠久的传统。林则徐在南疆看到这样一种医疗现象:在一个通泉的小池里,儿童仰卧在水里,用冰冷的流水冲洗腹部。这不是玩耍嬉戏,而是维吾尔医治疗肚子疼的一种办法。他写道:“河鱼有疾问谁医?掘地通泉作小池。坦腹儿童教偃卧,脐中汩汩纳流澌”(之二十二)。河鱼有疾,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河鱼腹疾,奈何?”因鱼烂先从腹始,后以指腹疾。
六、反映维吾尔族衣食起居
“村落齐开百子塘,泉清树密好寻凉。奈他头上仍毡毳,一任淋漓汗似浆”(之十七)。“赤脚经冰本耐寒,四时偏不脱皮冠。更饶数丈缠头布,留得缠尸不盖棺”(之二十三)。南疆的村落里都有“涝坝”(蓄水池塘),供人们生活汲水及牛马饮用。池边的小树林,又是乘凉的好地方。林则徐《乙巳日记》中记载喀什噶尔有百子堂,树密泉清,乃回人乘凉处。维吾尔人既知寻凉避暑,可男子们在酷夏仍然戴着毡皮帽,任凭大汗流淌,也不脱下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就是“四时偏不脱皮冠”。“赤脚经冰”在《云左山房诗钞》本中做“赤脚经冬”。上了年纪的男人们还用白布缠在头上,维语中把缠头布称为“赛莱”。“缠尸不盖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葬礼特点。维吾尔族的葬礼特点是土葬和速葬。土葬即不用棺木,速葬即尸体存放至多不得超过三日。四项基本要求是洗、穿、站、埋。洗就是洗净尸体。洗后将尸体擦拭干净,裹“克凡”(阿拉伯语意为寿衣,尸衣),谓之穿。然后将尸体放在公用的“塔卜”(抬送死者的专用床,平时停放于清真寺),或抬往清真寺,或放在自家院内。站即“占乃孜”,为死者举行的殡礼。参加者由阿訇或死者亲属率领,集体为死者举行祈祷。上述三项完成后,即可下葬。遗体用“塔卜”抬往预先挖好坟坑的墓地。坟坑呈长方形直坑,南北向,距洞底30厘米左右掏有偏洞,长2米,宽高各1米。安葬时,两人先入坟底,当遗体放入坟内后,由他们对接送至偏洞内,头北脚南放好,在头下置一块枕。然后将头部一端的布结开,使死者面向西方(表示归向安拉)。洞口用石板或土块封闭,直坑用土填平,其上砌成伊斯兰式的坟头。“留得缠尸”在《云左山房诗钞》中做“留待缠尸”。林则徐说“留得缠尸”是对“数丈缠头布”的亲切戏谑之语,并非死后用缠头布裹身的。
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禁食猪肉。他们吃牛羊肉,但必须是经过宰杀的活畜,而不吃自死的牲畜。忌吃猪肉是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一个重要特性。这是由于伊斯兰教承袭阿拉伯半岛古代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的结果。穆斯林严守伊斯兰教关于禁食猪肉等食物的规定,久而久之,便形成民族的生活习惯。维吾尔人爱用羊肉、大米加上蔬菜(主要是黄萝卜)或干果(如杏干、桃皮、核桃仁、葡萄干之类)做成抓饭,香味可口,是维吾尔人最好的饭食之一。只是和入羊油,味道有些膻。林则徐写道:“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之十八)。
南疆盛产胡杨,放入维吾尔人称为“务恰克”的炉灶里,夏季可以作饭,冬季可用来取暖驱寒。旷野上用胡杨点起篝火,彻夜闪动着通红的火苗(《云左山房诗钞》本做“燎原野火入宵红”)。这就是:“树窝随处产胡桐,天与严寒作火烘。务恰克中烧不尽,燎原野火四围红”(之二十四)。
维吾尔人还把小葫芦凿孔做成水烟,叫“麒麟”,把卖水烟的叫做“麒麟契”(维语音译,“契里木萨得库其”的简称,今多写作“契里木契”)。一个水烟可供数人吸用。林则徐自注:“淡巴菰俗名烟袋,回人之烟桶头甚大,似壶芦样,名气琳”(《云左山房诗钞》本无此自注),并吟道:“小样葫芦凿窍匀,烧烟通水号麒麟。娇童合唤麒麟契,吹吸能供客数人”(之二十五)。
南疆路程遥远,还有沙漠荒滩阻拦。炎热的季节里上路,想找个歇脚的地方,可真是难!幸亏当地官员安设了旅舍客店,维语称为“亮噶”,汉族人念得不准,错说成“阑干”(今多写作“兰干”)。这就是:“荒程迢递阻沙滩,暑月征途欲息难。却赖回官安亮噶,华人错唤作阑干”(之二十七)。在今天新疆的地名中,叫“兰干”的很多。大到山名、乡名,小到村名、站名。据粗略统计,约有近百个之多。这些地名大都分布在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兰干”,维吾尔语即为驿站、腰店子之意,清代史籍中写作“阑干”。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新疆,虽自古是丝绸之路的必经要道,但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交通甚为不便。特别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干旱少雨,又有流沙阻隔。这样,为过往的商旅提供食宿运输之便的驿站便应时而建。清代的“兰干”,有的设置在交通台站之间,有的则设在其它商道上。当时的“兰干”,现在有的仍作为交通站名保留下来,如且末至民丰间的安迪尔兰干。有的演变为山、水库、农场、水文站的名称,如喀什的兰干喀格山、兰干水库,和田的兰干农场,库车的兰干水文站。而大多数成为如今乡、村的名称。(注:董琳:《新疆地名中的“兰干”》,载《地名丛刊》1986年第6期。)
七、反映维吾尔族婚嫁丧葬
“宗亲多半结丝萝,数尺红丝发后拖。新帕盖头扶马上,巴郎今夕捉央哥(男名巴郎,女未适人名克丝,子妇名央哥)”(之二十)。宗亲,本指同母兄弟,也指同一祖先所出的男系血统。丝萝即兔丝和女萝,蔓生植物,纠结在一起,不易分开。《古诗十九首》: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后以比喻婚姻。巴郎是维吾尔语音译,指儿子或男孩。这里指新郎。未嫁人的姑娘称为克丝,今多写作“克孜”。《云左山房诗钞》本无此注。“发后拖”在《云左山房诗钞》本做“散发拖”。央哥,维吾尔语音译,指妇女。这里指新娘。维吾尔人多在宗亲之间通婚。新娘子披红挂彩顶盖头,由人扶在马上,在手鼓唢呐的伴奏下,被接到新郎家,婚礼后当夜入洞房。之二十一亦咏道:“才经花烛洞房宵,偏汲寒泉遍体浇。料是破瓜添内热,冷侵肌腑转魂消。”说明是翌日清晨,汲来清泉烧成热水,新婚夫妻净身,为了卫生健康。
“不从土偶折腰肢,长跪空中纳祃兹。何独叩头麻乍尔,长竿高挂马牛牦”(之十一)。土偶即泥胎塑像。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信仰安拉独一万能,穆罕默德为安拉的使者。在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清真寺里,绘有花纹图案,绝无偶像。伊斯兰教为穆斯林规定了一系列的功修。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一天必须做五次礼拜,祈求真主赦罪赐福。拂晓做晨礼,正午做晌礼,黄昏做晡礼,天黑做昏礼,夜间做宵礼。每星期五集中到清真寺做礼拜,称为聚礼,阿拉伯语称“主玛”。礼拜时面向西方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有一座“克尔白”,阿拉伯语意为“立方体的房子”。原为阿拉伯多神教徒敬神献祭的中心。穆罕默德占领麦加后,将其改建为清真寺,并规定了朝拜克尔白的制度。从此,克尔白就成为全世界穆斯林朝拜的中心),立站、赞颂、鞠躬、叩头、跪坐。双膝着地,上身挺直,诵经祷告做礼拜,这就是纳祃兹,波斯语Namaz的音译,礼拜祷告之意,今多写作“乃玛孜”。诗中“跪”字在《云左山房诗钞》本做“跽”。麻乍尔,阿拉伯语音译,今多写作“麻扎”。意为“圣地”、“圣徒墓”。我国回族根据其建筑形式称为“拱北”,阿拉伯语意为圆屋顶建筑。维吾尔族采用“麻扎”这一词汇,用于泛指一切坟茔陵墓。维吾尔人在麻扎跪地祈祷、超度亡灵的风俗,至今尚有保留。在新疆大多数麻扎周围,多插有树枝或三角小旗,并在树枝、旗杆和周围的灌木中挂上马、牛、羊尾,羊头、羊皮、羊角或绑碎布条等作为标志,类似汉族招魂之灵幡。林则徐的《乙巳日记》中记载他在和阗的见闻:“或言此地回子乃汉人种,汉时(西域都护)任尚弃其众于此;唐代置于阗都督府,亦驻汉兵。回人谓汉人为黑台,其音转讹,乃呼为和阗。回人丧事无挂纸钱者,独此地有之,盖汉人遗俗也。”(注:林则徐《乙巳日记》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卷,第558页。)此说是否有历史依据,有待考证,不过可以看出,南疆的这种风俗,保留了某些古老的萨满教的遗风。
“海兰达尔发双垂,歌舞争趋努鲁斯。漫说灵魂解超度,亡人屋上恣游嬉”(之二十八)。“海兰达尔”为波斯语音译,对伊斯兰教苏菲派苦修者的一种称谓,他们身穿特殊服装,披头散发,巡游各地,狂放不羁,其中大多数人是文盲和职业行乞者,多以念经、求雨、治病、禳灾、祈福等活动为主。“努鲁斯”,维语“春节”之意,今多写作“诺鲁孜”。节日时间在太阳历每年的3月21日。此诗意为:还有苦修者在努鲁斯节为人们唱歌跳舞祈求丰年。他们还为亡者超度,说亡者在屋顶上欢乐。
八、反映维吾尔人民生活艰辛
以上,林则徐写了维吾尔族在清代的历史、制度,写了南疆的农作节气、历法宗教、文化艺术、建筑医疗以及维吾尔人的衣食起居、婚嫁丧葬。他更写了南疆生产落后荒凉之状和人民生活艰辛之情,如:“桑椹才肥杏又黄,甜瓜沙枣亦糇粮。村村绝少炊烟起,冷饼盈怀唤作馕”(回语馍名馕也)(之十九)。初夏时节,桑椹才肥,杏子又黄。夏秋的甜瓜、沙枣,都是穷苦的维吾尔人家的干粮。沿途所见南疆村落,只有极少的炊烟,人们把叫做“馕”的冷饼揣在怀中,充饥度日。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南疆维吾尔人民艰苦的生活状况。林则徐在进关之后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臣与全庆奉命周历各城,查勘地亩,复经布彦泰随时函嘱密查各处回情,臣与全庆有所见闻,即俱不敢缄默。查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蓝缕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访闻此等穷回,尚被该管伯克追比应差各项普尔钱文。”(注:林则徐《商议新疆南路八城回民生计片》,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卷,第511页。)
奏折所反映的情况,如上引诗十九所写的一样。而“衣服蓝缕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的情形,又如诗二十三所说:“赤脚经冰本耐寒”。但并非情愿。林则徐认为这是南疆当地官员(伯克)向百姓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而造成的。他希望朝廷能严加约束地方官吏,不许无故盘剥百姓。
他还有一首诗反映南疆维吾尔人为避战乱灾害地窖储粮的习俗和高利贷的情况:“金谷都从地窖埋,空囊枵腹不轻开。阿南普作巴郎普,积久难寻避债台(借债者,本钱谓之阿南普,利钱谓之巴郎普)”(之九)。前两句是说当年为防备准噶尔骑兵抢劫,南疆维吾尔人家都把粮食埋藏于地窖中,囊空如洗,饥肠轱辘,也不轻易打开。维吾尔人窖藏粮食之俗,古亦有之。元时马可波罗就记载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维吾尔人“只要一听说大兵临境,不问什么人的军队,他们立即拖男带女,赶着牲口,奔走两天的路程,逃到沙漠深处,到某些有淡水的地方去躲避兵祸,以免生命财产遭殃。同时为了不受乱兵的抢掠,又把自己收获的粮食收藏在沙漠的地窖里,每月只取出刚够吃用的数量,除他们自己人以外,决不让别人知道藏粮食的地点。”(注:《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46页。)又据《清史稿·兆惠传》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叶尔羌黑水营之战中,清军虽陷入重围,但“掘井恒得泉,发地得藏粟”,坚持获胜。林诗后两句写高利贷盘剥。阿南,维语音译,指母亲;巴郎,维语音译,指儿子。清代南疆实行红铜所铸普尔钱。阿南普指母钱,即本钱。《云左山房诗钞》中自注本钱为“母钱”,巴郎普为“普子钱”,这里自注为利钱。高利贷严重到利钱相当于本钱,本利倍增,日积月累,越欠越多,借贷者真是难以还清债务。
林则徐在南疆勘地期间,虽然体弱多病,公务繁忙,但他还是深入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认真考察现状,尊重维吾尔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虚心学习维吾尔语言,思想感情溶入维吾尔人民朴质的爱怨之中,为维吾尔人民大办好事,受到维吾尔人民的热烈欢迎。流放新疆,使他有了接近体察下层民众的机会,热情淳朴而贫穷的维吾尔人民,与内地迥然不同的习俗风情,戈壁绿洲的边塞风光,无一不令他耳目一新,深深吸引、打动着他,为他的诗歌带来新鲜的气息,也使他写下《南疆竹枝词三十首》,成功地反映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风俗和思想感情。诗中使用了大量维语,平淡而又诙谐,写实又富有诗意,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流畅顺口,使整部词充满浓厚的维吾尔族的生活气息,不仅具有民歌特色,而且具有民族特色,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幅反映清代维吾尔人民生活的风俗图画。
标签:林则徐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竹枝词论文; 维吾尔族舞蹈论文; 清朝论文; 维吾尔族节日论文; 古兰经论文; 穆罕默德论文; 伊斯兰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