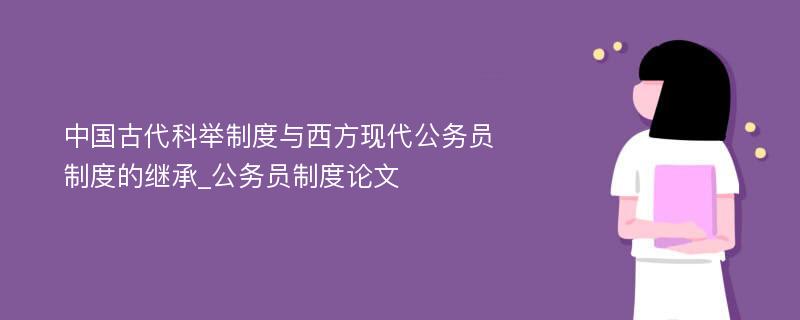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西方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近现代论文,公务员制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6201(1999)02-0049-05
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对许多人来说显然并不十分陌生。因为科举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留下的痕迹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也还是清晰而浓重,而公务员制度在当代西方社会发挥的作用正在变得日益巨大而深远。不过,许多人对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一些文章与著作虽偶尔提及,但并未进行详细的叙述与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加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西方学术界大量的关于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论述。这些论述使我们不可能不对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1933年,罗纳德S.苏曾经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我们认为,中华帝国科举制度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制度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的影响,而英国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注:Leonard S.Hsu, 《孙逸仙——他的政治和社会理想》University Park,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ernCalifornia Press,1933.)
上述引文告诉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的渊源。罗纳德S.苏大概是西方学界最早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不过,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并不是罗纳德S.苏,而是孙中山先生。1921年,在一份演讲报告中,孙中山先生就已经说过:“只有选举而没有考试,……所以美国的选举常常就闹出笑话。有了考试,那么必要有才、有德的人,终能当我们的公仆。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亦都是学英国的。”(注:“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98页。)孙中山先生的话绝非毫无根据。不过, 这些话过于笼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考试制度,但是,这并不能真正证明科举制度就是当代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蓝本。我们还需要直接的根据来证明当西方人建立公务员制度时,确实采用或者参照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据唐纳德F.莱茨的研究,自从1585葡萄牙人建立澳门殖民地以后,外国人论述中国科举制度的文件便得到妥善的保存并为西方国家的人士所广泛阅读(注:Donald F.Lach , 《亚洲对欧洲的影响》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vol.I,bk.2,ch.9,esp.pp.804~812.)。1943年,邓嗣禹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西方考官制度的影响的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他查阅了70多种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专著和论文,它们大多是发表在1570年和1870年之间的英语版本。依据大量的事实,邓嗣禹得出结论说:“无庸置疑,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西欧国家,……为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它们自己的特点。”(注:Ssu-yu Teng, 《中国对西方官员考试制度的影响》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943):pp.267~312.)与此同时,Y.Z.常则对西方国家借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的根据是:“有证据表明:第一,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广为人知;第二,有关那个时代竞争考试理论的期刊文章和议会辩论均与中国的这一制度相关;第三,议会内外一致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创立的一种制度,而且不容否认;第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先于中国而使用一种竞争性的官员考试制度。”(注:Y.Z.Chang, 《中国与英国公务员制度改革》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2 April 1942,p.544.)
唐纳德S.苏、邓嗣禹和Y.Z.常等人的研究使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西方国家借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的事实。不过,仅仅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加以发掘。事实上,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来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的。1600年,东印度公司获许建立,并且从1623年在印度又从1699年在中国开始活跃起来。邓嗣禹认为:1829年,公司在有限的基础上为印度引进了官员考试制度,“结果使中国的这一发明及时在印度得以充分发展”。此后,这一制度又应用于英国国内公共服务并建立了它的精英“通才管理阶层”(注:Ssu-yu Teng, 《中国对西方官员考试制度的影响》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943):p.295.)。随着形势的发展, 公务员制度在印度和英国逐步普及。19世纪印度殖民地政府最重要官员是地区官员,菲利浦·伍德罗弗称这些官员为“柏拉图式的卫道士”(注:Philip Woodruff, 《统治印度的人们》New York:Shocken Books,1953,vol.2.)。约翰A ·阿姆斯特朗写道:“他们的责任感以及良好的通才训练,使人想起描绘中国官员时用的‘多面手’一词,这样的例子在英国教育系统和英国国内公务员系统中不胜枚举。”(注:John A.Armstrong,《欧洲的行政精英》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271~272.)理查德A·查普曼因此断言:“确实, 公务员一词起源于东印度公司。它的官员被称之为公务员是为了区别于军事的和教会的雇员。”(注:Richard A.Chapman, 《英国高级公务员》 London:Constable&Company,1970,pp.8~9.)最积极倡导采纳中国官员考试制度的是英国驻中国广东领事托马斯·泰勒·麦道斯,他在1847年的著作中警告说:“如果英国对英王所辖之下的殖民者职位和头衔不实行公正的晋升制度,那它将不可避免地失去所拥有的全部殖民地。 ”(注: Thomas
T.Meadows , 《中国人和他们的反叛》 Stanford, Calif: AcademicPrints,1856,xxvii.)
在印度,尽管许多地方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曾经进入过1806年在海雷伯利创办的公司学院,但是,直到1829年,公司才引进公务员考试制度。然而,这种做法只是针对那些没有进入过海雷伯利学院的官员而言。当时,在英国容许进入公务员行列还纯粹是一种恩赐官职制,亚当·斯密和杰里米·本瑟姆都主张进行公开的考试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853年,查尔斯·屈维廉爵士和斯坦福德·诺斯科特爵士发表了著名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这个报告奠定了英国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基础,屈维廉与诺斯科特的祖父一样曾经进入过海雷伯利学院并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而麦考莱爵士则是屈维廉的姐夫。他们二人因为主张在印度实行有效的竞争考试制度而闻名于世。1854年的《麦考莱报告》主张对东印度公司的公务员实行考试,考试“限于那些有知识的部门,这些部门是英国绅士们所向往——可能吸引注意的——如历史、法学、金融和商业以及语言等等。而被考虑在列的则应该是那些毕业于牛津或者剑桥文科的高才生”(注:参见:《麦考莱报告》November1854,reprinted in the so called:《1968 年富尔顿委员会报告》: Her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1970,vol.I,pp.B,pp.119~120,pp.124~125.)。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两个报告放在一起来考虑,因为它们奠定了英国管理阶层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高级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模式。
海雷伯利学院关闭以后,招募和考试主要集中于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以满足其在印度求职的需求,与此相适应,《麦考莱报告》也及时得到了补充。1857~1858年以后,由于“英王法”取代了“公司法”,“牛津—剑桥”的应募者首先在印度然后在英国国内占据了英国见习公务员的统治地位。1870年6月4日,《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内容为枢密院的法令所补充,法令将公开的竞争考试作为进入枢密院供职的正式要求,并且强令所有的部门举行任职考试(注:Richard Chapman, 《英国高级公务员》;E.N.Gladden:《联合王国的公务员,1855~1970》London:Frank Gass & Co.,1976.)。至此, 公务员制度在全英国境内推广开来并开始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国家。
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法国的影响,在邓嗣禹的著作中也有述及。邓嗣禹转引伏尔泰和其他人的论述说:“如果有那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的生活,荣誉以及福利一直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就是中华帝国。”伏尔泰曾经说:“人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邓嗣禹依据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布鲁奈特利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总结道:“法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来源于中国。”例如,布鲁奈特利相信,“法国的教育确实建立在中国公开竞争考试的基础之上,而且通过竞争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无疑来源于并且效仿了中国”。在法国,这种制度受到了哲学家的普遍欢迎,特别是伏尔泰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注:Ssu-yu Teng, 《中国对西方官员考试制度的影响》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 (1943):pp.281~283.)。
就西欧大陆来说,法国的公务员制度和德国不尽相同。费罗·海蒂将其称之为“传统管理体制”,是因为它们与马克斯·韦伯的传统官僚理论非常相似。现代法国高级公务员制度中突出的特征是它的选官制度化。这种选官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依据等级、功绩以及现存的各类高级学院特别是国立行政学院为标志的培训得以实现。这一制度创立于1945年,它通过保证国家机器的连续运作来实现政治的稳定。“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象法国这样建立一系列制度旨在创立一个高级公务员精英集团”,并且依据这些制度形成“一个完整的公务员世界”(注:Ezra N.Suleiman,《从右到左:法国的官僚与政治》in Ezra N.Suleiman,ed.:《官僚与政策制定:比较概览》New York:Holmes &Meier,1984 p.117.)。 不过,尽管法国公务员制度有这样的特点,我们还是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法国公务员制度的渊源。而后者所形成的特点恰恰反映了前者的深远影响。
对美国来说,其公务员制度几乎吸收了各个国家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发生的时间较晚而已。范·里普尔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1860 年以前的外国公务员制度曾经影响美国”(注:Paul P.Van Riper,《美国公务员制度史》Evanston,IL:Row,Petersnand CO.,1958,p.63.)。直到1862年,美国驻法国的领事约翰·比格罗建议美国借鉴法国的方法考取税务员,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才开始其建立与发展的历程。约翰·比格罗的建议被重新登录在1868年国会关于中国、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公务员制度的报告中(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联席选拔委员会报告节选:《美国的公务员制度》40thCongress 2d Section,H Rep.47,May 15,1868 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8,pp.110~202.)。根据1871年的一个法案,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任命一个七人委员会以发起改革,这就为后来1883年彭德尔顿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个短期存在(1871~1875)的格兰特委员会提交给总统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经验给予了特殊的注意,其中谈到:“孔夫子倡导政治道德,中国人曾阅读过许多书,并使用过罗盘针、火药以及乘法表,而那时我们这个大陆还是一个未开垦之地。”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东方世界最开明和最持久的政府曾要求进行一种考试以考察进入政府工作的候选人的功绩”,美国人不应该否认这一益处。报告还补充道,应该“特殊考察英国的政治历史,因为它曾大大地受益于这些中国的方法”(注:美国国会众议院,U.S.Congress,House,《公务员委员会提交总统的报告》43rd Congress,lst Sessin, Exec.Doc.221,April 15,1874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74,p.24.)。
尽管邓嗣禹发现有“零散的资料可以论证中国人对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有直接的影响”(注:Ssu-yu Teng, 《中国对西方官员考试制度的影响》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943):pp.306~308.),但是,在美国,特别是1870年以后,对外国经验的许多参考与借鉴,主要来源于英国。其中包括《麦考莱报告》、《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以及英国的某些经验。在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中,采纳英国的经验的中心部分是竞争考试,这一法案首创了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其余被采纳的英国经验则是有关职业的相对稳定与政治的中立。
实际上,美国联邦职业行政制度与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通才或精英传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弗莱德里克·毛舍把主要的欧洲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划分为三种类型:英国类型,它的牛津—剑桥和公共学校的信徒以及它的职业—业余行政管理阶层;大陆类型(法国除外),它的律师统治地位;以及法国类型,它的职业精英集团的传统(注:Frederick C.Mosher, 《民主制度与公共服务》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2,pp.29~41.)。通过殖民主义,上述每一类型都被传播到了国外。目前,它们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占据支配地位。与此不同,美国的制度有别于这三种类型的任何一种,而且这种区别远远大于这三种类型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正如切斯特A.阿瑟总统所说的那样:“英国制度的一些明显的内容并没有被我们所积极接受,即使在最积极倡导公务员改革的那部分中也是如此。”(注:Paul P.Van Riper,《美国公务员制度史》Evanston,IL:Row,Petersn and CO.,1958,p.100.)没有被采纳的内容之一即包括文章写作的考试;相反,彭德尔顿法明确地指出考试必须带有“实践的特点”。另外一个被美国拒绝接受的英国制度的内容是体制的封闭——除了底层以外,而从一开始,美国的制度就在几乎所有的层次上都是开放的。
对上述两个内容的拒绝接受对美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带有根本性的体制方面的影响,因为注重“实践”的考试制度保证了专才而不是通才的主流地位,同时,“公开性”注定了这种具有渗透性的公务员制度缺少一种独立的行政管理精英集团:它更多地是开放的官僚而不是对外封闭的体制。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同时也看到了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间的差别。
尽管英国以及西欧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越来越更多地体现高等教育的扩大和专才的显要地位,但是,通常来说,通才以及随之而来的精英集团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专才与之相比,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美国的模式与此正好相反。因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及它的“道德人”的官员传统更多地与欧洲的模式相似而与美国的模式不同。当然,就大多数研究现代公务员制度其中包括美国的公务员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都认为西方人接受了中国人发明的竞争考试的概念,美国所建立的非通才的或非精英集团的模式,实质上也是间接从中国引入的。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亚洲国家尤其是朝鲜和日本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亚洲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情况较为复杂。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的入侵使其了解并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建立其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说,某些亚洲国家又因这种入侵受到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启发。尽管这些国家在古代时期就受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但是,它们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并不是直接从中国的科举制度转化而来的。因为公务员制度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尤其是两党或多党政治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科举制度只能是公务员制度的渊源,没有近代资本主义及其政党制度的催化,这一制度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公务员制度。就象发明了科举制度的中国并没有把这一制度直接改造成为现代公务员制度一样。
马克W.哈德斯顿和威廉W.博伊尔在1996年研究了各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及其渊源以后,得出结论说:第一,在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中,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华帝国的影响;第二,竞争考试以及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并且这种制度已由中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第三,中国的经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以及精英高级公务员制度;第四,这些制度的绝大部分都带有通才和非代表性官僚占统治地位的特征;第五,比较而言,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专才占统治地位的特点, 因而, 它通常更能广泛地代表社会(注: Mark W.Huddleson and William W.Boyer,《美国的高级公务员——寻求改革》Pittsburgh & Lond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6,pp.5~20.)。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些结论都是准确的。
以上我们理清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西方近现代公务员制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过,澄清科举制与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全部解决。我们首先注意到,科举制度在中国以及亚洲国家并没有直接转化为近现代的公务员制度。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当西方国家急于了解并效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近现代西方社会需要的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发明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人却正在迫不及待地铲除这一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对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却发现,这两项制度对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与两党或多党制的近现代西方国家几乎带来了同样的利弊:政治的稳定、行政的高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政治的泛滥还有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弊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上下接续。尽管古代中国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距甚远,但是,历史的共性并不因此失去其影响力。而研究这种历史的共性及其在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中的表现,恰恰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与全方位进行整体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科举制度显然是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交汇点。
收稿日期 1998—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