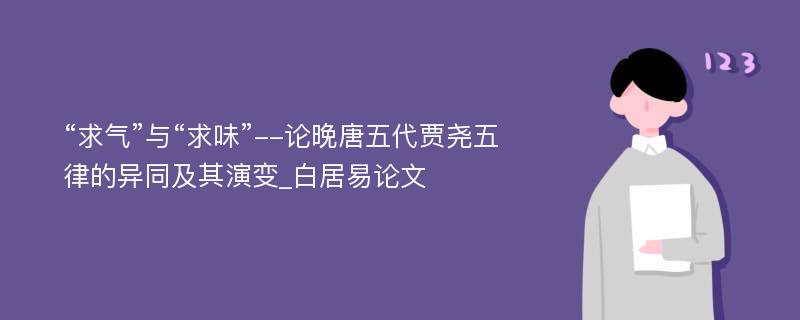
“求奇”与“求味”——论贾姚五律的异同及其在唐末五代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论贾姚五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两个以苦吟著称的诗人,贾岛和姚合的五律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后世的姚贾诗派又是如何接受他们的诗风,这些问题已经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张宏生先生的《姚贾诗派的界内流变和界外余响》(注:见《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一文,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但关于贾姚五律艺术的异同,张文的分析还留下一些待发之覆。
张文指出,贾岛与姚合的接近之处,在于苦吟态度和平淡自然的境界,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所达到的审美效果也有着一致性,即以刻苦推敲的手段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至于二人的不同,则表现为意象特色的不同,贾岛偏于使用“人们不大注意却有些希罕、幽僻乃至怪奇的意象”;而姚合则偏于使用一些常见的意象。
笔者认为,以平淡自然来概括姚贾五律美感效果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二人创作旨趣的差异。贾姚虽然都注重苦吟,但在艺术旨趣上,贾岛更追求奇特的表现效果,借此抒发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而姚合则用力于创造平淡含蓄的意味,表现普通人生的感受,有平淡自然之趣。简言之,贾岛五律偏于“求奇”,姚合五律偏于“求味”。至于二人语言、意象风格的不同则与艺术旨趣的差异直接有关。
贾姚二人在唐末开始被并称而逐渐成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唐末五代诗人,对贾姚的接受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取向。他们积极仿效二人的苦吟态度,但在艺术旨趣上则偏向姚合而远离贾岛,形成了以苦吟来创造含蓄意味的表现特色。从贾姚的个人创作,到姚贾诗派的流派创作,五律艺术发生了重要的流变。
一,“求奇”与“求味”:贾姚艺术旨趣的差异
贾姚二人都注重苦吟,贾岛自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姚合则是“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闻蝉寄贾岛》)。苦吟构成了贾姚五律最显著的创作特点。
但是,贾姚二人在艺术旨趣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古人对此已有所注意,宋人孙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指出,中唐以后,杜甫之诗分为六家,其中:“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后村诗话新集》卷1)。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指出二人“格调不同”, 所谓“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卷6)。古人所论是贾姚的风格差异, 而这种差异来自艺术旨趣的不同,具体说来,贾岛的五律注重宣泄内心的孤介奇僻之气,偏于“求奇”;而姚合五律则更多地流露沉潜和品味普通人生的闲适意趣,重在“求味”。二人性情不同,面目自然有异。
诗歌题材的选择,往往折射出诗人的趣味。艺术旨趣的差异,使贾姚二人对题材有了不同的偏好。贾岛集中多是羁旅怀人、萧寺孤馆之作,以萧瑟孤寒的境象寄寓一种孤介的气质。而姚合的五律多是风景流连、池台院落之作,其集中的《闲居遣怀》十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秋日闲居》二首、《闲居晚夏》、《闲居遣兴》、《春日闲居》、《早春闲居》、《游春》十二首、《题金州西园》九首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这些作品通过抒写官居生活的闲适之趣,传达了他生活的情味与沉潜的意趣。
当然,贾岛与姚合也有不少共同的题材,但表达的旨趣却各不相同。例如,二人都喜欢表现山林寺院中的隐居修道之士,但贾岛偏于表现超绝人世的孤高奇僻之气,而姚合则偏于刻画幽静绝尘的隐居之趣。如贾岛的《寄华山僧》:“遥知白石室,松柏隐朦胧。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五更钟隔岳,万尺水悬空。苔藓嵌岩所,依稀有径通。”全诗以奇险的句式造成峭拔之势,突出了华山僧孤高不群的气质。又如《宿山寺》:“众岫耸寒木,精庐向此分。疏星透林木,走月逆行云。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有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绝顶之上遗世独处的老僧,作为一个富含震撼力的意象传达出诗人迥脱风尘的志趣。又如《山中道士》:“发冷梳千下,休粮带病容。养雏成大鹤,种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寒泉尽日春。不得离隐处,那得世人逢。”诗中“养雏成鹤”、“种子成松”这两个意象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们刻画出山中道士遗世独立的坚韧与孤傲。这些奇在筋骨而不在肌肤的诗句,鲜明地反映出贾岛追求奇崛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反,姚合对隐逸方外的表现,则偏于飘逸幽静,例如《寄白石师》:“白石师何在,师禅白石中。无情云可比,不食鸟难同。屦下苍苔雪,龛前瀑布风。相寻未有计,只是礼虚空。”全诗着力刻画了白石师飘逸的行止,传达了隐居的幽静之趣,但于贾岛诗中的奇绝超拔之气则比较欠缺。
在不同艺术旨趣的影响下,贾姚二人的语言、意象风格,构思方式都显示出明显的差别。
贾岛经常采用感情色彩十分凄清的意象,如“寒泉”、“寒骨”、“破宅”、“寒鸿”、“孤鸿”等等。为了增强效果,贾岛还经常在同一诗中反复使用这样的意象,如“孤屿消寒沫,空城滴夜霖”(《送韦琼校书》);“独鹤耸寒骨,高杉韵细飔”(《秋夜仰怀钱孟二公琴客会》);“萤从枯树出,蛩入破阶藏”(《寄胡遇》)等等。姚诗的意象取材比较广泛,而且对意象的处理也采取比较自然的态度,一般不显示过分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意象风格的差异直接导源于贾姚艺术旨趣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美感效果。
除了选择奇僻的意象,贾岛还在寻找奇异的构思上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他很欣赏自己《送无可上人》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自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这两句诗一方面将人这个主体转化成“潭底影”、“树边身”这样的客体,以传达自伤自怜的情绪;一方面又将主语和谓语颠倒,以强调苦吟者的孤独和艰难,构思奇特,诗意深曲。贾岛的五律有时还表现出十分夸张的笔致,如“白石通宵煮,寒泉尽日春”(《山中道士》)。“煮白石”的构思出自道家炼丹之举,大历诗人韦应物在《寄全椒山中道士》中云:“日暮拾荆薪,归来煮白石”,构思巧妙而极富清雅高逸之趣。贾岛袭用其意而加以夸张,使飘逸变为僻涩,使韦诗淡远的意味丧失几尽。
贾岛在意象的安排上追求突兀的效果,如:“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哭柏岩和尚》)。这两句诗被后人讥为“烧杀活和尚”(《六一诗话》)。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贾岛事实上是在利用“焚身”的联想来造就一种突兀的表现效果。又如:“寒蔬修净食,夜浪动禅床”(《送天台僧》),贾岛抽去了夜浪与禅床之间的现实距离,在突兀的衔接里展示出榻上禅僧的孤清幽绝。这种突兀的意象安排似乎极大地吸引了贾岛的创造兴趣,以至类似的诗句在其集中相当常见,如“秋江洗一钵,寒日晒三衣”(《送去华法师》)、“行李经雷电,禅前漱岛泉”(《送丹师归闽中》);“鸟从井口出,人自洛阳过”(《原上秋居》)。
贾岛有时还将多重通感容纳在简短的诗句里,使诗意变得十分深微幽曲,如“磬通多叶罅,月离片云棱”(《夏夜》)。诗句将磬声的传扬比喻为流水,又通过赋予行云以质感而在“流云吐月”的传统意象里生发新的诗意。
贾岛的构思,意在“求奇”,因此在创造含蓄的回味上相对欠缺,古人对此已经多有批评。唐末著名的诗论家司空图就认为,贾岛的作品在创造“味外之旨”方面乏善可陈,所谓:“贾阆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寒涩方可致才”(《与王驾论诗书》)。
姚合五律的语言和构思,由于受到“求味”旨趣的影响,因此呈现出与贾岛十分不同的面貌。他很少使用奇僻的意象,而是善于以平淡的语言摹写景致,创造回味。如《送李起居赴池州》之颔联:“红旗高起焰,绿野静无尘”,通过比喻准确地捕捉了红旗在旷野之上迎风飘动的态势。又如《送裴中丞赴华州》之颈联:“径草多生药,庭花半落泉”,通过细节的捕捉刻画出华州公署的幽静。又如《武功县闲居》云:“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表现了山居萧索的景况;“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同前),刻画出为官僻野的萧条冷落。姚合对五律表现功能的开掘,前人早有注意,《唐才子传》卷6 云:“(姚合)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摹写也。”
姚合利用五律的语言特点创造出独特的表达,使诗意富于回味。五律诗句最重前两字和后三字的关系,姚合充分利用这种“二、三”结构,使每句所取的两个景物细节之间相互映衬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更加密切。如“隔屋闻泉细,和云见鹤微”(《寄马戴》),泉声因隔屋听去所以细微,鹤影因和云而见所以朦胧;用“二、三”结构安排因果关系,不仅突出了泉声微细、鹤影模糊的主观感受,而且也传达出一种幽寂闲淡的感情色彩。又如“夏尽滩声出,潮来日色微”(《送清净阇黎归浙西》),诗句的前二与后三,既有时间上的先后,也有因果关系,同时每句之中的两个动词也有词义上的映衬关系,如“尽”与“出”,“来”与“微”,这就使诗意富于起伏,突出了水落石出、潮升日淡的秋意,其中也渗透出分别时略带暗淡的心绪。又如“家山去城远,日月在船多”(《送顾非熊下第归越》),下句日月双关,既实指舟中目睹日月一次次昼出夜行,又虚指行旅生涯的漫长;将漂泊之动荡刻画入微。“鸟语境弥寂,客来机自沈”(《过昙花宝上人院》)则以词义的对立,表达复杂的因果关系;鸟语更见环境的寂静,客来机心自消,诗句突出了僧院的幽寂超逸。
贾姚的艺术旨趣虽然不同,但在实际创作中,彼此还是有许多影响。“求奇”的贾岛也有一些平淡有味的作品,而侧重“求味”的姚合也经常表现出对奇异语言方式的兴趣。贾岛集中有一些作品富于回味,语言也比较平易,如《忆江上吴处士》:“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诗中以节物之变,秋风萧瑟寓怀人之慨,很有“味外之旨”。贾岛还有一些“工于摹景”的诗句,虽然“推敲作诗”的传说不尽可靠,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幽居》)的确是摹景的佳句。又如《暮过山村》中“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准确地写出行旅的辛苦。虽然贾岛经常用一些僻涩的词汇来为摹景之句“锦上添花”,因而多少破坏了诗意的平淡含蓄,但他那些用语平淡之作仍然显示了与姚合的同工之妙。对贾岛的僻涩并不满意的宋代诗人,对他这些与姚合接近的诗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梅尧臣提出“意新语工”的创作追求时,贾姚“工于摹景”之句受到了同等的重视,《六一诗话》载:“贾岛‘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凉,官况萧索。……‘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另一方面,姚合有时也运用一些比较奇僻的语言方式,如《闲居晚夏》:“片霞侵落日,繁叶咽鸣蝉”,诗中动词的使用就相当奇异,又如“红旗烧密雪,白马踏长风”(《送郑尚书赴兴元》),“烧”字的使用就比较深曲。类似贾岛那种意象之间突兀的安排在姚合诗中也时有出现,如“夜猿啼户外,瀑水落厨中”(《送裴宰君》)。在刻画荒僻之景时,姚合也不时象贾岛一样大量地使用孤清的意象,如“蚁行经古藓,鹤毛落深松”(《过无可上人院》)、“斜阳通暗隙,残雪落疏篱”(《过城南僧院》)、“寒蝉近衰柳,古木似高人”(《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
尽管存在着这些创作上的近似,但贾姚五律的差别并未因此而变得模糊,正象平淡有味的作品在贾岛的五律中比较罕见一样,姚合对贾岛奇异的语言方式的吸收也是十分有限的。当我们考察贾姚对后世五律的影响时,他们二人在创作路数上的差异尤其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二,寒士精神与闲适趣味:贾姚五律差异的成因
贾姚五律的艺术旨趣何以有“求奇”与“求味”的不同,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精神志趣以及所接受的艺术影响,都有密切的关系。
贾姚虽然是交谊很深的诗友,但彼此的人生轨迹却差异很大。贾岛志向远大但遭遇坎坷,他一生未曾及第,直到晚年才摆脱寒士的身份,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小官。相反,姚合并没有多少高远的志向,而及第仕进之路又相对平坦。一个是怀才不遇的寒士,一个是仕途平稳而又胸无大志的文官,贾姚的心画心声自然不尽相同。贾岛壮志难酬,内心积郁着不平之气,他五律“求奇”的品格就主要显示了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而姚合则更多地流露出品味普通人生,恬淡自适的意趣,这种在当时文官阶层中普遍流行的闲适趣味,奠定了他五律“求味”旨趣的精神基础。
贾岛怀有十分积极的人生思想,渴望在政治上建立功业。在《剑客》这首诗中,他奇崛的志向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为不平事。”然而现实并不青睐这个胸怀大志的诗人。科场的坎坷,使他内心充满愤激的情绪,个性日趋狷介。《鉴戒录》记载他早年初入科场之后:“自是往往独语,傍若无人,或闹市高吟,或长衢傲啸”(卷8)。他曾写下《病蝉》一诗, 抒发科场屈抑之痛:“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吟酸尚极清。露华疑在腹,尘点误侵晴。黄雀并乌鸟,俱怀害尔情。”据《鉴戒录》记载,被这首诗触怒的公卿显贵,“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卷8)。贾岛被逐在长庆二年, 《病蝉》一诗是否是贬逐的导火索,有关的记载未可尽信,但这次处罚,是中晚唐科场对寒素士子最严厉的一次打击。唐末昭宗光化年间,韦庄上书请求特赐贾岛、平曾等人及第,以平息科场的屈抑之叹(《全唐文》卷889)。 足见贾岛等人的不幸,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同情。然而身后的关怀毕竟来得太迟,贾岛身前饱尝了世路艰辛。据李嘉言先生的《贾岛年谱》考证(注:见《长江集新校·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在科场贬逐前后,贾岛一生有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长安,寻找仕进之路。长安固然有许多的朋友,有干谒的机会,但对于一个未沾一第的孤寒士子来讲,更多的则是“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困顿。旅食京华,因人成事,在孤独与困顿中寻找希望,然而希望又一次次破灭,贾岛悲剧的一生,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唐寒素士子的屈抑之苦。
士不得其平则鸣;奇倔的心志和不平的呐喊,成为贾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古意》中,他感叹岁月蹉跎,自己身负奇才却无人知赏:“碌碌复碌碌,百年双转毂。志士终夜心,良马白日足。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眼中两行泪,曾吊三献玉。”在《寓兴》中,他抨击时事的荒唐:“今时出古言,在众翻为讹。有琴含正韵,知音者如何。一生足感激,世颜忽嵯峨。”在贾岛用力最勤的五律中,“求奇”的旨趣,展示了他抗俗自立的狷介个性。
与贾岛相比,姚合的人生道路则相对平坦。由于没有太高的志向,他对自己的际遇很容易满足。在感叹科举失败的《下第》一诗中,他为自己的败绩感到的只是惭愧:“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感时》则说得更为直接:“忆昔未出身,索莫无精神。逢人话天命,自贱如埃尘。”姚合的自惭自愧几乎到了委琐的地步,这和贾岛的愤激不平,无疑是鲜明的对比。入仕之后,姚合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上的抱负,他满足于眼前的际遇,时时流露出闲适自处的意趣。他说:“万事徒纷扰,难关枕上身。朗吟销白日,沉醉度青春”(《闲居遣怀》)。这一份万事不关心的悠闲,来自知足常乐,所谓:“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同上);所谓:“青云非失路,白发未相干。以此多携解,将心但自宽”(同上)。当然,官场生涯难免波折,姚合也时时有一些不如意的感叹,所谓“生计如云无定所,穷愁似影每相随”(《独居》)、“微官如马足,祗是在泥尘。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武功县中作》)。但无论是宦海浮沉的感叹,还是卑官贫贱的牢骚,这些都没有在姚合的内心激发出不平之鸣,他无奈地接受现实,甚至在其中找到新的乐趣。在另一组《游春》组诗中,官卑之叹就已经被闲适之趣所化解,所谓:“卑官还不恶,行止得逍遥”。内心没有奇崛的理想,和现实的和解就很容易达成。姚合追求着这种和解,他的自足与闲适化解了牢骚、磨平了棱角。作为一个接受现状的文官,他沉浸在生活的闲适之趣中,其五律的“求味”正是这种趣味的流露。
人生经历和精神志趣的不同,使贾姚在中唐丰富的诗学环境里,各自接受了不同的艺术影响,贾岛很早就与韩愈、孟郊、张籍等人建立友谊,成为韩孟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他们志趣相投,以复古来表达积极的现实理想,为寒士的屈抑发出不平的呐喊。贾岛在韩愈等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一展雄图的希望,在《携新文谒张籍韩愈途中》,他写道:“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青竹未生翼,一步万里道。仰望青冥天,云雪压我脑。失却终南山,惆怅满怀抱。”同一般的干谒之作相比,这首诗在屈抑的痛苦里展示了诗人宏伟的志向,只有真正的精神知音面前,一个身为下贱的寒士才能有如此激昂的声音。韩愈也同样非常欣赏贾岛,他将孟郊、贾岛视为最知己的诗友,其《赠贾岛》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又生贾岛在人间。”(注:此诗前人或疑其伪托,今人已否定此说。参见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3028页。)在艺术上,贾岛诗歌的“求奇”特色,显然受到韩孟诗派求奇尚怪倾向的很大影响。
姚合与韩孟诗派并没有多少交往,他早年是否结识韩愈,现存材料己不可考证,其集中有一首《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也只是一般的官场唱和之作。姚合与孟郊是否有交往,现存的材料也难以考证。他与张籍的交往比较多,但张籍的后期创作已经有浓厚的闲适趣味,与早年的新乐府大不相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总之,和贾岛比起来,姚合与韩孟集团的关系相对疏远,韩孟诗派好奇尚怪的艺术特点对他并没有多少影响。
姚合受白居易后期创作的影响相对较大。白居易被贬江州以后,政治热情减弱,人生态度趋于消极,知足守常的“闲适”趣味日见浓厚,其诗歌创作转向以近体为主,以平淡流易的语言表现闲适趣味。长庆二年,已经返回长安的白居易,在中书舍人任上求出外任,以求全身远害;宝历初,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在洛阳期间,白居易优游卒岁,他闲适的生活方式,以及充满闲适意趣的创作,对他周围的诗人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姚合宝历初任东都留台御史,在洛阳为官期间与白居易交往较多。白居易集中有《姚侍御见过戏赠》等酬赠之作。其后,姚合官职屡迁,但与白居易的友谊则保持下来,太和八年,姚合出任杭州刺史时,白居易还有诗相送。姚合参与了白居易周围的诗文交往,其集中有《和李十二舍人裴四二舍人两阁老酬白少傅见寄》、《和裴令公游南庄忆白二十韦七二宾客》等作品。姚合精神世界中一直有追求“闲适”的意趣,这在他及第后任武功主簿等职时已经开始流露,只是由于身居下邑,官卑职冷,“闲适”还实现得不那么充分,多少带上孤独自伤的情绪。与白居易及其周围诗人的交往,强化了姚合“闲适”之趣中的安闲自得,使他更优游地实践这一生活方式。几年后,他因官职变动离开洛阳,在《东都分司白宾客》一诗中,就十分倾慕地谈到白居易的闲适生活:“竹斋晚起多无事,唯到龙门寺里频”。而他本人在出任金州、杭州刺史期间的作品也是风光旖旎、和气郁郁,表达了流连风物的悠闲心态,其艺术旨趣和白居易的后期创作已经非常接近。
张籍对姚合的艺术也有一定影响,清人李怀民在《中晚唐诗人主客图》中就把姚合列入学习张籍一派。张籍早年是韩孟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他的新乐府显示出批判现实的锐利锋芒,但其后期诗风则越来越多地转向闲适一路,与白居易的后期诗风日益接近。张籍与白居易结交在元和四年,其后关系逐渐亲密。元和十五年以后,白居易从贬谪之地返回京城,张、白交往更加密切,而张籍晚年则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白居易闲适的处世态度。白居易闲居洛阳后,他有诗寄赠,对于白居易的栖隐不无倾慕,甚至说:“老人也拟休官去,便是君家池上人”(《送白宾客分司东都》)。张籍晚期的创作以近体为主,与早年的风格大不相同。他的五律善于用平易的语言刻画日常的人情体验,创造回味,如“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蓟北旅思》)、“去去人应老,年年草自生”(《思远人》)、“尽说无多事,能闲有几人”(《闲居》)、“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树影新犹薄,池光晚尚寒”(《早春闲游》)等等。
姚合早年与张籍结交时,很欣赏他的新乐府作品,在《赠张籍太祝》一诗中,他高度评价了张籍的作品:“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但长庆以后,张籍的诗风趋于闲适,而姚合则与他更为投契,在《寄主客张郎中》、《酬张籍司业见寄》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闲适意趣的投合。
白居易、张籍等人的后期创作,黯淡了批判的锋芒,流露出浓厚的闲适意趣,体现了某种安位守常的文官心态。在元和政坛积极有为的政治风气消失之后,这种内敛的心态越来越在官场中流行。由于精神志趣的接近,姚合的五律表现出与白居易、张籍近似的艺术旨趣,所不同是,姚合接受了贾岛苦吟的影响,改变了白居易、张籍等人五律语言过于流易的状态,创造出以雕琢求意味的表现路数。
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与安闲自适的闲适意趣,使贾姚五律呈现出“求奇”与“求味”两种不同的艺术旨趣。贾姚二人既然道各不同,那么他们相知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姚合早年由于官卑职冷,也有一些自伤的情绪,其官居的萧瑟孤独,与贾岛的孤清幽僻容易有一些共鸣,因此,姚合任武功主簿、万年县尉等小官时,与贾岛关系最为亲密。但是,官居下邑的经历毕竟是短暂的,随着官职的升迁,与白居易等人交往的增多,姚合很快就摆脱了暗淡的心情,真正体味到闲适之乐,此时,他与贾岛在精神志趣上就日见疏远。当然,姚合始终激赏贾岛的艺术才华,欣赏他的苦吟态度,但是苦吟对于姚合只是一种锤炼语言的方式。它丧失了贾岛苦吟所特有的“求奇”的精神底蕴。姚合多次谈到诗人在创作时要保持一种“峭冷”的状态,所谓:“欲识为诗苦,秋霜若在心。神情方耿耿,气肃觉沉沉”(《心怀霜》)、“诗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答韩湘》)、“格高思潮冷,山低济水浑”(《答窦知言》)。这种“峭冷”的心态,或许在姚合看来,很有助于精思竭虑的苦吟,但它与贾岛的奇僻心态貌合而神离。贾岛的奇僻贯穿于艺术和人生,其精神的奇崛在艺术中化为“求奇”的旨趣;姚合的“峭冷”却只是澄思净虑的创作状态,它帮助诗人摆脱过于庸常的心境,专注于艺术的陌生化创造,但不能使之体会真正的精神之奇。因此,姚合学习贾岛的苦吟,只不过是把它当作表现闲适意趣的语言手段而已。
贾岛之于姚合,有一种寒士感激的心态。姚合为官期间很关心寒素士子,他在任万年县尉时,贾岛、顾非熊、朱庆馀这些寒素士子与诗僧无可就是他的座上客(注:朱庆馀有《与贾岛、顾非熊、无可上人宿万年姚少府宅》。)。他在任东都留台御史和御史台侍御史时,无可、马戴等人又经常聚会于他的府邸(注:马戴有《洛中寒夜姚侍御宅怀贾岛》、无可有《秋暮与诸文士集宿姚端公所居》。)。贾岛在姚合任武功县尉时就与他结识(注:贾岛有《寄武功姚主簿》。),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一直得到姚合真切的关心。对此,贾岛不无知遇之感,在后来写给姚合的诗作中,他真实地流露了自己孤独无依的痛苦:“仆本胡为者,衔肩贡客集。茫然九州内,譬如一锥立”(《重酬姚少府》)。在长期的交往中,姚合自适自足的文官趣味,对贾岛也有一定影响。在愤激的不平之鸣中,贾岛也偶尔流露悲观落寞的心情;他也接受了闲适意趣的影响,写下一些平淡有味的作品。当然接受是有限的,终其一生,贾岛“求奇”的棱角并没有被磨平。
如果说姚合的“求味”旨趣反映了长庆以后文官阶层中流行的闲适意趣,那么贾岛的“求奇”在当时则是一种越来越孤独的声音,与贾岛友谊深厚的姚合并不是他精神上的知音。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事和艺术风尚的变化,贾岛的异代知音也日见稀少。
三,姚合五律奠定基本格局:贾姚五律在唐末五代的流变
贾姚五律在晚唐已经产生影响,到唐懿宗咸通以下的唐末五代诗坛,二人的影响几乎支配了当时的五律创作。唐末五代诗人对贾姚的接受体现了独特的艺术取向,他们学习贾姚的苦吟态度,在艺术旨趣上则偏向姚合,排斥贾岛,形成了苦吟与“求味”旨趣相结合的创作格局。
关于晚唐以下五律的创作状况,前人已多有论及,通行的意见主要有闻一多先生的“贾岛时代”说和宋元明清广泛流行的“晚唐两诗派”说。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中指出,晚唐是贾岛的时代,晚唐五律主要继承了贾岛的影响。而古人的“两派说”,内容比较复杂。
杨慎在《升庵诗话》(卷4 )中提出“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杨慎这个意见源于宋张洎《项斯诗集序》以及宋方回《瀛奎律髓》卷20朱庆馀《早梅》诗注。清人李怀民《中晚唐诗人主客图》承续了这种认识,将中晚唐的五律分为以张籍为代表的“清真雅正”派和以贾岛为代表的“清真僻苦”派。但在具体诗人的分类上又与张、杨等人有所区别,“清真雅正”一派包括了张籍、朱庆馀、王建、于鹄、项斯、许浑、司空图、姚合、赵嘏、顾非熊、任翻、刘得仁、郑巢、李咸用、章孝标、崔涂;“清真僻苦”派包括了贾岛、李洞、周贺、喻凫、曹松、马戴、裴说、许棠、唐求、张祜、郑谷、方干。
“贾岛说”突出了贾岛的地位,反映了贾岛苦吟的语言方式在晚唐五代所产生的深广影响,这是符合事实的,但它忽视了贾岛“求奇”的艺术旨趣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排斥。“两派说”的分类标准不无含混之处,张籍与贾岛,既有艺术旨趣“求奇”与“求味”的对立、也有语言风格苦吟与流易的对立,但列入张籍一派的诗人,很多也有苦吟的特色,与张籍流易的语言风格差别很大,如姚合、司空图;列入贾岛一派的诗人,多数又排斥了贾岛“求奇”的艺术旨趣。两派说在反映实际创作状况上不无局限。
事实上,晚唐之后的五律流变有独特的取向,在艺术旨趣上,倾向“求味”,排斥“求奇”;在语言风格上,则回避流易而走向苦吟。在唐末五代诗坛,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十分显著,姚合以苦吟求意味的表现方式奠定了当时基本的创作格局。张籍的五律虽然也有“求味”的旨趣,但由于语言缺少苦吟锻炼的特色,他的影响已经基本上被姚合取代。
唐末诗人特别重视贾姚的苦吟态度,方干自称:“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许棠云:“学剑虽无术,吟诗自有魔”(《冬杪归陵阳别业》)、“分合吟诗老,家宜逐浪空”(《下第东归留别郑侍郎》)。曹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崇义里言怀》)。
但是,苦吟毕竟只是语言的锤炼问题,诗歌的语言形式如何锤炼,必然直接受到诗人艺术旨趣的制约和影响。在唐末五代,“求味”的艺术旨趣显示了更大的影响力,孤介不平的情感内容受到排斥,语言表现也不尚奇僻,而注重以形式刻画锻炼去传达含蓄宁幽的意趣。在这些方面,姚合都显示出他巨大的影响力。
唐末五律情感平和,风格雅正,类似贾岛五律中孤介峭拔的情绪波澜基本上被回避。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薛能明确反对这种由于内容有乖“平和雅正”而导致的僻涩诗风。《北梦琐言》卷7载:“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许州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以掌’。”高蟾的作品传世不多,从《北梦琐言》下文的记载来看,他之所以引起薛能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意疏理寡”,也就是在作品中流露了过于怨讥的内容,而他那些不落讥刺的作品则得到了承认和赞许,如:“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这首诗受到时人的称赞,而它不过是将对唐末科场黑暗的讥讽转变为自伤自怨。
贾岛奇异的语言方式,在当时也很少被仿效。贾岛喜欢大量使用孤寂清冷的意象,唐末五律逐步回避了这种作风,就是当时那些辗转科场,不无悲苦之辞的寒素诗人也极少仿效贾岛。贾岛那些奇异的语言方式,在唐末五代的五律中就更少得到响应。当时工于字句之雕琢的许棠、曹松等人都没有多少奇僻的诗句,许棠集中的“饭野盂埋雪,禅云仗倚松”(《赠志空上人》)、“逼晓人移帐,当川树列风”(《边城晚望》)、“喷月泉垂壁,栖松鹤在楼”(《宿华山》)等,已经是最为奇特的诗句,但与贾岛之奇相比,还是比较平易。曹松同样以苦吟出名,但用语之奇似乎还不能和许棠相比,他的“直峰抛影入,片月泻光来”(《题鹤鸣泉》)、“林残数枝月,发冷一梳风”(《言怀》)、“湖影撼山朵,日阳烧野愁”(《岳阳晚泊》),是曹集中最奇特的诗句,但比之许棠又见平实。
真正得贾岛奇言僻句之神的是李洞,其用语奇僻之处随处可见,如“吏穿霞片望,僧扫月棱归”(《寄贺郑常侍》)、“溪声过长耳,筇节出羸肩”(《赠禅友》)、“夜寒吟病甚,秋健讲声圆”(《登圭峰旧隐寄荐福栖白上人》)、“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题慈恩友人房》)。这些诗句酷似贾岛之作,但在唐末的五律创作中却显得相当孤立。
唐末五律主要继承了姚合锤炼语言的方式,注重诗句中字意的映衬、对比,如方干“凉随莲叶雨,暑避柳条风”(《东溪别业寄吉州段郎中》),将下雨生凉,风中避暑的正常表达顺序进行调整,突出了凉意因雨而生,暑意因风而退的主观感受。唐末五律使字句间的变化安排极尽细腻,不光加强了字意之间的映衬,而且在字词本身的使用上也多用巧思,如方干“野渡波摇月,空城雨翳钟”(《送从兄郜》),使“波”与“雨”变成有意向的主动者,突出江中月影的孤单和雨中钟声的微茫,以传达送别时惆怅的心绪。富于巧思的诗句在唐末诗人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如张乔“孤峰经宿上,僻寺共云过”(《送陆处士》)、“板阁禅秋月,铜瓶汲夜潮”(《金山寺空上人院》),方干的“孤钟鸣大岸,片月落中流”(《早发洞庭》)、“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登雪窦僧家》),司空图“草嫩侵沙短,冰轻著雨消”(《早春》),郑谷“宿馆明寒烧,吟船兀夜波”(《送京参翁先辈归闽中》)、“春阴妨柳絮,月黑见芦花”(《旅寓洛南村舍》)、“极浦明残雨,长天急远鸿”(《夕阳》),李频“微泉声小雨,异木色深冬”(《送延陵韦少府》)、“野衔天去尽,山夹汉来深”(《汉上送人西归》),许棠“河水深荡塞,碛色迥连天”(《塞外书事》)等。
事实上,唐末诗人在对贾岛的接受上带有明显的姚合眼光,贾岛受到唐末诗人注意的作品,艺术旨趣都与姚合相当接近。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时,将贾姚共同列入“清奇雅正”一门,所引的诗例也毫无僻涩之处,如“夜半长安雨,灯前越客吟”、“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岛屿夏云起,汀州芳草深”。唐末诗格、诗式类作品吟咏贾岛的诗句也多不重僻涩,如《处囊诀》讨论诗眼,举贾岛诗句“天上中秋月,人间半世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文彧《诗格》论“诗有所得”,举贾诗“秋江待明月,夜语恨无僧”。论“诗病”,举贾岛诗句“久别丹阳浦,时时梦钓船”为正面例证。这种选择都可以看出姚合旨趣的影响。
姚合“求味”的旨趣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诗学传承上看,唐末诗人与姚合更为接近。唐末诗人李频学诗于方干,并受到姚合的赏识。方干也与姚合有直接的交往。李频对唐末的五律作者又颇多奖掖之力,他的诗学趣味无疑会有较大的影响。相反,贾岛虽然被当作师法的对象,但他与唐末诗人缺少直接的诗学继承关系。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精神上的疏远。如前所述,贾岛的“求奇”更多地流露出不平则鸣的寒士精神,而姚合的“求味”则主要体现了流行于文官阶层的闲适趣味。随着中晚唐社会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到唐宣宗大中朝以后,文官政治消极发展,自适内敛的官场风气更趋流行,以中唐韩孟集团为代表的寒士精神受到更多的排斥,即使是象“咸通十哲”这样辗转科场的寒士,也普遍接受了雅正的艺术旨趣,而这或许是姚合的“求味”产生更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当然,对这种背景的分析探究,还须进一步深入。从艺术上讲,贾岛“求奇”的语言方式,在创造含蓄不尽的回味方面不无欠缺,而姚合的语言方式则为“意味”的创造留下许多可发挥的余地,艺术上有比较多的发展空间。
总之,经过唐末五代诗人的继承与变化,姚贾诗派基本形成,姚合以苦吟追求意味的表现方式奠定了诗派基本的创作格局。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贾岛与姚合被并称而成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志时,这一流派就应该被称为“姚贾”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