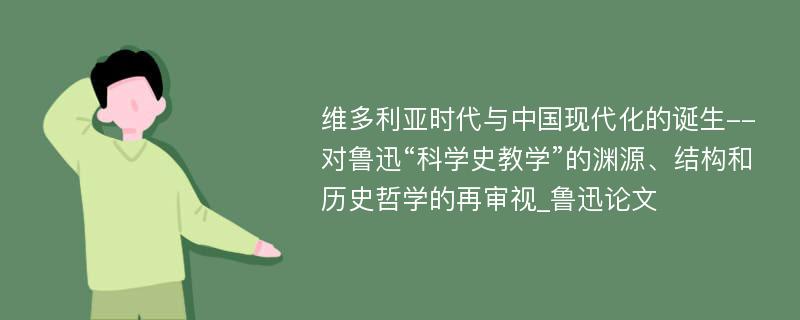
维多利亚时代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诞生——重考鲁迅《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结构和历史哲学的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鲁迅论文,命题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1-0032-30
这篇论文研究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章《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和涉及的一些思想史命题。我们知道在1907和1908年之间,鲁迅一口气为《河南》杂志写了五篇文章,涉及当时中国思想界许多重要命题,这五篇文章在当时也许没有什么影响,但今天却成为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文献。
研究这个时期鲁迅思想有一个难度,即必须分清楚什么是鲁迅自己的观点,什么是别人的观点,而他只不过是在引述。这件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因为鲁迅行文不用引号,叙述和引用时常混在一处,难辨真伪。再有就是这五篇文章中有三篇是编译,而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因此辨析材料来源成为阐释这三篇文章的重要工作。这三篇是《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和《摩罗诗力说》。《人的历史》是鲁迅惟一一次系统介绍进化学说发展史的文章,我们知道,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是进化论,相信自然、社会和人都是不断向前进化的。他的这篇文章开篇即出现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鲁迅原文为黑格尔)的名字,并把他作为进化论最新阶段的代表。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基本是对海克尔大作《世界之谜》第五章的编译。具体的情况留德学者张芸已经做了梳理工作,可参见其《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摩罗诗力说》资料来源工作最为复杂,广涉英、日、德等文献十多种,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考据工作,对我们研究鲁迅早期思想有重要的帮助[1]。
《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这项考据工作虽然琐屑,但还不算困难。鲁迅当时似乎有个习惯,虽然他不说明引文的出处,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供人索引,惯常的做法是把著者名字写出来,就像他在《人的历史》中开篇就写上海克尔的名字一样。《科学史教篇》出现的三个西方学者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也是鲁迅编译之对象。第一是赫胥黎,鲁迅对他非常熟悉,严复《天演论》译的就是他的《进化与伦理》一文。周作人曾说此书部分章节鲁迅是熟到能背诵的。《科学史教篇》根据的核心文献是赫胥黎的《科学之进步》一文。但如果细加考究,鲁迅对赫胥黎这篇文章的兴趣完全不是其进化学说,而是其文涉及的科学教育问题。故此文命名为《科学史教篇》。第二是丁达尔,他是爱尔兰人,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英国科普教育的主要推动者,赫胥黎的好友。他的论文有两篇被鲁迅部分编译,一是《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二是《科学的片断:写给不懂科学的人们》。第三是英国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华惠尔,他的巨著《归纳科学的历史》中的某些观点被鲁迅讨论。
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三个人物名字都出现了,下面的工作就是找到他们相应的著作。鲁迅曾说过,他以前的文章“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当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的很。”[2](卷7P4)这段文字现在看起来有点不真诚,他要真想找到“偷”来之物的来历,并不是特别困难。不过,这段表白也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当时读书写作的状况:他对自己写作的主题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对西方著作的把握是完善的。鲁迅总是按自己的需要去阅读西方材料,因此创造性误读就在所难免。
本篇的第一个目的是把《科学史教篇》编撰西学的部分全部找出来,以此确定这篇文章哪些是译介,哪些是鲁迅自己的评论①。鲁迅是早熟的思想家,在日本期间,已显示出他对现代性问题有着深刻的把握。但由于论述问题的复杂性、潜在对话者的多样性、思想又未臻成熟、行文缺乏规范、字句偏重古奥,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早期论文阐释难度。我们因此有必要区分他早期文本里并存的两套经验,一是历史经验,即中国文化政治的现实问题;一是理论经验,即西方对现代性问题的把握与阐释。这两套经验时常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这不利于我们明白某一个论点是鲁迅所作的历史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因此,一个笨工夫就是把《科学史教篇》西学资料都找出来,然后比较它们和原文之间的差异,即鲁迅录用原文的哪些部分,没有用哪些?用的时候做了何种修改?原文的历史背景和线索是否因此受到损害?由于从原有语境中剥离出来,这些引文的意义发生了什么改变?并且为什么要用这些思想家文本,而不是其他思想家的东西或同一思想家的其他文本。另外,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清楚,所谓鲁迅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东西,而是在多个复杂的知识场域逐渐形成的。研究鲁迅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复原这些原生态的知识场域,探究鲁迅的核心概念是如何在这些场域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在这些场域中常常有一个西学文本构成的对话空间,它是鲁迅思想形成的一个特定然而必不可少的空间。因此有一种纠缠,有一种分不清你我的原生的状态。鲁迅早年的文章都有这种性质,是一种任何清晰的规定性都无法起决定作用的思维的创造性过程,这个思的过程很开放,因此他的文本出现强烈的互文特征。我的研究不仅仅要尽力指出这种互文的意义呈现过程,而且指出这种呈现方式构成鲁迅思考方式的独特性,使他能超越中西两分的思维模式,而直指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为了不一下子使读者陷入琐碎的考据里面,而能从大处把握要讨论的问题,我先对《科学史教篇》所涉及的大的知识问题做一整体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和《摩罗诗力说》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它们各自的资料来源有种按国别划分的倾向。谈论进化学说时,鲁迅依据的主要是德国思想家的工作,他并没有直接转引达尔文、赫胥黎、穆勒和斯宾塞的著作。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潜在的影响,但基本上是从德国思想家的视角勾勒进化学说的历史发展。《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是清一色的英国科学家著作。《摩罗诗力说》相对复杂,但最重要的材料来自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这种按照国别为话题选材料的做法,是有意为之,还是纯熟巧合?如果是有意为之,我们就需追问为什么?因为鲁迅的这个考虑不能被轻易忽略。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外语能力的问题。鲁迅可以用日语和德语阅读。那么他选用海克尔文章来讲述进化论的历史是较为自然的选择。鲁迅阅读的是海克尔的德文原著应该是无疑的。因为据姚锡佩的研究,鲁迅在日期间购买了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宇宙之谜》和《生命的奇迹》三部德文著作[3]。在《人的历史》中,凡有原文引述,皆以德文形式出现。但鲁迅也肯定熟悉日本学术界对海克尔的研究,因为该文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时,叫《人间的历史》,“人间”是日文的“人”的概念。直到1926年搜集旧文重新刊印时才改成现在的名字。可见日语和德语确实是鲁迅在日期间主要工作语言。同样的,借助日语去研究拜伦等摩罗诗派也是势所必然,是最方便的方法。
但我觉得光从外语能力方面去解释这种现象是不够的。这忽略了鲁迅独特的研究方法。鲁迅在研究西方思想家工作时,有种倾向,即从其民族国家的历史特性来理解这些思想家的工作意义,而不是把他们的观念从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剥离出来,演绎成普适的理论命题。这个习惯和他著名的研究国民性的思路是一致的。鲁迅在考察世界文明之状况时,不是简单沿袭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在他眼中并不是整体一块,他总是注意到西方各国有不同的社会问题,文明发生发展的阶段也不尽相同。没有一个简单的抽象化了的西方。同时,鲁迅又是个民族主义者,相信文明的进步必赖以国家之力来完成。国不分大小,都是世界文明最有意义的单元。因此考察文明也须借助国家做分析的单位,做改革的动力,做实现的手段。在他那里,我们总可以发现细腻的历史逻辑和理性的民族意识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批判视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思考为什么在他早期论文里有种把他关注的理论和社会问题放在特定民族文化中来考察的倾向。
在《人的历史》一文中,鲁迅把海克尔称做进化学说之集大成者。这不仅是对海克尔个人崇高的评价,也是带有对德国民族理性思辨能力的高度认可。德国在鲁迅心里代表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意见是否是受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尚不得而知。但从鲁迅自身的思维逻辑上也可推出此观点。在《文化偏至论》里,作者表明了一个鲜明的观念,当文明走向偏至,必靠另一偏至之力匡扶之。一方偏至程度愈深,另一方反抗的力道也愈猛烈。这一激一荡,才有历史的进步。故而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才会在德国产生,皆因理性的代表黑格尔和海克尔也在德国出现。理性和非理性的力才会在德国知识界撞击出最强的思想力度。
我一直认为,从第一篇《人的历史》到《摩罗诗力说》,鲁迅思想的注意力是沿着现代文明偏至的一端(理性)走向偏至的另一端(非理性)。这种在他早期思想里的内在的对称结构,是足以使人惊诧的事实。因此,他不可能在一个被实用主义浸渍的英国文化里寻找现代理性的最高表现。他会不惜放弃达尔文、赫胥黎,而到海克尔身上去找他要找的理性之光。
现在我们回到《科学史教篇》。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鲁迅把教育问题放在英国背景来谈论呢?为什么英国国情强烈地引起鲁迅的内心震撼呢?它和中国问题相关性在哪里,又和鲁迅自身对现代性批判的相关性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阐释这个文本的关键。
这个问题很容易有个简单的回答,从而得一个笼统答案。或是以一个笼统的态度得一个简单的回答。这都不可取。其实,情况远非初看时那么一目了然。鲁迅关注的问题和他引述的西方资料既很对接又非常不同。我先对此作一个扼要说明。鲁迅的题目《科学史教篇》传递了其论文主旨,即通过研究西方科学发展史寻求一些历史教训。所以在此论文第一段的结尾处,鲁迅就言明:“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2](卷1P25)②那么这个宗旨是否与赫胥黎《科学之发展》的宗旨一样呢?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首先,赫胥黎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获得任何历史教训,这不是一篇历史反思性的文章,而是有鲜明的现实政治诉求,那就是呼吁英政府抵制教会势力,普及大学里的科学教育,同时指明科学研究在当今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要求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而鲁迅写此文章并不含如此实用之目的,它不是写给政府的奏章。他把着重点放在“人性之全”这个论点上。其文结尾是:“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鲁迅的关注点显然在什么是现代人这个中心问题上,是梁启超对现代“公民”的讨论的延续。
如此,所有的历史判断都有重大不一样的地方。对赫胥黎而言,教会是科学发展最大的障碍,是造成中世纪科学停滞的原因;对鲁迅而言,宗教也是人性之全的有机部分,其不但不与科学精神有本质的冲突,而是其本源的守护者。故鲁迅给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两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或为克灵威尔,为弥尔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此其成果,以偿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这当然和章太炎认为佛教可匡民心的思路有关[4]。
由于赫胥黎对中世纪宗教的看法稍显简单粗暴,他的文章又没有提供详尽的中世纪科学研究状况,鲁迅才借助华惠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一书去获得更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知识。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受到基督教精神的哺育,它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同时,古希腊的科学的特点和现代科学有何不同呢?鲁迅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中世纪科学不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宗教对科学的破坏性影响?鲁迅试图转向华惠尔的著作寻求答案,但从结果看,文章处处表现了鲁迅的历史哲学和华惠尔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根本冲突。
华惠尔对古希腊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有过著名的论述,即他的有名的“悬拟”这个概念。英文是“hypothesis”,今译假设,鲁迅译为“悬拟”,也许是日本学者的翻译,因为鲁迅对华氏著作的阅读可能是通过日文的翻译。这点待考。华惠尔对古希腊科学观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古希腊人科学不可能进展,原因是当时科学概念与日常生活观念基本是一致的(缺乏玄念),这使得科学概念不规范,不严谨,不清晰,不自足。鲁迅引述华惠尔对希腊科学思想的贬低:“华惠尔常言其故曰,探自然必赖夫玄念,而希腊学者无有是,即有亦极微,盖缘定此念之意义,非名学之助不为功也。”华惠尔的科学哲学是二元论,一方面培根是他的英雄,因为培根发展了近世科学研究的根据之一,即实验和实证思想;但同时他批评培根轻视假设的作用,这使得科学研究完全依赖于对物质世界的经验层面的观察,而失去与超验理想世界的联系。这超验的形而上思辨才是大胆假设的来源,才是从表象世界通往真理世界的路途。华惠尔对假设在科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做了清晰的哲学说明,其影响至远。英国思想界和德国思想界在1830年之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交往频繁,能读德语的学者非常少,为鲁迅熟悉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作者卡莱尔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是他率先把德语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情况介绍给英语读者,从而使得许多年轻学者开始重视学习德文③。华惠尔是最早了解康德哲学的人之一,他的科学哲学是把不为英语世界熟悉的康德先验论应用到自然哲学研究。这在英国是非常新颖的思想④,不但为当时科学家如赫胥黎和丁达尔所服膺,也是当时科学界解释达尔文进化论方法论的一个主要概念。它的影响通过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传到中国,成为胡适著名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源泉之一便是华惠尔哲学。但有意思的是,鲁迅对“悬拟”这个提法并不感兴趣。例子有二,第一,赫胥黎《科学之发展》第二部分也是着墨最多的部分是用华惠尔“假设”这个概念解释当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包括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但鲁迅对这部分索性略去未译。证据二,是鲁迅在文中直接对华惠尔对古希腊科学成就的贬低提出批评。
这牵扯到鲁迅的历史观和华惠尔与赫胥黎等的差异。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鲁迅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即对古心,白心,神思给予最高的价值判断。鲁迅对华惠尔的批评是,科学是发展的,概念的清晰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不能以后世的标准衡量古人。不管古希腊人科学思维如何幼稚,但其不乏伟大先行之精神,即探索前人所未知的宇宙之奥秘。如何才能准确地衡量古人所取得的成就?鲁迅提出类似的“理解之同情”的看法,用他的话说,就是“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华惠尔、赫胥黎之辈蔑视古人的心态引起鲁迅的反感情绪,使他一下子联想到自己祖国知识界的两个极端的历史态度,要么崇古,古代的任何东西都是完美的;要么蔑古维新,破坏一切。两者都凸显中国近世的思想进退失据。鲁迅说,“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因此,他加了一句攻击性很强的话,“略有思理之人,无不然也。”就是说,简单否定古希腊科学思想诸君,如华惠尔、赫胥黎,简直疯狂至无思理可言。
他接着引申,肯定希腊精神为“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所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可言。”相反,他批评那些以理性精神嘲笑神话迷信者,为可怜之徒而不自知。“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在这里鲁迅用一句话陈述了一个价值判断和历史判断。他说“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实验,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这句话包含的历史判断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但它同时还包含了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反历史判断,即神思乃人类精神源泉,不能用进步不进步来衡量。
鲁迅在这里显然是反对简单的线性历史观。鲁迅虽然也认同发展,却对历史的进程的复杂性似乎有更清晰的认识,反对非此即彼的态度,超越善恶原则,能以辩证的方法审视之。故他强调,“特以世事反复,时势迁流,终乃屹然更兴,蒸蒸以至今日。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鲁迅在这句叙述里用比喻的方式论证。水裔,即水边的意思。但什么叫进退良久波浪才抵达岸边?从这个比喻里我们很难推出“发展”这个概念,而更像尼采永恒的复归的概念,是一种历史的精神本质再一次成功的客观化而形成历史主体存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
很显然,在鲁迅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时,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严肃的也是困难的历史课题。他意识到了理性的历史和非理性的历史不一样这么个命题。如果科学代表的是人类理性,它的历史不管如何曲曲折折,它总能以逻辑的形式,客观的成果告诉你一幅发展的图景;但非理性的历史,如信仰和道德的历史就不可能呈现发展的面貌。这两个矛盾的历史如何能协调起来为当代人的生存作以价值规划?这个问题是鲁迅历史观里的核心问题。鲁迅在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的批判,认为科学发展不是依靠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自律性,而是和科研团体种种利益划分有关。鲁迅不可能如此后现代地处理掉他面临的问题。他要借助一些神秘、象征性概念诸如“根”“白心”“内曜”“源”来为科学精神提供一个更高级的源泉。但是如果有这个源泉,而且如他希望那样,这个源泉在人的本心,体现为一种信仰的力量,那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中世纪的信仰时代是科学发展最阴暗的时代。
鲁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怀着深刻的兴趣在华惠尔和丁达尔著作里寻找启示。他首先承认思想喑黯是一个事实,他援引华惠尔:“时亚刺伯虽如是,而景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摈斥夭阏之”。同时他罗列三位思想家诊断的药方。一位是培庚(Roger Bacon),他为学术衰微找到四个原因,摹古,伪智,泥于习和惑于常。华惠尔的诊断则是,思不坚,奴性,急躁,热中之性。他在《归纳哲学的历史》一书以四章分别解释这四个判断,四章的题目分别是:“模糊的观念”“注释学的精神”“教条主义”和“神秘主义”。鲁迅一定看过这几章,因为他说华惠尔在阐述自己上述观点时,“且多援例以实之。”但最能触动鲁迅的是第二章,“注释学的精神”,因为这和清学术考据传统有相似之处。故鲁迅说:“而亚刺伯之科学,在模前有,故以注疏易征验,以评骘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他完全接受华惠尔对中世纪缺乏创造力的批评,认为尽管中世纪知识分子勤勉有余,创新却不足,全部的问题因此是“精神之弛,因入退守。”
非常有意思的是,鲁迅终于找到了一个盟友来反驳华惠尔。这个人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丁达尔。我们能看到鲁迅和丁达尔的许多意见都契合,他把后者视其为知音。作为冷静的逻辑学者,华惠尔把激情看成是有害于科学研究的性格,丁达尔批评了这个观点,认为对于智力不足的人,激情是有害的,但对于杰出的人物,激情能更促进科学的发明。因为丁达尔把激情定义为道德的力量。其愈强,人的道德亦愈深邃,科学的创造力愈能被激活⑤。借助丁达尔的思想,鲁迅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盖科学的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
读到这里,鲁迅的写作意图才在读者面前豁然清晰起来。他是在把科学的问题道德化,这是他要从科学史中阐释出来的教训。换句话说,鲁迅是把科学真的问题换成道德善的问题加以讨论。他不断穿梭于西方经典文本,用偷换概念的方式,把逼问引向自己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被偷换成科学家。有此偷换,伦理的问题一下子被提了出来。所以他下此结论:“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所以他根本不理会赫胥黎津津乐道的科学方法论,因为那在鲁迅看来,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他是要从科学的发展历史中发现一个恒定量,一个没有历史的历史,而科学,艺术,宗教不过是这种隐蔽的精神之源的一个个支流。可以想见,这种伦理的真才是鲁迅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⑥。
我们不清楚的是:第一,这个精神之源之内有无质的区分,即,古希腊人的神思和中世纪人的宗教热诚是否是等同的一种精神。如果是这样,如何批评宗教而肯定神思?鲁迅的思想里似乎从未把宗教作一个反思的历史对象来思考。宗教一直是主观的问题而不是客观的问题,因此没有答案。这就是祝福里我对祥林嫂的问题闪烁其词的原因。因为所有的询问者必须自己给出答案,答案只能在自己的询问方式中被设定。第二,我们不清楚的是,鲁迅这个“回心”的思想,在此篇里表现为对古希腊精神的赞扬,有多大程度上是受尼采思想的启发。因为鲁迅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能模仿一下伊藤虎丸先生的语言,是很西方的。它比鲁迅所攻击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想还要保守,也正因如此,它比它们都要革命。但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回心的意义呢?它最终是个善的问题,即伦理题域里的问题,还是一个在的问题,即存在论范畴的问题?或许流行于19世纪末的以生物学为根基的生命论和活力说是其基础?第三,如何理解鲁迅的核心概念“偏至”?偏至和反偏至,被鲁迅视为文明进程的必然过程。那么这个概念只是中国道家学说里的“物极必反”观念的延伸,还是更像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矛盾客体?或者,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发现海德格尔的影子,是某个原初的东西永久地处于遮蔽与澄明的两难境地?不管我们有怎样的疑问,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科学史教篇》是我们研究鲁迅历史观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文本。但迄今众多的研究鲁迅历史观的著作似乎都没有重视这篇著作。可是不探讨鲁迅的科学史观,也就无法全面了解鲁迅的历史观。
下面我对鲁迅的历史观作进一步讨论。对我来说,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独特的历史哲学。不管是他前期的进化论,还是晚期的终末论,它们都是前期和后期鲁迅思想和创作里本源性的东西。《科学史教篇》还有许多资源供我们发掘去探求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即英国当时思想界的状况有什么深深触动鲁迅的地方?英国思想界整体的保守和革新的冲突形成了什么样新的思想的活力而引起鲁迅的共鸣?在多大程度上,鲁迅的历史哲学、文化理论和文学思想是在这个知识体对话过程中形成的?一句话,我们追问鲁迅的思想和英国维多利亚思想界的关联。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关系。这种整体性的联系现在中国学界还缺乏详尽的探讨。一说起这个时代,我们马上会想到那是个性压抑的时代。伟大的傅柯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这个根深蒂固的印象⑦。但那显然不是鲁迅印象中的维多利亚。鲁迅印象中的维多利亚时代肯定是与这三部书有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穆勒的《论自由》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两本书是年轻鲁迅所熟悉的,前一本对晚期鲁迅有深刻影响。这三部书发表于同一年,即1859年,一个伟大的时间点,维多利亚思想的黄金时代,它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世界震惊。然而,写《科学史教篇》的鲁迅似乎刻意回避这个年份,而把目光聚焦在后面的二十年。赫胥黎的《科学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Science)写于1887年,丁达尔《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Belfast Address)写于1874年,其《科学的片断:写给不懂科学的人们》(Fragments of Science:For Unscientific People)写于1871年。只有华惠尔的《归纳科学的历史》第一卷(History of Inductive Sciences)写得比较早,是1837年的大事。
这个时间段是一代新的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掌控话语权的时期。他们的出现强有力地推动英国公共科学教育的发展。这些人包括赫胥黎、丁达尔、克利福德(William K.Clifford)、斯宾塞和高尔顿(Francis Galton)等⑧。后者是达尔文的堂弟,“优生学”一词的创始者。他们基本都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不满于教会势力,力图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他们共同的专长是自然科学,但他们显然不认为科学是与政治、文化、经济无关的精神活动。因此在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后,则积极从事科学的普及教育工作,正是在所谓公共科学这个新的知识范畴,他们开始把科学的精英话语与公民教育等大众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积极建立科学与宗教、文化、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力图为大英帝国现代文明奠定新的更广大的根基。他们特别羡慕德国的教育体制,这不但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德国接受的程度远比在英国为高,其最新的发展也在海克尔那里完成。连赫胥黎都要亲自翻译介绍海克尔的著作。而且因为德国政府对科学教育和科研的投资力度比英政府要大,这成为赫胥黎等人去呼吁建立完善的维多利亚公共教育体系的重要依据。
鲁迅对科学在德国和英国不同程度的接受应该有所了解,所以他会选择丁达尔和赫胥黎的著作来研究历史教训。鲁迅可以很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都不是出身贵族阶级,都代表新的社会变革力量,都崇尚德国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科学的头脑。然而一进入公共教育领域,又都意识到科学教育乃“立人”之根本。因此,这些英国人对科学、道德、艺术和宗教一系列当时最重要的思想问题的探讨很可以被鲁迅引为知音。
由于丁达尔的《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是其任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主席时的就职演讲,鲁迅对此协会应有所了解。这个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它成立的时代,科学仍然是一个私人从事的活动,缺乏政府和工业支持。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它经历两个时期,从建立之初到1851年世博会在英国召开,是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科学教育推行者借助的是一套普世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去阐述科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科学可以促进和平,增进财富和幸福,实现人的自我提高。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51年之后,尤其在1870年代后,科普教育就和民族主义话语,新的军事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和大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率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连在一起。赫胥黎的文章和丁达尔文章代表这个新的趋势。他们都是根据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进化学说和原子理论这些科学最新进展来为科学普及作辩护。鲁迅对此三理论非常关注。在《人的历史》里他介绍进化学说,并提到等量守恒,即“质力不灭律”,他又曾撰文介绍分子理论。这些知识是和鲁迅对英国科普派的关注分不开的。
鲁迅对这个科普协会前后期不同的主导思想似乎都有所了解。《科学史教篇》前半篇谈的是“立人”问题,即科学是“恬淡,逊让,有理想和有圣觉”人的智力活动。但其文后半段探讨的是科学与实业和救亡的时代主题。他为此引述丁达尔《科学的片断:写给不懂科学的人们》的前言部分⑨,整整占了《科学史教篇》的两页。这部分完全是翻译。其文章结尾之处展现鲁迅要调和英国科学促进会前期和后期主张,故其云:“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但结笔之处却再次强调避免惟科学主义的泛滥,防止由于科学理性导致的人类精神“大枯寂”。展望未来中国不但应诞生达尔文,还要诞生卡莱尔⑩。
至此,《科学史教篇》全文结构已经非常清楚。它起始于编译赫胥黎的《科学之进步》开篇部分,引出科学与人类进步福祉之关系。紧接着,由于不满赫胥黎对古代(古希腊和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转求教于华惠尔和丁达尔的相关历史论述。中篇结于把科学定位于国泰时的人性之光。随后新的紧张感出现在科学与富国强兵的主题上,丁达尔的著作成为惟一引述的文章,这就是为什么丁氏有两篇文章成为此文主要资料。此部分结于救亡主题。随后作者又用了11行句子为全篇做一结尾,这结尾处的思想不能完全认为是启蒙主题的再次浮现,它包含的“本源”的思想具有超越救亡和启蒙的内容,进入一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这是鲁迅思想中最难分解的东西。现在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这个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想与维多利亚科学普及派的关系是什么?换句话说,难道科普派如赫胥黎、丁达尔和华惠尔的思想也可属于激进的保守主义一脉吗?如果是,他们和鲁迅的激进保守主义思想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哪里?
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界是一个地震高发地区。这震源是飞速前进的自然科学研究,而其所撞击的岩石是基督神学。自然科学兴盛必然催生对下一个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唯物主义哲学。然而,唯物主义在19世纪的英国主流知识界主要是以一种科学主义方法论出现的,把它真正转化成世界观是马克思的卓越贡献。赫胥黎和丁达尔是科学界唯物论的代表。但他们把唯物主义仅仅当成科学的方法论。丁达尔在其最有争议的《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里,对唯物主义做了充分的辩护。这篇演讲出现在一个敏感时期,就在两年前,教会的权威由于达尔文发表《人的后代》一书再次受到了挑战。故丁达尔的就职演讲就被教会认为是滥用公众权利,以其特殊的身份宣扬无神论。但实际上丁达尔本人对唯物主义有其特殊的定义。他早年深受唯心主义影响,是华莱尔终身崇拜者,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热情读者。然而其从事的科学研究使得他一步步转向唯物论。1860年代初期是他向唯物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但其转变的真正原因有一部分是痛恨教会对科学研究的压抑,认为在教会势力很大的英国没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唯物主义因此是民众最需要的思想武器,是培养理性思维的关键。但丁达尔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这决定他的唯物主义不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因此他主张唯物主义不是惟一的生命哲学,它仅仅是科学方法论。这才是他在《贝尔法斯特就职演说》(11)阐释的核心思想(168页)。所以他说尽管阑喀写了《唯物主义历史》一书,他也不是唯物主义者(137页)。而真正的生命哲学必须能够同时阐释美学、宗教和道德经验。对他来说,唯物主义对此无能为力。他的思想推至极处变成了不可知论,因为给予物质世界神秘的整体性的,给予人类社会一有机存在方式的不是人的大脑,而是超验的神秘力量。正因为如此,理解力并不是自然知识的惟一来源,客观知识还需依赖人的内在经验,即情感,激情和感知。正是这个意义上,他赞扬穆勒的实证主义,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斯宾塞的心理学(192—193)。
鲁迅显然明白丁达尔这份苦心经营,他援引了阑喀的一句话:“阑喀曰,孰辅相人,而使得至真之知识乎?不为真者,不为可知者,盖理想耳。”阑喀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真理性的知识不是真实的知识,也不是可知的知识,而是超验的经验,即理想。鲁迅对此非常赞赏,忍不住添了自己的一句评论:“此足铁证者也。”这就是说,鲁迅看重丁达尔的不是其唯物主义思想,而是其神秘主义倾向。
《科学史教篇》通篇肯定的不是科学至上的唯物主义论,而是由英国科学家所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虽然都是德国古典哲学核心部分,但它们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但鲁迅显然把它们混在一起,他所谓的“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是更接近于浪漫主义的基调。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发现鲁迅早年主张的“迷信可存”这一主导思想是借助英国科学界对迷信和科学的争辩来发展起来的。“迷信可存”可以说是鲁迅对赫胥黎、丁达尔和华惠尔的思想的敏锐而深邃之把握。
虽然鲁迅对华惠尔论述不多,我们也不知道鲁迅有多全面地了解他的思想,但他的思想无疑是英国思想界神秘主义与科学唯物主义搏斗中一个重要的声音。华惠尔出生于1794年,卒于1866年,其父为一木匠,希望子承父业,但华惠尔天资聪颖,很早就在数学上显出过人天赋。后就学于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最主要的成就是系统地提出科学研究里的归纳法,并写成在当时极有影响的《归纳科学的历史》和《归纳科学的哲学》两书。这两部书的写作具有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且其为之奋斗的理念具有悖论性质。一方面华惠尔要为科学辩护,抵制来自教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证明科学不会破坏宗教信仰,以此来批判激进的科学派别,即当时流行的实用主义。这样华惠尔的思想便成为科学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奇怪的组合,这在当时颇有代表性。像丁达尔一样,华惠尔也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他的英雄是柯勒律治。
有件事情和我们理解鲁迅思想有关。一是他和穆勒发生的著名辩论。穆勒非常不喜欢华惠尔,认为他的自然哲学有很强的神秘主义成分。他称为直觉主义。所有的科学概念都依赖人的直觉来发现,而不是通过具体的观察实验。这就是华惠尔核心概念“悬拟”的哲学基础。直觉一直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知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依赖的是人的直觉。而人的直觉总能倾听一种神秘力量引导,去认识宇宙和谐的整体。穆勒对此深恶痛绝。他给自己设定的工作是找到不依赖任何超验的力量的知识确定性基础,为此他甚至反对从笛卡儿到胡塞尔所奠定的当代哲学基础,即通过数学肯定必然律的存在。穆勒走到了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道路上。他们两人的争论在维多利亚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12)。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鲁迅把脚站在华惠尔一边。现在不能确定鲁迅是否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争论,但鲁迅似乎一直对穆勒的实证主义兴趣寥寥。许多学者认为鲁迅“个人”的观念受到穆勒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影响,但我觉得此点还有必要认真研究,因为,穆勒学术思想的基调和早期鲁迅正好相反,是坚信迷信之于知识的虚妄性。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知识论。鲁迅反对华惠尔的厚今薄古,不恰当地要求古希腊人有现代人这样的科学思辨能力,但鲁迅没有否定“悬拟”这个概念。他对“悬拟”这个概念的哲学把握是通过赫胥黎的“divine afflatus”一词,鲁迅译为“圣觉”,并明确注说,“英之赫胥黎,则谓发见本于圣觉,不与人之能力相关;如是圣觉,即名曰真理发见者。有此觉而中才亦成宏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集。说亦至深切而可听也”。赫胥黎的这个观点调和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试图为人类的知识找到一个神秘的超理性的源泉。因此,赫胥黎总反驳他自己的批评者,说自己不是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13)。
实际上,鲁迅对这些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没有这个兴趣,就没有这篇文章的写作。同样的,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反思他在十多年后中国出现的科玄论战中保持沉默的原因。他的这个暧昧的态度是深有趣味的,但这不是本篇要研究的课题。其实对于鲁迅而言,科玄论战战幕早已提前拉开,他就是这台大戏的总导演,而且在规格上属于更高级别,这不是一场局限于人生观的争论,而是对现代文明兴衰的直接的问答。鲁迅预见的是一个大崩溃的时代的到来,所以他说,“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他为他的时代提出的思的问题就是寻求拯救的方案。科学技术并不能完全承担拯救的任务,因为精神元气颓靡不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功利主义和唯物学说取代信仰和弥思,腐蚀了现世的精神性之根基,而科学技术正是催生唯物主义的土壤。
在日留学期间,鲁迅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哲学思想冲突的关注可能比我们了解得还要深。他不仅知道阑喀的《唯物主义史》,还应该读过它。他还购买了德文版的毕希纳(F.K.C.L.Buchner)的《力量与物质》一书[3]。而毕希纳是被赫胥黎批评的庸俗唯物主义者(14)。我想,鲁迅是应该熟悉这两位之间的过节的。
我想,尽管鲁迅在文中表示了种种异议,他总体上是把这群英国科学家引为同志的。但他对他们的思想也有理解得模棱两可的地方。比如《科学史教篇》开篇一大段是对赫胥黎《科学之进步》的编译,一上来就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鲁迅的译文里,没有区分科学与技术这两个概念,鲁迅统统使用科学翻译原文远为复杂的陈述。简单说,原文刻意在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之间作了区分,这样,赫胥黎的政治诉求变得十分明晰,他呼吁的不是增加技术教育的投入,而是基础教育。显然这个区分对鲁迅的思路来说不重要。
第二个问题是鲁迅起笔就写出了“科学学者”三个字。当时也许“科学家”这个概念还未通行,所以鲁迅用“科学者”翻译英文“scientist”一词。但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科学之发展》一文中。也几乎没有被赫胥黎使用过。这里面有个故事不可不知。这个词的发明者不是别人正是华惠尔。在英文世界里,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等概念都已出现,唯独没有一个更一般的词来描述这些科学工作者的共性。当时学界还使用“自然哲学家”这么个词。大家都觉得自然哲学家不准确,所以华惠尔出面提出这个最后被广为接受的概念。然而初始时,许多人抵制这个概念,赫胥黎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里很少见到这个新的时髦术语(15)。
问题也许变得更有意思,如果我们问赫胥黎使用什么词呢?赫胥黎自己也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不可知论者”。这又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也许只知道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进化论的哈巴狗。也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赫胥黎还是一个宗教团体的积极成员。英国在1869至1880年间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知名的“形而上学俱乐部”(Metaphysical School),里面的成员都是当时闻名的知识界精英,有科学家、神学家和社会左翼人士。他们时常聚会,就社会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这个俱乐部共存在了11年(1869-1880)。当时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参加这个社团的活动,他们主要讨论的是涉及与神学有关的社会和思想话题。大家形成的基本倾向是类似泛神论的东西。但聚来聚去,这个团体不能给自己的信仰以一个恰当的命名。赫胥黎这时又以其才思敏捷来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提出的是不可知论者(agnostic)这个词。赫胥黎解释说,他发明的这个词是针对那些狂妄之徒,他们声称人类知识是没有局限的,世界一切都是可知的。这种愚蠢的自信是科学的敌人。我们只能说我们会知道越来越多,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全部(16)。
不可知论是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信仰。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鲁迅了解不了解这个思想?他所习惯的“归谬”思维逻辑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启发?在《野草》里,鲁迅常说,他什么也不能确定,连最终黑暗是否实有,也只能猜测,这种对经验知识的绝对怀疑却又不陷于虚无主义,是否也和他探讨英国科学普及派的科学信仰有关?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编辑)
注释:
①现在不太能确定这几部英文著作鲁迅是在日读的日文翻译呢,还是英文原文。作者曾向旅日学者李冬木先生求教此事,李先生答应去查看日本现代翻译史,以确定是否这些著作在鲁迅旅日期间已经翻译成日文了,但这项工作不能一下完成,故此文只用英文原书和鲁迅文章对读。以后等确定日文翻译情况后,就某些具体观点作进一步修正。好在就本题目来说,即研究维多利亚思想科玄论战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受鲁迅具体使用哪个文本的影响。
②参见鲁迅《科学史教篇》,见《鲁迅全集》第一卷,25页。以下凡引自《科学史教篇》原文不另注出处。
③华莱尔对赫胥黎、丁达尔等当时所谓自然科学主义派的成员影响深远。他的核心工作是批评欧洲机械论唯物主义,认为这窒息了欧洲思想的创造力,他批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缺乏想象力,批评实用主义,与此相对的是翻译介绍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文化,参见Frank Turner,Contesting Cultural Authority,Cambridge,1993年第五章“维多利亚科学自然主义和托马斯·卡莱尔”。
④分析华惠尔和康德哲学观点异同的文章及他是如何发展他的归纳哲学概念的可参见Gerd Buchdahl,"Deductivist Versus Inductivist Approach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 Illustrated by Some Controversies between Whewell and Mill,"收入Menachem Fisch and Simon Schaffer,William Whewell:A Composite Portrait,Clarendon Press:Oxford,1991.
⑤这里再次显现卡莱尔的影响。卡莱尔强调宗教精神与当代神学机构里的教义不一样。他赞扬前者保留人类对未知的惊奇感,这是探索自然的前提。丁达尔和赫胥黎都接受了这个观点,正因如此,科学、文学和宗教有了共同的基础。鲁迅深受此观念影响。
⑥鲁迅的伦理观实际上非常复杂,经常是以超伦理的形式出现,在许多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都是超越善恶原则的。这点需要特别注意。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的整体思路对青年鲁迅应该是影响很深的。
⑦参见傅柯名著《性史》。
⑧英国公共科学教育是一个被广泛研究课题,本文下面关于英国公共科学教育发展状况介绍主要来源于Frank Turner,Contesting Cultural Authority:Essays in Victorian Intellectual Life,Cambridge,1993年,第八章。历史文献可参见The Culture Demanded By Modern Life:A Series of Addresses and Argument On The Claim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edited by E.L Youmans,New York:1897.
⑨丁达尔的这本书是为了他接受美国知识界邀请于此年赴美前收集成书的,书中明确注明是献给他的美国友人。1872年美国之行奠定了他作为国际知识普及者的声誉,在此书前言,作者明确指出科学和民族兴盛的关系,这是最令鲁迅感兴趣的地方。丁达尔如此做,显然意识到了美国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准备以此来推销科学理念。具体详情见Katherine Russell Sopka,"John Tyndall:International Populariser of Science"收于W.H.Brock,N.D.McMillan and R.C.Mollan,John Tyndall Essays on a Natural Philosopher,Royal Dublin Society,1981.
⑩鲁迅在他早期论文里对卡莱尔充满礼赞,如在《摩罗诗力说》中也引用其观点。但以《科学史教篇》为最。可见他是了解丁达尔和赫胥黎对卡莱尔的推崇的。现在不清楚是否他也了解赫胥黎在《天演论》里的“伦理”观也深受卡莱尔影响?
(11)Tyndall,John,"Belfast Address",收入其Fragments of Science:A Series of Detached Essays,Addresses,and Reviews,New York:D.Appleton & Company,1897,Vol.2.下面多处这篇文章引文都出于此书。
(12)关于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各自双方的立场,请参见Laura J.Snyder,Reforming Philosophy:A Victorian Debate on Science and Socie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2006,特别是前言和第一章部分。
(13)赫胥黎在私人信件和公开文章里不断否定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见其“On the Physical Basis of Life”,收入其著Methods and Results,New York,1897,155页。
(14)参见Huxley’s "Science and Morals",收入其Evolution and Ethics:New York,1902,第129页。
(15)请参见Sydney Ross写的文章,介绍“科学家”这个词产生和接受的过程。赫胥黎讨厌这个词,主要他认为这个词太美国化了,这是当时英国学界的一种普遍看法。但他也曾一不留神在自己的书上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Scientist:The Story of a Word," in Annals of Science,Vol.18,No.2,June,1962,第65至85页。
(16)详情请参见Bernard Lightman,The Origins of Agnosticism:Victorian Unbelief 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第一章。
标签:鲁迅论文; 赫胥黎论文; 维多利亚时代论文; 科学史教篇论文; 英国工作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读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古希腊论文; 丁达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