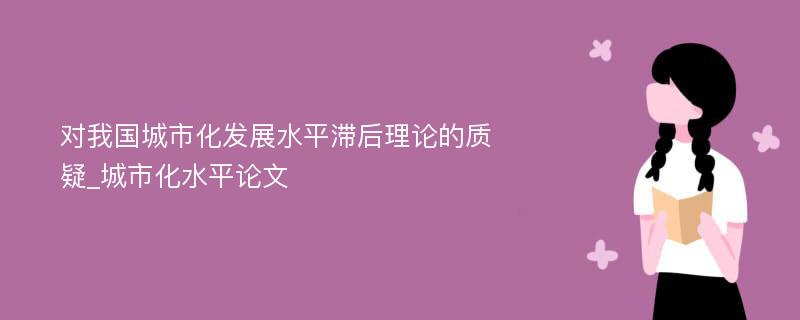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论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论的代表性观点及其主要依据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但在各种纷争的意见中,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滞后论成为主流意见(周一星,2001;钟水映,2002)。论证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学者主要是从三个角度展开的:
1.城市化与工业化、非农化联动发展的多国标准结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反差
首先,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转换问题。人们较多地引用钱纳里等学者的“多国模型”。基于1950-1970年间100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而建立的该模型,提供了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标准结构”,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关系方面,按照钱纳里模型,中国的经济发展从80年代的人均400多美元到2000年的800多美元,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49%-60%之间。而现实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0%左右,只相当于人均收入在200美元时的水平。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大大滞后了。其次,联合国曾经对世界上21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联动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化的水平也都有相应的提高。工业化的城市化弹性从1970年的1.8上升到1970年的1.7。中国的工业化在建国后的四五十年间里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工业化的城市化弹性却严重不足,大抵在1.0左右,有些年份甚至为零或负数,与世界各国的经验形成明显的反差(辜胜阻,1991;王桂新,1997)。再次,世界银行曾经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分别考察了亚洲20多个国家的情况,得出了U=0.52+1.882I(R=0.933)的模型。而中国的情况是,从1952年开始,截至1980年代末的模型是U=5.515+1.075I(R=0.679),截至1990年代中期的模型是U=10.9629+0.5789I(R=0.781),也同样表现出工业化的城市化弹性不足的特点。如果参照世界模型或亚洲模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大致要滞后10个百分点以上。
2.IU比和NU比的国际比较分析
人们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左右。如果IU比明显小于0.5,而NU比明显小于1.2,则说明不仅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人口也集中在城镇地区。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是超前发展了,会出现过度城镇化的态势。其表现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又无充足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过度膨胀的城镇会出现大量贫民窟等一系列城市病。相反,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而NU比明显大于1.2,则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这种情形说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了,会出现城镇化不足的态势。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NU比一直在1.5至1.6左右,IU比一直在0.8左右。这集中反映了我国在城乡壁垒的格局下,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非农化的进展而同步提高的实际情况。国家在改革之前是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甚至是城乡人口倒流(如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改革开放后,又是通过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试图用离土不离乡的独特发展模式解决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从而走出一条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和非农化的道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城市国有企业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增强了其竞争力,乡镇企业失去了市场和政策的竞争优势而显得后劲不足的时候,国家又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使得上亿的农民只能以非正式的身份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成为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城镇中生活,在城镇中生产经营,他们已经习惯于城镇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再回到农村重新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流动人口都是城镇市民中的一员。可是,由于户籍制度及相配套的其他政策的限制,这些人仍然被看成是农民。在现行的政策背景下,他们仍然不能跳出“农门”,实现身份的蜕变。由此,整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工业化和非农化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形下仍然显得步履蹒跚,进展不大,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镇化滞后的格局。按照IU比和NU比分别为0.5和1.2的一般水平,目前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应该在45%-50%之间,滞后达10多个百分点。
3.国内农村地区“隐性城市化”现象的分析
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问题时,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如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经典模型所描述的那样,随着中心城市工业建设的发展,出现大规模的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倒是乡村地区的非农业发展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职业转移。这种实现了劳动力产业转移但没有完成地域转移的人口,其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及居住点的形态上已经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城镇特性,只是由于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性限制,他们没有能够实现彻底的地域转移,其居住地在行政上仍然被称为乡村,这些人口仍然被统计为乡村人口。这种劳动力非农化加上一定程度的聚集性的人口过程,被称之为“隐性城市化”。它反映了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客观现实。有关学者采用特征比的方法,通过收入的非农率、平均一年从事非农业生产的时间、平均文化程度、平均每周闲暇活动时间、支出的购买率、逆恩格尔系数、10大类而用消费品相对拥有量、自来水普及率、煤气及液化气普及率、厕所普及率等10项特征指标,经过加权处理,定义出乡村区域非农劳动力的隐性城市化系数,最后通过隐性城市化系数测算出隐性城市化人口和隐性城市化水平。由于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较大,计算出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差异也较大。在较为发达的几个省份,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省,隐性城市化水平在20%以上。就全国而言,总体的隐性城市化水平也超过10%(王嗣均,1996)。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另一个侧面的描述和分析。
二、对三种评价方法的质疑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恰当把握
笔者认为,对比发达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及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发展现状,来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与潜力,固然可以在一些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但又很有可能失之于简单,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以上三种分析方法得出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结论,都存在着可商榷之处。
首先,拿不同时期、不同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互动历史资料,来说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固然没有问题,但套用其经验数据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方面,人均收入从400美元到800元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出现在100多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所谓多国模型中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料,也是30-50年前的。我们不考虑时空背景,仅仅从人均收入(而且是以汇率变化十分频繁的美元作为计量单位)这一指标,说明某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该在某个水平,就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今日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时的全球经济背景和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将直接影响到其工业化过程中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取舍。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巨额初始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外部渠道:一是通过殖民扩张,在殖民地进行掠夺,获取了巨额的扩张红利,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二是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速其原始积累的进程;三是引进外资。历史上,几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几乎都可以在上述三个方面找到佐证。以世界为(至少是本国和殖民地为主要)市场的工业化,使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自然有其独特的模式。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是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它们不可能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自己所用,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是它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他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是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使它们发展工业以带动城镇化。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常常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利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则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和NU比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份提高,IU比会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界一般水平,根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导致的后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绝大比例的国家,农民的工业消费品除了由城镇工业企业提供之外,相当大的比例是由农村地区非农企业自身提供的。这些分散在乡村发展的非农企业的存在,既有农村地区对其产品存在一定需求的客观原因,又因为它们有着自身的适应这种需求的优势。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较之其他国家要高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至于另辟蹊径,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它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依据所列的10大指标,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思路不能正确的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缺陷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按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中,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四普统计的城镇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简单地比照所谓国外模式和经验来把握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得出的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有这样一种倾向:不加深入分析,只从某一侧面出发,就大谈所谓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并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推动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仿佛在“严重滞后”的情形下,推进城镇化是轻而易举之事。可以预见,如果不对我国城镇化的真实发展水平与潜力做正确评估,就采取“跃进”的方式推进城镇化(这是我们多年来惯用的手段),很可能是,人为造出一些空壳城镇。这样非但不能提高城镇化的水平,反而可能打断城镇化的正常进程,欲速而不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借用国际经验和发展模式来评价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无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不协调的真正原因。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应该说它是由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而也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有别的特征,是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差的结果。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应该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的改善着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此就不涉及了。
〔收稿日期〕2002-10-08
标签:城市化水平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时政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