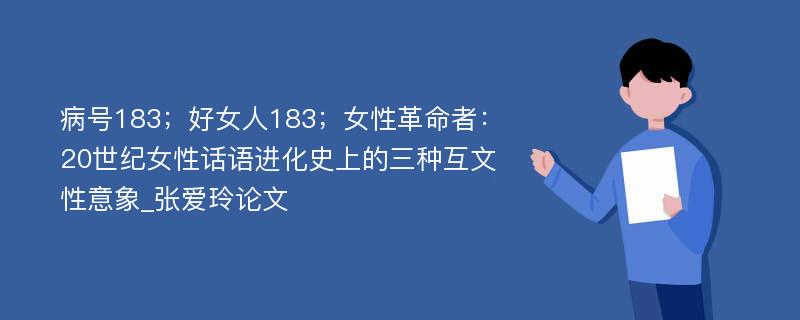
病女#183;良妇#183;女革命家——论20世纪女性话语流变史中的三个互文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家论文,话语论文,形象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9)06-0039-06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三个女性形象,分别问世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语境、人物的生存背景与作家的人生寄意当然各不相同。然而,若分析比较莎菲、白流苏和林道静三者思想行为的异同,便不难发现她们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话语流变史中承接、对应、比照的互文关系;同为离开闺阁的叛逆者,三位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分别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
一、从病女到良妇
在“五四”女性解放话语的起点上,丁玲给予后来者的勇气和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创作于1927年的莎菲形象是丁玲创作的起点,也可视作丁玲女性叛逆话语的顶点,她是作者朝气勃发的青春投射,满蓄着漫长历史进程中受抑制而累积的去旧迎新的激情,是个极端的叛女。
叛逆是莎菲性格与行为的标志,茅盾说她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1]她清高、孤傲而自尊,日记里她将整个世界视作她的敌人,个性主义与价值至上是支撑她的两块精神基石。相比父亲的疼爱、姐妹的欢笑和朋友的问候,她更渴望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沟通。莎菲从精神到言说都体现着对女性固有形象及现存秩序的嘲弄与否定,她正视并渴望情欲的满足,同时追求建立于自由、尊严和理解基础上的精神沟通,当她发现她所面对的是令人失望的男性群体时,莎菲便摆开了对男性社会居高临下的角斗姿势。“抑男扬女是丁玲早期小说创造无法自制的冲动”,[2]也是莎菲背离男性世界的极端话语符号。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3]莎菲的生理疾病、精神病态与社会病症被糅合于一体,丁玲将莎菲对社会的背离与反叛转化成一场关于肺病的生理斗争,疾病使人物性格的成因具备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也使莎菲与整个社会的不和谐、不合作与不妥协获得了叙述的可行性。肺病能促进情欲与精神亢奋,它既与莎菲谋求两性平等的情欲诉说相一致;同时又成为两性关系不正常社会病症的隐喻,莎菲的苦闷既是生理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尽管作者没有正面叙述社会环境对新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但读者始终与莎菲一起强烈感受到屋子、墙壁和天花板等压迫性形象,以及诸如“寒冷的冬天”、“刮风”等富有压抑意味的物质存在,小说从主观感受的角度,表明一个闺阁女子外立于社会时所承受的舆论控制力。
假如莎菲是无病的,假如莎菲留在大家庭里,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嫁给一个门第相当的男子,又将会如何?丁玲之后,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金锁记》等一系列小说告诉我们这些假设的真实答案,带着家族史的余痕,张爱玲为我们直面揭露传统社会上流家庭中残酷的闺阁黑幕,尽管七巧麻油店家女儿的低微出身不同于莎菲,然而,七巧的出身更容易、也更强烈地反衬出高门大户非人的人伦纲常。七巧固然不幸,相比七巧的试图反抗,三爷姜季泽门当户对的太太玳珍这样合乎规矩的少奶奶,则更显现出女奴般的麻木和呆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曹七巧与其妯娌们的人生之路,看到不得病、不离家、不死亡的莎菲的命运与出路。张爱玲曾谈及对“五四”一代女作家的看法,我们不能肯定张爱玲是否曾读过丁玲的“莎菲女士”,但从张爱玲回忆青少年时代和母亲一起阅读“五四”小说名作的情况看,①张爱玲的创作营养与思想背景里定有20年代女性话语的余音。深刻犀利的张爱玲独对丁玲有所肯定:“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②张爱玲所说的“力不从心”当然指的是丁玲未能将莎菲式的女权话语坚持到底,30年代初丁玲的创作急剧转向,未死的莎菲到40年代成了《在医院中》革命队伍里尽心尽职的陆霞,尽管个性难改,但女性苦闷已去大半,苦闷的内容也大相径庭,阶级斗争、国家革命等社会宏观命题掩盖了女性释放自我、追寻价值的性别命题。
如果说张爱玲《金锁记》的价值在于揭露过去之病痛、并表达女奴时代谢幕之希冀的话,那么《倾城之恋》表达的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书写文明真相的女作家对于“新女性”生存道路的务实解读与睿智预言,饱受争议的《倾城之恋》是张爱玲表达新女性观最直接最正面的一篇小说。它具有言情小说华丽甚至轻佻的外表,却又寄托着作者深刻的人生观与苍凉的历史感,对论者来说既充满阅读的乐趣又兼具批评的分歧与困难。③将白流苏与20年代的叛女莎菲联系起来看,同是由闺阁转型而来的新女性,她们之间的异同处都饶有意味。
两者的相似处不一而足,且略举一二。其一,流苏有和莎菲一样羸弱而病态的身体,有“娇小的身躯”“纤瘦的腰”和“半透明的青玉的脸色”,这些都是对传统女性弱者身份的疾病隐喻。其二,在19世纪以降中西文化碰撞的共同背景下,两篇小说的男主人公都具有南洋华侨的异域背景,《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凌吉士一样自私狡猾、世故风流、带着异域文化强大的冲击力,白流苏被范柳原激起性的烦躁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莎菲的情欲挣扎。其三,受新思想启蒙的流苏与莎菲一样选择了对男性世界、传统社会的反抗,先与丈夫离婚,后打算离家以三十岁残存的青春再搏一次人生。其四,流苏和莎菲一样渴望灵肉一致的爱情。在这一点上,读者往往误以为流苏再嫁不过只为物质的需要,但是,这样的说辞不过是以妥当的借口掩盖新女性思想的锋芒。假如流苏只求得到经济的安全,那么其前夫死后她听从兄嫂的安排回到夫家守寡继承遗产,经济上可更安全。之所以冒险上香港与范柳原周旋,其中包含着流苏思想中觉醒了的个体意识与女权思想,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镜子前的舞步”交代她从此将“忠孝节义”丢在一边的心理流程与思想转折,为满足自身从物质、情欲到精神的多重需要,她不惜大胆冒犯传统妇德。与倔强倨傲的莎菲相比,表面上,流苏是带着中国情调的、温良恭顺的传统女性,其人生追求不过是走做稳家庭良妇的老路,很像冰心笔下隐忍牺牲、崇高伟大的地母型女性,流苏的思想实质其实完全与此无干,流苏是个勇敢的彻底的个人反抗者,她抢了妹妹的相亲对象,盘算自己仅有的一点身份与青春资本与范柳原周旋,准备以再嫁的实绩出一口恶气,个人主义者的叛逆道路上流苏完全是莎菲的延续。
然而,流苏与莎菲毕竟是不同的,经济之忧患与亲情之匮乏是流苏与莎菲处境的最大差别,金钱社会的生存法则教会了流苏生活的经济学,同是离家出走,但是叛逆的目的、方式与归宿都截然不同,莎菲是未经世事的浪漫女孩,流苏则是在生活里滚爬过的世俗女人,莎菲有疼爱她的父亲,流苏的母亲是个空洞的符号,在家庭环境的压力与微妙的经济关系中,流苏连母亲这个最后的亲情庇护者也失去了。莎菲衣食无忧,而流苏寄居的娘家则是个充满穷酸气、又死撑臭架子的破落户,妯娌、兄弟与姐妹们为了蝇头小利而钩心斗角、互设陷阱。总体来看,流苏的背后是一个经济力量与伦理关系都处于倒塌溃败中的现实社会,她只能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寻找最佳生存方式,尽管流苏有勇气与浪荡前夫离婚,但最终却只能屈服于衣食住行、家长里短的生活铁律,“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4]对于南洋浪子,莎菲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嘲弄、鄙视凌吉士,流苏却只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费尽心机做成范太太,生活的重压像一只狼尾随着流苏,准备时刻扑灭她一星半点的精神希冀与价值追求,台面上罗曼蒂克的情感不断为生存底子里的琐屑所破坏和瓦解。
疾病限定了莎菲狭小的生存空间,但流苏本该是与之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相当广泛的社交圈,流苏的足迹已经从上海延伸到香港,她本该可以、也本该追求一番自己的作为,然而离开名门望族女奴之地的流苏,苍蝇似的转了个圈选择的依旧是“女结婚员”的小天地。既然输在经济之患,有知识有能力的流苏为何不转向社会谋求经济自立?事实上,流苏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第一次从香港惨败而归、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流苏曾想找个工作赖以糊口,但在当时舆论环境中,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两个身份并不相融;而且,即便流苏愿意放下大家闺秀身份独立谋生,社会也未见得能提供给她自食其力的岗位,无怪乎徐太太说:“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兜了个圈,依旧是依附于男人托付终身,这样的选择是历史与现实对女人反复教谕的经验总结,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症结由此清晰可见。莎菲志在“建立一个能自立于家庭主义网络之外的女性形象”,[5]流苏则将莎菲从云端拉回充满铜臭味与自私心的人间,以改头换面的新观念重回家庭,在良妇的伪装面目下打着个人主义者的算盘,做着个人主义者的美梦。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与丁玲的女性话语的巨大分野,两相比较,张爱玲的女权话语也许不如丁玲干脆勇敢,然而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人性关怀却比丁玲的情绪化姿态多了一份切实与中肯。
二、从良妇到女革命家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起点是从白流苏的终点开始的,白流苏的全部故事只是林道静前半段的演绎,良妇再次走出家门,成了追求自我、胸怀天下的女革命家林道静。问世于50年代的《青春之歌》虽因创作背景之故而带有强烈的革命史教育意味,然而,女作家真切的生命体验使小说的女性命题隐含地保存下来,时代背景尽管不同,但不同于过往的生活内容却显示出两性冲突的普遍性与难以割断的历史沿承。
林道静与白流苏具有相似的家庭基础与人生起点,都有缺席的母亲和荒唐的父亲,流苏的母亲是个卧病在床的糊涂弱者,林道静的母亲则是受其父亲诱奸的被侮辱者、并已早早去世,在男权社会中林道静与白流苏一样失去了母亲这一最后的亲情依靠;都有一个领着全家往破落户路上走的荒唐放荡的父亲,为女儿在金钱交易中被当作筹码埋下祸根;林、白两家都是经济日渐衰败的破落户,金钱社会中破落户较之一般穷人所遭遇的钱财威胁更为刺骨强烈,于是金钱的诱惑也更有可能吞噬了基本的人伦情感。在经济之逼迫与亲情之刺激下离家出走,从大家闺秀变成社会浪女,林道静与白流苏叛逆的现实动因几乎完全一致;林道静离开余永泽的动因中,也隐约地包含了经济窘迫所产生的自立愿望,林道静和白流苏一样经历过世事人情的教训和磨难。
然而,林道静与白流苏的个性又存在巨大差异,白流苏虽为个性思想所启蒙,但上海商业社会的成长背景养成了她温顺而长于心计的性格;与之相比,北京落败家庭中的林道静则更多了一份燕赵女子的豪爽之气,兼具勇敢与细腻的双性气质。走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始终带着这种双性气质的人格魅力,既如茅盾《蚀》中静女士般的细腻犹豫与多愁善感,又如慧女士般“仿佛在天性上就和革命有着某种亲合力”。[6]平静安稳的世俗生活是白流苏追求的终点,但林道静的人生显然绝不愿仅停留于此。这表现为两人家庭婚姻观的本质差异,林道静和白流苏一样有了一间独立生活的公寓房子,白流苏安心地留了下来,林道静却很快离弃了它,她下定决心拎起行李、很快就离开了那个“给了她幸福又使她无限痛苦的公寓房间”。
公平地说,是林道静抛弃了深爱她的余永泽,《青春之歌》将“弃妇”置换成了“弃夫”,这完全改写了中国文学中“女遭男弃”的叙事模式。林余的家庭生活平淡拮据却不乏温馨甜蜜,余永泽爱林道静,注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注重家庭营建和夫妻情感,努力以埋首学问和个人奋斗为林道静创造幸福生活,他为林道静受卢嘉川吸引可能离他而去的担心让读者不无同情。林余二人的矛盾来自于是否参与社会革命这一进步或落后的时代选择,倒不如说两性永恒的角色、地位与价值冲突是导致其关系解体的主因。当林道静以高傲的目光审视“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余永泽时,我们不难看出林道静与莎菲之间的精神贯通,莎菲嘲弄并拒绝凌吉士那“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和“几个穿得很标志的白胖儿子”的平庸观念。林道静与莎菲一样让男人吃惊和害怕,她们以自身的言说和行动追求着精神自由与价值独立。尽管孕育林道静的50年代文学语境与产生莎菲的20年代大为不同,然而,作者的文学营养和思想背景具有内在的历史继承性,杨沫的创作依旧处于“五四”文化的精神辐射圈中。杨沫谈《青春之歌》的创作心态时说:“受了18世纪欧洲文艺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也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要婚姻自主。”[7]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大量长篇小说中,《青春之歌》是唯一一部讲述知识女性成长史和心灵史的典型文本,尽管烙刻着浓重的时代印痕,但小说以超时代的视野探讨了“五四”以来女性解放话语的新命题与新出路。
林道静的生命中先后出现了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三个男性,其中卢嘉川对林道静的人生意义最为重大。将林道静弃余投卢的“情变”仅仅看成、或主要看成是一次政治上的弃暗投明是不够客观的,因为,共产党人卢嘉川的出现并非导致林道静离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的根本原因,早在接受卢嘉川的革命启蒙之前,林道静与余永泽之间早已危机四伏。林道静从未安心于平静安宁的家庭主妇生活,当余永泽埋头学问时她始终难以平衡自身的失落感,她问余永泽“你是大学生,有书读,有事做。可是,我,我这样的算个什么呢?”于是,她四处求职却四处碰壁,连余永泽都感觉她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马,林道静不能接受余永泽所设想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不乐意接受余永泽为她设计的缝补浆洗、生儿育女的主妇生活,也不乐于依靠余永泽的升迁以夫贵妻荣,她的目标是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这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蜗居于此只是暂时的无奈之举,一旦机会来临林道静就会离开小公寓、就会跑到广阔的社会天地中去。自由独立既是林道静拒绝花瓶道路的思想利器,也是她拒绝做妇人转向革命人的思想,两次选择在思想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白流苏的背后是一个经济力量与伦理关系都在溃败衰退的社会,林道静的背后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革命时代,个体永远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的时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被时代所劫持。卢嘉川之于林道静来说,是一个可以带她脱离和超越当时的烦闷日常生活的男性,这个男性是个共产党员,可说是大时代使然,即便没有卢嘉川,也会有张嘉川或李嘉川带她离开,这也可说是大时代使然,这个背景对白流苏来说是不存在的。换个角度看,林道静这样的“英雄”其实说到底不过是负荷沉重时代的“凡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8]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预设的规范,林道静尽管在自己的范围内挣扎,但也终究挣扎不到时代的圈子外去,她最终选择的白马王子是个共产党员,这是时代的预设。我们大可不该将林道静绑定在宏观的政治意图上,认定她孜孜追求的就是党员伴侣所代表的正确政治归宿,其实没有那么“纯粹”的英雄,生活本身是暧昧而复杂的,女性的解放道路本身是含混的。即便我们承认林道静与卢嘉川一起生活同样要面对性别冲突,但在追求女性本体的道路上,林道静离开余永泽的意义已足够明显了。刘慧英论述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时,将“女性对男性物质和精神依附的才子佳人程式”与“对女性自我回避和否定的社会解放程式”都视为“空洞化的女性模式”,[9]以此来看,林道静的离家是对“佳人才子”命定道路的反叛,它向读者显示和提供了一种新取向,走出家门的知识女性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以独立姿态与恋人并肩站立并共同战斗。
三、女奴终结以后怎样:白流苏与林道静的两条路
上溯去看,白流苏、林道静的叛逆思想与莎菲一脉相承,丁玲后来追述20年代的苦闷时说,“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既有“极端的反叛情绪”和“盲目的社会革命倾向”,却又因“对社会的鄙视而产生的疏远和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10]前者演化成了杨沫笔下在苦闷中投身革命的林道静,后者则演化成张爱玲笔下躲进小楼成一统、满腹心计谋平生的白流苏。白流苏与林道静分别显示了女奴时代终结以后女性道路的两种基本方式,这两种方式显示了豁达与郑重、斗争与和谐、飞扬与安稳等人生之两面,相互区别、彼此印证又互留退路。
白流苏的人生表面是良妇“就近的平安”,背后则是历史洞见者“苍凉的虚无”。这种女性观和命运感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她直接表达过,“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遍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11]白流苏的庸俗故事背后是透彻的人生观、广阔的历史观和荒凉的文明感,男女两性的矛盾并不仅在于性别角色的冲突,而是包含了文化、身份、财产、地位等种种人类文明的积累,历史沉积在两性关系中成了一堵“厚障壁”。《倾城之恋》将“厚障壁”具象为浅水湾的“一堵墙”,后来果然以近乎神话传奇的方式应验,于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将一切打乱重新再来,“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与张爱玲相比,杨沫的女性观超越世俗,却包含着与世俗生活无法割裂的切实联系,林道静的人生表面是国家革命和牺牲斗争,但其生活底子依旧不脱凡俗人生的诸种规定。林道静一波三折的情感历程和价值追求过程中,“如果说余永泽给林道静的是‘家’,卢嘉川给她的是献身和冒险,而随后出现的江华则将两者完整地结合了起来”。[12]当她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心中想着卢嘉川忘我地工作时,食不果腹、断炊、典当度日的艰难生活让她不堪其忧,江华在这时适时出现,他给林道静带来的不仅是思想指引更有生活照顾,有个细节真实可靠而暖人心脾,两人在岔路口分手时江华将身上仅有的钱全都拿出来给林而林则毫不犹豫地接过来,理想的激情加上踏实的生活,一对有理想的普通男女,杨沫在江华身上寄放了女性爱情的终极归宿和理想家园。
诚然,安稳的世俗生活常常是“不完全的”,白流苏虽然得到了范太太的地位和范柳原的真心,可还是感到人生的惆怅,因为现在“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飞扬的社会斗争中又带着两性关系中先天的历史承袭和世俗安稳被破坏的缺憾,尽管林道静在生活伴侣兼革命引路人江华的指引下实现了职业革命家的壮阔人生,但在成熟稳健的江华面前,她依旧是第二性的,是受启蒙与帮助的被动者,不仅失去了与卢嘉川那样的灵魂相应和价值对等,甚至也失去了与余永泽那时斗嘴闹气的权利,可见性别问题并不能在民族意识或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顺带着轻易解决。莎菲如果不病不死,她终究也许还是要革命斗争的。“莎菲的空虚和绝望,恰好在客观上证明了她的恋爱理想固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却并没有拥有时代的前进的力量,而她更不能依靠这样的一种热力当作一种桥梁,跑到前进的社会中去,使自己得到生活的光和力”。[13]对比来看,林道静在时代的搏击中克服了空虚和绝望,她是健康地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莎菲。白流苏大抵永远都成不了林道静,但良妇需要女革命家,林道静们可以唤醒白流苏们对不合理生活的认识,并为她们谋求安稳人生的环境与制度保障;而革命后的林道静们也依旧断不了莎菲、白流苏那样对白马王子的追寻之梦。叛女、良妇和女革命家,莎菲、白流苏和林道静,这20世纪女性话语流变史中的三个典型形象在关于女性生存道路的命题中相互区别、互相补充又彼此印证。
注释:
①张爱玲在《私语》一文中回忆说母亲订有《小说月报》(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由此可见“五四”文学与张爱玲创作内在深刻的精神联系。
②文中所引这句话是张爱玲在1943年3月16日《杂志》月刊召开的女作家座谈会上所说,后收在篇名为《女作家座谈会》的座谈会纪要中(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在另一篇文章《我看苏青》(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中,张爱玲曾表明她对“五四”女作家的看法。
③很多论者注意到这篇小说的重要性,但《倾城之恋》没有《金锁记》那样一目了然的批判主题,因此评论者往往对《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的价值评价分歧甚大。参考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与谭正璧《论张爱玲与苏青》两文(见《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