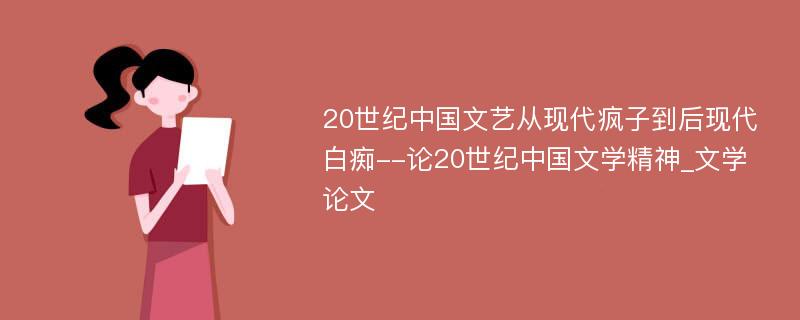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 从现代狂人到后现代白痴——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后现代论文,狂人论文,中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发端,大批狂人性的文学现象迅即占领文坛,从而开始了暴风骤雨般令人心神俱栗的20世纪文学旅程;当20世纪的黄昏降临,狂人纷纷老去,白痴一一安居主流,丙崽和他的兄弟们在文坛上招摇过市,形成了引人侧目的文学现象。从世纪初鲁迅、郭沫若、高长虹笔下的狂人到世纪末韩少功、余华、苏童手中的白痴,20世纪文学精神显然发生了某些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转折蕴含着什么?预示着什么?代表着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性话语蜂拥而至,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之深思。本文就此展开议题,并试图有所回答。
现代狂人的“现代性”伊底情结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20世纪文学中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以对人吃人现象的发现,对吃人历史的概括、救救孩子的凄厉呼声以及狂放的反抗/叛逆意识而著称。《狂人日记》后,鲁迅又在“长明灯”中塑造了第二个狂人形象。这两个狂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思想型狂人,以大无畏的勇气斩断任何传统脐带,彻底孤立和放逐自己于精神飘流状态;后者是行动型狂人,以拚死的决心搅乱现存秩序,不惜将自我置于看客的白眼包围中,作基督式献祭。魏连芟、吕纬甫是第一类狂人的灰颓,阿Q则是第二类狂人的拓展。与鲁迅的写实性狂人不同,郭沫若更多是诗性狂人,《女神》第二辑以笔走龙蛇的狂人气概喊出了时代强音,抒发了世纪初文化巨人和国民面对新世纪的满怀狂喜和气吞山河的胸襟。“凤凰涅盘”“天狗”“匪徒颂”“巨炝之教训”“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以满篇的狂人气质,诅咒和破坏旧物,呼唤创造精神,极为夸大自我欲爆裂的心灵力量,蔑视一切传统权威和偶像。高长虹则在“狂飚之歌”中直抒狂人胸臆。“朋友!你们将要笑我狂吗?庸人其所不知,则谓之狂热,你们真是庸人啊!我最大的希求,便是远离你们而达于狂人之胜境。无广大之灵魂者,必为狂人之所以摒弃,我将使你们于被摒弃之羞辱中,而得卑下的自欺的自慰”。鲁迅、郭沫若、高长虹的狂人写作,完整地勾勒了世纪初狂人的历史意识、现实观念和主体态度,它向我们表明,世纪初的确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了狂人的伟大时代。
问题是,缘何世纪初文学精神会以狂人形象作代表?最直观的原因也许是尼采活力论哲学和超人思想在本世纪初的广泛流传与接受。关于尼采给鲁迅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尼采无畏的悲怆、对一切古老和垂死之物必然毁灭的冷酷重申,对勇敢和幻想之力的强调,对超人精神的赞叹都给鲁迅的思考方式以最大的推动力。鲁迅《野草》中孤绝的个体就留有深深的尼采风。郭沫若供认表现主义作家妥勒的《转变》、凯若尔的《加勒市民》是他最欣赏的作品。而表现主义研究者弗内斯指出,任何表现主义思想都是源于尼采对自我意识,自主和热烈的自我完善的强调。高长虹的狂飚宣言则无论从形式文体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拟尼采式的,充满超人式情绪,尤其是那种高人一等、睥睨一切、彻底沉入自我得救狂喜的情绪更直接是尼采哲学的挪用。
将视野放宽,我们又会发现,狂人出现不仅是因为尼采,更是西方20世纪初年狂盛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我国知识分子冲击的结果。现代主义研究者欧文·豪指出,要为现代主义下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充满一切的否定词”。他写道,现代主义“存在于对流行方式的反叛之中,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弱的愤怒攻击”。欧文·豪的这种现代主义指认基本上符合世纪初狂人对于现代主义精神的接受视野。狂人正是在现代主义反叛中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依据,从而坚定地反叛一切历史理性和工具理性体系。
不过,用尼采和现代主义解释狂人的出现,仍嫌浅陋,因为狂人并不单纯是一个西方文化的投影,它富含更多本土内容,带有更多揭示本土世纪初文化本质的深邃思想。而要回答、认识狂人的这种深层文化心理,我们必须把狂人放到1840——1919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本土现代化历史中加以考察。
1840——1919年是本土文化理性精神发生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包括洋务运动、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三个阶段性发展成果。
尽管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运动,但它作为第一个认识到天朝神话体系破灭并开始承认本土乃第三世界弱国从而亟须学习西方的文化群体运动,因而是本土文化理性转型发展不可忽视的起点。洋务运动为第三世界精神观念提供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即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但洋务运动的第三世界现代化话题主要是一个追慕西方16——18世纪工业化成功先例的单纯物质现代化运动,它片面地将第三世界现代化奠定在物质的层面,而非全面的物质/意识层次,因此,洋务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现代理性深度参与下的物质运动。
严复、康有力、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继承了洋务运动的现代指向性,却将现代化的主题意指由物质的尺度转化成了精神的尺度,即他们普遍将第三世界弱国的观念认同为意识/心灵现实,从而以为本土急迫现代化的形象不是科学技术的推进而是国民精神、思想和心灵的改造。在此前提下,启蒙知识分子将本土现代化革命改写成本土现代性追求,现代性作为一个精神概念主要指用西方古典理性、社会进化观、民权论、开明专制政治论对本土进行智慧启蒙,因此,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成果大致有三:一是用进化的观点指出传统性必须让位于现代性,传统必须发生创造性转换;二是发现了国民性弱点,指斥传统文化的奴隶性、愚昧性、自私性、虚伪性、怯懦性和保守性是本土现代性的死敌;三是以现代性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梁启超指出中国世道人心的败坏,与儒家学说千年正统关系莫大,“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强一国之思想,使出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他号召用公德、国家、进取、权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等一系列现代性观念改造旧道德、旧文化,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现代化的新国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立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为世界之民而非陬俗之民”。
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话题显然为五四知识分子继承并加以深化,他们以对现代性的极端崇扬和对传统文明的彻底批判而成为20世纪初年的文化群体。陈独秀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断言:“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改变而趋觉性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甚至说出“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这样失去理性的狂言。概而言之,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观念乃以19世纪后期激进主义文化为底蕴的西方文化之横移,五四知识分子完全将现代性看成是本土摆脱落后处境的唯一方法。现代狂人正是在此种广阔的现代性思潮中降生的文化典范。
至此,我们也许就清楚了现代狂人缘何产生在20世纪初年的文化宗因以及狂人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动向了。现代狂人是1840年以来本土知识分子漫长现代性思考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代表着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本土沦丧处境深刻关怀之下的愤懑情绪,它是知识分子现代性的独白与写照,狂人曰:“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每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的这番独语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与现代思考的最核心观念,它既是狂人产生的基础也是狂人所致力摧毁的对象。
但是,上述现代性追溯仍只解决了狂人的主体建构过程,而未揭示出狂人的“狂性”渊源,为何现代知识分子独独选择狂人作现代性思考载体而不是神人、超人、疯子、英雄?狂人之狂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评价?从鲁迅的狂人形象言说,狂人之所以只能成为狂人,一方面揭示出传统文化思维及存在的强大,本土现代性代言人只能被逼入狂,以狂人狂语狂态超常反叛;另一方面则揭示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现代性是必须进行的革命活动,没有现代性输入,本土无以建设;但现代性又意味着承认殖民主义的若干文化逻辑,意味着取消本土文化之根,变成西崽,假洋鬼子。因此,本土知识者在20世纪初年陷入从现实理性层面反抗西方,从文化理性层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绝境。狂人正是这样一个自我矛盾分裂主体的真实写照。鲁迅的伟大亦正在于他坚持这种狂人心态的分裂与矛盾路线,从生到死都体现着知识分子良心磨难的存在状况。但对大多数人而言,现代狂人的现代性困境显然不能坚持多久,于是,一旦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风潮一来,狂人便纷纷抛弃1840年以来的本土/西方、反抗/认同、传统/现代诸知识困境,而转化成一些行动型革命者,这群癫狂的革命者我们在蒋光赤、殷夫、胡也频、叶紫、茅盾等左翼作家笔下可以一再读到。
革命战士:现代性的新载体
与狂人知识分子抛弃1840年以来的现代性困境的同时,一个新的现代性载体于20世纪2、30年代颓败的第三世界土地中生长出来,它们就是被现、当代文学所崇尚的纯洁的革命战士。这些纯洁的革命战士前身是中古文人笔下的农人、沈从文,废名笔下的野蛮强力者,逸世者、小国寡民状态中讨生活的山人以及叶紫、茅盾、丁玲、叶圣陶笔下的受压者、戴毡帽的朋友、反抗者、小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期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继起的毛泽东一代政治型知识分子将这些纯洁的人群充分现代化,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极富现代思想特征的意识形态化体系武装他们,使他们成为一群现代性的新载体。革命战士在解决知识分子现代性困境方面是有效的。因为,第一,他是坚决反西方的,它对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掠夺性深恶痛绝,它的纯洁性就是他和西方分道扬镳的证明;第二,它是坚决反传统的,毛泽东的四大绳索论坚决砸碎了套在革命战士头上的传统锁链。革命战士在传统与西方双重文化理性空缺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地上的现代性王国。这个王国49年以前是解放区,49年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充分表达了解放区现代性的成功喜悦。
人民共和国从载体的角度解决了1840年以来本土现代性的困境,使现代性话语成功地进入意识形态主流。尽管共和国在现代性思想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的途程中历经曲折,50年代末,70年代初,每次提出的现代化设计都遭到阻挠和失败,但共和国作为现代性的追求结局显然使现代性经典化、意识形态化了,因而,一旦改革开放时期降临,现代化就成为8、90年代不容置疑的主流话语背景。
共和国现代性的精神特色是什么?我们以为主要就是由革命战士所体现的申扬个人生命意识的英雄精神。正如第一位现代人浮士德所说,现代人要得到的就是用“神圣的知识‘来’证明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现代狂人绝不承认自己是“虫豸的亲戚”,作为这一狂人启蒙的结果,革命战士以英雄性在20世纪占有突出的地位。革命战士个人被认为是独一无二,有着非凡抱负,而生命变得更加神圣更加宝贵了的一种人。因此,写革命战士、塑造革命战士英雄业绩本身即成为一项富有现代性价值的工作,革命战士所确立的英雄精神构成了一种普遍观念的基础,即人能超越必然,不再为自然所限,并最终在历史的终点达到完全自由的王国。总之,革命战士最深刻的本质即为现代理性所揭示的人类中心主义奥秘,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他知道死亡是必至的,但它拒绝这一事实,拒绝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浮士德式扩张,革命战士身上的这种浮士德/现代性根底使他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革命战士的现代精神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50——70年代盛行的唯意志主义,在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表现是永远斗争、永远运动、永远追寻精神极点的狂热行动主义,在文化意识理性层面的表现是浮士德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梁生宝、刘雨生、王金生、朱老忠、萧长春、李有才、雷锋、王杰、邱少云这些文本英雄都是革命战士现代性写作的经典标志。
但人们面对由现代狂人和革命战士所代表的两种现代性载体时,常常偏向以为现代狂人才是现代性的真谛。故而7、80年代的当代文学在自己的时代重提狂人现代性写作,而对革命战士所代表的现代性内容完全忽略。其实这既是对现代性本义认识的偏颇,也是对狂人现代性思考的短视。现代性在本土的运动其实从来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知识理性形式,一是行动救世形式。在康梁变法的同时有义和团运动,在五四新文化的同时有工农革命运动,就是在7、80年代重提五四精神时,亦有农村/城市的经济改革运动,两种现代性形式——主流——民间——文化——行动双向地存在着,忽视任何一方或侧重任何一方都是对现代性认识的不完善,回顾西方现代性发展历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浮士德狂飚突进知识路线之外,尚有一个意大利经济——英法资本主义经济——欧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发展脉落,而知识型现代性最终亦需落实到现实型现代性国家建立的终点上。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本应是一个总结现代狂人、革命战士现代性双重偏颇的结合创造期,但由于此期认识上的迷误、重返五四、对现代狂人的反传统失误认识不足,终造成此期现代性追求演变为西化激进主义,他们把西方现、当代文化当作经典,一再戏拟、摹仿、借用,使狂人对于民族在西化现代性追求下的民族危机紧张感消失得一干二净,现代狂人变成了刘索拉、徐星笔下佯狂的空心人。他们为狂而狂,落入狂傲末流,到头来,谁也没有救下,反落个自己落荒而逃的结局。
将现代狂人、革命战士看作现代性两种不同形式的承担人,那么,我们会看到,革命战士其实是现代狂人的转型的继续,因为现代狂人纠正现代性困境的手法是对劳工表示崇敬。五四知识分子高呼劳工神圣,以半工半读自己养活自己为荣,鲁迅面对人力车夫的自惭,瞿秋白以“忏悔的贵族”自况……都向我们表明现代狂人越来越看清用西化的现代性启蒙本土是一桩永不可成功的宏伟叙事,是一桩加深本土沦丧的殖民工作,知识分子必须把现代性的实现主体让给来自本土代表本土的劳工/革命战士去承担,只有这群神圣的劳工/革命战士才能在反西方的基础上实现本土真正的现代性。也就是说,5、60年代知识分子的歌颂与忏悔行动源自一种真诚的本土现代性自救信念,来自一种对于本土现代性未来的深切依恋,没有这份真诚与期盼,就不可能有共和国时代那种全民上下、齐心协力大干社会主义的兴旺景象,就不可能有小说、诗歌、戏剧中那么多热情的爽朗、天真、纯洁的话语出现,完全以政治畸形对待之,显然否定的不仅是一时代的政治、更是本土现代性追求的合理化思想与焦渴心情。
后现代白痴:现代性的终结
80年代中期——确切说是寻根派出现的1985年是20世纪本土文学精神发生变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本土文学开始不注重现代性话题,而通过白痴形象将现代性话语一笔勾销,文学进入后现代时期。也就是说,白痴的存在本质就是指向现代性的终结这一话题的,白痴是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在本土运动发展的一个总评价。从西方文学的角度看,《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百年孤独》中的白痴典型代表着后现代精神世界特征:分裂的、现实的、零散的、偶然的、非理性的、非结构的、多重复制的……,从本土文学看,白痴写作从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开始,就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白痴性团队,这其中尤以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苏童贡献甚多。狗崽(《1934年的逃亡》),么叔(《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萧(《迷舟》)“我”(《褐色鸟群》)、司机、梅生婆、瞎子(《世事如烟》)、疯子(《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冯金山(《风琴》)山峰、山岗(《现实一种》)……我们几乎可以把先锋作家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定位于“白痴性人物”,这种归纳也许过泛,却极为恰当。现代汉语词典中的“白痴”定义如此:白痴、病,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轻者语言机能不健全,重者不能料理自己的饮食起居。将这个定义的表象叙述转化为概念性精神语词,白痴大致包括如下特征: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化、无深度性、卑琐性、不可表现性、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参与、构成主义、内在性、无我性、非同一性、被动性、冷漠性、游戏性……用这些白痴精神标准衡量先锋乃至此写实文本,其文学人物无一不是白痴化的。过多的原文引述没有必要,仅以余华《现实一种》中的片断场景为据“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山岗看着儿子象一块布一样飞起来,然后迅速地摔在了地上……那一刻里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而她抬起头来所看到的已是儿子挣扎后四肢舒展开来,象她的胃一样,这情景使她迷惑不解,她望着儿子发怔。儿子头部的血这时候慢慢流出来了。那血看去象红墨水。”人们一般以此论证余华的冷漠视角与态度。其实冷漠蕴含一种讽刺,而余华一点也没有,他只是在叙述白痴化的人物行为,这个行为就只是一些单纯的行为,残酷中亦有白痴式的美丽。
在我们看来,白痴作为现代性的终结,并非西方后现代文化启蒙的结果,尽管媒介文化已为第三世界本土塑造了一个类似发达社会的文化“拟态环境”,使第三世界仿佛已在信息共享、消费共享、未来空间共享的层面上达到了与西方共享文化资源的幻觉,但其实,拟态环境仍只是在虚假的影像上使本土和西方共存,而在心态、生存状况等实质性问题上仍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相距遥远。因此,本土的后现代白痴仍是本土现代性历史及现实文化的双重逻辑结果,本土后现代和西方后现代是在不同本质上的“共鸣”。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的终结与现代新文人对现代狂人的消解有相当紧密的关系。传统古典文人经明末狂禅和清代考据词章,生命力到1840年已经丧失,随之产生的现代新文人经过1840——1919年的酝酿发展,20世纪初期显露端倪,20世纪中期形成高潮。现代新文人的知识路线大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新儒家知识路线,主观现代性必须是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一是新古典知识路线,以西方古典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为思想纲领,坚持人性、人道救世的主张;一是新隐士知识路线,从生命有机主义角度出发,提倡保守文化本土纯洁性的观点。总结现代新文人三种知识路线,其内在的现代性核心是渐进主义/改良主义的方式,反对现代狂人的激进主义/暴力主义手段,认为现代狂人的知识路线很容易堕入彻底反传统,亲西方的路线中去。现代新文人通过他们顽固的抵抗,在20世纪历史中建立了一个现代性不可忽视的对立营垒,从而以一种潜对话的方式解构现代性。
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性的终结与本土化运动密切相关,而本土化写作高潮的到来又与现代新文人传统于80年代中期后的复活有相应关系。显而易见,新儒家思想在此期的兴旺,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写中国人日常生活状态的闲适小品文的流行,学院派教授/文人重倡的人文精神等文化事实均告诉我们,现代新文人传统于8、90年代复活了,现代新文人传统以复活直接给反现代性的话语提供了知识文化背景。与新文人传统复活相关,本土化作为现代性的对立写作开始出现并盛行于世。寻根派的本土区域文化写作;莫言、马原、洪峰的本土视野神奇文化写作;刘惠云池莉方方的本土世俗生活文化写作;陈忠实、唐浩民、高建群的本土德性人格文化写作;张承志、张炜的本土生命精神文化写作……都向我们表明,本土化观念已取代现代性而成为当今文化的焦点,人们开始普遍抛弃现代狂人、革命战士的现代性启蒙救世观念,而立足本土生存、放眼本土生活、研究本土生命,刻画一个毫无外来文化视角干扰的纯粹本土主体形象。
通过历史和现实层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后现代白痴其实是本土化文学运动中出现的非现代性形象,它的“痴”是对现代性话语的“悬搁”,是对现代性中西化倾向的拒绝,是对本土生存状态的总结。“痴”是一种空白,但这个空白绝对不是人的生存、生命、追求、理想、理性的空白,即它并不是非人的,而只是它抛弃了20世纪所形成的理代理性释义生活的方式方法,抛弃了西方理性的手段形式,用本土的观念写作人、写作生活,它的痴是西方之痴,本土之智。
从后现代白痴的生存状况来看,无论他所生活的家族、乡村外在环境怎样,他无一例外地都卷入了暴力、宿命的生活中不能自拔,他要么沉溺暴力,成为无动于衷的杀人机器;他要么葡匐在宿命阴影中,成为命运不可捉摸的机关。如果不对宿命、暴力作形而上的抽象,而将它看成是形而下的隐喻,那么我们会发现,暴力、宿命其实都是生存资源匮乏的符号,暴力是对生存资源掠夺的暴力,宿命是对生存资源紧缺的无奈,如此观之,白痴的生活正是本土长久以来最迫切感觉到的生产力发展问题。生产力的不发达,必然造成生存资源的占有/反占有、掠夺/反掠夺;生产力的发达,必然会消除暴力和宿命在本土的符号功能,使人的生活能够在暴力和宿命的符号之外得到表现。因此,我们认为,关键不在于文学是否把20世纪过往的生活表现得血肉横飞,阴谋四布,宿命充斥还是烦恼多多,俗性十足,而在于文学通过这样一些符号形式揭示了本土存在的状况和亟待解决的困境。其实,现代狂人、革命战士都充分意识到生存资源匮乏是第三世界事实,只是他们提出的方案都是非常唯意志主义的,非常知识理性化的,这种方案有可信性却无可行性,因而必然给本土发展提出一些有缺憾的救世方针。后现代白痴表明,本土最缺乏的并不是生存智慧,那不是一种需要现代性启蒙指导的心灵缺失本土,本土是被过多生存智慧缠绕的本土,这些缠绕的话语海洋将本土生存的真象反而淹没了,使人找不到生存本体,本土最缺乏的是对生存匮乏的关怀,是对生存事实的童贞般的惊奇,《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猫子最关心的话题是炎热天气中温度计都爆炸了,而四却漫天虚构对实存的温度计漠不关心,猫子/本土/生存事实和四/现代知识/生存智慧的对立恰是现代性在本土上空游荡的象征,白痴正是试图解除这种象征的举动。
通过后现代白痴对现代性的终结,90年代的本土文学已开始某种程度上的生存关怀写作。从各家杂志的标语口号上看,无论新状态、新体验、文化关怀还是新市民,其内在核心都是在现代之后的意义上写本土,何顿、刁斗、述平、韩东等晚生代作家在无现代意识的前提下,已写作出大量本土性文本,这些文本平实、自然、散淡、轻松,虽无主义、孤独、焦灼、苦闷的做作,却自有本土人民生存情怀和生命历程的复现。
施宾格勒说,西方已经没落,在20世纪晚期这样一个终结性的时候,文学除了回归本土,依靠本土,怕也是别无选择了吧!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