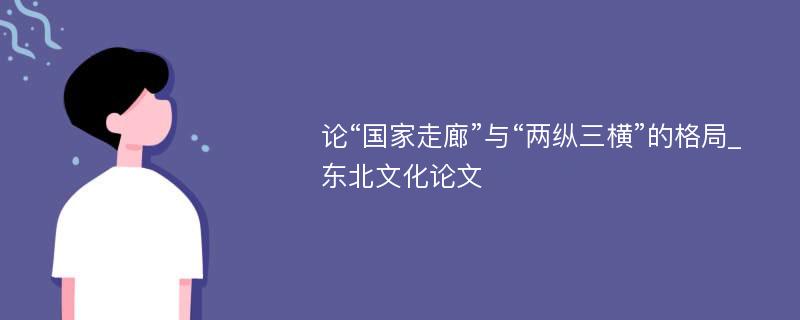
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廊论文,格局论文,民族论文,二纵三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费孝通先生讲话的主题
关于“民族走廊”及民族“全国格局”问题的提出,要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次重要讲话谈起(注:费孝通三次讲话内容按时间顺序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费先生的三次讲话,一次是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第二次是1982年5月27 日在武汉同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题为“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第三次是1982年12月7日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讲话, 题为“民族社会调查的尝试”。这三次讲话虽然谈的是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等具体问题,但引申出的话题却很宏大。三次讲话实际都集中了一个主题,即检讨过去民族调查及民族研究存在的缺乏整体观点和宏观眼光的缺陷。从而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要“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问题[1]。
费先生分别从两个具体问题,即川西北平武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和广西大瑶山瑶族的内部关系问题,引发出两个互为补充的重要观点:一是关于地域联系的观点,提出“要解决(白马藏人族属)这个问题可能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至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2];二是关于民族关系的观点,指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因而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由此,费先生提出了“走廊”研究和关于民族研究的主张,“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3]。并通过划分地理及民族“板块”的方式,将其主张进一步引申、扩大为全国民族大格局的构想。
费先生在第一次讲话中即谈到了位于藏东、川西汉藏和藏彝之间的“走廊”。在第二次讲话中,不仅将前次所谈的“走廊”正式冠名为“藏彝走廊”,又提出了“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两个概念。明确指出,这些地带“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并就此进行概括:“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在第三次讲话中,更全面、更详细地提到:“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从连续三次讲话的内容中反映出,费先生以区域“板块”联系的方式建构全国民族格局的构想,一次比一次清晰和完善。
费先生的三次讲话尤其是其中的区域联系观点和宏观的整体观点,不仅在当时对于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为他后来形成具有指导全局的学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思想,作出了重要的铺垫。
2.“民族走廊”的认识
关于“走廊”的认识,费孝通先生可谓是首先做这项工作的人,正如他所说:“我是在1979年提出这个问题的”[4]。他实际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从而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费先生在第一次讲话中所提出的“走廊”,实际指的就是历史民族“走廊”。照他的话说就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例如,他所说的汉藏及藏彝之间的“这个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在第二次讲话中,费先生首次提出了“藏彝走廊”这个术语。同时还使用了“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的提法。费先生不仅提出了新的学术概念,而且还在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领域里,将“走廊”研究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他在第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象下围棋,一子相连,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在第二次讲话中又说:“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他不仅确认了“走廊”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且还将“走廊”作为构造全国民族总体格局的重要构件。
上世纪90年代初,李绍明先生首次对“民族走廊”作出了定义。他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写到:“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5]。
李绍明先生的“民族走廊”定义是对费先生提出的“走廊”概念最先作出的规范化处理。尔后亦为学术界所引用。另外,李绍明先生还在其文中特别指出:“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意义。”这可谓是响应费先生对“走廊”学说的倡导。不过,由于他对“民族走廊”的讨论所针对的是具体的“藏彝走廊”,而且主要是与古代交通和文化交流相联系,未涉及全国民族格局的问题,因而“走廊”学说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论“民族走廊”
要建立起民族学的“民族走廊”学说,关键在于对“民族走廊”进行全面定位,包括“民族走廊”的产生、定义,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等。以下是笔者对“民族走廊”定位的看法:
1.“民族走廊”构造
“民族走廊”是李绍明先生按照费先生的观点首先规范的一个特定概念,是借用“走廊”这个普通词汇来确立的一个民族学概念。概念中的“走廊”一词与之原来词义已有重要区别。
在讨论“民族走廊”这个概念之前,不妨先作这样一个假定:在中国历史或民族史发展长河中,存在“民族走廊”的特殊环境构造。
如果按照地理条件及其特征把世界划分为若干人文地理“板块”或文化区域,那么,中国无疑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区域。中国东及东南边沿是海岸线,北及西北为高原草原、沙漠地带,西及西南为高原及高山屏障。大体而言,中国所在的地域及其地形是力量来自西南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撞击以及来自东部的太平洋板块挤压的地质构造的结果。因此,形成中国历史区域的各种自然地理要素,有着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本质联系”。由于印度板块的撞击并插入青藏高原底部,造成中国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并形成地壳厚度向东递减的趋势。再由于太平洋板块的西向抵触,造成青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大体多呈北—南走向。正是这样来自东西向的构造运动,合力造成了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形式。在由西向东的三级地形面的两条地壳厚度急减地带,即地形面发生转折的两条过渡地带,都是北—南走向呈条带状的山脉分布地带。河流到此沿断裂下切,并顺山脉走势转向,从而构成北南纵向山脉地带河流与山脉相间的高山峡谷地貌。
由地形的三级阶梯形式决定,中国的河流大势向东,特别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由西向东,流过第二级地形面即由曲折而转为平直。致使大江大河洪积和冲积而形成的冲积平原,大都集中在东部江河中下游地区,尤其集中在低平的第一级地形面上。这一情势至关重要。世界四大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惟有在中国,大江大河是向东流。而且其流域空间辽阔,有两条地形复杂的地势过渡地带,自然空间形式多样,而不像其他古文明区域大多呈简单的线型形式。
综观世界历史,凡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地区,都曾发生过远古人群从河流上游及山地向下游冲积平原地区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只是因山河所致,其运动大势向东。远古人群走向冲积平原的结果,就是在世界各个具有地理“本质联系”的区域,建立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积平原农耕文明。早期的文明区域通过自身具备的文化积累功能,迅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引力和扩张中心。尔后无论扩张、排挤或吸引,都造成了一种与先前走向冲积平原相反的逆向运动。
从考古材料上分析,中国远古人群确曾有过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总体方向的运动过程。而至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产生以后,历史民族或族群运动的总趋势即发生逆转,开始逐渐呈现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运动趋势。这种方向变化的时代划断,从理论上说大体可以新石器时代为界。而依实际而言,则当以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产生为界。
早期的古代民族或族群在江河上游必定会选择径由山脉和河谷构成的通道,而向下游及冲积平原地区移动。同时,其中某些部分必定会受阻或滞留于某些山区,尤其三级地形面上的两条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的复杂的地形过渡地带。而当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产生之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主要因受到排斥或扩张的压力,也必定会选择经由山脉和河谷构成的通道,远避冲积平原,而向冲积平原边缘的地形过渡地带移动。并以这个地带的复杂地形,既作为屏障又作为通衢,而在其中长期栖息和流动,或迁移到他地。这一运动模式作用的结果,不仅造成冲积平原中心与边缘带状分布的民族分布格局,而且,还使那些具有屏障和通衢双重性的地带,形成为“民族走廊”。例如,在第三级向第二级地形面即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过渡的岷山、龙门山及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还有在第二级向第一级地形面亦即从四川盆地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的巫山、武陵山及雪峰山纵谷地带,都是形成“民族走廊”的自然基础和天然地带。前者即形成了“藏彝走廊”。
简要地或者比较形象地说,即是:中国自然地理形成东部冲积平原与边缘山区和地形转变地带的高山峡谷区这样的构造。其所承载的历史活动,即使得一定的历史族群集团在冲积平原地区建立起早期农耕文明中心,并逐渐将其扩大,而将冲积平原边缘和地形转变地带留给了另一些历史民族或族群,即后来的少数民族。由此形成了中国特定的农业时代的历史过程以及“民族走廊”的历史构造过程。
以上即是“民族走廊”构造的自然和历史前提及其大略过程。这就表明,在中国历史或民族史发展长河中,存在“民族走廊”的特殊构造,这个假定是可以成立的。
2.“民族走廊”的概念
由上可知,关于“民族走廊”的形式、性质、涵义及特点等,大致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1)“民族走廊”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凡“民族走廊”都位于非冲积平原地区,或在冲积平原边缘及河流上游地区。其中活动的民族或族群主体为非冲积平原农业文明中心的民族,包括后来“变成”为非中心区域的民族。换句话说,“民族走廊”实际就是后来形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的那些历史民族或族群活动的特殊地带。这种特殊地带的产生,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民族走廊”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2)“民族走廊”具有自然与历史的双重因素。从自然方面来说,“民族走廊”不是单一的自然空间形式,而是由众多山川组成的、具有各种地貌的、复杂的自然形式。其总体自然形式的平面呈条带状;其空间范围大体以其自然形式的转变地带为界。在一条“民族走廊”中,包含有若干由山川构成的纵横的天然通道和一些易于封闭的相对隔绝地带。从历史方面来说,“民族走廊”对于在其中活动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正因为有保存的条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积淀民族文化,成为历史文化的沉积地带。另外,在“民族走廊”中有某些易于流通的道路,形成古代商道(如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易被来自古代文明中心的力量所经略和开发。但从总体上说,在农业时代,“民族走廊”一般是不易被政治中心所控制和开发的地带。
(3)“民族走廊”具有历时性。而且,其历时性与其中族群的流动及方向变化,具有相关性。在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形成以前,大体以趋向冲积平原的迁徙活动为主;方向大势由西而东,由南而北。此后,则大体以退避、避居和迁移为主;方向大势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大致从元代以后,除战争等强力因素逼迫流动而外,“民族走廊”活动大体以维持当地民族社会文化生存为主。“民族走廊”中民族或族群传统社会文化的萎缩、变异、涵化、沉淀,乃至消亡,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加剧,其演化的速度受到“民族走廊”与中原之间距离的影响。一般而言,离中原距离越远、交通越困难的地方,“民族走廊”中的历史文化及“残存文化”因素就保存得越完好、越丰富,“民族走廊”的特性就表现得越显著、越具有典型性,如“藏彝走廊”即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走廊”主要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产生以后的历史民族动向。
(4)“民族走廊”在今天来看,其特征是: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色彩浓郁;沉积的历史文化丰厚,具有古老性、残存性、变异性和流动性等特点。
综上所述,大体可以给“民族走廊”下这样一个定义:
“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
“民族走廊”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走廊”大体在新石器时代即开始进入形成过程;其最终形成以及构造活跃、活动频繁时代,是在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产生以后,即大体在尧、舜、禹以后。典籍记载:舜时,“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6]。这是“民族走廊”起始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民族走廊”的活跃期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此后,随着农耕经济在山区及边远地区普遍确立和稳定,尤其在元代实行土司制度之后,除“阿尔泰走廊”部分地段而外,“民族走廊”始进入“休眠”期,并走向衰落。明清以后,即已成为少数民族顽强维护自身仅存的生存地带和自身文化传统的区域。到今天,“民族走廊”不仅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沉积地带,其中“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费孝通语),已使“民族走廊”成为一种特殊的自然和历史文化景观,成为珍贵的、亟待保护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
三、“民族走廊”的全国格局
1.“二纵三横”构架
笔者在此提出,全国“民族走廊”主要有五条,即“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以及“古氐羌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为南—北纵向的“民族走廊”;其他三条为东—西横向的“民族走廊”。如此构成全国“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
“二纵三横”,作为自然地貌或地理形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构建全国民族总体格局的“民族走廊”的特定构架,则可以视之为一种假说或见解。这个假说或见解的雏形实际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如他说“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等),笔者只是将其丰富和具体化。这个假说或见解的提出,主要依据于如下三个方面:(1)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例如, 文献记载的三苗出彭蠡洞庭之间,西羌“附落而南”,“廪君蛮”入清江,匈奴、柔然西迁等民族历史活动线索。又如遍布南方的崖葬和呈带状分布于川滇西部的石棺葬等考古文化所提供的历史信息。(2)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包括建国前土司统治地区, 以及建国后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域。因为少数民族现实的分布状况,实为历史运动的结果。(3)少数民族口头传说和谱牒、巫经等文献记录,以及其他民俗材料。例如,苗瑶语族各语支民族都有曾来自中原地区的历史传说;西南藏缅语各语支民族大都有从西北雪山地区迁来的传说等等。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两条“民族走廊”接触和交汇地带,通常也是民族交汇,关系复杂,彼此融合的地带;民族情况更显示出复杂性。例如,费孝通先生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民族内部关系相当复杂的广西大瑶山区,就正是处在“壮侗走廊”与“土家—苗瑶走廊”接触和交汇的地带。又如,“藏彝走廊”南端延伸部分与“壮侗走廊”西端延伸部分,大致在云南形成交汇区域,致使云南成为少数民族分布最多、民族情况最复杂的省份。另外,从现实状况来看,除“民族走廊”本身大多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带而外,依照历史记载所表现出的“走廊”族群运动的方向性,在“民族走廊”的出口地带,必定也多是少数民族聚居较多或较集中的民族聚居区域。如象“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及“壮侗走廊”的出口地带——云贵高原,以及“阿尔泰走廊”的出口地带——新疆西部地区。
2.“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及民族活动概略
以下所述某语族不同语支族群按一定方向沿“走廊”不同的通道运动,例如,藏缅语族三大语支民族或族群,分别通过“藏彝走廊”五条不同的通道南下等等,均属笔者提出的假说或见解。有关论证,笔者将另辟专题,恕在此不赘。
二纵——“藏彝走廊”和“土家—苗瑶走廊”。
“藏彝走廊”位在青藏高原东缘中国地势第三级台阶向第二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呈西北—东南走向;以藏东川西北高原峡谷地区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川,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座标位置大体在东经97—104°,北纬25—34°之间。 直线距离南北长约1200公里,东西宽约750公里。
“藏彝走廊”北起甘青交界的西倾山南侧阿尼马卿山至岷山一线,即青海果洛、海南及甘肃甘南交界地区;南抵滇西高黎贡山、怒山及云岭南端,以及金沙江南侧至乌蒙山西侧一线,亦即云南腾冲、保山、永平、洱源、宾川、元谋一线;其西界沿巴颜喀拉山西侧,南抵横断山系西北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宁静山之北端,即大体在青海鄂陵湖、玉树至西藏昌都、察隅一线;其东界由北而南自岷山东侧沿龙门山、邛崃山、大凉山外侧,直抵乌蒙山以西,即大体在甘南宕昌,四川平武、北川、九顶山、宝兴、天全、峨边、马边至云南昭通、会泽一线。
古藏缅语民族或族群从青藏高原借道“藏彝走廊”东进南下,主要由五条通道:
其一、自青藏高原沿阿尼马卿山(积石山)两侧,从黄河大拐弯处东进,以及从甘南洮河上游地区南进,而入川西北草原地区。一些在岷山西侧沿岷江上游南下,一些则从黄河南侧进入大渡河上游,并沿大渡河南下。这大体是羌语支族群所取的道路。
其二、在青海玉树地区金沙江东侧及巴颜喀拉山南麓,东入雅砻江上游,再向雅砻江下游、金沙江流域,以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运动。这大体是羌语支及部分彝语支族群所取的道路。
其三、在青海巴颜喀拉山西侧,沿金沙江、澜沧江及两江之间的宁静山、云岭山路,南出云南剑川、洱源地区(由此延伸,尔后可沿哀牢山、元江一线运动)。这大体是彝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
其四、从青海与西藏交界的唐古拉山脉东段两侧,沿怒江、澜沧江上游及两江之间的他念他翁山、怒山山路,南出云南保山、腾冲一带(再由腾冲往西,经缅甸之密支那进入伊洛瓦底江上游。或从保山一带东进洱海地区,再入澜沧江下游和元江流域)。这大体是缅语支和部分彝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
其五、在藏东沿雅鲁藏布江北侧、念青唐古拉山南侧,东入藏东南察隅地区,再顺察余勒河可转入东北印度,并通过印缅边界一些山口入缅甸,进至缅甸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这大体是缅语支所取道路。
“土家—苗瑶走廊”位在四川盆地东侧地势第二级台阶向第一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呈东北—西南走向;以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川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108—111°,北纬26—31°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600公里, 东西宽约300公里。
“土家—苗瑶走廊”北起巫山、长江一线;南抵乌江、沅江上游湘、黔、桂交界地区;南端接珠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地区,即与“壮侗走廊”接触或交汇。其东界在武陵山、雪峰山西北端一侧,大体在鄂西长阳、湘西慈利、隆回至桂北越城岭一线;其西界沿长江与乌江,大体在渝东南石柱、彭水至黔东北务川、思南,以至黄平、都匀一线。
“土家—苗瑶走廊”主要通道有五:
其一、在长江巫山峡区借峡道南入“走廊”,北接大巴山及汉水中游地区,南经鄂西清江流域,入沅江和乌江流域。这大体是古土家语族群运动的路线。
其二、从长江入清江,进入鄂西清江流域,并与沅江上游酉水流域相汇;亦可转至乌江流域,向南入黔东北及黔东南。这大体是古土家语及部分苗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土家语族群多走水路,苗语支族群则多择山路。
其三、从长江溯乌江及其支流与沅江流域相接,由此南下入黔。这大体也是土家语及苗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
其四、从洞庭湖区溯沅江及武陵山道进入“走廊”,并溯沅江上游支流及两侧山道南下,抵黔东南苗岭及黔桂交界地区。这大体是古苗语支族群所取的道路。
其五、从洞庭湖区于沅江东侧,沿雪峰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山路,南下湘、桂、黔交界地带,并入桂东山区。这大体是古瑶语支族群所取的道路。从湘、桂、黔交界地带沿大庾岭,借南岭山道往东,则可能是畲语支族群所取路线。
此外,还有一道,即从淮河流域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沿南北走向的大别山—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山路,南接大庾岭。古苗瑶语族群尤其瑶语支、畲语支族群或许也取这条路线南下。在大庾岭一带,往西南为瑶,往东南为畲。或者,在幕阜山一带,畲与瑶即分道而向江西、浙江方向运动。
三横——“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和“古氐羌走廊”。
“壮侗走廊”即费先生所说的“南岭走廊”。“壮侗走廊”位在东南珠江、闽江流域与长江流域分水岭地区,略呈东—西走向(稍偏北—南);以南岭一系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及丘陵,以及大体呈西—东走向的珠江支流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104—116°,北纬23—26°之间。直线距离东西长约18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
“壮侗走廊”东起闽南武夷山区;西迄珠江支流北盘江、南盘江上游地区,即黔、桂、滇交界地区,直抵乌蒙山;其北界在南岭北侧一线;其南界大约以北回归线为界。“壮侗走廊”中段北侧,即在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分水的苗岭南麓一带,与“土家—苗瑶走廊”相汇。西端延伸部分与“藏彝走廊”南端延伸部分遥相接触。
古壮侗语民族或族群借“壮侗走廊”西进,主要有两条东西向的通道:
其一、溯珠江而上,沿珠江支流红水河北侧向西,经苗岭南侧,入黔南、黔西及滇东地区。这大体是古侗水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
其二、沿红水河南侧及郁江往西,经左、右江流域,入越南及滇东。这大体是古壮傣语支族群运动的路线。
“阿尔泰走廊”位在长城以北,呈东—西走向;以平阔的蒙古高原及草原、沙漠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75—120°,北纬42—50°之间,直线距离东西长约2000公里,南北宽约1000公里。
“阿尔泰走廊”东起东北大兴安岭及辽河上游一线;西迄西北阿尔泰山及天山西端一线;其南界在燕山、阴山、河西走廊北侧至塔里木河一线;其北界在额尔古纳河、贝加尔湖南侧至阿尔泰山一线。“阿尔泰走廊”西段如果南界再宽一点,即大体相当于费先生所指的“西北走廊”。
“阿尔泰走廊”至少有两条东—西向的大道,或分南北两路。
其一(北路):其东端,越大兴安岭,可进入东北松嫩平原,或沿小兴安岭进入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平原,并转入俄国西部滨海地区。其西端,沿天山北侧,以及沿阿尔泰山南侧,可分两路西出,经哈萨克丘陵,通往西伯利亚及东欧平原。
其二(南路):其东端,从大兴安岭南侧即辽河上游地区向东,可入东北辽河平原,并直至长白山区和朝鲜半岛。其西端,沿天山南侧,可西出帕米尔山口,再沿兴都库什山两侧,往东南入印度河流域,往西南入伊朗高原,直至西亚。或者,在兴都库什山北侧顺锡尔河、阿姆河,经里海、咸海都拉平原,可西进东欧平原及黑海沿岸。
“阿尔泰走廊”历史上主要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各族群东西运动的地域。另一个重要情况是,在中国,只有北方游牧社会区域对于冲积平原农耕文明区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冲击力。因此,从文献上看,至迟在先秦时期,“阿尔泰走廊”上的民族集团南向运动的趋势,就已日趋明显,以至最终造成在中国范围内民族由北而南运动的大趋势。其向南运动与长城以内区域发生历史关系,就大体而言,突厥语族群多取道河西走廊及附近地区;蒙古语族群多取道阴山及河套附近地区;通古斯语族群则多取道燕山及滦河流域地区。
“古氐羌走廊”位在长江、黄河流域分野的秦岭地区,呈西北—东南走向;以东西走向的秦岭山脉及渭河、汉水等河流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坐标位置大体在东经104—111°,北纬31—34°之间。直线距离东西长约800公里,南北宽约350公里。
“古氐羌走廊”西起岷山北麓洮河、渭河上游及白龙江流域、汉水上游地区,亦即甘肃临夏、甘南和陇西地区,略在甘肃岷县、陇西一线;东迄秦岭、大巴山东端,略在陕西商南至湖北武当、房县一线;其北界沿渭河一线;其南界在大巴山脉南侧一线。“古氐羌走廊”西端与“藏彝走廊”北端大体衔接,并部分重合,因而亦为藏缅语尤其古氐羌族群所取的东进路线。其西端延伸部分接青海河湟地区及河西走廊,并由此遥接“阿尔泰走廊”西段。其东南端则与“土家—苗瑶走廊”衔接。从广义上说,“古氐羌走廊”包括其西端河湟地区及祁连山通道。
“古氐羌走廊”主要通道有三:
其一、于渭河上游地带西接河西走廊,东沿渭河进入关中平原。这大体为古羌族群东进路线。
其二、在洮、岷地区,西接河、湟及祁连山南路;东取岷山—米仓山—大巴山—巫山山路,或取汉水上游河谷通道,可东入长江、汉水下游地区即江汉平原;其东南端接“土家—苗瑶走廊”。这大体为古氐、羌族群运动路线。土家族先民部分即取此道进入“土家—苗瑶走廊”。
其三、沿岷山北麓东入或从渭河流域经陇南南下,至白龙江、西汉水流域,及嘉陵江上游地区;再向东即接大巴山、汉水通道;向南则与“藏彝走廊”东界部分重合,即沿龙门山东侧,接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地带。这大体为氐人族群运动路线。
四、结语
1.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笔者以费孝通先生、李绍明先生为代表,对前人的研究作了清理和小结。在继承前辈的研究工作的同时,笔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提出在中国特定自然历史条件下“民族走廊”的特殊构造问题;对“民族走廊”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作出了更加细致和准确的界定;勾画出“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的全国格局。
2.笔者提出的“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构架,尽管还比较粗糙,论证不够,甚至在某些环节可能有误,但从总体思路上说,进行这样的构架是具有合理性和启发性的。一是这个构架大体能够综合反映出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基本态势和一般趋向;二是这个构架牵涉到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基本能够框定全国民族的总体格局。
3.笔者在“民族走廊”和“民族走廊”的框架方面所做出的工作,有助于在民族学领域里确立“民族走廊”学说。
4.笔者从宏观着眼于研究“民族走廊”及其总体结构,丝毫没有降低某一具体“民族走廊”研究的重要性,相反,由于宏观研究为个体研究建筑起了整体基础,因而不仅要求更加强化“民族走廊”的个体研究,以使宏观研究更加深入和完善,而且还为个体研究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