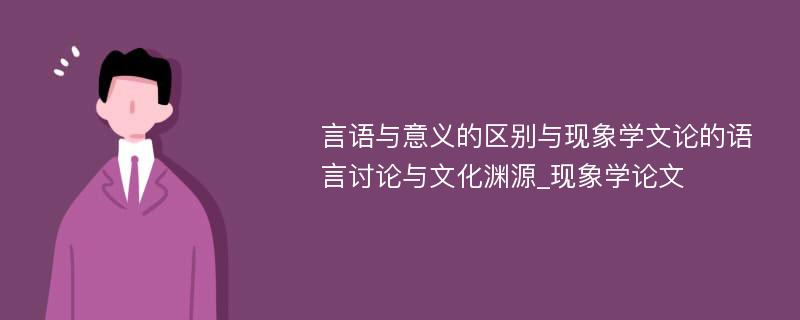
言意之辨与现象学文论的语言论述兼文化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文论论文,论述论文,语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一千七百年前,魏晋玄学家就探讨过语言问题,言意之辨充分地体现了他们深邃的智慧,以及对语言的深刻认识。而且,魏晋玄学之言意之辨和中国古典文化联姻,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论,这是魏晋名士始料不及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象学文论家建立文学本体论学说,也论述了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两者并非有相互影响的事实联系,但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表现出某种文化类同。本文试图从文化哲学层面上,比较言意之辨和现象学文论关于语言论述的异同,并从中西文化之渊源探究其原因,由此剖析语言异同性中所包含的文化现象。
一、言、象、意──文学作品结构的四层次
要了解言意之辨和现象学文论对语言的论述,首先我们要了解两者论述语言所参照的关系物,也就是语言自身置入的参照系统。在这一点上,魏晋言意之辨和现象学文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魏晋玄学要穷尽整个宇宙的内在本性,认识事物的本体,就要经过言、象、意三个阶段。玄学大师王弼注释《周易》,抓住言、象、意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周易》的言指卦、爻辞;象指八卦象,六十四别卦象及阴─阳─两爻象,总称之为卦象,用来象征某种事物;意指爻辞和卦象中表明的义理,宗旨①,王弼具体分析卦与爻以及爻与爻之间的各种关系(卦爻辞),阐明了六十四种具体的表征(卦象),因而得出了六十四个必然之理(义理)。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这段话中,言、象、意三者的层次关系很明显,由言到象,由象到意,撇开了王弼注《周易》的玄论不谈,他所阐述的言、象、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魏晋玄学就是把语言置于言、象、意这样一个参照系统中,来加以探讨的。一般来说,从王弼注《周易》到言意之辨,言、象、意的含义有些变化,言指文学和语言(包括日常的言语),象指具体的物象,意指思想,意义。
无独有偶,现象学文论家英加登(Romam.Ingarden)在他的德文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中,重点研究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他认为,文学作品由四个异质的层次构成,这四个层次是:(1)语音结构层次;(2)意义单位层次,(3)再现的客体层次;(4)图式化观相层次。简述之,语音结构层次是文学作品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它包括字词、句子的语音素材(音调,音色、音的力度等)和字音形式。意义单位层由每一个单位的字词,句子的字音形式表现的意义构成。再现客体层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物象,这些虚构的物象组成一个想象的世界,它只具有实在的外貌,并不独立存在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图式化观相层次指虚构客体向主体显示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的“观相”组成的层次只是骨架式或图式化的,它们包含着许多潜在的意义。这四个层次,层层递进,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使文学作品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现象学文论家把语言置于作品本体结构中,通过四个层次的相互关系来论述语言的特点和功能。此外,关于艺术作品的本质意义,英加登认为并不能仅仅了解作品的所有层次就能获得,它需要读者对艺术作品的“观念”(又译为“形而上的质”)的洞察,英加登把作品的“观念”定义为“一系列在作品中或通过作品得到具体显现的综合的,本质的,互相调节的审美价值性质。”②在这里,英加登所指的艺术作品的“观念”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对照出魏晋玄学和现象学论论述语言的参照系统。言、象、意中的言对应作品四层次中的语音结构层和意义单位层,象大体对应再现客体层和图式化观相层。因为言意之辨的象是由《周易》的卦象演变而来的客观物象,而再现客体层是虚构的主观表象,图式化观相层是再现的作品整体世界,它包含潜在的意义。两者都含有潜在的意义,都是形象,但有主观和客观抽象之分。不言而喻,言意之辨的意和英加登的作品的“观念”的意思相同。我们比较考察了两者论述语言的参照系统,下面我们看看在相似的参照系统中,它们怎样论述语言的特征和功能。
二、语言──获得意义的基本因素
首先,从语言的基本功能来看,言意之辨和现象学文论认为语言是理解和获得意义的基本因素。我们知道,魏晋玄学之言意之辨发自汉末的名理学,当时,社会上出现一股清谈之风,士人们热衷于品评人物,即人物的言语外貌是否与其精神才性相符?由于魏晋名士崇尚老、庄之学,他们多主张言不尽意论。晋人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记载说:
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以此为谈证。其实,纵观言不尽意论者的言论,他们并不是认为语言没有认识作用,而是明察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微妙,认为语言表达意义,但不能表达出最深奥的意义。也就是言不尽意论者,魏代名士荀粲所说的“理之微者”。在《老子指略》中,王弼说:“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名号生乎形状,称谓出乎涉求。名号不虚生,称谓不虚出。”这就是说名称可以确定事物,它们从事物中产生,人们用某一称谓来表明这种事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又说:“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些言论充分说明言不尽意论者肯定语言具有认识的基本功能。过了60余年,被称为“王弼之亚”的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注释《庄子》,提出“寄言出意”,“因物立言”。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寄,托也。”“即“寄托”的意思,郭象的“寄言出意”就是肯定“出意”必须借助语言,从语言中寄托意义,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和王弼所见略同。
主张言尽意论的欧阳建,一方面认识到语言可以表达出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走向极端,把语言等同于意义、思想,没有看到语言和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他在《言尽意论》中说:
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在这里,他把语言和意义(理)的关系,当成是事物和它的影子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比喻。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言不尽意论者和言尽意论者都认为语言是获得意义的基本因素,肯定语言具有认识作用之功能。
现象学文论把语言作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本体构成的基本因素之一。英加登从作品本体论出发,认为理解作品的意义,必先理解作品的语音层和意义单位层。在论述这个层次时,英加登说:“对语词的语音形式的听觉理解同书写形式的视觉理解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致这些经验的意向性关联物似乎也处于特殊密切的联系中。语词的语音形式和视觉形式似乎只是同一“语词躯体”的两个方面。……语词躯体同时是某个另外的东西的“表现”,即语词意义的“表现”,它指涉某个东西或发挥一种特殊的意义功能。当我们充分掌握某种语言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时,我们不仅把语词声音理解为纯样声音模式,而且还应认为它传达或能够传达某种情感性质。”③英加登认为,理解语词的声音是和理解语词的意义同时发生的。语词和语词的意义又构成更高一级的句子的意义。在英加登的现象学文论中,作品的语音层次是一个固定的、典型的语音结构,这种结构使作品有一种不随时代变化和读者的变化而改变其意义的内在同一性。语音层次为文学作品其它三个层次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语音层次发出不可还原为音晌新东西组成了意义单位层,因此,意义本质上同字音紧密相连,意义就是字音的意义,统观这两个层次的“语言”特性,我们发现,英加登所理解的语音层次的字音是一种“不变的语音形式”,负载着字的意义,通过变化的语音素材将其具体化。正是意义层次使得作者有可能使一部文学的艺术作品充满他的意向,而又使读者有可能重新意向一部作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层次我们才可以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越出了我们个别的意识行为。”④不言而喻,语言的这种基本的认识功能在作品本论中得到全面认可。
现象学文艺美学家杜夫海纳(M·Dufrenne)把语言当作文学作品的物质材料来看待,他认为每一件艺术品都需要一种物质材料做基础,如颜料,声音,石头之对于绘画、音乐、雕塑。感受作品时,我们首先注意作品的物质材料。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他从审美角度论述作品的物质材料,认为作品的物质材料在被感受时,成为一种给人美感的“动美感”的东西。⑤它足以构成一种审美对象,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具有某种意义。在《美学与哲学》著作的第二部分《艺术与符号学》中,杜夫海纳从符号学的角度论述语言,认为语言使我们利用代码传递信息,其意指语言就是一种代码,在语言中,信息和代码是相互依存的,也可以是平等的。
三、语言──认识的局限性
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不仅看到了语言的基本认识功能,而且,在言、象、意三者关系中,辩证地论述了语言认识的局限性。这一点,现象学文论也加以充分地论述。魏晋名士,特别是言不尽意论者,如王弼、荀粲、嵇康等人,看到了语言认识的局限性,“言不尽意”极其精炼地概括了语言的这种局限性。何劭在《荀粲传》中记载了魏代名士荀粲的言论,说:
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 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 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粲认识到语言的认识作用很有限,它不能表达出某种深奥的意义,比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因此,六籍里面记载的东西,仅是圣人留下来的无用之物,荀粲之言过于偏激,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也认为:“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这就是说我们从语言中并不能得到意义。但是,要获得意义又要经过语言阶段,即王弼的“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这种矛盾关系在于王弼所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言尽意论者也陷入对语言认识的矛盾之中,在主张言可尽意的同时,欧阳建也承认语言认识的局限性,他在《言尽意论》中说:
夫天不言而四时行焉,圣人不言而鉴识存焉。形不待名而圆方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而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玄学对语言的局限性的认识,渗透到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之中。例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能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可见语言表达意义只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即言不尽意之说。魏晋诗人,玄学家稽康送友人入军,表达自己面对离别的内心情感,其诗云:“目送遍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兄秀才入军赠诗》)这首诗表明自己胸中的离情别恨,“谁可尽言”呢?
现象学文论又是怎样论述语言的局限性呢?英加登从分析字词,句子着手,论述了语言表达意义时所表现出来的图式化的,意义含混的特点。首先,英加登认为作品的字词意义和句子的意义都是意向性的,也就是说,它们的意义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一个字词的意义指这个字词意向性所指称的客体,即与该字词的字音结合在一起的意向性对应物。英加登认为:“同一个字,意义相同,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用法,因此,尽管存在着词意的同一性,但其变化都是难免的。”⑥一旦某个词与句子中的其它的词相联系,词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成为更大的意义单位,作为整体的句子的功能性成分。同时,词的意义的变化还在于该词实现的概念的某一方面都会创造出一种意义。可见,人的意识作用规定了字词的存在方式,意识的意向性活动开启了一系列意义产生,发展过程⑦。字词的意义正是由意向性投射完成的,这说明语言的字词意义是不确定的,变化的。
由字词构成的句子的意义指向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事物,并指示其意向性关联物。英加登认为,个别的字词与意向对象相关,句子则与意向的事物状态相关,句子关联物往往是纯粹的意向性关联物,即句子关联物是由意义单位的意向性所意指,并超越意义单位的意向性,这就是说,句子的意义比字句的意义含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文学作品的句子不同于科学著作中的句子,前者是“准判断”,我们并不断定其指向的事物状态的真实与否,而只是将其看作纯意向性的事态。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作为纯粹意向的关联物与现实事物的完整性,明确性相比,是不完全确定的,图式化的和意义含混的。这说明由字词和句子构成的文学作品语言的含混多义性,它不能真实准确地表达事物的存在与状态。由此,在英加登看来,语言可以表达意义,但其表达的意义又具有不确定性、多义性和含混性等特点。可见,语言在表达意义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语言──本体论意义的探讨
我们知道,言意之辨对语言的论述是以玄学思想为基础,言与意的关系在玄学中有许可哲学思辨的因素,这一点,现象学文论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些哲学思辨中包含了玄学家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认识。所谓本体论意义也就是确定事物是自在还是他在,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魏晋言意之辨中的两大论者:言不尽意论者和言尽意论者,并没有正面探讨语言的本体论问题,但他们一些言论都包含了这层意思。言不尽意论者中,王弼的言论最有代表性。哲学上,王弼认为,形形色色的万有现象是“末”,宇宙的本体是“无”,万有是宇宙本体“无”的外在表现,这种贵无的本体论哲学是他对语言本体论意义认识的基础。在言、象、意的关系中,王弼认为言象是“末”,意是“无”,即本体,因此,否定了语言的本体论意义,言、象、意的这种本末,有无关系,说明意是第一性的,这就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的意思。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进一步说:“言者,象之蹄者;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这些话正如孔繁所解释:“言、象仅为得意之工具,而非意本身,因此,得到意,工具即可丢掉;如同得到兔可以丢掉蹄(套索),得到鱼可以丢掉筌(竹篓)一样。”⑧汤用彤先生也说:“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则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⑨现实世界的万有事物,纵使千变万化,都是本体“无”的外部表现,要尽意、知本,就需要通过可见的具体物象。言与象都是观意,得意必经的途径,是寻意的工具,若滞于言象,即拘泥于文字、物象,自然会失其真意,所以,王弼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著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然而,忘象乃得意也,忘言乃得象者也。”很明显,这是与他本体论哲学中提出的“崇本息末”的认识方法相一致的。在《老子指略》中,王弼认为:“老子之文,欲辨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意也。”其“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辨而愈惑。”这里的“一言而蔽之”即“崇本以息末”,这是王弼注释《老子》的方法,《老子》的五千文言论,文字是“末”,其著述的宗旨,义理是“本”,如果拘守于具体的词句,反复辨论、探究、责难,那么就要失掉《老子》的宗旨,越辨越迷惑。
语言是现象,是工具。言和意的区别是现象和本体,有限和无限的区别。王弼的新解释,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当时所谓“忘言忘象”,“忘言寻其所况”“善会其意”“假言”等都是承袭《周易略例·明象》所言。即使崇有论玄学家郭象,也同王弼一样,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如果拘泥于“言”,则不能从中得到义理,他提出“寄言出意”并以此方法来注释《庄子》,目的在于摆脱字面的束缚而发挥自己的思想,从认识论上说,寄言出意就是把语言看成表达思想的工具。
魏晋玄学家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来解释老、庄,周易之学,探讨本体存在而契合玄学之旨,语言便成为一种表意的现象,寻意的工具,不能进入玄学家“道”的世界,语言只能存在于认识过程之中,作为一种现象来界定自身。
现象学文论建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基础上。现象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方法,就是悬置法或加括号法,即在认识之前,首先把客观外在世界悬置起来或加括号,悬搁不论,而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英加登探究文学的艺术作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如此。他首先建立作品的本体论结构,认为文学作品语言的两个层次──语音结构层和意义单位层是作品本体论结构的两个重要层次。英加登认为“只有先揭示出对于这种结构来说是本质性的要素,才能据此进一步认识作品的艺术性质。”⑩可见,在英加登的文学本体论结构中,语言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具有一种客体的本体论意义。我们从语音结构层和意义单位层来看英加登是怎样肯定语言的本体论意义。
语音结构层和意义单位层是作品整体结构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并且具有独特性。即“(1)每一层次由于其特有材料的不同而具有特殊的性质;(2)每一层次对于其他层次以及整个作品的结构所起的作品也各不相同。”(11)这种特殊的性质和结构使语言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东西。在语音结构层,字词的语音形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也是一个意向性对象。语音和字的意义连在一起,通过意向性的语音素材而将其潜在的各种稳定要素具体化,语音层次与意义层次有着必然的联系,而意义层次对构成文学作品的其它层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影响着后面几个层次的正确性。意义单位层则展示出一个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独特的世界,它显示的意义是通过意向性从质料的形式指向客体的东西,“虽然它来自意识作用,但它已超越这种作用,具有不属于精神的东西,即指创作主体意识物化。”(12)因此,意义在具体化中受到意识的改造而又具有独立的客体性。语音层次和意义单位层不只是纯意识的对象,也是纯意识指向的本体,又是一种融本质和现象于一体的意向性结构。文学作品就是纯意向性的客体,在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基本的四层次结构,它是一种永恒的动态结构,这种本体论的作品结构在于其中构成的每一层次,都是一个意向性对象,又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客体(实体),它们本体地自为地存在着。
以上分析了言意之辨和现象学文论对语言论述的异同,当然,仅仅停留在对现象异同的考察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深入其文论的深层结构,从中西文化传统之根本来揭示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从本质上把握这种异同性中所包含的文化性特征,这才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真谛所在。
五、语言的文化性特征──中西文化探微
言意之辨和观象学文论源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对语言论述的异同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老、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魏晋言意之辨。老、庄哲学讲求“闻道”,老、庄哲学中,“道”存在于一切自然万物之上,它无形无名,无生无死,变化无常。因此,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一落言筌,便成了有限。“道”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也是人生最高最完美的境界。这种“道”的学说在魏晋玄学中演化为宇宙本体论哲学思想。玄学家们用老、庄哲学突破汉代哲学对感性经验现象的关注,对具体科学问题的探讨,而通过宇宙万有现象,探求世界万物的内在本性。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下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13)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家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无”,形形色色的万事万物都是“无”的外在表现,要探究宇宙本体,则要通过外在的具体物象。
我们知道,言意之辨起于汉魏间的名理学,而名理之学又源于品评人物。东汉末年,社会上出现的清谈之风,从指陈朝政向臧否人物的清议转变,识鉴人物的容貌和才性。魏晋名士以老,庄的自然人性论为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的,与生俱有的。一方面,要从人物的言谈举止观测其神理,充分重视人物的情性;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人物的容貌,以貌取人,否则以“形貌取人必失于皮相”,要“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闻于无音,然而评量人物,百无一失。”据欧阳建《言尽意论》记载,当时,识鉴人物均引言不尽意为笑证。名理之学亦是如此。汤用彤说:“名家原理,在乎辨名形。然形名之检,以形为本,名由于形,而形不待名,言起于理,而理不俟言。然则识鉴人物,圣人自以意会,而无需于言。魏晋名家之用,本为品评人物,然辨名实之理,则引起言不尽意之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15)可见,老、庄的哲学渗透魏晋玄学之中,成为玄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老、庄哲学中,“道”不仅是万物之本,融于万物之中,自然万物是现象,道是本质,是无限之物,而且自然万物本身又不能界定“道”,庄子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6)人的听觉,视觉和言语都不能获得“道”。玄学认识宇宙本体和自然万物,正是以老、庄之学为依据,“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17)以上论之,我们可以看到言意之辨深深地植根于老、庄文化传统之中,言意之辨关于语言的论述契合老、庄文化之宗旨。
此外,老、庄哲学认识到了有限与无限,具体和抽象的对立统一,要求最终摆脱有限,具象的羁绊,归于无限,也就是“道”的境界。特别是庄子学说,要求摆脱一切“物役”,而进入等生死,齐物我,一寿夭的境界。这种文化思想影响玄学注重于讲神识,重超脱,轻具像,忘形骸。言意之辨中,玄学家主张“得意忘言”“忘言忘象”就是这种文化思想的认同。从思维认识来看,这是强调思维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质的飞跃。玄学家否定语言的本体论意义,始终把语言当成工具,当成有形之物就不足为怪了。
从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文化讲求知识的科学性,准确性。古希腊哲学讲“爱智”,也就是求真知。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由求于己以求真知,柏拉图等人则在经验知识之上建立理念性知识,形成了探求客观世界(对象)存在本质的文化传统。这种理念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西方,胡塞尔的现象学继承了这一古希腊以来求真知的文化传统,排除了近代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对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背景,从绝对主体方面探知本源(客观世界的存在本质)。现象学文论家英加登和杜夫海纳把现象学原理运用于文学研究。在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的“世界”中,“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意识的“对象”。因此,现象学得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任何事物都是意识指向的事物,任何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语言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外在表现,因此,语言必有所“指”。胡塞尔说,“说话”总要“说”些“什么”,重要的不在于“说”的“声音”本身,而在于“什么”,是这个“什么”使“声音”成为“语言”(话)(18)。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英加登在作品本体结构中对语言的论述。英加登把语言结构分成语音层次和意义单位层次,它们都指向某物,并被意识所意指,即具有意向性,语词和句子指向一种被称为意向性关联物的客体。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语言有两种意义作用:一是指向具体的客观对象;二是表达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使客观对象成为意向性的客体,即意向性关联物。意向性关联物具有不依赖于客观对象的独立性,因此,客观对象与意向性关联物之间存在着游离关系。这样,语言的能指和其所指就不是完全重合一致的。英加登在作品结构中分析语言表达意义的局限性时,基本上符合这种文化认同。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句子作为纯粹意向性关联物与客观对象的完整性,明确性相比,是不完全确定的、意义含混的。在现象学中,胡塞尔提出了意向性这一重要概念,他把意向性定义为对某物的认识,并把它视为纯粹意识的重要属性。在他的纯粹意识构成的“世界”中,客观事物呈现出来,成为纯粹意识意向性的对象。这是一个纯粹思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本质“呈现”出来,成为现象,客体转化为主体,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融为一体,因此这又是一个真正绝对而自由的“世界”。了解了这种现象学本体论观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英加登对语言的本体论意义的肯定。语言,它的构成单位;字音,字词和句子,与它们意向性所指向的客体是不可分的,它无条件地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论结构。就象胡塞尔用意向性这个概念把现象与本质,意识与存在,精神和物质紧紧地捆在一起一样,英加登也用意向性这个概念把语言(现象)与意义(本质)置入文学作品的本体论结构中,使之不可分离。总的看来,现象学文论对语言的论述表现为以绝对主体探知客观世界存在本质的文化认同,讲求知识的科学性,精确性。语言自然不扮演一种认识工具的角色,语言本身就是意识的对象,是绝对主体探知的本体。
注释:
①参见《魏晋玄学史》许杭生等著,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P98。
②④《英译者序》安·克芬利,R·奥尔森 见《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罗曼·英加登著,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P11,P9。
③《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罗曼·英加登著,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P18-19。
⑤参阅《当代西方美学》朱狄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89。
⑥(11)《文学的艺术作品》罗曼·英加登著,英译本,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P85,P29。
⑦参阅《英加登的作品结构论与审美价值论》,王岳川,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5期。
⑧《魏晋玄学和文学》孔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P46。
⑨(13)(14)(15)(17)《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28,P26-27,P27,P28,P27。
⑩《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李幼蒸,见《美学》第2期。
(12)《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毛崇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P198。
(16)《庄子·知北游》,见《庄子今注今释》陈鼓应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P580。
(18)参阅《思,史,诗:现象和存在哲学研究》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3。
标签:现象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文学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易经论文; 玄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