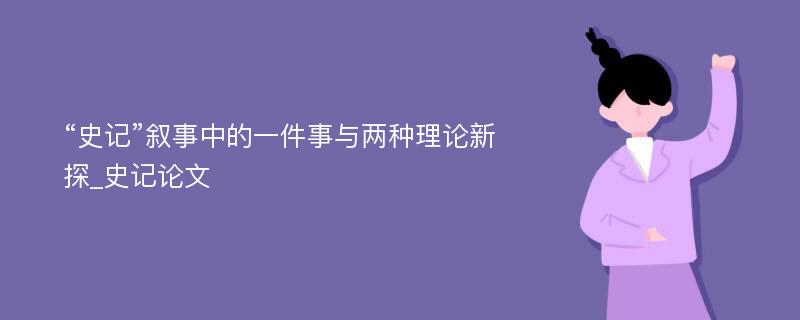
《史记》叙事中的一事并见两说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见两说新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它特定的时空段内,只会发生一次,最终只能有一种结果,照常理也只应有一种符合历史的记载。但历史学家具体记述这一事件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却可能不只存一种记载,从而使这些材料的呈现方式比较复杂。《史记》中就出现了不少一事而并录两说的情况。对此,以班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曾批评其“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① 但是,一事并见两说,作为《史记》叙事行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具体情形远非疏略抵牾这样简单。诚然,班氏之语,是注意到了某些史事记述中的前后不一,但他同时忽视了太史公此种记事方式的深意。若细加揣摩,探本求源,就不难发现,这些前后不同的说法之所以在文中出现,实际上是有着多种情况的。
一 婉约其辞 以明真相
同是对黄帝的记载,《封禅书》中的说法较之于《五帝本纪》中的说法可谓殊多不同,尤其对黄帝之死的描述更是大相径庭。
《封禅书》中引申公言: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且战且学仙,得与神通,并最终骑龙上天的黄帝。
《五帝本纪》中写黄帝之终,却云:
黄帝崩,葬桥山。
言辞间更强调他是一个德泽万世,却也难逃生老病死的人。
《封禅书》中虽然盛推鬼神之异,对神灵怪异之事渲染得浓墨重彩,但太史公最终以“然其效可睹矣”终篇,就足以表明其实属子虚乌有。而既然上古圣王一样也是血肉之躯,那么,秦皇汉武如此地大造舆论、敬天尊神、大举封禅,就实在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意欲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罢了。司马迁曾亲身扈从封禅,对于上至君王、下至方士的这些欺世惑众的伎俩与说辞,可谓“具见其表里”。② 但是,史公毕竟身处汉廷,“先代褒贬,诚无所讳,而于汉时之君相,岂敢放笔直书,明知褒贬乎?”③ 所以,推测这种自相抵牾的说法,应是司马迁在以杂见错出之词,委婉刺讥。余有丁也指出:“太史公论神仙祷祀迂诞之说,极意妆点,皆寓讥武帝且明其不然也。”④ 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中荟萃有诸家评说,众学者于此节虽措辞稍异,但从观点上大都一同此理。
这种暗含深意的一事两说,有的是如上文载于不同篇章中遥相呼应,有的则是在同一篇中便前后互见,彼此异词,使得悬念重重。
对于孝惠帝有无亲子的记述,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太史公先是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⑤、二年(公元前186年)⑥、六年(公元前182年)⑦、七年(公元前181年)⑧ 分别记载了刘怀、刘义、刘武、刘太以孝惠子的身份受封,而后,在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即兴灭诸吕的事变当年,却又说:
非子,诛,国除为郡。
常山王与梁王、淮阳王等就是在这次铲除诸吕的政变中一起丧命。这些皇子们以子封,却以非子诛,直让人如坠五里雾中。
在《吕太后本纪》中亦有这种先后是子又非子的颠来倒去的论定。先言: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字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予武为壶关侯。
……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
据此可推知孝惠后宫有子,只不过孝惠皇后本人无子罢了。但是,在周勃安刘,兴灭诸吕的时节,又云: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
若据诸大臣之言,则孝惠帝根本没有嫡亲的子嗣。少帝与诸王只不过是“他人子”,被扶立仅仅是因为吕后要借以增强吕氏党羽的势力。
史公说法,前后错综,但只要细心对比分析,人们就不难发现一些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指出:“前云美人子,直非吕后子耳。未必非孝惠子也。此直名他人子,是当时深文。”⑨ 柯维琦《史记考要》亦曰:“少帝非张后子,或是后宫所出,亦不可知。史谓大臣阴谋,意少帝毕竟吕氏党,不容不诛耳。”⑩ 梁玉绳也赞同这种观点,并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公于《纪》两书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诛’,皆有微意存焉,非歧说也。”(11)
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从通篇的语境看,诸王和少帝确实极有可能就是孝惠帝亲子。诸大臣之有此言,只不过是决心要对吕氏斩草除根的同时,怀疑这几位王子也是吕氏党羽。而且,扶立新君,拥戴之功,也能更方便他们日后的飞黄腾达。是此,“非真孝惠子”,只不过是挥起屠刀前的欲加之罪。而就在这一借口下,在新皇入朝听政的当夜,这些人便对孝惠帝的子嗣展开了血腥的杀戮,“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12)
非子之诛,在刘汉王朝是已成定论的说法,尽管太史公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也仍然不得不依样录入。但是,正如韩兆琦所说:“他不甘心让历史这样地欺骗后人,故而在《史记》的几篇之间,甚至在同一篇里有意地参错其词,留着一些明显的疑窦,让后代细心的读者自己明白其底蕴。”(13) 观史公于《匈奴列传》赞中感叹:“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4) 这是他在感慨当年孔子的无奈,可以说,也是在感慨时下自己的悲哀。迫于现实政治的压力,一些时候,太史公自己也不得不隐寓而微其词,“此等处需痛自理会,方能识得真景”。(15)
二 假托叙事 为得其情
“三年不蜚不鸣”的隐喻在《史记》中两度出现,但时间、地点、人物各自不同。在《楚世家》中曰: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
在《滑稽列传》中却又云: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讽喻庄王之说又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16),但讽齐威王之说则未知何据。对于这种前后相左的记述,有的学者从《史记》中年代记述混乱的事实出发,批评史公:“前后彼此一任错综”。(17) 邵泰衢《史记疑问》曰:“齐威元年后于楚庄元年二百三十二年。淳于乃齐威之臣,优孟谓楚庄之人,《滑稽传》云:‘淳于髡后百余年有优孟,优孟以谈笑谏楚庄王’。是以齐威而反前楚庄矣夫?”(18)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从揣摩史公笔法的角度出发,推断其说是暗含深意。在《史记会注考证》中,泷川资言就引徐孚远之语,曰:“楚庄、齐威,皆有雄畧,故先纵乐以观群臣,大鸟之喻,为得其情也。”(19)
从具体情节分析,这是一个激励一代明主振作奋起的重要隐喻,在性质上它不同于行文中的细枝末节,在文中的不同场景下竟前后出现两次,照常理推测,史公不会全无所觉。而且,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史公已明确交代,“楚庄王侣元年”是在“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而“齐威王因元年”已经到了“周安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78年)。那么,楚庄王在位当早于齐威王二百余年。但在《滑稽列传》中,楚庄王反而晚于齐威王。一代霸主的起讫年代上下竟出现了几百年的偏差,照理史公亦不会全无所察。是此,这种抵牾便可以基本排除主观疏略的可能,既非疏略,便是有意为之。
设若再从叙事手法上分析,徐孚远所言的假托叙事,为得其情的处理,在古代载籍中也确实时有所见。就连《李将军列传》中记述李广射术之精,“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也有学者推断是一种未必信实有证的比附,而事件的真正原型当为《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养由基。《史记会注考证》中就引何焯语,曰:“《吕览·精通篇》云:‘养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饮羽。’诚乎虎也,与此相类。岂世因广之善射,造为此事以加之与?”(20) 李笠也认为这是为了“夸张术艺之精,初非信有其事也”(21),并进而从书法叙例的高度总结:“史贵翔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谲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22) 观《滑稽列传》,其戏谑调笑与其他篇章的雄浑酣畅相比,的确是一部风格特异的迥出之篇,就连学者钱大昕于此也指出:“此传之言,多不足信”。(23)
综合分析这两种意见,当是喻事假托之说较为合理。淳于髡一节,太史公很可能只是纯用赋笔。正如学者吴见思所说:“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嬉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24)
三 信以传信 疑以传疑
《孟子荀卿列传》中有: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齐太公世家》中有: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这样的一事两说的材料,从行文上看,很明显是作者有意留存下来的,司马迁分析这种处理是闻疑传疑。(25) 这种疑者传疑的传统,又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孔子时,这种方法就曾经被提倡和使用。《论语·为政》: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26) 《史记·三代世表》中太史公也提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显见,太史公对孔子的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极为推崇的。于是,在孔子卒后500年,太史公再次发扬了这种“多闻阙疑”的精神,对无从详知和难以判断的材料,进行了疑者传疑的处理。
何焯《义门读书记》云:“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分析指出,《史记》中叙事不同,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来源不同,太史公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27) 显见,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史记》叙事中的这一重要特点,同时多数学者也都对太史公的这种处理给予了肯定。
年代久远,传闻异辞,难免会歧说并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支持,考辨真伪的工作便很难进行。没有一位史家不想在历史撰述中给后人留下一个确切的说法,但牵强地别裁去取,未必得当,搞不好,还会曲解历史,贻害无穷。所以,“历史上有若干不能解决之问题,指出其不能解决,便是解决”。(28) 太史公的“盖”、“或曰”等这些不确定的字眼虽然给后人留下的是不确定的答案,但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中一种最负责任的做法。将委实难决的材料照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来,留待后人研讨,这不仅表现了采编史料应有的严谨性,更表现了一位史家求真的精神和超凡的勇气。
在《史记》中还有些一事两说的材料,虽然并没有鲜明地表明作者有意存疑的态度,但是,我们从它们与现存古籍的对读比较中推测,很可能也是史公难以决断,故两言之。
如:对于春秋末年“吴晋争长”这一历史事件,《史记》中就存在着“长吴”与“长晋”两种不同的说法。
于《晋世家》曰: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此说同于《国语》(29)。
于《吴太伯世家》又曰:
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此说同于《左传》(30)。
既是两君争长,自当有一胜一负,或长吴,或长晋,历史现实中绝不会是两种结果并存。但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却偏偏就是各执一词,一说“长吴”,一说“长晋”。《左传》与《国语》中的这些相应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史记》中这种前后不同的说法并不是史公疏忽间造成的抵牾,它们都有依据,只是各自依据的材料说法不同。设若大胆推测,可能是因为没有更可靠的材料支持做进一步的判断,故而吴晋争长之事,才胜负难分。“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31),在难以取舍的情况下,太史公最终选择了这种两说并存。
韩非使秦之事,《秦本纪》和《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也颇有出入。于《老子韩非列传》曰:
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
于《秦始皇本纪》却云:
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
这两种说法,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可供对读的文献证据,但是也有学者推断,这是史公杂采秦、韩两国史记,疑以传疑。徐孚远就曾提出:“韩非弱秦,即李斯谮非之辞载于秦史记。”(32) 此说虽无确凿的证据,还是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设若联系韩非亡于秦国的悲惨结局,联系李斯与韩非的微妙关系,从情理上推测,这种分析与解释也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
以往的学者,著书叙事之间常常有自己特殊的凡例义法,而后来的读者,如果不能明白这些叙事方法,就往往会感到扞格难入,不解其意。学者靳德峻正是有感于此(33),才著《史记释例》,专门探究太史公义法,并强调:“不知厥例,何以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不知史公之史法与史意,何以究史公之史学乎?”(34) 史公著书,多微文见意,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在研究《史记》时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史记》中那些有文献证据乃至没有文献证据(尤其是没有文献证据)的一事两说,都是太史公有意为之的匠心安排。像《吴世家》、《楚世家》中对边民争桑引起两国交兵的记载:一说是“楚边邑卑梁”(35),一说是“吴之边邑卑梁”(36),就很难说是因为史公依据了不同的记载,从而才有不同的说法;还是因为史公在吴、楚两国的边界问题上本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从而导致了不应有的抵牾疏略。而且,《史记》中像这样的一事两说的材料还有一些,如《武帝本纪》中,尧、舜时期流四凶的不同说法;《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中,对吕不韦献赵姬时赵姬是否有孕的不同记载;《殷本纪》和《周本纪》中,对纣囚西伯于羑里的不同记述,等等。虽也有学者推测其可能是太史公主观上有意为之,但是在没有进一步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史公疏漏的可能。毕竟,《史记》一书,洋洋五十余万言,上下贯通两千余载,所钩稽参考的材料林林总总、错综繁杂,采录中难免会有错漏重出的地方。正如班彪《略论》所言:“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
诚然,太史公之书法,义旨深远,寄兴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义起子彼,有若鱼龙之变化”。(37) 我们推崇史公的书法义例,本无可厚非,但因爱史公之甚,就为之牵强附会,巧为弥缝,却是不可取的。与之相对,像有的学者,对材料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问题,不假思索揣摩便穷究责难,我们亦应引以为戒。(38) 正如学者刘知幾所言,我们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39),而面对《史记》行文中的这一重要特点,我们也只有态度公允,平心静气,既不偏爱护短,又不穷究责难,认真研读,细心体会,才能深刻认识《史记》行文中的这一重要特点,才能真正领悟太史公所欲撰著的“一家之言”。
注释:
①《汉书》卷62《司马迁传》。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
③ 靳德峻:《史记释例》,商务印书馆,1933,第18页。
④ 茅坤:《史记钞》卷40《封禅书》,明泰昌元年西吴闵氏刻本,第7~8页。
⑤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元年:“四月辛卯,初王怀王强元年。强,惠帝子。”
⑥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二年:“七月癸巳,初王义元年。(皇子)哀王弟。义,孝惠子。故襄城侯,[后]立为帝。”
⑦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六年:“初王武元年。武,孝惠帝子。”
⑧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后七年:“(七)〔二〕月丁巳,王太元年。惠帝子。”
⑨ 吴见思:《史记论文》第一册卷九,广益书局,1936,第11页。
⑩ 凌稚隆:《史记评林》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第183页。
(11)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第250~251页。
(12) 《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
(13) 韩兆琦:《(史记)书法释例》,《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4)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5) 茅坤语,见《史记钞》,载《史记读法》卷首,明泰昌元年西吴闵氏刻本,第5页。
(16) 《吕氏春秋·重言篇》:“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因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榖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榖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榖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166页。
(17) 邵泰衢语,见《史记疑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48册,第726页。
(18) 邵泰衢:《史记疑问》,第726页。
(19) 泷川资言(撰),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004页。
(20)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780页。
(21) 李笠:《史记订补·叙例》,载《广史记订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5页。
(22) 《史记订补·叙例》,第5页。
(2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史记考异》,载《钱大昕全集》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6页。
(24) 《史记论文》第4册,卷126,第12页。
(25) 《史记索隐》:“太史公闻疑传疑,事难的据,欲使两存。”见《史记》卷86《刺客列传》。
(26)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第2462页。
(27) 张守节:《史记正义》,见《史记》卷3《殷本纪》。
(28) 傅斯年致胡适信中之语,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第58页。
(29) 《国语·吴语》:“晋乃命董褐复命曰:‘寡君未敢观兵身见,使褐复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请贞于阳卜,收文、武之诸侯……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许诺。”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613页。
(30) 《左传·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见《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2171页。
(31) 刘知幾语,见《史通·采撰》,载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17页。
(32) 转引自李笠《史记订补·叙例·抵牾例》条下,载《广史记订补》,第3页。
(33) 靳德峻:《史记释例,序》曰:“往哲造书,各具其例。后之读者,不达于此,每致扞格。”见《史记释例》,商务印书馆,1933,第1页。
(34) 见《史记释例·序》。
(35) 参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36) 参见《史记·楚世家》:“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37) 吕祖谦语,见凌稚隆《读史总评》,载《史记评林》第1册,第151页。
(38) 例如王若虚的《滹南集·史记辨惑》中,对《史记》分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接、姓名冗复、字语冗复、重叠载事、疑误、杂辨等十类,穷就责难,多为学者所不取。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册。
(39) 刘知幾之语,见《史通·惑经》。
标签:史记论文; 太史公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读书论文; 封禅书论文; 国语论文; 滑稽列传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黄帝论文; 西汉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