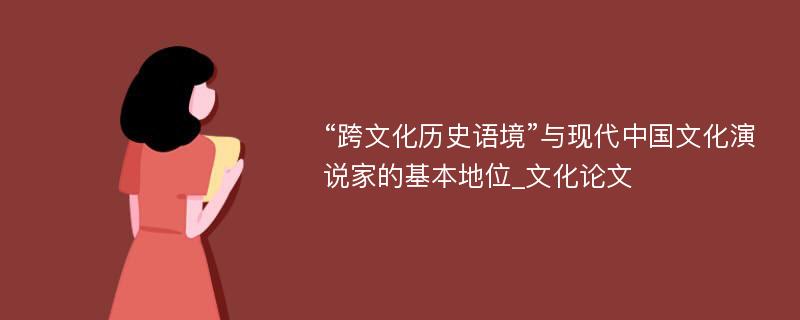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当今论文,跨文化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已呈现不同的出发点。但这些出发点都没有使我们摆脱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情感上认同于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式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理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注:转引自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2000年5月版。)于是情感在徘徊莫知所之中郁积,对自家的历史或由爱走向溺爱,走向“中国文化本位论”,或由爱及恨,走向“全盘西化论”,不过两者都用情感的强度遮蔽了理性的批判。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和超越这种格局呢?本文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需要大家理性考量才能确定其意义的视角,这就是:过去150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跨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历史语境?如果历史语境对于置身其中的任何因素具有规定其意义、配置其空间、塑形其发展模式、施加左右其发展方向的力的功能的话,那么弄清楚中国文化卷入其中的这个文化历史语境,就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中国意识的危机
那么,1840年迄今,中国文化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历史语境呢?为了不在表面上兜圈子,让我们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所遇到的三个“话语事件”的个案分析开始,以便昭示出这个历史语境及其意义。
第一“话语事件”个案涉及到研究过去150年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被广泛征引的一个经验模式。这个经验模式认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佛教的传入是第一次,“五·四”前后遭遇西方文化是第二次。第一次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撞击曾经引起了中国文化的变化,经过漫长的磨合,佛教才在本土被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五·四”前后中国遭遇西方文化,也应该如同佛教进入中国一样,有一个缓慢的中国化的过程。例如,王元化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就说,“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如果参照第一次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注: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72-274页。)
细致考察的话,这个广被征引的解释模式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它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和“五四”前后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这次相遇当作是同质的,仿佛不存在根本的差别,所以前者完全可以挪用来理解和指导后者。其二,由于佛教传入中国虽然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本土文化的结构,中国本土文化完全是以一个主位文化的身份,来消化、修改和融化佛教这个异文化“他者”。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感到佛教的异己性质过大时,还可以主动地进行“回吐”,因此,这第一次遭遇的经验是一个隐蔽的“中体西用”经典模式。这样,将前一种经验模式无差别地挪用来解释第二次经验,其实就是将“五四”前后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遭遇历史隐蔽地置于“中体西用”的模式之下。其三,在这一解释模式的挪用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设定,这就是“五四”前后西方近代文化的涌入,仍然和佛教传入中国一样,最终异文化的东西只是具有词汇的意义,只能丰富中国文化的词汇,而不会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语法,因此,对异文化的东西进行收编、规划和做出阐释的最终权能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结构。但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显然,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验与“五四”前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的历史对等看待,是一种简单地“史鉴模式”的挪用。这两次经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没有必要重述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震荡、崩解和普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这已是普遍的看法。那么,在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遭遇中,传统中国文化还能保持本位地位、把西方文化的冲击控制在词汇的水平并最终加以融合吗?这里,我认为列文森的观点是深刻的。按照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观点,“……只是通过思想上的渗透彼此才互相影响的欧洲和前近代中国,仅仅扩大了它们各自的文化词汇,只是到了19和20世纪,当西方对中国进行社会颠覆,而不是思想渗透时,中国的文化语言才发生变化。”(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1-372页。)列文森认为,自1550年到1840年,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都是在利马窦所主张的“合儒、补儒和超儒”的模式下进行的,因此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并没有使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改变,却丰富了中国本土的词汇,也就是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的部分科学知识被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融解进了自身语法规范之中。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局面改变了,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开始被离析,被离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成了词汇,而外来的异文化却成了进行意义阐释和作出规定的语法。以前是用自己本土的语法和语言的结构来消化外来的文化,现在,自己变成了词汇,外来的文化却变成了语法和结构,言说的合法性和理据是异文化的东西。(注:参见上书第一卷“结语”。)这一深刻的变化,其实我们可以在过去100年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不断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支持这一典型的方面,看得更为清楚。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19世纪末开始,传统中国本土文化作为一种言说世界的话语体系的完整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被打碎,成了碎片,就像倾颓的建筑物所留下的断砖残瓦,建筑物已经不在,这些断砖残瓦已经不再按照建筑物的原有结构而具有意义。如果这些断砖残瓦不能在新的语言中获得重新规定,它们将真正地死亡;如果它们有复活的机会,那就得让新语法来重新配置它们。正是在此意义上,佛教东传的经验模式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中国与异文化的遭遇,因为这次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被裂解成了词汇,而进行词汇解释和配置的是一个新的历史语境。
看到这幅图景,许多人或许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抱一种悲观的看法了。但问题在于,如果传统文化不裂解成词汇,中国文化发展的重新整合就没有机会。如果传统文化的裂解是发展的机会而不是死亡,那就要看如何进行整合了。那么,被裂解成词汇的传统中国本土文化,其被重新阐释、重新整合的新的语法,真是如列文森所说的西方文化吗?让我们来思考另一个案。
第二个“话语事件”涉及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遭遇中不断被问及的一系列问题。20世纪中国在与西方文化的遭遇中,不断地从自身内部产生一系列根本性的自我质询:“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美学?”“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有没有知识分子?”“中国有没有思想家?”“中国有没有真正的逻辑学?”“中国有没有发展出市民社会?”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有些人企图通过揭示这些问题背后的“西方标准”和“西方话语霸权”,来解构这些问题;有些人则企图从逻辑上证明这些问题为虚假问题而使其消失。我们先不管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分析这些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些自我质询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特点:相对于某种“标准”,中国本土文化在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方面有所亏欠或不足。这是中国本土文化在进入新的语境系统时在自身内部所产生的“文化悬欠”。如果不是用新语言来言说传统中国,那在传统的本土文化封闭的系统内中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文化悬欠”呢?原因在于,当本土的言说者用新的话语结构和语法来言说的时候,新的语法结构所阐释出的“意义空间”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恰当的配置,寻找不到充足的对应语义,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虽然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中能找到相对应的某些词汇或事实,但本土文化资源的这些词汇和事实相对于新语法所阐释的“意义空间”却过于狭窄,当把这个狭隘的“意义”填到新的文化结构所阐释的“意义空间”中的时候,就会出现“填充不足”的现象。这就像给小孩穿上大人的衣服一样。如果我们把异文化“他者”的文化结构所阐释出的“意义空间”作为“能指”的话,那么这个能指在本土资源中获得明确的意义匹配就是“所指”。当本土的文化资源所提供的意义匹配不能满足新的语境所提供的能指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所指亏欠”,或叫做“文化悬欠”。从上面列举的的问题所涉及的面和问题的重要性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目前所面临的“文化悬欠”是惊人的。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惊人的“文化悬欠”呢?不可否认,在这种“文化悬欠”产生背后有一个异文化“他者标准”,比如,西方近代发展出了西方形态的“完备的”哲学、美学、逻辑学、知识分子等,将此质之于中国本土文化,才能阐释出中国有没有哲学、美学、逻辑学、知识分子等问题。这里确实存在一个西方制定标准并用以责问本土文化有没有按照这些标准所具有的东西的“话语霸权”,而且在这种“责问”中,必然会得出一个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矮人政策”(注: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01页。)的逻辑。所以,用解构的策略把对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构成参照性阐释的异文化“他者”消解掉,看来是一种选择了。但是同样显然的是,在这种对异文化“他者”标准的拒斥中,不仅存在着对自家本土文化的凝滞性执著,而且把异文化“他者”与本土文化纳入到了“非此即彼”的对立格局中。这种态度不仅是对阐释的拒绝,也扼杀了由异文化“他者”进行参照性阐释时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发展可能性意义拓展。
我们已经强调过,如上这些“文化悬欠”只有在异文化“他者”的参照下,才能被阐释出来,在本土文化的原有结构中不可能阐释出这些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与异文化“他者”的这次遭遇形成了一个深具阐释力的构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个制造“文化悬欠”的构架的话,就会发现,在异文化“他者”的参照性阐释下,相对于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来说,由于它不能提供“完备的”本土语义来填充异文化所彰显的能指,所以出现了“语义填充不足”;但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这些“文化悬欠”却拓展出了中国文化当今发展的“可能性意义空间”。简略表述就是,相对于本土的过去阐释出的是“文化悬欠”,相对于本土文化发展阐释出的却是“可能性意义空间”的拓展。那么,这即表示,如果本土文化仍然处于自身的封闭状态,就既不会有“文化悬欠”问题,当然也就不会阐释出其发展的“可能性意义空间”。至此,我们的分析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与异文化“他者”的遭遇虽然摧毁了传统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结构,但同时这种相遇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发展进行“可能性意义空间”拓展的阐释学历史语境,在这种相遇的阐释学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文化悬欠”既阐释出了本土原有的不足,形成了有待跨越的距离,又拓展了发展的“可能性意义空间”,以便促使本土达致意义的完足。因此,在这个进行“可能性意义空间”拓展的阐释学历史语境中,异文化“他者”的到场是这个语境构成的必要条件。
那么,在这个历史语境中异文化“他者”是否是“标准制定者”,而它就不受这个语境的约束吗?让我们进入第三个“话语事件”的个案分析。这个“话语事件”涉及到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现代中国教育和学术中的设立问题。让我们仍从广被引征的一段话开始:“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至于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注:《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71、39页。)这是王国维1903年在《哲学辨惑》中表达的思想。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可决也。”(注:《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71、39页。)前段话之所以广为引证,是因为它以极富洞察力的方式敏锐地揭示了20世纪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境遇:中国文化与异文化“他者”之间的相互激荡。但是,许多引征这段话的人都没有计较这里的思想是基于在中国设立哲学学科的问题而发的。
王国维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到当时中国新式教育所创办的大学中是否设立哲学科的问题。当时朝廷主事之人在《奏定学校章程》中,主张大学的经学科和文学科均不设哲学,而设“经学”“理学”,并以“经学”当西方的神学。王国维以为不当,他援引的理据主要是西方和日本大学的学科设置,但在他的学理逻辑中,是明显地认为西洋有彼土之哲学,中国也有哲学,即诸子哲学和宋以后的理学,甚至他认为“六经”也是哲学,因此不该把经学与西方的神学对等而设立独立之经学,经学学科应该合并在文学科名下。不过,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却没有独立的经学和理学,而是把它们统在了“中国哲学史”这一科目的名下。就对哲学本身的认识而言,他不仅认为哲学“必博稽众说而唯真理是从”,而且认为如果必须讨论人生问题,哲学就是学问中必然设立之学科。虽然王国维知道“哲学”这个词是从西方而来的,但在他的思理中,“哲学”并不是西方的,而是解释“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的学问,这个学问西方有,中国也有。在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他谈到了佛教东传和19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的最初影响,认为“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同时他主张“学无中西”,认为“思想上之事”不能“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一面毋以为政治之手段”,才“可有发达之日”。(注:《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71、39页。)显然,王国维在1903年前后就超越了“彼”“此”的对立,把“哲学”作为“自由研究”、解释“宇宙人生上根本之问题”的学问来设定了。
考虑到经学、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尊地位,王国维之在20世纪初就力主设立哲学,并把经学、理学统在哲学门下,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阐释行为,它关涉的不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学科设置问题,而且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经学、理学的核心地位被降低成了哲学的局部。据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京师大学堂这个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就有专门的“经科”,而且每一种经都有一个学门,如“尚书门”、“毛诗门”等。到1915年,由京师大学堂而来的北京大学就已经将“经科”废了,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了文科各门课程中去了。(注: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301页。)这说明王国维关于设立哲学学科的“话语事件”已经转变为“历史事件”了。这个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的结构如何衰退、而新的元素如何占据核心的整合过程。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王国维能够突破传统中国文化原有结构的凝固力,阐释出本土原本没有而现在被他置于核心位置的哲学学科,并把原来居于至尊地位的经学、理学贬低为哲学的局部而使它们边缘化呢?显然,如果没有西学的启迪和发明,王国维不可能在本土设立哲学,更不可能在“经学”独尊的本土文化中发明出哲学层面;同样,如果他只是执著于模仿西学,那他就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而不是一个否定神学、主张“学无中西”论者。就他主张“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看,他洞察到了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进行阐释和拓展的力量;就他主张“学无中西”看,他既不是后来的“全盘西化”者,也不是一个“中体西用”者。因此,可以说,王国维走入了一个既不脱离中西、又不将两者对立起来,既不胶着于西方话语场所、又不胶着于本土话语场所,但又将本土与异文化“他者”纳入交互参照、相互发明的“间性话语场所”。我们把这个“间性话语场所”称作“跨文化历史语境”。正是这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以及这个历史语境的话语阐释逻辑,不仅使他设置出了作为独立学问的哲学(当然也包括美学),也使他按照这个更大的历史语境重新配置了原来处于核心位置的经学、理学。中国本土文化的原有结构也因此而彻底改变。王国维敏锐地洞察到19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所陷入其中的新的历史语境:在与异文化“他者”的相互激荡、相互发明中来发展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在这个历史语境中,既不遵从西方的话语逻辑,也不遵从本土文化原有结构的逻辑,而是要遵从与异文化“他者”所建立的关系逻辑,并在这种关系中发展独立的、不做种族、国家、宗教之工具的自由学术。
从以上三个个案分析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佛教东传的模式中,中国本土文化是以本位地位吸收佛教并最终使其中国化了,佛教在东土的地位是由中国本土文化阐释和配置的,并丰富了中国文化的词汇。因此它是一个“轴心时代”的事件。但是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与异文化“他者”尤其是西方的相遇,却裂解了本土文化的完整结构和本位地位,使其降低为词汇并受一个比本土“轴心话语”更大的历史语境的阐释、配置和编码,这个更大的历史语境就是“跨文化历史语境”。“跨文化历史语境”是以两个或多个异文化“他者”以主体而不是客位的身份同时在场为构成条件的,因此,它对任何卷入其中的文化体进行的是跨文化的阐释、配置和可能性意义空间拓展。
“跨文化历史语境”的基本底蕴
“跨文化历史语境”是在崩解“轴心话语”中诞生的。在“轴心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体各自独立,相互隔绝,这种孤立和隔绝的状态,不仅是地理学的,而且也是精神和心理气质上的,为了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或维护自身信仰的“神”的尊严,一个文化体会对任何“他者”保持自身的封闭,并且拒斥任何异文化“他者”进入自身的世界。如果我们把每个文化体都看做是一种言说世界的方式的话,那么,“轴心时代”不同文化体言说世界的主要方式是一种隔绝和封闭中的“独白”,而不是在“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言说世界。但是,16、17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探险家和商人踏上异文化的疆界,并在那里遭遇“他者”时,“轴心时代”就开始告别,“跨文化历史语境”就拉开了历史帷幕。到19世纪,“跨文化历史语境”可以说已经把整个全球都卷入了其中,它彻底打破了“轴心时代”的格局和每种文化体言说世界的独立性,使得任何独立的文化体要保持自身言说世界的封闭性都已经不可能了,历史进入了一个“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时期。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彻底且无法规避地卷入到了“跨文化历史语境”。那么“跨文化历史语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意味着“轴心时代”各自独立、相互隔绝的文化体在自身范围内言说世界的“独白式语言”的终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每个原来独立的、封闭的文化体都会遇到一个或多个异文化“他者”,这些“他者”不再能够按照一个“轴心话语”的封闭性被置于其言说世界的范围之外,而是打破隔绝和封闭,以主体身份侵入到了原本隶属于“你”的本土领地,这些“他者”构成了“你”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你”不仅不能摆脱它们,甚至“你”还得聆听这些“他者”的言说。也就是说,在“轴心时代”,异文化“他者”可以被置于“客位”,并受“本位”文化的支配,但在“跨文化语境”中,任何进入此语境的异文化“他者”都具有主体的身份。对异文化“他者”的主体身份,中国现代文化的言说者直到现在还不能理智地接受,因此也就不能理智地与其交往。
其次,在这个总是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文化发展的语境彻底改变了,即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交流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跨文化历史语境”是一个更为开放的语境,它不再追求各自封闭、相互隔绝的文化主题,而是在“你”与“他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即歌德所说的“世界”——一个“间性领域”。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每一种文化必须充分参与到对这个“世界”主题或世界性道路的言说中,同时,一个民族之文化身份和根基的确认不再是根据某个单一文化或“轴心话语”,而是通过参与“世界”主题和道路的建构来为自身的文化身份塑形。也就是说,“跨文化历史语境”对任何卷入其中的文化体的配置、阐释和配置是在强行与异文化“他者”主体的参照中进行的,这就使任何卷入其中的文化体要保持本土的原有模式和连续性成为不可能,一个文化体的身份确认必须在“跨文化语境”的解释、配置和编码中重新建构。任何文化体如果仍然企图通过固守本土文化的本位地位来建构其新的文化身份,都将面临尴尬的命运,因为它将自身的生存设置在了过去,并因这种活在过去而自行放弃了自身的现存历史,即把自身革除在了正在进行中的历史之外。
其三,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一方面,每一种文化都会感到自己的文化疆界扩大了,原来属于“他者”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自己的传统的一部分,成了“你”可以随手取用的资源;另一方面,“你”自身本土文化的唯一性、神圣性和作为“中心”的地位却降低了,那些在“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本土资源面临着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老子也在德国现代思想界获得新的生命;而儒家在杜维明先生关于儒学复兴的设计中获得了世界性的配置和阐释。
其四,如果任何文化都承担着对历史之可能性道路和空间的开启——“问道”使命的话,那么,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这种对“历史之可能性道路和空间的开启”,就不能在封闭的、狭隘的环境中进行,而是在这个开放的、充满竞争和冲突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在“轴心时代”,一个民族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竞争,走孤立存在的道路。但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你”必然遇到异文化“他者”主体,当然异文化的“他者”也必然遭遇作为异文化主体的“你”,“你”与异文化“他者”共存在,走封闭孤立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你”与异文化“他者”之间有交流和融合,但也有竞争和冲突。因此,“跨文化历史语境”是一个竞争的历史语境,交流和竞争、融合和冲突是其基本主题。
其五,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任何文化的发展的立足点都不能简单地放在“传统根基”上,而必须放在“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上,是对“问题的追问”引导人们前进,引导人们探求一种道路,而不是用“传统的神圣”来限定或规范其道路。这样,原来属于“他者”的资源才能被剔除掉其“异己”身份,而被整合于“对问题追问”的公共领域;同时,本土文化资源的“地域局限”也会因“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而被打破,被提升到“世界”的公共领域,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并对世界发言。这样,“对问题追问的优先性”原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间性领域”,一个在话语层面的“边缘结合带”,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边缘人”。生活并植根于这“间性领域”或“边缘结合带”,成了“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要经验。表面上看,这是以失去本土“文化根基”和精神上的流放为代价的,实际上失去的不过是原有“轴心”的封闭性根基的唯一性或单一性而已,而真正获得的不仅包括自身文化疆界的无限扩大,而且使原有自身封闭性根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得以重新释义、规定和配置。正是在这样的“边缘结合带”,近代德国从温克尔曼到19世纪的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和尼采,都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扩展到了古希腊,认为自己是古希腊精神的“后裔”,但成就的却是一个个真正的德国现代思想家和诗人。同样,被称做“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鲁迅先生,也处在这样的“边缘结合带”,这也不妨碍他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总之,“轴心时代”结束之后,历史进入了“跨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语境”,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相互遭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普遍的、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参照和对话的关系”。就不同文化之间“交互参照和对话”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它以历史的具体存在确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和相互“交集”;另一方面,这种“交互参照和对话关系”,又折射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因此,“跨文化历史语境”是比“轴心话语”更巨大的、视野更广阔的意义阐释的话语场所。巴赫金在描述16世纪欧洲复杂的语言交流时曾说:“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便发生在这个阶段。两种语言直率地、热烈地凝视着对方的面孔,每一种语言都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和局限。”(注:转引自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6页。要说明的是,刘禾教授在引述巴赫金的这段话时,并不同意巴赫金所描述的情况完全可以被用来描述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化的“跨语际实践”,因为此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跨语际实践”“绝大多数是单向的”。而我认为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中国此时期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应该说,自1841年林则徐责成魏源编撰《海国图志》开始,中国文化就卷入到了这个与异文化“他者”之间“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相互凝视着对方面孔”,并“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和局限”的“跨文化历史语境”之中。
结论: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立场
如果我们承认自《海国图志》以后,“跨文化历史语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历史河床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化受这个历史语境的巨大牵引、规范和模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表述出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应采取的基本立场:
第一,自觉地完成从凝滞于自家传统的“轴心话语”立场向“跨文化历史语境”的开放立场的转变,在“跨文化历史语境”的牵引下拓展和阐释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可能性意义空间”,有效地克服“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近一个世纪来,我们始终力图克服“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却未果,这主要是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附着于本土文化的“轴心话语”这块故土上不忍离去,也就进入和获得不了“跨文化历史语境”的超越视野。“全盘西化”论其根底也是对“轴心话语”的附着,只是其立足点从本土转向了单一的“彼方”而已。
第二,对“跨文化历史语境”所包蕴的“主体间性”和阐释学对话关系做深湛的理解,以超越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西方挑战中国应战”的“极性”的思维模式,把本土和异文化“他者”均纳入到“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学对话中。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跨文化历史语境”中的“主体间性”和阐释学的对话关系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现实是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我的思考是,只要一个民族不被消灭,他的存在就使他具有与其他民族同样的自由主体地位。因此,问题不在于谁拥有“话语霸权”的强势,而在于该民族是否发挥了他的自由主体地位而不被遮蔽或自愿放弃。此间需要的是智慧、创造力和勇气。
第三,过去150年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巨大而急速的牵引下,经历的主要是传统崩解的痛苦和精神迷失,由于各种力量的掣肘,“跨文化历史语境”所具有的重新解释、重新配置和重新编码的“可能性意义空间”的拓展功能并没有被我们自觉地完全发挥出来,这样,中国现代文化面临着如何将这150年来积累的资源与传统本土文化的资源整合起来的艰巨任务,也面临着重建文化身份的课题。可惜的是,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重归传统的“轴心话语”才是民族文化身份重建的归路。在此种道路的选择中,隐蔽地存在着这样一种自欺的心理,这就是把“跨文化历史语境”当作别人强加的历史,就像过去150多年来中国所经历的耻辱一样。但这种选择恰恰将自身革除在了正在进行的“跨文化历史语境”之外。这种自我革除所导致的结果是双重失利,即既不能维系传统的“轴心话语”的“本位”地位,也丧失了主动参与“跨文化语境”的主体地位,使自己被牵着鼻子走。
第四,应该清楚地看到,传统中国的本土文化要获得现代意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有效资源,并支持而不是阻碍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那它就必须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方能获得新的意义,也才能摆脱其狭隘的地域性,才能走向世界。在此,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保持警惕。
标签:文化论文; 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跨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王国维论文; 经学论文; 轴心时代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