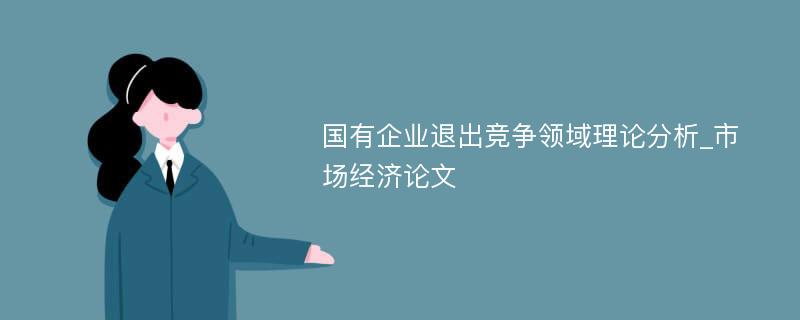
“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性论文,国有企业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主张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声音不绝于耳。即便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鼓噪声依然此起彼伏。究竟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应不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本文拟对此热点问题略述己见。 一、“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论”违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正确认识国有企业该不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必须以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为指导和前提,背离了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不利于坚持和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 公有制为主体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主要体现在相对量上。从相对量的角度看,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例在50%以上,才说得上占优势。然而,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8年年末,在全国二三产业中,企业总资产为207.8万亿元,其中,公有制企业资产仅占32.8%,国有企业的资产占比为30%。这表明在二三产业中,公有资产早已不占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部分丧失,其主体地位已受到严重削弱和威胁。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与国有资产的质量和数量有着密切关联。衡量一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既要看其质,也要看其量,应把质与量统一起来看待。量与质比较,质居第一位,但量也不能忽视。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而质变又会带来量变。对于国有经济的量,不能只看绝对量,还要看相对量,即看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如果只是绝对量增长,而比重却下降了,这就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增长得更快,国有经济的实际地位降低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掌握控制经济命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国有资产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越大、质量越高,其控制力、影响力和主导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因此,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其中自然包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 公有制为主体,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正是基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考虑,党中央才一直把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作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背离了这个前提条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会走到私有化的邪路上去。因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是整个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公有制经济最主要部分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无疑会极大地削弱公有制经济的整体实力,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可见,“退出论”严重违背基本经济制度,因而是极其错误的。 (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不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定位为“共同发展”,而“退出论”则是为了遏制国有经济的发展。从基本经济制度所强调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来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并行不悖、共生共存共荣的“共同发展”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你退我进的敌对关系。在竞争性领域,既应允许、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发展壮大,更应允许和支持国有经济做大做强、发展壮大。 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有赢利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赢利水平越高,发展就越快。竞争性领域是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事实上,在我国竞争性领域,有不少优势国有名牌企业,其发展成长势头强劲,让这些发展得很好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国有企业是否退出竞争性领域,应由市场说了算,绝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如果像“退出论”主张者说的那样,让国有企业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专注于非营利或微利的公益性领域,那么,国有经济如何才能发展壮大?如何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说穿了,“退出论”只不过是私有化主张的代名词,分明是只让私有经济发展,而不让国有经济发展,从而相对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显然是与基本经济制度背道而驰。 (三)“退出论”与西方国家摧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图谋不谋而合 目前,在我国的县域经济中,国有企业早已所剩无几,与民营经济不成比例。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有所壮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略有上升;另外,国家出于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类尤其是煤炭资源类企业进行整合,迫使一些浪费破坏资源的小型资源类民营企业退出战略资源类行业,这实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明智之举,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国退民进”之争的背后,实质上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博弈,是私有化主张与反私有化主张的搏杀。显然,无论“退出论”主张者承认与否,“退出论”都带有明显的维护私有经济利益的目的。在“退出论”主张者中,不乏对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感兴趣而仅仅对发展私有经济情有独钟者,甚至不乏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私有化主张者。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对“退出论”主张者的真实目的也就不难把握了。很明显,“退出论”主张者仅仅维护的是私有经济的利益,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这与某些西方国家妖魔化公有制、必欲置我国公有制经济于死地的战略图谋不谋而合。关于西方国家企图毁灭我国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毫不掩饰地说:“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那些力主国有经济退出全部竞争性领域的鼓噪声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西方国家销蚀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战略图谋遥相呼应,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二、“退出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规律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它不存在任何偏见,而是接纳所有竞争性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无论企业的性质如何,皆可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规律的开放性源于市场的开放性,是市场经济活力之源,一旦丧失了这种开放性,市场经济的活力就会大打折扣。让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明显是一种所有制歧视,是要将国有企业屏蔽于竞争性领域之外,这无疑与市场竞争规律的开放性乃至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悖。 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市场竞争规律,一些企业被淘汰应是一个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就国有企业而言,因其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退出市场,是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一市场竞争规律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退出论”主张者的意图,是让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全数退出,其中自然包括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让那些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这哪里是优胜劣汰,分明是人为地剥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生存发展权利。 与市场竞争规律一起发挥作用的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涵是: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依据价值规律,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会因不能弥补生产经营成本而出现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为市场所淘汰;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然而,“退出论”却不管国有企业个别劳动时间的多少或高低,也不管国有企业管理是否科学、生产技术是否先进、能否获取超额利润,让国有企业统统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显然与价值规律背道而驰。 三、几种“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论”理由辨析 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者为了达到迫使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目的,挖空心思编排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下面对其几种所谓理由分别进行分析。 (一)关于所谓“国有企业低效率论” 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或者无效率,是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主张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偏执一端,片面地认为国有企业就是低效率的代名词。 1.企业效率高低与企业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来看,国有资本所有权归国家或全民所有,这一点应该说是明确的,不存在所有权虚置的问题。不同的信息结构、市场环境及产品性质决定了相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不同的效率,私有产权并不等同于效率。实际上,真正同企业效率关联度大的是经营权而非所有权。现代产权理论表明,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经营者并非一定是所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现实表明,在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型企业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大都是分离的。国有企业中有效率高的,也有效率低的,私有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因而所有权与企业效率没有必然的联系。“私有产权效率论”、“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国有产权低效率论”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产权理论的一个翻版,是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一系列严格理论假设前提下所得出的逻辑结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修正和放松这些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已经证明了该结论的不成立。 2.应该动态地看待国有企业效率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经历了一个效率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摆脱出来,企业运行的体制机制僵化,背负着办社会的沉重负担,企业还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发展市场经济还不适应,的确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些国有企业也由于不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被市场淘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国有企业也逐步由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转变,通过政企分开、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剥离了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逐步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应该看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大都是适应市场经济变革的效率比较高的企业,国有企业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搏风击浪,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其中不乏具有自己品牌和自主创新能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优秀企业。因此,不能刻舟求剑,拿看待老国有企业的老眼光来看待已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型国有企业。 3.应该全面地看待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第一,总体概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从总体上看究竟是国有经济效率高还是民营经济效率高,实际上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说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没有民营经济效率高,只不过是因“私有产权优越论”作祟而做出的臆测而已。第二,至今尚未见到一个从总体上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的效率低于民营经济,实际上这样的实证研究也是谁都难以做到的。如前所言,企业效率与所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观点对于从总体上认识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也是适用的。第三,国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在工资待遇方面、依法纳税方面,还是在为职工缴纳社保方面和资源环境保护方面,国有经济要比民营经济规范得多、付出也多。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国有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它们本身就是保本经营或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性绩效。“退出论”所讲的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经营性绩效的含义,而这部分企业的存在会从总体上拉低国有经济的总体绩效。从这个角度讲,即便说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效率低于民营经济,那也是国有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得到的较少而付出的更多的结果,这恰恰说明了国有经济对增进人民福祉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因而不能以此作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理由。 (二)关于所谓“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 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关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与民争利”中的“民”的确切含义,即必须弄清楚这里的“民”到底指的是什么。学界和实务界对“民”的内涵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有的学者对“与民争利”的辩驳显然是把“与民争利”中的“民”理解为“人民”或“人民群众”,如果单从字眼上或从广义上来看的话,这样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与民争利”放在“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之争抑或国有企业该不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之争的语境下来理解的话,“与民争利”中的“民”显然不是指的广义上的“人民”或“人民群众”,而是特指“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 究竟应如何看待“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辩证地仔细分析。 1.国有企业已不是民营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关资料显示,在“十一五”时期,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资在21个行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均由外资控制;外资在制造业的市场占有率在30%以上。近几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资控制度已达到60%以上。外资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只会导致“国退洋进”,其结果很有可能不是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发展,而是跨国资本的垄断,危害极大。 2.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价值、追求利润,舍此则不成其为企业,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国有企业的资本需要在经营过程中保值增值,只有这样,它才能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循环下去,才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也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实现社会目标。从法律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具有和其他企业平等竞争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的权利。 3.即便存在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情况,那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将其作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理由。从争夺竞争性细分市场份额的角度讲,的确存在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情况,但市场份额与企业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市场份额并不是天然地应该归属于某一性质的企业,它既允许民营企业获取,也允许其他性质的企业获取;谁获取的市场份额越大,说明谁的竞争力越强。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恰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有企业是有竞争力的或者说是有效率的,不然的话,它们怎能争得市场份额。况且对市场份额的竞争是在企业之间相互进行的,如果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话,那么,必然也存在民营企业“与国争利”。应该说这都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正常现象,怎能作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理由呢? (三)关于所谓“竞争环境不公平论” 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竞争环境是否公平以及“竞争环境不公平论”作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理由能否站得住脚呢? 1.如果说竞争环境不公平的话,那么,这种不公平不但体现在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国有企业的不公平上。按照“退出论”主张者所言,所谓竞争环境不公平,是指对民营经济不公平。这种观点只看到或只片面地讲问题的一面,而闭口不讲问题的另一面,即不讲竞争环境对国有经济也有不公平的一面。竞争环境对国有经济的不公平,一是体现在政策环境对国有经济不公平上。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些地方的政策环境对公有制经济不公平,有的乘国有企业“改制”之机肆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有的地方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支持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排挤,使非公有制经济相对于公有制经济具有明显的政策优势,从而获得高速度的膨胀。二是体现在如前所述的国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比民营企业重得多。问题的实质在于:“全面退出论”实际上主张的是,把赚钱的买卖都转让给私营经济,而让国有经济专门去干不赚钱的、亏本的买卖,这难道符合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逻辑吗? 2.市场竞争环境正在逐步由不公平走向公平。竞争环境由不公平趋向公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融资环境而言,现在银行系统已走向企业化经营,政府部门顶多在贷款上起沟通协调作用,贷给谁不贷给谁,决定权在银行。银行的贷款指向主要取决于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还贷能力,与企业属性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就法治环境而言,我国正在由传统的人治走向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纠纷裁处问题上,我们不否认现实中法院裁决存在对民营企业不公平的现象,但这只不过是局部性的个案现象而已,并非全局性的不公。随着法制建设的向前推进,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依法办案已经或正在成为司法部门的常态,政府干预司法的现象会越来越少,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法治建设,按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快进键”,依法治国新时代正在到来,企业竞争环境将会越来越好。 3.以竞争环境不公平为理由让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不合情理。如前所述,竞争环境的不公平是多维度的,并非单单存在对民营经济的不公平,如果说因为存在对民营经济的不公平就让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话,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因为存在对国有经济的不公平而让民营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竞争环境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绝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像不能因噎废食一样,竞争环境不公平,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推进社会系统治理现代化来使之趋于公平,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些年也是这么做的,而不能因为竞争环境不公平就让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民营经济论文; 公有制论文; 国企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所有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竞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