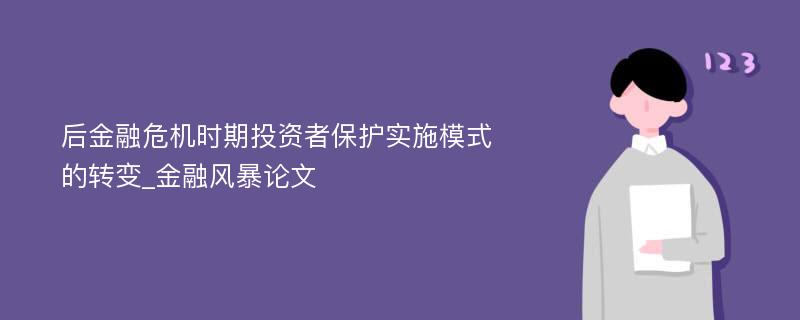
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者保护实施方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投资者论文,方式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投资者保护与资源配置:文献回顾
关于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或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或通过实证的方法表明:较高水平的投资者保护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对投资者权利受到侵害,从而干扰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当经理通过在职消费等形式侵占投资者的利益时,报告利润就会低于潜在利润,资源流入就会少于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量,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Wolfenzon建立了一个投资者保护(股东保护)法律环境下公司治理的市场均衡模型,证明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股东权利保护更好的国家,公司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价值更高,股息支付水平也更高,所有权集中度更低,股票市场更发达,资本配置更优。Kose John,Lubomir Litov and Bernard Yeung通过对39个国家1992~200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以下假设: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国家,公司内部人将其大部分财富投入公司,他们比外部投资者希望的更趋于保守性投资,因而放弃正的净现值投资;内部人还会忽略那些有风险、但会带来价值提升的项目以保护他们预期的私人利益,更好的投资者保护降低了预期的私人收益水平,使内部人风险厌恶程度降低。另一方面,当投资者保护水平低时,公司的非股权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工会、政府等,会限制公司有利于价值提升的风险承担行为,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Kose John,Lubomir Litov and Bernard Yeung又实证了风险承担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而更好的投资者保护导致更快的增长。此外,Charles P.Himmelberg,R.Glenn Hubbard and Inessa Love研究也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国家,其内部人持有的股权比重较高,从而使内部人面临特质风险,导致内部人对风险性收益的估价低于外部投资者,形成投资不足,资本不能达到最优配置。
综合起来看,投资者保护水平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首先,从公司层面上,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公司内部人以股东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成本,使其行为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相一致,抑制其对落后行业过度投资,从而加快资源由落后行业向增长行业的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其次,从证券市场整体层面上,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会增加内部人转移利润的成本,增强公司信息的可信度,使公司的报告理论等于其真实利润,从而一方面充分发挥利润引导资源流动的信号作用,另一方面激励风险套利者搜集公司特定信息,从而使股价中公司特定信息的含量比重提高,股市的同步性降低,充分实现资本市场传递信息的功能,引导资源导向最优配置。这与思拉恩·埃格特森的思想相吻合:一种经济的结构性生产边界是否趋近于技术性生产边界,依赖的因素之一是,目前和将来所有权能被清晰界定的程度及被安全保护的程度,以及今后是否能够以较低成本并且有秩序地解决有关所有权和履约方面的争端。
二、投资者保护水平变化的性质:一个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
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股票、债券等证券类资产可以被视为投资者产权的承载物,投资者认购、持有股票、债券等证券类资产的行为,实质上是选择利用不同方式(股权或债权)将自己手中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源投入某个领域,目的是为了通过承担相应的风险而获得投资收益。由于不同证券所对应的资本用途不同,投资者持有证券资产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也各不相同,即投资者享有按照自己的风险——收益偏好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利。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如何界定投资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边界。在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中,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之间,而且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由于拥有信息优势,控股股东有动力、有能力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从而在边界上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中小投资者由于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集体行动的问题,其自我保护能力最弱。因而投资者保护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指的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规则,界定中小投资者与内部人(包括控股股东在内)之间的权利边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免遭公司控股股东的侵害,从而维持其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在投资者保护完善的情况下,即当投资者权利得到清晰的界定与实施、消除了不确定性时,投资者可以得到运用产权的全部收益,从而激励投资者追求产权的收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也就是投资者权利的界定与实施不完全,投资者权利中那一部分未被清晰界定或有效实施,从而处于无主状态(即公共领域)的利益,就会引发各方对其的争夺,刺激分配性努力,抑制生产性努力。
因此,虽然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变化在性质上并不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它涉及到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利益边际的调整,因而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就是抑制控股股东掠夺中小投资者的能力,从而减少其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Albuquerue and Wang估算了美国和韩国的外部投资者为了获得完善的投资者保护,而各自愿意放弃的资本存量:美国与韩国的外部投资者为了获取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分别愿意放弃其资产存量的0.38%和11.17%,而这分别意味着43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价值与47亿美元的韩国市场价值。同时,美国和韩国的控股股东分别愿意放弃其资本存量的2.1%和8.4%来保持现状。因此,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意味着从控股股东向外部股东的财富再分配。Albuquerue and Wang认为,由于控股股东更不受集体行动问题的约束,控股股东与企业家位居政策制定过程中最有权力的利益集团,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必要性与依据
加强投资者保护可以通过充分界定与实施的投资者权利边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效率的提升。但是投资者的权利边界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完全清晰地进行界定,因为事前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不确定性并通过制度安排进行消除,在既定的权利边界安排基础上所展开的交易过程,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权利边界的进一步界定(无论是通过正式规则还是非正式规则)与否,取决于界定权利的成本——收益比较。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通过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收益上升。
(一)金融危机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
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内部人与中小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掌握信息,中小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其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较高,而且由于在集体行动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使得内部人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成为可能。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能力,取决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的成本越低,因而具有更大的动力实施侵害。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增加,信息传递的质量、效率下降,从而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动力将随之增加,资源配置效率将随之降低,因而,有必要增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Johnson,Boone,Breach and Friedman更是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如果对投资者保护程度低,恶化的经济前景会导致内部人加剧其掠夺行为,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挫,减缓经济走出危机的步伐。
(二)金融危机加剧了不确定性,改变了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未来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从而一方面降低了长期收益的贴现,使内部人攫取、掠夺等机会主义的短视行为增加;另一方面,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加大,倾向于收缩投资,从而削弱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证券市场规模萎缩,那些对外部融资需求迫切的企业难以获得融资机会,不利于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抑制了经济活动的开展,减少了社会产出。而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有利于通过更加清晰、明确地界定投资者权利边界,减少、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激励投资者追求产权的收益,增加投资者的生产性努力。
(三)金融危机后加强投资者保护的历史事实
从历史事实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也是改善投资者保护、推动投资者保护模式转换的契机。例如,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促成了美国Glass-Steagall法的出台,建立起了金融防火墙。1933年《证券法》规定了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1934年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强化了对证券发行与交易的监管,从而使金融危机成为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四、目前我国投资者保护实施方式上存在的观念误区
(一)投资者保护的不同实施方式
人们对资产所实际拥有的权利如何,是同时取决于多个实施方式的。正如私人保护可以作为官方警察制度的补充或替代:公司有私立安全警卫、家庭有邻里看护组织、社区有私人保安,投资者权利保护可以是私人实施与国家介入的公共监管实施的结合。私人实施即那些投资者自主地运用那些旨在降低私人缔约与诉讼成本的规则而实现的投资者保护;公共实施即是由政府的积极介入而实现的投资者保护。
在一个时点上,投资者保护水平是不同实施方式的综合,对权利的不同维度进行保护的不同实施方式之间构成一种均衡。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每一种实施方式所确定的投资者权利水平,取决于该实施方式的成本——收益比较。每一种实施方式的成本承担者与收益获取者都不同,从而任何一种实施方式都不能完全取代其他实施方式。每一种实施方式的成本都是针对实施者而言的,如果改换了实施者,则成本可能会十分高昂而不可行。如果对于任何一方权利的某些维度的保护成本都超过其收益,则这些权利的维度就被置于公共领域,因而投资者权利保护水平的确定是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二)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投资者保护实施方式上存在的观念误区
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使得人们认识到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维持投资者信心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何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实施方式上,却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过于倚重、强化政府参与介入的投资者保护的公共实施,忽略了投资者保护的私人实施。由于信息不对称阻碍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权利行使,从而阻碍资源优化配置。而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是“信息供给成本最低的人应该搜集与供给信息,并为信息的遗漏与误导负责”。Id Porta,Rafael,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 Andrei Shleifer考察了投资者保护之所以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是因为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规则通过其私人实施,而不是因为公共监管实施,从而说明有效的制度选择采取了公共规则的私人实施方式。此外,巴泽尔认为,在权利界定中,如果一方承担更大部分的变化性时,该方就成为更大的剩余索取者;那么反之,当一方成为更大的剩余索取者时,他应该承担更大部分的变化性。因而依赖政府通过一系列“救市”行为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政府控制投资者资源配置方向的认可,而对投资者支配资源权利的忽视。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投资者的收益做出承诺。证券资产的所有者享有承担其资产价值变化的权利。所有者“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所有权的排他性把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的资源的使用方法。”①因此,政府所谓的“救市”行为不能被视作是保护投资者的举动,这样一来只会增加投资者的道德风险,从而妨碍投资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动力。
公共监管实施的另一重要不足在于:容易使监管力度、时机受制于来自利益集团的游说,从而导致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波动。投资者保护的私人实施方式包括自我实施与非政府的第三方实施。自我实施即在公司层面各方主体出于利益的一致性而自觉实施的投资者保护。Armando Gomes认为,即使当外在的公司治理机制匮乏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会内在地承诺不剥夺中小投资者,因此形成的声誉效应会使得公司的股票价格更高,公司更容易上市。从而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由于保护匮乏所导致的问题。而实证研究也表明,当法律提供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有限时,公司为了获取外部投资,会通过各种机制来确保投资者的收益,从而实现投资者保护的自我实施。Craig Doidge,G.Andrew Karolyi and Rene M.Stulz将投资者保护区分为国家提供的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同时表明:在国家施加的投资者保护,基础上,公司根据成本——收益比较来决定选择什么程度的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这种实施方式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股息政策等制度安排实现。
此外,非政府的第三方,如证券交易所、证券行业协会等通过其交易与监管规则、协会章程等制度安排实现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例如,证券交易所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等手段来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证券业协会通过协会章程、会员管理制度等进行从业机构与人员的自律,以维护投资者利益。这种实施形式的特点是:主要通过发挥声誉功能依靠组织成员的共同参与,以自律为特征。Brian R.Cheffins分析了英国法律在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包括商人银行、证券经纪人、投资信托,与证券交易所出于声誉考虑通过自律实现的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保护的私人实施优势在于:由于信息的传递时滞短、链条少而成本更低。因此,政府在通过公共监管积极介入投资者保护的同时,推动投资者保护的自我实施与其他第三方实施,有助于降低投资者保护的成本,改善保护效果。
五、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方式
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投资者保护的不同实施方式之间的配合协调,有助于实现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
(一)强化司法机构的事后处置效力与效率
调整投资者保护的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之间的配置,需要调整证券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在事后处置方面的平衡。卡塔琳娜·皮斯托与许成钢提出了“不完备法律理论”,认为法律是内在不完备的。②他们提出:应对法律不完备的办法,是将部分立法权与执法权分配给监管者。如果说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行政监管对保障证券市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话,随时间推移,行政监管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其监管成本也逐渐增加,这时候应逐步调整行政力量与司法力量在事后处置方面发挥作用的比重。与行政处置相比,司法部门的事后处置有利于发挥投资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激励,减少投资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被动性,降低处置成本。因此,应逐步建立中小投资者针对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其他侵权者的诉讼机制,强化对中小投资者的司法救济。同时,应强化侵权者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发挥政府之外的民间第三方组织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行政力量与司法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在政府实施的投资者保护手段内部进行权衡,以提升投资者保护的有效性,那么政府实施与其他民间第三方实施之间也可以彼此配合。例如,对证券交易所的设立采用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或设立更多的证券交易所,可以加强证券交易所之间对上市资源方面的竞争,将有助于证券交易所自律功能的发挥,使其承担起监管一线的工作,强化信息的披露,从而减少信息传递的时滞,弱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这样一来,压缩了内部人侵害中小投资者权利的空间,也降低了监管成本。
另外,应注重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一个活跃的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发挥其自主性、首创性和灵活性来弥补正式法律规则的不足,通过市场交易主体彼此的监督约束机制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因此,应适当收缩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力辐射空间,改善目前我国证券业协会的边缘化状态,激发其活力,使其被虚置的功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准许成立投资者保护协会,鼓励投资者自发的制度创新
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应该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投资者保护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建立,有利于降低投资者集体行动的成本,增强其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而有助于自主性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制度创新,例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小股东信托表决制度等,政府主管部门应予以肯定并及时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从而不断维护市场参与主体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降低市场微观主体的自我保护成本,保持制度建设的自我更新能力。
(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与健全交易机制
保护投资者权利,最终表现为尊重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收益偏好自由决定资源配置方向、选择投资对象的权利。如果金融工具过于单一,投资者选择集合过小,那么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在确定是否进入证券市场时,就只能以从事证券投资活动是否会获得超过机会成本,即银行储蓄的收益为标准,从而使具有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进入同一个风险场所。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应该是细分的,可以使投资者按照自己的风险——收益偏好进行选择。因此,应该发行短期国债,向市场供给无风险资产,同时鼓励金融工具创新,使金融中介在符合自身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供给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从而填补各种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组合的空白。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偏好的过程,也就是投资者权利被不断趋于清晰界定的过程。
此外,健全的证券市场交易机制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起到提升投资者保护水平的目的。例如,建立证券市场的做空机制,可以使投资者监督上市公司、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能够通过市场渠道得到补偿,从而提高投资者监督公司行为、保护自身权利的动力。
注释:
①[南]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2000,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30页。
②如果法律能准确无误地规定出所有相关的适用情况,而且如果证据充分即能切实地加以执行,那么法律是完备的(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