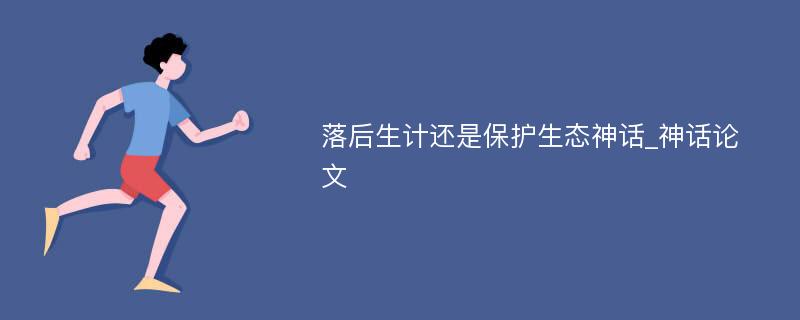
落后生计方式还是保护生态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计论文,落后论文,生态论文,神话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6)02-0066-05 迄今为止,游牧是草原民族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生计方式。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凡有草原的地方,只要有人经营牧业生产,游牧生活就会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跨越时空。因为无论是时间维度的人类发展历史,还是空间维度的不同地理区域,游牧都可能成为草原民族所操持的一种生计方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生计方式之下的游牧体制支撑了许多草原民族从远古走到现在。在东亚大陆,游牧的蒙古族甚至有在历史上创造了震惊世界、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轨迹的辉煌业绩。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语境中,蒙古族的游牧体制由于本身无法契合所谓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标准,被视为落后生计方式而饱受诟病,在内蒙古草原上推行定居政策遂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加之在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现代化的追求不止于理论上的构建,更要求行动上的践行,于是草原上的蒙古族在这种背景之下迅速停止了游牧的脚步,很快实现了符合现代文明标准所要求的定居。从游牧走向定居,这种发展政策的推行,使得游牧的蒙古族传统生计方式遽然改变,也打破了草原蒙古族原先在游牧体制下所特有的相对稳定的一系列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平衡。事实证明,这种平衡被打破之后,至今没有找到在新的体制下如何保持或者恢复平衡的支点。因为伴随着定居,尤其是实行草畜双承包政策以后,一系列推动草原社会发展的目标追求,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却日益加剧了内蒙古草原自然和社会生态的双重恶化。 在这种经济和社会环境之下,围绕游牧体制就有了许多话题,其中著名的要数游牧是落后生计方式还是保护生态智慧的两种观点的交锋。笔者在本文中把这种交锋称为两个“神话”之间的论战,即在持有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遵循游猎——游牧——农业——工业这种线性发展模式者的眼里,游牧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计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终将被现代工业方式取代,此为社会发展的“现代神话”;而在为游牧体制辩护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另一个观点,即游牧是一种保护草原生态的智慧,类似凯·米尔顿提出的“原始生态智慧神话”[1],认为游牧是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和睦相处的生计方式,游牧的蒙古族在草原上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生态智慧。两个神话,两个极端,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作出的任何学术讨论都可能被视为萨林斯所说的“答案就在两者间”的皆大欢喜的折中结论[2]。当然,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不愿被当作是对两个神话的“两面讨好”或者是“和稀泥”,而是旨在打破神话,反省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 一、“现代神话”与蒙古族游牧体制是落后生计方式的由来 在国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习惯于用汉族的农业耕作和蒙古族的游牧生计进行比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得出的结论多是汉族的农业及其一系列文化优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近年来,由于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的多样,尤其是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已经很大程度改变了过去那种农业比游牧先进的刻板印象。蒙古族的游牧体制和汉族的农耕体制原本是两个民族操持的生计方式与各自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农业是农业民族适应土地环境的选择,游牧是草原民族适应草原环境的选择,且不可互相对置。假如在耕地上进行游牧,在草原上进行耕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承受来自环境的报复。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习惯站在“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立场上去认识和看待异民族及其文化,总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异民族。这一点,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中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中,由于华夏民族较早发明了并掌握着文字书写系统,并垄断了书写历史的权利,所以见诸史书的其他民族,包括游牧民族就会被放置在其反面进行观察、认识,许多史书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即可反映这点。历史上的“华夷之辨”本质上就是华夏民族及其文化优于四夷部众的主张。《礼记·王制》中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类描写明显是站在农业民族角度对所谓的夷、蛮、戎、狄等民族的打量,反映的是经营农业的华夏民族“先进”、操持渔猎、游牧生计的其他民族“落后”的“我族中心主义”立场,因为夷、蛮、戎、狄不像华夏民族食熟食、吃粮食,而是喜欢吃生食、肉食,且没有统一的文字书写系统,从而也失去为自己发声辩护的权利,所以这种刻板印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及至近代,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但是我们认识西方人的态度和立场仍以自我为中心——华夷有别,就连多同西方人打交道的林则徐都认为洋人走路小腿不会打弯,生活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大黄……我们之所以战败是技不如人,并不是文化输给了对方,所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世的“体用之争”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只是在“体用之争”还没有结果的时候,当时引领世界潮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便随着洞开的国门涌进了中国。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尚不明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什么,但在战败的失望与悲观情绪之下,主张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形成压倒优势。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西方侵略者认识中国人的观点和侵略中国的理由,但是当一部分人借鉴于此眼光向内的时候,蕴含“华夷之辨”糟粕的中华文化的血脉中便被注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因。一些人开始把西方人看我们的有色眼镜拿来观照我国的少数民族,其结果只能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处于历史发展链条的末端。原本“华夷之辨”在许多人眼里就是少数民族乃“化外之人”,需要“怀柔教化”,此际这种认识又从西方的“先进”理论中找到了根据,于是这副“眼镜”恰如给许多国人特意验光配制的一般,戴上之后竟无丝毫不适之感[3]。民族及其文化有先进、落后之说,从此就有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支持,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科学”外衣。 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理论情境中谈论蒙古族的游牧体制,其结论能且仅能有一个,即这种生计方式落后于社会发展潮流,必须加以改变,向发达的农业社会迈进。1930年,国民政府召开蒙古会议,通过了《蒙古农业计划案》和《蒙古垦殖计划案》[4]。蒙古会议决议案明确表示:“蒙古以游牧为主,不耕不做,居无常所,其生活不适于当今世界,按人类进化程序,蒙古地方应由游牧入农业时代。”[5]国民政府针对蒙古族的会议以及计划案的目标十分明确,便是要蒙古族弃牧从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性质发生了改变,但是关于建设牧区的政策主张却因袭了国民政府,继续实施定居化政策,并作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实现定居化的决策[6]。当定居成为衡量草原蒙古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发展方针都是围绕定居制定和实施的,所依据的理论就是消灭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给出的发展目标就是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迈进。不必怀疑,推动草原牧区实现现代化的良好初衷,政策的推行也不遗余力,国家的财政投入尤其巨大,希望达到的宏伟目标更加美好……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牧区现代化目标远未实现,草原生态环境却破坏殆尽,几乎无力支撑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尴尬局面。问题出在哪里,症结又何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给出了很多答案。但是如果不对打着“科学主义”旗号,信奉游猎——游牧——农业——工业线性发展模式的“现代神话”的彻底批判和反思,则无法扭转草原生态环境凋敝、社会问题频发的局面,而这才是问题的总根源。说游牧体制落后、在草原上推行定居政策、改变牧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等举措,无不是建基于这一“现代神话”之上。 由于“现代神话”的思想基础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并且是现代必然战胜传统的过程,那么蒙古族的游牧体制必须被放置在现代化的对立面,成为革故鼎新的对象。换句话说,只有把游牧体制“塑造”为落后的生计方式,才能彰显现代化牧业体制给出的愿景,否则“现代神话”将无由立足。 为了确立“现代神话”的语言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要确立“现代神话”的合法性,“现代神话”把科学的合法性转移到自身上来,从而拥有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现代神话”相信科学万能、迷信技术,认为人类社会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甚至否认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把尊重、顺应自然生态环境的理论一概视为“环境决定论”,并加以批判。“现代神话”尤其相信自己依靠的是科学,能认识、掌握甚至可以打破自然规律的制约,按照自己理想的发展蓝图规划、设计社会秩序,凡是被它打上“落后”标记的传统,完全可以被摒弃。有意味的是,当这种被设计出来的、无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制约因素的、无意尊重当地人文化传统的发展目标没办法实现或者失败的时候,“现代神话”论者又常常把这种结果归罪于“传统”的惰性和抗拒。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蒙古族的游牧体制根本无力抵抗“现代神话”的语言霸权。于是,“现代神话”得以一路高歌猛进。 二、对于“现代神话”和保护生态神话的质疑 就在“现代神话”的引导下,草原社会向设定的现代化理想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一个出乎所有“现代神话”论者预料的情景出现了:短短几十年中,草原退化、沙漠化、荒漠化程度和速度是历史上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无法比拟的。尽管政府下大力气、用尽手段,包括退耕还草、围栏封育,甚至推广比农村还严格的禁牧舍饲等农民饲养牲畜的方式,仍然无法遏制草原生态恶化的势头。因此,人们不得不对草原社会的发展方式、发展政策产生疑问。就在这种现实问题的催逼之下,产生于西方的,反思以经济增长、工业化为基调的现代化模式的理论也在中国传播开来,特别是对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罔顾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评,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响应,形成对“现代神话”的质疑,关于草原生态环境牧区发展模式与政策的反思即为其例。 的确,“现代神话”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在实践中无法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一些民族所处的具体自然生态环境相契合,注定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奉和追捧。有趣的是,人们在质疑“现代神话”的过程中,又制造出另一个神话——民族传统生计方式拥有类似凯·米尔顿批评的“原始生态智慧”——回归游牧,草原上的蒙古族就能与草原生态环境和睦相处,并且可以解决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破坏生态环境的困境。 毋庸讳言,笔者也曾秉持这种观点,并呼吁回归游牧。现在本文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补充、修正。正如文章的开头所言,游牧是草原民族沿用最长的一种生计方式。历史上的许多草原民族就是在这一体制之下繁衍、发展的。说明游牧体制的确是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尊重、顺遂草原生态环境,适合、顺应马、牛、羊、驼等草食家畜的动物习性的生存手段。需要认清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游牧生计是草原蒙古族的谋生手段,是一种生存策略,并不是一种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刻意设计的生计方式。 首先,游牧是一种生存经济,是为了保证生存,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断积累财富,是关于“经济”这一术语的一般性认识,草原上的蒙古族经营游牧业却不能用这一指标去衡量。衡量游牧经济也应该摒弃“我族中心主义”的标准,因为游牧经济是一种生存经济,与汉族农业耕作追求的五谷丰登、连年有余截然不同。蒙古族选择游牧是为了在草原相对脆弱的生态体系中维持生存,积累财富非但不能成为生产目的,反而是威胁牧民生存的非理性行为。移动性是游牧的蒙古族应对环境变化的主要手段,季节更替轮回,雨、雪、风、霜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同草场载畜量的差别,草食性家畜的习性等等都决定着他们必须不断移动,以规避风险、趋利避害。这也决定他们必须保持轻装简行,多余的财物只能羁绊移动的速度和效率,给人、畜、草场带来危险和压力,其他则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几辆勒勒车就可以运走一户牧民的全部家当,包括居住的蒙古包。移动是游牧社会的生存法则,但是在草原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人羡慕汉族的定居生活。针对这种情况,拉铁摩尔指出,草原上也经常出现统治者为追求尊贵奢侈的生活而破坏游牧的生存法则的现象,追求一种像内地汉族贵族那样的定居生活,只是财富的积累妨害了游牧的移动性,因此这种追求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必须退回到对自己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去[7]。在积累财富和维持生存之间,尤其是二者出现矛盾时,任何民族都会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选择游牧、以利生存,这不仅仅是蒙古族的选择,古代蒙古高原上来来去去、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诸多民族,包括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无不以游牧为计,原因即在于此。 积累剩余财富是游牧体制的累赘,但是又不能把游牧的蒙古族视为食不果腹、风餐露宿、朝不保夕,每日为活命而奔波的群体,因为正常的游牧生产足以保障牧民群体的日常生活。但是,蒙古高原草原环境十分脆弱,反常的气候和人为变故有使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需求也不能满足的时候,于是就会出现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争端。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中原,表面上是为了掠夺中原地区的财物,其实质多是因为气候变故引起草原环境恶化,或者是中原王朝关闭“榷场”“互市”,断绝游牧和农耕民族双方正常的贸易往来,使具有非自足性特点的游牧生计不足以维持人们基本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解决了生存危机,他们便回到草原继续以游牧为业。“原初丰裕”和“非自足性”貌似矛盾,却是游牧社会的真实反映。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特别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有其内在的文化和经济的缘由。 其次,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是游牧体制的衍生效应。同样因为草原是相对脆弱的生态体系,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选择适应这一生态环境的生计方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恰好与草原生态环境构成一个相对完美的“消费—产出”模式,而草原牧区的一系列现代化目标追求,如定居、垦荒、矿业开采等等又对草原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正是因为这点,有人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游牧体制神话化了。值得提醒的是,在任何环境中,人的生存都是第一位的,所以保护草原自然生态环境只能是游牧体制的一种衍生效应。蒙古族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自然而然、顺应环境的行为,出发点绝不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而是为了群体的延续。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倒向游牧体制是一种原始生态智慧的神话一边。人类学界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叫“高尚的野蛮人”,说游牧民族拥有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天然美德,恰好是为“高尚的野蛮人”作注解。这种认识不是否定游牧体制与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良好互动,更不是否定蒙古族关于草原环境实践中蕴含的科学的地方性知识,仅为说明,不可把游牧体制上升为原始生态智慧的神话。因为“现代神话”和原始生态智慧的神话都无法拯救当今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游牧体制的问题上,无论是社会的主流观点,还是处于非主流的一些认识,都需要从文化上进行一番反省,否则不是倒向“现代神话”一边,就是倒向“保护生态神话”一边,但是无论倒向任何一方,都无益于正确认识游牧文化,也无益于解决当前草原蒙古族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和社会问题。 三、适合草原生态环境的发展路在何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游牧体制也须向现代游牧业体制迈进,它的核心价值也要从过去偏重保障游牧群体生存向恢复和保护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保障草原社会生活富裕转化。“现代神话”由于割裂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注定走入发展的死胡同,而简单地回归传统游牧体制,也可能冻结草原社会的发展,毕竟如今的草原牧民经营畜牧业已经不仅仅要求解决温饱、生存问题,而是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传统游牧体制满足不了牧民的这个需求,因此,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实现广大牧民的小康生活目标、实现牧业现代化,需要另辟蹊径。 在“现代神话”看来,蒙古族必须放弃传统的游牧体制方能实现现代化,现在可以断言,此路不通。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发展已经证明传统和现代一脉相承,蒙古族传统的游牧业与现代化生产方式并非“两张皮”。“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它的牧人仍在沿袭传统的游牧方式饲养牛羊,只不过这里的牧人已经动用直升机放牧了;同样以发达的畜牧业闻名的阿根廷,它的牧人也是操持游牧手段进行放牧的;北欧的萨米人在北极圈内放养驯鹿也以游牧为业,但驯鹿转场则动用了现代船舶,鹿拉雪橇已换为机动雪橇。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生活在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也叫爱斯基摩人,因其过着传统的渔猎生活,曾一度被视为没有前途的民族,被一些人类学家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但是这个群体却通过利用工业技术来实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目的[8]118。因纽特人“已经进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支配的那种越来越有利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中去了”,所以萨林斯说“爱斯基摩人还在那里,并且还是爱斯基摩人”[8]119。亦即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仍旧保留,实现了现代化的是他们的思想和生产技术。大量人类学研究的例子表明,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完全可以和任何民族操持的生计方式相契合,蒙古族的游牧业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其中的关键在于促进一个民族群体发展的进程中,要让这个民族群体保留一种既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为我所用地吸纳现代技术优势的信心和决心,而不是以实现现代化的名义给他们的传统文化挂上“落后”的标牌,在打击他们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驱赶着他们去实现我们给设定的现代化目标,使他们既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文化依靠和基础,也失去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接管道,在夹缝中承受来自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针对内蒙古草原社会的发展,乌兰夫曾提出“定居游牧”思想,即人要定居下来,牲畜要游动起来[9]。但是我们并没有好好领会乌兰夫这一关于草原畜牧业发展的正确理念,更没有行动去实践这一思想,它在发展现代化游牧体制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也就无从得以验证。前文中我们提到的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它们的牧人都是实行“定居游牧”的,从而达到既利用、保护草原环境,也达到了游牧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必须认清的是,当今内蒙古草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繁荣,要靠复合型产业的支持,单纯依靠现代化游牧体制不足以支撑这一点。但是无论发展哪种产业都要以尊重、依托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态环境为前提,假如排除了蒙古族在草原生产实践中的宝贵知识和经验,无视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及基础作用,可以说任何发展方案都将破产,并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族群体带来戕害。今天恢复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资源已经刻不容缓,草原社区的发展若没有草原生态环境资源的支持,一切发展目标、希望都将是幻影,草原牧民实现中国梦迫切需要良好的草原生态环境的支撑。 收稿日期:2016-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