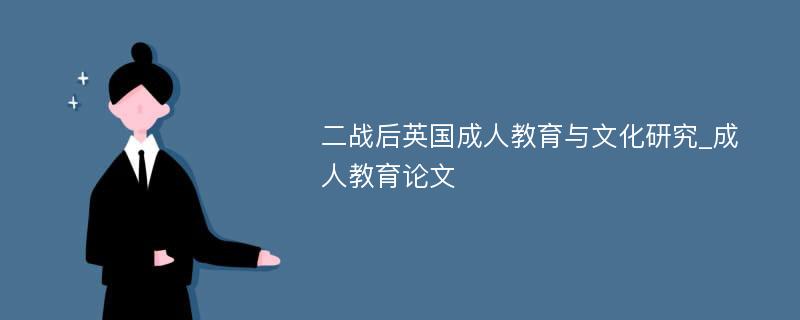
战后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成人教育论文,战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格外热门的话题,它广泛地渗透到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各个学术领域,成为最具活力的学术思潮。近年来,我国也掀起了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众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深入探讨与英国文化研究相关的各类问题。
然而,文化研究又是最含混、最难以确定的领域,迄今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文化研究的演进》一文中,柯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指出:“要想精确地定义‘文化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人们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并且说在界线的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确切范围。人们也不可能指出文化研究所特有的统一的理论或方法。众多源于文学批评、社会学、历史、媒介研究的观念、方法和关注焦点都聚合在文化研究这个便利的标签之下。”[1](p.14)斯帕克斯的论述表明,文化研究的定义、范围、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完全确定的和唯一的。事实上,翻开文化研究的著作,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背景切入文化研究的领地,有时文化研究甚至给人以大杂烩的印象。①
文化研究的这种模糊性也影响到了文化研究的起源问题。虽然斯图亚特·霍尔说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开始”,但在考察文化研究的历史的时候,起源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于“文化研究”这个术语诞生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纳在《英国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这种说法考虑的是文化研究真正进入大学,它成为一种正式建制的时间。霍尔在《早期新左派》中把文化研究的历史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后来被认为是文化研究奠基作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文化与社会》(1958)。
但是,在论述文化研究的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包括威廉斯、霍尔都谈到了战后英国成人教育②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编辑部的采访时,威廉斯说:“我首先在成人教育课堂中考察文化的观念。”[2](p.97)后来他又谈道:“我们开始看见许多文章根据50年代末期的这本书或那本书而来追溯文化研究的诞生。一个字也别信它。有关艺术与文学及其与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关系的教学观点的变化始于成人教育,根本不是发生于其他地方。”[3](p.162)威廉斯的论述表明了文化研究与成人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楚地说明了成人教育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一、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奠基者
战后英国成人教育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为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成人教育传统的国家,英国成人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成立于牛津大学的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0世纪红色30年代,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对象的成人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英国民主思想高涨,教育民主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战后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也为成人教育提供了动力。因此,在政府的引导下,英国的大学纷纷开设自己的成人教育院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批后来在英国学术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年轻人进入成人教育的领域,开始了其学术生涯。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者雷蒙·威廉斯、查理·霍伽特、E.P.汤普森和斯图亚特·霍尔都是在战后进入大学成人教育领域,并长期任教于成人教育班级。威廉斯于1945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人教育机构,教授文学和国际关系,并在那里工作长达15年时间,直到1961年他进入剑桥大学;霍伽特于1946年进入赫尔大学的成人教育机构,担任成人教育的指导教师,教授文学课程,时间长达13年;汤普森则于1948年担任利兹大学的校外成人教育讲师,在那里工作到1956年;离开牛津大学之后,斯图亚特·霍尔也曾长时间在伦敦附近从事成人教育工作。
应该说,成人教育为这批学者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由于成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阵地,是各种政治观点交锋的前沿之一,这些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立场。
在战后最初的一段时期,学生的主要成分是工人,这些年轻的学者需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实际状况组织教学,表达自己的观点,企图以此引导学生,并以此作为参与当时政治的一种手段。同时,这些学者充分利用成人教育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充分利用成人教育提供的舞台,在教学过程中宣讲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政治观点,把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带进课堂,同时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学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适时地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进而奠定自己在英国学术界,尤其是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能说没有成人教育就没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但可以肯定地说,成人教育滋养了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位有着类似经历,长期任教于成人教育学院的理论家霍伽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文化问题,强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文化一词的涵义,致力于消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的观点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他们的理论思考、研究方法、亲身经历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奠基文本
今天,人们在谈论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时,首先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理查德·霍伽特的《识字的用途》、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些著作是英国早期文化研究范式——文化主义的开创性著作,是文化研究中最活跃和最具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霍伽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以自传的形式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形象地勾勒出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史,同时讨论了教育和媒介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霍伽特关注的焦点是英国工人阶级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围,使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不为人们关注的工人阶级文化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为后来的文化研究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解决当时的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时,霍伽特求助于教育,并且努力通过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推动教育改革。同时他把自己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才能成功地运用到流行音乐、报纸杂志、通俗小说等各种大众文化现象上,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本加以分析,对后来的文化研究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因此,《文化的用途》无愧于文化研究的一块基石。
虽然《文化与社会》(1958)一书在内容和方法上还带有利维斯的影响,但威廉斯不是单纯地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而是把文本置于观念体系之中,研究文本与观念的关系,追溯观念尤其是文化观念的发展历史,考察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文化的这个词的涵义从狭隘的文学文化中解放出来,使之变为“整个社会方式”,把其他知识形式、制度、风俗和习惯等原来被排斥的东西涵盖进来,这极大地扩展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他批判了英国文化传统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开始重视大众文化现象,初步提出了共同文化建设的构想。
在《漫长的革命》(1961)中,威廉斯彻底地与英国文化理论中的文学—道德传统决裂,进一步把文化的涵义扩展到人类学意义上。“把争论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它把后者定义为‘整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意义和定义被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改变,文学和艺术仅仅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社会交往形式。”[4](p.19)威廉斯重新定义的文化把英国的文化传统从文学的或者说审美的层面扩展到人类学的层面,为后来的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不仅如此,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还对一些新的文化对象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为后来的文化研究作了示范性的研究。他根据翔实的历史资料研究了教育和英国社会、阅读大众的增长、通俗报刊的发展、“标准英语”的发展、英国作家的历史、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问题。这种研究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角度来研究文化,把文化从高雅的殿堂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出文化的功用及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功能。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汤普森考察了1790-1830年间即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劳动和经济历史,质疑工业革命的公正性。他指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中,汤普森重新发掘被忽视了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从此工人阶级成为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范畴。
对于这几位奠基者的奠基作品人们做了很多研究,本文想要强调的是,这些著作的产生都与成人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从出版年份来判断,这些著作都创作于作者从事成人教育的时期。这些著作中最晚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时间为1963年。显然,这些著作写作期间,作者都是大学成人教育工作者,这些著作凝聚了他们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思考,是他们成人教育期间的研究结晶。其次,成人教育直接影响了这些著作的内容。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的采访时,威廉斯坦承,“我在成人教育课堂中第一次开始思考文化的概念”。[2](p.97)后来对整个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与社会》中的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当时威廉斯在成人教育课堂讲授文学课程时的内容,正是在讲授英语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威廉斯“开始讨论文化与社会的主题”[2](p.81)。
对霍伽特来说,由于其本人出身工人阶级,他的学生也大多是工人阶级或其子弟,他比较多地接触到了工人阶级文化,加深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理解。因此,霍伽特更加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力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工人阶级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文化。他的《识字的用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工人阶级学生写的论述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书中既包含他本人的早期经验,同时也包含着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文化,对工人阶级学生提出的疑问的思考和解答。
三、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
今天,跨学科性已经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种跨学科性首先表现在它坚持认为人们必须在它生产和消费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中来研究文化,因此文化研究从不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总是把触角伸到其他学科的领域中去,力图突破传统学术体制的限制和封闭,动态地考察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联系,阐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文化研究总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英国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文化和艺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开放性。
其次文化研究也不追求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它不断地从诸如文学的文本分析、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语义学等学科中吸取营养,提取其中的有用因素。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多种研究方法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书中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探讨意义的生产、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而后又运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编码和解码的机制和意义。
在英国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度里,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范式源于何处?在考察英国成人教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是英国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这种特征影响到了后来的文化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战后成人教育的跨学科研究特征是后来的文化研究的重要先驱。
那么,战后英国的成人教育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呢?首先是一种教学的需要。战后,由于恢复和重建的任务繁重,大量的教师进入成人教育领域,这些教师有的具有文学背景,有的具有社会学背景,有的具有语言学背景……这些教师往往处于同一个部门,教师之间学科背景的不同为教师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由于师资紧张,一个教师常常需要身兼数门不同学科的课程。文化研究的三位奠基者威廉斯、霍伽特和汤普森在大学里都是主修英国文学,有着良好的文学训练。威廉斯和汤普森毕业于剑桥大学,虽然均不属于利维斯圈子,但利维斯在他们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霍伽特则在利兹大学学习英语。他们虽然都是作为英语教师被招入成人教育的,但在成人教育系统中,他们不仅承担文学类课程,同时还承担其他课程。威廉斯除了讲授文学之外,还给学生讲授国际关系、工会研究、商业演讲之类的课程;而汤普森则讲授社会学和历史方面的课程(最后汤普森自己没有成为文学研究专家,而是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种教学的需要客观上迫使教师广泛涉猎不同的学科,开阔了教师的视野,使得他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学训练和文学教学方法运用于不同的学科。
英国成人教育的跨学科特征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学生的需要。英国战后成人教育的学生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工人,有商业领域的人士,也有大量中产阶级的妇女。这些人中有许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经常阅读的只是通俗的报纸和小说,广播、流行音乐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兴趣不是集中在纯粹的精英文学中,他们不想通过成人教育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专家,他们需要的是通过成人教育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工作。因此,这些学生非常关注现实,希望能把学习与自己的未来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实际上,这是英国战后成人教育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也是政府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的宗旨。面对这样的学生,成人教育工作者不可能按照传统大学的教学方法,他们必须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的实际调整自己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打破传统单一模块的教学内容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其结果是,以威廉斯、霍伽特等为代表的英国成人教育的文学教师突破传统的束缚,运用自己擅长的文学方法分析学生关注和熟悉的现象,引导学生去研究这些现象,于是流行音乐、大众媒介内容、通俗小说等为传统文学研究所忽视或鄙视的文化现象登堂入室,进入课堂。这些东西日后都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
英国成人教育跨学科特征的第三个原因是英国成人教育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我们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大学的文学研究始终坚持比较严格的规范,语言是其重要特征。所谓的文学批评,剑桥学派可以说是典型代表。时至今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种传统依旧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若按照传统大学的学术研究规范,我们很难想象《文化与社会》和《识字的用途》这样的著作诞生。而战后的英国成人教育虽然与传统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这些教学点远离大学校园,所以尽管大学本部作为管理机构会提出很多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规范,这些教师从地域上来说远离大学本部,从学术研究来说处于边缘,因此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依旧有着相对的自由,在研究中更少受到限制。在接受《新左派评论》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威廉斯是这样描述这种关系的:“但是来自大学的压力是始终存在的:你必须提高学术标准,你必须有专著,不应该有跨学科界线的情况存在……住在远离牛津100-150英里的地方,你拥有极大的实践自主权。”[2](p.80)对此状况,利兹大学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教授、英国成人教育的权威S.G.雷布尔德曾在1946年指出:“……校外教师构成了一个脱离大学的群体。他们不属于任何教学组织,不属于任何系别……在大学里没有任何职位。他们的职位名称不属于大学的学术职位,他们没有机会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工资。”[5](p.362)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年轻的学者处于英国学术生活中心的传统之边缘,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传统学术研究的束缚,把历史、文学、艺术、流行音乐等等不同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开创了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研究范式,为后来的文化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成人教育与文化研究的政治干预倾向
今天,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英国文化研究的人都承认,英国文化研究不是局限在学术领域的研究,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干预倾向,总是介入政治的领域。它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伦代尔就曾指出:“严格地说,文化研究既没有永恒不变的论题,也没有自己专属的理论立场。然而,文化研究却总是具有介入批判政治的意识,尤其是认识和改变社会的支配性结构的意向。无论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者,还是文化研究的旁观者,都能觉察到它的介入性。因此,大多数文化研究者认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它涉及并在政治上介入由特殊社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一系列特殊问题和现象。”[6](p.3)也就是说,英国文化研究强调实践和干预,密切关注社会变革,关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系统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领导权。
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干预倾向与成人教育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得各国民主思想普遍高涨。英国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英国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本身就是民主高涨的产物。由于战后英国成人教育与WEA和NCLC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成人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英国各种思想斗争的一个舞台,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整个牛津大学(成人教育)代表团甚至被视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2](p.80)。许多成人教育工作者,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教师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每位WEA教师都是具有这种或那种色彩的社会主义者”[2](p.69)。威廉斯、霍伽特及其他许多成人教育教师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下层贫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战前的罢工、红色的3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任教于成人教育的时候,汤普森、萨维尔是英国共产党,威廉斯虽然退党,但有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20世纪后半叶许多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与英国战后成人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就是从成人教育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这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教师尽管在许多方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组织和教授早期以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体的学生时,这些教师力图把在传统大学中很少得到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引入课堂,鼓励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并以此来思考和解释现实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他们都毫不隐晦自己的政治立场,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威廉斯甚至认为,“要是在课堂中不表明你自己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2](p.80)。
在教育工人阶级学生的同时,英国战后那批成人教育教师对于工人阶级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被剥夺状态,更好地理解了工人阶级需要和追求。这些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原有的立场,进一步激发他们研究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辩护的决心。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带来的相对富裕使得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稳定的提高,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学者不能不重新思考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命运。因此,《文化与社会》直接针对利维斯的文化精英主义思想,要求把文化创造和享受的权利还给工人阶级和普通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着力追溯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开创了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研究范式;而《识字的用途》则专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对未来的思考。尽管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文化与社会》、《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都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都表现出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倾向,都关注工人阶级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的生活,这种研究范式为英国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主要阵地,英国成人教育教师面对战后的纷繁复杂的局势,秉承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干预现实的传统,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把自己的教学、研究与现实的问题结合起来。他们不但与流行的精英主义文化思想斗争,而且积极投身于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因此,无论是在苏共20大、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还是在核裁军运动(CND)中,这些人都是中坚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新左派运动才得以蓬勃兴起。从这个意义来说,英国文化研究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干预色彩也是起源于战后英国的成人教育。
五、结论
大批具有文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的新一代成人教育教师在成人教育这块特殊的阵地上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广泛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实验。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客观的条件,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把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哲学等学科融合起来,分析新近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从而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同时,由于这批新生代的学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们走出学术的象牙塔,积极投身于现实的运动中,成为英国新左派的中坚力量,这也决定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干预倾向。在多年的成人教育工作中,以威廉斯、霍伽特和汤普森为代表的学者的实验和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兴起有多种多样的看法,而且每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成分。但是,谈到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成人教育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深入研究战后英国成人教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的起源及未来走向。
注释:
①文化研究的这种复杂多义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化这个术语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术语的多义性。文化研究有广义的文化研究和狭义的文化研究之分。广义的文化研究是指任何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阐述,它的覆盖面极其广泛,可以涵盖诸多的学科,也许用对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来称呼它会更准确。狭义的文化研究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于英国,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建立为标志的一种学术思潮,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指的是狭义的文化研究。
②英国成人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成人教育与英国工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劳动学院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和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在英国成人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战后,NCLC慢慢萎缩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虽然WEA依旧在发展,但由于战后对WEA的性质和使命的理解的分歧,同时由于大学更有财力支持成人教育的发展,英国成人教育更多地转到大学。此后,英国成人教育发展迅猛,英国成为世界上成人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在探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有时使用WEA,有时使用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威廉斯就基本上使用了成人教育这个说法,因为WEA本身就或多或少依附于大学。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一并采用成人教育的用法。关于成人教育、NCLC、WEA之间的关系及论争,可以参阅雷蒙·威廉斯在《政治与文学》中的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