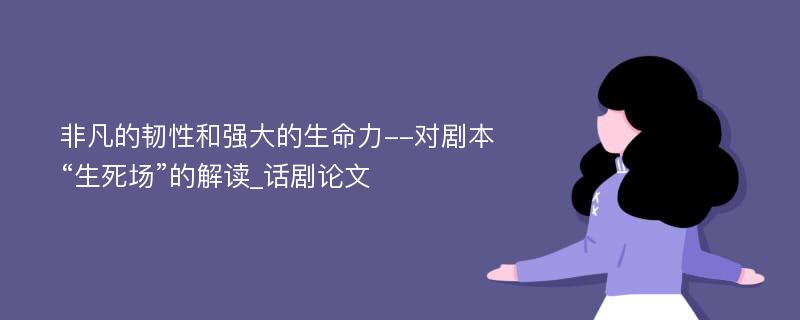
非凡的韧性与雄强的生命力——话剧《生死场》的编导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导论文,韧性论文,话剧论文,生命力论文,非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触动我的是那种非爱非恨的生活图景,以及面对“生、老、病、死”不动情的麻木态度。站在20世纪末,回眸中国现代文学,一些作品依然跨越时代地向我们走来。于是,改编《生死场》的想法产生了。
随着对小说的进一步了解,我感到华夏文化孕育的生命精神已力透纸背呈现出来。抓住这一精神主旨,改编构想随之形成。话剧《生死场》,不能全部继承小说中动人的散文化风格。为了舞台可视性,我忍痛将人物关系大量调整,以赵三及二里半两家人的恩怨串联起由土地增税激发的农民暴动的失败经过和妇女频繁生育导致的漠视生命现象,及日本鬼子到来依然故我、不觉不醒的麻木态度等事件。在剧情发展中运用适量插叙、倒叙、定格等手段,将小说中散点事件增减或凝练。直到日本的侵略行为破坏了“生、老、病、死”的和谐,这幕反反复复的乡土戏剧才宣告结束。当生死已不能自己把握,村民们抗争了,慷慨赴死。编剧方面只顺时针对描写民众的觉醒过程。剧本自觉追求着内容、精神的一致性,为二度创作及未来演出意义寻找依据。
萧红原小说注重“向着民众的愚昧而写作”,而我们的话剧要强调的是民族非凡的韧性和生命力的雄强,对民族命运进行反思,找到华夏民族的主体生命精神,呼唤民族自醒意识的复归。
话剧《生死场》以乡土外观承载精神思索。戏的风格呈现为:带有叙事诗品格的乡土话剧。舞台上的表现特点,是朴拙的民风展示,使观众感受到基层民众独特的叙事方式和方式背后的历史分量。其主题思想是:民族自尊心需平日培养,民族命运要集体肩负,民族凝聚是托起明天的基础。
全剧的矛盾冲突共分四层。
第一层:来自生死的矛盾。中国民间流传着一种基本死亡信仰,人死变鬼,从阳间转入阴间。一旦相信这种说法,生命毁灭的巨大恐惧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中国百姓面对死亡的基本方式。剧中人就是全然相信这种说法的,这样的人自然蔑视生的可贵。而中国自古以来,对死亡以后的迷信就多于对现世生存的考虑。于是,对人的自由与人的权利就简单轻视了。生是自然,死亦漠然,这种生死观念,制造了众多灾难。生死本身具有哲学意蕴,为这个戏带来了思考品格。
第二层:来自人民内部的矛盾。赵三与二里半便是这群人中并不典型的两个。
第三层:统治阶级与下层人民的矛盾。当手无寸铁的下层人民成了被摧残对象,农民就会起来暴动。但是,由于农民的无知与弱小,内部总是出现种种矛盾,加上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疯狂镇压,这种起义与暴动往往以失败告终。戏中的赵三杀地主事件,就是这种闹剧的典型。
第四层:帝国主义带来的民族矛盾。戏中出现的抗日场面是早期日本侵略东三省时,民众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自发抗日的悲壮景象。这景象吹响了东北抗日的号角,也为后面的全民抗日做好了积极准备。
话剧《生死场》中的人们被“生、老、病、死”的轮回驱使,麻木地生活着。现代社会带来了日趋成熟的自我价值观念,人们又被规范于某种社会需求之中,但“生、老、病、死”依然存在,民族基因不会根本更改。《生死场》恰借萧红“向着民众的愚昧而写作”之言为基础,警惕时代进步所常常忽略的自醒意识,呼唤民族脊梁的挺拔。
表演是戏剧艺术的核心,全剧的构思,最终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完成。话剧以塑造人物见长,要分析角色的情感性质,确立角色的思想线、行动线,以体验人物全部的情感、行为作条件,塑造出属于这个角色的个性结构,这是我对演员的总体要求。同时我要求他们注意运用自然主义表演和表现主义表演的结合,寻找细腻和明确、集中和丰富、夸张和真实的分寸因素,力求创造出优异的表演技法。我提出了“姿态狂热与形象魅力及运动的肢体语言”这样一个命题,追求朴素、粗犷、力度的造型特征,解放思想,解放形体,明确这是一次新的探索,自觉形成和谐统一的演出韵律。
在舞台视觉形象方面,要寻求整体视觉效果。我不追求形似,只要求传神,使象征成为主要手段。以朴拙、力度为原则,透视出写意观念的融合。加入戏曲时空表现的一些最基本技巧,如可变性、流畅感、自由度与装饰风格。我要求服装、化装应与舞台布景一并思考出和谐的语言体系,摒弃唯美情绪,在参与年代考证的同时,重视戏的格调、人物个性及力度。灯光除渲染、烘托舞台气氛之外,要加强表情写意功能。多用局部光,切忌满台亮。色彩变化不要频繁,直到抗日,才逐渐加强色光,配合戏的内容,逐层渐进地发展色彩构成,准确传递舞台视觉形象的诗化功能。音乐、音响作为听觉形象,力求精致处理,强调运用单纯、简约的民族调式。悲壮、激昂的场面,要通过音响扩大民族音乐气势,让观众感到民族力量的震撼。
创作过程是相互启发与磨合的过程,是一次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生死场》演出的成败,取决于全体演职员的驾驭能力、文化艺术的修养,取决于我们的理解与沟通。我们正在携手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共同努力,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