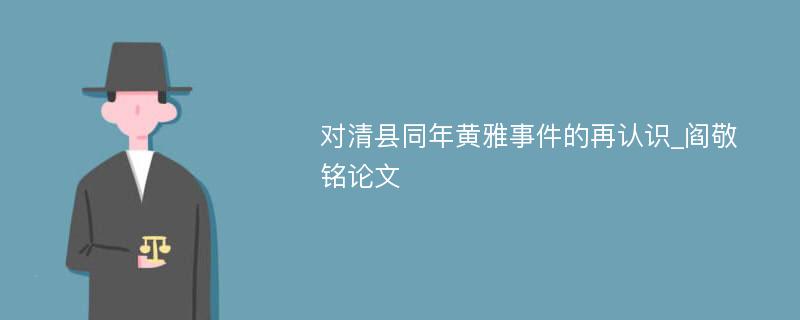
清咸同年间黄崖事件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年间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6)03—0086—06
为避太平军祸,“移家而北,转徙济南、博山”[1](卷四《兵事录》,第635页) 的太谷学派门人张积中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结寨肥城长清间黄崖砦,弟子不下万人,蔚然成一家言”[2](第2页)。同治六年(1866年)十月六日,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率兵破寨,张积中及门徒200余人自焚,寨民被戮逾2000人。事后,民间对张积中普遍抱有同情心态,清廷则坚持强硬立场,学术文化界更是众议纷杂①。笔者综合文献及实地考察,发觉前人立说皆有似是而非之处,因而就此加以辨析和检讨,并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
一、“教”案辨
因张积中所奉之太谷学派旧有太谷教、崆峒教、大成教等称,故有人称黄崖事件为“教”案。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张积中黄崖山讲学与民间宗教有根本区别,理由有二:
(一)张积中无僭“教”之名
积中北上前,得“督兵大臣周天爵以奇才荐□两江各军戎幕”[3](卷一《方域志》,第97页),若其学为异端,必难见容于幕府。后至黄崖山,阎敬铭也承认其“习静居山,以授徒讲书为业。……并无违悖情迹”。“学问优长,多以性理教人等情。”[4](卷宗号03—166—18(153)) 张积中以儒家为纲,旁兼释、道,教育弟子“学孔孟之学,而不能任孔孟之任,惰也。言孔孟之言,而不心孔孟之心,惑也”[5](第一辑第二卷)。察张氏言行,未见涉“教”之名。 御使乔树柟翻案时也强调“张积中之所学究是否邪教,自有一定之是非”。[6](第136页)
屈汉斯因张氏旁涉释、道学说,以欧洲正统教派与异端来臆会儒家与太谷学派的关系,[7] 窃以为不妥。从中晚唐以降的儒佛交流及禅宗、道学等哲学派别的分合演变轨迹中,容易看出儒、释、道三者思想本有联系的事实。笔者以为太谷学派与所谓正统儒家(实质清代儒家无一统之言)的区别,仅可比拟《春秋》三传之差异。刘蕙孙等人有专论[8](第184—193页),此不赘言。路遥提出判定民间教门的两大标准是其“教理、信仰撷取了儒释道三教一些词汇与观念,由于它偏离了正统,而被儒、佛、道斥为异端”与“从信仰异端发展为具有叛逆性活动”。[9](第3页) 就黄崖事件来看,撷取佛、道词汇与观念多少为其偏离正统之度尚难确定,且其反政府活动与其讲学无必然联系。
山民称张积中“圣人”,非其本意。他曾明剖无奈心迹:“淡于利禄,肆志诗书,以世乱未平,隐居求志。虽不敢希古人达人寔,自谓无愧袅影。无如韬光未□而。处士虚声动,人间听相从。”[4](卷宗号03—166—18(60)) 此语出于阎敬铭奏折附件,若阎作假,则可证他也承认张氏本无求圣之意。况且,传统儒者,本都隐藏希圣希贤之心,以“圣人”之称作为其立教野心,恐有不当。
(二)张积中无行“教”之实
兴巫炼气与仪式神秘是后人冠张积中行“教”之实的主要依据,实际上两者皆有可商榷之处。
传闻周太谷“能练气辟谷,符箓役鬼”[3](卷一《方域志》,第97页),“明于阴阳奇赅之数”[10](第569页)。《骨董琐记》形容李光炘“相传有诸异术,能搬运法。……扬州围急时(指太平天国事),运使乔松年哀晴峰(李光炘字)行法,为致巨金作饷。”[1](第81页) 李与张为同门,太谷曾悉传所学,其“练气辟谷,符箓役鬼”之术想必也传之。从时代角度来理解张积中黄崖山所为,并不玄怪。旧儒,皆涉医道,庸者草头药汤,秀者不乏悬壶之能。中医与巫者之炼气煮砂有千丝万缕之勾联。积中为硕儒,晓医道,在山寨为四民医治,少不了煎汤煨药,也不排除行驱邪除魔等迷信做法。有些所谓的修炼之法,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也颇流行。《骨董琐记》作为一本日记,其真实性有待检讨。周太谷于《易》用力最深,并有自己的解释体系,故可合理地理解“诸异术”为其对阴阳八卦五行的精深研究,或可忖度为某些特异功能乃至魔术的可能。
张氏纳弟子及拜神明也确有繁琐仪式。在仪征时,“慕者踵门伏地,敂颡流血,积中坚拒之,谓‘无善根,非造福济世不可’。先令放生施食,作诸善事,而阴诇其隙曰‘某事惜力,某事惜财,不足证道,为太谷所弃”。[10](第570页) 居黄崖山后,“礼神恒以深夜,参拜升降,礼节繁缛。……旃檀燎烛,熏赫霄汉,十余里外望其光,乡愚辄称张圣人夜祭,顾非其徒不能入窥也”。[3] (卷一《方域志》,第98页) 其“山规”规定:入寨者,除在公局登记外,私产纳半入库。禁恋色、吝财、馈赠与宴请,不歧视妇女。东汉到近代,地主豪强的村寨圩庄中常有类似规定。且黄崖山寨对于违“山规”者,无强制律令,以说教为主,不改者逐出山寨。故仅凭“非其徒不能入窥”的仪式和所谓“山规”作为其持“教”之据,乃至屈汉斯以“作为异教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夜间举行仪式”[7] 等列证,似乎过于勉强。
其次,统治者未以“教”为名作镇压口实。阎敬铭奏折中未提张积中以“教”谋逆之意。清政府对民间教门取高压态势,如开始即定其性为教门,此后绝无如此波折。
事后,阎敬铭在与门人书信中未加掩饰地提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所尤异者招降解散数日,无一出者,中有书生,何其愿从之死?大惑不解。”[12] (第143页) 前人以此旁证张积中惑人之深,但换角度理解,可见无论朝野舆论如何,阎有自己的认识,其“大惑”有相当程度是“不解”于张所学是否为“教”,“中有书生”表明其对整个事件的性质不敢遽下结论。
二、“匪”案辨
阎敬铭奏折中称呼黄崖山民众共20处,分别为“匪徒”、“逆”、“逆党”、“逆徒”、“匪”、“贼”、“匪党”等名目,体现阎敬铭对于该事件的认识。清廷高层,则基本按奏折定其“匪”性。这种评判的出现有两大原因。
(一)主办大臣操之过急,过于严厉
身为山东巡抚,杀戮民众,阎敬铭罪责难卸。然其身为封疆大吏,深知牧民之术,惹下恶名恐非本意。刘蕙孙考证其先向军机处报功,在朝廷颁下升赏后才进行剿杀。[13] 笔者从其考,但阎下决心的过程应值得推敲。阎氏为官,清廉严厉,不拘私情,清廷评价其“清勤直亮,练达老成,宣力有年,克勤厥职”[14](第4473页),这种作风可作为其处置黄崖事件过于严厉的注脚。
王小花供认“曾有人召其往黄崖山认张积中为师,彼处已集徒多人等情”后,阎敬铭考虑“王小花语涉可疑,饬令提省究办,研审数月”。最终认定“王小花并不认识张积中,系闻人言,而传言之人追究未获”。阎觉得“王小花与张积中两不相识,未便提案对质”。并认为:“张积中系忠荩人家,宗族亲戚科第簪缨,似不至聚匪为非。”[4](卷宗号03—166—18(153) ) 对于“忠荩人家”且尚有亲戚为官的张积中,阎氏也有顾虑。对黄崖山寨讲学及布列商肆的行为,阎仅粗知其事。事后,阎敬铭搜集到部分张氏文稿,如“知所先后说”、“中隐十而见五说”、“三奇说”、“八门说”、“周南”[4](卷宗号03—166—18(61)) 等,才对其所学有所了解。故阎氏一直存有疑虑,其戒备之心随张积中民间声望的增加而加深。
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二十日,阎敬铭接报,称“拏获匪犯冀宗华、冀兆栋,供出同拜黄崖山张七即张积中为师。现山中业已聚集多人,会彼等赴青州一带勾结,定期九、十月间起事。先取青州,后取济南等情”。旋又“接临朐县何维堃电称获匪祁嗣清等十一名,均供认与黄崖山结□,乃余供与冀宗华相同”。阎氏遂派“守备唐文箴会同肥城知县邓馨、长清县知县陈恩寿于二十四日赴山拏张积中到案”。[4](卷宗号03—166—18(153)) 张积中拒不就命。 阎“又檄藩司亲自长清饬县令人山告谕,至则不□入”[1](卷四《兵事录》,第635页),阎敬铭终于失去了耐心。
(二)黄崖山民众授以政府口实
史料称黄崖山寨的不当举动破坏了统治秩序,超越了统治者容忍极限。学术界公认《山东军兴纪略》有夸溢之辞,但相关史料皆有类似记载,这个史实该被承认。
这些不当举动包含抗拒调查、自立武装、杀害兵吏、骚扰乡间等四个方面。
抗拒调查:守备唐文箴等人“赴山拏张积中到案”时,张积中“深藏山寨,闭匿不出”[4](卷宗号03—166—18(153))。“又檄藩司亲自长清饬县令入山告谕,至则不□入”。至大兵压境,“抚帅再示招谕”,张依然“覆言事须从缓”[1] (卷四《兵事录》,第635页)。政府对编户齐民有管理权力。张积中屡次抗拒调查, 显是一种反政府行为。
自立武装:咸同年间,山东民间常见团练武装,但武装须得到政府认可,擅自武装仍属反政府行为。黄崖山实行兵民一体的山寨自治,“益市弓弩、兵仗,习战事”[3](卷一《方域志》,第98页),设“武备房”,招募乡勇。初为自卫,但未得政府批准。屈汉斯还指出一个细节:在阎敬铭发出最后通牒后,黄崖山民众开始“加固堡垒,囤积木柴、粮食、煤和蜡烛。然后黄崖山上的居民退居这个堡垒并在隘口上装了一门大炮”。[7](第32页) 囤积给养尚属正常, 而安装大炮已是对抗的信号。阎敬铭上报清廷之缴获山寨军械数量与类型并不可靠,但用兵上万,足证山寨具有相当军事实力。
杀害皂吏:陈恩寿等往黄崖山拏张积中对质,“该员等守至夜间,适在山庄居处之候补知府、前任济南知府吴载勋为张积中姨表兄弟,仓皇移家出山。并闻山上洶洶聚人。该员等见事已变,乘夜逃出,竟有多人追逐,陈恩寿尚有家人一名在后,即被杀害”。有学者认为冲突出于误会,但第一刀为黄崖山先起,基本已无异议。这一刀坚定了阎敬铭的决心。
骚扰乡间:史载:东张庄武生王宗淦“出家资练乡勇,备战守。积中党屡次诱引,终不从。至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积中将起事,先纵火焚宗淦宅”。[15](卷五) 清兵进剿前,黄崖山寨之人“掠长清之下巴、贵德、马家山、黄花园、辛庄,肥城之石岗、东张庄,夺乡民骡马”。[10](第572页) 严薇青认为“黄崖山可能为了自卫,采取坚壁清野的措施,焚烧包括东张在内的附近村镇,以至波及王宗淦的房宅”。从而导致了“好义任侠,负不羁才”[16] 的王宗淦疯狂报复,他以全家为清兵人质,亲率乡勇为头阵攻击黄崖山。阎敬铭也奏道:“二十五日,该逆等遂将各处山路堵塞,禁绝人行,并逼胁附山各居民入寨。……下山焚掠,共焚烧村庄十余处。二十七日,该逆党头裹红巾分路焚掠,在东张庄杀死民人数名,杀死驿卒二名。”[4](卷宗号03—166—18(153)) 张积中也承认:“又有匪徒籍我之名,四出焚掠。”[4](卷宗号03—166—18(60)) 此话若为阎敬铭伪造,则其似乎不应有为张氏辩护之理,故有相当可信度。
以张氏为人修养,杀害皂吏与骚扰乡间两事,似非其所为,对此的解释应归结于其对黄崖山寨的实际控制力上。黄崖山寨后期,张氏更多的是作为精神领袖而存在,军事首领可能另有旁人,且这些人已具有独立意图。“据武定府知府张鼎辅访闻,入山匪类,多有巨猾,如文生张洸汉、张铃阁,尤为著名盐枭之首。”[10](第574页) 如此,张氏才有“奈及门桀骜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禁之不得……徒拥虚名,非能自主”[4](卷宗号03—166—18(60)) 的感慨。
综上,张积中的黄崖山讲学不属于民间教门范畴,而清廷从统治秩序角度考虑,以“匪”案定性,似无可辩驳。然黄崖山寨的匪化是在政府高压态势下的非主观渐进过程,政府与山寨都有责任。
三、黄崖事件发生的社会生态
黄崖事件的性质难以简单判定,这或许正显示了历史真相的复杂与多元。与其纠缠于非此即彼的定性分析,不如将黄崖事件置入社会史研究视野内,更会获得新的认识,丰富后人对当时历史的理解。笔者以为,黄崖事件与咸同年间山东地区的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咸同年间山东灾荒与流民问题为黄崖山寨聚众提供了条件
以黄崖山为中心,县治在距离其10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有历城、长清、齐河、泰安等近32个县级行政单位,笔者称其为黄崖山密切联系区,在黄崖事件发生前的11年间,该区域内所发生的较大灾荒如下表:
年代
黄崖山密切联系区内受灾县 灾种
1855
几乎全部县黄河改道、 运河决口
1856
肥城、东平、济宁、邹县、长清、阜、泰安等十数县旱、蝗、洪、风灾
1857
滋阳、寿张、曲阜等旱、蝗灾
1858 无大灾
1859
鲁中、南部分县旱、洪灾
1860
部分县洪灾
1861
新泰、历城、泰安、兖州、东昌、长清、肥城等数十县 震、风、雹、旱灾
1862
莘县、阳谷、寿张、济阳、济宁、汶上、滋阳等风、涝、旱、瘟灾
1863
东平、章邱、济阳、历城、齐河等洪、旱、雹灾
1864
济阳等涝灾
1865
部分县洪灾
这一时间段中发生在该区的自然灾害具有频率密、程度重、灾种多的特点。11年中仅有1年(1858年)未发生较大的灾害,而存在1855—1857 、1859、1860、1861—1863等7个中、重灾年份,且大多为复合灾。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海[17](第39页),形成了密切联系区内持续数十年的黄泛区。1856年,肥城、平阴、东平、济宁等县遭受旱、蝗、洪、风灾,“死者枕藉”,“道殣相望”,“五谷不登,人相食”。[18](第8页) 1857年,旱、洪、蝗灾导致“人相食”[19](第194页)。1859年,旱灾使“麦无收,秋禾减产”[18](第8页)。黄崖事件发生的前半年,洪、雹迭虐,成为又一重灾年,密切联系区各县全部受灾。
受此影响,黄崖事件前,整个密切联系区内的农村经济日渐残破,客观上为张积中在黄崖山聚众奠定了基础。山寨民众构成复杂,既有难懂积中讲学之义的农夫,也有退隐官僚吴载勋之流。士大夫的积聚,有其文化向往,而山寨中更多的则是逃荒避难之人。据笔者实地调查,黄崖山周围群山环绕,交通闭塞,以大峰山等山脉为屏障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附近数千亩沃田,较少受外来洪灾影响。张积中并在山东各要隘孔道设立店铺,阎敬铭等人称张积中有聚众敛财之意,可证山寨的物质生活还是有相当保障的。自道光以来,鲁西南灾区即“十室九空”,流落在荏平、东平、东阿等地的“饥民,纷纷求食”,“男妇老幼,十百成群,攀辕乞丐”,“尽转沟壑”。[20](卷八十七,咸丰三年三月) 1866年,山东饥民达数十万,这个庞大的饥民群体处于不断地流动之中,类似黄崖山寨这样的“乌托邦”[21] 必然成为时人向往之处。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忖度,即使没有张积中的讲学活动,黄崖山寨的单纯聚众也是可能的。
(二)咸同年间山东民间军事化结构同质了黄崖山寨
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与捻军两大军事集团的冲击下,被清政府视为“土匪”、“教匪”、“团匪”的民间反政府军事武装在山东风起云涌。黄崖山事起前,除捻军外,山东尚有清政府视为长枪会匪、水南匪、水套匪、邱莘教匪、幅匪、邹县文贤教匪、曹州会匪、淄匪、黑旗军及大小团匪等数十股较大民间反政府军事武装,其众不下百万。这些武装普遍拥有较强的组织与作战能力,他们的形成是灾荒与苛政,乃至民间自卫的结果,如刘德培起义初期即为抗捐粮之举;而一些所谓的“团匪”前身则为乡民自卫武装。由于漕运的废弛,数十万漕工失去生计,这些武装成为他们的主要存身处。这些武装自立山头,相互之间分合复杂,各有立场。民间军事化结构形成不仅使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下降,而且加剧了社会恐慌情绪,盲目了政府对民间团体的处置。这就为阎敬铭血洗黄崖山埋下了伏笔。
张积中为阎敬铭所虑的隐因是民间军事化结构下黄崖山寨的走向问题。
《三续淄川县志·兵事门》、《宜园笔记·淄川刘德培抗粮始末》、《味古斋抄本刘德培记略》等书讲述了张积中弟子司寇平与刘德培的联系,张积中曾为司寇平相面,称其有帝王相,刘等可为佐命,遂有异志。后遭邑绅王某告发。济南知府吴载勋(张积中表兄弟)派候补知县张道生(张积中之子)前往查看,张道生“饰词禀复”,“刘、司势力坐大,终至爆发了起义。”刘蕙孙认为“这些有一定的根据”[8]。笔者查询中国第一档案馆藏奏折,大致不讹。可证张积中与刘德培起义有一定关联基本属实。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正发捻逆股及朴军防紧急之际”,[4](卷宗号03—166—18(153)) 冀宗华等供认拜张积中为师及预备起事等状,膨胀清廷对黄崖山的警惕之心。“彼时,西捻股甫经防军击,已向嘉祥奔窜,……该逆徒虽系甫经啸聚,惟闻有勾结东府匪徒及北路盐枭甚多。”阎敬铭因黄崖山“逼近省垣,更虑内外勾结,大肆蔓延”,遂决心“必须迅速及早除灭”[4](卷宗号03—166—18(153))。阎敬铭为其罗织的罪状还有:“该匪业经勾结武穴一带盐枭数万名,四山□更有外援,……黄河水次□有□船为送军械之事。又据逃出村民供称,该匪已于日内遣匪党赴沙西勾结捻匪,令来扑运,以为内外勾结。”[4](卷宗号03—166—18(58)) 罪状虽为罗织,但可佐证当时“匪情”之炽。 统治者担心黄崖山民众与捻军相呼应,由于黄崖山“逼近省垣”,某种程度上较捻军更属肘腋之患,阎敬铭仓促决断,终酿悲惨之局。
刘德隆称黄崖山寨“与近代史上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山东刘德培起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2](第218—219页) 捻军入鲁,张积中曾形容:“归德为已破之垣,徐守为不守之户。贼马所踏,村郭为墟。夏邑、永城达亳州七百余里,烟火俱空,白骨连天,黄蒿满地,《流民》莫绘。”[5](第一辑第二卷《白石山房文钞》卷二) 其兄“积功知临青州,阖门死粤匪难”[1](卷四《兵事录》,第634页)。从避天平军祸而北上, 与太平天国有杀兄之仇到与农民起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张积中对山寨实际控制力下降外,也是黄崖山寨在当时山东民间军事化结构下生存的必然选择。清季太谷学派南宗于苏州归群草堂开讲,未遭政府镇压。屈汉斯认为“当这一学派成为一个脱离国家控制的、独立的团体时,当清政府担心它与反叛分子结盟时,才开始对它实行镇压”[7]。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恰恰忽视了山东民间军事化结构的存在。
史载:“是役也,杀人万余,而未得谋反实据,文介(阎敬铭字)意亦不自安。尝责正起、成谦、心安三人曰:‘汝辈皆言谋反是实,今奈无据?若三日内不得,则杀汝。’三人急,命搜得戏衣一箱,使营中七缝工稍补治之,即以为据。”[23](第1115页) 后人多以此为阎敬铭陷害张积中的证据。然没有“戏衣”,黄崖山寨就一定清白吗?其“精神领袖”张积中无反意,可为公论。但民间军事化结构对其影响混淆了清廷的判断。加上当时形势的紧张,黄崖山寨的种种不当行为被视为“反”迹则理所当然。《清稗类钞》有文:张积中“聚徒讲学,尝告人谓黄崖可避乱,独先移家往,从之而去者,渐积至八千余家。筑砦购守具,为久居计,无异志也。徒以依附者众,又诡秘相习,不知敛戢,至使当道疑为山贼,同于灵运而遽罹浩劫,遂为官府邀功者所利用耳”。[23](第1112页) 其“无异志”为后人所肯定,官府的“邀功者”所“利用”的正是黄崖山寨的不当举动。所以,认为黄崖事件完全是“冤”案,也违背历史事实。
黄崖事件发生于一个灾荒频繁,民变蜂起,政府统治与社会伦理失范的年代。政府对民间控制力的下降为张积中扎根黄崖山提供了宽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其太谷学说号称拨乱反正,以宣扬孔子正统为志,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欢迎。而旁及释、道乃至“异术”则又迎合了中下层百姓的口味,但仅是黄崖山之所以兴盛的魅力元素。清政府清剿山寨是民间军事化与政府控制的矛盾激化行为。清政府将黄崖山类同于一般“匪”类,这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看法,但也是当时政府所能判断与决定的惟一途径。故,黄崖山寨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的社会生态所决定的。
收稿日期:2005—10—13
注释:
① 具体争论可参见以下文章:戴莲芬:《黄崖教匪》,载周去病标点:《鹂砭轩质言》,上海进步书局,光绪五年;刘蕙孙:《同治五年黄崖教案质疑》,《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刘蕙孙:《同治五年黄崖教案质疑补》, 《史学集刊》1936年第3期;严薇青:《“黄崖教案”余闻点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德]屈汉斯:《对“黄崖教案”的思考》,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