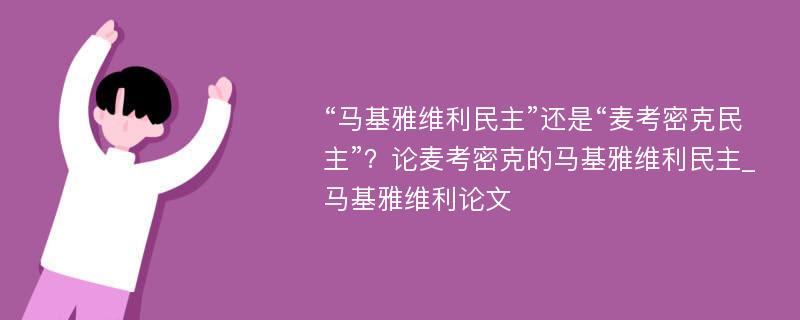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还是“麦考米克式民主”?——评麦考米克著《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维利论文,马基论文,评麦考米克著论文,麦考米克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基雅维利的精神正在当代获得新的延续。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麦考米克在其出版于2010年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式民主》①中指出,当代的选举式民主无法避免经济精英垄断政权,必须在选举之外赋予平民以额外的制度支持,才能平衡富人的力量;而马基雅维利恰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原理和制度方案。根据他总结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麦考米克为当代美国设计了一个“保民院”,这个保民院由51个随机选取的非富人阶层的公民组成,具有否决权、公投提案权、弹劾权三项基本宪法权力,承担起守护共和国自由的使命。(pp.183-184) 麦考米克教授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其马基雅维利解释尤以“平民主义”(populist)路径而著称。②在解释路径上,麦考米克教授与剑桥共和主义学派存在严重的分歧。麦考米克批评斯金纳、维罗里、佩蒂特等剑桥学派学者过多地将马基雅维利放在古典共和主义复兴的语境中进行解释,赋予其过强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未能注意到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激进性和创新性。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平民立场,试图在一个贵族与君主主导的时代对平民进行赋权。③这一观点当然不是全新的。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指出,马基雅维利其实是在给人民上大课,《君主论》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其真正目的并不是给君主出谋划策,而是向人民揭示君主的阴谋诡计。④但卢梭并没有在学术上完成这个证明。卢梭以后的平民主义者们继续受到马基雅维利的激励与启发,尤其是两位共产党人——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阿尔都塞。葛兰西在《君主论》中读到了马基雅维利对当代“新君主”共产党的告诫,⑤而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位孤悬在16世纪,与19世纪的共产党人气息相通的思想家。⑥同样,这两位天才的思想家也没有对马基雅维利的文本进行足够深入和细致的学术解读。 《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则在学院派学术的意义上对“马基雅维利=平民主义者”这一命题进行了证明。在这本著作中,麦考米克主要基于《君主论》、《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三部作品,阐发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原理,并对其制度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对平民(popolo)与“大人物”(ottimati或grandi⑦)之间差异的深刻理解。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都存在两种不同的脾性(umori),“大人物”的脾性倾向于压迫,平民则试图摆脱“大人物”的压迫;既然“大人物”的野心并没有止境,平民在摆脱为必然性(necessità)而斗争之后,仍然要为对抗“大人物”的野心而斗争。如果说守护某物的责任应当被放在对其最缺乏占有欲望的人身上的话,那么,守护共和国自由的责任应当被赋予平民。在马基雅维利笔下,罗马提供了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在那里保民官具有否决权,平民具有立法权和对共和国官员进行公开指控的权力。这些制度比选举更有助于维持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大人物”很容易俘获选举制度,将其变成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所构想的制度模式,完全可以应用到当代世界,尤其是美国。为了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当代的关联,麦考米克不能不注意到当代世界与16世纪在情境上的不同:在当代世界,帝国主义已经臭名昭著。因此,如果他所阐发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帝国扩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那么,这一模式自然也就无法在当代世界获得足够的正当性。因此,麦考米克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作出“去帝国化”的处理。 在我看来,麦考米克的努力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提出一种对当代具有启发意义的民主模式;第二,论证马基雅维利是这种民主模式的思想教父。这两个层面事实上可以相对分离。即便没有第二个层面的证明,哪怕我们将第一个层面的民主模式称为“麦考米克”模式,它对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实践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如果审视麦考米克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作的思想史证明,这部作品的薄弱之处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作为“平民主义者”的形象塑造,是以压制马基雅维利文本中的另外一些重要主题作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帝国扩张的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大人物”正面作用的思考。 本文将对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首先讨论麦考米克的文本解释路径,揭示其长处与不足,这同时也是一个反复界定麦考米克所赞成的民主模式的实践指向的过程。然后,讨论将转向这种民主模式的实践启发意义。既然我并不认为麦考米克忠实概括了马基雅维利的民主模式,那么,我同时需要说明,准确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又具有哪些要素和实践意义。我将证明,麦考米克所赞同的民主模式是对真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批判式发展,二者并不能相互等同。 一、麦考米克的解释方法 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解释,基本立足点就在于马基雅维利对贵族(ottimati)/大人物(grandi)与平民(popolo)两种不同脾性的区分,即前者倾向于压迫,而后者仅仅是要逃避压迫。然而,一般解释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个区分,而是马基雅维利那些看似愤世嫉俗的对人类自然(natura)的全称判断。比如,在《君主论》第17章中的这个判断:“关于人类,一般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利益的。”⑧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中,他又指出:“自然创造人类,使其能够欲求每个事物,却不能得到每个事物;如此一来,由于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是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意,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感。由此导致他们命运的不同,因为一方面有些人欲求拥有更多,另外有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由战争导致一个地区的毁灭和另一个地区的成功。”⑨ 解释家如果重视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这些一般描述,通常会很快将此与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观与帝国观联系在一起:因为人是贪婪的,欲求无度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而在扩张和征服中就会出现帝国。这一解释看起来也符合《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那段话的字面意思。但努力对马基雅维利“去帝国化”的麦考米克并不愿意接受这一解释方向。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的一般教诲不应按照其字面意义来理解,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于“大人物”和平民的区分。他引用了《李维史论》第1卷第5章最后几句话,在那里,马基雅维利指出,大多数时候骚乱是由“大人物”引起的:“大人物”既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源,又害怕失去手中已有的资源,同时,他们可用以作恶的资源也更多。是“大人物”的“不端和有野心的行为举止”,在那些不拥有这些事物的人心中燃起占有的欲望。换言之,“大人物”拥有资源,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或公共福利,而是为了压迫比他们低的阶层;而平民并不天然嫉妒“大人物”,只是在受到“大人物”压迫的时候,他们的欲望才被激发出来。用麦考米克自己的概括来说,少数人和多数人“分别被不同质的欲望所驱动”(p.5)。因此,马基雅维利对两种脾性的区分,而非对人性的一般描述,才更具有实质意义。 更具体地看,“大人物”到底是被什么欲望所驱动的呢?在传统解释看来,这些“大人物”之所以压迫平民,是因为他们对荣耀具有极大的渴望。但麦考米克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马基雅维利眼里的“ottimati”或“grandi”,其主体其实并不是追求荣耀的世袭贵族,而只是跻身权贵的富裕阶级,他们的首要渴望是攫取更多的财富,甚至罗马的贵族也表现出这一倾向。麦考米克着重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中对罗马贵族的评论:“罗马贵族在涉及政治职位时,总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没有引起对公民政体过分的骚动;但是,当涉及财物时,贵族是如此顽固地保护。”罗马贵族为了阻止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最终采取了谋杀这样极不光彩的手段,这说明他们首要的欲求对象并非荣耀,而是财富。(pp.4-5)麦考米克进一步指出,从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城市国家的历史来看,多数贵族也并不追求罗马式荣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而非积极的帝国扩张政策;更倾向于维持国内秩序的和谐与稳定,而非阶级斗争。(p.56)由此他推出,马基雅维利对“大人物”本性的认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麦考米克将“ottimati”或“grandi”解释为富人,当然是为了在当代推广“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模式这一实践目的。在近代革命之前,“大人物”往往拥有许多身份性特权,而不仅仅是在财富上存在差异;而当代的“大人物”与大众之间很少会在法律身份上出现不平等,但他们可以运用自身优越的经济社会资源,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以利于攫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因此,要让“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模式与当代无缝对接,就要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所针对的对象,从根本上还是社会的富裕阶层。 在厘清“ottimati”或“grandi”的含义后,麦考米克告诉我们,理解《李维史论》的关键是理解这部作品所呈献的两位青年人:科西莫·鲁切拉伊(Cosimo Rucela i)与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Zanobi Buondelmonti)。解释家们对《君主论》的呈现对象大做文章,通过理解梅迪奇来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意图,然而,很少有人在《李维史论》上花同样的精力,也许是因为解释家们觉得《李维史论》的呈献对象比较简单。过去一般的解释将这两位青年人解释为共和政体的同情者,而“共和之友”自然地等同于“平民之友”。但麦考米克却提醒我们,“共和之友”未必是“平民之友”,因为共和国里存在着“大人物”和平民之分。这两位青年人“出身于拥有相当财富和名声的家庭,凭借着家族谱系、教育和才能,有望在政治体中占据显要的位置”(pp.36-37)。从低于他们的社会等级人士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是ottimati或grandi的一分子,也分享了ottimati或grandi攫取财富和压迫平民的倾向。 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麦考米克将两位青年人的“大人物”身份之重要性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为他们身上有“大人物”的本性,马基雅维利的教育就只能顺势而为,将有违“大人物”利益的政制方案巧妙地包裹在复杂的修辞之下。简单地说,马基雅维利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建立帝国的不朽功业,而“大棒”则是所谓“必然性”(necessità)。 正如上文已指出的,为了论证“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在当代的适用性,麦考米克不能不大力对“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和在当代已缺乏正当性的帝国主义作出切割。这就要论证,马基雅维利对帝国荣耀的强调,只不过是用来引诱“大人物”家庭出身的青年人的修辞,并不完全是他内心的信念。“大人物”的攫取倾向是无法消除的,问题就在于将其导向何方。让青年人对建立帝国的不朽荣耀感兴趣,就可以将他们的攫取倾向导向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为平民主义政制的引入提供条件。马基雅维利对威尼斯、斯巴达与罗马的比较就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罗马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功业远胜过前两个城邦。但罗马建立帝国的手段,是将平民武装起来,并允许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进行实质的参与。一个青年人如果对罗马帝国不朽的荣耀感兴趣,那就必须认真考虑罗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政制手段。这一手段至少在国内来说,是不利于“大人物”对平民施加压迫的。这就类似于将毒药包裹在糖衣里,让两位青年人服下。 马基雅维利自己是怎么看帝国扩张的呢?麦考米克认为:“考虑到帝国扩张在马基雅维利关于自由的消亡与共和国的覆灭的叙事中所占据的决定性角色,它可能并不是最可取的”(p.38)。除威尼斯、斯巴达与罗马之外,对另外两个共和国例子的处理,表明马基雅维利对帝国扩张弊端的认识。第一个是雅典,马基雅维利在多处赞美雅典的强大,然而,雅典正是由于帝国的扩张而导致对希腊的奴役以及自身内政的崩溃。(p.58)第二个是瑞士联邦,瑞士人过着自由的共和国生活,军事上也很强大——马基雅维利甚至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30章中说,今天的法国国王都向瑞士人进贡⑩——但瑞士人并不进行罗马式的帝国扩张。在麦考米克看来,瑞士这样的国家的存在,表明在罗马帝国主义模式之外,还存在别的共和强国模式。(11)但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将这一模式推荐给两位青年人,正因为这一模式给了平民以充分的自由和平等,但并没有给贵族相应的补偿,如果向两位青年人推荐瑞士模式,恐怕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除了帝国事业这根“胡萝卜”之外,马基雅维利还抡起了“必然性”的大棒。最集中的讨论是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6章中:“由于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处于运动中,不能保持静止不动,它们必然地要么上升要么下降;许多事情是理性没有促使你去做,而必然性却促使你去做的;因此,即使组建了一个能够不扩张而维持自身的共和国,但必然性促使它扩张,便会逐渐销蚀其根基,使它更快毁灭。”(12)然而,即便在这里,麦考米克也找到了一处说明马基雅维利的教导具有高度修辞性的证据。“必然性促使它扩张”对应的英文译文是:“if indeed necessity brings(a republic)to expand…”麦考米克给“if needed”打上了斜体,指出这表明马基雅维利或许对自己所说的这个主题并没有绝对的信心。(p.57) 不仅如此,麦考米克还注意到,马基雅维利所描绘的罗马,与李维所描绘的罗马以及今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重构的罗马,实际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别。马基雅维利通常会比较忠实地转述李维对罗马贵族如何欺骗和控制平民的报道,但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平民德性的赞美和对他们错误的辩护,基本上不见于李维的文本。(p.61)在李维那里,保民官也根本不具备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如此重要的功能。马基雅维利也根本不谈平民在罗马的“百人团大会”投票中所居的劣势地位——在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官员选举和其他国家重大事项的大会里,头两个等级如果足够团结,他们的投票就基本上可以决定结果,后面的平民等级的投票几乎是可有可无的,而这本来就是一种寡头制色彩十足的政制安排。此外,罗马“部落大会”和“平民会议”开会时并不审议,而只是表决通过既有的议案,但在马基雅维利的笔下,审议成为会议非常重要的功能,这使得平民可以揭露贵族的不合理图谋并加以遏制。马基雅维利对“平民会议”的讨论也没有注意到,“平民会议”的决议是到较晚时期才具有约束全体罗马人的法律效力的。在麦考米克看来,马基雅维利对李维的偏离,应当被看成一种积极主动的解释行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对李维所提供的材料进行筛选,编织出一幅符合他自己政治理念的罗马图景,至于它是否符合史实,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麦考米克进一步论证,平民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对贵族如何控制平民的描述,识别贵族利用帝国扩张来压迫平民的图谋,从而最后实现对帝国扩张的超越。这一论证具有双重的意涵:第一,平民的觉醒最后可以实现国内民主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分离;第二,马基雅维利的《李维史论》另有别的隐含读者,那就是平民。(p.59)后者接近于卢梭的解释路径,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在给人民上大课,里面给君主的建议,最终是对人民的启蒙。 二、“去帝国化”能否成功 本节将从不同层面上对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解释提出质疑,但所有这些质疑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对马基雅维利民主观“去帝国化”的努力,是否经得起文本与情境的考验? 麦考米克正确地指出,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一般判断与其对“大人物”和平民不同脾性的判断之间存在明显紧张。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一般判断缺乏实质意义,真正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大人物”与平民不同脾性的判断。“大人物”具有无限扩张的贪欲,而平民的欲望却是有限的,二者是两种质地不同的欲望。然而,麦考米克对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的断定过于轻率,缺乏详细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撑。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两个层面是否不可调和?在我看来,情况未必如此。马基雅维利只是没有清晰地点出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点,即人类贪婪欲望在行动中的体现受制于具体环境,以及在具体环境中所形成的政治心理结构。但他的文本为寻找这样的连接点提供了线索。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58章对民众与君主的比较中,马基雅维利指出,在作为个体考虑的君主和在人民身上,变化无常、出尔反尔、忘恩负义等罪恶并无两样,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但对于法律尊重的多寡却造成了行为的变化。(13)而我们知道,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尊重法律从来都不只是个人自愿与否的问题,而是首先与外在的必然性相关。由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平民欲望表面上的有限性,只是因为“大人物”对他们的长期压迫,构成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必然性——他们占有的资源有限,欲望的扩张受挫,反过来对欲望本身形成限制。近代之前,欧洲极其微弱的社会流动,使得平民无法期望更多;而“大人物”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而可以更加直接地表现出欲望的扩张。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平民的欲望被激发出来时,同样可以呈现出强烈的扩张倾向。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第3卷第1章中提供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案例。按照麦考米克所总结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理,平民欲求某种东西,往往是由于受到贵族的压迫,从复仇的欲望中产生。但同样由贵族压迫而起,佛罗伦萨平民发动斗争,不是像罗马平民那样满足于和贵族共享最高职位,而是要将贵族排除出最高职位,并对他们进行羞辱,在放逐反抗的贵族之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完全有利于胜利者一方的。(14)在文本中,马基雅维利没有对佛罗伦萨平民何以产生这样的垄断权力的欲望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但如果对语境进行分析,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佛罗伦萨平民欲望扩张的前提,恰恰在于佛罗伦萨贵族本身的孱弱。而在罗马共和国早期,罗马平民在受到贵族压迫时只是进行撤离,这与贵族的团结和强大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些假设还需要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来证明。但至少,麦考米克有必要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处理马基雅维利两层教诲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武断地宣布其中一层缺乏实质意义。 进一步看,麦考米克对《李维史论》进行的“去帝国化”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解释前提的设定:《李维史论》是写给两个“大人物”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因此,马基雅维利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利用两位青年的“大人物”倾向来进行自己的论证。如果把一切都还原到这个说服的情境中来,即便马基雅维利在文中对人类社会的一般状况作出比较绝对化的判断,也都不能从它们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而必须进行“目的解释”。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马基雅维利对帝国扩张的诸多判断就被解释成为引诱两位青年的“胡萝卜”,而关于“必然性”的强势陈述,则被理解成为恐吓他们的“大棒”。 然而,当麦考米克暗示平民可以通过马基雅维利对贵族如何控制平民的揭露,最终实现对帝国扩张的超越,实际上又在不经意中超出了他所设定的前提假设,使论述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意味着,《李维史论》除了两位青年人之外,还有别的预期读者,尤其是平民读者。这一假设符合我们的常识,但作为一个学术假设,它仍然需要学术的证明。我们需要考虑一个事实:《李维史论》并没有在马基雅维利生前出版,尽管里面的很多观点,在他所参加过的佛罗伦萨贵族青年奥里切拉里花园聚会上陈述过。因此,马基雅维利希望后人如何对待他的《李维史论》,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便能证明马基雅维利有这样的意图,这些平民读者与两位受献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基雅维利如何在文本中通过复杂的笔法,对不同的言说对象传递不同的教诲又变成非常复杂的解释问题。这都超出了这本书所能承载的重量。 让我们暂时先抛开预期的平民读者,而专注于麦考米克对两个青年性格与倾向的探讨。应该说,麦考米克注意到这两个青年的贵族出身,比以往学者对两位青年比较泛泛的“共和之友”认识有很大的进步。然而,关键仍然在于如何解释两位青年的贵族出身与他们的政治倾向之间的关联。麦考米克的著作在这方面的处理存在很大的跳跃,基本上可以说采取了出身论或血统论的解释路径,推定两个出身“大人物”家庭的青年必然是“大人物”的倾向。出身论、血统论在概率统计的意义上当然是有很大道理的,但要用它作为一个单一规则来引导所有解释,无疑还需要辅助的证据。我们不清楚的是,两位与马基雅维利有长期交往的青年是在其人生的什么阶段碰到马基雅维利的,在马基雅维利将作品呈献给他们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他们父辈的政治倾向是什么?而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父辈的倾向保持一致?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现实中经常存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很多贫困白人可能因为宗教的原因而支持共和党而非民主党,但这一态度可能恰恰有违他们的经济利益;第二个例子是,在18世纪,卢梭多愁善感的文字竟能打动如此多的贵族,使他们也开始津津乐道“高贵的野蛮人”与所谓自然平等,但这种理论实际上与他们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这两个例子都超越了简单的出身论和血统论。 因此,麦考米克如果要夯实其解释前提,就需要作进一步的微观史(micro-history)研究,从一切可能的文本踪迹中重构两个青年人的形象,勾勒出其性格与政治倾向。这同样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如果能成功实施,我敢说可以贡献另一部微观史杰作;但这样同样超出了本书所能承载的重量。 下面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胡萝卜”和“大棒”的探讨。“胡萝卜”与“大棒”都是具体语境中的话语工具,但问题就在于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所表述的帝国观和自然观仅仅是针对两位青年人的话语工具,还是已经构成了马基雅维利自己比较牢固的基本信念? 要回答这一问题,比较便捷的切入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看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政治经验,其次是看马基雅维利在具有不同修辞对象的其他文本中是否表述过类似的观念。马基雅维利个人的生平与帝国扩张的政治经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佛罗伦萨本来就是一个有建立帝国野心的共和国,统治着若干附庸城市以及广阔的乡村地区。这位共和国前秘书厅秘书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将1494年因法国人入侵而失去的附庸城市比萨夺回佛罗伦萨人手里,并通过建立一支国民军,成功地逼迫比萨人臣服。马基雅维利大量关于雇佣军、援军和国民军的讨论,包括他的《用兵之道》,都与他重新征服比萨的政治经验密切相关。在他任职期间,他还探讨过如何处理附属城镇的叛乱问题。在一篇作于1503年秋天、题为“关于基亚纳谷地叛民的处理方式”的备忘录中,马基雅维利批评佛罗伦萨人在前一年对待阿雷佐的叛乱时,没有学习罗马人在征服其他共和国时摧毁其继续反抗的力量,而只是对阿雷佐人进行了羞辱,这必然会激起当地人更大的仇恨。在这里,他公开表示了对罗马人行事模式的欣赏(15);而《君主论》中关于如何统治新征服的领土,尤其是原来生活在共和制度下的领土的讨论,则进一步展开了对这一模式的详细阐述。 作为一个有帝国野心的共和国,佛罗伦萨又处于其他有帝国野心的列强的压迫之下。马基雅维利政治经历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和周边以及意大利地区之外的列强打交道。他出访过法国宫廷、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宫廷,与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贾近距离接触过,而这些都是一度威胁佛罗伦萨的势力。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必然性迫使一个国家扩张,放在当时的语境中非常容易理解,最大的必然性就是被大国吞并的压力。在邦国林立、列强环峙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并没有资本置身于霸权战争之外。这一认识集中体现为他对佛罗伦萨是否应在大国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讨论。在《君主论》第21章评论索德里尼政府在1512年的外交政策时,马基雅维利认为,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国家受到必然性的驱使,需要和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国家结盟,在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其中一方。中立政策只有对极其虚弱的国家才有意义,对佛罗伦萨这样试图追求伟大事物的共和国来说,只有旗帜鲜明,才能赢得真正的朋友。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15章中,他又对索德里尼政府在1499年法国与米兰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之间的争端中行动迟缓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6)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看起来不得罪别人,但实际上却会引起别人的猜忌,无法赢得真正的朋友。一个虚弱的国家,因为别人对其无所期待,当然也不会猜忌。但是,在列国争霸时代,一个虚弱国家的生存却会成为基本的问题。因此,必然性会迫使佛罗伦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力量。 麦考米克针对马基雅维利的罗马模式崇拜提出了若干质疑,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瑞士模式与雅典模式在他的写作中占据着一定地位,尤其是享有自由平等但又缺乏帝国扩张野心的瑞士模式,或许可以成为罗马模式的一种替代。然而,麦考米克只看到了马基雅维利对瑞士的赞许,却没有看到他在其他地方从帝国建构的角度对瑞士所提出的批评。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4章中,马基雅维利比较了帝国扩张的三种方式:一种是像古代托斯卡纳的小共和国那样结成联盟;一种是为自己寻求盟友,但同时保留在盟友中的霸权地位;第三种就是像斯巴达与雅典那样直接征服。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将瑞士作为联盟方式的当代代表。然而,他对托斯卡纳(伊特鲁利亚)联盟的批评却是非常严厉的,这个由12个城邦组成的联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意大利之外,最终将自己控制下的伦巴第丢给了高卢人。托斯卡纳联盟的问题就在于,一方面它决策非常缓慢,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获取新的领土会带来十分麻烦的内部分配问题,在高昂的商议成本的约束下,他们甚至丧失了对外扩张的欲望。因此,当他们的力量增长到可以自保的程度的时候,就既没有“必然性”的压力,也没有意愿让扩张的过程持续下去。他们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接纳保护国,收保护费,因为保护费比领土更容易在内部分配;另一件事情就是给别的城邦当雇佣军——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提到了瑞士。(17)因而,对托斯卡纳联盟的批评中,同时也隐含了马基雅维利对瑞士的批评。 当然,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4章的论述中,马基雅维利也写道:“如果对罗马人的仿效看来可能是困难的,那么对古代托斯卡纳人的仿效就不应该看来是如此,尤其是对于现代的托斯卡纳人来说更是如此。”(18)但这是否意味着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为托斯卡纳模式不是最佳的,但可能对当代佛罗伦萨来说是最现实的?恐怕也不是。须知在第1卷“前言”中,马基雅维利反复强调今人虽然口头上崇拜古人,却并不认真虚心地学习他们的治国之道。(19)“如果对罗马人的仿效看来可能是困难的”指的不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佛罗伦萨人去模仿罗马,而是佛罗伦萨人缺乏模仿罗马人的主观意愿。 抱有“平民主义”情怀的麦考米克也对直接民主的雅典表示了高度好感,并认为马基雅维利对雅典也抱有好感,证据是,马基雅维利在不少地方称许雅典的武力。然而,在《李维史论》第2卷第4章中,雅典是通过直接征服获取臣民的典范之一,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这样的征服是无效的,雅典人很快就失去了他们的征服成果。(20)这两个方面比他在字里行间偶尔闪现的对雅典的赞许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后者服务于更小的语境论证的需要,而这两个方面则关系到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框架。 至于马基雅维利对人世间事物变动不居、起伏不定的观念,可以说是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绝不仅仅是在《君主论》与《李维史论》中。在其长诗《论机运》中,马基雅维利描绘了一个多变与反复无常的机运女神形象,她转动着命运之轮,碾压着凡夫俗子:“而那些轮盘日夜不停地转着/因为老天愿意(谁也不能与它作对)/懒散和必然性围着它们盘绕。”必然性(necessità)从机运女神(fortuna(21))的轮盘的转动中呈现。没有人可以预测她的行踪,“因此就应该把她当成自己的明星/而且尽我们之所能,每时每刻/按它的千变万化使自己得到适应”。(22)这里所呼应的正是《君主论》第25章对fortuna的讨论:人应当改变自己的自然(natura),以做到与时俱进。适应fortuna的过程,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也就意味着要根据必然性行事。在长诗的后面,马基雅维利回顾了世界上各帝国兴衰更替的历史,从埃及兴起到罗马帝国的覆灭。没有人能够长久“获得她欢心”,即便是罗马帝国高贵而神圣的功业最终也分崩离析。然而,这并不是给帝国事业泼冷水,而是揭示,不管人们是否热爱这个事业,都会被迫加入其中。 当然,这首诗呈献的对象是焦万·巴蒂斯塔·索德里尼(Giovan Battista Soderini),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任领袖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侄子。也许在此麦考米克会要求运用对《李维史论》的解释规则:既然这位青年人也是“大人物”家庭出身,那么,马基雅维利献给他的诗歌也不应当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如果《李维史论》是“胡萝卜”为主的话,那么,这首诗里马基雅维利主要用的是“大棒”,用fortuna来威吓这位青年人走上他的道路。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因为马基雅维利交往的对象几乎都是当世的“大人物”,将麦考米克式解释规则运用于马基雅维利的所有文字,必然会带来“不可证伪”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它从本质上是一种信仰。 如果帝国的事业并非无关紧要,邦国亦无法自决是否从事扩张,那么,帝国建构就不能被完全归结为“大人物”的阴谋,在很多时候,它和整个共和国的共同利益紧密关联。此时,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马基雅维利对“大人物”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考虑《佛罗伦萨史》第3卷第1章中对贵族与平民关系的评论:平民拒绝与贵族分享权力,而贵族为了重新取得一部分权力,不得不在外表上装作平民的样子,在言谈举止、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要向平民看齐。其结果是,“贵族身上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宽宏气质也就丧失殆尽”。而如果与贵族分享权力,平民是可以从贵族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马基雅维利引用罗马的例子指出,“平民能够同贵族的领袖们一道参与官吏、军队与政权的管理,贵族的精神气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平民”;但由于拒绝贵族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佛罗伦萨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任何一位明智的立法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重组为任何形式的政府”。(23)这一结果比罗马贵族的堕落造成的结果要严重得多。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佛罗伦萨平民并不具备掌舵的能力。(24) 麦考米克在对《李维史论》的解释中,努力论证马基雅维利对平民政治能力的肯定。在我看来,麦考米克的论证确实证明平民具有成为自由守护者的能力,但胜任自由守护者并不一定意味着胜任国家的掌舵者。从罗马的历史来看,罗马平民是逐渐获得选举共和国高级官吏的权力的,这一渐进过程本身也是平民向贵族学习治国才能的过程。如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的,共同掌权使得“贵族的精神气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平民”。这个学习的过程,在麦考米克的分析中并没有获得呈现,更谈不上理论上的重视了。 更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探讨平民的政治能力的前提是,平民已经被整合到一个纪律严明、尊重法律的政治共同体之内。正如他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58章对君主与人民的比较中指出,“一个为所欲为的君主是个疯子,一个为所欲为的人民是不明智的”;而如果人民是受到法律约束的,那就可以表现出比君主更大的明智。(25)那么,平民又是如何被整合进政治共同体,并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 这里我们就触碰到一个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很少探讨的主题:宗教。麦考米克的著作只在三处用到“religion”(宗教)一词,倾向于将宗教视为“大人物”操纵平民的工具,并且暗示马基雅维利对贵族操纵手段的揭露,有助于平民摆脱这些操纵。然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难道宗教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消极的地位么?只要对比一下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论述,就可以看到他如何重视宗教对于统合政治共同体的意义。《李维史论》有云,宗教对于“派遣军队、集合平民、使人良善、使恶人感到羞愧”起到极大的作用,以致作者认为,罗马应该对立教的努马比对罗穆卢斯更为感恩,因为“在有宗教的地方,可以很容易地建立武力;而在有武力而没有宗教的地方,却要经历艰难的努力才能创立宗教”,努马所从事的使命要比罗穆卢斯更为艰难。但是,立教的结果是一连串的积极反应:宗教导致好的法律,好的法律产生好的运气,好的运气又产生事业的美满成功。(26) 当然,罗马人对宗教的利用是单向的,操纵者是贵族,平民始终是被引导者。宗教上的操纵用于防止平民向贵族夺权,以及在战争中鼓励士气。(27)如果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帝国事业持有非常积极的看法的话,没有理由认为他对贵族在战场上的操纵持完全消极的态度。贵族用宗教来阻止平民在城墙之外对执政官施加约束,最终也与帝国扩张事业相关——如果罗马城内平民对于贵族的制约关系被扩展到城外,那么在战斗中,平民可能会随时对他们的贵族指挥官发难,后者的权威就会发生动摇,这样就难以打造一支令行禁止的军队,从而推进帝国扩张的事业。 如果像麦考米克暗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要搞“启蒙”,把贵族操纵宗教的秘密公之于众,公民宗教必然很难发挥作用。这时候新的问题就会出来:用什么东西来凝聚人心,使平民服从法律与纪律呢?如果没有整合平民的手段,平民就会沦为一盘散沙,麦考米克所讨论的平民的德性与政治能力也就无从说起了。尽管有许多人将马基雅维利视为民族主义理论的源头之一,但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还很难想象19世纪民族主义的盛况,更难想象无所不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马基雅维利会为自己制造额外的问题吗?这似乎还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下结论的问题。 三、当代朝向:“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麦考米克式民主” 在我看来,麦考米克从“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中剔除帝国扩张追求,并将其归结为马基雅维利自己的意图,恐怕得不到足够的文本与情境支持。这种剔除可以说是麦考米克自己的理论创新。因此,有必要区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麦考米克式民主”。前者包含了帝国扩张的倾向,后者剔除了这一倾向;前者使得贵族与平民都成为帝国事业的利益相关方,二者既斗争又合作,在“混合政体”中相互平衡,而在后者的模型中,强调的是平民对贵族野心的制约。 马基雅维利既没有世界和平的设想,也不是什么“正义战争”理论家。他从政的时候服务于佛罗伦萨的帝国建构事业,他的写作也将共和主义与帝国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全面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需要一个被剥削和压迫的外部空间。“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所内涵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交织的逻辑,对于我们理解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欧洲列强正是通过对外扩张与殖民,才得以释放国内的社会压力,获得足够的资源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当下层阶级也成为帝国事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改善。英美两国都是这一政治逻辑的范例。英国的权贵们掌握的东印度公司在海外扩展英国的国家利益,大量失地失业的贫民被送往或者自行前往新大陆寻觅生计,大量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节省了英国本土的管治成本。于是,在19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选举权范围扩大,政治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阶级战争。英国的工人也被纳入贵族文化的领导权之下,流行于欧洲大陆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却处处碰壁,在这里,下层人士也乐于阅读莎士比亚。而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处于不停地向西扩张过程中,从18世纪到20世纪,美国经历了从领土型扩张向霸权型扩张的转变,当代美国的霸权体现在军事、货币、能源、粮食等各个方面,尤其是通过美元霸权,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由全世界承担滥发美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当上层阶级的野心与贪欲能在境外获得更大满足的时候,通过所谓“涓滴效应”,下层阶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益,从而成为帝国事业的利益相关方,并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一定的政治效能感。 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限度也就在于,它的良好运作需要将“做大蛋糕”的过程不断持续下去,当扩张丧失后劲的时候,这一模式就会造成很大的反弹。因为这时候精英既然不能制造增量,就会与平民来争夺既有的资源存量,压迫就会进一步加重。同样以美国为例,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下层阶级对权贵阶级所发出的抗议,尤其指向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克林顿时期的金融管制放松,而克林顿政府之所以放松金融管制,恰恰又是因为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做大蛋糕”缺乏后劲,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但金融自由化并没有真正推进美国在国外的利益扩张,金融业的虚假繁荣,反而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外流,等到金融泡沫一破灭,美国的平民就遭受惨重的损失,华尔街的高管们却照样可以领到天价的花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已经丧失了制造业第一大国与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遭到了欧元与人民币的冲击。一旦“做蛋糕”的进程停滞不前,债台高筑的美国开始削减政府开支,所谓“柿子捡软的捏”,首先会砍的就是与谈判能力最弱的平民相关的项目经费,而这会使得诸多社会矛盾加速爆发。 当麦考米克提出他的民主模式时,美国的全球扩张已经遭到重大挫折,进入一个收缩和调整期。在这一时期,与帝国扩张脱钩的“麦考米克式民主”的针对性就变得非常强了:无法在外部获得足够资源的精英们对下层阶级的压迫会更加明显,下层阶级也需要更多的手段来制约精英阶级。“麦考米克式民主”为下层阶级的斗争提供了新的制度想象:必须在现有的竞争性选举之外,获得更实质的对下层阶级利益的制度保障。但即便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奥巴马要推进全民医保这一政策都遭到美国上层阶级如此激烈的反对,如果要从政策层面的改革走向体制层面的改革,必将引起精英更为激烈的反弹。“麦考米克式民主”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 对于帝制中国而言,“马基雅维利式民主”原本是一个完全没有现实性的政治模式。中国早熟的国家很早就统治着辽阔的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要保有这些疆域本身就有很大的困难,进一步扩张已经丧失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逻辑更近似于斯巴达和威尼斯而非罗马,要求上层阶级节制欲望,同时也要求下层阶级服从上层阶级,这种服从后来又从科举制所提供的社会流动渠道中得到补偿。如果没有“克己复礼”,没有对欲望的节制,任由精英与平民的欲望横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收获的极有可能是战争与分裂。 然而,从19世纪开始,中国回归列国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仍身在其中。按照梁启超在《新民说》里的说法,中国所遭遇到的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而是具有强大内部动员能力的“民族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仅仅是若干外国君主和贵族,而是一个个虎视眈眈的民族。(28)因此,中国的政府必须具有远远超越帝制时代的动员能力,才有可能抵挡得住这种外部的压力。于是,威尼斯式或斯巴达式的共和国,因其避免动员下层社会,就不再适应这个时代。这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由皇帝和士绅所构成的传统政治秩序,或者康梁等立宪派曾经设想的由“中流阶级”(士绅)所领导的共和国,均告失败。兴起的是新式政党,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是“武装的先知”,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熔于一炉,将最基层的民众动员和武装起来。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平民革命,其激进程度远远超过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然而,随后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革命的平民主义传统与工业化驱动的官僚化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并以革命的平民主义传统的挫败而告终。 在中国新的ottimati或grandi势力日益增长之时,无论是“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还是“麦考米克式民主”,在中国都可以体现出比其在美国更大的针对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已经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国恐怕很难逃脱世界霸权更迭的政治逻辑。只有中国资本顺利扩张,持续“做大蛋糕”,国内的社会矛盾才可能避免过于激化,精英阶层才能感觉平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不至于威胁到自身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麦考米克式民主”内部包含的非选举的大众政治参与模式,在一党长期执政的体系下,恰恰可以对许多制度建构有启发。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熊彼特所界定的精英竞争的民主模式,而是希望政府治理能真正体现出对大众的回应性,那么就需要谨慎对待很容易被资本俘获的竞争性选举,同时探索其他增强政府回应性的制度手段。麦考米克提出的由抽签(而非选举)产生的平民代表对精英进行评价和制约的做法,非常值得引入当下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这可以大大加强执政党的“群众路线”。 对照以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麦考米克分析框架的另外一个薄弱之处。他提供的仍然只是对ottimati与popolo的静态分析模型,而没有为思考当代ottimati与popolo的生成机制提供理论框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分层和冲突都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要认清楚这个逻辑,就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的剖析。然而,麦考米克虽然表现出了“平民主义”倾向,但毕竟似乎在有意地避开马克思主义。氏著只有一处出现“资本主义”,而且是在“参考文献”部分所引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书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精英已经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所谓制约资本精英,也就需要一个全球的面向。如此,源于“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麦考米克模式”就很难避免和另一个马氏——马克思——发生关联。 四、结论 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是一本既深刻又片面的书,而且恰恰因为片面,才达到了深刻。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解释马基雅维利,麦考米克对选举民主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建构出一个有助于平民制约本国经济精英的政治控制力的制度模型,而这在全球多数国家都出现贫富分化加剧局面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认为马基雅维利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的原作者,则面临着许多文本解释上的困难。在我看来,麦考米克运用了过于简单的解释规则,将说服精英青年接受更为平民主义的政制作为马基雅维利写作《李维史论》的根本目的,而帝国建构仅仅是说服的话语工具。然而,这一解释低估了帝国建构在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未能展现出有德性的“大人物”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必要区分“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与“麦考米克式民主”,后者发展了前者,但不能与前者相等同。 无论是“马基雅维利式民主”,还是“麦考米克式民主”,在当代都具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和解释力。然而,为了理解当代ottimati/grandi与popolo的分化是如何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必不可少,而这是后来者可以在麦考米克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的探究。我们期待麦考米克所起的话头不断有人回应和接续,更期待中国的政治经验能在这种回应和接续中,为世界各国提供启迪。 注释: ①John P.McCormick,Machiavellian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以下随文注页码。 ②麦考米克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解释,至少可以追溯到以下论文:"Machiavellian Democracy:Controlling Elites with Ferocious Popu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2,2001,pp.297-314; "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 'Guicciardinian Moments'," Political Theory,Vol.31,No.5,2003,pp.615-643。(这两篇文章的中译文参见:《马基雅维里的民主》,陈华文译,《中大政治学评论》,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马基雅维里反对共和主义》,郑红译,应奇、刘训练编:《共和的黄昏》,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编者注) ③参见McCormick,"Machiavelli against Republicanism:On the Cambridge School's 'Guicciardinian Moments'"。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1页。 ⑤参见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⑥参见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在马基雅维利笔下,ottimati意为“显贵”,grandi意为“大人物”,意义基本相同,指向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并获得显赫社会与政治地位的阶层,其反面是平民(popolo)。下文直接用意大利原文,不一一交代。 ⑧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65页。 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247页。 ⑩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425页。 (11)麦考米克这一立场相比于巴龙与维罗里来说要温和得多,后两位学者居然认为马基雅维利最赞许的并不是罗马式的帝国主义,而是托斯卡纳式的共和国联盟。参见Hans Baron,"The Principe and the Puzzle of the Date of Chapter 26,"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21,1991,p.102; Baron,In Search of Florentine Civic Humanism:Essay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hought,2 Vo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Vol.Ⅱ,pp.148-150; Maurizio Viroli,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 State: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1250-16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62。 (1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66页。 (1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04页。 (14)参见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王永忠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11页。 (15)马基雅维利:《关于基亚纳谷地叛民的处理方式》("Del modo di trattare i popoli della Valdichiana ribellati," in Machiavelli,Opere,Vol.Ⅱ,Vivanti ed.,pp.22-26);中译文见《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交著作》,下卷,王永忠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901-902页。 (16)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69页。 (17)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34-336页。 (18)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37页。 (19)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42页。 (20)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34页。 (21)在罗马神话中,fortuna是一位女神,掌管着人世间财富、权力与荣耀等外物诸善的分配,其意图不可为凡人所猜度。作为神灵,fortuna有两个常见形象:一个形象是一手掌舵,一手握着象征着丰饶的羊角;另一个形象是转动所谓“命运之轮”,碾压过凡人的血肉。在马基雅维利的用法中,fortuna保留着其罗马神话背景,根据不同语境可被翻译成“命运”、“机运”或“好运”。下文直接用意大利原文,不一一交代。 (22)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全集·论机运》,徐卫翔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第297、299页。 (23)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第111-112页。 (24)当然,这些文字也许有修辞上的考虑,因为《佛罗伦萨史》是马基雅维利为梅迪奇家族所做的“课题”成果。然而,即便是在最亲平民的《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论证平民具有掌舵能力。 (25)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306页。 (26)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82-183页。 (27)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第188-193页。 (28)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