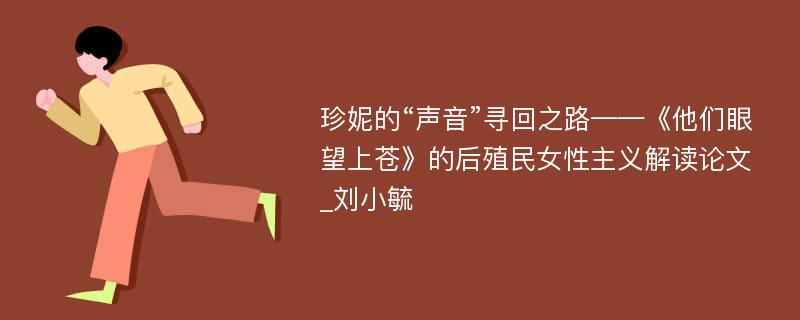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他们眼望上苍》是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小说通过黑白混血女主人公珍妮经历三次婚姻逐渐走向成熟过程的描述,反映了美国非裔女性被迫失去“声音”、丧失话语权等问题。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斯皮瓦克的“属下”观对小说主人公珍妮如何逐步打破种族、性别和经济地位的桎梏、并找回了“声音”进行分析,揭示了“合法婚姻”外衣之下黑人女性身份边缘化的事实,以期引发现代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属下;声音;斯皮瓦克;他们眼望上苍
一、引言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黑人女作家之一,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活跃分子。她毕生都在为保持黑人文化的传统而奋斗,发表了4部小说及50余篇短篇小说、戏剧和文章。其中,《他们眼望上苍》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写了主人公珍妮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黑人女孩经历三次婚姻后最终成长为自尊独立的女性。这部小说打破了传统的黑人女性卑贱形象的模式,生动展示了女主人公珍妮尝试挣脱性别与种族双重桎梏、寻回自我“声音”的一生坎坷之路,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黑人妇女的新形象。该作品没有对剑拔弩张的种族冲突以及黑人生活的悲惨和凄凉进行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叙述的方式以及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真实而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边缘化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现状。因此,《他们眼望上苍》被称作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最早描写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之一,也被《诺顿美国内人文选》列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在文献研究方面,国内外对该作品的分析涉及多个层面,其中包括女性主义角度、跨文化研究角度以及叙事语言角度等。近年来,一些评论家开始挖掘赫斯顿作品中所体现的后殖民思想。然而,身为非裔美国黑人女作家的赫斯顿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复杂情怀及难解之谜未能得以完全诊释,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主人公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发掘珍妮如何从被三重压迫的泥淖中一步步走向自尊与独立、唤醒黑人女性身份意识、解构“属下”身份、寻回“声音”。
二、后殖民女性主义和斯皮瓦克的“属下”观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促使第三世界的妇女开始觉醒。80年代以后,将代表西方学术界“少数话语”的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联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Feminist Criticism)发展起来,成为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产生了较强烈的冲击。至90年代,这种批评已极大地改变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面貌。后殖民女性主义是文学作品解读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它以探寻文化霸权的批判与非殖民出路为特征,关注种族、性别秩序下边缘化的“他者”身份[1],对殖民主义及性别歧视和把第三世界妇女建构为他者的事实进行揭露,探究作为女性的殖民主体所遭受的殖民压迫和性别歧视。
在这一领域,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 1942- )是最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斯皮瓦克与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共同被誉为的“后殖民三剑客”之一,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其论述包括“属下”不能发言、女性贱民主体、全球后殖民状况等不仅在文学、文化批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还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理论,使她成为了赛义德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2]54。由于她来自第三世界的身份背景,她通常将目光聚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关注那些沉默的、没有话语权或不能表达自己的群体,称之为“属下”(subaltern)群体。“属下”一词本源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使用的意大利语“subalterno”,译为英文的“从属”,用来指欧洲社会的从属或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3]100。斯皮瓦克在1988年发表了“属下能说话吗?”长篇论文,把“属下”这一术语的范围扩展到第三世界,所指由“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无组织的农民工,以及流浪街头或乡村的零散工人群落和团体”,到指在都市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此外,在这一“属下”阶层的内部,斯皮瓦克强调了女性的双重困境,即在经济和性别上都处于从属地位[3]101,是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在此基础上宏观来看,“属下”女性还陷于种族边缘化的泥淖,尤其是黑人女性还面临种族歧视问题,可以说黑人女性遭受着三重压迫,困难重重。
“属下能否说话”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话题,也是贯穿她书写生涯的一条主线[4]37。她通过对福柯和德勒兹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激进理论、以克里斯蒂瓦为代表的西方女权主义以及印度属下研究小组的批判,中得出结论——属下不能说话。因此,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斯皮瓦克则指出她们是“最底层的无产阶级”[5]52。由于缺少关注者与倾听者,黑人女性数百年来都处于理论话语的空白区域,成为了没有话语权的沉默者;或许即使发出了声音,也会由于没有倾听对象而无法产生意义,只有通过非属下的中介、其声音才有被听到的可能性。
三、珍妮的“声音”寻回之路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是一位黑人女性,经济地位从属,在小说设定的环境中处于无声的社会边缘地带,受到种族、性别、经济三重压迫、话语权被剥夺,属下特征明显。然而,在珍妮所叙述的成长过程及三段婚姻中,她逐渐觉醒并探索独立的道路,一步步从不能说话的“属下”逐渐找回自己的“声音”,走出三重压迫的泥淖,解构其“属下”阶层的身份。
在珍妮为好友费奥比开始回溯的最初,外祖母南妮的一席话就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调——种族、性别和经济地位的三重压迫的基调。她作为白人家庭的佣人,对外孙女珍妮说道:“白人是一切的主宰。……白人扔下担子叫黑人男人去挑,他挑了起来,因为不挑不行,可他不挑走,把担子交给了家里的女人。就我所知,黑女人在世界上是头骡子。”[6]18这是当时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的真实地位和现状,加之珍妮出身的经济地位,可谓四面楚歌,是边缘化的极端代表。
随着六岁那年珍妮在照片中发现一个黑人女孩站在了本该是她所站立的位置上,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肤色与其他白人孩子并不相同,开始感受到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开始产生焦虑。此外,根据约定俗成的“一滴血法则”,黑人的肤色即使看上去和白人一样,也会永远被排除在白人之外[7]21。此外,又因为她与众不同的肤色和更好的着装,珍妮又受到了学校里黑人孩子的孤立。至此,这些冲击不断提醒着她被边缘化的黑人身份的事实,也一步步为她意识的初步觉醒“声音”的寻回做好铺垫。珍妮的经济地位和黑人身份让她在这两个层面失去“声音”,而在她所述的三段婚姻里,她的“属下”身份使她有声音却不能发出,即便发出也无法被倾听。尤其在前两段婚姻生活中,在性别层面上,她只能“被从属”于她的丈夫,失去话语权,只剩沉默。然而,珍妮并没有就这样放弃抵抗这三重桎梏,而是一点点反省、一步步反抗,最终得以获得自由、独立,寻回了自己的“声音”。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1. 反抗身体压迫
在珍妮的种族意识尚且未被完全唤醒之时,祖母将她一把推向了另一个深渊——洛根·基利克斯,为她开始了性别意识觉醒埋下伏笔。珍妮的外祖母见证了她与珍妮的母亲两代人遭受三重压迫的苦难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她决定给珍妮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在珍妮十六岁时,外祖母将她嫁给了一位拥有着六十英亩土地的名叫洛根·基利克斯的人,她自此便成为了典型的男权社会“物物交换”婚姻模式的牺牲品。用年经美貌来换取物质保障的珍妮是作为“物”而存在的,此刻她是一个被物化了的“客体”。她的婚后生活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洛根·基利克斯是一个典型的守财奴,而且性情暴躁。他的眼睛里只有“玉米面团子”,没有精神世界的追求,“甚至从来不提美好的事物”[6]28。在他的眼里,珍妮只是“在白人的后院里出生和长大的”[6]36,是他让她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她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于他,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去生活。珍妮一旦不服从他,没有完成农场里任务,他就会对她进行身体和言语上的攻击。他把珍妮当成了一头干活的“骡子”。他认为男女应有各自的分工,女人应该负起自己在所谓“家庭”中的责任,甚至完全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可以说,在与洛根·基利克斯的这段婚姻中,珍妮的经济情况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因为那六十英亩的土地有所提升,但她的身体自由依然被牢牢压制,“声音”也淹没在洛根主宰的男权家庭中。
然而,在洛根如此的身体压迫和控制下下,珍妮并没有一味地忍受和顺从。她从结婚最初的怀疑、反感与忍让,直到在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乔·斯塔克斯仿佛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来到了她身边,那时的珍妮自然义无反顾地离开那个骡子一般的男人,逃出这令她无法喘息的身体压迫,走向幻想中的幸福。
2. 打破话语奴役
在珍妮与乔·斯塔克斯私奔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天真地以为找到了命之所至,却不知是走入了另一个深渊。最初,乔·斯塔克斯实现了他对珍妮的承诺,成了伊顿维尔这个黑人城里的权威人物——市长,而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市长夫人。乔迪按照白人世界的模式来塑造他的社会关系,理想中的男女关系再次体现了这一社区的男性霸权。尊贵的身份和丈夫的经济实力使得她拥有了较高的权力及地位,似乎改变了她第一次婚姻中“骡子”的地位。然而,这一身份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虽然可以掩盖但却改变不了珍妮再次被“边缘化”的事实。因为当她凌驾于其他黑人妇女之上时,却还是要听从于丈夫的摆布,无法拥有自己的“声音”。如当众人鼓掌邀请市长夫人讲话的时候,乔却打断了掌声,并声称“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娶她的。她是个女人,她的位置在家庭里。”[6]51这番话初次打破了珍妮对这段婚姻、话语自由的幻想和向往。
此后,珍妮成为他炫耀的工具并被逼迫做不喜欢做的事,且不能有任何怨言,只能看着自己的影子照料着商店,在店里必须要戴上头巾,不能把乌黑浓密的头发露出来,因为在他的观念中,珍妮归他所有,在店里只能让他看。此外,所有的事情都由乔·斯塔克斯来决定,珍妮没有丝毫自主权和发言权,她的声音被丈夫的“大嗓门”所吞噬。这次婚姻同样没能改变父权制社会男权统治的事实,在这场婚姻中珍妮依然没有摆脱成为“骡子”的命运。乔·斯塔克斯通过压制珍妮来确立自身的话语权,而珍妮面对这样的压迫,并没有退缩。她以退为进,忍让但不卑躬屈膝。最终,她当众用语言反击了乔迪,加之身体旧疾,使得乔迪终于一病不起。在乔的病床前,当乔心痛地抱怨珍妮当众嘲笑他是没有同情心的表现时,她最终爆发,点明问题所在:“这不是因为我没有同情心,我的同情心多得用不完,我根本从来没有机会来表示我的同情心,你从来也不让我表示。”[6]100这最后一击让乔迪在疾病和精神双重打几下撒手人寰,珍妮在第二段婚姻中打破了话语奴役,遇到了可以与她自由言语、行动的甜点心。
3. 追寻生命自由
在珍妮和她的第三任丈夫甜点心的结合使他完成了外表与内心的统一,有少女走向成熟,完成了性别意识觉醒。他们居住在大沼泽地,这块土地上的黑人们乐观地保持着鲜明的黑人文化。珍妮在追寻自我身份的旅途中从未背弃过黑人文化,而是把自己逐渐融入到黑人社区的生活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根,完成了种族意识觉醒。在展现种族身份的同时,为了追寻文化共性,珍妮也显示了自己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及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望。一方面,她热爱着丰富了她精神生活的黑人文化,另一方面,她还和巴哈曼的工人们交朋友,学习他们的舞蹈、尊重印第安文化,代表了作为黑人的珍妮愿意和不同文化和谐共存的心愿。在这块黑土地上,珍妮“可以听、可以笑、也可以讲话”,她逐渐摆脱了白人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摆脱了男性霸权的桎梏,终于获得黑人女性应该发出的、可以被聆听的“声音”。
小说最后,珍妮出于自卫被迫开枪打死得了狂犬病的甜点心。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珍妮拥有了与白人一样的与主流文化对话的权利,她的法庭陈词采用了标准英语的叙事模式。她终于认识到,女性不应该单单依赖婚姻、丈夫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发表观点或是找寻价值,而是要依靠自己的价值建构来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不在沉默,发出向着独立自由追寻的“声音”。
四、结语
在小说结尾,珍妮通过自身努力,终于在三段婚姻之后在打破三重压迫的道路上更进了一大步,使其属下特征相对削弱,并且最终寻回了自己的“声音”,掌握了作为黑人女性话语权,成为了黑人新女性的典范。
这部作品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赫斯顿的诸多思想及用意。她觉察到社会及家庭对弱势群体黑人女性自我认知的限制及对其地位的否定,在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中借鉴了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对身处三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在白人主流文化和父权制社会中重拾话语权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作品中的主人公珍妮被刻画成一位女性主义勇士,她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逐步成为一位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妇女;从一个沉默的客体变成一个有着自己声音的主体,最终从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回归了自我的主体身份。赫斯顿通过塑造珍妮这个人物表达了她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强烈诉求,即使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小的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石海军. 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许晓琴. 斯皮瓦克“属下”研究及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于性别和种族的双重视角[J]. 妇女研究论丛,2008(3):53-58.
[3]刘辉. 轮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0-104.
[4]陈永国. 从解构到翻译:斯皮瓦克的属下研究[J]. 外国文学,2005(5):37-43.
[5]管莎莎.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解读《土生子》[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2-60.
[6]佐拉·尼尔·赫斯顿. 他们眼望上苍[M]. 王家湘译. 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7]金花漫. 黑人·女人·人——《他们眼望上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身份”解读[J]. 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6(1):21-23.
论文作者:刘小毓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7/30
标签:珍妮论文; 黑人论文; 斯皮瓦克论文; 属下论文; 自己的论文; 女性论文; 声音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