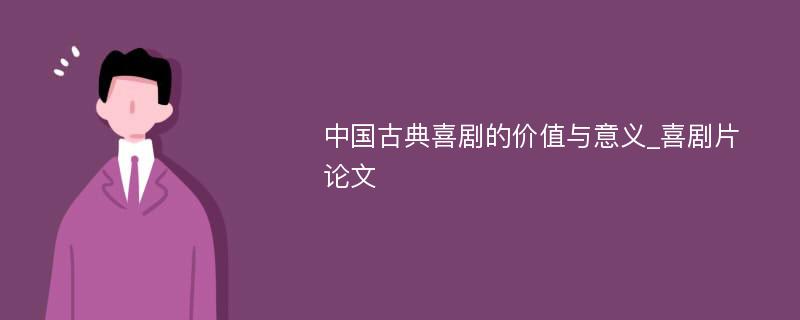
中国古典喜剧的价值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典论文,喜剧论文,意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古典喜剧数量之多、传统之悠久、地位之独特、成就之显著,构成了中国戏曲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古典喜剧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与独特的成就,而且体现了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的某些基本特质。中国戏剧的形成、生存与发展,都与喜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古典喜剧价值的认识与评价,实质上关系到我们对中国戏剧的整体认识与评价。以中国戏曲的独特生成过程与文化功能为视角,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中国古典喜剧的特点、价值与意义,或许可以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古典戏剧,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戏曲的某些本质性特征。
一
中国古代并无悲剧和喜剧的概念。用悲、喜剧分类的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戏曲,是从近代开始的。本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引进西方悲、喜剧观念,在新的视野上观照中国古代传统戏曲。
较早运用悲剧、喜剧观念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是中国近代戏曲学的奠基人王国维。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考》中率先将喜剧与悲剧同时并举,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尽管此时王国维对喜剧的认识远不如他对悲剧的看法丰赡、深刻和系统,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喜剧与悲剧这一对西方美学观念是同时进入王国维的理论视野的。而早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就曾对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普遍存在的“大团圆”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概括:“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显然,在接受西方审美观念的同时,他也沿袭西方学者推祟悲剧,轻视喜剧的传统。在王国维心目中,明清喜剧无非是搬演“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远不如悲剧崇高,因此,未能对喜剧的特点与审美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王国维几乎同时的另一位学者的观点,或许更能说明问题。1904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十七期上发表题为《中国之演剧界》的文章,引用日本评论界的观点,认为我国戏曲的最大缺憾是“无悲剧”。蒋氏认为:“要之,剧界佳作,皆为悲剧,无喜剧者。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其效之差殊如是矣。嗟乎!使演剧而果无益于人心,则某窃欲从墨子非乐之议。不然,而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悲剧为主。国剧刷新,非今日剧界所当从事哉。”蒋氏发现了中国古典戏曲中存在大量喜剧的事实,但其偏颇在于,他颠倒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夸大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因而得出了片面的结论。随后,1918年,胡适先生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则进一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指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公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在这之后, 鲁迅先生则在国民精神的范畴内,发表了更为一针见血的见解:“中国人的精神,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说出来;因为如果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国民性的问题。”(注: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存》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123页。)在当时,这些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近代学者的看法。
应该说,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是站在精英文化的角度,从文人传统出发,对古代戏曲小说的“大团圆”结局进行了抨击,这种抨击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强烈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即针对国民精神中的劣根性有感而发的。这种抨击,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唤醒民众,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评价其观点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它的特殊的语境。然而,也应该看到,当时他们论述的重点,不是艺术的、审美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精神的问题。尽管二者不无联系,但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同时,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所谓的“大团圆”,包括悲剧中的“光明的尾巴”或“欢乐的尾巴”都并不能等同于喜剧,也不是中国古典喜剧的唯一特征。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否定部分而否定整体(其实“部分”是否应该否定,也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可以说,历史曾经有过这样的机遇——作为重要的审美形态之一的喜剧观念,在本世纪初便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近代学者自身的局限,而未能把西方近代喜剧美学的精髓与民族喜剧美学的优良传统加以融会贯通、革新创造,因而也就失落了在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建构一种既富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的喜剧美学体系的机遇。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古典喜剧的成就曾经引起不少有识之士浓厚的兴趣,不少研究者都曾涉足其间。然而,由于客观的社会原因和主观上理论准备的不足及资料的限制,虽有散金碎玉之作时见报刊,但未能取得系统的、显著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出版及其《前言》的写作,则是运用西方美学观念,结合中国戏曲创作实际,解读中国古典喜剧的尝试。编选者们不仅为古代喜剧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并从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目安排等方面涉及了我国传统喜剧的一些本质特征,初步梳理了中国古典喜剧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问世,以及随后《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古典喜剧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古典喜剧的独特审美价值,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
二
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喜剧传统的国家。虽然中国自古并无喜剧的概念,戏曲的成熟也只是发生在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宋元时期,但其喜剧因素的萌芽,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先秦时期活跃在宫廷中的以“滑稽调笑”为主的俳优,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也是最早的喜剧演员。而秦汉时期在民间出现的角抵戏,则可视作中国较早的喜剧雏型。至于从南北朝到唐代的参军戏的产生,宋代滑稽戏的出现,其喜剧因素的丰富与喜剧意识的明确,则更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第一代职业演员是喜剧演员,最早的戏剧形态是喜剧,最古老的戏剧传统是喜剧传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喜剧是中国戏剧的先祖。正因为戏曲与喜剧具有一种先天的血缘关系,喜剧传统便成为戏曲中一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传统,一种最普遍和最常见的现象。喜剧不仅受到普遍的欢迎,而且在悲剧中也少不了插科打诨等喜剧性的因素。喜剧传统的悠久与深厚成为中国古典戏曲的显著特征。
与喜剧传统的悠久与深厚相联系的,是中国古典喜剧的独特地位。和西方传统的悲剧地位远远高于喜剧,并被视为“最崇高的艺术形式”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喜剧不仅与悲剧受到同样的重视,“摹欢则令人神荡,写怨则令人断肠”成为优秀戏剧作品的共同标准,而且还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最能体现喜剧的特殊地位和国人对喜剧的浓厚兴趣的,是丑角在剧团中的引人注目和备受尊重的情形。如前所述,中国戏曲中最早的喜剧因素、最初的喜剧形态,是通过宫廷俳优以“丑”的方式出现的。丑角并不能等同于喜剧,但却鲜明集中地体现了喜剧性的特征。丑角是戏曲中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特殊人物,也是戏曲舞台上备受欢迎的角色。中国戏曲界历来有尊重丑角的传统,俗语说:“无丑不成戏”。这种传统,在旧时的戏班中尤为突出。由于“丑”地位的特殊,历代戏曲理论专著及记载戏曲活动的笔记也有不少有关丑角的记录。《史记、滑稽列传》是最早为“丑”(滑稽者)立传的文字。此后的不少史书都有关于滑稽者的记载。而历代笔记中有关“丑角”艺人的记载则更为丰富多彩。应该说,丑角备受尊重,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丑角是戏曲中最能制造喜剧效果的特殊人物,观念对丑角的喜爱,表现的正是对喜剧的喜爱。而“丑角在戏班子中的特殊地位则形象地反映了喜剧在我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注: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本,第273页。)。
不仅如此,在一些特殊的喜庆的场合,喜剧常常成为不可缺少的节目,没有了喜剧,便没有了吉祥欢乐的气氛。清代词人陈维崧曾写过一首《贺新郎》词,其小序中说,赴宴坐首席最苦,因首席要点戏。他和杜于皇都有曾因点错了戏而受窘。杜于皇曾见戏单上有“寿春图”,名甚吉祥,于是点了这个戏,“不知其斩杀到底”,结果是“终座不安”。陈自己曾点《寿荣华》,“不知其哭泣到底”,结果是“满堂不乐”。陈维崧因此在词中写道:“欢场百戏鱼龙吼,却何来败人意兴,难开笑口”(注:陈维崧《贺新郎·自嘲,用赠苏昆生韵,同杜于皇赋》,陈乃乾辑《清名家词》第2卷,上海书店印行,引自开明书店1937 年复印本,第493页。)。由此可见,悲剧在不少场合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直到清末,北京戏班的海报,除了写出本班角色姓名外,下面还要写四个字“吉祥新戏”。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对待悲剧演员的评价。著名演员谭鑫培因善唱悲剧而闻名,但沈太侔《宣南零梦录》记谈小莲语,则云:
观谭伶之面,枯如人腊,瘦若僵尸;聆谭之声,幽咽苍凉,如鸿嗷,如鹤唳。试与孙菊仙黄钟大吕相较,谭调实商角也。亡国之音,哀甚。(注:转引自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804页。)
这里,虽然所表达的是对演员个人的评价,实则代表了国人对悲剧的一种普遍态度。虽然在戏曲发展的历程中,也曾有人提出过戏曲创作“乐人易,动人难”的独到见解,然而,在中国,在实际生活中,喜剧的流行程度和影响程度都远远超过悲剧。
中国古典喜剧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与独特的地位,而且还有鲜明的特色与显著的成就。在古代西方,喜剧一般只用于讽刺。亚里斯多德《诗学》第二章指出:“喜剧总是摹仿比今天的人坏的人。”古希腊佚名《喜剧提纲》则说:“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传统的喜剧观念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才部分地打破这一束缚。而在中国,喜剧传统中不仅有讽刺,也有歌颂。歌颂喜剧的发达,成为中国古典喜剧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元杂剧时代,表现得最为充分。“元代四大爱情剧”《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中的前三个剧本,都是喜剧,《西厢记》更是“天下夺魁”,成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不仅写出了“感天动地”的悲剧《窦娥冤》,也有优秀的喜剧作品《救风尘》、《望江亭》传世。元杂剧中歌颂喜剧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成就之卓越,都为后世所望尘莫及。至明清两代,歌颂喜剧虽不如元代繁荣,但仍连绵不断,各有佳作。至清代地方戏兴起之后,歌颂喜剧再次得到了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如《穆柯寨》、《杨排风》之类的优秀的英雄喜剧。歌颂喜剧是幸运者的典型,在这类喜剧中,喜剧主角凭借他的机智、勇敢、幽默,面对不幸,战胜不幸,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为了命运的幸运者。在这类作品中,喜剧主人公常常代表了生命,代表了意志,代表了智慧。因而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
简而言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喜剧传统的文明古国,喜剧在人们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喜剧艺术有着独特的成就。喜剧的发达亦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显著特征。
三
如前所述,喜剧的发达是中国戏曲的显著特征。然而,对于这一具体特征的评价,研究者们则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词,毁誉参半。在古典喜剧的研究中,对中国古典喜剧价值与意义的判断,关系到喜剧地位的定位与喜剧的发展命运,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焦点问题。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他们物态化的结晶,是一种民族的智慧。”(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 中国古典喜剧正是一种“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一种民族的智慧”,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产物。曾经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乐感文化”,“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都不能否认,乐观自信的乐天色彩,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乐”是《论语》中孔子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述而》)在孔子的心目中,“乐”不仅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小惧。”(《子罕》)“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这种中国文化的乐观自信色彩,应该说是植根于远古先民的古老而质朴的信念:“物不可以终难。”,(《周易·序卦传》)从远古的时候开始,人们便始终相信,没有不可克服的灾难,也没有无法变易的忧患。“生生不息”是大自然永恒的规律。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的基因,奠定了中国古典喜剧的哲学基础。
在传统文化的基因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古典喜剧,则以其自身的艺术方式集中地体现了乐观自信,以柔克刚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这方面,《西厢记》题材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从元稹的《莺莺传》“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到王实甫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西厢记》喜剧,对真实的生活事件的描写并无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创作主体的态度。正是创作主体的态度,决定了作品的不同主题和结局。王实甫和他的前辈董解元,对真挚爱情的肯定判断,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具有了幽默机智的色彩,取得了弱者对强者的胜利,获得了幸运的结局。剧本浓厚的喜剧气氛,所表现的正是建立在对真挚爱情肯定判断基础上的乐观与自信。这种乐观与自信,“不是廉价的感情宣泄,而是民族精神和历史经验在审美形态中的表现。”(注:郭汉城《写在〈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前面》,《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156页。)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从悲剧演变为喜剧,《西厢记》并不是唯一的特例,但却是最为成功的例子。喜剧并非一定浅薄,悲剧亦非一定深刻。由此亦可见一斑。至于其他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在对结局的处理上,则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和相似的模式。这并不奇怪,因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8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典喜剧表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它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开阔的视野。
除了上述认识价值之外,中国古典喜剧还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首先体现在中国古典喜剧的平民性上。喜剧来自民间,而且从来就是一种平民性的艺术。喜剧所描写的内容,往往人皆凡人,事皆小事,不硬充高雅,也不故作深沉。选择民间视角观照生活,运用民间话语表达平民心态,天然的平民性决定了喜剧的通俗性。曾经创作了大量喜剧作品的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就曾明确提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演习部·选剧第一》)并具体指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与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词曲部·词采第二·忌填塞》)正是这种“贵浅显”的平民色彩,加上轻松欢快的节奏,使喜剧具有了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吸引力,满足了大众的审美要求,因而具有了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
其次,中国古典喜剧的审美价值还在于它的娱乐性。如前所述,戏剧是一种全民性的大众娱乐方式,平民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居住分散,终年劳作,只有在节日才能聚在一起看戏娱乐。娱乐是节日的主要功能,而戏剧,尤其是喜剧,是节日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因而喜剧必须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表现出明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常常将题材的趣味性、情节的巧妙性、手法的夸张性、风格的幽默性、表演的技艺性有机地融为一体,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因而具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价值。
最后,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生命的节奏感是古典喜剧最重要的审美价值。中国人十分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上》)悲欢离合,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在生命的过程中,“喜剧表现了自我保护的生命力的节奏,悲剧则表现了自我完结的生命力节奏。”(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喜剧不是以对生活的真实性描写取胜, 而是以对情感的真实描写取胜。喜剧精神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如果说悲剧是一种描写意志的艺术,那么喜剧则是一种描写智慧的艺术。在中国古典喜剧中尤其如此。无论是关汉卿笔下的赵盼儿、谭记儿,王实甫笔下的红娘、莺莺、张生,还是《陈州粜米》中的包公,或者是《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中的唐成,也无论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人生遭遇和强大对手,最终他们都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历尽坎坷,化险为夷,幸免于难。他们不屈不挠地为自己开辟了生存之路。喜剧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的节奏,从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和魅力。
世界是多元的,人类的审美需要也是多方面的。真正的艺术只有审美价值的不同,而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从审美效应来看,“美好事物的毁灭能产生崇高的美,美好理想的实现,同样也能产生另一种崇高的美——力量的美,意志的美,激发鼓舞与兴奋。各种审美范畴、审美效应,在人的审美活动过程中,也处于辩证状态,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非各自孤立绝对排斥。”(注:郭汉城《写在〈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前面》,《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第156页。)任何过分强调和夸大喜剧作用的观点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任何否定或贬低喜剧价值的观点也是无视事实的。没有万能的艺术,喜剧也不是万能的,但却是不可替代的。
四
从本质上说,喜剧的价值与魅力来自人们自身的审美需要。“喜剧在各个时代里,都是文明民族所喜爱的娱乐”。(注:哥尔多尼《回忆录》第一部第四十章,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57页。)在中国古代, 虽然并无关于喜剧的系统论述,但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乐”与“乐”(le)的独特的微妙作用,“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矣。”(《荀子·乐论》)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人之在世,“浮生常恨欢娱少”,需要“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此圣人之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注:(元)胡祗谲《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三怡堂丛书本。)给沉重的生活增添几分色彩,为辛劳的百姓带来几分欢乐,适应人类的生存需要,诞生了最初的艺术,也诞生了最早的喜剧。喜剧的性质,亦如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所言:“喜剧是一种艺术形式,凡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欢庆的时候,比如庆祝春天的节日、胜利、祝寿、结婚或团体庆典等等,自然而然的要演出喜剧。因为它表达了生生不已的大自然的基本气质和变化,表达了人类性格中仍然留存着的动物性的冲动,表达了人从其特有的使其成为造物主宰的精神禀赋中所得到的欢快。人类生命力的形象令人吃惊地包含在意外巧合的世界之中。”(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可以说,以充满生机的欢快节奏表现人类的生命感受,是喜剧成为“文明民族所喜爱的娱乐”的主要原因。
中国深厚的喜剧传统,国人对喜剧的情有独钟,则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和更为深刻的原因。首先,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戏曲,与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安土乐天、安居乐业观念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乐则安,安则久”,(《礼记·乐记》)“安”与“乐”密切相关。因此,其艺术精神是以宁静与和谐为基本特征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儒家传统的美学原则,“至善至美”是其最高审美境界。所以,中国戏曲没有建立起西方悲剧那种恐怖与崇高的概念,不注重对哲学命题的穷究,而着重追求生理上与心理上的愉悦,着重发挥戏剧的抒情与观赏的功能,着重培养“善”的伦理感情。喜剧地位的独特与创作的繁荣,以及歌颂喜剧的大量涌现,都是这种传统的民族心理的具体体现。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传统的差异,不仅是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亦是其自身鲜明特色所在。无视这种差异,忽视自身的特点,便无法正确认识中国古典喜剧。
其次,与中国古典喜剧传统密切相关的是中国戏剧深厚的民间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国戏剧的民间传统决定了中国古典喜剧的传统,中国古典喜剧充分体现了中国戏曲民间性的基本特征。在西方,戏剧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是由官方倡导的,是主流文化中的一种。所以,作为西方戏剧起源的古希腊戏剧从一开始就有作品传世。可以说,西方戏剧传统主要是一种文人传统,一种纯文学传统。西方悲剧的发达与悲剧理论的繁荣,正是这种文人传统与纯文学传统的产物。而喜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则是渊源于民间的戏剧传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四章中指出:喜剧是从低等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而来的。因而喜剧历来不被古代的西方文人所重视,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喜剧传统作为民间传统只能以隐性的形式发展。在中国,尽管民间传统并不是中国戏曲的唯一传统,但却是其最主要、最重要的传统。无论是元杂剧还是南戏,不仅艺术的渊源来自民间,而且其独特的演出方式与戏班组织和主要欣赏对象,都是来自于民间。在中国,戏剧演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商业行为。艺人到勾栏瓦舍演出,称为“卖艺”,观众到剧场买票看戏,是花钱买“乐”。因此,民间戏曲传统便更多地表现为喜剧传统。观众的趣味和爱好制约并影响着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而为平民百姓制造欢乐,消愁破闷,便成为戏剧的主要功能之一。清代著名戏剧理论家李渔曾云:“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李渔的话从一个侧面形象地说明了大众的审美需要对剧作家的深刻影响。在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中,戏曲的民间传统决定了其深厚的喜剧传统,而喜剧传统一经形成之后,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戏曲整体的发展轨迹。
此外,中国深厚的喜剧传统,还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古代,戏曲是一项全民性的娱乐,人们对戏曲的热情,就像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热情一样。“中国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婚丧嫁娶,最重要的节日庆典,都与中国传统戏剧的演出不可分割。它表现的是一种对生存幸福的祈求,是种族生存与发展的本能文化需求。”(注:吕新雨《戏剧传统的命运》,《读书》,1998年第8期,第143页。)戏曲表演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仪式,一种与普通人自身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仪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角色,戏曲其实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它既能满足对于艺术的审美愉悦,也能实现一种文化的参与共融的要求。而喜剧的喜庆色彩,作为吉祥和幸福的象征,正因为表现了一种生存幸福的祈求,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期望与寄托,便特别得到人们的青睐。可以说,中国古代戏曲的演出方式与民族的生存方式的水乳交融,为喜剧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足够的契机,使之成为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曾将艺术反映生活的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对现实有如火上加油”,一种是反省性的反映,“则有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第7页。)以综合性表演艺术为其显著特征的中国古典喜剧,和以庄学、玄学为基础的中国画的审美特征十分相似,二者均恰似“一杯清凉的饮料”。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由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带来了大量以精神紧张为特征的现代病。而中国古典喜剧传统,对于缓解现代人的心理压力,解除生命的疲困,将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即将来到的新世纪中,现代心态与古典模式的互补与共存,具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现代生活为喜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新的空间,古老的中国喜剧艺术必将在人们对传统的认同与重构中获得新生,重新闪耀出东方文化的异彩。
标签:喜剧片论文; 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西厢记论文; 丑角论文; 团圆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