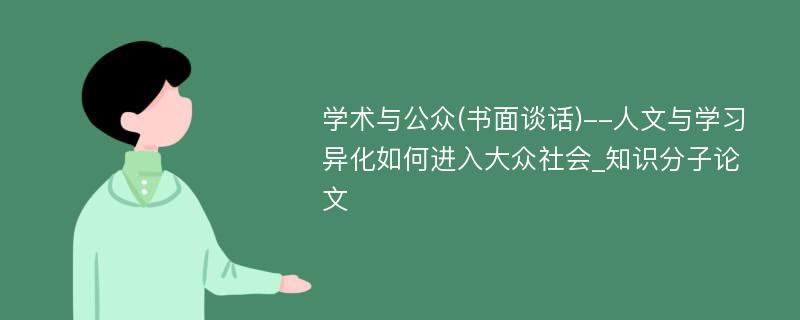
学术与大众(笔谈)——人文学术为何疏离又怎样进入大众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学术论文,笔谈论文,人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4-0014-03
一、人文学术疏离大众社会的问题
从各种媒体对易中天、于丹以及余秋雨等“明星学术”的喋喋不休中,我得知他们如何一举成名,拥有多少“粉丝”,也得知他们不慎之中出错几许,还得知他们怎样“卑躬屈膝”地媚俗与迎合主流,而我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恰恰不得而知:他们拥有那么多电视观众和畅销读者,并引发各种争议的深层问题是什么?
由于上述提及的这些“学术明星”都是人文知识分子,加之他们所讲述的又多是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传统经典,因此有人认为,“明星学术”映射出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虚空的问题。具体地说,主流话语无法化解因市场经济的震荡而引发的各种思想情感的焦虑,而契合市场经济的现代思想文化观念体系又不曾确立,因此“学术明星”试图以传统文化填补主流话语失范而遗留的价值真空。这种分析固然不错,然而从十几年前知识精英的“人文精神”讨论,到最近的主流话语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表明这个重大问题已经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何况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是否具有维系道德精神的文化功能值得怀疑,因而无须赘述。
我倒认为,“明星学术”这一文化现象,突显了我们这个年代学术疏离大众和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分离的问题。“学术明星”拥有数以万计的电视观众与畅销读者,表明大众社会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据报道,《于丹〈论语〉心得》发行近400万册)[1];而由媒体推动的一波又一波关于“明星学术”的讨论,则意味着社会对于学术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说到底,它们不过是学术疏离大众和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分离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当然,我这里主要论及人文学术,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当前我国投身科普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大众科普读物也是少之又少,而且往往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不爱看[2]。知识精英远离公众视野,以致很多年轻人对歌星、影星、球星的“奇闻轶事”倒背如流、如数家珍,而对那些著名学者却一无所知。
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媒体文章已经触及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可是它们要么点到为止轻易绕过;要么在问题表层的平面上绕圈子,无力深入。也许,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媒体缺乏由学术底蕴支撑的学理穿透力。其实早在“明星学术”文化现象出现之前,学术疏离大众和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分离的问题,就已经通过种种迹象曲折地表现出来。先是部分流行歌曲的歌词和精彩广告充斥日常生活,成为大众话语的基本语法;后是各种类型的“段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调味品。这些轻盈的抚摸与解构的反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出大众社会复杂的心理症状:社会变动不居造成的身心疲惫,现实无情引发的感伤与无奈,社会不公引起的激愤和自嘲,价值多元的不适带来的人格分离,精神价值的匮乏引致的心灵诉求,还有欲望解放导致的欲望焦虑,等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这些流行歌曲或者“段子”:思想不够正确,情感过于褊狭,说法不够贴切,情趣比较低下。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它们立足现实,关注大众生活并且迅速表现。问题在于,它们只能停留在症状的表现上,而不能洞穿其症结,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当代学术文化的缺席,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缺席。
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知识分子,近些年来悄悄从社会文化的聚光灯下黯然退出。这一方面显示出社会的进步:公共性批判越来越理性化、专业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
二、人文知识分子为何离大众越来越远
我想,任何一位具有现代意识与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会认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因此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着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是非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尽可能地践行,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理论,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应如何顺应新时代公共领域的专业化趋势,以此保持与大众社会的密切关系。
为什么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大众社会分离?我认为这里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从社会历史方面讲,“空间”有限则很难“公共”。尽管当代社会在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方面有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且市场经济与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也为实现这种自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有勇气承认,迄今为止作为体制化的公共空间在我国社会还是相当有限的。一般而论,公共空间是指知识分子就涉及社会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参与并进行平等、理性探讨的地带,也是知识分子依据理性、以普遍道德法则的名义向社会传播思想文化的场所。它是群体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现实条件。没有一个可以自由发出纯粹理性和道德声音的实质性公共空间,则很难形成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功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然而,就连最早提出公共空间概念的哈贝马斯也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在法律保障下独立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的领域,因此它的形成必须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宪政国家的建立。据此,在现代中国建构一个健全的公共空间,显然需要一个难以测定的漫长历史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历史现实。然而尽管如此,当代知识分子也不能以此视为无所作为的理由,诚如艾略特所说:“一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旷日持久,而且需要几代人都予以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成为人们推迟研究该问题的正当理由。……情况最终会证明,是我们所推迟解决或忽略不管的问题,而不是尽了力却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反过来使我们遭殃。”[3]
从知识分子本身看,问题则比较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文知识分子纷纷祛除思想激情,将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实投向学术研究,一时学理之风遍被学林。对于这种学术转向,应该从两个方面分析。从积极的方面讲,缺乏专业化的理性“知识”也很难“公共”。这种学术转向固然是一种被动的文化行为,但却无意之中契合了人文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国人文学科长期以来一直寄生在庞大而统一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评开始,“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韦勒克语)盛行,学术文化遭受政治文化的强行侵入与蚕食,而“文革”期间学术领域名存实亡。新时期文学是在主流话语内部萌发的,同样具有显豁的思想倾向性,因为它原本是精神教化的虚假性走向极致的结果。也正是因为新时期文学一方面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另一方面学术机制依然保持着一体化形态,所以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仍旧依附于主流话语。他们常常把关注大众社会的道德勇气作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公共”的重要标志,而忽视其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讲,20世纪80年代人文学术从动辄得咎到难以为继,其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
在有限的“公共空间”无畏地直面大众社会,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仅仅停留在道德勇气与问题意识上,而缺乏专业化的道德批判和建设性的理性精神,显然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学术转向之后,一大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逐渐从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剥离出来,在传统学术与外来学理的话语习得中,建构起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使他们在人文学科背景下表达生活经验。尽管知识分子空间因缺乏同一性而分化成各种文化立场的学术话语,但它毕竟有助于形成相对独立于权威性主流话语、并可为人文学科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的自足的学术体系。
从消极的方面讲,人文学科过于学术化而容易导致僵化现象,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精英把自己凌驾于大众之上,逐渐形成独断的、自我宣传和自我保护的精英团体;二是鄙薄学院墙外的现实,以致离群索居和自我陶醉;三是把前人和权威的话语作为知识大厦的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又出现两个新的问题:一是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知识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导致一些具有学院特质的学术弊端重新显现。学院学术原本注重学术规则和美学标准,讲求研究的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于是有的理论研究囿于形式规范而脱离生动的社会现实,蜕变为单纯的专业操作,以致原本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文学科一旦进入专业化知识工场,便形同丧失灵魂的生物标本。二是在学院体制化过程中开始遭遇“科学管理”的威胁。新世纪的曙光似乎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千禧年”运动,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办学规模迅速膨胀。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因扩招过度而导致的教学质量的滑坡,制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管理制度,而所有的制度均体现为量化的形式。于是支撑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的良知和学理,在工具理性的精确换算中扭曲变形;学术流水线上不断涌现毫无创造意义的学术赝品。学院体制化的结果,不仅阻碍了学术的自由选择和创新,而且导致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分离和学术疏离大众。
三、学术进入大众的方式
在谈论学术如何进入大众社会的问题时,我认为,首先是知识精英必须贴近大众社会,真正了解大众社会的需求和发现大众社会的问题,并像萨义德所说,根据公平与正义的普遍原则为公众并且向公众发言,勇敢地批评所有违反这些原则的行为[4]。
在知识精英与大众社会问题上,新中国有过行政动员的经验,即采用行政的手段将知识精英驱赶到基层社会,强行规定“三同”政策(同吃、同住、同劳动)。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倒是贴近大众社会,社会分层问题也不突出。但是,体制社会赋予他们溶入大众社会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他们将同一性的主流话语灌输给大众社会;另一方面是以民间的疾苦感召他们,让他们内化主流话语。这种行政动员的方式,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显然不适用。且不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是否合理,就是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关系也只能是对话式的,而且即使是知识分子话语本身也不可能是同一性的。
其实,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高考体制,决定了绝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自大众社会,他们对于大众社会并不陌生,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层加剧,知识职业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程度进一步加剧。这样导致知识精英对于学院墙外的现实问题和大众社会的诉求越来越淡漠,回避现实生活冲突的犬儒倾向也越来越显豁。因此知识分子必须聆听大众社会的吁请,坚执公平与正义的普世价值的使命感,敢于依据理性抵御现实的各种压力和诱惑,发出独立的声音。否则任何关于学术与大众的问题都将失去实质性的意义。
至于学术如何进入大众社会,我主张两种传播方式:一是兼职的传播方式。尽管当代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电子媒体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甚至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学术明星”现象表明,无论是大师还是教授,只要具有社会道义的使命感,关注现实和倾听大众社会诉求,具有将深奥的学术理论通俗化并能通畅表达的能力,都应走出高雅的学院,通过各种媒体与大众社会对话,一道回应来自现实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征兆。
二是对话的方式。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曾使他们强烈地执著于理想,并怀有对大众进行思想改造的使命,以立法者的姿态俯视芸芸众生。但现代社会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自信,因为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而且在根本上向着未来无限开放的进程。在这个不知结局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成了阐释者。[6]我们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由不同个人、不同团体和不同阶层构成,在诸多问题上他们各自具有赋予自己的言说以正当性的权利,也各自具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性标准,多种的参照体系决定了平等对话的方式。而且,只有在公共话语空间内相互对话和理解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不同的人所看到东西的共性。
对话的方式之所以具有现代特质,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观性和内在性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和发达,个人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在一个各种意义都烟消云散的世界里”,对话和沟通是我们能够依赖的极少几种意义的可靠源泉之一。我们需要很好地运用相互对话和理解的机会,塑造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与自己的生活方式。[7]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论文; 社会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知识精英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