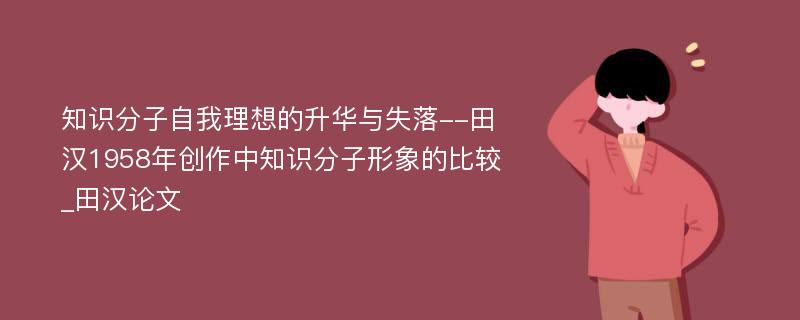
知识分子自我理想的高扬与失落——田汉1958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形象论文,自我论文,理想论文,田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8年,正是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大跃进”热潮的时候。这一年的3月初 ,荒疏于话剧创作多年的田汉在一次文艺创作“大跃进”座谈会上提出了今年要写十部 剧作的“跃进规划”。当然,田汉没有完成他的十部规划。但在这一年他前后完成了两 部大戏:《关汉卿》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两个作品在完成之后都引起了巨大反 响,为田汉赢得广泛赞誉。今天看来,显然,同年创作的这两个作品艺术成就落差极大 ,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已被公认是田汉创作的高峰,田汉“正是在《关汉卿》中找到自 我”,“缺了《关汉卿》,田汉就成了一块无光之玉,一条无睛之龙”。(注:董健: 《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818页。)后者是一部时事报导剧, 是纯粹应景趋时之作,是生产大跃进在创作上的狂热表现形成的败笔。剖析前者成功与 后者失败的原因,并总结出艺术创作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文章已有不少。本文试图比较两 个作品对知识分子形象截然相反的塑造与描写,进而分析创作主体田汉内心深层的知识 分子情怀,探讨他在历史剧《关汉卿》中回归自我,又即而迷失于描写现实生活的《十 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历史与个人的原因。
《关汉卿》一剧塑造了距今七百多年的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捶不 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碗豆”的艺术形象。田汉并不是要用戏剧为人物立传,而 是“决定把情节集中在关汉卿以怎样的动机和从哪里得到力量来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 》一点”(注:田汉:《田汉文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1、3 75页。)。这动机和力量除了目睹朱小兰被诬杀与朱帘秀的鼓励及舍命协助之外,主要 源于关汉卿的精神,即“敢爱、敢恨、敢骂、敢争、敢还手的反抗精神,那种‘玉可碎 而不可去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强烈的是非之心和正义 感,一生‘为民请命’的精神”(注: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 版,第791-818页。)。众所周知,关汉卿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优秀动人的杂剧作品,是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则如凤毛麟角。这是田汉在创作中一度遇到的难 题,但这个难题与缺憾又马上为秉持着浪漫主义气质的田汉提供了自由创造的巨大空间 ,正是在高度虚构的情节框架下,关汉卿的“知识分子英雄形象”被坚固地树立了起来 。
离开写作《关汉卿》的北京远郊西山古庙回城,田汉接着便三下首都西北郊区的十三 陵水库工地劳动、采访。他被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和“新的”精神 面貌所鼓舞,很想有作品来“记录这个工程,来描写这个伟大的交响乐”。后与金山“ 恢复以前在上海搞救亡戏剧的战斗作风”(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田汉专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写一页,排一页,6月1日动笔,9日完稿。 这就是《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创作过程。
和《关汉卿》一样,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田汉也用浪漫主义之笔描写了英雄 形象,而且,这一次他描写的不是一两位或三五位英雄,而是英雄群像,是数以万计的 英雄群像。这种对巨大场面中大量人物的浮光掠影的描写使得我们无法用“塑造艺术形 象”来评说作品,这实在不是对形象的精工细琢的“塑造”,甚至也称不上“描写”, 也许用“扫描”一词更为贴切。
当然,造成《关汉卿》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的英雄描写异质的主要原因不在作品 中英雄数量的悬殊,最重要的在于《关汉卿》塑造的是知识分子英雄形象,而《十三陵 水库畅想曲》歌颂的是劳动者英雄,或者说是工农兵英雄,知识分子在《十三陵水库畅 想曲》中恰恰成为需要改造的反面人物。在田汉笔下,可敬可爱的英雄是那些干劲冲天 (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甚至一连36小时不下火线)、无私忘我(心中只有党,没有个人, 没有“不愉快”)的工、农、兵。而以知识分子为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则受到 了强烈抨击和嘲弄。正如剧中一位“老红军出身的作家”针对一位教授所说的:“在我 们这个强烈的交响乐里头,他(教授)是一架泄了气的破风琴。”生物教授被骂为“死物 教授”。大学生、大学教授“十年窗下糊涂得紧,还不如来一次十三陵”——这里才是 真正的大学。在这里吃窝窝头,就是吃改造思想的“改造丸”。在这里叫你认识到“知 识分子就是比农民脏”,这里的奇迹能压碎知识分子的“灵魂”,使其深感“悲哀”, 而要摆脱“悲哀”,就得“改造”。剧中以郭沫若为模特儿的郭团长(首都文化界工地 慰问团团长),更是“高屋建瓴”地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好说什么“任重道远”,那是 吹牛,他们挑不起重担,他们天生就是属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所以非经体力劳动 锻炼不可。(注: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818页。) 而作家胡锦堂在剧中更是被重点抨击的“典型”:他不仅蔑视劳动人民的伟大工作,说 十三陵水库建设是“劳民伤财,费时失计的事”;还嫌弃劳动人民孙惠英,是当代的陈 世美;并且作风极不正派,所以被群众称为“坏分子”,是要抓起来的人。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对工农兵的高奏颂歌,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的指责、抨击,与 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现实呼应一致。从40年代解放区延安整风运动起,中国共产党便 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于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利害原则与文化观念”,而置换以知识 分子为重点的所有人以往的文化观念,是建立这个利害原则和新的文化观念的重要工作 ,这种“置换”也就是“思想改造”(注:席扬:《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时代 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97页。)。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被纳入自上而下 严密的组织体系内,进一步确认了体制内的工作者身份。政治文化权力中心对他们的改 造更是体现为党对他们的义不容辞的帮助、提高。不合作者迅速被划入统一战线之外, 成为进攻打击的对象。在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与讲话中,知识分子的危害性 被多次强调。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被认为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所以 一定要继续改造。而承担知识分子改造重任的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主人,即工、农、兵 。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政治文化权力话语“ 在理论上越来越加大加深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差异,形成了知识分子越来越孤 立的生存环境”(注:席扬:《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版,第182、197页。),数次的改造运动又对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洗脑与肉体上 的打击、镇压。田汉的“畅想曲”正是在这种社会现实语境中,对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对 工农兵、知识分子不同态度的鹦鹉学舌。在田汉与工程进展似乎同样紧张兴奋、热火朝 天的场面描写文字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上荒芜苍凉的景象。人的 主体在作品中悄然隐遁。这种人的主体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则是指作家主体;二则 是指作家主体笼罩下的客体——作品中的人物的主体意识。”(注:许志英:《中国现 代文学主潮》(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314、300页。)特别是创作主体 ,也即作家——知识分子独立的情感、思想理性隐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纸面上一泻千 里、泛滥充溢的是空洞而虚妄的政治斗争热情,以及极力争取融入时代的“英雄主义大 合唱”的焦虑与最终汇入大合唱的兴奋和狂热。就在这高亢的大合唱中,知识分子主体 意识被义无反顾地放逐了,而五四以来建立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改造的忧患意识” 传统也在诸神起舞、众声喧哗的时代终于被遗弃和流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能思 考的盲目服从,文学开始了‘侍臣文学’的艰难跋涉”(注:许志英:《中国现代文学 主潮》(下),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314、300页。)。
结合这样的语境观照《关汉卿》,这个作品具有了我们惯常所数说的其戏剧艺术价值 、艺术成就之外的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思想意义,而恰恰应该是在这种意义上, 《关汉卿》成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田汉。这就是:《关汉卿》一剧树立起了一位伟岸的 卓而不群的知识分子英雄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身上寄托着作为知识分子的田汉对中国 古代的知识分子英雄(如他少年就已仰慕的文天祥),对五四以来,包括左联时期、抗战 时期的知识分子精神、人格情操、价值理念的理想、憧憬与肯定。这个作品表达着田汉深层的知识分子情怀。
目睹无辜平民朱小兰被诬杀,激发了关汉卿反思自己“当真只能救得人家的伤风咳嗽 ”,从而否定闲适趣味,决心创作《窦娥冤》,以写杂剧的笔为刀,“一定得把这些滥 官污吏的嘴脸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一定得替那些负屈衔冤的好心女人鸣鸣冤、吐吐 气,让大家知道在百姓们的心里还是有公道的,还是看得清是非的”(注:田汉:《田 汉文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1、375页。)。但是剧本演出触 怒当权者,关汉卿反对改戏,也拒绝了朱帘秀让他出走的好意相劝,终至被捕入狱。在 狱中,他得知剧本唤起了民众:壮士王著在剧本“为万民除害”、“把滥官污吏都杀坏 ”的呼声的鼓舞下,刺杀了权臣阿合马。他怒斥前来劝降的叶和甫,在面对死亡迫近时 ,仍不改为天地之心、替人民立言的初衷:“我们的死不就是为了替人民说话吗?人家 说血写的文字比墨写的要贵重,也许,我们死了,我们的话说得更响亮”(注:田汉: 《田汉文集》(第七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1、375页。)。正当关汉卿 身陷囹圄之时,他的朋友、群众为了营救他发动了签名运动,搞了一个给皇上的《万民 禀》,百姓为“请命”者“请命”。
关汉卿以笔为刀,为民请命,代天地立心,替百姓立言,为古今立人的思想,向来是 古代圣贤以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的价值理念和现实立场。仅五四以来,以笔作匕首与投 枪,作战斗的武器,为民族、国家争自由民主进步,就一直是一大批启蒙主义知识分子 的价值选择。他们以文字为马,在铁屋中呐喊,呼唤着中国“人”、“人性”、“人道 ”与“自我”的复苏。《关汉卿》中写作成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正是 “左翼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以及拒之的自我定位”(注: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818页。)的表现。面对敌人不屈不挠,顽强反抗,正是革 命知识分子斗争精神和正义人格的写照。而人民之为“请命”者“请命”更是古往今来 知识分子受到民众肯定的最高理想的表现。田汉写作《关汉卿》,正如周贻白所感觉到 的,田汉是写他眼中、他心中的关汉卿。他把自己满腔的“知识分子情怀”燃烧到这个 剧本的创作中去。
翦伯赞引黄宗羲的话说: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从老庄之“道德”,到王实 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 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6页。)对于田汉《关汉卿》的创作而言,当然也并不 例外。夏衍说:“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注: 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91-818页。)结合田汉一生的戏 剧活动,我们更能体会到《关汉卿》是田汉“一生之精神所寓”。新中国成立之前,田 汉一直以“在野”派自居,绝无丝毫的“媚官”意识,决不与“官府合作”。一贯自觉 的“在野”精神说明田汉是一位真正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属于人民大众的艺术家。自30 年代初,田汉一直把他的艺术活动作为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期据以战斗的武器。1935 年2月19日,田汉作为一个文化人,被当成政治犯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一遍遍读莎士 比亚:“……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丹麦是一所牢狱”。1942年,田汉剧作《再会吧,香港!》被当局禁演,专制政治 引起观众的愤怒和反抗,台上与台下、观众与艺术的强烈共鸣的场面深深印入了田汉的 记忆,以至十六年后创作《关汉卿》时,这成了一个潜在的触媒。在《关汉卿》中,阿 合马下令停演《窦娥冤》,王著等观众大都站在关汉卿一边,还在台下呼应,带头高喊 “为万民除害”。田汉写《秋声赋》时,他问女演员朱琳:“要担一定风险的,你怕不 怕?”朱琳脱口而出:“你敢写,我就敢演!”田汉写湘剧《武松》,高潮在杀西门庆, 意在反抗豪强,替天下受欺辱的百姓鸣不平,这引起了当局的反感,官老爷们责令田汉 按指示删改,否则将封闭剧院,勒令停演,但田汉鼓励他的朋友们说:“不要紧,一字 不改,照演不误!”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例举田汉戏剧生涯中与《关汉卿》剧情相似 的地方,就是为了说明,《关汉卿》应该当作身为“剧作家”、“作家”乃至“知识分 子”的田汉的一个理想化的自我描绘来看待。而在这种对“知识分子”理想自我的描绘 中,毫无疑问,也包含着对自我的肯定。就像田汉与夏衍的一次促膝夜谈,讲到中国知 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的许多可爱之处时,夏衍说:“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算是最好 一群!”(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67页。)所以,关汉卿形 象的塑造,“扩而言之,借助历史人物塑造这样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实际上寄托了 老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种‘自我形象’、‘自我认同’与‘自我定位’”(16)。
很显然,关汉卿这样一位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树立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对知识 分子的评击、否定态度截然相反,也与当时整个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截然相反,“可以说是公开文学中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最后表露”(注: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6页。)。在前后相距不长的时 间内,田汉的知识分子自我理想何以在《关汉卿》中得到热情洋溢的表达,而在《十三 陵水库畅想曲》中又完全失落了,完全否定了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肯定了他们被 改造思想、被洗脑的必要性呢?
外界因素造成的创作状态的迥异当然是导致“真田汉”与“假田汉”交替的原因之一 。“畅想曲”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应景趋时之作;《关汉卿》则并非应景之作。田汉起 初并没有创作《关汉卿》的打算,他是在着手准备1958年中国的关汉卿纪念会上的专题 报告时,大量阅读关汉卿的作品,深受感动,从而勃发创作热情。所以《关汉卿》的创 作算是缘情而发,为情造文,有感而作。一旦进入激情燃烧的创作状态,主流意识形态 所规范的政治思维、创作观念则完全被排斥在外,创作主体尽情发挥自己的才华,听凭 感情波澜的冲击和直觉火焰的喷发。相似的人生体验,又使他能跨越时空,在关汉卿那 里找到深深的共鸣。田汉完全可以像郭沫若1942年创作《屈原》时那样说:“我就是关 汉卿!关汉卿就是我!”但是50年代的田汉是绝对不被允许这样称道的。值得注意的是, 在写作的前一年,即1957年,田汉刚则受过一场惊吓:有人要把他打成“右派”,还是 周恩来的一句话“田汉,我了解他”救了他。而且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对他30年代被 捕入狱的经历讳莫如深。处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实际上不被信任之境,田汉只能借七 百年前的关汉卿表达自我。
作家主体在政治文化控制下的被压抑、放逐,以及心灵深处潜在的一种与前者相抗衡 的反动力从而形成的十七年文学创作者普遍的两重分裂人格是造成田汉五八年创作成就 悬殊的个体原因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田汉是以一种完全反规范的知识分子独立姿态来 创作《关汉卿》的。事实上,1958年的田汉是十分革命的,也可以说是十分左倾和激进 的。经过1957年的一场虚惊之后,他积极参加那时中国文联组织的一些到工农中参加访 问,接受“教育”、“改造”的活动,而且每每有诗歌颂之。我们只能说,在权力中心 话语强硬地一次次规定知识分子身上顽固的“原罪”,从而使作家的自卑情绪、惶恐焦 虑情绪日益增长的同时,他们在潜意识里也困惑和怀疑着,毕竟,他们是从五四走过来 的一群。遥想五四时期,甚至在左联、抗战等白色恐怖时期,他们一个个站在时代最前 列,是“如何挥斥方遒,意气风发,天马行空,敢歌敢哭,敢爱敢恨”,而在全国人民 翻身大解放、当家作主的清明时期,他们却“一个个变成了低头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提起笔来,只能“望风而动,捕捉形势的最新发展,揣摩一项新政策的内 在含义”。(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6 页。)独立人格的丧失不能不被他们自己所察觉。在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文化生活严重 失衡的状态下,我们无法想像这些经历五四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没有感觉 到被扭曲被污辱的难堪与痛苦。在低头“改造自我”的过程中,他们偶尔也会把潜意识 中的东西流露出来,不管是否为自己所发觉。正是这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潜意识,使 得我们今天重新观照十七年文学时,依然发现些许人性的光辉、艺术良心的光辉,而倍 觉珍贵。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田汉的独特气质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在野”派自我标榜的田汉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时,“仍然眼睛向下,关心民瘼,对艺术很痴迷,对做官 很外行,生活艰苦,两袖清风”(注:许志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福建教育 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314、300页。)。他身上一贯的“江湖艺人”的气质和民间立 场使得他在“惟上”与“从下”中始终坚定选择了“从下”。把《关汉卿》与郭沫若新 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剧《蔡文姬》相比较,后者虽然也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在郭沫 若的本意中塑造蔡文姬知识分子形象是次要的,他的创作是要重塑曹操的贤君形象,很 显然,这是“惟上”的表现。而眼睛朝下的田汉则选择了“为民请命”的关汉卿。田汉 毕竟是天真烂漫,“为民请命”的思想在《关汉卿》中有所宣泄,并使作品获得巨大成 功,三年之后,田汉就为这思想找到了更大的突破口,这就是1961年《谢瑶环》的创作 。这一次,郭沫若没有写信祝贺,他这次不敢置一词了。而满怀政治热情又不懂政治的 田汉正在被他笔下“为民请命”的英雄女巡按感动和鼓舞着。终于1966年《谢瑶环》被 当作一棵反党反革命的大毒草揪了出来,田汉当然也作为反革命分子生平第二次被捕入 狱。这次他再没能出来,也没有人替他请命。终至1968年12月10日暗暗地、不为人知地 死去。而《关汉卿》在文革中也成为田汉反党反革命的策略之一,成为批判的靶子。
《关汉卿》被前捧后杀的命运使人哑然失笑,又引人深思。事实上,1958年的《关汉 卿》只是侥幸逃过一劫。作品塑造的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范不相符合的知识分子英 雄形象,表达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也是当时语境所绝对排斥的。而且,“许多历史剧都 是为现代人而写的”,“历史剧照样可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那么,在一个普遍称道 的“明朗的天”之下,“为民请命”意味着什么?难道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还有贪 赃枉法、草菅人命的“滥官污吏”?还有负屈衔冤的普通百姓?所有这些都是《关汉卿》 可能引爆田汉的问题。“历史剧”成全了田汉。田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具感受政治风 向的躯壳,他无法识破当时“热火朝天”的生活的假相,识破所谓“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的局限性、落后性、反历史性,(注:董健:《论田汉》,《南 大学报》1998年1期。)然后秉着他个人的思考,写出他个人的感受来。而沉湎于历史和 个人经历中,他的真情实感却燃烧起来、活跃起来,从而回归自我。“历史剧”也掩护 了田汉,他一时免受批判,想想他在《关汉卿》里不仅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而 且还描写了爱情、人性,而这些正都是十七年文学的禁忌、雷区,田汉正是在“历史剧 ”的招牌掩护下,逃过一劫,虽然这逃脱的时间不长,厄运不久就降临。
田汉在历史剧《关汉卿》中回归了自我,又继而迷失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对现 实生活的描写赞颂中。田汉的知识分子独立意识在前者对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树立中重 新确认,又马上在后者对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批判攻击中失落殆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 思的现象。况且终究《关汉卿》也“毕竟是一个梦,一个很美的梦,一个田汉一生做得 最有才华、最有思想、最有光彩的梦”。(注: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1996年版,第791-818页。)这个“梦”温暖着田汉,慰藉着田汉,使得他即使是在周 恩来建议改成悲剧结尾后,依然舍不得自己的那个喜剧结尾。田汉式的生命、情怀和理 想都复活、燃烧在关汉卿之历史的躯壳里。然而田汉真实生命却终究是以悲剧结尾。中 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到底是历史使然,还是知识分子秉性使然,甚或是知识分子这 种社会身份使然,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反躬自问的问题,整个社会、历史都 应该在这里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