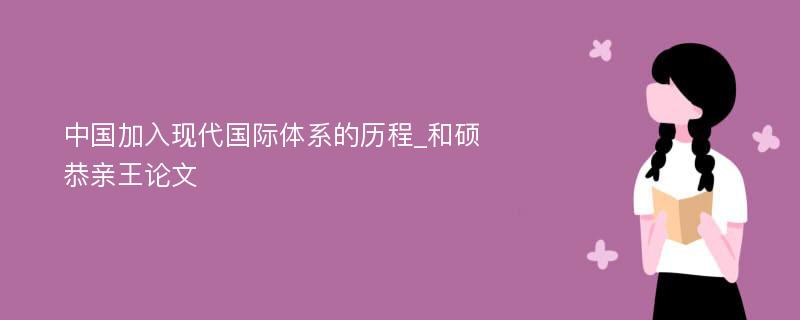
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加入论文,历程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1)06-0104-09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巨大的影响,许多人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并非空穴来风。然而,一百多年前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却是一段充满艰辛苦楚的历史。回顾这段历史,能对我们认识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的来之不易提供一些启示。
要探讨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首先应了解一下这个体系扩展的基本特征。按最简明的定义,“近代国际体系”是“一种表指独立政治实体(国家)之集合体的政治体系,这些实体非常频繁地并且依据一些规律性程序进行交往”。[1](P147)(这里明确一下“近代”的概念。受苏联史学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倾向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史称作“现代史”,以别于此前的“近代史”。但就国际体系的特性而言,一次大战之前与之后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故本文所涉的“近代”将包括整个20世纪。)这个体系中的行为主体(国家),理论上具有独立和相互平等的权利,它们依照一些公认的行为规范开展相互交往。近代国际体系起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一般认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是它建立的标志。随后,它不断向外扩展,首先接纳了彼得大帝的俄罗斯,接着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纳入其中。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为近代国际体系的全球化作了准备。
需要明确的是,“扩展”的标准是什么。某个地区进入近代国际体系,不仅仅是该地区与近代欧洲国家发生联系,而必须是该地区的国家承认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原则和行为规范,并以独立主权者的身份与欧洲国家进行正常的交往。最能辨认的一个标准或许是,某个欧洲外地区的国家与欧洲国家建立常驻使节制度,相互派遣和接纳常驻外交代表。常驻使节对近代国际体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百科全书》“外交”词条称,近现代外交“首先需要发展现有的民族国家制度,继之以建立常驻外交使团”。[2](P188)常驻使节制度能使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持续化、正规化,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交往体系。
下面就对照这种标准来探讨一下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历程。
一、东亚国际秩序
东亚加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方式,既不同于近代国际体系向东欧等地区的自然扩展,也与许多欧洲外殖民地取得独立而后加入近代体系的进程存在区别。在东亚加入近代国际体系之前,这里存在着一个相当精致的、稳固的、与近代欧洲体系迥然相异的国际秩序,它为近代国际体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照物。
东亚的秩序源于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一直认为华夏处在世界的中心,而中国的统治者便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即所谓“天下共主”。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3]便是这种理念的最好佐证。中国的统治者,从夏、商、周的“王”到秦以后的“皇帝”,被称为“天子”,其意为“上天之子”,即上天指定的统治天下的君主(“天下共主”)。因此,中国人坚持不承认存在任何与中国的统治者地位相同的君主。公元607年,日本国君遣使隋朝,因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强调日本国君与中国皇帝的平等地位,令隋炀帝大为震怒,责其“无礼”,日本使者因此无法完成使命。[4](P108)此事件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基于这种理念,中国皇帝努力构建一种统率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封贡体系”,或“朝贡体系”,也有将之称为“华夷秩序”者。[5](P12)封贡体系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形成截然相对的比较,它全然排斥“国家主权”的概念,否认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费正清和邓嗣禹指出,封贡体系是古代中国人文化优势的自然结果,逐渐被中国的统治者用来实现自保的政治目的;在实践中它具有非常根本的和重要的贸易基础,而且它充当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6]从结构原理上来说,“封贡体系”是中国内部的分封制度在国际上的延伸,当然封贡体系比分封制度更加松散一些。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地区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他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入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最典型的是万历年间明廷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的日本侵略军),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的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封贡体系在西汉朝就开始出现,主要是针对中国西北的诸多游牧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封贡体系的规模和坚固性时有变化。当中原汉族政权本身衰落不堪(如东晋朝、南宋朝)时,中国皇帝自然无法维持传统的封贡体系,有时甚至要反过来向异族政权称臣。但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传统理念却没有因这些艰难的岁月而湮灭。到明朝和清朝初期,中国在东亚构建的封贡体系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强大的蒙元王朝,四邻震惊,除西北陆上诸部落向明朝俯首称臣外,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海外入贡藩属国近约17个。[7](P62)至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活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威望,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各国君主纷纷向中国皇帝遣使甚至亲自前来表示臣服,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海外藩属国达63个。[7](P77)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而它在中国西北边疆对厄鲁特部落的长期征讨又慑服了中亚的许多小汗国和部落。至乾隆年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都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总结的那样,“至朝贡受封之国:朝鲜、琉球旧属藩封,廓尔喀、缅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罗、阿富汗、敖罕(浩罕)、巴达克山则余威之所震,拱手内服者也。惟哈萨克三部、厄鲁特二十部……朝贡略如缅越,而羁驭有间,其制盖在藩部属国之间,名曰附庸”。[8](P169)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相当稳固地含括了自中亚以东的广大区域,似乎只有实施“锁国”政策的日本企图摆脱之。[9]但在中国皇帝眼里,日本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藩属。
事实上,不仅是“不驯服”的日本,所有前来与中国发生交往的国家,或者说所有中国所知道的国家,在中国皇帝眼里都是藩属国。新航路开辟以来陆续前来东亚的欧洲国家,也自然地被归入这一类“倾心向化”天朝文物的朝贡国家。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如同此前和此后的许多次欧洲国家使团一样,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失败了。乾隆皇帝在接见马戛尔尼一行当天赋写的一首诗反映了中国统治者给西方国家的定位:“博都雅(葡萄牙)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竖亥横章输近前,祖功宗德逮遥瀛。”[10](P231)对于英国希望派遣外交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乾隆皇帝在回复英王的信中以“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一言干脆利落地回绝了,并颇为大度地原谅了英国的“冒昧”,称“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8](P816,P818)正如欧洲人对中国的东亚国际秩序一无所知一样,中国对欧洲近代国际体系也是一无所知。因此,近代国际体系在向东亚扩张时遇到了强劲的阻遏。
二、东西方国际体系的碰撞
由于悠久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某种稳固性,也由于中国背负的传统包袱过于沉重,中国在面临近代国际体系之时确实缺乏灵活性。必须承认,中国对传统信条的恪守,是鸦片战争的原因之一,即使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也没能立即正视所处的新环境。英国要为实现其商业利润打开中国的大门,就需要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进行一场革命,这势必要遭到坚决的反对。[11](P256)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几年中,尤其是在咸丰帝(1850-1861年)时期,处在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企图继续维持东亚的封贡体系,抗拒西方列强的进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中国军事上屡屡受挫之时,清廷仍想方设法规避西方列强强行施加的掠夺要求和国际行为规范。清廷抵制最激烈的是西方列强在北京设立常驻外交代表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害怕夷使“久驻京师,则凡有举动,纤悉必知,既速且详,动为所制”,而且夷使“所到之处,建立高楼,用千里镜窥测远近……宫禁重地,园庭处所,尽为俯瞰”。[12](P953)咸丰皇帝指示清廷代表桂良、何桂清,设法在1858年上海税则谈判中诱劝英法方面放弃他们已通过《天津条约》获得的公使驻京等权利,为此不惜放弃重大的国家利益,提议免除英法进口商品的全部关税。(注: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0,第1127-1128页;卷31,第1173页;卷32,第1191页;卷33,第1223页。)虽然咸丰皇帝最终在大臣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个计划,但事件本身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对被拉入国际体系的畏惧。
但是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不同和清廷对传统国际秩序的坚持,并不能证明西方向东亚封贡体系进击的正当性。相反,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方式表明,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在向外扩展时一贯采取了非正义的手段。自地理大发现时代起,欧洲在构建近代国际体系的同时,开始了向海外的扩张。欧洲殖民者在作这种扩张时完全不受欧洲国家相互之间交往模式的约束,他们根本不理会主权平等的原则,而是对扩张所至之处的原居民采取赤裸裸征服、屠杀甚至种族灭绝的手段。有学者尖锐地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欧洲基督教国家把它们相互间的义务与它们对非基督教主权国家的义务是当作两码事来看待的。“国际关系中目前的平等原则,乃是在欧洲向外扩张的前夕,产生与封闭的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各国之间的竞争,而……在20世纪以前,这种平等原则只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才得到尊重。”[13](P39)哥伦布在1492年前往西印度探险之初就被西班牙国王夫妇授予了印度“总督”的头衔;[14](P458)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完成前往印度的航行返回欧洲后便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尔一世隆重地封为“阿拉伯、波斯和诸地征讨、航海暨通商大臣”。[15](P185)这种融探险、通商和征服于一体的传统行为方式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持续了下去。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待中国的手段,便是这种强盗行为的延续。英国在向中国发起进击时,先是试图以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大门,当这一招失败后便采取了有组织的鸦片输出之邪恶手段,并继而以赤裸裸的武力实现其开放中国市场的目标。觊觎、鸦片和炮艇形成了欧洲将中国拉入近代体系的三个阶段。[16]欧洲列强在把一个理论上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国际体系扩展到东亚时,凭借武力的优势,对东亚国家采取一种不平等的巧取豪夺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悖论。英法等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体系强加给了中国;随后又将原属东亚封贡体系中的亚洲各国当作殖民对象,陆续把这些国家纳入到自己的“附属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国际体系向亚洲的扩展绝非一个先进的体系取代一个落后的体系,而是一个不平等体系取代另一个不平等体系而已。正是西方列强推行其国际体系的手段之不合理性,近代国际体系在东亚扩展遭遇的曲折,不能完全归因于东方国家的反应迟缓。
三、中西关系调整的国际背景
无论清廷的主观愿望如何,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对中西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国际背景来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使列强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列强对此颇有点沾沾自喜,正如英国贸易部次长路易斯·马特莱在1862年坦言的那样:“显然地,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比他们有义务给予的更多的特权割让——甚至已超过符合他们真正利益所能割让的特权。”[17](P33)而要保持这些利益,首先就要保证给予这些利益的清政府能够继续存在,并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履行条约义务,不节外生枝。列强在内心里依然抱着鄙视中国的不平等立场,但鉴于已经取得的权益,它们不想因为频繁使用武力而危及巨大的贸易利益。英国贸易部的政策建议书很好地反映了列强的这种心态:“当然,武力可以从中国夺得一切:但任何行动必然会有反作用;只要自然法则继续生效,那么,一个时代的诉诸武力肯定会给后来的人留下复仇的遗产——未来的欧洲人或许指望他们的先辈没有在用刺刀耕种的中华大地上播下仇恨的种子”。[18](P165)
出于这种简单明了的政治现实考虑,列强在战后改变了对待清政府的策略,从通过武力进行掠夺转向通过合作保持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合作政策”。按美国学者芮玛丽的概括,合作政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1)西方列强之间的合作;(2)与中国官员的合作;(3)承认中国的合法权益;(4)坚持条约权利。[19](P21)在这四个方面中,“坚持条约权利”是政策的目标,而“与中国官员的合作”,或者说保证清政府与列强的合作,则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主要途径。
合作政策的最热心的倡导人是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P194),他影响了其他列强驻华外交官,如英国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法国公使伯尔德密(J.F.G.Berthemy)和俄国公使倭良嘎哩(A.G.Vlangali)等,这些公使又努力对其各自政府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由于英国在华利益远远超过其他列强,英国驻华外交官在合作政策中的作用也逐渐加大。除列强外交官外,另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Hart),他作为清廷聘用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5年随总税务司公署移居北京,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保持了更加密切的交往,清廷对他可谓言听计从。赫德成为在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
合作政策在19世纪60年代表现得较为明显,至70年代中期归于终结。这段时期内,列强更注重通过已经与北京政府建立的直接外交渠道和缓地解决中外之间的争端。根据这一精神,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在1862年训令英国驻九江领事:“当你用尽了一切协议的方式而仍然有着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你一定要把这件事诉诸北京,而尽量避免行使恫吓……一定要通过中华帝国政府的参与来解决这种争端”。为了保证英国总体的在华利益不因一些个别纠纷而遭损害,英国政府也作了一些约束在华英商行为的举动。1863年,英国政府明确向在华英国商人宣称,女王政府“将要对中国政府在抵抗对它的政权和行政的不法侵犯方面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7](PP33-37)另外,列强政府愿意尽量不对中国的内外事务施加高压的影响,至少它们表面上这样宣称。在1868年蒲安臣使团访问伦敦之际,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Lord Clarendon)向使团重申,英国将不强迫中国“进展过快,而要使它的发展安全稳妥,适当符合其臣民的情感”,并表示英国将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压迫中国采纳新的制度。随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也向使团表示,北德意志联邦将以北京方面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与中国交往。[20](P298)
在促使清政府与列强合作方面,外国在华外交人员采用了各种方法来影响中国政府,尤其是敦促清廷采取行动,建立和开展与西方国际体系相适应的外交机制和实践。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将当时西方最有影响的国际法著作、美国法学家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翻译成中文《万国法原理》,1864年初通过美国公使蒲安臣呈送给总理衙门。赫德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F.Wade)也遵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旨意,向中国方面就中外关系和洋务提了一些“友善的”建议。赫德在1865年给总理衙门提呈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在1866年提呈的《新议略论》,除建议洋务、劝告清政府恪守中外条约外,都提议清廷派驻驻外使节,称此举“于中国有大益处”,俾中国“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云云。[21](P20,29)
合作政策下的中外关系固然摆脱不了西方列强掠夺中国利益的总体特征,其间的一些事件,如1863年的“阿本思船队事件”,更反映出中外利益的激烈冲突,但无可否认,在行为方式上,列强政府与此前时期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清政府带来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加入近代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中国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加入”
从传统的封贡体系到近代国际体系,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痛苦、艰难的历程。但应该看到,中国并非一味消极地被“拉入”近代国际体系。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也含有主动的因素。事实上,中国人并非天生无法适应外部新环境,在17、18世纪中,中国曾经主动对自己的外交行为作过调整。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第一项条约,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便是一个背弃封贡体系理念的条约,它“确乎含有与约双方君主和国家地位平等原则”。[22](P50)1827年中国又在平等基础上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接纳俄罗斯的商队和留学生,并在1829-1832年间向俄国首都派遣了两个外交使团。[20](PP114-116)在对待某些中亚小国(如浩罕)时,中国也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它们相处。故有学者称,“即使是在朝贡体系运转得最完美最令人满意的时候,中方交涉者也表现出校正理论以适合中国实力现状的高超技能”。[14](P33)遗憾的是,康熙、雍正朝的这些外交经验没有得到制度化,雍正朝以后,中国完全丢弃了一度有过的外交灵活性,回复到对传统封贡体系的恪守。不过,在19世纪初,中国传统的封贡体系仍然有所调整,例如,清廷并非一视同仁地对待东南亚诸国。嘉庆年间,清廷基于对外交往的事实,对南洋国家作了“藩属国”与“互市诸国”的划分,这表明中国并不想把封贡体系中的政治关系加之于所有国家。[6](P203)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对英国的交涉中就努力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作了一些与世界国际关系体系潮流接轨的努力,如他组织人翻译了大量西方报刊和文献,包括当时西方流行的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 de Vattel)所著国际法的部分章节。(注:有关详情,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第234-241页。)随着林则徐获罪于道光皇帝,他的这些开明做法被清廷抛弃了,但魏源等少数民间人士仍继续林则徐了解西方世界的努力。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无奈的抗争,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开始清醒过来。同光中兴时代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分享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他们都努力争取在“千古未有之变局”中体面地生存。
在清廷尝试调整与列强的关系时,前述列强的“合作政策”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交涉的经验,清廷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批人对“夷务”的认识有了一个转变,意识到列强并非要灭亡清王朝,中国通过遵守条约义务(即便这些义务不合心意)能够保证对外和平。战争结束后恭亲王称“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23](P2674)这与他在早先称“夷情狡诈不测”[24](P2396)的断语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依照这种乐观的想法,从前被认为是耻辱的条约现在变成了一种用来确定最大让步底线的有用工具,超过这条底线中国就不予同意,而洋人在法律上也不得逾越这条底线,即恭亲王所称的“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23](P2675)
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反清起义的现实需要及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构成了推动清廷调整对外政策方针的内部环境。为了肃清内部叛乱,同时在西方帮助下加强本身的军事力量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终目标,清政府必须接纳西方以获得一段时期的和平。恭亲王等人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比作心腹之患,把俄国的领土野心比作肘腋之患,而将英法等列强的贸易要求比作肢体之患。故必须对西方列强“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一切等“贼匪渐平”后再作“补救”。[23](P2675)
可见,清政府最初调整对外政策,只是它力求对外和平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作为中国接纳近代国际体系的起步,这套权宜之计有着深远的意义。清廷对外政策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861年1月在恭亲王提议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文祥和桂良掌管;在总理衙门之下还设有南、北各一个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十几个通商口岸和开放口岸的一应事务。这改变了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和两广总督等机构兼办外交从而使内政与外交界限不分的状态。这是中国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第一项认真的措施。[25]
在清廷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之后,中国迈向近代国际体系的步伐便逐渐顺着其自身的惯性行进。对外交往的日益顺畅,伴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主管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其个人的外交经验也不断积累,视野不断拓宽。丁韪良呈上的《万国法原理》译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恭亲王下令将该书作仔细润色后刊印300册,分发给京内外大员。恰在《万国法原理》刊印期间,清廷面临一件外交纠纷,使恭亲王有机会检验西方国际法的有效性: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hfues)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根据新近从《万国法原理》中获取的关于“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知识,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在恭亲王的压力下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洋钱的赔偿金,还向恭亲王奉上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等颂辞。[26](PP29-36)
李福斯事件的结局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使他开始信赖于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1867年10月,清政府一改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竭力规避与西方列强谈判的态度,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修约谈判期限前3个月就主动筹划修约谈判事宜。由此达成的《阿礼国条约》(1869年10月签订的《中英新约》),虽然仍使中国出让了一些权利,但它至少是一项形式上完全平等、内容上也体现了互惠互让原则的条约,而且它还是中英通商以来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协议而后订立的条约,[27](P30)与1842年以来中外签订的历次“城下之盟”有着重大的差别。
《中英新约》的谈判和签订表明,清廷的外交政策执行者已相当熟悉并采纳了近代国际体系的许多行为规范。但是,从建立总理衙门以来的诸多进展,尚停留在中国“接纳”西方的层面上,还称不上中国“加入”了近代国际体系。因为,尽管有赫德和威妥玛等人的一再敦促,清政府对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一项始终犹豫不决,清廷只是派遣过一个低级别的非正式使团随同赫德考察了欧洲列国(1866年),无所实效。如本文开篇所言,相互接纳和派遣常驻使节乃是近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性。因此,只有当中国向国外派遣了常驻使节,才能视中国真正地加入近代国际体系。
在《中英新约》谈判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对外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议题之一就是“遣使”。各地大员对此意见不一,如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就表示反对,[28](P4)两江总督曾国藩则认为中外既已通好,彼此遣使往来,实属常事,无须过虑一些技术上的困难。[29](P3)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又折中的举动,于1868年2月聘请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出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使团的行程历时两年半。蒲安臣使团作为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第一次派出的正式外交使团,是中国进入近代国际体系行程中的重要一步。在蒲安臣使团之后,清廷在1870年又为天津教案派崇厚出使法国。但是,清廷派遣常驻使节则一直拖延到1877年,是年,清廷为马嘉理案派郭嵩焘前往英国向英国女王道歉,随后就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中国又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设立了使馆。故西方学者称“到1880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30](P101)
结语
起源于西欧的近代国际体系在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中,充满着暴力和不公。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近代国际体系迥然相异,两个体系之间必然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中国经过惨淡的抗争,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双方调整了相互关系,中国方面逐渐从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加入近代国际体系。随着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近代国际体系基本完成了向全球的扩展。本文讨论的主要是近代国际体系规模的扩展,而非该体系原则的实现。身为国际体系中正式成员的中国仍继续遭受列强的欺凌;而中国原有的东亚藩属国命运更惨,它们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连形式上的平等权利都没有取得。事实上,在一个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时代,近代国际体系最重要的“主权平等”原则从未真正实现。即使是在欧洲内部,也不乏有主权平等原则被严重破坏的事例,甚至有几个国家遭遇瓜分乃至灭亡的命运——如18世纪初的西班牙和瑞典,18世纪下半叶的波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