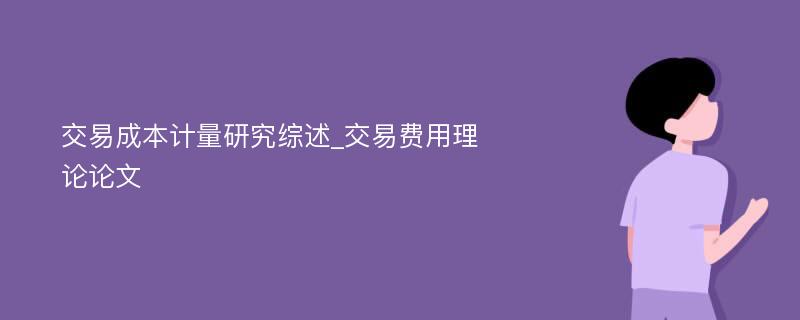
交易费用计量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费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7)04-0020-07
自科斯开创性的把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引入经济学分析以来,对交易费用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交易费用的定义问题,另一个就是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当然这两个问题之间是有关联的,正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才导致其计量范围和方法上的不一致①。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把交易费用界定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或者是“在开放市场上通过交换完成一项交易所花的成本”;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威廉姆森则将其界定为“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诺思将交易费用界定为“规定和实施构成交易基础的契约的成本”;埃格特森认为它是“个人交换他们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巴泽尔把它界定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张五常则将交易费用界定为“所有那些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达尔曼则将交易费用描述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议价与决策成本、检验与执行成本”;菲吕博顿和瑞切尔认为交易费用包括那些用于制度和组织的创造、维持、利用、改变等所需资源的费用[1]。
从上述对交易费用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或体制运行的交易费用,如阿罗的定义;另一类是在既定制度下测量商品或劳务的标准及技术变化引起的交易费用,如巴泽尔的定义。前者从宏观层面上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后者则是从微观层面对其进行了定义。据此,我们可以将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层面上的计量,另一类是微观层面上的计量。这样的划分可以解决交易费用定义上的差异以及生产和交易费用是否被联合决定的问题[2]。下面笔者将按照这种思路,对有关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一、宏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计量研究
(一)对经济体交易费用的计量
Wallis和North在其论文《美国经济中交易部门的测量:1870~1970》中,第一次开拓性的对交易费用进行了测量。他们将整个经济部门分为交易部门和转换部门,其中交易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批发零售业以及公共交易部门②,转换部门即为农林牧渔业、矿业、制造业、餐饮业等。交易费用包括来自于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和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其中交易部门的交易费用用该部门所利用的资源的总价值表示,转换部门的交易费用以转换部门内从事交易服务的职员人数和薪酬的乘积来计量,两项加总即为整个经济中交易费用的总规模。根据上述方法,Wallis和North计算出美国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由1870年的24.19%~26.00%增加到1970年的46.66%~54.71%(数字区间表示公共交易部门估算范围的不同),并且他们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即经济越发达,交易部门的规模也越大,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也越大[3] (P126-178)。
运用Wallis和North的测量方法,Dollery和Leong对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也进行了计量,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交易费用占GNP的比重从1911年的32%上升至1998年的60%,从而证实了Wallis和North的结论[4]。Dagnino和Farina等在对阿根廷的研究中发现,在1930~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GDP的比例变化不大,由1930年的25%升至1970年的28%,但是到1980年却突然上升到35%,且这个比例一直持续到1990年[5]。张五常将全部第三产业的产值以及第一、二产业的量度和监管费用作为总的交易费用,计算出香港的交易费用占其GNP的80%。
Ghertman运用OECD数据,对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在1960~1990年间交易费用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以横轴表示人均交易费用,纵轴表示人均收入,绘出了一条交易费用-收入曲线,并以此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通过研究,他发现四国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分别由1960年的55%、40%、38%和34%增加到1990年的62%、56%、52%和63%,且交易费用-收入曲线斜率越大的国家,其交易费用越节约[6]。
(二)制度、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
有关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涉及另一种计量交易费用的方法。这些文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论证制度与经济增长有关。从本质上讲,它们测量的并不是交易费用,而是由于制度的无效率所导致的成本。
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关于俄罗斯由于制度无效而导致腐败严重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俄罗斯普通民众每年用来贿赂的资金高达30亿美元,这大约是他们交纳的所得税的一半;而俄罗斯商人每年大约要花费330亿美元用于行贿,才能使企业正常运转,这个数字大约是2002年联邦预算总收入的一半。另据调查,俄罗斯交警每年要收受3.68亿美元的贿赂,仅次于教育部门的员工,他们每年收受金额达到4.49亿美元[7]。
有关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除了前文已经提及到的Wallis和North等人的论文以外,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陈志昂和缪仁炳借鉴Wallis和North的测量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划分为生产、运输和通讯以及交易三部门,并假设交易费用与从事交易的人数正相关,因此通过检验从事交易的人数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来间接说明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论为:1978~1990年间从事交易的人数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45,1993~1996年间该系数为0.99,均属高度相关,从而证实了中国交易费用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强相关关系;在不考虑农业费用,并将文教科卫部门视为交易部门的条件下,交易费用占我国总费用的62%[8]。在其后续的研究中,他们对该计量方法做了改进,将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分为三大部门,即非交易服务产业、交易服务产业和国家服务部门,并将所有从业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提供交易服务的人员,另一类是提供转换服务的人员。通过计算各个部门中提供交易服务人员的数量与其平均工资的乘积之和,即为全国总的交易费用。其结论为:我国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8.4%上升到2000年的43.2%;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且高度显著[9]。
金玉国借鉴North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和交易部门,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外在性交易费用——交易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进行了计量。外在性交易费用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所有交易部门的增加值之和。通过测量发现:按当年价计算的外在性交易费用的绝对数从1991年的4429.7亿元,增加至2002年的20576.10亿元,增加了3.5倍;消除价格变动影响后,增加了1.78倍,说明计算期内交易费用的绝对规模是扩大的。但从相对规模来看,交易费用占GDP的比重似乎没有变化,即该数列是一个平稳的时间数列。在经济规模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交易费用的比重下降0.103187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经济体制转型因素,我国相对交易费用平均每年递增0.153%,而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一增长趋势被体制转型节约的交易费用所抵消[10]。
(三)简单评论
通过上述对有关宏观层面上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宏观层面上交易费用的计量方法,基本上都是借鉴Wallis和North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这种计量方法所测量的交易费用实质上是市场上可计价的各种交易部门的价值加总,不包括各种非市场化的资源损失,这样必然严重低估经济中真实的交易费用总额。其次,将社会运行成本划分为交易费用和转换费用,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计量上却不具有操作性。因为社会活动在交易活动与转换活动之间的划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当某些活动既具有交易功能也具有转换功能时(这种活动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会使交易费用的计量存在很大困难。最后,这种计量方法属于简单的统计测算,没有进行深度分析,尤其缺少动态均衡分析。
二、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计量研究
近年来,有许多文献都从微观层面上对交易费用进行了计量,它们所涉及的领域颇多,既有企业管理领域,又有政府管理领域;既有环境领域,又有金融领域,等等。因此对所涉及的领域进行全面考察既不实际又不可取,本文也不打算这么做,而是根据Eirik和Rudolf对微观交易费用的划分——将微观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一个大致分类,并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计量方法进行述评。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这里的市场型、管理型和政策型交易费用,与Eirik和Rudolf所指的有所不同③。这里的市场型交易费用是指在市场上交易所产生的可直接计量的费用;管理型费用是指组织运行的费用,包括不可直接衡量的非市场交易费用;而政策型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一项政策或制度的实施所产生的各种费用。
(一)市场型交易费用
在金融领域,交易费用一般是指在金融市场上投资的成本,它主要包括经纪人费用和买卖差价。由于在这一领域,人们对交易费用的界定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并且金融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得,因此对其的研究与计量非常之多。Stoll和Whaley用价差加上佣金的方法来测量交易费用,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费用占到了市场价值的2%,而在小型证券交易所该比例则达到了9%[11]。Bhardwaj和Brooks研究发现,交易费用在售价高于20美元的公债中占到了2%,而在售价低于5美元的公债中则占到了12.5%[12]。Collins和Fabozzi提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测量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13]:
交易费用=固定成本+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佣金+手续费+收费;
变动成本=执行成本+机会成本;
执行成本=市场影响成本+市场时机选择成本;
机会成本=预期的收益-实际的收益-执行成本-固定成本。
其中:市场影响成本(market impact costs)是指由于买卖价差和券商的让步所导致的资产价格的变动;市场时机选择成本(market timing costs)是指由于市场其他参入者的影响导致交易时资产价格的变动;执行成本(execution costs)是由于要求合同立即执行所产生的成本,它既反映了对流动性的需求,也反映了对交易活动的需求[7]。
David、Joseph和Charles通过建立一个证券收益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交易费用的方法。在他们的模型中,交易成本不仅包括佣金和价差,而且还包括预期的价格影响和机会成本。假定边际交易的事后收益可以观测得到,那么边际交易者所面临的所有成本就都是交易成本。他们只需每日证券收益的时间序列数据,就可以求得任何一个公司的有效交易费用。利用这个模型,他们计算出从1963~1990年,大证券交易所和小证券交易所的平均交易费用占其市值的比例分别为1.2%和10.3%[14]。
Joel Hasbrouck将交易费用界定为实际交易价格和隐含的有效交易价格之间的差异,并将证券的交易价格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随机部分,另一个是固定部分,其中随机部分与有效的交易价格相等,而固定部分反映的就是有效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异,即交易费用。通过建立模型,他发现纽约证券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平均占到了股票价格的0.33%[15]。
Polski运用Wallis和North的研究方法界定和测度了1934~1998年间美国商业银行业的交易费用。她把商业银行业的交易费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所有的利息支出,它反映了银行业的资金成本;另一个是非利息支出,它主要包括:(1)员工工资和报酬;(2)房屋租赁费;(3)其他各种费用,比如支付给董事、经理、受托人以及咨询委员会的费用,法律费,广告费,公共关系支出,促销支出,慈善捐款,办公经费,信息加工费,电话费,检查及审计费等。她的研究表明,美国商业银行业的总交易费用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34年的69%上升到1989年的85%,然后下降到1998年的77%[16] (P56-72)。
(二)管理型交易费用
1.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交易费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和事后两个部分,事前的交易费用包括协议的起草、谈判和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等费用;事后的交易费用包括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不适应成本、矫正事后不一致性所产生的讨价还价成本、与治理结构有关的设立与运行成本以及实现可信承诺的保证费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分是相互依存,且直接计量它们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对制度的比较来对交易费用做出测量。他认为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也就是把一种合同与另一种合同进行比较,才能估计出它们各自的交易费用[17] (P33-36)。也就是说,对威廉姆森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交易费用的绝对量,而是与其他契约形式相比的相对水平。
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认识到交易具有三个基本属性,即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以及资产专用性,并从这三个基本属性与事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结构选择和成本补偿的关系出发,间接地考察了交易属性与交易费用的数量关系。在他看来:(1)交易发生的频率越高,就越有可能补偿规制的确立和运行的成本,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就可能越低;(2)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越高;(3)资产的专用性越高,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交易费用越高;(4)在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不管交易频率的高低,与企业组织体制相比,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低;(5)当资产的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都很高时,与企业组织体制相比,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较高。威廉姆森正是从这些可观测到的交易属性出发,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以比较制度分析作为分析方法,比较得出了不同契约(制度)的交易成本大小,从而很好地回避了如何计量交易费用的绝对量这一棘手问题。
2.非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研究。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Wallis和North的研究方法只衡量了通过市场交易的那一部分交易费用,而现实世界中还存在许多交易费用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衡量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De Soto则开创性的研究了Wallis和North所忽视的那部分交易费用,即非市场交易费用(non-marketed transaction costs),例如排队等候的时间、获得开办企业许可的支出以及贿路官员的支出等。这些非市场交易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大量存在。非市场化的交易费用对于理解经济绩效极其重要,因为这部分交易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一样,不仅影响生产的契约安排,而且还影响市场中生产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类型。
在De Soto的开创性研究中,他考察了在秘鲁依法开办企业所需的成本。他和他的研究小组试图在不行贿、不利用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结果,按照正常手续完成所有设立企业的程序总共花了289天的时间。但是,当他在佛罗里达重复该试验时仅花了2个小时[18]。在秘鲁花费的时间相当于佛罗里达的1000多倍,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交易费用差距。Zylbersztajn和Graca估算了在巴西开办一个服装企业所需要的成本,其中货币成本约为人均GDP的11.3%,另外还得经过9道程序,耗时64天[19]。
Gabre-Madhin对埃塞俄比亚的谷物市场进行了研究,并测算了交易双方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她以每笔交易中寻找交易对象的劳动时间成本以及在寻找交易对象过程中劳动资本的机会成本作为衡量交易成本的基准。她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占到了总成本的19%[20]。
Lee Benham考察了公寓转让的交易费用。在开罗,个人购买一套公寓并对所有权的转让进行注册时,需向第三方额外支付的费用相当于购房价的12%,房地产经纪人的服务可以自由选择,其费用大约是销售价的1.5%。而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依法转让所有权的费用大约是销售价的1.5%;如果有房地产经纪人的参与,其费用将占到销售价的6%。可见,在国家控制的部门,开罗的费用是圣路易斯的8倍;而在竞争性部门,开罗的费用仅是圣路易斯的1/4[2]。随后,他和Alexandra调查了在几个国家拥有一部商务电话的费用。在两星期内安装一部电话的实际价格从马来西亚的130美元到阿根廷的6000美元不等。另外,他还考察了与进口大型掘土机所需的曲轴相关的交易费用的国际差异。与美国相比,在1989年的秘鲁,正式获得这种曲轴所花费的货币价格是前者的4倍,等候所花费的时间是前者的280多倍;在阿根廷,货币价格是美国的2倍,等候时间是30天;在马来西亚,货币价格和等候时间与美国大致相同[18]。
通过以上对非市场交易费用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它无法通过市场交易直接衡量,因而对它的计量研究主要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比较完成同一项交易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从而得出交易费用的高低。
(三)政策型交易费用
Colby在对水资源从农业领域转向其他用途的研究中,提出了“政策诱致型交易费用”(policy-induced transaction cost,PITC)的概念,顾名思义,这种交易费用指的是一项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它包括律师费、工程和水文研究费、法院诉讼费以及支付给政府机构的费用,但是不包括水资源的使用费。Colby的研究表明,完成每英亩一英尺(灌溉的水量单位)水的转让平均所需的政策诱致型交易费用为91美元,但是每个州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在科罗拉多州完成同样的交易需要政策诱致型交易费用为187美元,在犹他州为66美元,而在新墨西哥州则仅需54美元。另外一种计量政策诱致型交易费用的方法是计算等待政府机构审批所需的时间,在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和犹他州该时间分别为29个月、4.3个月和5个月[21]。
McCann和Easter对明尼苏达河的非点污染源(nonpoint pollusion source,NPS)的污染控制项目进行了研究。为减少NPS污染,政府采取了四种不同的政策,他们分别估计了这四个不同政策的交易费用的大小。在他们的研究中,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收集与分析所花的费用、颁布授权法的成本(主要是指游说成本)、政策的设计与执行成本、有关项目的维护与管理成本、检测成本以及诱导成本等。他们采用与项目建设者们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调查并估算整个项目的劳动投入量,然后将劳动投入量乘以工资水平,从而换算称货币成本。研究结果显示:向肥料征税的政策的交易费用最低,为94万美元,其次是进行管理培训的教育计划,其交易费用为311万美元,接着便是保护所有播种耕地的政策,为785万美元,最后是对地役权实行永久性保护的扩展计划,为937万美元[22]。
McCann、Colby和Easter等以环境政策为例,分析了在政策选择和政策设计中,交易费用对政策的效率和可持续性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他们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用于界定、建立、维护和转让产权的资源,并将其分为7类:(1)在界定产权过程中,信息收集、分析与研究的成本;(2)颁布授权法的成本;(3)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成本;(4)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维护和管理成本;(5)签订契约的成本;(6)检测成本;(7)解决矛盾的成本。同时,将政策的生命周期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期,在该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政策,但是还没有提出来;该阶段的交易费用主要是(1)类交易费用。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政策已经被提出,并经过了讨论、协商;该阶段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3)类交易费用。第三阶段为早期执行阶段,该阶段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4)类交易费用。第四阶段为全面实施阶段,此时政策已经产生了效用,所包括的交易费用为(1)~(7)类交易费用。最后一个阶段为项目完成阶段,此时政策工具已经很好的确定下来,并得到了全面实施,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为除(3)类交易费用之外的所有交易费用。他们指出,在计量政策的交易费用时,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还要把几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有些交易成本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有些是事前估计的,有些是事后计量的。比如,在第一个阶段,交易费用主要源于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研究,此时应采取的计量方法是通过调查或者采访政府部门和利益相关者来获取相关资料。在最后一个阶段,测量源于信息收集与分析研究的交易费用,可以采取的方法有查看政府报告、金融数据和政府预算等[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计量政策型交易费用的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因不同的政策阶段、不同的交易费用类型而有所不同。
三、结语
本文根据交易费用的不同定义,将交易费用分为宏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和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同时将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策型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正如文中所述,计量交易费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交易费用计量的复杂性,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计量方法来测算所有类型的交易费用;同时也表明了理论研究的紧迫性,迄今为止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交易费用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交易费用的计量问题直接关系到交易费用理论的现实说服力,交易费用能否准确计量已成为新制度经济学能否步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关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计量交易费用的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要想更准确地对其进行测量,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尽管近年来在宏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的计量方面已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但方法仍然比较单一,且存在很多局限性,因而需要借鉴其他方法,以完善对宏观层面上交易费用的计量。
(2)计量微观层面上的交易费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对其中的非市场交易费用和政策型交易费用的计量却乏善可陈,几乎都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且仍然停留在经验层次,尚未提出一个可直接计量且经得起检验的方法。
(3)目前有关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计量的文献较少,虽然70年前科斯就为我们打开了企业这个“黑箱”,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其所知仍然甚少。因此,有关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计量研究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比较研究,可能是经济学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本文在相同的意义上交替使用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这两个词,即认为它们是等同的。至于不同的著述者对这两个概念作不同的理解或解释,则需要读者根据他们的论述去体会和把握。
②公共交易部门与政府有关,它所提供的交易服务主要包括国防、邮政、警察、金融管理、教育、市政服务、社会福利以及农业补贴等。
③Eirik和Rudolf将交易费用分为市场型、管理型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其中,市场型交易费用是指使用市场的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是指企业内部发号施令的费用;政治型交易费用是指在政治体制中制度框架的运行和调整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