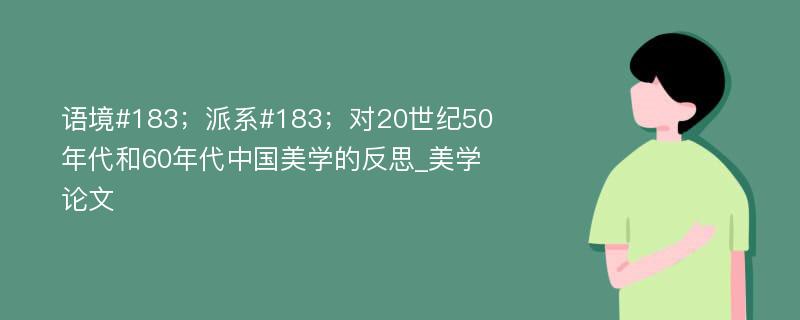
语境#183;派别#183;反思——关于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别论文,语境论文,美学论文,五六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331(2015)04~0018~06 一、语境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有个特点,就是总是要学习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中国的现代美学,实际是一个至今还在延续的现代性事件。作为西学的美学,20世纪初就被中国学者引入了中国,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把西方的美学观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为中国现代美学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使中国有了美学。三四十年代,朱光潜的美学体系明显地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也与西方现代文化有着相当的关系,而蔡仪的美学体系,则标志着前苏联文化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一方面宣布要“赶英超美”,一方面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这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政治色彩极浓的基本语境,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学大讨论是深受当时的整体语境的影响的。在当时的语境中,西方现代文化被批判为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资本主义文化,而前苏联文化则成了进步的、向上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说,中国现代美学是一件现代性事件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就是这个现代性事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前苏联的美学是从二战以来发展起来的。从二次大战以来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正是西方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时期),前苏联美学有了很大发展。当时苏联美学的队伍主要由第一代的洛瑟夫、阿斯穆斯、里夫希茨(他们主要研究美学史),第二代的卡冈、布罗夫、叶果罗夫,以及第三代的斯托洛维奇、鲍列夫、万斯洛夫等人所构成。与西方现代美学完全不同,前苏联的美学模式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学流派。这一点从叶果罗夫的著作《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反动派实质》的书名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二是关心西方古典美学中的美的本质问题,并以此为整个美学研究的重心,这显然是对西方古典美学的承继,因为美的本质问题也是西方古典美学研究的重心。三是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即首先要认定美的哲学基础,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并以此来划分美学派别。当时的苏联美学界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派别:首先是以叶果罗夫、波斯彼洛夫等人为代表的自然派,主张美是一种自然的属性。其次是以卡冈为代表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派,再次是以斯托洛维奇、鲍列夫、万斯洛夫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派,他们主张美是一种社会属性或价值。有趣的是,前苏联的美学界也曾发生过一场美学大讨论。这场美学讨论从1956年开始,长达10年时间。这场讲论的重要诱因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被重视,争论的焦点则依然是美的本质问题,在这场争论中,苏联的自然(客观)派、主客统一派、社会派之间针锋相对、争论得异常激烈。[1](P217~237) 以上之所以要介绍前苏联的美学情况,是为了让人们对我们当年国内美学大讨论的语境与模式有一个更好地了解与理解。 再看我们国内当时美学界的情况。从外部来讲,前苏联文化模式对中国当时的美学讨论的语境有着支配性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国内密切关注前苏联美学界的新动态。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学界渐趋活跃,渐趋繁荣的艺术创作迫切需要建构美学理论,美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知识场域已成共识。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于1956年增设“美学组”的举措立即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注意。几个月后,新中国便成立了“美学组”,最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报美学小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小组”。其次,苏联美学论著陆续引进中国。如罗森塔尔的《苏联美学问题》、铎尼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克林列夫的《音乐美学问题》等。第三,聘请苏联专家前来讲学。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其表象背后既体现着意识形态对美学知识的重塑,还蕴含着美学家们遵行某种规范探讨学科知识的潜流。第四,派遣美学家赴苏交流。[2]从国内的情况讲,1956年的“双百”方针推进了共和国成立后的这场美学大讨论。而就这场美学大讨论的具体起因而言,它却是因为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加以清理而引起的,其结果则演变为——如有的学者所说——那个文化专制时代中的一次“最具有学理内涵”的学术碰撞,并在这种学术碰撞中,形成了共和国早期美学研究中的四个主要流派。我们完全可以说,苏式的文化语境与美学模式从根本上影响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大讨论,我国美学大讨论中产生的主要美学派别与前苏联的美学派别基本相互暗合,这也不是偶然的。(据凌继尧先生介绍,他80年代去前苏联访学,当他向苏联学者介绍中国的当代美学时,前苏联的学者表示不愿听,因为中国的现代美学与前联的现代美学太相似了)。 二、派别 如前所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中国美学形成了四个派别: 一是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朱光潜的美学体系是在民国时期受西方现代心理美学影响而建构起来的。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文化成了“先进”文化,西方现代文化成了“落后”文化,朱光潜早期的美学思想在新的语境中就自然不合时宜了,他必须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新的语境。事实上,那场美学大讨论正是从朱光潜对自己过去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开始的。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反省与批判自己的美学思想,认为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旧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康德、柏格森、克罗齐这些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因而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的这种反省与批判,意味着他向西方现代美学的告别,向前苏联美学的靠近。 我们当然无须怀疑朱光潜的真诚。但是,朱光潜毕竟是位有着自己美学体系的美学家,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是有着他自己的“前理解”的。他这样总结他过去的美学思想:“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一个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于美还是这样的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3]这也就是说,朱光潜对自己以前美学思想的内核仍然是坚持的。但是,由于语境的变化,朱光潜不能不改原先西方现代美学式的话语而为苏联式的话语。他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提自己美学的“新的观念”,《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可以说是朱光潜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代表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朱光潜特别关注其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论,并在这种理论的启发下,提出了他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新的观点”。为了论证他的“新的观点”,朱光潜提出了“物甲物乙说”:“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在这个反映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的。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了认识的对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只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入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4]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谈“物甲”是为了强调“物是第一性的”,是社会存在;谈“物乙”是为了强调美是离不开“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属于社会意识。朱光潜对美的这样一种解释,与他过去的主张明显是有联系的,他想通过“物甲”来强调物质的第一性,而他强调的重点仍然在“物乙”上,“物乙”显然是在主体对客体意识作用下的产物,在他看来,“物乙”是不同于实象的“物甲”的,它是一种主观的意象,是意识形态的,所以他才说美必然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4]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把文艺当作一种意识形态,那么,美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也就是说,物甲只不过是产生美的条件,物乙才是真正的美,凡是未经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东西都还不是美的,而只是美的条件。 为了适应当时语境的变化,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统一说,在用语上确实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他不再大谈“直觉”、“距离”、“移情”,这些美学话语,而是更多地去谈“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这些哲学话语。正像他自己所说:“我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的直觉创造形象的主观唯心主义。我接受了艺术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艺术为生产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的艺术形象孤立绝缘,不关道德政治实用等等那种颓废主义的美学思想体系。”[4]尽管如此,朱光潜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与自己过去的美学的内在精神联系还是显见的。只不过在新的语境下,朱光潜已经不再关心审美活动中主客何以合一,而更关心的是对审美活动中主客合一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只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朱光潜的美是主客统一的“新的观点”,仍然受到了蔡仪、李泽厚等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旧货新装”,在那种语境下,这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的。 二是蔡仪的“美是客观说”。蔡仪原先的美学体系原本就是在前苏联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对当时的语境自然是很适应的。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发表,蔡仪等人便发表批评文章,认为朱光潜的“新的观点”是“旧货新装”。蔡仪本人则依然坚持自己过去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美学思想,认为美是客观的,美感则是人对客观之美的主观反映。他反对自己的论敌们:“自然我们也承认人之所以认为某一对象的美,是和他的生活经验,当时的心境及他的思想倾向等有关系。但是对象的美如果没有它本身的原因,只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所谓‘美学评价’也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根据,那么美的评价也就只能是因人的主观而异,既无是非之分,也无正误之别,美就是绝对地相对的东西,这就是美学上的相对主义。实质上也就是美的完全否定,是美学上的虚无主义。”[5]蔡仪从认识论模式出发,坚定地认为,美是客观的,自然的美就在于自然本身的属性,认为是先有客观的美,才会有人的主观的美感。 由于蔡仪的观点过于机械,同样受到了论敌的批评。朱光潜认为蔡仪将美与美感截然地对立与割裂开来,是只抓住了“存在决定意识”,而没有重视“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朱光潜进而指出:“美感和艺术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有它的社会性,所以它的活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活动。”因此,蔡仪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有时不免是“片面的,机械的,教条的,虽然是谨守唯物的路向,却不是辩证的”[6]。李泽厚等人也对蔡仪的“美是典型说”提出了批评。李泽厚指出,蔡仪的“美是典型说”,完全把美当作了纯然客观的自然属性,这种神秘的典型就很有点像柏拉图的理式,很容易走向神秘主义,因为人们无法在纯然客观的自然中分析出美来的。还有的学者更尖锐地反问蔡仪:“哪一棵松树是最典型的松树呢?”“典型的臭虫美吗?” 三是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这场美学大讨论中,当时的新秀李泽厚,以他的新说对当时的语境有所突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同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李泽厚强调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美学的哲学基础。李泽厚非常重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的一段论述:“从前一切唯物主义……所含有的主要的缺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和从直观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不是理解为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真正感性的活动。”[7](P54)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的观点,正是李泽厚美学的理论基点。 李泽厚在《论美·美感与艺术》一文中,强调美学研究从美感入手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关键在于用什么观点和方法去看待美感问题。在他看来,美感具有“美感矛盾二重性”,即它是直觉性与社会功利性的一种统一。他还依据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乃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产物”的论断,认为“美感矛盾二重性”来源于美是一种“人化的自然”,这种“人化的自然”是一种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李泽厚特别强调,他所说的社会性是客观的社会实践性,而不是朱光潜说的意识形态性。在谈自然美即“自然的人化”时,他同样强调,应该区别两种所谓“人化”,即客观实际上的“自然的人化”(社会生活所造成)与艺术或欣赏中的“自然的人化”(意识作用所造成)。他进而指出,自然之所以成为美,是由于前者而不是由于后者。同样,也应该区别两个所谓“离开”,即“离开人”和“离开人的比拟”,离开人(即离开人的生活,离开自然与人的客观关系),自然美便不存在;离开人的比拟(或离开人的文化,离开自然与意识的主观联系)自然美仍不失其为美。而历史上“人对自然的美感欣赏态度的发展和改变,就正是以自然本身对人的客观社会关系的发展和改变为根据和基础。”所以,他强调:“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美是社会生活中不依存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的存在。自然美只是这种存在的特殊形式。”[8]李泽厚关于“美感二重性”,关于美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美是“人化的自然”的观点,在当时的语境中之所以赢得了人们更多的赞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既唯物又辩证”的要求。 四是吕荧与高尔泰的“美是主观说”。在前苏联的美学中,没有这一派,但在中国的美学大讨论中却出现了美的主观派,这显然是对当时语境的一种“僭越”。同为主观派,吕荧与高尔泰其实是很不同的。吕莹认为“美是人的一种观念”。吕荧在批评蔡仪“美在客观说”时指出:“美,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美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同是一个东西,有的人会认为美,有的人却认为不美,甚至于同一个人,他对美的看法在生活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原先认为美的,后来会认为不美;原先认为不美的,后来会认为美。所以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9]他还指出:“美的观念因时代、因社会、因人的生活所决定的思想意识而不同。”“自然界的事物或现象本身无所谓美丑,它们美或不美,是人给它们的评价。”“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10]尽管吕荧也引用了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他的观点仍然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同样主张“美是主观的”,但高尔泰更强调“美就是美感”,他把这称为“美感的绝对性”。高尔泰指出,美与美感虽然体现在人与物的两个方面,但却是绝对不可以把它们割裂开来的。美只要被人感受到,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要想超越美感地去研究美,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超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任何想要给美以一种客观性的企图都是与科学相背离的。因为“美产生于美感,产生以后,就立刻溶解在美感之中”[11]。他还进一步地指出,艺术中的自然就是人化的自然,艺术的美就是艺术家的主观创造,艺术的美是属于那些能感受到它们的人们,因而“人的心灵,是美之源泉。”[12]高尔泰论美很少引证马列语录,而是更多地依照自己的感悟、联系艺术创作,来直接地表达与论证自己的美学观点。由于高尔泰“美是主观”的观点明显僭越了当时苏式的语境,所以他的观点在当时自然地成为了异端(其实,高尔泰的美学观点中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美学意蕴的,这也可以从他后期的美学思想中见出来)。 三、反思 如前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总体语境政治色彩很浓,同时,前苏联的美学模式也在暗中影响着中国的美学大讨论。主张“美是主观”的高尔泰,之所以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甚至为此付出生活上的沉重代价,就因为他僭越了当时的语境。关于中国上世纪的那场美学大讨论,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反思,本文对那场大讨论本身已经没有太多兴趣,本文有兴趣的是对前苏联美学模式做些反思——因为正是这一模式在暗中支配着中国当年的美学大讨论,因而对这种模式的反思才是对当年美学大讨论的更为深刻的反思,希望对我们的美学研究能有所启迪。 应该说,当年苏联式美学模式是有着严重欠缺的美学模式。首先,冷战式的思维使这种美学模式的视野所及充满了过度的政治色彩,因而显得相当褊狭。美学原本是门西学。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美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但在前苏联模式中,这一切都是“腐朽反动”的,是不值一提的,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这种做法势必造成当时中国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遮蔽,这种遮蔽也阻隔与延误了中国现代美学对现代西方美学的了解以及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对话,影响中国美学的全球化进程。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美学流派纷呈,出现了与古典美学完全不同的风貌。如分析美学就认为西方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美的本质是个假问题,传统美学是个错误;心理美学流派——从世纪初的距离、移情、直觉诸说到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对人的审美心理都做了非常有益的独到研究;现象学美学主张描述“面对事物”、“直观本质”的审美活动以显示审美活动的意义;存在主义美学反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或对立,主张“人在世界中”,人与世界不可分,从而把美理解为是存在但却是不可言说的……这些显然都被当年苏联美学模式给遮蔽与阻隔了。也正是因为这种遮蔽与阻隔,使得中国当年的美学大讨论的理论视野非常地封闭与褊狭,完全拒绝了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对话,使人不能不想起《浮士德》中的诗句:“周围是碧绿的大草原,却在枯索的原地转圈”。这不是说西方现代美学如何,而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的美学,是离不开对现代西方美学的了解与对话的。 其次,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使这种美学模式显得相当呆板机械。这种认识论框架首先要求认定美的哲学基础,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并以此来划分美学派别,判定对错。其实美学不是认识论,是不能以主客相分的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审美活动关涉人的价值,审美是离不开人的,是离不开主客相融的审美活动的,审美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种主客相融的审美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从中国古代的美学传统来看,中国古人主张,“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主张审美活动中“心既随物以宛转,物亦与心而徘徊”(刘勰),主张“境生乎心”(方回)与“境生于象外”(刘禹锡)。显然,强调审美活动是一种主客交融的中国传统美学不支持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再从西方现代美学来看,存在主义美学强调,“人在世界中”,人与世界的交融才是美学的哲学基础;现象学美学干脆说,审美对象就是(人的)“审美知觉+艺术作品”。西方的现代美学同样也不支持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当年美学大讨论中,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明显地与这种认识论模式的局限有关。李泽厚后来对当年的美学大讨论也有反思:“在美学范围内,‘美’这个词也有好几种或好几层含义。第一层(种)含义是审美对象,第二层(种)含义是审美性质(素质),第三层(种)含义则是美的本质、美的根源。所以要注意‘美’这个词在哪层(种)意义上使用的。你所指的‘美’到底是指对象的审美属性?还是指一个具体的审美对象?从而,‘美是什么’,如果是问什么是美的事物、美的对象,那么这基本是美的对象的问题,如果问哪些客观性质、因素、条件构成了对象、事物的美,这就是审美性质问题。但如果要问这些审美性质是如何来的,即美从根本上是如何可能的,这就是美的本质问题。”[13](P461)在李泽厚的这段话中,审美对象显然是对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的肯定,审美性质显然是对蔡仪客观说的肯定,而美的本质则是对他本人的美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统一的肯定。尽管在这段话中,李泽厚试图把当年争论者们的不同观点调和、融合起来,但他的调和与融合仍因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美学模式的影响,而显得不彻底,显得难以圆融。就以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而言,美的本质已经在这种主客统一的审美活动中显现出来了,即现象学所说的“直观本质”,因而也就不需要再从“美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中把它推论出来,而且从客观“根源”(社会实践)出发也无法推论出“美的本质”,由此也可见李泽厚仍然没摆脱前苏联美学模式主客相分的局限。 再次,前苏联的美学模式是把美的本质问题视作美学研究的重心,这表明前苏联美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西方古典美学的模式。我们知道,美的本质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来的,他认为在数不清的具体的美的现象之后,还应该有一个抽象(可以用语言定义)的美的本质,而西方古典美学,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柏拉图这一问题的不断解答。如前所说,到了现代,西方现代美学已经发现美的本质是个假问题,已经放弃了传统美学对美的本质思辨与定义式把握,而走向了描述审美活动以显现美的意义的现象学方法,而我们当年的美学大讨论因为受前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仍然在围绕着美的本质争来争去,并试图从关于美的本质的定义出发,来推导出一套美学理论来,其结果连当年参加美学讨论的人都对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表示不满。朱光潜后来反思道:“放弃亲身接触过的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住美的本质。法国人往往把美叫作‘我不知道他是什么’(Jene sais quoi)”。[14](P12)最近也有学者反思那场争论时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现今走不出美的本质的怪圈”,“由于‘美的本质’的答案纷繁众多,研究者难以认同对方的观点而展开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论战’,在几十年的争辩中,各派谁也说服不了谁。可以说,这是一场又一场无结果的争辩,也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辩,各家发挥的都有是片面的真理——就像佛经上所说的‘瞎子摸象’的游戏。这场‘争辩’与‘论战’很难说提升了中国美学理论的研究水平,但这种争辩所形成的研究传统与惯性却一直持继至今”[15]。当中国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始重构体系时,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前期的)朱光潜”,而“回到朱光潜”其实也就是要从抽象思辨美的本质而走向描述具体的审美活动,也就是“走出古典,走向现代”。[16](P72~107) 如前所说,发生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美学大讨论当然有它的学术成就与影响——空前地普及了美学这门学科,并培养了一批美学研究者。而且,李泽厚的美学观点在“新时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美学的主流话语——实践美学,当年“异端”的高尔泰的美学观点在“新时期”也发展为很有生气的“美是自由的象征”的学说。但如果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中国现代美学本身的发展来看,那场美学大讨论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受前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这场美学大讨论的理论视野是非常褊狭的,理论模式也很僵化,争论的问题也基本是西方古典式的,甚至理论的用语也是哲学的而非美学的,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这些在客观上都延误了中国现代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的交流与对话,也影响着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进程。所以,这场美学大讨论固然如有些论者所说,它是在当时政治色彩过浓的语境下发生的一场“最具学理内涵”的学术争鸣,但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的总体发展看,由于制约那场大讨论的前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那场大讨论的局限与缺陷都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我们当年把前苏联美学模式当作是“最先进”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学者的感慨:“当我们今天回过头看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时,我们很难对其中的一些成果进行评估,由于缺少一个必要的参照系统,我们很难说它们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17](P5)标签:美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李泽厚论文; 认识论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