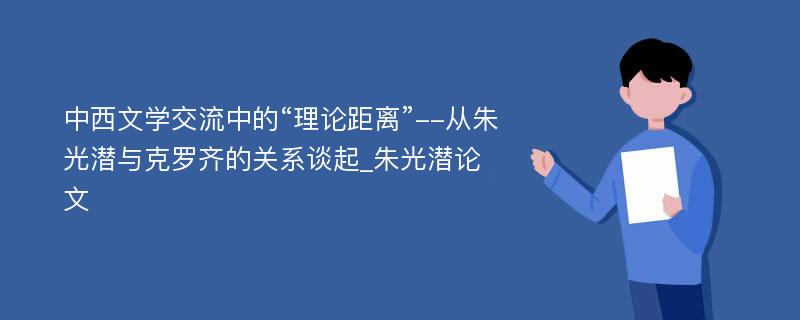
中西文学交流中的“理论距离”——从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克罗论文,距离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西文论的思想联系中至少可以看出,交流能够促进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价值的新的理解和发现,而并不是制造对抗,否定某种文化。在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这种理解和发现原本是互相发生和深化的。对于西方文化认识得越全面,眼界越宽阔,就会越能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意蕴和价值,在文艺美学上有所发现和创造。而在文化上的偏激和狭隘几乎是孪生兄弟,只有在封闭状态中才会滋长泛滥。这一点我们从克罗齐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朱光潜的美学道路上可略见一斑。朱光潜首先是一个学者的身份和眼光接触到克罗齐的,克罗齐的美学观念曾在他的美学研究处女作《悲剧心理学》(1933年出版)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是,值得回味的是,1982年,当这部处女作的中译本出版之时,朱光潜却在自序中写道“一般读者都以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中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中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一)
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问题当然不能怪罪于读者,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连朱光潜自己也“误读”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尼采,而不是克罗齐的信徒。但是,难道朱光潜自己真地长期以来没有搞懂自己,而读者也张冠李戴了吗?到底是读者搞不清楚,还是朱光潜自己从误解走向更大的误解了呢?其实,这个问题恰巧反映了朱光潜美学思想来源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朱光潜原本受过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特别是老庄思想、陶渊明诗文、《世说新语》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也造成了他后来倾向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潜在基础。也许是像华兹华斯、夏多布里、许莱格尔等人的诗文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他理想中的所谓“魏晋人”的性情追求,朱光潜曾经很喜欢他们。所以,当他接触西方文艺美学的时候,内在的精神追求需要多方面的理论支撑,也促使他和很多西方理论家在思想感情上发生共鸣,例如克罗齐、康德、尼采、叔本华、立普斯(Lipps)、黑格尔、布劳、柏格森等等, 除此他还猎涉了罗斯金(Ruskin)、谷鲁斯(Groos)、汉斯立克(Hanslick)、 佛莱因费尔斯(Muller Freienfelr)、布洛(Edward bullough)、理查兹(I,A,Richards)、鲁卡斯(F,L,Lucas)等人的学说。可以说,朱光潜是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广泛吸取的一位学者,他的理论学说从一开始就投下了西方理论家的多重叠影。而用这一角度来解读他的第一部文艺美学著作《悲剧心理学》也非常贴切。因为在朱光潜看来,悲剧快感始终混合着多种因素的情感,而发现和理解这些因素恰巧离不开上述西方理论家的学说。也可以说,《悲剧心理学》是一部检索和消化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著作,他虽然没有说出多少作者自己的见解,但是它已显示出了一种综合的欲望,作者企图在吸收西方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
这里牵扯到了一个“理论距离”问题。所谓“理论距离”,也许缘起于美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psychical distance),意思是说为了实现审美的纯粹性,必须在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设立一定的距离。在这里我把它引入了理论交流领域,即认为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理论家为了避免自己在吸收和运用他人理论过程中失去自己所采取的一种姿态和策略。这既是理论家能够保持自己清醒和清明状态的条件,也是进行理论综合,有所创造的心理基础。实际上,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是朱光潜最早选择的理论支点,用来描述审美悲剧心理的特征。他自己曾说说,“无论是康德和克罗齐纯粹形式主义的美学,或是柏拉图,黑格尔和托尔斯泰明显道德论的美学,都不能作为合理的悲剧心理学的基础”,为此他认为“心理距离”是一条“有用的标准”,可用来描述悲剧的审美现象,“说明它的原因和结果,并确定他与整个生活中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朱光潜一直保持着,后来他在《悲剧与人生的距离》一文中还指出:
象一切艺术一样,戏剧性和人生之中本来要有一种距离,所以便带了几分不自然,人事哪里有恰好分成五幕的?谁说情话象张君瑞出口成章?谁打仗只用几十个人马?谁象奥尼尔在《奇妙的插曲》里所写的角色当着大众说心理隐事?以此类推,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带面具,穿高跟鞋,拉了嗓子唱,以及其他许多不近情理的玩意儿都未尝没有几分情理在里面。他们至少可以在舞台和世界之中辟出一个应有的距离。(注:《朱光潜全集》(三),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第377页。)
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他在描述悲剧审美心理特征的时候拒绝运用这些理论家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某种理论上意识的矛盾。也就是说,距离并不仅仅存在于“舞台与世界”之间,而且在于各种不同的理论之间,尤其是朱光潜与他所钟爱的西方文艺理论家之间。
用“理论距离”的观点来看朱光潜与克罗齐以及其他西方理论家的态度,就会发现,朱光潜理论上的独立性和自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靠这种距离来实现的。但是这种距离在某种情况下不仅造成了读者对朱光潜的“误读”,而且也使得朱光潜被自己所遮蔽——由于布洛的“距离”,他有意无意的掩饰,或者淡化了自己与尼采的理论联系。在这里,理论上的距离决不象审美上的距离那么轻松和纯洁,它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心理意味,他可能成为保持理论上个性化和独立性的途径,但是也可能成为敞开自我的心理障碍。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朱光潜所声言的“在我心灵中所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直觉说”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的意义并不是要否定朱光潜晚年的真诚性,而是为了理解他早年的这种自我回避的真实意味。因为在最早的《悲剧心理学》中,朱光潜曾经为了保持和康德—克罗齐的距离借助了黑格尔、尼采等人的学说,又为了和尼采保持距离而引入了布洛;而在随后不久所写的《文艺心理学》中再次表现了自己和尼采的距离,又重新意识到了克罗齐的重要性;直到50年代,为了和所有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划清界限,拉大距离,他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等文章,开始了长期的自我批判过程,直到80年代才真正开始找回理论的自我。这是一条相当崎岖的理论道路,“理论距离”在这期间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问题是何以造就了这种“理论距离”?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这种“理论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理论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尤其对在理论意识阶段处于相对滞后状态的理论家来说,在文化心理上往往有其空落的一面。也就格外警惕自己完全落入外来文化的圈套,失去了自己理论的独立性。况且本民族的文化熏陶也会使他感到理论和思想方式上的存在隔膜。但是这种情形也会促使它广泛接受和吸取各种学说,不拘一格地进行选择。除此之外,还得考虑现实政治和生活对理论家可能造成的影响,生存压力会直接左右他们的理论态度。对朱光潜来说,这些因素都会产生作用。他和克罗齐的理论距离也是在不同情况下变化着的。而值得欣慰的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克罗齐,并且在不同的理论距离之中理解和把握了克罗齐,推动了中国诗学的复兴。
在这个过程中,走近克罗齐和远离克罗齐,表面上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沟通的意向。关键一点就是对于各种学说的深入了解,感悟和发现他们之间,特别是对立学派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在《文艺心理学》中,朱光潜就不再强调克罗齐与尼采之间的不同,而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内在相同之处,认为康德、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的共同之处就是着重“形式的成分”,“特别这种艺术的独立自由,在牵扯到科学伦理种种问题,他们所主张的其实还是变相的形式主义”。(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 月,第89页。)
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克罗齐的重新认定理解为对尼采的某种肢解,或者是对形式主义的全部肯定,那就误读朱光潜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不仅加强了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艺美学历史渊源的认识,而且为克罗齐的形式主义美学注入了生命活力。因此,在朱光潜的笔下,克罗齐的“直觉”的美学原本就植根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之中,与尼采超越意识密切相关,不可能完全脱离人和人的生命状态。这也就使朱光潜有可能在基本接受克罗齐美学观念的同时,为其他不同的美学观念留下广阔的吸收和讨论余地。
例如他对于文艺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里面,朱光潜不仅包容了西方各家学说,而且试图突破禁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因为“道德”在此处的所指并不等同于西方美学中的普遍含义,而包含了中国现实生活的特殊需要。为此,1981年7 月朱光潜再读即将重新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样稿时特别补注:“讨论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七,八章,实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时AI写作的,其中的‘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31页。)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不同的美学观念到了朱光潜笔下,就似乎变得团结起来了,说来说去差不多是一家人了,这是因为在《文艺心理学》潜藏着作者的另一种用意,朱光潜并不是仅仅在分辨文艺道德说的谁是谁非,而是试图用一种美学的力量来对抗社会,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所以,他不仅欣赏克罗齐,而且喜欢托尔斯泰,因为他们都是用美和艺术来解放情感和美化人生的;他并不认为文艺能脱离政治,但是他并认为不是道德决定艺术,而是有艺术和美决定了道德(政治)的价值和意义,所以道德(政治)必须建立在符合美和艺术的原则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下面一段提示艺术启发作用的话中领悟到更多的东西:
这种启发对于道德有什么影响呢?他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他的目的原来说是在维护道德,而结果适得其反。儒家的礼教,耶教的苦行主义,日本的武士道,都可以为证。(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 月,第130页。)
不难看出,由于理论的距离,朱光潜对西方理论的解释和吸取,包含着多种意义,有时候存在着一个潜在的意义结构。所谓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多义性和隐意结构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
这自然又会涉及到克罗齐。他不再只是一个面孔,而拥有了几个面孔。由于现实感的介入,在朱光潜的视野中,西方美学理论园地五彩缤纷,一时会显得比较遥远,他们之间的差别也会模糊不清,但是这就使他有机会回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且在中国文学及其观念中找寻克罗齐的意义。实际上,朱光潜正是这么做的。1931年,就在他写完《文艺心理学》不久,就开始写作另一部美学著作《诗论》,以复兴中国的诗学理论。这原本是一部充满克罗齐理论色彩的著作,但是作者在序言中却有如此言说: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意味式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断。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恰是治诗学者所需要的方法。(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3页。)
显然,这里所说的构成中国诗学不发达的弱点,恰恰又是克罗齐所偏重的方面,是他诗学的精粹所在。这一点朱光潜不会不清楚。所以他才感到进行比较诗学研究在中国是刻不容缓的事。他说:“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以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以我们以往在诗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其次,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这运动的成功和失败对中国文学的前途必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4页。)其实, 《诗论》所偏重的也正是中西诗学理论的比较,朱光潜从中所得到的不仅是差异,更多的是共鸣。值得注意的是,《诗论》前后写了好几年,共十三章,但是从前至尾读去,感受会有变化,刚开始时朱光潜明显的偏向于西方诗学理论,尤其是克罗齐的美学观念,认为中国的方法不可能解决诗的起源等理论问题,但是渐渐地有了变化,开始注重于对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开掘,最后竟有点沉迷于中国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不能自拔,以论述陶渊明为全书的结束。从诗论到最后论诗人,这似乎有点走题,似乎离克罗齐越走越远,但是实际上表现了朱光潜对中国传统美学境界的进一步认同;而这种认同并非是对克罗齐学说的背弃,而是从诗的内在心灵方面的进一步靠近。他这样理解作为诗人陶渊明的研究价值:
诗人与哲学家究竟不同,他固然不能没有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未必是由方法系统的逻辑的推理,而是从生活中领悟出来,与感情打成一片,蕴藏在他的心灵深处,到时机到来,突然迸发,如灵光一现,所以诗人的思想不应该离开他的情感生活去研究。(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213页。)
这也就是说,不但诗人的思想,而且真正的诗论也绝不是从逻辑推理中来的,而是从诗人的创作,诗人的心灵和人格中来的。正是由于如此,朱光潜从陶渊明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诗学真谛,同时加深了对克罗齐内在精神的体悟。
从《诗论》的写作可以看出,朱光潜并没有因为克罗齐就为自己的理论探索设置一个封闭的圆圈,而是试图做出一条自己的路,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的:“本文用意不再批评诸家的表现说,而在建设一种自己的理论。”(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75页。)而正是在他这条不断延伸的理论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艺理论交流的新的风景。
在《诗论》结尾,朱光潜曾对陶渊明做了如此评价:“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渊明所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象他做人一样,有最深厚的修养,有最率真的表现。‘真’字是渊明的唯一恰当的评语。‘真’自然也还有等差,一个有智慧的人的‘真’和一个头脑单纯的人的‘真’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Spontaneous与naive的区别。渊明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蒸馏过,洗练过的。所以在做人方面和做诗方面,都做到简炼高妙四个字。”(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223—224页。)
这也许是朱光潜对诗的真谛的一种感悟。而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联想到中国传统的“真”能动人的“精诚”之语,而且能觉察到英国批评家理查兹(I.A.Richards,1983—1979,又译瑞恰兹)的身影。记得韦勒克曾如此写到过:“理查兹不能摆脱‘真诚’观念——英国批评传统的一个特点所造成的迷宫。他看到了它的某种困难,因为他借助鉴赏力和训练有素,对‘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产生了怀疑。他看到,一首诗中的情感‘不一定是现实中个人的“真实情感”’,他承认,‘它会是想象的情感’。他不赞成下列说法:‘诗歌应该出自内心,即:诗人用言词打开他的内心’。他看到,‘真诚’同自发性相联系,同卢梭的浪漫主义虚构——‘自然的人’相联系,但是他仍然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它是我们最坚持不懈地在诗歌中要求的品质’。‘真诚’对他来说仍然是‘优秀诗歌的标准’,但是他竭力重新界说它,赋予它一种专门的意义,为此他求助于孔夫子的话,这些话同理查兹的思想与词汇毫无明显关系。我们最终了解到,真诚不过是‘自我完善的愿望’,‘服从于那种在心理中“寻求”更完善秩序的倾向’。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有条理的心理’:一首诗如果帮助我们‘整顿我们的心理’,它就是‘真诚’的,因材施教而是有价值的。”(注:[美]雷内.韦勒克著,章安祺、杨恒达译《现代文学批评史—1900—1950年的英国文学批评》,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8—329页。)
作为英美新批评学派(The New Criticism)代表人物, 理查兹和艾略特曾经在批评界遥相呼应,有很多共同之处。前者曾与迷恋中国文化的庞德过往甚密,而后者与中国文化及文学有着更为亲近的联系。理查兹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当过教授,曾于1930年和1950年两次来到中国讲学,是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重要著作有《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科学与诗歌》(Seience and Poetry , 1926 ), 《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Rhetorie,1936),《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 , with C.K.Ogden,1923), 《屏幕与别样的诗》(The Screens andother Poems,1960),《玄想的方法》(Speculative Instruments,1950),《柯尔律治论想象》(Coleridge on Imagination,1934)等,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中国文论思想的理解和发挥。对此已有研究者指出:“瑞恰兹与中国文化关系较深。他提出的中和诗,有的也称之为包容诗,与儒道的中庸之道有关系。在与人合写的《美学原理》中,一头一尾都引用了《中庸》,卷首引朱熹题解‘不偏之为中,不倚之为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包容诗和综合性,其实就是中和诗。瑞恰兹认为,好诗总是各方面平衡的结果,对立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比单一的明晰的情感经验更具有审美价值,更能培养人的人格。此外,有些诗具有排他性,写欢乐缺乏忧郁,写悲伤缺乏滑稽,写理想缺乏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瑞恰兹确实在建立一种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二重组合’的文学观。”(注:胡经之、王岳川主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12页。 )不过,平心而论,理查兹的“中和之诗”是一种中国的“中庸”和西方的“平衡”观念的混合物,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艺美学理论中理智与情感,客体与主体的对垒与冲突。但是他所发现和开拓的理论的多义性则给后来者以很大的启迪。
(三)
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兹不但接受了中国文论的很大启发,而且反过来又参与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就对朱光潜来说,他之所以能从克罗齐走向新的思考和综合,与理查兹也有很大关系。在《文艺心理学》中,他就表现出对理查兹的兴趣,在一些基本点上有所认同,例如谈到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他就大段引用了理查兹的观点:“托尔斯泰是一位虔诚的耶教信徒,不免把宗教的成见应用到艺术理论上去。但是近代科学家中也有些人深深地觉到文艺和道德的密切关系,虽然他们对于道德并没有什么成见。英国心理学派批评家理查兹(Richards)就是如此。在他看,谈到究竟,艺术总须有价值。‘价值’起于事物对于人生的关系。离开人生,便不能有所谓‘价值’。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保存和推广人生中最有价值的经验。”他还如此解说并发挥了理查兹有关“中和”的理论: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经验呢?人类生来就有无数自然冲动(impulses)。这些自然冲动如食欲、性欲、名欲、利欲、哀怜、恐惧、欢欣、愁苦之类往往互相冲突。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让某一种冲突自由实现,便须把所有的相反的冲动一齐压抑住或消灭去。但是压抑和消灭不是理想的办法,它是一种可惜的消耗。道德的问题就在如何使相反的冲突调和融洽,并行不悖;就在对于它们加以适宜的组织(ORGANIZATION)。“对于人类可能性损耗最少的就是最好的组织”。换句话说,在最有价值的经验中,最多数的相反的冲动和兴趣能得最大量的调和,遭最少量的损耗和压抑。活动愈多方,愈繁复,愈自由,愈不受阻碍,则生命亦愈丰富。据理查兹说,艺术的经验是最丰富的经验,因为在想象的世界里,实际生活的种种限制不存在,自然的冲动虽往往彼此互相冲突,我们却可把它们同时放在一个调和的系统里,不必借压抑一部分冲动才可以给另一部分冲动以自由发展的机会。(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第112—113页。)
所以朱光潜很赞同理查兹“不附和文艺为欲望的升华说,却承认压抑自然冲动是一种生机的损耗”的态度,认为“我们要尽量地发展人的可能性,须走文艺的路,因为在文艺中相反的冲动可以调和”。
而更重要的是,理查兹的理论打开了艺术主体世界通向外在的表现力的道路,使文学批评开始真正关注艺术形式和文本分析。这也就使朱光潜有可能从克罗齐“直觉即表现”的主观怪圈中走出来。他在《诗论》指出:“每个艺术家都可以告诉克罗齐:诗所表现的不能恰是画或其他艺术所能表现的。这种分别就起于传达媒介。每个艺术家都要用他的特使媒介去想象,诗人在酝酿诗思时,就要把情趣意象和语言打成一片,正犹如画家在酝酿画稿时,就要把情趣意象和形色打成一片。这就是说,‘表现’(即直觉)和‘传达’并非先后悬隔漠不相关的两个阶段;‘表现’中已含有一部分‘传达’,因为它已经使用‘传达’所用的媒介。单就诗说,诗在想象阶段就不能离开语言,而语言就是人与人互相传达思想情感的媒介,所以诗不仅是表现,同时也是传达。这传达和表现一样是在心里成就的,所以仍是创造的一部分,仍含有艺术性。至于把这种‘表现’和‘传达’所形成的创作用文字或其他符号写下来,只是‘记载’(RECORD)。记载诚如克罗齐所说的,无创造性,不是艺术的活动。克罗齐所说的‘外达’只有两个可能的意义。如果它只是‘记载’,从表现(直觉)到记载便不经过有创造性的‘传达’,便由直觉到的情趣意象而直抵文字符号,而语言则无从产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它指有创造性的‘传达’加上记载,则他就不应否认它的艺术性。克罗齐对于此点始终没有分析清楚。”(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81—82页。)可见,朱光潜对中国传统诗学及创作的重新认识和理论总结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也有西方理论家的启发和推动。
就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经历了从艺术主体的解放到表现形式的自觉,从探讨艺术中介的意义进而意识到传播过程的价值的过程。由此形成了从主体论向本体论的转换。理查兹和艾略特等人所代表的“新批评派”在此期间表现了一种倾向的转变,不仅仅在新的历史时空中更新了西方文艺美学传统,而且体现了与东方文化及其文学联结的新观念。继理查兹之后,燕卜荪是另一个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生密切关系的新批评派理论家。 据韦勒克说,
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1906—1984)无疑是理查兹最有天资, 最有影响的学生, 他1928—1929年在剑桥大学(当时他只有二十二,三岁)时便是理查兹的学生,他写了一篇英国荣誉学位考试论文,这篇论文显然经过扩充和加工之后,已于1930年以《歧义的七种类型》的标题出版,理查兹非常得意。而韦勒克没有提到的是,燕卜荪受其导师的影响,同样对中国有浓厚兴趣, 也曾两次来中国讲学。
除了《歧义的七种结构》(SevenTypes of Ambiguty,1930)之外, 燕卜荪的主要著作还有《论几种田园诗》(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1935), 《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s Words , 1951 ), 《密尔顿的上帝》(Milton's God,1961),《传记的运用》(Using Biography,1984 )等。
还未见到对燕卜荪所受中国影响的深入研究,但是细读其《歧义的七种类型》等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包括他的老师理查兹在思想上非常接近于中国传统文论。理查兹所意识到的“诗学的张力”及其对文学语言多义性和复杂性的关注,恰好迎合了中国诗学中对微言大义的考量,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比兴手法的精妙绝伦之处。朱光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诗论》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诗与谐隐”,从很多方面来考察中国诗歌语言文字中的类似现象。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素以谜语巧妙名于世界,拿中国诗和西方诗相较,描写诗也比较早起,比较丰富,这种特殊发展似非偶然。中国人似乎特别注意自然界事物的微妙关系和类似,对于它们奇巧的凑合特别感到兴趣,所以谜语和描写诗都特别发达。”(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40页。)至于中国诗中的比喻,双关,意象与情趣的契合等等,他都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在“关于诗的境界的几种分别”讨论中,朱光潜从分析王国维“隔”与“不隔”出发,也涉及到歧义的类型问题:“我们不能希望一切诗都‘显’,也不能希望一切诗都‘隐’,因为在心理和生理方面,人原来有种种‘类型’上的差异。”所以他也相当重视讨论诗学中的语言问题,把它看成是解决艺术表现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克罗齐从内在心理上突破了西方文艺美学的理性逻辑,那么燕卜荪则在文本和语言方面打破了西方文学创作中确定性的观念,比理查兹更突出地提出了文学创作朦胧性和含混性的价值观念。无疑,这种观念在西方表现为一种独创性的手段,因为他走出了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语言观,发现了文学创作中某种不确定因素和状态的意义,由此而来,艺术欣赏和评判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析、评论和说明的过程,而成为一种充满猜想、品味、赏析、并容许进行创造性想象和发挥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批评观念有相通之处。其实,燕卜荪在他论及朦胧意味时,就引用了陶渊明的《时运》一诗中“迈迈时运,穆穆良朝”作为例子,说明在简单的词语中如何“潜藏着天机”。(注:见[英]威廉—燕卜荪著,周邦宪、王作虹、邓朋译《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9—30页。)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交流的深入,文艺理论的创造和建设中的中西界线也越来越朦胧和模糊了。
标签:朱光潜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悲剧心理学论文; 文艺心理学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美学原理论文; 心理学论文; 诗论论文; 美学论文; 文艺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