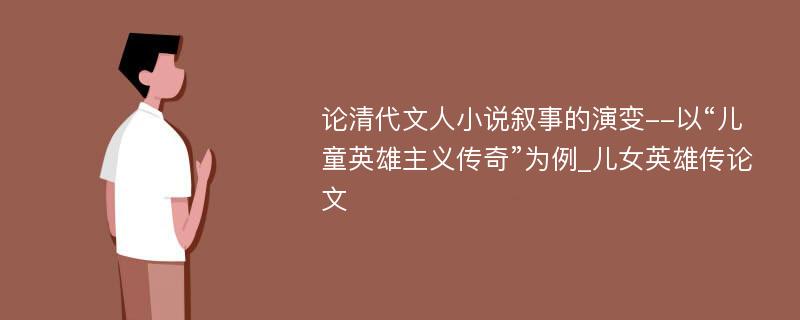
论清代文人小说叙事的演进——以《儿女英雄传》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英雄传论文,清代论文,文人论文,儿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06-07
通常而言,古代白话小说叙事的演进是以客观的呈现逐步代替说书人主观讲述为标志的,但通俗小说的说书程式也给一部分作家提供了可供改造的资源。在清代小说中,李渔拟话本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虽风格相差绝远,但都属通俗平易的代表,两者都有意利用说书体的讲述情形,强化叙事者对文本的干预,降低故事的独立性,在形式上凸显叙事的主观作用,在旧形式中翻出了新意境。本文拟从文人利用说书体叙事方式的角度,论述文人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探索和演进。
李渔和文康的小说,一个用说书人的玩世姿态挑战社会禁忌,一个试图借温情的民间立场和田园理想回应《红楼梦》等文人小说的悲剧蕴涵,手段和立意固然大相径庭,但在叙事方式上并非薰莸不同器。此“器”所指就是说书体的叙事方式。李渔是戏曲家,尊崇戏曲创作“至苛且密”、“寸步不容越”的程式是其胜场。这种思路移之于小说,就是将说书模式处理材料的自由度更大地发挥,刻意强化说书人对故事的凌驾和虚构,赋予个性化叙事者最权威的地位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则是一部模仿口头文学的“评话”小说,以它的评话叙事方式和结构之独特,受到许多学者的注意。陈寅恪认为《儿女英雄传》结构的精密、有系统,转胜于《红楼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1](P67)。
本文认为,文康说书体小说和清初李渔的拟话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人利用口头文学传统的两种类型。《儿女英雄传》在内容和叙事方式上,有意和《红楼梦》对垒,因为“说书是一种乐观喜庆的艺术”[2](P256)。故而其叙事技巧和风格本身就寓含着创作主旨,同时在叙事方式上多有创新。如引进了说书人对叙述的评论功能,虚构的叙事者——说书人和作者一同作为人物进入故事层面;通过拆解人们熟知的故事和人物,作者如民间说书人那样运用段落模块,以达成包含新旧不同意味的意旨。内化的评点使行文与批评更为贴合。用重复叙事的方式解决线性结构和空间叙事的矛盾。这些叙事手法的演进值得探讨和总结。
一、说书人内化了小说评点
白话小说起源于佛教的俗讲和市井说书,进入文人独创阶段的小说一直保留了故事讲述者——说书人。他的存在“形成事件的模仿和叙述者的评论双线发展的特殊修辞效果”[3](P100)。这个角色在明清白话小说中或是被淡化,或者被有意突出,成为有效的表达手段。如李渔拟话本、《豆棚闲话》等作品中,说书人既有修辞化功能,又有个性化趋势。虚拟的说书人背后是两种叙事传统的融合:一是说书情景的延续,二是史家对历史铨评议论姿态的传承。前者是职业化地干预叙事过程,后者居高临下进行道德评判。这两种传统使说书人左右逢源,取得了介入叙述的更大自由。《儿女英雄传》的贡献是使说书人具备了外在于文本的小说评点功能。通过颠倒叙事层次,说书人背后的作者被置于叙述层中,说书人通过对其创作过程的评论而将评点内化到小说叙事之中。
在小说的《缘起首回》中,作者称:“这部评话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小说。”[4]评话是口头讲述小说的体例。在宋元时代有“平话”如《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长篇故事;在明清有曲艺艺人用方言讲说的小说,又称评书,“扺掌而谈,别无帮衬,而豪侠亡命,跃跃如生”[5](P94)。不论是小说还是曲艺,其共同特点都是偏重口头文学的形式。这句话暗示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舍自《金瓶梅》以来,经三百年的发展已是高度成熟的书面化叙事方式而不取,转而模仿艺人们的说书体。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已逐渐淡化的说书人形象,在这部小说中重新活跃起来。文康重拾口头文学所遗的“宣讲精神”,即“他在屋中写作,正如在热闹场中设座,群众正在座下对着他听一样。因此,笔下写出的语言,须句句对群众负责,须时时照顾群众,为群众着想”[6](P16)。这同旧式的文人小说盛极而衰,旗人之中“子弟书”等口头文学的流行不无关系。
从晚明到清代的拟话本,说书人这个角色的议论功能时时处于被过度开发的状态,文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广泛而感性的议论,既超出了职业说书人的视阈,又超出了小说的文本负荷,是推动拟话本走向衰亡的一股内在力量。
文康笔下的说书人对文本的干预也不取职业说书人的谦卑姿态,而时常调侃说书的老套,如‘一宿无话’这四个字,久已作了小说部中千人一面的流口常谈”。他在小说中屡次把这部“稗官野史”比附于史传文学,以八股眼光揭示小说结构,以史书的“正传”、“附传”讲人物塑造。如此则文人小说中的说书人同史传文学的“太史公曰”的血缘关系,可能比话本的说书人更近一些。自《史记》的“太史公曰”到《聊斋志异》里的“异史氏曰”,叙事者对文本和事件的介入比之职业说书要深广而权威,比附史传的叙事者无疑抬高了说书人的文本地位。
在《儿女英雄传》之前,说书人始终是文本中的一个人物。限于他所在的叙事层次,他不能对位于上个层次的作者的叙述活动进行评论。对叙述活动的评论是由评点者来完成的。明清时代的书坊往往借评点以扩大小说的影响和销路。有的评点出于作者的友人,如李渔请好友杜浚为之评点《无声戏》、《十二楼》;有的出自作者化名自评;更多的是后来的读者的阅读心得,自谓能搔到作者痛痒处。但评点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它并不以忠实于原文精神为鹄的。评点者一面涂抹窜改原文,一面将“文章”拆解开来,张竹坡所谓“作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7]。金圣叹称“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张竹坡说“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评点者的宣言表明了他们与小说文本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和疏离。从作者角度看,与其让后来者把小说拿来“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读”[8],何如甘苦自知,将意见和评点内化在作品中。《儿女英雄传》的说书人就承担了这一功能。同时,他对文本干预的自由度和权威性更上一层楼。
首先,作书人处于故事层次中,他的身世、处境、创作情况是说书人叙述的一部分。在宋元话本里,说书人本要求“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讲论古今、褒贬是非是说书人分内之务,但他的“秤评”通常只指向故事层面:“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9](P4);《儿女英雄传》则把作书者——燕北闲人作为一个人物,放到说书人的叙述内容之中。
通常,位于话语和故事层之间的说书人是作者的叙述对象,而当作者化身人物进入说书人的讲述时,叙述层次就会发生变化。说书人和作者所在的层次似乎发生了错位,说书人处于文本之外。“说书的当日听人演说《儿女英雄传》这桩故事的时候,……”(第4回)“在我说书的,不过是照本演说;在作书的,却别有一段苦心孤诣”(第12回)。说书人同文本的疏离,使得他具有了评论叙述过程的权力。作者的创作过程便成为故事层次的一部分了。
如说书人讲述作者的来历:
幼年在塾中读书,一生也不曾作得一个好梦。只着了半世昏迷,变成粪墙朽木,作了个燕北闲人。(《缘起首回》)
调侃作书者的辛苦:
只可怜那作《儿女英雄传》的燕北闲人,这事与他何干!却累他一丸墨是磨灭了,一只笔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从这书的第四回《末路穷途幸逢侠女》起,被他没日没夜的磨,磨到第二十八回,才磨得《宝砚雕弓完成大礼》。咳!百岁光阴有限,一生事业无穷,那燕北闲人果然生来的闲身闲心……想来他也该作得些些事业,爱个小小声名。也须女嫁男婚,也须穿衣吃饭。却都不许他作,偏偏的要他作个闲人——闲人之为闲人,苦矣!(第28回)
讨论他的写作技巧:
这回书越发累赘了!也不知那作书的是因当年果真有这等一桩公案,秉笔直书;也不知他闲着没的作了,找着钻钢眼,穿小鞋儿,吃难心丸儿,撒这等一个大躺线儿,要作这篇狡狯文章,自己难为自己!(第22回)
这类议论和描述动摇了故事文本的权威性,引起了小说叙述层次的混乱。说书人具有了超叙事者的色彩,可以独立于主叙事层次之外。这样在故事层画就包含了三个叙述层次、五方关系:超叙事者文康——他叙述了燕北闲人做的梦;主叙事者燕北闲人——写了除《缘起首回》以外的所有回目;次叙事者是说书人,由他对着观众在讲述这部小说。但主叙事者燕北闲人又在次叙事者的叙述中成为人物。作者、说书人、“作书人”——燕北闲人、虚拟听众、书中人物等五个方面构成了复杂的关联,从而在话语与故事之间撑开一个较大的空间,可以引进不同声音,各种意见和辩驳在文本中形成了“作用力场”,容纳了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和对作者意图的解释,说书人发感慨、对小说结构做分析。这套修辞技巧是戏中戏的形式。因为叙事层次的颠倒和错置,书中人物和作书人、说书人有时同处一个叙述层次,也可以议论作书人和说书人的叙述活动。十三妹有意卖关子,“好让那作书的借此歇歇笔墨,说书的借此润润喉咙”(第9回);褚大娘子阻止大家去二十八棵红柳树庄上小住,称这样会使文章的气脉散了,“又叫人家作书的怎的个收场呢”(第21回)。
说书人脱离故事情景出来打岔,打断了观众的注意力,在文本中就出现了故事与说书之间表里两层间的距离。叙事层次的复杂关联则使说书人的功用发挥到了各个层面:他的评论功能从论事——讨论书中人物、事件,扩展到“论文”,评点小说叙事的技巧,还有对其时的社会现象和文艺作品的议论。
其次,说书情景的强调和模拟使小说结构趋于单纯。说书需要连贯的叙事时间,需要回到简洁流畅的线性结构:“燕北闲人这部《儿女英雄传》,自始至终止这一个题目,止这几个人物。便是安老爷、安太太再请上几个旁不相干的人来凑热闹,那燕北闲人作起书来,也一定照孔夫子删《诗》《书》、修《春秋》的例,给他删除了去。”文康之所以模拟说书人叙事方式,跟其时南北方曲艺盛行,以及旗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文人小说创作渐趋沉寂,平民的讲唱文学承宋人话本正脉,“历七百年余年而再兴”,清末旗人之家嗜好曲艺如子弟书、戏曲、评书,“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10](P229),又加以文人化的议论。
从小说史的叙事演变来看,文人小说对说书情景的模仿一直是白话小说叙事形式探索的一支流脉。文人作者注重在小说中表达自我,表现个性,如何在小说文体中争取更大的话语空间,成为改造“说书人”的动力。明末的短篇小说往往强调故事的虚构性,降低故事的独立性,使作者可以时时干预叙述过程。如明末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故事层就包括叙述者——乡间豆棚架下讲古的几个人和他们的故事与议论。故事的叙述过程与豆子生长、衰落的时序相吻合。韩南先生把几位叙述者轮流讲述的形式比作拱顶式的结构,它使十二篇小说有了某种整体性。这几位叙事者各自的身份、立场和个性,隐约地在其所叙故事和发言中表露出来。李渔拟话本小说中也往往通过故事串、通过把故事作为主观议论的例证,使人物完全处于被干预之下,代表作者意见的说书人则可以议论滔滔。而短篇小说毕竟发挥的空间有限,《儿女英雄传》里的一百多段议论,才使说书人成为“在以前的中国小说里,还不曾有过如此生机勃勃、肆意渲染、滔滔不绝的叙事者”[11](P12)。
研究者历来对这位叙事者褒贬不一。或以为他的“打岔”冗长讨厌;或以为能“深得评话艺术的阃奥”[12](P465)。有研究者指出,在叙事艺术上,这部小说多出的著书人、说书人等角色,使小说在叙事方式、成书过程和接受途径上呈现出复杂的表象[13]。这种复杂的表象自然是艺术形式上求新的一种努力。本文认为这种内化至少有两处直观的优势:一是使评点更贴合文本,其二是很自然地解决了全知叙事者使用限制视角的问题。说书人可以直接把责任推给作书人:“这事大约除了安老爷和燕北闲人两个心里明镜儿似的,此外知道个影子的少了。”(第23回)“便是我说书的说来说去,也只看得个热闹,到今日还不曾看出他的意旨在那里呢?”(第26回)“那著书的既不曾秉笔直书,我说书的便无从悬空武断,只好作为千古疑案。”(第31回)
二、故事层的模仿与变形
《儿女英雄传》是受《红楼梦》影响产生的作品,《红楼梦》里的叙述者包括青埂峰下的顽石、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等,似乎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中石头和空空道人是经历和参与故事的“同故事”叙事者,他们应是《儿女英雄传》燕北闲人的先声。不同于《红楼梦》的是,文康有意通过说书人对燕北闲人创作背景的评点,指出小说对其他作品的模仿,是出于作者主题表达的需要。在此我们主要从叙事的角度考察其故事层的模仿与变形。
文康本是“吾们旗人多富贵,家庭内时时唱戏狠听熟”[14](P8)的八旗子弟,他所受的通俗文艺的熏染在多方面影响了小说的故事层面,说书人也有意强调这一点。《儿女英雄传》提到了数十种小说、平话、弹词、戏曲,这些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都成为说书人评点和戏仿的对象。在大结构方面它师仿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奇书体小说常用的下凡历劫的框架。人物上,宝黛钗之金玉良缘、木石姻缘的痛苦纠葛,为金玉双凤共嫁安骥的圆满所取代;主题上少男少女美好的理想世界破灭和家族衰败的哀音,因作善降祥、德福一致而更迭为轻快的曲调;主人公金凤、玉凤的名字也取自宝钗、黛玉。据孙楷第先生考证,十三妹侠女的形象出自《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韦十一娘是个有神仙法术的侠女,十三妹虽然天生的英雄气壮,“是个脂粉队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但也只是个心高气傲的凡人。为了让十三妹行侠这段情节取得和剑侠故事相似的惊奇效果,小说运用限制视角叙事。十三妹自第4回出场,到第19回方由安学海揭出她的姓名和来历。因为有作书人的存在,说书人在对事实缄口不言时,就把一切推到叙述的上一层:“无如他著书的要作这等欲擒故纵的文章,我说书的也只得这等依头顺尾的演说,大众且耐烦些,少不得听到那里就晓得了。”(第13回)
不单是叙事者,书中人物也时时将其所处情形同此前的戏曲小说人物进行对比。
能仁寺里十三妹不肯说出姓名:“你们大家看着我这个样儿,还是《平妖传》的胡永儿?还是《锁云囊》的梅花娘?”(第8回)安学海智劝十三妹报仇,褚大娘子称:“你可别认成《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水浒》上吴用智取生辰纲,作成圈套来讪你的。”(第19回)安老爷称要由着十三妹当姑子去,“岂不成了整本的《孽海记》、《玉簪记》?”(第23回)
说书人用褒贬的口吻,评价《红楼梦》里少女寄托爱情的小物件,声称何玉凤绝没有宝砚雕弓的姻缘之想:“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珮’,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第26回)他揣度何玉凤的守宫砂知识来自《天雨花》的左仪贞(第28回)。说书人还用一千多字的篇幅,一一对比安家人同贾家人的性情、作为,而后感叹:“世人略常而务怪,厌故而喜新,未免觉得与其看燕北闲人这部腐烂喷饭的《儿女英雄传》小说,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艳谈情的《红楼梦》大文?”(第34回)作者似乎抱着诚实或解嘲的心态提及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所接受的“影响”。
从《儿女英雄传》创作的时机看,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正是文明衰落之时,小说创作缺乏新鲜事迹的刺激。熟极而烂,作者几乎无法做到不重复、不蹈袭。小说对前人作品中的故事、人物和意象,有整段挪借也有零散分拆。如能仁寺救安骥、杀和尚让人想起《水浒传》的清风岭与野猪林;而十三妹、安骥的相遇又让人想起宝黛初会的情形;安骥外出时长姐的金镯子松脱了,说书人拿《西厢记》里“猛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的曲文来调侃并暗示收长姐为妾的情节。这样的情形同早期的说书人也不无相似之处。研究民间口传文学的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洛德(Aibert Lord)在《故事歌手》中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传说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由多个系列的模块式的段落组成,这些段落可以重新组合,以在不同的场景产生出不同的故事。”[15](P81)早期话本的职业化说书人就有一套世代相传的讲述技巧,大到人物、情节小到具体的情景传写,都有固定的套数和言辞。不同于职业说书人,文康对这些模块的运用“自具炉锤,别成异采”[16](P106)。《儿女英雄传》的说书人把人们熟知作品的情节段落作为模块来组装其文本,更多的是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反讽的修辞效果。那些情节和人物的来源是如此的为人熟知,即使经过拆解、变形,仍能使人想到它们的原有的含意,同时文本又使之指向了新的意味。这种挪借有些像诗词中的用典,使情节和人物具有了多重的含意。在小说戏曲受轻视的时代,这种模仿经典形式的引用,有明显的戏谑味道。
三、论事兼论文的评点式叙事
小说“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评点之作用就是“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17]。受八股衡文模式的影响,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评点都是把小说文本当做文章来作结构分析的。
由于《儿女英雄传》叙述层次的错乱,说书人具有了独立于文本的权威。他对小说人物情节的议论,就超出了传统的说书人。第29回说书人说“这部书前半部演到龙凤配合,弓砚双圆。看事迹,已是笔酣墨饱;论文章,毕竟不曾写到安龙媒正传”之后,还读我室书主人董恂批点“叙事之中夹以议论,叙事之首冠以议论,《醒世姻缘》等书往往有之。然彼则论事,此兼论文,现身说法,似因实创,亦庄亦谐,非甘拾人牙慧”。董恂指出了《儿女英雄传》说书人在功能上的提高。按冯镇峦的《读聊斋杂说》总结的评点五大例“一论文,二论事,三考据,四旁证,五游戏”,传统的说书人通常限于故事层面的“论事”,即对情节人物的阐释和判断。其余几项针对叙述过程的议论,位于文本中的说书人或“作书者”就难以胜任。因为“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需要跳出文本之外的旁观角度。
清代小说中有以作书人面目出现的叙述者,如《女仙外史》、《歧路灯》、《九尾龟》、《荡寇志》等,它们也试图在叙事者的“论事”之外,添入些许意见,如无名氏的《海游记》就塑造了作书人的形象:“作书的是谁,乃是个山人,以渔樵为话,不与外人往来,不但年代不知,连自己的姓名都忘了。”晚清邹弢的《海上尘天影》既有作书者的形象,也试图把叙述过程纳入话语之中:“看官,作书的到这个地方,最难下笔,既不便说秋鹤要留,又不能说莲因肯留,仔细一想,还是叫他去罢。”[18]但这里作书人直接出面的讨论创作,已经是西风东渐的影响了,而且似乎还不如说书人将其内化显得更自然灵活些。
在小说评点史上,对文本的修订一直没有停止过,评和改总是相伴而生。但金圣叹、张竹坡们对文本的删改增添之处,并不在文本之中表注出来,文本是相对独立而自足的。创作过程也不在评点之列。《儿女英雄传》因作书人成为一个人物,他的创作是说书人叙述的一部分,因而在故事叙事过程中附加了创作心理的向度。第29回提到张金凤给何玉凤立的长生牌位,说书人称是燕北闲人一时高兴写了这个情节,“不过觉得是新色花样,醒人耳目”,后来难以处置这牌位,“替他(作书人)算算”,“大约那燕北闲人也是收拾不来这一笔,没了招了,掳了汗了,就搜索枯肠,造了这一片漫天的谎话,成了这段赚人的文章!虽是苦了他作书的,却便宜了你我说书的、听书的!”说书人于传统“论事”之外的“论文”,既指向文本也指向创作。文笔的摆布、剪裁的刀尺、构思的工拙都在讨论的范围。说书人有意卖弄破绽,作书人的叙述过程的各种考虑和可能性都呈现在评点式的叙事中,成为情节戏剧化的一部分。
说书人可以把考据放到故事里,如“说书的当日听人演说《儿女英雄传》这桩故事的时候,就考查过杨子《方言》那部书”(第4回);也可指出燕北闲人当日作书时曾考据过朝廷官制;至于旁证和游戏,则更因说书人与作书人的分离而出现了游刃的从容空间。
就评点的见识而言,这位说书人的见解并没有免于拾人牙慧之嫌。他的论文之道不脱明清评点家的文章笔法。如结构上把四十回小说分出四个段落,即“几番结束”,指出各个人物的正传、附传。用八股衡文之法来评点人物行为:“这位安老爷真会作这篇一折一伏、一提一醒的文章:前番话,把十三妹一团盛气折了下去;这番话,却又把他一片雄心提将起来。”(第19回)
在艺术手法上,说书人又以画家画树比喻文章的穿插布置、渲染烘托。“这班人物自开卷第一回直写到上回,才算一一的穿插布置妥帖,自然还须加一番烘托绚染,才完得这一篇造因结果的文章。”(第33回)这也是取自金圣叹、脂砚斋的口吻。因而,《儿女英雄传》中说书人最大的贡献在内化评点这一叙事形式上。
四、重复叙事
重复叙事本是口头文学的重要叙事方式之一。从说话艺术而来的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类似的结构和修辞手法。如民间叙事的“三迭式”或五次、七次事件、情节的重复,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都很普遍[19](P138-141)。但《儿女英雄传》中这种民间文学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说书人的评点看,小说里的重复描述和评价似乎是为了解决说书体小说的线性结构与史传叙事互文散见的矛盾。史传文学中的世家、列传都是以传主为中心展开生平叙事,其他人物的表现和感受通常会放到别处,此即“互文散见”的叙事法。但“互文散见”法比较零碎,不适合说书的要求。戏曲中首先发展的元杂剧也是一人主唱,在事件中只抒发一位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从说书体小说看,情节和事件在紧张之中,说书人的视角随主人公而动,其他人物的情感反应、心理活动难以兼顾。常规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说书的形式更是如此,而事件的发生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只能投射到一条直线上。“说书的只有一张嘴”、“作书的只有一支笔”,即是线性的叙事时间与事件人物的多纬性矛盾。重复叙事用变换的视角和立场来补充故事的细节与层次,能使讲述始终保持线性结构的简洁、流畅。
重复叙事在小说中的作用概括来说有三种:其一是扩大叙事容量,表现不同人物的视角和内心感受。第12回《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孺人姑媳祝侠女》安骥父子团聚,安骥和张金凤将十三妹救命赠金之事分别向安学海夫妇讲述,同于救命之恩,父子、姑媳的视角并不相同,一个感激赠金解厄,一面祝谢连姻之德。说书人议论道:“列公听这回书,不觉得像是把上几回的事又写了一番,有些烦絮拖沓么?”说书人指出这种看似重复的讲述是文章必需的“伏应虚实的结构”,“非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从小说几处大的重复叙事段落看,叙事者所要“找足”的是不同人物的视角、立场和对事件的理解,它增加了事件的丰富性。线性时间的连贯使说书人难以停顿下来,就一个场景中的各个人物心态感受展开细致的描述。重复叙事通过“找足”的方式把其他人物的心理历程和感受呈现出来。如张金凤从第7回到25回,逐回出场,但只是个和她在小说中的地位不相称的背景人物。出于刻画这个人物的考虑,在25回由她出面劝何玉凤嫁给安骥。从她的视角将能仁寺被救以来的经历和心理感受讲述出来。说书人称之为人物的“正传文章”。
其二是如说书人所说的行文所需。为了照顾听众:“要不把这段节目交代明白,这书听着可就没甚么大意味了。”
其三是文章笔法的虚实照应。因为说书人的概念里并无悬念、叙事时间一类小说创作的术语。他以作文法分析小说结构。所谓虚实,有时指小说的悬念或者预叙,说书人按文法称之为“魂魄”。第16回安学海同邓家父女笔谈,商量如何说服十三妹,说书人让听书的不要为这个西洋法子烦躁,称这是伏笔虚文,后文必有实事针锋相对。“把文章的筋脉放在后面去,魂魄提向前头来。”
从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看,古代长篇小说的特点是在时间跨度中显现人事的循环和虚无,是“无—有—无”的循环。《儿女英雄传》出于主题的需要打破了这个结构,缩短了时间的跨度,简化了人物关系,注重宣讲,必然导致情节平衍,因为事件不多,重复叙事似乎不可避免。
古代长篇小说从讲史发展而来,融会了饱经兴废的历史理性和智慧。一般来讲,把时间跨度放得较长的话,事件和人生的大势与本质,小说悲凉的底蕴会自然地显现出来,因而传统的长篇小说都有较长的事态时序。《三国演义》近百年;《水浒传》从仁宗朝嘉祐三年洪太尉误走妖魔到梁山好汉魂聚蓼儿洼的徽宗末年,时间跨度为五六十年;《金瓶梅》从宋徽宗政和间西门庆登场到宋钦宗即位金兵南侵,普静禅师点化众人转世,其时间正好是旧时的“一世”——二十年;《儒林外史》从元末王冕出场到明万历二十二年,南京名士渐渐消磨尽了,从市井中走出几位奇人,跨度更达二百二十多年;《西游记》和《红楼梦》因有神话框架,历时不知几世几劫。这样的时间跨度本身就能显示出人生的渺小、喜乐圆满的不足恃,时间本身构成了主题的悲剧性意蕴和底色。《儿女英雄传》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三两年,事件集中在前半部,后面故事平衍,戏剧性情节不足。这样细写人生的某一阶段的叙事,割断了奇书体小说天人之际、世事循环的大框架。即使是对人生和世事持有怀疑精神的人,也会承认人生中这种阶段性的上升和喜乐精神确乎是可能的。在这个短的时段中,事件的自然时序并没有在话语层次被重新安排,它本身也并没有太多内涵。说书体强调这一直线的简洁、齐整,不枝不蔓,但相应地会牺牲事件中不同人物的视角、体会的立场。这样重复叙事的引进就增加了事件在文本中的分量,人物不同的眼光和立场也为文本叙事带来新的纬度。
如上所论,明代小说的重复叙事较多含有承袭口头文学的成分在内,能在看似松散的、缀段式的情节中起到组织和结构的作用,《儿女英雄传》则似乎是作者主动选择的叙事手段。通过说书人点出的小说的几番“结束”,重复叙事成了叙事节奏与频率的组成部分。“讲述人有才能从这个缺陷(指重复——本文注)中发挥出一种游戏性快感”[20],小说的若干幽默味道正是从这些地方生发出来。
《儿女英雄传》中的说书人和作书人两个角色叙事层次的颠倒,是传统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新探索。评点式叙事使小说扩大了信息容量,使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有机地统一在文本中。这个说书人将小说的创作、评点和传播等功能形象化地整合起来,使作者对小说文本的介入更为从容自然。文康把作书人、听众、书中人物几方关系都交叉在说书人身上,处在多重关系交叉点上的叙述者——说书人,比职业的说书者或者《聊斋》“异史氏曰”那样“论赞式”的叙事者自我呈现,可以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批判干预的能力。
注释:
①李渔称“人间最乐事莫过于填词”,即指作者的自喻性,也是对故事在文本中地位的贬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