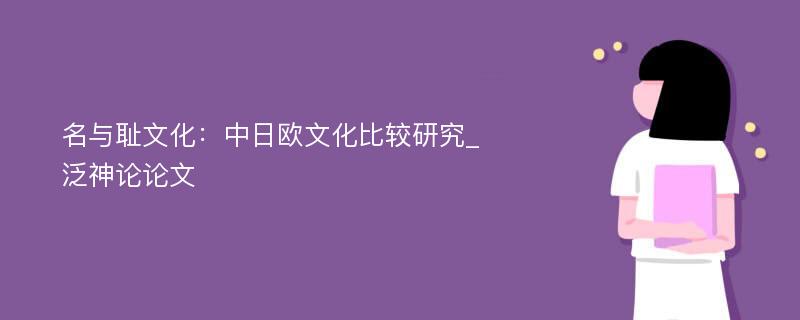
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欧洲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顺洪编译
1 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
看到“名与耻的文化”这个标题,人们马上会想到,它与路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花与刀》提出的问题相关。路丝·本尼迪克特是最近闻名的文化人类学女学者,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了有关日本人心理的调查研究,1946年,其研究成果以《菊花与刀》为书名出版,至今畅销不衰。
该书分析了日本人的性格,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本尼迪克特把世界文化分成了两大类型,即“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就是说,当人做了坏事时,可分成作为“罪”的意识类型和作为“耻”的意识类型的两种不同文化处置方式。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归入“耻的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她谈的纯属大的类型问题,并非认为日本人一点儿罪的意识也没有,西洋人一点儿耻的意识也没有。她指的是罪和耻的意识分别担任主角。迄今为止,反对本尼迪克特观点的几乎还没有,一般人都认为,日本人耻的意识比较强,罪的意识相对薄弱。
本尼迪克特进一步认为,“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从强烈意识到的他人的议论所造成的强制力中产生。”这种观点明显认为,罪的意识是高一等的意识,而像日本人那样,以自己的面子或他人的议论为基础的行为,尚处于道德意识的低级阶段。这种对“耻的文化”的评价,却遭到日本人的反对,所涉及的问题是,“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竟究孰优孰劣?与其相关,日本人耻的意识为什么比罪的意识强烈呢?
我是搞中国思想史的,对日本的某些关键性问题不太清楚,只好以中国的思想史为中心,联系到日本历史来考察。从实际情况看,与日本相比较,中国“耻的文化”倾向更强一些,“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
2 罪意识强的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的情况与今天恰好相反,比起耻的意识来,罪的意识强烈得多。例如,儒教的经典“五经”中,《诗经》和《书经》问世最早。《书经》中相当于“耻”的词出现了10次,而相当于“罪”的词却出现了50次以上,不仅在次数上,就是从内容上看,罪的比重也占优势。还引人注目的是,《书经》里谈到罪的时候,总是与天罚相对应。就是说,在中国,罪的概念本来就意味着“对天神命令的违反”,中国人自古就崇拜天神。
不过,其间也发生过历史的自然变迁。《书经》时代,天神被认为是人格神,具有人一样的意志和感觉。不久,其人格神要素就迅速淡薄了,后来,天神终于转化成了和天理、天道一样被称为理与道的非人格的东西,即理念。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人,当时,天已由人格神被转认为叫作理与道的理念东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呢?这个问题很大,今天仅提出这个事实,不细加论述。
3 泛神论的人世观
最高神天神失却人格,转化为道、理的理念存在,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宗教的变革,也是根本世界观的变革。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大致可分成有神论和泛神论两大类。所谓有神论,例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把神完全作为人格神,而且认为,这样的人格神在万物之上,支配着万物。泛神论的宗教观,虽某些地方残留着人格神的要素,但更多的是道或理的形态(不定形或无形),认为神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即“一草一木皆有神”。属于泛神论类型的宗教有很多,有原始宗教,如萨满教等,还有高级宗教,如佛教等,认为“所有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中国的佛教亦如此,认为“天入人间,住于人间”。住在人间的天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的天性、人性。反言之,所谓人间的天性,就是进入人间的天。
孟子提倡“性善说”很有名,他的观点是从泛神论得出的必然结论。也就是说,人性是进入人世间的天,除了善以外没有其他。孟子的性善论一直作为儒教的正统思想被继承。朱子学和阳明学等,亦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孔孟儒教观与基督教那样的属于有神论类型,认为人虽生在人间却本来背负着重罪的厌世主义的宗教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教的人世观是乐观主义的。
4 儒教的泛神论产生无神论
泛神论的宗教观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结果,那就是无神论倾向的出现。
实际上,同是泛神论,却含有两种类型。泛神论虽都认为“神在世界之中”,却有“神在世界之上”和“神在世界之中”的区别,前者把重点放在“神”上,后者把重点放在“世界”上。比如,在西洋哲学中,确立了最典型的泛神论体系的斯宾诺莎,同属泛神论,他强调的是神,即“神在世界之上”,从而成为“接近有神论的泛神论”。然而,就连斯宾诺莎这样的泛神论,也受到了来自正统基督教的“那是无神论”的强烈责难,更何况像“神在世界之中”那样,把重点放在世界上的泛神论呢!于是,不久便从中产生了无神论,进而发展到唯物论。
那么,儒教的泛神论属于哪一种呢?它应属于“接近无神论的泛神论”。第一,孔子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无神论者。“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意思是说,对鬼神敬而远之,才是知者应有的态度。孔子病时,弟子问:“向神祈祷您病愈吗?”孔子说:“丘早已祈祷过了”,委婉加以拒绝。他认为,如果一生做好事,“即使不祈祷神也会受到保护”,因而,没有特别依赖神的必要。在这一点上,荀子更彻底,他明确指出:“所谓祭神,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愚民欲求的一种仪式的演出,君子不相信神的存在。”
这种无神论的传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根很深。曾亲自为中国命“中华民国”国号的革命家、学者章炳麟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泛神论者,而泛神论即无神论的逊词。”这句话,实际上是无神论的变相说法。
5 中国的耻——道德的根本
兜了半天圈子,我们再回到罪的意识问题上来。前面说过,“所谓罪,是违反神的命令的意识。”这种罪的意识是典型的宗教性意识。那么,对无神论的强烈倾向如何看呢?可以说,它与对应于神的罪意识不相同,它是对应于人或世间的耻的强烈意识。关于这一点,若把《书经》和《论语》相比较,会非常清楚。
如前所述,在天神信仰观念很强的《书经》中,罪的意识占压倒优势。在《论语》中情况则相反,“罪”一词只出现过三次,而“耻”一词不仅频繁出现,而且意义重要。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篇》)意思是说,如果用权力和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虽暂时免于犯罪,但其意识中只想着如何顺利地逃脱法律,却没有羞耻之心。相反,如果用道德和礼仪来治理百姓,百姓会有羞耻之心,并能走入正路。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把耻作为内在的,并从内在表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在这方面,后于孔子的孟子,与孔子完全一样。孟子提倡有名的“四端说”,其中讲到:“羞耻之心,义之端也。”就是说,耻于并憎恨恶事之心,是正义道德之基础。孔孟从以上思维方法,产生了“礼义廉耻”四德思想,成为立国的四大支柱。关于中国把耻意识作为道德的根本,清朝的大儒阎若琚也说过:“耻乃根于心之大德也。”
由此看来,中国人对耻的看法,与本尼迪克特相反。本尼迪克特认为,“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因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外在压力而产生。”中国人却认为,“耻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本尼迪克特从内在和外在上区别罪与耻,似乎有些牵强。我认为,把罪看做是对应于神的、宗教的意识,把耻看做是对人世的、社会的意识,较为正确。
在基督教有神论有力支配的欧美,罪的意识成为道德的基础。在泛神论及无神论支配的中国与日本,耻的意识成为道德的基础。
6 在泛神论中,罪意识失去了道德意义
下边考察一下泛神论、无神论倾向强的地方,如何认识罪的意识。
《书经》时代,即信仰天神最盛的时代,中国人同样具有很强的罪意识。
到了孔子时代,由于进入近乎无宗教的状态,罪所具有的宗教意识开始消失,它渐被认为只是刑罚的对象。这种变为刑罚和法律对象的罪的意识,已不具备成为道德意识基础的资格。
本来,法律是强制性的东西,强制性的东西便称不上道德。在满员的电车中,自发地为老人让座是道德行为,假如法律规定“不为老人让座者罚钱”,那么,让座的行为便成了合法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正如孔子说的,用权力和刑罚治理百姓,道德就没有了,总是考虑如何逃避法律,也就失掉了羞耻之心。正因如此,孔子以后的中国,罪成了刑罚的对象,失去了道德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与欧洲人罪的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和中国,罪只有一种说法。而英语有两种,作为法律对象的罪,即犯罪,叫做Crime Guilt;具有宗教意义的罪,叫做Sin 。在日本和中国没有这样的区别。古代大概是Sin的倾向比较强,后来发展为只用Crime Guilt的意思。
再看一看日本古代的情况。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罪”一词大量出现,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本人罪的意识很强。
同样称为罪的意识,神道和基督教情况则大不相同。神道意义上的罪,似乎是近于污秽、不洁的东西,它被认为不是人内在的东西,而是从外部来的如灰尘和脏物一样的东西。神主好像赶灰尘一样在人们头上掸,“赶跑吧,清除掉吧!”于是,轻轻地给赶跑了。如此乐观的人世观,与基督教黑暗的严酷的原罪观,性质完全不同,它不能不被归入到泛神论的系列。
本来,连欧洲和美国,基督教也在渐渐衰落。本尼迪克特说:“在美国,耻的比重有迅速扩大的倾向,罪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令人强烈感受到了。在那里,这种现象被认为是道德的堕落。”假如宗教意识的后退,进而罪意识的后退,是意味着道德堕落的话,那么应该说,日本和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堕落了。
鉴于上述,可以认为,日本和中国被归于“耻的文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站在泛神论的立场,尤其是站在“近乎于无神论的泛神论”的立场上的事实被找到了。
7 政治形态与耻的内容
在日本和中国,虽同属于“耻的文化”,但耻的内容有微妙的差别。日本从古代就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很大影响,尤其是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御用学问,影响更为深刻。尽管如此,日本与中国之间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不同从哪里产生呢?那就是两国政治体制根本不同。日本仅在一百年前,还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形式完备的封建制国家。而中国呢?早在两千几百年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就废除了原来的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这和明治维新政府断然实行的废藩置县,是完全一样的。两千数百年来,经过了多少历史变迁,它采用的政治形态是:上边一个天子,下边官吏大夫(不是世袭的,限于一代,通过考试从民间录取),再下边是庶民。它没有日本大名、武士一类的世袭阶级,具有与分封制完全不同的社会构成。
近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普及的结果之一,就是流行起了全用封建主义一词概括近代以前历史的观点,把民国以前的中国统称为封建社会。这样一来,中国、日本就都成了封建国家,而他们之间的区别,很难得到充分的说明。当然,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中国式结构的社会叫做家产制,认为其产生了与封建制不同文化的也有。
总之,在日本与中国,由于存在着封建制有无的不同,产生了互不相同的思维方法和广泛的文化,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现在要说的问题是,耻意识的不同,亦是因社会构成的不同而产生的。
8 日本人的名誉心
日本人耻的概念有什么特性呢?这个问题,从外表,即名、名誉的特性说起,可能比较清楚。
马克斯·韦伯把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分成许多类型,分别指出它们的特征。其中,把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列入了个别的类型。韦伯认为,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支撑这两个封建制度的精神阵地,都是武士的忠诚心、忠义和名誉心。
通常,忠诚、忠义和名誉难以两立,忠诚是对国家与君主的自我献身,以自我否定为基础,而名誉是以自我扩张为基础,二者完全相反。因而,在许多封建制度中,是只有忠诚心呢?还是只有名誉心呢?二者只居其一。然而,韦伯在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找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并不矛盾地共存在一起的方面。他得出结论认为:忠诚心、忠义是一种道德,名誉心也是一种道德。
如今,一般情况下,名誉被很多人认为是具有反道德影响的词,是应鄙视的东西。然而,在欧洲和日本的封建时代,重视武士名誉和忠诚心,都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如今已成为很好的古典著作。在该书中,新渡户稻造强调,严守忠义和名誉是日本武士道的中心道德。同时还讲到,武士道和西洋中世纪的骑士道精神完全一致。真若如此,封建时代武士的名誉,就成了构成那一时代本质的一种重要道德。而我们今天所具有的名誉观念,即只以被社会高度评价为内容的名誉观念,与其有本质的不同。以英语为例,名誉Honour和Fame的区别,两个当中,Honour还残留着中世纪骑士道的传统,Fame好像只是被世界承认(reknown)的意思。
然而,假如这种封建时代的名誉具有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其反面的耻,即名誉不好,从负的方面说,自然也是属于道德的东西。所以,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耻是对于他人的、社会的意识,是脸面意识,不具有道德价值”,是把并非一回事的羞耻,与中世纪骑士道的不体面等同起来了。因为,本尼迪克特毕竟是美国人,没有接受像欧洲人那样的中世纪传统。
9 中国人的名誉心——面子
中国在两千年以前分封制就没有了,不存在像日本和欧洲那样的武士阶段。即使有一部分职业军人,也没有力量使中国文化和思想受其影响。在那里,取代武士成为文化和思想中心的,是具备文学教养的官吏阶级。因此,在耻的意识方面产生了与日本不相同的东西,并非不可思议。
秦始皇以前,中国也有分封制,从孔子和孟子活跃的春秋战国看,与武士道的名誉观念非常相近的例子,也是有的。到了秦始皇以后的统一王朝时代,出现了韦伯所说的家长制官僚国家的特征,分封制度的名誉观念消失了,文人官僚特有的名誉观念产生了。所谓文人官僚特有的名誉观念,简言之,就是在体面、脸面意义上的名誉,即面子意识。面子就是颜(脸),颜是人体对社会议论最敏感的部分,“ぃぃ颜をする”(高兴)、“得意颜になる”(得意)等许多日语中都有“颜”字。人非常害羞的时候,“颜が赤くなる”(脸红),清楚地说明了有其生理基础。
中国非常强烈的面子意识,与西洋的荣誉观念大不相同。有一位在美国定居,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人的随笔,为美国人所熟知的人,名字叫林语堂。他在《吾土吾民》中,这样说过面子问题:
面子这个词,很难翻译出它的准确定义,把面子和西洋的名誉、荣誉混为一谈,是可悲的错误。在西洋,被他人打了脸不能提出决斗的男子,失掉了荣誉,但并不等于失掉了面子。在中国,不给他人面子是最失礼的事,就如同西洋人把手套扔给对方,挑起决斗一样。在中国,有无数人因失掉面子而走向自杀,有时候甚至发展到出现打倒政府的罕见的大事件。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那么,面子和荣誉心有哪些区别呢?如前所说,荣誉心是从作为封建时代的骑士道精神发展而来的道德意识,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作为武人的品格、尊严意识”。本来,在西洋,从古远的封建时代开始,荣誉的武人特征就已淡弱了。但是,荣誉心的本质,即“个人尊严意识”、“威严意识”,还相当程度地保留着。而中国,从封建时代开始,已经过两千年,荣誉的要素已经消失,替代其的是面子意识的发达。这个面子的本质,就是“朝向社会的脸”,所谓“面子好”,英语的意思,可以说是“有声望”。这一意思,如果用本尼迪克特式的语言表达,不正可以说“荣誉是内在的品格的意识,面子是以社会的、即外在品格为中心的意识”吗?
10 武士的名誉心
我们重新回到日本人问题上来。日本人的名誉意识,与西洋的荣誉意识、中国的面子意识相比,应怎样认识呢?
刚才提到的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说:“所谓武士的名誉,就是人格的尊严及价值的意识。”他认为,名誉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意识。但是,新渡户后来以日本人为对象写的东西中(例如《修养》),认识就大不一样了。比如他说:
欧洲的Honour(荣誉)一词,在我国不含有名、名誉的意识。英语的Honour(荣誉)是从Honesr(正直)来的。德语的“埃依莱”一词,是从“埃依路里兹非”(正直)来的。“埃依路哈佛特”的意思,是“有价值于名誉的正直”。这样,对于声誉来说,被人赞誉与否,便成了第二位的了,而反省自己对与否,却成了根本性的东西。在日本,这样的思想不是没有,从名誉一词的构成考虑,所谓声誉,是把标准放在了自身之外,而把他人和社会的评价作为衡量的标准。
新渡户认为,封建时代武士的名誉感,是高尚的道德。但是,尔后的日本,名誉并未被认为是内在的自觉的品格,而是外在的“社会的好评”。用英语来说,声誉一词比荣誉更为接近它的意思。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言而喻,根本原因是远离了封建时代。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原因。第一、封建武士的名誉、荣誉,本身就是声誉的要素。第二,还受到儒教重视声誉的影响。
封建时代最初的名誉,把内在的自觉的道德,即武勇和正义作为本质,毋庸说,其中也包含一些声誉、名誉的要素。例如,把跑得最快、最先抵达终点作为一种名誉,其中就有和他人竞争的意识。在势众的敌人面前自报姓名,本身就表现出了武士的名誉心,想让世人知道自己的荣誉的要素。
还有一点,受儒教的影响也相当大。在德川幕府时代,儒教是御用学问,具有贴近封建道德的一面,比如强调对君主的忠诚、忠义,但并不教导日本武士的名誉意识。
原来,儒教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意识比较强,非常轻视武,所以未产产武士的荣誉观念,反而非常重视名声、评价的意义。《论语》中有这样的的句子:“君子嫉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子罕篇》)意思是说,在世上得不到名声,是对社会没有价值的证据。儒教这种尊重名声的思想,在《孝经》的一个句子中达到了顶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为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行最重要的内容,是立身出世,扬名后世,使父母广为人间所知。按《孝经》来做,真正孝敬父母的话,当了总理大臣,得了诺贝尔奖,成了大名,都应让世间知道父母的名字。
接受了这种儒教教育的江户时代武士,在原来荣誉心之外,又加上了名誉的要素,是难于避免的。比如,在重要比赛上取得胜利,脸上光彩大增时,所谓“提高社会评价”的名声要素总会增加。因为在这种武士的名誉中,已加入了名声的要素,所以,封建制度已经消失的今天的日本,正像新渡户所提出的,在名誉一词中,名声、荣誉的要素增强了。
与名誉观念相反,今之日本人耻的观念,是关于社会对己坏的评价的意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耻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以这种耻意识为基础行动的日本人,是“由于外在的强制力而从事善行”。当然,日本人并非把耻的意识作为全部道德行为的基础,根据善与恶的判断决定行动的,也并不稀少。但事实上,只是在不可抗拒地陷入恶的情况下,才具有比罪的意识更多的耻的意识。
11 宗教的意识(罪)与社会的意识(耻)
“罪的文化”与“耻的文化”的对立,将继续到什么时候?如最初所说,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是内在的道德意识”,“耻是从外面施加的强制的意识”。不言而喻,这种解释是把罪的意识置于上位。日本人孩子时被错误地管教,是因为特别注重“社会的评议”。由于修改了教育法,日本人似乎也有了罪的意识。
在这一点上,新渡户稻造的思考方法和本尼迪克特是一样的。新渡户在《处世之道》一书中,说了以下的意思:
罪的观念和耻的观念,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屡次听到“日本人没有罪的观念”的批评。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事实。的确,日本人罪的观念,也许没有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那么强。可是,连佛教和神教也宣传罪的存在,虽说它们与基督教所说的罪多少有些差别,但总是不能否定有罪的观念。因此,尽管修养方法不同,但不是也能发挥同基督教大力宣传罪的观念一样的力量吗?
新渡户思路如此开阔,根源在于他是基督教信徒,承认罪的意识比耻的意识有更高的价值。的确,作为一般的倾向,根源于基督教的罪意识,比起耻意识来,更内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这还具有相对的流动性。比如,在基督教信徒中,也有人接受了“神在自己之外监视着自己”的观点。那种情况下,“神眼”的光射在自己的身上,罪有成为外在意识的可能性。反之,“注意着世间之眼”的耻意识,根据情况也可变成非常内在的东西。
比如,耻的意识非常强的中国,有所谓的“四知”说,那是在后汉杨震有名的故事中出现的。有一个人去杨震处行贿,被杨震拒绝了。贿赂的人说:“这是夜里的事情,不是没人知道吗!”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孟子还说过“仰俯不耻于天地”,现代汉语中也有“不愧于良心”的说法,它们都可以说是耻内在化的例子。
由此看来,所谓罪是内在的意识,耻是外在的意识,不能一概而论。而罪的意识具有道德价值,耻的意识不具备道德价值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罪是对神的意识,耻是对人的意识。换言之,罪是宗教的意识,耻是社会的意识。
12 世俗化(脱宗教)的世界史的趋势
当今世界上,最脱却宗教的民族,日本和中国可以说是双璧。在欧洲和美国,宗教正在衰落,但基督教还根深蒂固。属于回教圈的地方,更强的信仰还在继续。我从报纸刊登的旅行记中,看到这样一件事:飞机在伊朗、土耳其上空飞翔,突然,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离开了机械,平伏在操纵室的地上开始祈祷。为什么呢?据说是回教徒的“祈祷时间”到了。因为飞机有自动操纵装置,所以安全没关系。这种事情,作为日本人来说,很难理解。
像爱尔兰那样的宗教战争,历来就有。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战争,也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对立意识。在这些宗教信仰强的地方,仍是由罪的意识所支配着。那么,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说,也是属于不信佛的日本和中国,当然是应该属于“耻的文化”圈了。
现实情况是,即使欧洲和美国,基督教的信仰也在逐渐淡薄。尼采呼喊“神死了!”已过去近一百年了,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是很自然的。本尼迪克特也这样说:“在美国,耻的比重有迅速增大的倾向,而罪的意识已感觉不到像以前那样强烈了。”
假如非宗教化、脱宗教化是世界史上的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必须承认,世界正从“罪的文化”向“耻的文化”转移。这种情况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另当别论。而日本与古中国,在“耻的文化”这一点上,似乎成了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注:本文的副标题及小标题号码系编译者所加
标签:泛神论论文; 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