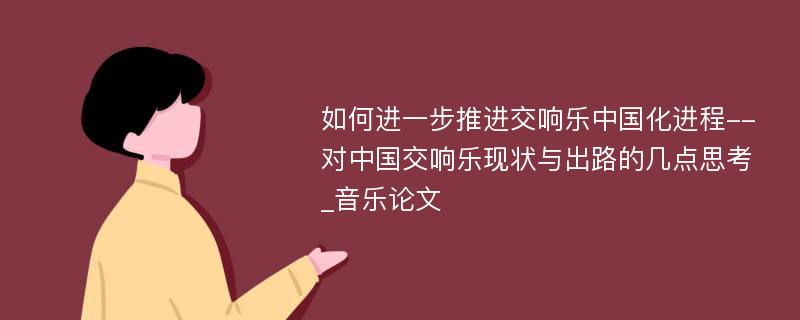
交响乐的中国化进程如何进一步推进——对中国交响音乐现状和出路的几则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响音乐论文,交响乐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历史和五代人的努力
中国交响乐从黄自先生1929年在美国创作交响序曲《怀旧》以来,已经整整走过70个年头。在这70年中,经过了数代音乐家的努力,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才算进入到了“正式议程”。尤其是在第五代作曲家们的革命性引发之后,它的势头就变得更加的强劲了,它的力度也大大增加。诚然,“五代人”的说法,几乎为当今音乐界许多人士所共识。我的估计,之所以如是“断代”,主要是以相应的年龄作为计量依据,或者是把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作为划分背景,即:第一代指萧友梅、黄自辈,第二代指贺绿汀、马思聪、江定仙、江文也辈,第三代指朱践耳、罗忠镕、吴祖强、杜鸣心辈,第四代指王西麟、杨立青辈,第五代指谭盾、瞿小松、叶小钢、郭文景、陈其钢、许舒亚辈。
无疑,交响乐作为一个纯粹从西方引进的外来音乐体裁,对中国人的音乐文化传统来说,是全然陌生的。然而,在走过了这数十年的历程之后,尤其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来说,已然除去了以往的那种隔阂,人们对这样一种有着相当哲理意味并足以容纳重大主题和多种情调的体裁,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可,并通过它也能或多或少实现自己的审美需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过数代中国音乐家的长期积累之后,交响乐的“中国化”问题也已经有所凸现,甚至,已纳入到这一体裁未来发展的议程当中。作为历史,毋庸讳言,中国人在运用这一纯粹外来的体裁进行创作的时候,难免要经历从“抄袭”到“模仿”再到“移植”,以至进入相对自觉的“创新”,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如果说,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大规模大面积的影响,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是西方传统音乐冲击中国传统音乐;那么,第二次就是发生在八十年代,是西方现代音乐冲击中国新音乐。在此两次影响和冲击当中,中国音乐家以其罕见的方式,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就把西方音乐的基本观念和各类技法都“拿”了过来。在第一次以后,仅仅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就搬动了西方传统音乐的数百年成果。在第二次以后,又是仅仅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就搬动了西方现代音乐的数十年成果。然而,在这数十年当中,最最耀眼的一道风景,无疑是八十年代“新潮音乐”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老中青“三代同堂”共同作业的,更加令世人感叹不已的壮丽景观。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和相应的“库存”
可以肯定的是,与70年前相比,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不仅已经走出了“描红”的阶段,而且,可以说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和相应的“库存”。再加上它的国际影响,一批作曲家接受国际委约,并参加音乐节活动,或者他们的作品在世界上获得奖项,比如,1989年留法作曲家陈其钢接受“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文化工程”委约;1990 年朱践耳《第四交响曲》荣获瑞士第16 届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 1991年留美作曲家周龙《禅》在法国d'Avray 第五届国际作曲比赛荣获首奖;1992年留法作曲家许舒亚《夕阳·水晶》荣获法国第五届国际交响乐作曲比赛大奖,并被定为下一年贝藏松国际指挥比赛决赛必选曲目;1993年留美作曲家谭盾荣获美国当年度表演艺术最杰出作曲奖;1998年留法作曲家陈其钢担任第九届贝藏松国际作曲大赛评委会主席;以及多名中国作曲家多次参加国际新音乐节,集中展示他们的新作品等等。除此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影响的国际认可,已不再是五六十年代曲调中所包含的民族特色,或者仅仅是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东方传奇,真正的标示在于:有了一种属于中国的方式。尽管,这一点目前似乎还不可能给出足够的数量依据,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显然的,几乎在时下每一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有别于西方音乐作品的痕迹,那就是在音响结构中所有意无意给出的一种特殊“声律”,具体而言,就是一种更加自由化的“声象”和一种更加散文化的“律动”。对此,不妨在作曲家的作品中举出几例。前不久刚刚由中国交响乐团首演的朱践耳《第九交响曲》,其中,有一个总是处在乐曲关键部位的角色,一把大提琴以深沉而充满叹吟的咏叙述说,就像是一个时间老人娓娓道来,不断轮回着的历史长序,作为主导动机而贯通全曲,而这种带有咏叙性的线性形态,其不断揉挫的“腔韵”给出的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节律,其润涩交替的“色相”给出的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和音。与此相仿的另一个具重大题材意义的作品谭盾《交响曲1997——天地人》,也是用一把大提琴贯穿全曲,而其“声律”的自由散漫,同样具有中国的风采。还有王西麟《第三交响曲》,其第一主题是一个典型的意义陈述,在极其窄小的缝隙当中,蠕动的“躯体”无尽地伸展,其低音像一条“通轴”贯穿始终,而在它的周围就像是无数“枯藤”盘旋,通过二分钟的时间而撑开一个庞大的音响空间,粘连不断,又包含太多太多的人文情怀。此外,陈其钢《逝去的时光》,则有一种飞扬的舞动和宁静的荡漾;瞿小松《Mong Dong》,将语调、音腔、律动、声象作综合结构, 虽然没有在“世界”话语当中,却以“地方性”取胜;叶小钢《地平线》,将特定的藏民族音调和普通管弦乐语言互动,并在整体调性框架当中,寻求局部音位的曲张和变节;郭文景《蜀道难》,通过夸张的地域性极强的方言语调和极具风格的川剧高腔,以求极端“音腔行态”,并依此撑开音响空间;杨立青二胡与管弦乐队《悲歌》,尽管其曲调底盘(以民间管子曲《江河水》为结构原型)为传统本身,但十分明显,二胡音响在此再创之中有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大大扩展了二胡在音响质料上的某些空间,甚至有极限的扩张,而这种扩展和扩张本身,就是对传统程式和规则的一种突破。
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交响乐创作和演出市场
通过以上个例,可见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作曲家的探索、奋斗,中国交响乐已开始显现业绩。今天,如何使交响乐的中国进程更加实在地得以推进?作曲家王西麟曾经用“本体化”这个术语来进行表述。他认为,一部交响乐的历史,就是一部交响乐作品乃至作曲家的历史,因此,要想真正实现交响乐的“本体化”,出路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演出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进而,他之所以发出如此忧思的合理性,就在于:我们确实缺少一个由创作到演奏,到录音,到出版唱片和乐谱,再到传播,通过国际交流而介绍和弘扬中国音乐文化,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交响音乐文化的社会机制。平心而论,这样的机制要真正建立乃至顺利运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它也会像交响乐事业在中国一样,需要数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眼下最可有所作为的是,先把创作和演奏的环链接续起来,并使之经常化乃至制度化。当然,光是这一环链的问题就很多,比如:在演出方面,中国作品上演率低,接受群体的比例大大小于西方古典音乐;国外乐团来华演出基本不演中国曲目,至多在返场中有一个点缀,等等。在创作方面,驻团专业作曲寥寥无几,专题委约极少,征集作品限制过多,等等。另外,也缺少可良性循环的音乐批评,学者的参与空间几乎没有。除此之外,我觉得,在此前提下,还存在着更具长远危机的问题,比如,目前几乎全国所有的交响乐团,所保留的曲目过分单一,连西方经典的现代作品都非常少,更别说中国当代作品了。长此下去,不仅没有新音响经验的积累,就连原有的音响经验也会老化。于是,古典传统作品就成了“首选”,甚至“独选”,库存量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还会面临不断的萎缩。而有些作品的重复率又过高,包括个别中国作品。虽然不乏音乐会效果,甚至会得到外国人的青睐,但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法上,已有“老龄化”之嫌,至少,不会再入主流。在这一点上,我也有这样一个忠告:千万不要低估现阶段的音响受众的听赏水平,即使是业余爱乐者,其职业化音乐趣味的迅速上升,也是不能无视的。尤其,随着大量音响制品以及高技术视听设备的迅速发展,通过这一途径造就出来的爱乐者,将会对音乐厅现场展示提出最尖锐的挑战。至于说,创作与演奏的环链如何接续的问题,一个比较现实而可行的做法,就是通过一个中介机构,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间的,包括出题、筹资。出题方面,可以有主流性的倡导,也可以有学术性的引导;筹资方面,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可以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确定买方卖方,一旦成交,除了规定演出方式次数之外,还可以根据条件录制音响,但至少,必须要有著作权益的落实。总而言之,就是要形成一个交响乐创作与演出的“市场”,虽然不可能即刻上马,但一旦成型并坚持下去,前景将是非常可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