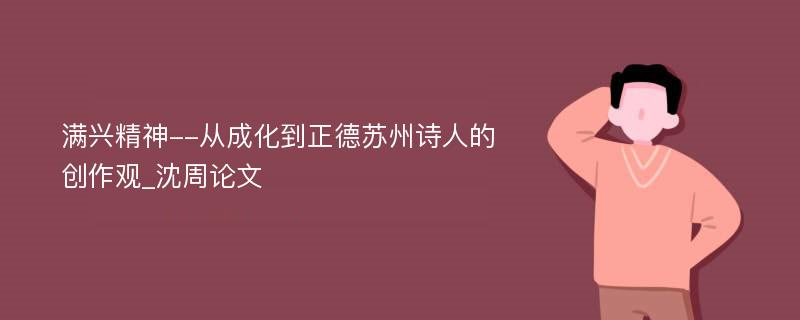
漫兴精神——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创作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至正论文,成化论文,苏州论文,诗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弘治五年(1492),苏州文苑领袖沈周在《跋杨君谦所题拙画》中写道:“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天下事专志则精,岂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并当号予为漫叟可矣。”① “漫兴”一词,并非沈周独创。早在唐代,杜甫即以此为题写下七绝组诗九首。他这“漫兴”,有“兴之所到,率然而成”之意②。杜甫之后,该词便为历代文人所常用。系以这一题目的诗歌,多在内容与形式上比较自由,具有一挥而就的特征。从逻辑上讲,漫兴,当是“兴”的下位范畴,显然没有脱离“兴”涵义中的“感发”这一要旨。它与“兴来每独往”之“兴”相近,是指心物适然相逢产生的审美心理。而值得注意的是,漫,含任意而行、不受羁勒之义。这样,比之与其意义相近的“感兴”,漫兴一词又无疑格外强调了“兴”的开放活泼、自由随意的表现样态。回到沈周处。既然他自称“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那么在他这里,漫兴无疑是被用来指称创作观念的;其要义,当在于创作的灵动自由、不受羁勒。
为什么对这一提法如此关注?因为考诸史实,可以发现,所谓漫兴精神,不仅是沈周的夫子自道,而且也是典型体现在成化至正德间整个苏州诗人③ 群体中的。近年来,学界对这一地域性创作群体已关注渐多,也普遍将其认定为独立于茶陵派、“前七子”之外的诗歌流派。然而,如何相对准确地把握该群体的典型创作观念,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某个文学群体之所以能够不为同时代其他流派所湮没,主要原因,自然在于其拥有某种卓然自立的文学精神。而如果缺乏对苏州诗人相关问题的明确辨析,那么我们对其“卓然自立”价值的认定,就终归缺乏说服力。把握住“漫兴精神”这一要点,我们不仅可能看清苏州诗人在成化至正德诗界中的独特价值,也会对明诗在成化至正德这一新变期内的整体演化特征,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沈周以漫兴指称自己的创作观念,绝非信口言之。从有关其诗歌活动的诸多事实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自我概括,是相当准确的。怎样理解沈周诗歌活动中的漫兴精神?我们不妨先引文徵明相关评述于下:
其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所拟莫不合作。然其缘情随物,因物赋形,开阖变化,纵横百出,初不拘拘乎一体之长。④
时至明代,中国古代诗歌形式风格的几种基本风貌已全面确立。此时诗人的创作,很难完全独立于既有审美传统之外。不过,选择怎样的传统,却能够折射出其创作观念的某些重要特征。从文徵明的分析可见,面对先贤遗产,沈周表现出对白居易、陆游诗的偏爱。而我们知道,这一脉诗的基本精神是明白流利、自然晓畅,不主张过分拉大诗歌语言与生活语言的距离,也不刻意强调格法。当然,以宗主汉魏盛唐的古典诗歌审美原则评判,上述特征无疑常有“流易”、“浅俗”之嫌。不过,因为在形式、语汇上的限制相对较少,这种写作方法也往往更有利于对自我情感的真率表达。就此而论,沈周上追白、陆,似乎已隐约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他喜爱一种不受古典诗歌美学范式束缚的、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而紧接下来我们便看到,在追溯沈周所承传统后,文徵明果然又有了“然其缘情随物……初不拘拘乎一体之长”这样更重要的补充说明。看来在他眼中,仿效白、陆,尚不能概括沈周的创作精神;缘情而发、随意挥洒、不受既有体格束缚,才是其诗歌最为重要的品格。归根结底,这一品格,其实正是沈周自称的“漫兴”。在为沈周《落花诗》所作跋语中,文徵明又重申了这种观点:
(沈周诗)兴之所至,触物而成,盖莫知其所以始,而亦莫得究其所以终。其积累而成,至于十于百,固非先生之初意也,而传不传又何庸心哉?惟其无所用心,是以不觉其言之出而工也。而其传也,又奚厌其多耶?⑤
在他眼中,本着“无所用心”之情怀,随自由不羁的“兴”(这当然即是沈周所谓漫兴)支配的创作活动,足以使沈周获得充分的愉悦;而其佳作的产生,也自是顺理成章了。后来四库馆臣的判断,倒是与此颇为近似的:“(沈周)诗亦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兴于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其于诗也,亦可谓教外别传矣。”⑥ 不过想要真正了解沈周的漫兴,仅凭上面这些评述性文字,仍远远不够。我们不妨具体地探究他在创作实践中显出的典型特征。这,恐怕是其创作观念最直接、最鲜活的表露。进入沈周诗歌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这里,姑按不同诗体分别讨论。我们可先举其《咏钱》为例:
扁扁团团铜作胎,能贫能富亦神哉!有堪使鬼原非谬,无任呼兄亦不来。总尔苞苴莫漫臭,终然扑满要遭搥。寒儒也办生涯地,四壁春苔绿万枚。⑦
成化、弘治以降,复古派日渐成熟,他们以盛唐七律为该体“正典”的观念也产生着广泛影响。但可以看出,沈周此诗,仍以传达自由的情趣为要,且并不以语体的典雅化为用功方向⑧。与此相似,在他的其他七律中,重情趣、不讲工致、不涉安排的句子也随处可见,如《咏帘子》中的“外面令人倍惆怅,里头容眼自分明”,《咏杨花》中的“扑面吹衣雪点晴,乱纷纷地亚夫营”等等⑨,均是显例。他作于晚年的七律组诗《落花》三十首,则将这类风貌表现得同样鲜明。而对于他来说,以体制短小的绝句表现即兴的诗情,是比律诗还要方便得多的。他所写绝句,有不少是亲切随意,而情韵自在其中的佳作。如《墨牡丹》,既像一位游心艺事的老者随口吟成的平易之辞,又自然地流露出高远的人格精神来:“老矣东风白发翁,怕拈粉白与脂红。洛阳三月春消息,在我浓烟淡墨中。”⑩ 还有一类,便是《和吴匏庵所题拙画诗韵》这样的直白随意之作:“城里人人要写山,扁舟一系即忘还。从渠楮笔忙终日,城外看山他自闲。”(11) 与这种写法相似的,尚有七绝《闻杨君谦致仕赋此以致健羡》十五首等。而像其七绝组诗《次韵天台陈勉卖痴呆八绝》这类作品,就已是不顾审美意蕴,只径把随兴而来的打趣之语形诸笔墨,便告终篇。姑举其中一例:“只恁多呆只恁痴,惺头个个好男儿。疾行快走皆先去,风雨来时却着谁?”(12)
比之近体律绝,古体诗篇幅、格律都较自由,所以也为抒情、叙事提供了相对宽裕的空间。在这一体裁中,沈周的漫兴,便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抒发机会。如《伤阿同》:“阿同年十四,蓬垢身短小……今年忽患痘,头面见稍稍。周身渐稠密,匝肉无空道。色白浆不成,识者谓难保。怆惶十三朝,焦黑如火燎……”(13) 写这首诗,沈周似乎没有对素材进行审美提炼的意图;将阿同患病的形貌用自然主义手法叙出,尤显有失雅道。不过也由此可见,作诗时,他只以说尽心中哀恸为目的,别无追求审美效果完满这一愿望。而自由叙写,不作篇章结构、修辞等方面的考虑,正是沈周很多古诗的共同特点。举例来说,他的《送三妹归吴氏》、《哭亲》以及吟咏农村生活之辛酸的《春雪歌》、《低田妇》、《十八邻》、《苦雨》、《淫雨》等等,在表现理念上均与上面的《伤阿同》相似。它们不以浑朴高古的格调取胜,而是在质实、直白中见真情。当然,他的古诗所表现的情感,不只是忧伤,更有快乐。这类作品,便往往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显得通俗活泼、充满情趣。像《经尚湖望虞山》:
日午放舡湖上头,虞山随船走不休。高云仰见出翠壁,飞影下接沧波流。青林人家隐山麓,鸡鸣犬吠闻中洲。鸬鹚群栖竹叶暗,蜻蜓特立荷花秋。采莲还歌采莲曲,落景在树犹堪游。小舟争渡各先去,独逆风波浑不忧。(14)
整首诗不过是将整个下午的所见所闻一气流走地铺写出来。它的音调虽然缺少宛转回环、一唱三叹之美,但到底不失爽利上口;描写尽管每失浅直,不过每一句中的景物,却也都生机勃勃。全篇读下,只觉鲜活的气息扑面而至。在这里,沈周的目的,恐怕正是要用诗笔率真地传达他盎然的游兴吧。而《戏陈天用索画》,便另有特点了:“溪山本是纸上影,崔嵬在我胸中储。从人所好或吐出,向纸看有摩挲无。三郎不来拜汝姑,乞画却恼姑之夫。况是长卷费手力,雨气迷眼兼模糊……”(15) 这里的诗句,似乎是截取日常交谈中的一段口语略加整饬而成。它是浅俗的,又是活泼风趣的。它取消了庄重与客套,把对晚辈亲戚善意的嗔怪,表现得多么亲切。而其《九月无菊》的风调,似乎便是开唐寅《桃花庵歌》之先河了:“今日九月九,无菊且饮酒。明年九月九,有菊亦饮酒。有花还问酒有无,有酒不论花无有。好花难开好时节,好酒难逢好亲友……”(16)
到了乐府类作品中,他这种自在随意的写作特点,便表现得愈加鲜明。下面这首《牧童谣》,单就其形式风格来看,仿佛真就是骑在牛背上的小童随口唱出的歌曲:“朝放牛,暮放牛,朝朝暮暮牛放收。骑牛吃草抱牛睡,牛若渡水我亦泅。牛东信东西信西,我弗强牛牛自由……”(17) 而即便是在旧题下写作,他也一定要把自由活泼的俚俗风貌表现出来。如《长干行》:“与郎同在长干住,自小相逢不相忌。郎骑竹马到侬家,当着爹娘与郎戏……”(18) 我们自然会想起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同题作品。可虽有这样的典范在先,沈周仍要顺着自己最为熟悉的当代语言习惯写来,不求形式风格之典雅,但求情感不受羁勒地铺写发挥。与之类似的情爱题材写作,在沈周诗集中着实还有不少。像《西湖竹枝词》、《箱奁》、《春思二首》、《并蒂莲》等等,其任兴缘情、无复依傍的写法,均是与上举这首作品颇为相近的。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沈周的诗歌创作中,活泼情感的自由表达,乃是重中之重。至于作品主题是否符合雅正标准,形式风格是否能上比先贤,他似乎并不想用心考虑(19)。这里自然流露出的,正是漫兴精神。当然,对这种创作观颇有意见的,也大有人在。王世贞就尖酸地讽刺沈诗“如老农老圃,无非实际,但多俚辞”(20)。这便是以他重格调的诗歌观念为裁断尺度,嫌沈周在漫兴指引下的写法太过随意、缺乏提炼、不讲高古了。王世贞的评判是否合理,此暂不论。不管怎样,在认定沈周诗歌创作观念以漫兴精神为主要特征这一事实上,他与文徵明可谓貌离而神合。
二
沈周的漫兴精神,在苏州诗坛的其他主要成员处,有着普遍的体现。他的好友杨循吉写诗就以随兴而发、不计工拙为特征,所以钱钟书觉得其作风已隐开公安派(21)。而在《朱先生诗序》中,杨循吉曾明白地阐述过自己的创作观:
予观诗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能直吐胸怀,实叙景象,读之可以论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斯定为好诗……大抵景物不穷,人事随变,位置迁易,在在成状,古人岂能道尽不复置语?清篇新句,目中竞列,特患吟哦不到耳。(22)
这种观点,肯定的是创作内容的独立自主、表现方式的自由不羁。在他看来,格律体裁这类形式因素,对诗歌创作成功与否根本起不了支配作用。观其终极指向,虽无漫兴之名,内里却实含漫兴之要义。与此相近,曾学诗于沈周的都穆(23),也在其三首论诗绝句中清晰表现出这类观念:“学诗浑似学参禅,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学诗浑似学参禅,笔下随人世岂传。好句眼前吟不尽,痴人犹自管窥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语要惊人不在联。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24) 这三首绝句,乃仿照北宋吴可以禅喻诗的名作《学诗诗》所写。不过二者内蕴却不尽相同。吴可作品,或揭示学诗当经历一个由长期修养而入超然无碍境地的过程,或标“圆成”为诗的极境。而都穆诗则不然。“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呕心并剔肺”云云,恰好赞美的是即景会心式写作,否定的是“渐修”的必要。而他虽无反对“圆成”的意思,却特别强调“语要惊人不在联”、“但写真情并实境”——如果这样的话,是否“圆成”,即是否在审美特性上无可挑剔,反倒不是关键了。与此相近,平时就如沈周般雅好白、陆诗风、且不重“格律气骨”的文徵明(25),也时常会写出“吟怀清兴斜阳里,不待推敲诗自成”(26) 一类诗句。这似能说明,在他的脑海里,至少存在着对“漫兴成诗”的一种情境想象。而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唐寅。他并没有多少直言创作观念的文字流传于世。不过,其诗歌创作本身,恰好在客观上体现出典型的漫兴精神。学界久已认为,漫浪不羁,是唐寅诗歌的典型气质。整体上看,比之沈周,唐寅诗语言的活泼通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主要作品既能尽情表现审美的愉悦,又能痛快地宣泄失意后的颓丧;既可以毫不掩饰地袒露声色之好,又可以不留情面地讽刺世态炎凉。他的败笔,源自这种无所顾忌的风尚;可是若没有这种风尚,他的诗歌就不会如此具有个性,令人不管爱之憎之,均一读难忘。可以说,从唐寅处,读者当体会得到漫兴为诗可能达到的情感强度。
然而我们的探讨远不能到此为止。因为苏州诗坛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向来被认定为复古派中人。他们就是桑悦和祝允明(27)。这种判断是否恰当?细读文献,不难发觉,这二人的创作观到底如何,其实仍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
首先来看桑悦。的确,他曾冠冕堂皇地大谈以《诗经》为终极准则、以汉魏诗为“亚经典”的价值判断方式(28)。单从这一点讲,他当然与复古派如出一辙。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应该注意的是,判断一位明代诗人是否属于所谓复古派,并不能仅凭其片言只语下结论。我们似乎更应留意:这类言辞在该诗人的文学思想中,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该诗人的相应创作,是否与其理论相互呼应?而从这两点出发,我们或许会对桑悦的诗歌精神做出更加准确的解释。
众所周知,桑悦乃是成化、弘治间吴中傲诞之风的代表人物。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喜欢用夸张的方式发表言论,以期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同样是论诗,他还讲过这样的话:
吾诗根于太极,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峙之,水以流之……散之则同元气流行,收之于心,发之于言,被之管弦,则可以感天地,动鬼神。(29)
上述议论中,不见一丝学古的动机,如此自夸自耀,亦属古来罕有。难怪正统文人朱彝尊要喝骂其为“大而夸狂也,几于悖矣”(30)。而事实同样证明,说出“吾诗根于太极”的桑悦,并不愿意用经典范式束缚自己的创作。他的“文章同元气,随物能赋形,变化莫可测,刘累难持衡”(31) 等诗句,便多少反映了这种心理。而其《和古人诗》的小引,一样颇为耐人寻味:
水部正郎傅曰川寄来二苏和陶诗,玩味久之。古人云:“我为尔,固不能;尔为我,亦敝矣。”毕竟陶诗自是陶诗,苏诗自是苏诗,亦两不能相为者。闲中戏和其杂诗十二首,不知有陶风味否?恐亦未免为桑诗也。(32)
短短几句话,其实讲的是“诗歌应自具面目”这一道理。从“恐亦未免为桑诗”一句中,我们更能见出,即便是在声名显赫的先贤面前,他仍是相当自信的。那么,他所谓桑诗,特征何在?五言古诗《感怀》五十四首,堪称桑悦的代表作。我们可选二首为例:
异域有海水,一饮人皆狂。举世何为者,役役日夜忙?何时骑元气,瑶池览秋光?饥餐白鹄血,渴饮蟠桃浆。
大家有广厦,巍巍切云霄。梁栋飞浮蚁,风雨时飘摇。平原土肉厚,甘露春如膏。松榆郁成林,中有百尺蕉。(33)
以五古组诗写心境,似乎是在追踪阮籍传统。但从上引诗篇来看,我们丝毫感觉不出其与古朴浑融的汉魏诗歌有何关联。无论立意还是遣词,它们均不以典雅为尺度,更谈不上阮籍式的“言在耳目之内,情系八荒之表”。一言以蔽之,它们不过是桑悦兀傲狂放个性的任意抒发、直白表露。这种写法,在他的绝句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翻看这类作品,诸如“东市撑船过西市,不知撞破几烟楼”,“太阳略垂照,死鳞弄光辉”一类表达,触目皆是(34)。而即便是在律诗中,他也会时时写出这样的句子:“端的乘槎去,荒唐秉烛游。”(35) “壁立万仞坡,登登路无穷,足虽踏实地,身已凌太空。”(36) 可见他对格调的轻视,至少不在沈周等之下。桑悦的创作特征,从他人的评论中也可见一斑。如王世贞就觉得,桑悦“诗如洛阳博徒,家无儋石,一掷百万,又如灌将军骂坐,虽复伉健,终鲜致语。”(37) 不难想见,在这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眼里,桑诗粗豪率意、了无韵度,其人是根本没有资格被列入复古派名单的。
那么,祝允明的情况又如何呢?无可否认,他的诗歌辨体思想,为沈周等人所不具备,这正体现出他梳理传统的自觉性。而他排斥宋诗审美传统,也容易使人将其视作复古派的同道(38)。可是,祝允明同样是一位“喜流动,便舒放”(39) 的才子。在谈到创作时,他也时时表露出对不受约束的自然状态的向往,对抒写真实情感的渴求:“欲务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偎人脚汗而不能自得。”(40) “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41) 能发表如此议论者,其精神旨归恐怕仍是与沈周等有契合之处的。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也曾大谈“辨体”,但他却似乎并没有以其指导创作的意图——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与复古派异趋。顾璘在《国宝新编》中谈到他读祝氏作品的感受:“祝子傲睨冠绅,游戏文囿,蓄之海汇,发也云蒸。”(42) 一向对苏州诗界颇有微辞的王世贞,则如此评论祝允明的诗歌:“祝希哲如盲贾人张肆,颇有珍玩,位置总杂不堪。”(43) 显然,顾璘、王世贞都觉得,祝氏作品体现出一种纵横施展的文才。不同之处在于,顾璘由衷赞美这种才华;而王世贞则觉得这种才华没有得到恰当的规范。这些评价,多少触及到祝允明诗歌创作的本质特点。今日通观其诗歌作品,便可发现,它们呈现出多元化审美特征,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样态,确实没有明确的师法对象与准则,而惟以情感表达需要为重。有些作品,他写得短小活泼、饶有情趣,像常被后人引用的《首夏山中行吟》:“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44) 而像《述行言情》五十首这样的诗篇,就显得典重、沉郁。姑举其中一例:“六极兼弱贫,百罹萃凶孤。素薄综物怀,坐为鄙人图。仓箱既凉匮,米盐务锱铢。自持绮桐姿,埋沈向泥涂。”(45) 有些作品,他写得极为绮艳。请看《吴趋》:“阊阖红楼起,皋桥绿水迥。绮罗摇日丽,车马逐云来……”(46) 至于近似沈周俚俗之风者,当然不占少数。除了比较有名的《癸丑腊月二十一日立春口号》十五首等,我们还可找到不少其他例证。如:“我侬贪花已特甚,你侬贪花又过之。无明彻夜恣淋漉,教他红绿尽离披。明年花时再如此,定唤花王讼雨师。”(47) “一年数日固是促,一年一年年不休。便到百年年一度,欲是长荣非短筹……”(48)
总而言之,向来被今人划入复古派阵营的桑、祝二人,其实并不具有复古派的最基本特征。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在两个原则问题上的态度是很容易识别的。其一,在言论上,他们重视典范、梳理传统,但并未规定必须对其加以效法;而且时时强调自主表达情感、自由选用形式风格的合理性。换句话讲,复古,并没有构成他们理论的逻辑重心,而只是他们理论的一个侧面。其二,他们的确没有将其本就有限的复古言论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就这两点而言,他们与突出强调“格调”、且用不同范式严格规范各体诗歌写作的“前七子”一派可谓大相径庭,而与自己的同里师友们反倒非常接近。我们不妨这样评价:从本质上说,复古观固然是桑、祝二人诗学的组成部分,但它尚不足以吞没其与沈周等人相近的基本创作理念,也没有影响到其自由随意的实际创作方式。他们的创作观念,最多只是对漫兴精神的一种调节,而不是背离。
三
在以沈周为代表的苏州诗人群体中,漫兴,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创作观念。在作品题材上,他们无论是雅是俗,多提倡直接表达,缺乏刻意提炼主题的祈向;在形式风格上,他们不强求高古典丽,而是时常自然而然地把通俗的、当代化的言语习惯带入诗中。正因为此,他们的作品,便有不少在情感表达上呈开放状态,短于含蓄精警,长于真率自然;与此同时,也时时流露出情趣化的取向来。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苏州诗人的漫兴精神中,实潜藏着多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在观念和实践上以兴为本,自然是对诗歌抒情本质的认同。而漫兴,又格外强调的是一己之情不受任何拘束的抒发;这,既意味着在主题上可以畅所欲言,又意味着可以拥有不受外在典范限制的形式风格。所以,以漫兴为典型特征的创作观,实际上具有反典范化的意义指向,蕴藏着对诗歌创作以真为本、以个性展示为目的的追求。在以汉魏盛唐诗为写作范式的中国古典诗学中,“真”与“雅”,是一对内在的基本价值尺度。就这类古典诗学观念来说,完美的作品,理应是二者的和谐统一。而上述苏州诗人的漫兴精神,则体现出强化“真”而脱弃“雅”的倾向,从而也就具备了脱离古典诗学系统的内在可能性。在明代诗歌史的纵向流程中,这样的观念既是对前期台阁文学精神的突破,又表现出通向理论思考更激进、也更有深度的新时代的可能。当然,实事求是地讲,成熟的文学思潮,往往以鲜明、深刻的理论思考为标志。与日后的徐渭、李贽及公安派诸公相比,苏州诗人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与特征,似还缺乏深刻、透辟的理性提炼与理论总结;因而,其漫兴精神潜藏的诸多重要特征,便不易真正彰显出强大的思想力量,更不用说形成对古典诗学精神自觉而有力的挑战。但不管怎样,这种精神的“启下”特征,毕竟是显而易见的。在明代诗歌史的纵向流程中,以漫兴为创作观的苏州诗人群体,显然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环节。
除了上述“承上启下”的价值,苏州诗人漫兴精神的客观存在,同样为我们揭示出明代诗歌在横向的特定时段内多样共生、复线发展的事实。通过对其考察,今人有可能捕捉到明诗演变过程中某些被忽视的重要细节,从而对明诗流变的真实样态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以台阁体、复古派、性灵派间此消彼长式的单线演进模式描述明代诗史。这一思路落实到对成化至正德这一段“新变期”的研究,便容易得出以下结论:茶陵派与“前七子”乃是诗坛主轴,其他诗人,则或是其别调,或是价值有限、无庸细论。这种观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延续着明代复古派自己的判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胡应麟这段有名的总结:
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生,此老砥柱其间,故不易也。(49)
文学史诠释,难免从某一特定视角产生,也总会以特定价值观念为评判尺度。正因为这样,这种诠释往往既有其独到的优势,也有其限度。如果我们过分夸大这类优势而同时忽略其限度,恐怕就会失去多角度观照文学史的机会——在一元化思路引导下的读解,往往会遮蔽那些本来颇具研究价值的文学史现象,也可能妨碍我们向文学史事实的不断趋近。回到本文探讨的话题。上述以茶陵、七子为明前中期诗坛主轴的诠释方法,自然会引导相关考察集中于明代复古派,这当然有助于研究者细致把握其在“复古”或“新变”各方向上的意义。不过与此同时,有别于茶陵、七子的创作流派,往往会被“中、晚、宋、元诸调杂生”这类胡应麟式的判断简单地涵盖,很难得到应有的评价。而通过对苏州诗人漫兴精神的考察,我们发现,明代成化至正德间的诗坛上,并不仅仅有复古派的独唱,而是呈现出多声共鸣的局面。这一时段的诗歌活动,实具有多元共生、复线发展的特征。由此,我们自然也会看出,成化至正德这一明诗新变期的意义,恐怕就不仅在于塑成了日后影响甚巨的复古派,而更在于:它培育出多样化的诗歌美学流派,为明诗的进一步演化,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作为这多元共生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诗人及其漫兴精神,就更不能被我们一笔带过了。
注释:
① 沈周:《跋杨君谦所题拙画》,《石田先生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崇祯刻本。
② 杨伦《杜诗镜铨》引《杜臆》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③ 对于这一群体,学界亦有“苏州文苑”或“吴中派”等指称方式。本文专论其诗歌创作,故以“苏州诗人”称之。又,若非特别说明,此后本文“苏州诗人”均指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
④ 文徵明:《沈先生行状》,《文徵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4页。
⑤ 李佐贤:《书画鉴影》,《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386页。
⑥ 《石田诗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中华书局2003年影印本,第1489页。
⑦ 沈周:《石田先生诗钞》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崇祯刻本。
⑧ 按,收入此诗的《石田先生诗钞》卷八录沈周弘治九年至正德元年间作品。
⑨ 沈周:《石田先生诗钞》卷七。
⑩ 阮容春:《沈周题画诗辑录》,《沈周》,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11)(13)(14)(15) 沈周:《石田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沈周手稿本,第495页,第485页,第435页,第629页。
(12) 沈周:《石田先生诗钞》卷七。
(16) 沈周:《石田诗选》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8) 沈周:《石田稿》,第441页,第285页。
(19) 需要补充的是,从写作年代来看,上述特征实呈现于沈周一生各个时期。陈正宏《沈周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沈诗作年多有考辨,其结论能说明此问题。限于篇幅,此不细引。
(20)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33页。
(21)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明宣德间刘珏诗似竟陵,此“亦犹公安派诗之隐开于杨循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22) 杨循吉:《灯窗末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3) 都穆《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61页)言及这一事实,可参看。
(24) 都穆:《南濠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1345页。
(25) 可参阅文嘉《先君行略》,《文徵明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2页。
(26) 文徵明:《题画》,《文徵明集》,第1104页。
(27) 这方面观点以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为代表。
(28) 桑悦相关观点集中于其《唐诗分类精选后序》(《思玄集》卷五)、《跋唐诗品汇》、《复王元勋秋官书》(俱见《思玄集》卷九)三文。
(29) 桑悦:《思玄集》卷二《庸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0)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31) 桑悦:《思玄集》卷一○《感怀》。
(32)(33)(34) 桑悦:《思玄集》卷一一,卷一○,卷一五。
(35) 桑悦:《思玄集》卷一三《对月》。
(36) 桑悦:《思玄集》卷一三《上云南坡》。
(37) 王世贞:《明诗评》卷四,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影印本,第83页。
(38) 参见拙文《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
(39) 《祝枝山与谢元和论诗书》,转引自陈麦青《祝允明年谱》,复旦大学1996年版,第85页。
(40) 祝允明:《答张天赋秀才书》,《祝氏集略》卷一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刻本。
(41) 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2) 转引自顾起纶《国雅品》,《历代诗话续编》,第1101页。
(43)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历代诗话续编》,第1033页。
(44)(45)(46) 祝允明:《祝氏集略》卷五,卷三,卷三。
(47)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四《嘲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同治刻本。
(48) 祝允明:《枝山文集》卷四《作拾花诗后意味衰促又作一首解之》。
(49)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