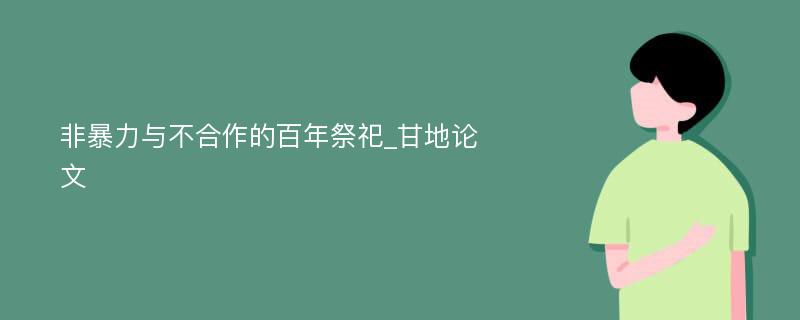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百年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暴力论文,不合作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亦可直译为“坚持真理”),亦即坚信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是甘地思想的支柱之一,产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甘地的世界观关键在于“非暴力”和“真理”。这两大要素是人类文明内在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非暴力进程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悠长历史中并不多见,可是非暴力信条却描绘了文明进程的新图景,而且非暴力在为家庭、个人认同、各种模式的集体生存构建价值观念方面,在为不同阶级及其社会范畴——诸如种族、种姓、部落、社群、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价值观念方面,乃至在为像沃勒斯坦学说中所列举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构建价值观念方面,作用几乎无所不在。不应当只从字面意义将“非暴力”理解为一种弃绝物质暴力的信条或态度。同样,“追求真理之旅”是一种有力的实验性的操练,亦即一种不断进行探索和实验的操练,以期为社会和文明及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找到一种恰当的现实模式。甘地对于病态世界的诊断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术语。这种诊断所依傍的就是这两个神奇的语词。必须全面领会这两个语词,而不能仅从牛津辞典里查找它们的含意。建立这种不容轻视的“世界观”,需要不懈地诉诸理智和实践。从这层意义上说,甘地是一位实验者,并且是一位十分大胆的实验者。他不仅决心获胜,而且准备面对失败;他从未停止过极为艰辛的进军几乎难以登上的真理之巅的旅程。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他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社会,以防止充斥着剥削、侵略、残酷竞争、异化和卑下到令人痛心的生活的世界永久存在。
同样沿着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陡峭山脊攀登的马克思,以较为世俗而深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语汇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国家机器将会消亡,主张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从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实质上源于社会主义关于人的概念。埃里希·弗罗姆在其颇具影响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不管人们的收入是否平等,也不管他们是否丰衣足食,而将个人组成团体并使之像机器一样自动运转的社会。”①他又进一步援引马克思的话:“即使作为一个抽象的‘资本家’的国家是雇主,即使‘全部社会资本都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家公司的手中’,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保罗·蒂利希所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一项针对社会现实中爱心毁灭的抵抗运动’”。②
当我们纵观主宰19世纪的思想进程,从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大卫·索罗1849年的《抵制文官政府》,从罗斯金1860年的《时至末日》到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再到甘地1909年的《印度自治》,似乎有一种明显的观点和思虑趋于集中的现象。
“非暴力不合作”是甘地创立的一种抗争手段,其内涵在甘地生前及甘地于1848年遇刺身亡之后,在全世界几经变迁。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精神力量的运用”、“真理领域永恒性的实践”。在与一个由资本的霸权力量所诱发的不公正的政府、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极为僵化的社会体系对抗之时,这种意义就彰显出来。在一份有关旁遮普动乱的国大党报告(《圣雄甘地全集》第17卷第151页至第158页)里,甘地在论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时写道:“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坚持真理,也就是真理的力量。我也称之为爱的力量。”他又进一步阐释:“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学说只是将管理家庭生活的法则延伸到政治领域。家庭的纠纷与分歧,通常是依从爱的法则而解决的。”在解释爱的法则之时,甘地指出:“爱的法则就是真理的法则。没有真理,就没有爱;没有真理之时,也许仍会对祖国怀抱感情,对他人的伤痛生出恻隐之心;仍会有年轻男子对于姑娘的迷恋;仍会有无知的父母对子女过度的和盲目的溺爱。真正的爱是超越所有动物本能的,是绝不偏私的。所以,‘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犹如一枚硬币,你在正面看到爱,而在反面看到真理。”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在甘地奋起反抗南非殖民政体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作为南非人口组成部分的印度人,大多是小商人或从印度前来的契约佣工。由英国人和布尔人组成的白人统治阶级日渐注意到这些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勤劳而俭朴的印度人。纳塔尔省的曾引入成千上万的契约劳工——半奴隶——在糖料种植园和矿场中劳作的欧洲人,无法容忍自由的印度裔商贩和农民与他们为伍,而在布尔战争之后,德兰士瓦的欧洲人则毫无根据地杜撰了印度人在侵入南非的妖言。③
为了骚扰印度移民,南非政府处心积虑地颁布了一项规定,强制所有八岁以上的印度男子、妇女和儿童登记,而且要求他们亲自登记并携带身份证。如此行事旨在羞辱和打击受过教育的印度人。1906年9月11日,为了抗议这项歧视性措施,一场集会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这场集会旨在抗议《亚洲人注册法令》。该法令是歧视性的,除了强加给印度移民的贸易限制之外,亦使他们处于无选举权的境地。
正是在这场召开于帝国剧院的集会上,甘地设想斗争必须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当时他的想法依然是模糊的,嗣后方才渐趋明朗。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制定出一种抵抗战略,即为了推进事业,人们必须忍辱负重,承受一切苦难。他断言:“宁死也不屈从于该项律法。即令不太可能的情况发生——其他人都逃散而只剩下我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无论其他人做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誓言,即令面对死亡。”④
起初,人们用“消极抵抗”来描述这种新的抵抗原则。然而,甘地认为这一术语并不足以表述他所创立的斗争模式。“消极抵抗”一词是随着妇女选举权运动而时行起来的,而且那场运动未能免除语言和肉体暴力。正在以其专栏使斗争大众化的《印度舆论》向读者征集这种新型运动的名称。“Sadagraha”这个意味着坚定不移和良好行为的词给予甘地深刻印象,不过他还是把它修改成了“Satyagraha”,即“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一个实验性的和演变中的概念,其中“实践中的非暴力”和“对真理的信念”是两个不变的特点,而其余内涵则可变化和予以更改。甘地早期传记特别是其南非时代传记的作家之一多克先生,曾在1908年向甘地问及“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产生情况。甘地答道:“我记得小时候在学校学过一首古吉拉特语诗歌,其中一节让我难以忘怀。它的大意是,‘如果有人给你一杯水,而你还报他一杯水,这不算什么。真正的美在于以善报恶。’那一节诗对于当时还是幼童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于是尝试付诸实践。我接着想到了‘登山宝训’。”⑤甘地的第一个传记作家约瑟夫·多克在其《甘地传》一书中以下面的词语描述这次会晤:“但是,您肯定首先想到的是《薄伽梵歌》吧?”我问道。“并非如此,”他回答说:“我当然相当熟悉梵语的《薄伽梵歌》,可我没有将它的教义用于那一特殊的研究之中。真正使我清醒认识到消极抵抗的正确性和价值的是《新约全书》。当我在‘登山宝训’中的有关章节读到,‘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以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之时,我简直欣喜若狂,我发现自己的见解在无意之间得到印证。《薄伽梵歌》深化了这种印象,而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⑥赋予它永恒的形式。”
很明显,至少在初期阶段,大多数人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暴力”的,因为人民手无寸铁,而面对的却是各种强有力的机构,如政府、帝国主义、专制政治、君主政体、军事体制,它们是由独裁者经营的,有时甚至是由所谓“民众”管理的。在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情形一直如此。在所有世代,人们的反抗往往都受到武力的镇压、重创和抑止。人民对那些强有力机构的抗议运动自然采取了“非暴力”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些连续不断的运动一直没有任何具体的理论,也没有固定的方法。通常,这些不对等的冲突均以人民的失败告终,但这种运动归根结底可以通过不同的持续的影响留下一些印痕,从而能够逐渐在道德层面上使体制发生变化。主要的宗教运动和精神运动有时也会采取本质上属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范畴的形式。一个最杰出的范例就是耶稣基督的人生以及他在面对酷刑时的至高无上的牺牲精神。在甘地的一生中,“登山宝训”在他的思想上始终占据至高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佛陀也曾领导过一场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式的运动,并以创立一种主张非暴力的宗教而告终。
数世纪以来,一长列人民运动和宗教社会运动,都带有非暴力斗争模式的印记。这些运动大多是自发的,零星的,表达了人民深重的怨愤和痛苦,而这些不幸的、无辜的而且手无寸铁的民众,却要面对从实行高压政策的政府机构到各种专制独裁组织等强大对手。所以,这些对抗的结果要么是抵抗运动屈服,要么是导致民众逃亡和大规模迁徙,要么就是人们针对新形势做出新调整。
甘地为这种历史上无所不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发出崇高的道德的呼声并使之具备符合道德的面貌。他赋予这种自发产生的抵抗形式一种伦理的和道德的色彩,并且建立起在面对巨大困难之时都能不屈不挠坚信真理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策略。事实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在已知的人类历史上,人们抵抗形形色色的顽固不化的邪恶、不公和剥削等强大势力,同时依靠人文范式,在伦理的和道德的层面,单枪匹马或集体行动,与社会不公进行斗争,而作为一种并不明晰的过程,消极抵抗始终持续存在于这一历史之中。
我们也许无法查证历史上的所有这些为真理而斗争的伟大运动,因为其中大多数运动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充满了借助真理亦即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勇敢的合乎道德的抗争。甘地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界定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时机,甘地强调过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选出一些圣雄在其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实验时期中下的各种定义,其措辞据各个时期需要的侧重点而有所调整。圣雄的这些表述,反映了在斗争的不同时期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不同应用与解释。因此,作为一种由道德范畴所孕育出来的工具,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在历史的不同阶段都在一定程度上无所不在。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与忘我精神不可共存。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就是自我牺牲。”(《印度舆论》,1908年7月4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意味着,凡是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均应至死不予放弃,应不遗余力地坚持真理并为之承受苦难。不要烦扰任何人,因为烦扰别人有违真理。承受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就是真正的胜利。”(《印度舆论》,1908年9月26日)
“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我们不断地向真理迈进,直至我们吸收真理,而我们的自责将因而减轻。”(《印度舆论》,1908年10月10日)
“坦率地说,如果不是以恶制恶而是耐心地与之抗争,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就不会出现威胁、暴力和伤害一类问题。”(《纳塔尔信使报》1909年1月6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不能与贪婪共存。”(《印度舆论》,1909年12月18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基础只是自我牺牲和苦行热情。”(《印度舆论》,1909年12月13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一柄锋利的多刃剑。它可以被用于任何情况。两个相互对立的人如果都使用这柄剑,双方最终都会愉快。它无须流血而卓有成效。它不会生锈,也无人能将它偷走。”(《印度舆论》,1909年12月18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基础就是真理,只有那些不信奉流血的人才可以有效地利用它。”(《印度舆论》,1911年10月7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从不考虑胜败。它永远只会胜利。依靠体力摔跤会有输赢,而较为强悍的一方每每会胜出。”(《印度舆论》,1914年2月4日)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并非弱者的武器。比之存在输赢的体育竞赛,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印度舆论》,1914年7月15日)
事实上,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抗争辞典里的一种新武器,为抵抗行为的构建加上了伦理道德的色彩。甘地坚信,只有正确的手段才能使人达到正确的目的。因此,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道德武器的变化,将导致一种在道德上适宜并具有持久影响的变化,而且会将人类文明的日常事务提升至空前的高度。甘地的杰出弟子维诺巴·巴维,亦即甘地主义建设运动的领袖之一,曾在解释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实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将它与消极抵抗区分开来:
1.消极抵抗常常是武装抵抗的先兆,而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则排除武装抵抗。
2.消极抵抗不能被用于自己的亲友,而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则甚至可以用于自己所爱之人。
3.消极抵抗背后的意图在于困扰对手,而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则排除任何此类想法。⑦
甘地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这一工具实验性地用于帮助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对抗复杂的帝国主义机器。帝国主义将帝国资本和帝国政府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孪生的集中的暴力和帝国资本的渊薮之中,帝国资本是一种剥削性质的经济工具,代表政府暴力和资本暴力。甘地即使用符合伦理道德的抵抗武器与这种暴力进行斗争。他对抗帝国主义的庞大机器的武器就是非暴力和真理。他在南非和印度的实验空间中雕琢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这种新的武器,并在这一进程中为人类贡献了一种全新性质的斗争手段——非暴力不合作主义。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历史长河中抵抗和变革的最为发达的文明的武器。曾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为弱者和失败者所使用的武器,突然之间成为足以创造更高的道德价值观念从而导致更高文明的具有潜力的工具。正是甘地在1893年至1948年之间所作的不懈斗争,才使得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理念成为一种在道德层面上抵抗世界帝国主义的单一强大势力的行之有效的武器。
从战略上看,改革和斗争的其他手段也许更为明快有力,但应当承认的是,它们都无法使人们到达具有更高价值和建立公民世界体系的最终目标。这就使得这些手段难以避免自己的固有弱点。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战略性斗争进程更贴近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基调,而缺乏伦理道德的色彩,才导致今天的诸多问题。这也同样适用于变革之学。在变革中,走捷径和权宜的非科学的调整,都可能导致倒退而非前进。1917年之后开启的整个新的世界体系悲剧性的崩溃,即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那一新的世界体系是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建立的,并伴有世界史册上记载的变革事业所从未采用过的大量的科学的精确性。不言而喻,1917年的革命是一种新文明的先兆,但它不久即受制于长期影响社会的诸多弊端。革命性的变革是世界的财富,这些变革的手段也是世界的财富。但是,如果变革的进程和手段无法适用于具体的情况,那么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后殖民和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挫折,并非内在于体系工具的缺陷,而是在于既定参照情况与自己的基本情况不符,从而导致问题的出现。
就“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而言,其实验先是集中于印度的反殖民运动,而在早期阶段则集中于发生在南非的与印度居民相关的问题上,是由圣雄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斗争手段可以成为基层民众运动的潜在武器,成为表达人们的压力、人们的抵抗、人们的意识和警觉的手段。反殖民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层面的尽可能广泛的联合阵线和保护阵线。只有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这种多维手段,具有尽可能深入的渗透作用的反殖民运动才会发生,民族动员才会实现。
马克思主义和甘地主义都把国家看作一种行使集中的暴力和高压统治的机器。一个阶级或一些阶级为了共同利益并使之合法化而用暴力反对另一阶级或另外一些阶级,从而使得国家政权成为一种暴力工具。那么,什么力量可以抵消国家内部畸形累积的暴力呢?这种抵消力量就是葛兰西所理解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⑧因此,非暴力不合作可以充当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调和力量。显然,公民社会的唯一武器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由于公民社会并不拥有强制力量,所以它自然倾向于使用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手段。所以,如果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这一手段缺位,民主就可能消失,因为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言,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科学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规范的进行道德伦理实践和起警戒作用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在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国家机器会消亡,而甘地则主张从基层公民社会组织运动开始,从而最终取代对国家机器的需要。这是一种逆向颠倒的过程。
从个人层面上看,在基督和佛陀的人生旅途中,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主要出现在宗教、精神和社会改造的领域之中,而且更多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甘地将其整个运动化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体活动,使之或多或少是“以群众为中心的”,以至前现代的不识字的村民也愿意分享其精神,从而低层文化与高层文化之间的差别得以缩小。一旦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获得群众参与的模式,乌托邦思想就突然开始成为可能。集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经验在印度过去的历史上并不罕见。例如,甘地的早期传记作家多克先生在一段引证赫伯主教的文字中提到,在19世纪初期,印度北部城市贝拿勒斯的居民由于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其强征高额房产税而大批离开该城。那些市民无意犯上作乱,而是决定集体离开自己的住房,到城外的大片旷野静坐。⑨此事表明,印度人是如何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产生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
印度国民大会党这一重要的自由讲坛,最初是一个由律师和持不同意见的精英所组成的团体,但除了提拉克之类少数好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还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盲目的印度教沙文主义,它主要是一个请愿组织。甘地事实上拯救了这个组织,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工具,并促成了一种得到有机发展的世界观。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改造国家的武器,也成为一种平稳运转的政治管理机器;它将导致高尚的文明,而不逢迎一定的民族国家和政治经济学。它只是在开始影响印度的自由斗争之后,才变得卓有成效。在甘地出现之前,整个运动是零星的,自发的,而且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全国计划而多少显得有些散乱。
对于甘地来说,让印度国大党接受“非暴力不合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并不容易,相反还非常艰难。这项任务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甘地早期在比哈尔的查姆帕兰和古吉拉特的凯达为开展农民运动而进行的尝试。甘地后来在一种“以乡村为中心”的运动中使农民运动发生变化,使之从以阶级为基础的农民动员转向公民社会动员,因而使整个村庄成为一个运动单位,而不再仅局限于农民本身。在古吉拉特的阿默达巴德市,他尝试以一种新型调停方式解决劳资争议,而在凯达,他又返回乡村
和农民的生活范围。
甘地接过印度最大的政治论坛——国大党,从而有了优势。此前,国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少实际经验的城市知识分子的党,由具有很强的立法能力的城市律师所主宰。甘地率领国大党走向村庄、农民和工人,而这并非一种常规的阶级政治演练。正是通过带有道德伦理呼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甘地得以为古吉拉特省艾哈迈达巴德市的棉纺工人们解决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同样,他奔走于比哈尔省查姆帕兰县被英国种植园主以强制条件予以束缚的种植靛蓝的农民之中,从而开始了他与乡村和农民终生不渝的密切联系。
尽管甘地成为国大党和印度独立斗争的最高领袖,但他依然由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教派分裂而忧心忡忡。殖民政府为回应独立斗争的要求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导致代议制机构的初步形成,而这一机构却始终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不应有的界线形影相随。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加重,最终在英帝国的一手策划下导致巴基斯坦的成立。英帝国圆滑地充分利用了教派自治的污浊气氛,不时导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彼此之间的敌意,从而给予教派分裂势力操控印度国是的机会。
圣雄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代议制政体议会形式中的激烈竞争而产生的贪婪腐败之风的增长。有关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犬儒主义在议会道路的坚信者之中广泛传播。其中许多人认为,通过参与殖民地的代表会议,他们可以自动加快赢得自由的步伐。其实,他们在当时只代表了10%的人口,而且主要是权势者、富人和上等阶层。甘地对此心怀疑虑;他更为信任群众的以非暴力不合作为手段的不服从和不合作运动。他希望大多数民众能受到新式的文明的斗争艺术的训练,而这一点在殖民地代议制体制之下几乎无从实现。
尽管甘地能够引领民众,但是除政治自由议程外,对于他提出的诸多问题,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就迫使甘地于1934年非常决绝地做出退出国大党的决定,并且从此再未重新加入该党。这一决定是在1934年于孟买召开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会议之后产生的。在那次会议上,甘地提出一份国大党章程修正案,要求国大党宣誓凭借“真诚的和非暴力的”手段获得自由,而不再采用当时国大党章程中规定的“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全印国大党委员会拒绝了圣雄的修正案,这就成了他作为国大党人的旅程的终结。⑩自那以后,他由于恪守自己所怀抱的理想,因此虽然可以依旧出面领导和提供意见,但他再未正式担任国大党领袖职务和获得党员身份。然而,他对民众的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以至国大党每当面临严重问题时总得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乃至让他指导方向。
我们应当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圣雄甘地退出国大党这一事件。真理和非暴力在他的心目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他的辞典里根本没有“捷径”一词。甘地确实做了准备,如果有必要,个人的非暴力不合作可以替代大众的非暴力不合作,直至民众充分掌握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要旨,而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这正是甘地强调只有真正领会非暴力不合作要旨的人才能开始践行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原因所在。
甘地随时准备在真理的召唤下修正错误,而这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在寻求真理过程中应当具备的一种品质。1933年,甘地曾经中止民众的抵抗运动,因为他发现人们并未完全遵从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战略和信条。甘地宣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一种“精神武器”,因而只能由像他本人一样的合格的人才能使用。“这种说法,出自一位政治运动领袖之口,是令人惊讶的。”(11)尼赫鲁对其导师不可思议的行为方式发表了如是评论。甘地从不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所以退出国大党,是因为他发现,大量领导者接受他的意见是出于忠诚,而非出于信服。
他退出国大党,从而让党内的其他成员得以自由行事。他是真理的追寻者,而且他准备为此而在曲折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他当然并不认为散兵游勇的力量大于整体的力量。他在1915年返回印度之后宣扬并提倡实践非暴力。在十五年之后,他看到那些声称追随他的人对他几乎毫无理解,因而深感痛心。他在中止公民不服从运动之后,恳求从事建设性工作。这些工作主要集中于废除贱民制度(12)、手纺运动(13)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团结问题(14)。他认为,建设性工作比频繁积极推动运动进程更适于以平静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精神训练和改造民众。归根结底,一切政治和对自由的要求,最终都是印度人民对国家自治的要求,以在印度人民发扬民主予以赞同的基础上,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国大党的许多领袖无法理解为何中止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也不明白为何强调建设性工作。国大党的一部分名列前茅的领导人难以理解建设性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足为奇的,那是一种为了深入动员民众并使他们做好参加独立斗争准备而做的铺路性质的工作。虽然甘地起初对国大党人在殖民政府立法机构的安排下工作的倾向感到不快,因为仅有10%的印度人口拥有选举权,但当他看到国大社会党形成印度国大党的核心之时却没有那么不快。他最亲密的弟子尼赫鲁是国大社会党人的无冕之王。尼赫鲁于1936年当选为国大党主席,并在该年国大党年会上宣布,社会主义是印度人民自治的唯一选择。他阐述道:“在我谈论社会主义之时,那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甘地并不反对国大党里的由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混合组成的社会主义者。他只是将他们称为“忙乱之人”,意指他们只是在玩弄理念,而从来不做实事。作为一名无与伦比的群众运动观察员,甘地于投身一项伟业之前在培训党和群众方面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监督员,而他非常厌恶空洞的政治辞藻和让标语口号凌驾于政治之上。
因此,如果他认为群众运动在偏离非暴力的基本信条,他就能够勇敢地做出毫不踌躇地退出运动的决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在设法解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问题以及导致巴基斯坦成立的印度分治问题。从穆斯林联盟于1946年8月16日号召采取直接行动以后,国家陷入了血腥的宗教骚乱之中。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得出结论,为了阻止以教派骚乱为形式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宗教暴力,它准备接受穆斯林联盟和印度殖民政府所构想的分治。事实上,从麦克唐纳在1932年公布裁定书之日即开始实行的殖民政府的方案,意在鼓励印度穆斯林分裂主义。圣雄甘地要求英国人离去,以让印度人决定自己的国家是否需要实行分治。他说:“当英国政权仍在印度起作用之时,我们无法清楚地思考。英国政权的功能不在于改变印度的版图。它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撤离印度。”(15)
穆斯林联盟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的号召损害了国家,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沉浸在一种持续的教派激情和放纵暴行的氛围之中。东孟加拉的气氛令人惊惧,甘地于是决定前往东孟加拉的村庄,特别是诺阿卡利县的村庄,而此时国大党的领袖们正在新德里就权力移交的细节进行谈判。他在离开之前声明:“我不能发现真理。互不信任太严重了。就我所知,我用以宣誓并在六十年来一直支撑我的真理和非暴力,(16)似乎未能显示我归在它们名下的特质。为了验证它们,同时也为了验证自己,我将前往斯里兰普尔村。”(17)
诺阿卡利县斯里兰普尔村的二百户印度教家庭,在骚乱之后只有三户留存下来。甘地将自己的随从人员分布到邻近的村庄。皮埃莱拉尔、苏希拉·纳亚尔、阿巴、卡努·甘地(Kanu Gandhi)和苏切塔·克里普拉尼(Sucheta Kriplani)每人入驻一个村庄。在斯里兰普尔村,甘地仅有的同伴是自己的速记员帕尔苏拉姆、自己的孟加拉语翻译尼尔马尔·库马尔·鲍斯教授以及马努·甘地。在随后的六周里,一个木床架白天充作他的办公桌,晚上则充作他的卧具。他的工作日延长至16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20个小时。他睡得少,吃得也少,自己铺床,自己补衣,自己烧饭,处理大量邮件,接待来访者,看望当地的穆斯林。数年以来,他被穆斯林联盟的报刊诽谤为头号敌人。现在,他让斯里兰普尔村的穆斯林们自己作判断。(18)
甘地的到来对东孟加拉的村民起了镇静剂的作用,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减轻了愤怒,也软化了民众的性情。他将和平问题从政治层面提升到人性层面。他呼吁道,无论未来的政治蓝图如何,坚守文明生活的标准均应成为所有政党的共同立场。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凌晨两点醒来。只有神的恩惠在支撑着我。我能够认识到,自己有严重的缺陷,因而成为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我的周遭漆黑一片。神何时才会引领我走出这样的黑暗,让我进入他的光明之中呢?”(19)
当天,他离开斯里兰普尔,开始逐村漫游。在昌迪普尔村,他丢弃凉鞋,如古代朝圣者一样赤足行走。他喜欢聆听的泰戈尔的一首歌,多少表达了他的极度痛苦。
独自前行吧,
如若人们对你的召唤无动于衷,那就独自前行吧,
如若人们心怀恐惧,在沉默中面壁掩饰自己。
唉,不幸的你呀,
敞开你的心胸,独自说出你的思想吧,
即使在穿越荒野时,众人转身将你抛下。(20)
正是深厚的人道主义,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创造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的热切愿望,构成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核心。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甘地一直深深地沉浸在这种实验之中。1948年1月30日,他遭到印度教狂热分子纳图拉姆·葛德斯的暗杀。葛德斯曾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印度教法西斯组织国民志愿团的训练,而且是印度教大会政治的参与者。其时,甘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各自的领袖于1948年1月18日在新德里保证并发誓保持教派和睦之后停止绝食尚不足12天。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抗争手段意味着新型文明建设的一种工具,是国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所无法复制的。新生的国家仍由曾浸染于殖民地文化的同样的旧官僚掌控,不可能改变其色彩。它是一个后殖民国家,但还不是一个亲民国家,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依然在引导着航船的方向。在十月革命之后,一种新的激进的配备了浸染于意识形态的新型人员的国家建立起来,随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革命接踵而来,直到这种革命后来又蔓延到古巴和越南,而这就是区别。独立之初的印度政府自身却仍然保留了旧的殖民体制的框架。随着制定共和国宪法、国家计划和新工业政策这类大型的急进化项目的完成,官僚政治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在较低的层面上,它依然完全未受影响。
甘地在晚年曾怀着建立一种非暴力和复兴国家的精神状态的明确愿望起草了一份计划,以在全国重新组织建设性工作者,为穷人和村民服务,从而创建一种有机发展的国家建设模式,而不是十分折衷地借用这里或那里的现存模式。他还指出,国大党在成功实现印度独立的目标之后即应解散自身,以组建“人民公仆联盟”(Lok Sevak Sangh),从而为改善亿万民众和农村的生活而工作。对于一个身为独立斗争运动最高领袖的人而言,这无疑是激进的一步。他不想只是将权力从英帝国政府转移到印度政府和领袖手中,而这一政权依旧如同帝国政府机关那样以同样方式行事。他主张“真正的自治”(Authentic Swaraj)(21)。他不赞成在自由印度将权力从帝国政府移交到一个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控制的政府手中。当自由印度的新宪法在1950年开始生效之时,他的诸多理念当然得到回响,虽然这部宪法尚有很多缺陷和滞后之处。
如果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得到采纳,从而成为官僚、人民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主导价值体系,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下,唯一可以想见的就是变化,而自治的目标就能实现。甘地知道,对于他的许多同仁而言,赞同这些价值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他在说“我欺骗自己,使自己相信人们恪守非暴力”之时,他是忧心如焚的。对甘地而言,非暴力比独立更重要,而印度人当时却背弃了非暴力。甘地悲伤地看到,一个被分裂的印度将在8月15日获得自由,而整个次大陆却在此时陷入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相互报复的血腥大屠杀之中,他们在盛怒发作之下相互施暴,已经失去理智。甘地宣告:“我不能参加8月15日的庆典。”(22)甘地表示,32年的工作以一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在为一个帝国的撤离和人民自治政权的诞生而于新德里举行盛大庆典的那天,既是末代印度总督亦是自由印度首任总督的蒙巴顿勋爵,在位于新德里总督府里的觐见厅(Durbar Hall)为新任命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持宣誓仪式。此时,甘地却呆在1500公里之外的一户穆斯林的房子里,在印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教派骚乱的场景下,闻着正在燃烧的屋舍中传来的血和烟的气息。他在试图消弭暴力与疯狂。正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力量使他来到这里并支撑着他,而他从未停止对真理和非暴力的坚持。就在他的所有同事都在德里忙于权力移交的令人目眩的仪式之时,他却身在一位试图传布明智之声的贫穷的穆斯林的废弃的茅舍里。甘地决心继续坚持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直至人生的最后一刻。
This is a Chinese version of a paper specially written for this journal by Prof.Dipak Malik,director of the Gandhian Institute of Studies at Rajghat,Varanasi,India.A centenary has elapsed since Mahatma Gandhi put forth his doctrine of Satyagraha in 1908.His ideas and experiment have exerte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both Ind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fate of Satyagraha in both depth and detail,and therefore is very helpful for Chinese readers to understand Gandhi's mind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enior Indian scholar.Ms.Hu Jing,a graduate student with the Department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Graduate school,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did the translation,and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revised and edited by Prof.Liu Jian,deputy editor-in-chief of this journal.
注释:
①Erich 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69),p.58.
②同上书,第59页。
③B.R.Nanda,Mahatma Gandhi:A Biography(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90.
④Louis Fischer,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90.
⑤Doke Joseph,M.K.Gandhi(Madras:G.A.Natesan and Co.,1909,p.88.
⑥Kantilal Shah ed.,Vinoba on Gandhi(Rajghat Varanasi:Sarva Seva Sangh Prakashan,1973),p.48.
⑦Kantilal Shah ed.,Vinoba on Gandhi(Rajghat Varanasi:Sarva Seva Sangh Prakashan,1973),p.48.
⑧安东尼奥·葛兰西,20世纪意大利主要理论家之一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他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一种手段,借以使社会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受国家强权和其他机构的干预。公民社会全然不依傍高压统治的工具,而宁愿利用社会基层合法化的而且获得巨大发展的共识。
⑨多克前引书,第132-133页。
⑩Acharya Rammurti,"Satyagraha,"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seminar in April 2008 at Khadigram,Jamui,Bihar,India,p.3.
(11)B.R.Nanda前引书,第364-365页。
(12)贱民制度是印度教种姓等级制度的一个严重缺陷。在这种制度之下,被称为“达利特”(Dalit)的最低社会阶层不允许与上层社会的印度教徒来往、接触或同席用餐。这曾是印度社会制度的一种祸害,有20%的人口被迫永远离群索居,住在村庄南面的聚居区,从而被剥夺了文明生活的所有设施。与这种制度的斗争即发轫于佛陀,经过中世纪,又一直延续至现代印度。甘地和贱民领袖B.R.安贝卡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国大党内的许多人并不像甘地那样对这一问题怀着痛切的感受,他因此中止了大众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从而发起反对这种歧视的运动。
(13)甘地倡导人人穿用自己纺织的土布。这是他反对从英国进口服装的著名策略。这一策略随后成为一种抵制帝国主义并打击其经济的新颖手段。
(14)印度在其所有历史阶段均有一种不同信仰和平共处和并列存在的强大传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在殖民统治引入以宗教集团的区分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时遭到扰动。甘地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对于同殖民主义斗争至关重要,但像国民志愿团和印度教大会一类印度教团体以及在M.A.真纳领导下的穆斯林联盟,都宣扬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存在为基础的两个民族理论。甘地、国大党以及革命者均弃绝这一理论。殖民政体利用这些歧见,挑动一个教派与另一教派争斗。教派政治在殖民政体的支持下从中出现。对甘地而言,这是他一生中遭遇的最大挑战。他的呼声被完全忽视,而且他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分裂一直感到悲伤,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精神从来不曾终结。在他遭到受训于国民志愿团的狂热的印度教政治活动分子纳图拉姆·葛德斯暗杀之前,他正在准备前往巴基斯坦,以为两个邻国之间的和平及建立友好关系发出呼吁。他甚至决定留居巴基斯坦,并为此而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请求。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裂的教派主义政治导致圣雄遇刺,并且它至今仍然绵延不绝,以致在1992年12月,国民志愿团组织的狂热民众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印度人民党一类政党,就利用这种形势而得以在印度秉政。
(15)B.R.Nanda前引书,第194页。
(16)同上书,第495页。甘地在这里用“Ahimsa”(不害)一词表示“非暴力”之意。
(17)同上书,第476页。
(18)同上书,第494页。
(19)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6),Vol.I,p.470.
(20)B.R.Nanda前引书,第496页。
(21)Swaraj意即自主,但它有双重含义,因而也指“自治以求自我改善”。甘地使用此词时总是包含这样的双重含义。
(22)Louis Fischer,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Grenada:Grenada Publishing,1982),p.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