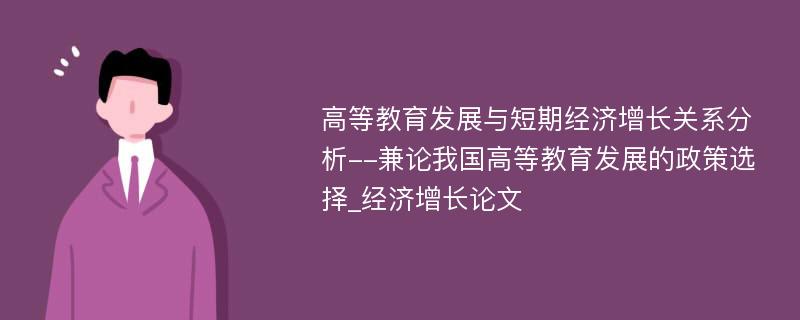
试析高等教育扩张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兼论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关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254;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2204(2006)02—0069—04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程度越高,以知识、技能、素质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本的含量越大,对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即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受教育者的人数和层次正相关。许多国家一定时期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199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企业和理论界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汽车、住宅等产业市场一直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产业。许多学者提出“发展教育,启动内需”、“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投资的热点”① 等政策主张。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扩张,1999年至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分别为156万、220万、260万、290万、340万,每年以30万~60万人的不等规模递增。② 高等教育能否成为短期经济增长的“推进器”?笔者结合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认为,高等教育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拟通过高等教育的扩张来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方法有待商榷。
一、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短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上一般把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萨缪尔森最早把纯粹公共物品定义为每个人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这种产品消费的减少的产品。这种产品具有两个特性:效用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私人产品则是指可以由消费者个人享受的,不产生外在效益的产品。另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它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可以将不付款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性,可以为社会共享。教育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教育的效益可以分为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教育产品受益的外在性主要表现在教育的社会效益上,同时,教育产品在消费上又具有排它性。教育机会是有限的,一些人消费意味就着另一些人将无法消费。
然而,教育从整体上讲是准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各层级教育是同质均匀分布的,实际上,各级各类教育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在受益外在性(社会收益)和排他性上表现各异。从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到高中、高等教育,它们在受益外在性方面逐渐减少,在消费的排他性方面则逐渐增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和教育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甚至层次越高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越少。[1] 劳动经济学中一般用教育的收益率来反映教育的回报,教育的收益率分为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其中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主要反映教育投资对个人所产生的回报,而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则是指教育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回报,如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成果来看,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随着教育阶段的上升而下降,即初等教育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则最低。③ 显然,从公共财政的投资排序来看,应当是优先和重点发展义务教育,进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其他非义务教育。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共同目标特征。而在中国,自“十五”规划中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后,高等教育实行跳跃式扩张,国家、社会、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高等教育投入,但高等教育投资仍显不足。而且,在国家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又挤占了义务教育的教育资源。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高等教育盲目扩张的后果是降低了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教育供给水平下降,最终有损于经济运行。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用这样一段话描述高等教育的作用:“对高等教育不能指望过多。它确实能促进机会的均等,但那也仅仅是很小程度上的。对经济发展而言,它能够对达到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它自身并不能导致GNP的增长。它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但它担负不起这种发展的责任;它不能拯救灵魂。它能有助于纯粹的学术,但它不能保证这些学术成果能为人类增添幸福。它能为评论社会行为提供机会,但它不能保证这种评论的有效性;它不能拯救世界。”④
二、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与短期经济增长
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投入产出分析表计算出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关的各部门的产出乘数及影响力系数。“产出乘数”反映某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量。高等教育扩大一定的规模将导致各有关部门的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若干个价值单位。将各有关部门增加的不同价值单位与其对应列的元素之和(产出乘数)对应相乘,其总和就是高等教育扩大一定规模时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力大小。“影响力系数”可以用来比较某部门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大小。该系数的分子反映的是某部门产品或劳务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价值单位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总产出规模的增量;而分母则反映各部门这一增量的平均值。因此,影响力系数是某部门对总产出规模的影响与其它各部门影响的平均水平的比较结果。影响力系数若大于1,表示该部门高于其它各部门的平均影响水平,若小于1,则表明低于平均影响水平。换言之,影响力系数反映了各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拉动作用的大小。[2] 根据北京大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短期经济增长作用》课题组研究表明,教育的产出乘数不仅小于汽车、住房等消费的产出乘数,而且小于众多行业产出乘数的平均值,其影响力系数的排序也十分靠后,通过高等教育投资扩张这条途径来拉动短期经济的增长显然不合适。
同时,中国在教育领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过度消费。所谓过度消费,是指居民对教育的投资超过家庭消费结构的正常比例,甚至超过其实际的支付能力,这种现象在中国广大农村比比皆是。当有限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大部分投入到教育消费时,势必要挤占其它项目的消费,住房、汽车等原本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消费被教育消费这种形式所替代,而教育消费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远不及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所带动的乘数效应。
1998年高等教育扩招前夕,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等人认为,240亿的高等教育投入将会拉动近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所作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40亿元的教育投入将导致国民经济总产出的增量仅为567.2亿元。⑤ 1999年普通高校招生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招生计划增幅达44.4%,以全国平均学费标准为3900元/生/年计,每增加一个学生所带来的总产出为14954元,再乘以扩招新增的48万学生,此次扩招带来的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仅为71.78亿元。⑥
三、过度教育与短期经济增长
过度教育,是指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而造成教育的过量。就个人而言,教育投资收益的边际收益率为零,就是适度教育与过度教育的临界点。这个属于过度教育的理论判据。过度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主要有以下几种:(1)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教育和受教育层次较低者的失业率。(2)高才低用,教育层次较高者从事原先通常由层次较低者承担的工作。(3)与接受过同一教育水平的老毕业生相比,现今的毕业生实际收入下降。过度教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无论是受教育者的个人收益率还是社会收益率都将趋于零或负值,也就是说,教育投资成本不能有效地收回。
教育供给与需求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基本矛盾,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度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教育供给大于实际需求,将会导致接受过教育的人失业,这就是过度教育对就业产生的消极效应。具体说,是指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超出了自身工作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所受的教育超出社会的吸纳能力而造成的知识失业现象。一定时期内,社会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需求是有限的。过度教育的短期和直接效应是抑制就业,长期效应是导致生产水平下降。教育程度高于工作需求的人才,对工作容易产生不满,出现不利于工作的较差的表现。研究表明:在过度教育的情形下,虽然加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就业人士的教育水平上升,但生产力增长水平却有下降的趋势。工作场所生产力研究也发现,工作的表现与教育水平没有直接的正向关系。同时过度教育还会导致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处于自愿性失业状态,长此以往,社会矛盾会逐渐凸显,社会的稳定性会越来越差,影响经济的健康运行。[3]
长久以来,许多人对高等教育扩张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厚望,通过上述分析,中国在运用教育的经济政策时需注意以下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需考虑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高校超常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会使得国力无法承担,国家财政教育拨款缺口较大。一味地追求规模,结果是高校办学条件日益恶化,以牺牲教育质量换取数量,走的是一条“高投入、低产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另外,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部分超过了其实际承受能力,成为许多家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们牺牲了基本的生活质量来供养子女上大学,接受也许将来并不能收回成本的高等教育。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在扩张需求和财政能力制约的两难中,必须反思其发展速度。世界历史上发达国家高校在校生增长率与GDP增长的指数都高度相关,近几年中国GDP年增长率平均在8%~9%之间,而高校实际增长速度早已超过10%。如果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想走出一条“超常规发展的路子”,实现“跨越式发展”,最后可能会造成整个教育资源的浪费,对高等教育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二)高等教育的扩张不仅要考虑“增长”,更要考虑“发展”
按照萨缪尔森对经济增长的定义,“经济增长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指,一个国家潜在的国民产量,或者,潜在的实际GDP的扩展”[4]。而对“发展”的解说,缪尔达尔有一个经济学界较为接受的说法,认为“发展是整个社会制度向上的运动。换言之,这不仅涉及到生产、产品的分配和生产方式,也涉及到生活水平、制度、观念和政策”[5]。可以看出,这两个概念有根本的不同。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宏观经济的内在作用应着眼于发展。发展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不应在于数量的扩张,而应在于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高和制度的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短缺不是单纯数量性短缺,而是结构性短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制度上的短缺。所以急需营建连接教育和市场的机制,扩大高校在市场中的活动空间,增强高校在运营过程中的自主权、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标准等,为高等教育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高等教育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不仅仅是一味追求“增长”。
(三)高等教育的扩张要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
按照马丁·特罗的看法,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是一个目标理论,而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对历史和现实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总结。实际上,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依赖于教育民主化意识的觉醒,也依赖于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和结构。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的发展而稍为超前,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这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6] 另外,因为教育的周期较长,培养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超前量。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1998年以前,高等教育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1999年以后又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一方面导致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冲击了劳动力市场。所以,当前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
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资源约束经济建设最为严峻的时期。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提倡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节约型社会要求正确认识高等教育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高等教育现有的发展方式,走出一条内涵式扩张道路,合理优化配置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实现高等教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5—06—17
注释:
① 《广西师范学院院长认为高教将成未来消费热点》,《人民日报》(网络版,http://unn.people.com.cn)2002年9月25日。
② 摘自相应年份《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③ 摘自中国教育行业分析报告(2004年度报告)。
④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The Purpos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76—77页。
⑤⑥ 北京大学课题组:《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与预期经济增长》, 《科学时报》1998年第8期。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大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